反思“本土性”:重审中国早期摄影史料
董丽慧
一、问题:追寻“本土”之眼
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中国门户的逐渐敞开,照相业和首批照相馆在19世纪中期前后落地中国,成为摄影术进入中国的一个主要契机,其中,早期经营者主要是来华寻找商机的外国人。被称为“首位来华专业摄影师”的美国人乔治·韦斯特(George West,1825~1859),在19世纪40年代入华之前,也曾于华盛顿开设照相馆,这是华盛顿最早的照相馆之一。1844年,韦斯特跟随美国首个访华外交使团顾圣(Caleb Cushing, 1800~1879)抵达澳门,在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后,韦斯特并未随顾圣代表团返航,而是留在广州,以达盖尔银版法(Daguerreotype)摄影术和西法绘画谋生。根据1845年韦斯特在香港发行的英文报刊《中国邮报》(ChinaMail)上刊登的广告,韦斯特此时已在香港开设了照相馆,制作达盖尔银版单人和合影照片,主要顾客仍是在华外国人①。
同时代的西方社会,摄影术正处于日新月异的技术改革中,其中潜在的商业利益,是推动人们对这一技术发展投入热情的一大动力。除了开设照相馆经营人像业务,把记录当地风土人情的照片售卖给报刊、博物馆,或制成明信片、印刷成专题图书出售,也是摄影师的一种常规谋生方式。包括随军战地摄影、海外新闻报道在内的纪实摄影,在当时往往也并非是由政府主导的政治宣传行为,而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技术。1856年一位英国随军医生在写给赴殖民地军官的建议中,就写道:“我强烈建议每位助理外科医生都应该全面掌握摄影技术……没有哪种专业追求能像摄影这样……回报如此丰厚……凭借摄影,我们可以对当地的人、动物、建筑和风景进行忠实的记录,这些照片将会受到所有博物馆的欢迎。”②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战地摄影师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1832~1909)随英法联军登陆京津,拍摄了大沽炮台的遍地尸体残骸,在首批照片印制出来时,就已经同时在军队中寻找顾客,“在军官和香港人中间能卖出几千幅照片”;回国后,比托更积极地将照片结集出版并登报宣传,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以至于摄影史学者泰瑞·贝内特(Terry Bennett)认为,“自19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比托的商人身份就超过了他的摄影师身份。”③
因此,作为佐证人种学和民族志的“客观”证物,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商业手段,这些充满异国风物的图片,首先是为了满足19世纪欧洲流行的对非西方世界的猎奇,当然既要以发现彼时在西方社会并不寻常的东方视觉奇观为基本视觉需求,也要遵循潜在客户的观看方式,即西方主流视觉文化习惯。其中,中国风景和中国人的服饰、发型、人种特征等,作为他者眼中的视觉奇观,自然成为外国人镜头下早期中国摄影的主要内容。而由摄影术所承载的视觉文化习惯,一种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追求从视觉上如实描摹对象、以制造拟真的视幻觉为要务的、主流写实艺术传统,以及对一种不经人手的客观性的孜孜以求,既是催生摄影这一项技术的基本视觉文化土壤,也已然内化为摄影装置先天具备的视觉展现形式。
那么,同样是为了谋生,当西方摄影师以经商之道和猎奇之眼,将取景框对准他们眼中具有商业价值和异域特色的中国风物,以满足海外市场需求之时,是否存在着服务于本土顾客群体、以满足本地市场需求、为中国顾客拍摄人像为生的中国摄影师群体呢?相比西方人的“他者”之眼,中国摄影师的取景和审美是否存在某种原发的“本土性”?如今成为范式化的早期“中国式”摄影样式,是否就是由中国摄影师创造的、能够代表中国审美趣味和传统的“本土”风格呢?
笔者认为,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有必要回到两则常被当代学者引用,以佐证中西摄影师审美趣味不同、且中国摄影师胜出的案例原典。而重审这两则中国早期摄影史料的目的有二:其一,重审史料及其作者所处具体历史语境,反思不经思考按表层印象引述前人文字的问题,指出以这两则史料确证中国早期摄影“本土性”审美不仅是不充分的,更是对中国摄影“本土性”“中国性”是否存在、以及何以存在等重要问题的简化;其二,在挖掘和澄清中国早期摄影评论背后所潜藏的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早期摄影“中国性”的建构问题。
二、王韬:来自“本土”的比较
第一则原典是王韬在19世纪50年代末的日记。1858年下半年,王韬曾与友人在上海一同观看了法国人路易·李阁郎(Louis Legrand,约1820~?)的摄影过程,并在日记中以“照影”称呼摄影术。其中,除简单描述摄影器材及必要的日光和化学过程,王韬尤其强调了西人“照影”方法的两大优点:一是耗时少(顷刻可成);二是成像逼真(眉目毕肖):“阁郎善照影,每人需五金,顷刻可成。益斋照得一影,眉目毕肖。其法以圆镜极厚者嵌于方匣上,人坐于日光中,将影摄入圆镜,而另以药制玻璃合上,即成一影。其药有百余种,味极酸烈,大约为磺强水之类”④。
王韬提及的法国人路易·李阁郎,是19世纪50年代后期最早活跃在上海周边的西方摄影师之一,至今留下一套80幅关于中国风景的立体照片,存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其中有九幅风景照片曾制成木版画,刊登在1861年11月9日出版的法国《画报》上⑤。1859年上半年,王韬又同友人观看了广东人罗元佑在上海开设的栖云馆,并以“西法画影”称呼摄影术:“晨,同小异、壬叔、若汀入城,往栖云馆观画影,见桂、花二星使之像皆在焉。画师罗元佑,粤人,曾为前任道吴健彰司会计,今从英人得授西法画影,价不甚昂,而眉目明晰,无不酷肖,胜于法人李阁郎多矣”⑥。
此处王韬提到的栖云馆,有可能是迄今最早出现于文字记载的中国人开办的照相馆⑦。这段文字,也使罗元佑成为迄今有确切文字记录的最早开设照相馆的中国摄影师。从中亦可见,在上海开办了第一家照相馆的罗元佑来自于广东,其摄影术师承英国人,这与中国早期照相业传播和发展的整体路线(即从香港、广东,进而扩散至内地的“广东效应”⑧)相一致。
在比较了李阁郎和罗元佑的摄影后,王韬认为罗元佑更胜一筹,这一判断如今常被学者用于引证中国摄影师的作品质量优于西方摄影师⑨。不过,王韬究竟指的是在哪个方面罗元佑“胜于”李阁郎,却语焉不详。回看王韬原文,根据断句的不同,此处“胜于”至少有三种理解方式:一种是价格上的优势,即罗元佑的摄影价格更低(价不甚昂),但却能达到同样逼真的成像效果(眉目明晰,无不酷肖),因此“胜于法人李阁郎多矣”;第二种是操作手法上的优势,即画面清晰(眉目明晰)且逼真(无不酷肖),因而“胜于法人李阁郎多矣”;第三种理解方式是,罗元佑的摄影风格与构图,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品味,故而“胜于法人李阁郎多矣”。其中,第三种理解方式常被学者采纳,以王韬的论断,佐证中国摄影师具有不同于西方人的独特审美品质,因而中国顾客更喜中国人的摄影趣味⑩。
然而,上述三种理解方式无论哪种成立,王韬表达的也只是具体到个人的比较(即“画师”罗元佑的作品,优于同为“画师”的李阁郎),而并没有以二人作为华人和西人的代表,更未从文化和人种上,区分华人和西人摄影质量和品味的差异。而相比1859年这段留存在王韬日记中的私人笔记,到19世纪80年代王韬公开出版《瀛壖杂志》时,更直接地将“法人李阁郎”和“华人罗元佑”并称为“在沪最先著名者”⑪,不再对二者加以区别。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王韬在日记中提到,在罗元佑照相馆所见的“桂、花二星使之像”,通常被认为就是1858年《天津条约》和上海《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方签约人、钦差大臣桂良和花沙纳的合影肖像(图1)。一般来说,这一说法出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摄影史的权威著作《中国摄影史1840~1937》,书中以王韬日记为据(此二人肖像被罗元佑用作照相馆招牌广告),推知此二人肖像照片理当出自罗元佑之手⑫。的确,从留存至今的这张照片看,其整体上充满了符合中国人审美的视觉符号、对称构图、对身份等级的着意彰显:画面为简洁的中式布景,呈左右对称构图,“桂、花二星使”两位像主均为正面全身坐像,桌上相对并置着用以区别官员品级的顶戴花翎,且格外以支架抬高,中心桌布上装饰有类似一品文官补服的仙鹤图案,醒目地处于整幅构图的中心对称纵轴线上,以突显像主尊贵的身份等级。但是,摄影史学者泰瑞·贝内特的研究推翻了这一说法,指出这张现为温莎皇家收藏的照片,实际拍摄者并非华人罗元佑,而是英国外交官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⑬。那么,这张照片就很难再成为华人摄影师具有独特“中国性”审美的佐证。

图1 :罗伯特·马礼逊,《桂良与花沙纳合影》,1858年,英国温莎皇家收藏
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显得更为复杂:西人马礼逊所摄照片何以呈现出极具“中国性”的画面?更进一步,既然“中国性”审美出自于西人之手,那么,这种“中国性”究竟是原发的“本土性”,还是后天被建构的“他者性”呢?无独有偶,类似由西方摄影师拍摄,但被冠之以“中国性”审美特质的早期摄影,还有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华活动的美国摄影师弥尔顿·米勒(Milton M. Miller, 1830~1899)雇佣中国人摆拍的一批“中国式”照片。这些照片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被认为是典型“中国肖像风格”的代表,“以图证史”般佐证、形塑、建构着中国人对自身本土肖像传统的认知。巫鸿教授的研究指出,弥尔顿·米勒的照片,实则建构出一种被视之为“中国性”的、讲究画面对称、整身、全脸、无阴影的“中国怪癖”(Chinese peculiarity)⑭。而 这,在 随后入华的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1837~1921)笔下,则被进一步上升为可代表“一般中国人”怪异、扭曲、恐怖、低俗的审美趣味,甚至给出了看似合理化的解释:“凡是本地人拍照,大多都带着佛祖般呆滞木然的表情,脸部正对相机,左右手分别成90度直角。一般中国佬(A Chinaman)都会尽量避免1/2侧面或3/4侧面照相,原因是既是肖像就得看得出他有两个眼睛、两只耳朵,脸也得圆如满月。全身的姿势也必须遵守这种对称原则。还有脸部,也一定要尽可能避免出现阴影,即使避免不了,两侧的阴影也得相当。他们说影子并不存在,这只是大自然的意外,而不能代表面部的任何一部分,因此不该呈现在相片上。然而,他们偏偏人手一扇,只为了制造一点阴影……”⑮
然而,正如巫鸿的研究所表明的,这一看似充满了奇异“中国性”、并在当代持续被视为19世纪本土审美视觉确证的中国人形象,并非中国审美传统的自发绵延,而是19世纪西方摄影师以“他者”之眼,截取、拼合、演绎中国视觉文化传统的再发明——“经过这种调整或再挪用之后,被挪用的本土视觉文化完全掩盖了殖民者最初塑造这一风格的意图,从而将西方的执迷演变成了中国的自我想象”⑯。
三、赖阿芳:“他者”视角下的比较
另一个常被学者引用佐证中国摄影师技高一筹的案例,是香港早期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摄影师赖阿芳(Lai Afong)(图2)。目前没有留下有关赖阿芳的中文史料记述,除留存至今的“华芳”照相馆摄影外(图3)⑰,最常被引用的文字记录,来自于上述1867~1872年在华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森的英文著述。汤姆森在1875年出版的游记中(图4),称赞华人摄影师赖阿芳的艺术品味,并特别将之作为与上述“一般中国佬”不同的、“唯一的特例”:“我们折返回皇后大道,在一系列巨大的招牌前停下来,只见每块招牌上都用粗粗的罗马字体写着某位中国艺术家的名号和风格。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阿芳,摄影师’……阿芳请了一个葡萄牙助理帮忙招呼欧洲顾客。他本人是个矮小、略胖、性情温和的汉人,他的品味是有教养的(cultivated taste),他也有很好的艺术鉴赏力。从他的作品集可以看出,他一定是个热爱自然之美的人,因为他的有些照片不仅技巧极为纯熟,他对拍照姿态的艺术性选择也是引人注目的。就这方面而言,他是我在中国之行遇到的本土摄影师中,唯一的特例(the only exception)。他的门口一张照片也没放,而他隔壁的阿廷却在一个玻璃柜里展示了20来张恐怖至极的人脸相片……”⑱

图2 :华芳照相馆,《阿芳像》,1865~1880年,英国爱丁堡苏格兰国立肖像美术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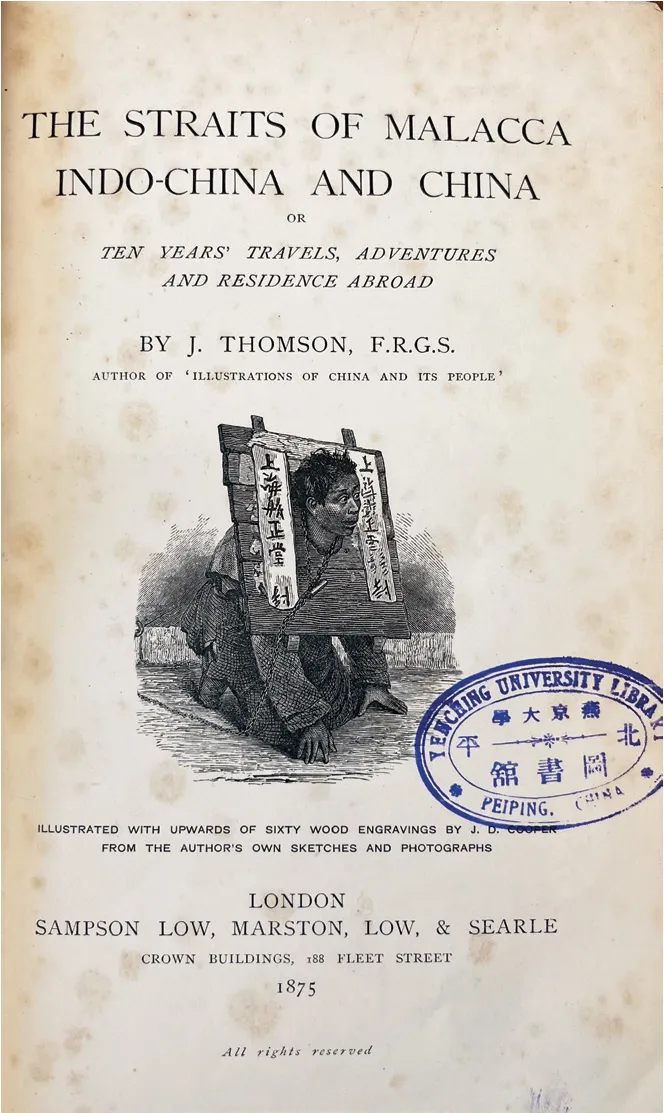
图4 :《十载游记:马六甲海峡中南半岛与中国》扉页,1875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其中,与王韬具体到“法人李阁郎”和“华人罗元佑”的实例类似,汤姆森也具体描述了华人摄影师赖阿芳的摄影作品。但是,相比之下,王韬并未将实例上升至总体民族性差异的比较,而汤姆森则在文中自然流露出区分人种和族群的意识。毕竟,相比在中国本土内观“西法画影”的维新派文人王韬,从殖民宗主国来到属地考察的汤姆森,自然携带着具有英帝国殖民时代特色的“他者”之眼,下意识地以根深蒂固的西方视觉文化传统,拣选他认为中国本土值得被西方人观看的景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汤姆森将华人摄影师赖阿芳作为本地摄影师中“唯一的特例”,并对这一“特例”的“高雅”艺术品味大为赞赏。
汤姆森有意识划分出“华人摄影师”群体,以作为与西方摄影师比较对象的诉求,更明确地体现在他发表于1872年的另一篇文章《香港摄影师》中。这一种族鉴别和区隔的意识,与汤姆森本人作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和皇家人种学会会员(1866年获选)的身份和使命不可分割。因此,汤姆森称香港“华人摄影师”的作品,比“我国一些损害摄影艺术名声的、无名的、业余摄影师更好”,还进一步将其对“华人摄影师”的印象,上升至概括“中国人”国民性的高度⑲。这一从人种和民族性角度构建中国人“他者”身份和形象的雄心,更集中体现在汤姆森的四卷本巨著——《中国与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ofChina andItsPeople, 1873~1874, London)中。这部图书收录了汤姆森在中国拍摄的200多幅照片,并一一配以对应的文字解说。
当然,相比同一时期欧美社会对中国的敌意言论,以及武力征服中国等异域文明的实际军事行动,汤姆森显然展示出更温和的文化态度、更友善的同情心和更包容的理解力。因此,我们不能跨越时代局限,以21世纪多元文化平等共处的标准,苛责汤姆森身处19世纪英帝国殖民扩张叙事中自以为是的“客观”,毕竟汤姆森的“他者”之眼迥异于诉诸暴力对抗的激进种族主义之眼。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汤姆森的镜头及其文字所形塑的“中国性”,并非如其所视的那样“客观”。正如荷兰历史学家西佩·斯图尔曼(Siep Stuurman)在对“跨文化平等”观念史的研究中指出的,欧洲殖民主义的“教化使命”作为启蒙运动的一种副产品,在19~20世纪,成为欧洲人的一种既非出于原始“仇外心理”、也看似并非“恶意”的普遍时代观念:
“由于承担教化使命的大多是欧洲白人,种族等级制的概念从未远离。19世纪和20世纪的科学种族主义绝非前现代仇外心理的返祖残余,而是典型的现代世界观。甚至纳粹偏执的反犹理论也代表了一种极端的、精神错乱的种族学说,19世纪的大多数欧洲知识分子都赞同这种学说。”⑳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汤姆森百科全书式“客观”展示中国的渴望,对实地考察的实证性信赖,以及相信能够克服和抹除“他者”之眼的主观性,实则既是彼时英帝国海外扩张的时代精神产物,也是促成西方人入华实地拍摄照片的原因之一。而实地拍摄的照片,又为汤姆森的观察增添了可信的“客观性”。这一“客观性”不仅能给汤姆森带来作为人种学和民族志科学研究者的声望,还事关汤姆森中国行拍摄的这些照片的商业价值,这也促使汤姆森及其出版商格外重视照片出版和展示方式上的推陈出新。1872年回国后,汤姆森一改以往零售照片的商业模式,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技术和新颖的图文排版方式,印制了这套四卷本巨著,一经出版即大获好评,总印刷量近3000册,不仅成为当时西方世界认知“中国”的一个窗口,更系统地建构了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视觉形象。
在汤姆森的镜头和文字下,一个古老而神秘、宁静而有待被开发、虽然落后但可被改造的“中国性”,因视觉形象的直观可见,而显得“客观”可信。正如汤姆森通过对“华人摄影师”的观察,得出对“中国人”的整体结论:“中国人的头脑适于进行摄影化学这一程序繁杂的精工细作。”㉑这段话当然可以用来佐证19世纪西方人眼中,积极向上的中国形象,但是,这里的逻辑显然不是称赞中国“本土性”的优越,更不是发掘中国独特的审美品质,而是观察到中国人是可被教化的。
由此,中国人被塑造成可被文明世界同化的“他者”,一个等待被开发和被启蒙的对象,而西方人显然是此中作为改造主体的文明人,实则是为殖民扩张、以文明征服野蛮的文化合法性背书。这其实与汤姆森对赖阿芳审美品味的称赞如出一辙。因此,这一来自“他者”的称赞,既不能被视为中国本土摄影师的审美眼光普遍优于西人的佐证(毕竟在汤姆森的语境中,赖阿芳的高超艺术水准只是中国本土摄影师中“唯一的特例”),也不能用以证明中国摄影师具有某种“本土性”原发的摄影美学品味,更不能用以佐证这一中国审美正是中国顾客喜爱中国摄影师的原因。
四、并非“妖术”:“数百年以来恶意的妖魔化”
现有史料显示,当摄影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初入中国之时,中国人对这一新技艺的反应,既不像当时摄影术在西方舆论中的那样,是令西方人震惊的一项让大自然自动显现自身的、伟大的视觉“奇迹”;也还没有像后来鲁迅笔下描写的19世纪后期,在经历了多次战败和割地赔款后,摄影术与许多西洋方物一同,被视为西方文化侵略的一种方式,成为令中国“乡下人”恐惧的“妖术”㉒——19世纪中期中国人对摄影术的自觉反应,多数并非恐惧,亦非震惊,而是起初好奇、进而想了解,之后视之为平常物。
根据《埃及尔中国日记》,19世纪中期前后,普通中国人对摄影“是孩子看到新奇事物时候的反应……而非震惊”,也并不恐惧,更多是“朦胧的好奇”,在当时的广州和澳门,“行人对我的拍摄要求每每非常配合”,双方交流友善,整个拍摄和观赏照片的过程“笑声不断”㉓。在澳门期间,当法国人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 1802~1877)给普通行人拍照时,中国人很乐意在镜头前摆姿势,埃及尔也在此期间向中国人展示了相机的内部构造和达盖尔银版照片。在广州城,埃及尔拍摄的达盖尔银版照片也非常受欢迎,“照片被一抢而空,每个人都非常高兴地拿到自己的小照”㉔。
然而,19世纪中期中国人(尤其是上层士绅)看待摄影术的这一“平常心”或“客观”态度,又常常被今人以历史决定论的后知后觉,描述为时人对先进技术的愚昧无知和夜郎自大,这一看法实际上早在19世纪中期西方人的记述中就已经开始了。1849年10月24日下午,美国人本杰明·林肯·鲍尔(Benjamin Lincoln Ball, 1820~1859)在厦门美国传教士住处,与美国驻澳门领事和三位中国官员一同观看了神父家人的达盖尔银版照片。鲍尔先生在寄回美国的家信中,描绘了中国官员和“国家国民”的“彬彬有礼,善于言辞”,但十分不理解中国官员面对摄影术的毫不震惊,并将中国官员“泰然自若”的观赏态度,解读为一种带有“欺骗性”的“优越感”:他们虽然“彬彬有礼”却“不以为然”,“他们或许已经发现我们的艺术和科学遥遥领先”却“不愿承认”,“他们佯装泰然自若的神情仍显示出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是如此坚固,以至偏见似乎已从中扎根”㉕。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视这样的评判为“客观”的史料呢?学者包华石(Martin Powers)在对17、18世纪入华欧洲旅行者见闻的文本研究中注意到,欧洲人对异域风土的评判,基本都基于西方传统的政治权力观念和“零和博弈”的文化参照系统,而将本国的文化政治建制、喜好与问题,投射到异国的现实之中,以便构建一个拥有荣耀与权力、更为进步的“西方”身份:
“在这种参照系统里,欧洲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任何相遇都会被解释为存在竞争关系,因此欧洲人会提倡采取防御的姿态。这样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欧洲旅行者会采取一种浮夸的书写方式……处于一个像欧洲那样施政权力与荣誉合而为一的社会,世界范围内的荣誉分配会被视为一个零和博弈(zero-sum game)……通过把在本国寻见的错误投射到精心建构的亚洲形象上,欧洲的理论家们就可以在情感上及修辞上删减这些错误实践,把这些行为排除在他们正在为‘西方’构建的新身份之外。”㉖
鉴于此,包华石教授提出问题,“应该如何扭转数百年以来恶意的妖魔化,同时避免在不经意间美化受害者呢?”㉗正是为了解决长期以单一西方视角为评判标准而造成的跨文化误读问题,包华石找到了形象化抽象概念的“转义策略”(tropic strategies)和基于图像而非文字的“跨视觉分析”(transvisual analysis)两种基本研究方法㉘。笔者认为,这两种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对早期摄影史料的分析和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既不能完全将“他者”视角下的评判视为绝对的“客观”描述,也没必要在全盘否认“客观”价值的意义上无视作为史料留存至今的“他者”陈述。重要的不是追问诸如此类的史料中有没有“客观”,而是提醒我们重审何为“客观”、以及如何提取文本中真正能够反映“客观”的记述。
五、结论:反思“本土性”
那么,由此回到前文提出的关于中国摄影是否存在“本土性”传统、以及“中国式”摄影样式何以建构的问题。随着“在中国发现历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论的兴起,20世纪后期以来,学界研究纷纷将目光转向发现“本土性”传统,以源发于中国传统内部的能动性,扭转20世纪长期主导中国史研究的“冲击——反应”方法论,改变以往由“他者”发起、而“本土”被动接受的近代化历史叙事。正是在这一研究趋势中,21世纪以来,摄影史论学者从早期摄影史料文献出发,发掘19世纪中国本土的摄影实践活动,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致力于证明中国本土摄影有其自发的内在逻辑,以及独特的中国审美风貌。
尤其是一系列19世纪照相馆老照片的发现,为独特的中国审美提供了佐证。比如: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人经营的照相馆在本土全面开设,进入了中国摄影史上的“照相馆时代”。此后,中国照相馆摄影在不同时代,也具有了不同的本土风格:19世纪70年代,清晰、肖似、快捷、廉价,是照相馆广告词和同时期照相馆人像的主要特征;19世纪80年代的照相馆摄影,则更追求风雅的布景和仿效“行乐图”的艺术性特质;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洋元素更多为中国照相馆所喜爱,出现了“洋化”的风潮;从20世纪初到民国,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国内掀起抵制洋货的几次浪潮,中国照相馆也出现了向传统布景和中式审美“回归”的趋势;20世纪20~30年代继起的,则是简洁的“现代”风格,“美术照相”成为照相馆广受欢迎的招牌特色㉙。
但是,正如巫鸿所提醒我们的,“不加批判地使用‘本土’一词,本身就已经接受了殖民者的立意和术语……它的目的已不再是构成‘真实’的当地风格,而仅仅是消费这种风格。”㉚尤其是19世纪50~60年代,相对于以“他者”目光捕捉和售卖猎奇影像的西方摄影师,主要服务于中国顾客的中国摄影师,似乎并未对等地出现在同一时期。仍以赖阿芳为例,学者胡素馨(Sarah Fraser)注意到,赖阿芳的顾客群体仍是外国顾客:在1889年的一份英文广告中,可以看到,赖阿芳照相馆熟练地借用了“本土样式”(native types)之类明确建构“他者”中国形象的词汇,向彼时默认和熟悉这些用语的、潜在的外国客户售卖照片,以满足西方人眼中“合理”的异域形象和固化期待㉛。胡素馨认为,虽然到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19世纪60~70年代以后,中国摄影师和中国照相馆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中外摄影师镜头下的中国风景和人物照片并无太大区别,在体裁和类型上都十分接近;而正是在这些照片的共同塑造下,“China”这一带有羞辱含义的概念,开始实现国际化的传播,同时在形象上,也被摄影照片建构为落后的、停滞的、与西方文明异样的、他者的、需要被征服和改造的另类存在㉜。
因此,仅就本文对两则中国早期摄影史料的重审而言,笔者认为,往往正是对待史料态度的粗疏,让我们一再错过了追问“中国性”有无、何在、何以发现、绵延或建构等真问题。虽然王韬日记中对于华人摄影师罗元佑的记述和称赞,可视为中国本土摄影实践的一个开端;汤姆森笔下对于华人摄影师赖阿芳的嘉许,也可视为中国本土摄影师获得国际同行评价的一种佐证,但是,并不能由此就简单认定中国早期摄影的“本土”优越性。这并不是说笔者就此判定“本土性”不存在、甚至说“中国性”是被建构的假问题。恰恰相反,笔者对这一问题始终抱持积极研究的态度,重审的意义也并非落脚于批判,而是寻找新思考的起点。也只有建立在缜密辨析的基础上,本就稀有且珍贵的中国早期摄影史料,才有可能真正为我们呈现出历史“客观”的原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