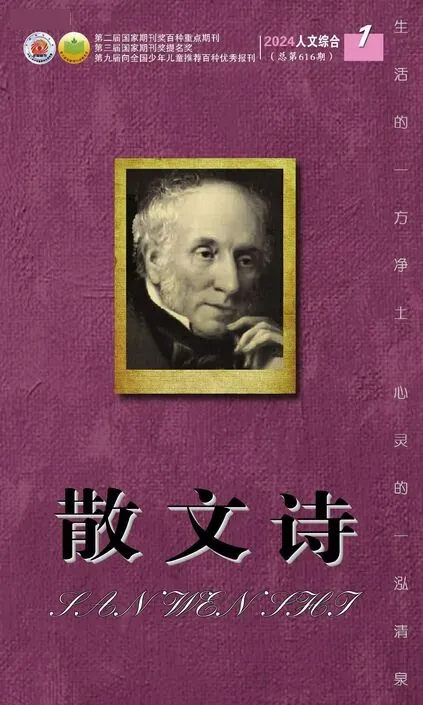西安谣
◎陈惠芳
兵马俑
秦始皇驱动着天下的劳力,
至少干了两件大事。
地上有长城, 地下有兵马俑。
劳苦的命, 留下了后世瞻仰的奇观。
贴着“暴政” 标签的始皇帝,
一开始就有了众说纷纭的雄厚资本。
大国工匠也有了数千年的历史。
这些扶起来的兵马,
这些褪去了彩绘的泱泱大军,
依旧是那样的威猛。
如果再次化身金戈铁马,
照样可以扫六合, 平天下。
咦! 秦始皇给自己, 给后人,
挖了这么多坑。
这坑里, 不光有兵马俑,
还有秦帝国的残骸。
钟鼓楼
敲钟的人, 走了。
送钟的人, 来了。
敲鼓的人, 散了。
制鼓的人, 歇了。
你我他, 站立在那里,
眺望前世今生。
帝王将相, 平民百姓,
都像钟声、 鼓声一样飘移。
千年帝都, 曾是满目疮痍,
又是一地繁华。
风声雨声读书声,
钟声鼓声厮杀声。
声声入耳之后,
时光打了一个结, 也松开了。
帝都赋
念着西安的姓名,
喉咙口又涌出了丰镐、 长安、 大兴……
周、 秦、 汉、 隋、 唐,
一个一个王朝雄踞于此。
改朝换代的悲喜剧一幕一幕上演,
走马灯式的帝王, 熄灭了最后一盏灯。
最可叹大唐土崩瓦解,
那个朱温真是一个瘟神。
大唐留下一个“长安” 之名,
留下一条丝绸之路。
就撒手西去。
乱哄哄的五代十国,
成了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 的大戏台。
桂冠坠落, 野草疯长,
城内城外就是草民。
血脉犹在, 根犹在。
芸芸众生命比纸薄, 比城墙厚。
华清池
南依骊山, 北面渭水,
好一个离宫, 好一处温泉。
唐玄宗和杨贵妃洗得兴起,
水花飞溅, 都是唐诗。
而我视之, 它是一池泪。
安史之乱后, 大唐以泪洗面。
而我视之, 它是一坛酒。
贵妃醉酒之后, 醉醺醺走到了马嵬驿。
大国小池, 要么波澜不惊,
要么惊涛骇浪。
羊肉泡馍
由湘入陕。
在西安回民街第一次吃了顿羊肉泡馍,
回到长沙, 打了个饱嗝,
还是那个味。
风味, 风味。
不管是东南风, 还是西北风,
风吹草低见牛羊。
味道浓, 味道淡,
喉咙口是一个风口。
回民街, 是一条美食街。
老米家、 老孙家、 老杨家……招牌林立。
连鱿鱼都做成了花样, 像艺术品。
牙口不好, 咬不动, 就喝汤,
将羊肉泡馍汤喝成了鲫鱼汤。
口味重, 重口味。
湘人与陕人的区别,
就是一份辣椒炒肉。
大雁塔
此塔64 米, 5 层砖土。
此塔存佛像, 存舍利, 存梵文经典。
此塔高, 此塔不可攀, 高不可攀。
此塔除了大雁与《西游记》, 皆不能飞越。
此塔旁, 有玄奘法师像。
谁人不识唐僧、 唐三藏?
想不到玄奘法师本姓陈, 名祎。
陈祎, 大唐的一个家门,
西天取经, 取回了真经。
不知道唐太宗送迎的时候,
玄奘法师是怎样的庄严心境。
不知道主持修建此塔的时候,
玄奘法师是怎样的高瞻远瞩。
大雁塔, 小雁塔,
大事小事身后事。
玄奘法师犹听雁塔钟声。
未央宫·大明宫
汉唐。 未央宫, 大明宫。
泱泱大国, 泱泱大宫。
《诗经》 滋润了王朝的象征。
富丽堂皇, 也是一卷大诗。
从汉至唐, 从未央宫至大明宫,
从一个皇帝到另一个皇帝,
从一道圣旨到另一道圣旨,
铁打的江山, 流水的主。
唯没有谥号的劳作者,
儿孙满堂, 生生不息。
加固, 只是加固一种回忆。
重修, 只是重修一种荣耀。
当所有的脚步渐渐消失,
它们只剩下一种饱满的空。
灞 桥
遥想这一地名,
就有一份霸气。
踏上这一地方,
就有十足霸气。
春秋战国, 称王称霸。
秦始皇的祖先秦穆公称霸西戎,
将滋水改名为霸水, 以彰霸功。
由霸水而易灞水, 由灞水而架灞桥,
亦有了灞桥风雪、 灞桥折柳的景致与别离。
当古灞桥成为遗址, 新灞桥凸起,
古往今来, 流水不腐。
当年, 嬴政“送至霸上”,
秦军东征, 奠基大统一的霸业。
当年, 刘邦“还军霸上”,
勇赴鸿门宴, 将西楚霸王逼死乌江。
灞桥, 一座更替了朝代的桥,
一座见证了兴衰的桥。
霸陵原在此, 白鹿原在此,
丝绸之路在此。
我在此, 只是一个小小的逗号。
大唐不夜城
入今朝夜, 入昨日唐,
火树银花不夜天,
仿佛在梦境中。
曾被封存的人,
像是从大唐的嘴里吐出。
人山人海。
结伴行, 也曾失联半个小时。
李世民依然高高在上。
大唐天子与一介草民合影,
天衣无缝。
想起了李白, 想起了杜甫,
想起了杨玉环, 想起了武则天……
人活一世, 人活一辈子,
或长或短, 都是枯与荣。
陌生的面孔晃动在无边夜色中,
百家姓与族谱, 忽明忽暗。
我是谁?
谁是我?
一个与生俱来的符号,
在复制的盛唐里,
享用了短暂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