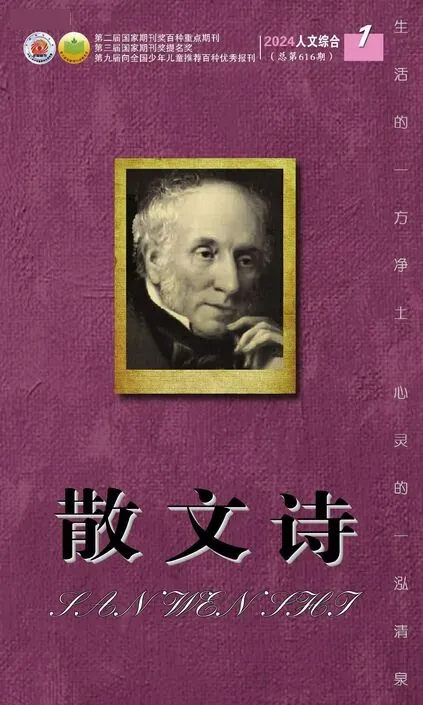小素描
◎邵永刚
莪默·伽亚谟
莪默·伽亚谟。 是世界上名声最高的波斯诗人,《鲁拜集》 的作者, 诗风豪迈、 旷达、 深情, 被称为“东方之星”。
有一位尼达米回忆, 在一次宴饮中, 伽亚谟说: “我的坟, 将来一定会在那个地方; 那里, 树上的花, 将每年两次落满我的坟头。”
伽亚谟故去几年后, 尼达米来到他的墓地, 那是一个春天的暮晚, 只见那坟头有一株梨树, 一株桃树, 无数的花瓣几乎覆没了整个墓冢。 想起伽亚谟曾经说过的话, 尼达米掩面而泣: 死亡也可以这样美!
蒲 柏
亚历山大·蒲柏, 18 世纪英国杰出诗人, 因宗教信仰被剥夺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权利。 幼年患结核性脊椎炎, 造成驼背, 身高没有超过1.37 米。 小史诗《夺发记》, 丰博优美; 哲理诗《人论》 清隽高贵。 为英语诗歌奠定了高度。 得年56 岁, 以诗人始,以诗人终。 在世时攻击他的人络绎不绝, 讽刺他的文字连篇累牍,然而都湮灭了, 蒲柏还在——
“人皆有错, 难能宽恕。”
“羞涩腼腆的花神把大地描绘得五彩缤纷。”
蒲: 草本, 朴茂、 葳蕤, 年年春天依水而生; 柏: 木本, 长青, 历霜雪而不凋也。 英语的说法: 历史是最有风度的。 汉语的说法: 知蒲柏不尽。
两诗人
……雨果写一位母亲新亡, 她身边5 岁的孩童, 聪明活泼,嬉闹歌唱如常, 毫不知母亲已永远离他而去, 雨果接着写到——
“悲哀是一枚果子
上帝不使它生在
太柔软的载不起它的嫩枝儿上”
心肠柔软, 笔锋冷冽, 宽厚仁慈。 小说而外, 雨果独占法国诗坛头鳌五十载, 名至实归, 所来不虚。
写《恶之花》 被人称为“魔鬼诗人” 的波德莱尔, 一次动情地喃喃道: 巴黎的夜晚, 每个窗口都亮着灯, 真想走到每个窗口去看看。
大慈、 大悲, 妥妥的上帝视角; 格局, 情怀, 才华, 都是。
他们担当了人性中最大的可能, 而且发挥到了极致; 现在有人把他们看成过时过气的, 哪知道他们是不朽的。
大师雨果、 波德莱尔同出于法国, 开始是法国的光荣, 后来是人类的光荣。
克劳德·西蒙
克劳德·西蒙, 于1954 年大病, 愈后著《春之祭》, 个性尽出, 艺术上得大突破。
之前默默种植葡萄, 寂寂无名。
大病, 就是吃苦, 直面生死, 艰难淘沥, 之后, 会大不一样。
每个大人物都是同自己抗争的。 失明了的荷马、 弥尔顿、 博尔赫斯, 聋掉的贝多芬, 都是。
耸入云端的峰峦, 一个人就是一个时代。
不抗争, 谁会知道你?
西蒙, 他严肃, 诚恳, 风风雨雨种葡萄, 收葡萄, 酿酒, 终于成了: 《弗兰德公路》 通向这里通向那里, 透脱, 俊逸, 畅达时间的各个路口。
纪德说: “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
人性中最大的可能, 之于他就是艺术。 那里有个人, 有自由,有无限, 有光明……
勃朗宁夫人
伊丽莎白·芭蕾特·勃朗宁, 即勃朗宁夫人, 生于伦敦, 知识广博, 相貌极美, 曾译希腊文学《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等。 因最爱的弟弟不幸死于海难, 她悲痛, 隐居, 以至瘫痪。
因慕其才, 小她六岁的罗伯特·勃朗宁热烈求婚, 先遭拒绝,后被其真情所动。 往意大利度蜜月, 在煦风、 阳光、 爱与葡萄酒的滋润、 滋养里, 得以康复。
一对神仙眷侣楼上楼下分别写爱的十四行诗, 互诉衷肠:
“不要怕重复,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我爱你!”
一对神仙眷侣缱绻悠游于美丽的意大利。 一日, 她在与丈夫喁喁谈笑中, 觉得累了, 就偎在他的臂弯里轻盈睡去——无病无痛, 悄然仙逝。
《被放逐的戏曲》 《孩子的哭声》, 是她的名诗。 但流布深广的, 还是她写给爱人勃朗宁的44 首《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 异美、 温煦。
生命, 有多靓, 多甜, 就有多么异美、 温煦。
仿佛泪水, 诗篇与爱, 就是天堂。 那扇天堂之门——窄呀,一个人进不了, 但两个人却是可以挤得进去的……
杜 甫
盛唐过去了, 杜甫不过去。
人好, 诗就会好——“万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纵横捭阖, 沉郁豪贵, 饱蘸浩叹的浓墨, 他本是来救世的,救不了, 结果倒是超越无限世代地救出了诗人自己。
“望一座山比造一座山, 更容易让人走神儿。” 夜读老杜, 那一份沧桑与巍峨, 总是让人久久感叹、 唏嘘!
云烟里孤绝的高峰在着, 有敬畏有仰望, 尘世也还是值得一救的。
戈蒂埃
“为艺术而艺术” 这个口号, 由戈蒂埃最先提出。
青年戈蒂埃以画家的身份来到巴黎, 却成了诗人。 有诗集《珐琅与玉雕》 等。 他喜欢鲜花、 黄金、 大理石, 他不在乎酒,而在乎酒瓶的形式。
福楼拜嘲谑他: “可怜的戈蒂埃, 诗句写得这样好, 就是写不好一首诗。”
精湛的酒瓶也使人快乐, 沉醉。 艺术何用, 美就成了。
哪 吒
削肉还母, 拆骨还父……之后, 以藕为肢、 荷叶为衣、 莲花为其头面而重生的哪吒, 成为了永远的孤儿。
不再是某只巨环上的一个扣。
不再是某张巨网中的一个结。
一个真正配得上风火轮、 乾坤圈、 混天绫的赤子, 精灵。
好是道德的, 极致是反道德的。 喔, 一个伟大的世界, 比起你的正确, 它也许更喜爱你的错误。
在本质上, 哪吒是个诗人。
埃兹拉·庞德
……时间像一把木椅, 安静地呆在阳光中, 安静地呆在他的眺望里——
“当我倦于赞颂晨曦和日落, /请不要把我列入不朽者的行列。”
诗章里的比萨, 被风一吹, 还是原来的样子。
还是那么美。
诺瓦利斯
“蓝花诗人” 诺瓦利斯, 被歌德、 席勒等视为“百年难遇的奇才”。
童年蒙昧, 九岁罹患重病, 其间突然心智猛醒、 勃发: 一个安静的男孩, 大大的眼睛、 有灵气的眼睛, 那种颤然欲碎的异美与脆弱、 高贵与陌生, 令人既敬畏又怜悯。
爱因斯坦曰: “我实在是个孤独的旅客。”
诺瓦利斯曰: “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 到处去寻找家园。”
安静、 内向、 敏感, 诺瓦利斯, 一个首先称得上心灵诗人的人, 留下了《夜颂》 《圣歌》 等浪漫主义杰作。
在创作长篇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 的过程中, 肺痨夺去了他的生命。
年仅29 岁。 这样的夭折, 加上他巨大的独创性和罕见的美姿, 使他的形象富有一种异样的诗意光华——
“……夜/在我们身上打开的千百万只眼睛, 我们/觉得比那些灿烂的群星更其神圣。”
“世界在远方/从来没有一个孤独者像我一样/孤独”。
这个无限辽阔的人类世界原是神奇的, 因为那些奇崛灵魂的游走, 与精神漂泊, 为其注入了新的生命。
精神还乡!
斯塔尔路过人间
孤寂而灼热的灵魂: 俄罗斯裔法国画家, 尼古拉斯·德·斯塔尔。 公正, 不料得到的是折中——犹豫、 含混, 撕扯不清, 而非酣畅表达。
《红瓶子》 与《你能让满山花开神就来》 完成后不久, 斯塔尔就自杀了。
那是1855 年的事。
“以荒诞开始, 总不能也以荒诞结束吧。” “我不画你们所看见的或你们所想到的。” 边缘化, 不定型, 他抓到一手不好不坏的牌, 他选择——
不玩儿了。
小 结
……雨后, 星汉灿烂
……流萤曳曳, 遍野蛙鸣。
那会儿的乡野, 真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