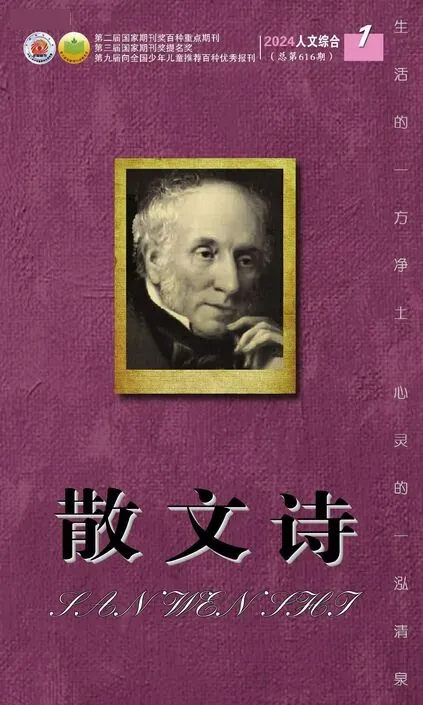行走的悬念
◎陈美桥
行走的悬念
在轨道的翅膀上, 站起来。
固执地站成, 一棵被命运煽动的大树。
你弯弯拐拐的名姓, 从看不见的小小结点, 经我身体长成年轮。
每绕一圈, 都在分秒必争。
江河与麦田, 在车窗外坠入移动的深渊。 信号灯前, 总有我颤抖的轨迹。
一块块枕木不断咳出山川的秘密, 谁都来不及开口说话。
只有你刚刚传递的电波, 受命于信号的断裂, 还在轰隆声中起起落落。
它们似乎带着隐秘的力量, 要在流逝中作出最后搏击。
直到胸前的沟壑, 上下起伏, 又险些振翅欲飞。
它才静静潜于漆黑的隧道, 准备引燃某种悬念。
想听的声音
我含着一串四川话, 搭上了绿皮火车。
不争气的牙髓质, 不断在车厢内涌动湿气。 像我, 总是排不掉忧伤。
原谅一个人, 太想靠近目标时, 上下颌会艰难地做出不规则运动。
脚底轻薄。 窗外流淌着雨水, 恣意地荡漾出关节炎复发的疼痛。
暮色又那么狠命地拍打着我。
我会成为旷野上那只哀鸣的寒号鸟吗?
终于, 我认出那根隐秘的旗杆, 也终于踅进你的异乡。
一个人在空空的木房内, 除了蹲下, 仍唯有饮泪蹲下。
我听到陌生的语言从墙外撞进来, 不断在体内艰难上升, 接着痛苦沉落。
我只想听到, 你的琵琶几时出窍, 于不远处, 弹出那把沉默之刀。
雪山的遐想
大雪裹满松树, 比唇还厚。
成群的苍松, 像一个人能言善辩, 吐出的每个字句, 都巧妙地溜向滑动的缆车, 组成山岭上完美的颂词。
而大地的冰凌, 一次又一次推搡着我。
脚下那些循环的坚硬, 多像狡猾的狼族, 每一次面对深山嚎叫, 仿佛都是猜度天意。
我们错过太多个皎洁的冬天了。
这寂静中喧哗的高地, 寒气拼命精心雕琢, 只为在大雪内部供奉一尊月老。
我们应该十指重叠, 然后紧扣, 再敲响锅碗瓢盆。
让皱纹细密地嵌进肌肤, 弯出生活的弧度, 绕成那根隐匿的红线。
要燃一堆柴禾, 融化捧过的积雪。 还要为炊烟让道, 去缝合生活的缺口。
生活素描
她像一座自暴自弃的雕塑, 散漫地从梳篦上捉下几只虱子。
来不及重新将稀薄的棉团在头顶打结, 虱子便在磨口旁边,“砰砰” 地炸响。
她的指甲上, 蹦出几处殷红的鲜血, 那是从她身体里开出的小花。
一朵, 两朵……静静的村庄, 只有她一人开花。
他站在窗口呼喊“救命”, 偶尔路过的人便稍息, 立正。 恍若当年正在演练的士兵。
他将手伸进宽大的裤兜。 现实却像一具枯木, 只能掏出荣誉的树根。
先是一节轻轻拉扯, 就可能分身的绸带。 再有几枚生锈的勋章, 咀嚼过微凉的暮色。
只有时钟为他一人敲响, 他才敢把自己推向封闭的阳台。 两扇被杜鹃啄过的窗户, 搀扶着摇摇晃晃的人生。
哦, 86 了! 他说, 这摇摇欲坠的人生。
然后, 又把自己摊在床上, 像一张泛黄的信纸, 等着某天被焚烧过后, 靠近收信的人。
荷塘密语
荷塘, 盛满拉纤的太阳。
太阳用桨撬动倾斜的船只。 无论花瓣滑行何种幅度, 都是世人眼中膜拜的圣像。
蜻蜓在振翅时被度化, 蜜蜂在蜜吻中被度化, 又摇来一条水蛇, 抖动智慧的铃铛。
那些产卵的, 哺乳的, 那么多不同的肉体, 都深植四德的根系。 穿透的蛙鸣, 也是经风声点化的梵音。
其实, 荷花每翘起一枚花瓣, 茎杆就会在泥里按一个手印。一切的游弋, 都会降低果实的预期。
大雨降落的时候, 花瓣会受到暗语鼓舞, 最后决绝地叩响水面。
你是否还虔诚地渴望储存一碗荷上的露水, 用来浸泡幸运的手势?
你是否急于将一颗颗苦心抽离, 才敢面对荷塘敞开的密语,对未来信一半, 留一半?
秋夜的脚步
今夜, 风雨如期而至。
亿万个奔跑的理由, 正在加速转动。
风雨交加之时, 大地摁不住鼓起的寒凉。
松树是一只呼啸的野兽, 用一把胡须理清成熟的条理。 拔下来的, 是某些悬浮着的金黄构想。
这茫茫山野, 云团怀着谦卑之心, 每挂一棵树梢, 都饱蘸浓墨。
树下的蘑菇开始惊声尖叫, 像一副带泪的颧骨, 逐渐铺陈许多斑点。 它的唇线走势曲折, 可能隐藏某种毒性, 还有数不清的蛊惑人心的新鲜。
一些事件, 同样在今夜破土而出, 走珠般滚入中年的褶皱。
谁知那是一场圆满的修行, 还是嵌进体内无法取出的碎片?
想到黎明会在远方迷路, 高耸的梯子可能随时抽身。 这雨夜攀沿的脚步, 接近一棵幼苗生长的土壤, 已经开始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