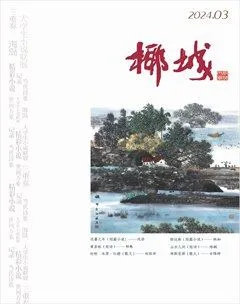村校·本草·红楼
作者简介:刘丽华,湖南省作协会员。有作品散见《散文》《散文百家》《山东文学》《黄河文学》《厦门文学》《雨花》《牡丹》《海外文摘》《小小说选刊》《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出版小说集《我是谁的朱砂痣》。
1
母亲坐在阳台上翻看她的学生影集,一脸的幸福,她桃李满天下……想当年,母亲30岁,兜着她的枕边书,一部本草,一部红楼,牵扯着年幼的我,离开师范附小,去了父亲的老家支教。那是一个没有通电、没有学校、没有诊所的偏远村庄。
那时,父亲已在县城落脚,爷爷奶奶早已过世,叔叔也移民了,老家没有一个亲人,可母亲坚持去那里传授普通话教学。我们到达时,一个破旧的仓库做学校还待修缮,母亲和她要任教的复式班,就安排在一个军嫂的农家小院里。
那是一个有着药草幽香的柴门院子,通往柴门的小径边有紫苏、鱼腥草、薄荷。篱笆上是七绕八缠的瓜豆藤蔓,一路开着黄花紫花攀爬上了柴门顶棚,又从顶棚翻下身来吊着几个瓜崽、几根豆角。柴门是用杂木做的双关门,轻轻一推,吱呀开了,往里探视,一座带杂屋的砖木村舍,将院子隔成了前院与后院,院落里散落着石磨、连枷、畚箕等农具……
记得村支书领着我们母女进院时,喊一声“他二婶子”,一位在堂屋摆放课桌的农妇应声而出,她两根麻花大辫子,红衣绿裤,浓眉大眼,笑呵呵地迎上来,双手在蓝花围裙上擦了擦,一把接过母亲手里的行李,眼睛打量着母亲,母亲也在笑,母亲唇红齿白,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一头短发,模样儿颇像电影《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当然,母亲衣着不同,是白衬衫,蓝裤子。这时,二婶大嗓门说住她家柴方水便,烧火有干柴,吃菜地里摘,用水缸里舀。说着,把我们往东房领。
东房门口站着一个我这么大的小姑娘,她是二婶的女儿桃宝,她一声不吭,好像在琢磨我们是谁,来她家干嘛。东房收拾得窗明几净,宽敞舒适,床铺也铺好了。母亲看到缝纫机的刹那,眼里闪着光亮。我知道,母亲对这个房间很满意。
老支书帮二婶布置教室,先将黑板挂在堂屋正面,上面写着“欢迎孩子们入学”,又将十五张单课桌摆成三组,一组是为在邻村读三年级的学生准备的,其它两组是安置没开蒙的新生。二、四年级,安妥在另一个仓库,由本村一名高中文化的男青年执教。从此,村里的娃儿再也不用去外村上学了,还可让不少失学的孩子也背上书包。现在回想起来,母亲是在做大事。
教室安顿好了,支书一走,二婶提个竹篮带我们前院后院地遛达。往前院的坪边下个小坡,就到了果园。园里有桃树、梨树、板栗树、枇杷树等,板栗正挂着果,葡萄架上也硕果累累,二婶摘了一大串紫红透亮的葡萄,我吃着这甜甜酸酸的小水果,看着二婶爬梯子摘板栗,桃宝在树下捡浑身是刺的板栗球,她用石头砸,用牙咬,将嫩黄的栗肉给我吃,她也吃,我们嚼得脆响……
后院是一畦畦菜地,红尖椒朝天生长,冬瓜南瓜躺地长个,葵花向阳盛开……猪圈、鸡窝、茅厕安在西侧。北面倚山,山脚下有一股潺潺的泉水,流经一节节竹槽,叮叮咚咚滴在一只硕大的水缸里,我这才知道二婶清甜的茶水是山泉,母亲说比城里南门井的水还要好喝。水缸旁边,开了一扇小篱笆门,就几根柴木钉成,那是方便邻居也能喝到泉水。
那样一个花草果蔬的院子,只住着二嫂和桃宝,桃宝爸常年在部队。东房的窗前置有石桌石凳,一到清晨,或晚上,石凳上有了些凉,善编草垫、草苫的二婶,往凳上都放一个秸秆垫子,坐着软软的,很舒服,还散发出好闻的稻香味来。这四个座位,像是为我们设置的,四位各坐一方,在那里吃饭、做事,怡然自乐。
第一顿农家饭,就围坐石桌吃的。二婶满院子捕捉那只乌鸡,赶得鸡飞狗跳,隔一道篱笆墙的颜婶从后院赶来,帮忙拦截才捉住,杀鸡水烫拔毛,二婶手脚麻利。双孔土灶下,噼噼啪啪燃着劈柴,前孔架口铁锅用木甑蒸饭,后孔以砂锅炖鸡,炊烟袅袅,正好前头旺火,后头文火,炖得满院飘香。母亲说乌鸡的药用价值很高,“乌鸡白凤丸”就是用它制的,二婶说农家人的乌鸡白鸡黄鸡都是啄野食长大的,不值钱,说着,她将木甑饭端上石桌,循着饭香,桃宝和我扑了上去,看到粒粒饱满晶莹如玉的白米饭,我们抓一团塞进嘴里,烫烫的,可哈哈气一咀嚼,软糯软糯,不要菜,就吞了下去。二婶从兜里掏出颜婶家添喜给的红壳鸡蛋,先让我们解馋。
吃蛋的工夫,四个大花瓷碗齐齐上桌:一碗南瓜花炒鸡蛋,一碗豆豉蒸腊鱼,一碗清炒丝瓜片,一碗板栗鸡汤。我和桃宝人手一只鸡腿,一啃骨肉分离,我碗里黄黄紫紫煞是好看,色艳金黄的是南瓜花蛋,乌紫的是香香的紫苏,我分辨不出哪是花哪是蛋,可能吃出花比蛋更爽口,母亲夸二婶一桌菜色香味齐了,又美味又营养,便细细道来:栗子利肠,健脾胃,补肾气,遇上乌鸡更滋补;南瓜花在医书里有保护心脏的作用;紫苏炒腥味菜,可解腥毒。二婶说乡下人用南瓜花苞炒蛋,是省点蛋,而她混炒给我们吃,是想让我们城里人吃个新鲜,那鱼肉里下苏叶,只为添个香味……那顿饭,我吃得打饱嗝,因二婶用劈柴烧出来的,硬是与母亲煤火燃的味道不同,这味,就是柴火味,农家味。
2
很快,我喜欢上了这个花香果香瓜香稻香药香的院子,只要扭一圈脖子,就可看天,看地,看山,看水,这是城里那个四面住家的四合院里没有的。有人担心吃“皇粮”的孩子入了乡也随不了俗,我不,我一踏进柴门,就成了桃宝的跟屁虫,玩疯了。显然,柴门篱笆院里的放养,远比泥砖四合院里的圈养,更让我快乐。
一晚,我反常,不吃不喝不動弹,母亲给我摸摸额头把把脉,说我发烧了。母亲就怕我生病,尤其在乡下,连个就医的地方也没有。现在想来,很庆幸母亲是在姥爷的药铺里溜大的,并跟姥爷学过中医,所以,她带上了《本草纲目》这部老医书,还有姥爷常用的经典古方及药材来乡下,如柴胡、黄连、麻黄……当时母亲就查方子,去地里扯了把葱,取白段,找二婶要了淡豆豉、生姜,给我煎了葱豉汤,我服下,出了汗,寒气排了,热也退了。
二婶给我小火慢熬了一碗米粥,我推开,母亲就用勺子刮着那表层厚厚黏稠的粥油喂我,我也不张嘴。母亲翻开我最喜欢的连环画《红楼梦》哄我:你看人家宝玉还有他的丫鬟袭人也是病了,他们放下山珍海味,就喝这个米油汤给喝好了,中医管它叫“米油”,这层米油可是咱们百姓的参汤,大补元气哦。母亲还念念有词,我前些天问母亲当时念的是什么,她说:“贫人患虚症,以浓米汤代参汤,每收奇迹。”难怪我一吃下那米油,就来了神,三口两口把那碗米粥给喝了。母亲说二婶家随处是药,地里的、树上的、梁上的、窖藏的,坛坛罐罐里的,如绿豆、赤小豆、蚕豆、石榴、杨梅、冬瓜、苦瓜、玉米须……二婶越听越神奇,说没想到这些五谷杂粮蔬菜水果都是药,她家真是遍地是药了,这源于住过的一个知青,也爱看医书,那些艾草、金银花等野生植物,都是他移植到院里来的。母亲问二婶,这知青是不是名字叫黄精?他妹妹叫黄芩?也下放在这里,二婶说你都知道呀。母亲听父亲讲过这对兄妹是中医世家,要知道,黄精、黄芩都是一味中药名,长辈给这兄妹俩都取个中药名,可见对中医药有多钟爱。黄精去了省城大医院,黄芩也是县中医院的大夫。
二婶指指院墙边一蓬密密匝匝的晚饭花,说这也是黄精栽的。这是一种胭脂红的小喇叭花,总在我们吃晚饭时盛开,像是点亮着许多小火炬,在为农家人的晚餐捧场,且香气驱蚊,难怪我们坐那儿吃饭没蚊子叮咬。母亲说晚饭花也是一味药,学名叫紫茉莉。二婶说颜婶子有一年患了妇科病,就是这个知青用这花儿给弄好的。也正是这红艳艳的喇叭花,让我和桃宝嘴上吹,头上戴,将一朵朵穿起来,一串串地吊在柴门上当门帘,当村民进进出出扫落一串时,我们就以刺耳的哭声抗议。
二婶不太会缝纫,平时只踩个鞋垫子,或縫个脱线。母亲能裁能缝能绣,这是我记忆里最疼我的姨姥姥传给她的绝活,姨姥姥上过民范女校,她参与的《清明上河图》局部湘绣已被博物馆收藏,姨姥姥还酷爱古典文学,如对《红楼梦》里的服饰绣品有着浓厚兴趣,她留给母亲好些老绣片,我和桃宝的荷包、肚兜,就是母亲用这些老绣片缝制的。姨姥姥是姥爷的续弦,人和心善,视没娘的母亲为己出,她满腹诗书,感染着母亲。这是后来我听母亲说的,平日里姨姥姥陪姥爷聊红楼药膳、红楼民俗,姥爷也与她聊些红楼衣饰、刺绣、美食……他们的神聊,不知不觉让母亲迷上了《红楼梦》。
一天,母亲去镇上开会,用积攒的布票,扯回了红绿两种花布,在煤油灯下给我和桃宝做衣裳。先缝好的红花衣服我们一穿上,二婶左看右看,说她家桃宝像个红薯坨,丽宝倒像个洋葱儿似的。母亲指着国画册上《捡枣子的小姑娘》给二婶看,说这个像桃宝吧,多好看呀!二婶一看,说红扑扑的脸蛋像,胖乎乎的身子撑得花衣满满的也像。从此,二婶再也不说桃宝像红薯坨了。桃宝的名字叫桃红,是三月里桃花朵朵红的时候出生的,该是沾了桃花的精气,脸蛋一年四季像朵桃花。
没过多久,屋里多了一幅大照片,照片上是我与桃宝身穿绿花衣、头扎红绸子的半身照,我们笑成了两朵花。在那个黑白照的年代,照片上的颜色都是相馆人工添加的,嘴唇也抹了彩。这张大照片招惹村民都来看。这照片是有来头的,那是我们去镇上赶集,母亲给我们各扯了一对玫红绸子,扎在羊角辫上,带我们上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从那木梯子上下来时,个矮的我们拾到了贰元纸币,原地等失主,等来的是相馆馆长,她说孩子们拾金不昧,以扩一张大照片来奖励。后来我俩跳了《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这支舞,衣着头饰就是照片上的装扮,我们一边起舞,一边想着馆长的表扬,脸上喜滋滋……这舞代表一年级参加公社国庆汇演拿了一等奖。
村里有个五保户奶奶,二婶与母亲时常帮老人洗洗被子衣服,晒干叠好了,我们总是抢着送去;或做了好吃的,我们也争着去送。一次回到院子里,两只小馋猫坐在木墩上吃东西,我舔着一块糖,桃宝啃着一块饼。二婶说我们两脚勤快,原来是惦念老奶奶的那点东西,这是人家给她吃的,却被我们吃了。桃宝说奶奶没牙,嚼不动,她要我们帮忙吃,她还对二婶“嘎嘣”着小门牙,表示自己嚼得动。我发现桃宝发上有饼干碎屑,给她去弄,可我粘糖的手一扒,弄得她头发粘糊糊,桃宝急了,立马洗头,我给她灌水,水却灌入了她左耳,使其嗡嗡作响。母亲得知,先用棉签去吸水,再去篱笆边摘些薄荷叶来捣汁,涂上桃宝的左耳膜,就没事了。
我们喜欢帮二婶干农活,二婶穿辣椒串,我们剪辣椒柄;二婶晒菜干,我们择菜;二婶扒松针,我们扛竹耙,当一前一后走在田埂上时,我一脚踩空掉进沟里,二婶拉我手臂染上了毒疮。母亲用一个茄子,取瓤一块,敷贴在二婶的疮肿处,肿毒就消退了。
这些不花钱却管用的小方子,成了我们缺医少药的农村生活的支柱,连学生娃和村民都受用。
3
二婶没念过书,每次桃宝爸来信,她都要母亲念她听,然后让母亲代她写家书,她说一句,母亲就写一句。说着说着,到了最体己最想说的了,二婶脸就红了,话也说不出口了,以至后来我一想起二婶,就是她这个羞涩样儿,正如母亲说的像个未过门的姑娘,而二婶听了,脸更红了,头更低了,害羞地拉着我红肿的手,涂抹起自制的冻疮膏来,那是母亲教她取老丝瓜烧灰,加猪油调和而成的。
母亲每天从上课、备课、批改作业、家访、家务中忙里偷闲,教我和桃宝读古诗词,她怀着对柴门小院的情感,让懵懂的我们,背了不少柴门诗句,如白居易的“布被辰时起,柴门午后开。”王维的“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岑参的“然灯松林静,煮茗柴门香。”吴鼎芳的“柴门凉气入,风动白纶巾。”往往这个时候,二婶会放下千层底不纳了,跟着一起吟诵,院里书声朗朗,招来篱笆外一圈老少观众。
二婶问母亲《红楼梦》书里有啥,可让她反复看,看得痴迷时饭都烧糊了。母亲就抽空一回一回地讲解给二婶听,二婶听得也痴迷,总在等待母亲下回分解。母亲说二婶如能自己读,那又将是另一番滋味,且常读常新。二婶使劲点头,母亲就教她学拼音,查字典,二婶则成了一名旁听生,一个农妇,不怕孩子笑话,一笔一划学写字,念拼音,学加法,有村民笑二婶是母亲班里的“大学生”,换句话说,母亲的复式班实际有16名学生,包括没到学龄的桃宝与我也在正儿八经地上课。
当桃花灼灼红时,村里来了放映队,晚上在大晒谷坪播放越剧《红楼梦》,小孩子都不知所云。次日母亲捧着厚厚的《红楼梦》给三年级上课,她讲这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红楼梦》,而越剧《红楼梦》,只是这部书中的选节,并简述剧中林黛玉进贾府后的故事,我们一年级的学生也随同来园里赏桃花。桃花树下,母亲讲解着林黛玉写得最好的诗是《桃花行》:“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问有谁知道林黛玉为何葬桃花?一片摇头,母亲说林黛玉与贾宝玉初次见面时,黛玉眼里的寶玉是“面若桃瓣”,桃瓣就是桃花瓣,桃花易凋零,而宝玉想娶的人是他这个林妹妹,可贾府给他掉包换成了宝姐姐,所以,林妹妹葬桃花是在暗示她与宝玉的悲剧……
小班长感叹:“原来树上的桃花,不只是能结桃子啊!”母亲表扬班长会思考。她说这么讲红楼,一是让孩子们能看懂越剧《红楼梦》,二是对这部名著有个启蒙,等将来能阅读这部书了,就会明白曹雪芹笔下有太多未知的文化……当我们追着放映队去邻村重看《红楼梦》时,果真看得明白些了。今天回过头去看,母亲的教学走在了时代前面,林黛玉进府不是后来选入了教科书吗?
母亲说桃花岂止入诗,还可入药,医书里说“千树桃花万年药”,其桃胶、桃仁都是药。我和村娃们就捡过桃核,砸过壳,卖过仁给药商。
到了菊花飘香时,母亲又将《红楼梦》里十二首菊花诗,即《忆菊》《访菊》《种菊》《对菊》《供菊》《咏菊》《画菊》《问菊》《簪菊》《菊影》《菊梦》《残菊》一首一首地在课堂上诵读,并板书出黛玉的《咏菊》,点评为十二首之冠。二婶忽地站起身说她的名字叫美菊,一时,满堂哄笑,二婶也笑,并美滋滋地说:“没想到父母给取的土名字,还能作出这么多的菊花诗来,还能上名著……”课余,她把菊花诗全抄下来,练习“美菊”几页纸,写信给桃宝爸,说她“为随军扫盲”天天读书写字。因桃宝爸军龄一到,二婶是要随军的。
说到桃宝爸,我没见过真人,只看过他穿军装的英武照片,我说桃宝的解放军爸爸好威武,桃宝就学她爸的样儿对我行了个军礼,我问她长大了是不是要当女解放军?桃宝没反应,她眼睛看着我爸,我爸从县城回来休假,正在坪里切牛肉,支书家杀了大黄牛,一早送来的,母亲说“牛肉补气,与黄芪同功”,要他加黄芪给我们炖汤补身体。桃宝连吃也听不进了,她说你爸不当解放军多好,能经常回来。我这才知桃宝想她的军官爸爸了。不过,当慰问军属的一来,桃宝好兴奋好忙碌,我呢,跟随她跑出跑进,跑前跑后,莫名地亢奋……
桃宝和我同年,两个五岁多的孩子闹别扭可是分分钟的事。如打扫院落,起初并排扫,从里边的院旮旯扫往院门口,扫着扫着就调头分开扫,桃宝不让我的大扫帚扫到她家门口去,说那里是她们家的。而“寄人篱下”的我,一点也不马虎,要她别扫我家窗台下,说那里是我们家的。这当口,二婶跑了过来,扬手打桃宝嘴巴,不许她说“我家你家”的,说咱们住在一个屋檐下,就是一家人,会相伴一辈子的。
可我们只住了一年多就搬去学校了。有师生来给我们搬家时,二婶和桃宝不知所措,总在念叨“学校不好住就搬回来”。那个屋檐下,正挂满了鞭炮似的红尖椒,屋梁上,码着黄灿灿的玉米棒,那红的似火,黄的似金,把整个院落渲染成了一幅重彩油画,而这一对纯朴的母女,就站在这油画里的柴门口目送我们。
后来,二婶带着桃宝去了部队。那时二婶能读能写能缝,在来信中她一称一个“晏老师”,桃宝爸也附言,说非常感谢“晏老师”让他家属成了文化人,字典也被她翻烂了一本,她与战友们聊本草聊红楼,还给大家缝缝补补,军营里的这个“嫂子”可受欢迎了!还夹有全家福、与战士们的合影,桃宝的单照背面写着:送给好伙伴丽宝。那天,母亲整天都在笑,并带我去了镇上,给远方邮寄(下转第112页)(上接第109页)一包稻花鱼干,放入我们的母女照,附上各自的话。
若干年后,母亲几位学生师范毕业已回乡教书,学校也新建了一所,母亲这才返城,那一年母亲42岁。我们又回到了四合院,我已成了大姑娘,《本草纲目》《红楼梦》已是我的读本,食疗本草成了我的养生指南,而读红楼,写下了一篓的感慨。我这才明白:母亲当年去贫困乡村的底气,就源自这二部宝典的支撑!一部千草皆药,一部百科全书。正如姥爷说的,母亲可让草变宝;也应了姨姥姥的话:书中有黄金,日子自富有。
只是,我不知桃宝受二部书的影响有多深?那时,桃宝一家也换了地方,我们两家就失去了联系。可我知道,“欲向桃花问消息,柴门深锁碧溪深”,那个无法回去的柴门院子,将是我们四个人一辈子的世外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