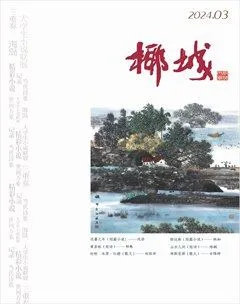遥望冬天
作者简介:王丹,祖籍湖北,现居海口。中学英语老师,海口市作家协会会员。有诗歌、散文若干篇散见于《三峡晚报》《湛江日报》《海南日报》《山东诗人》《思维与阅读》等报刊。
降温了,风吹在脸上干冽且有些寒意了,这南国的城市已经颇有些冬天的味道了。微信里,北方的姐姐告诉我,她那里已经在下大雪了,家里人都窝在家里。老头儿(老公)在听着音乐蹬自行车,挥汗如雨中,女儿在备战雅思考试刻苦中,老妈妈在电脑上玩麻将。她在厨房准备热气腾腾的饭菜呢。冬天就适合缓慢地生活。不论是围炉煮茶,还是踏雪寻梅,都急不得。茶要细细煮才能回味悠长,梅要慢慢赏才能闻见幽香。记得有句歌词这样写:“暮冬时烤雪,迟夏写长信”。我的城市在冬天不会下雪,却适合在冬天想起一些人和一些事。
命运之神把我空投到这南国。几次梦醒,哑然失笑;走在哪里,定在哪里,遇见谁,原来都有安排。也曾在四季的时光里流连忘返过啊;二月春风的剪刀轻抚过我的脸;六月的荷塘也有和小伙伴们头顶莲叶,寻觅红莲的身影。秋风秋雨里也有我们少年强说愁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可这些都比不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带来的惊喜。
故乡的冬天怎么能没有雪。真正的下雪天是不冷的。起初下的是雪子,小小的颗粒状,继而是小小的柳絮状,飘飘洒洒,对于我来说,那是欢喜的事啊。我会去追着那些“柳絮”用鼻尖儿、额头去迎接它,用嘴巴把它藏在心里。有时候我走在雪里,默默地想一些心事,尽量地保持安静。我怕惊动每一朵雪花,从而引起一阵或大或小的慌乱。一些雪任性地落在我的脚下,很快被我碾碎,化成一小摊泥水。一些雪落在柳树梢头,随风荡着秋千。一些雪落在路边的枯黄草稞里,在那里占山为王,引吭高歌。很快,落下来的雪覆盖住了已经润软的或者即将融化的雪,天地之间一片白茫茫了,而我却更生欢喜了。我的父母都是闲不住的人,很多时候家里只有我和妹妹。有时候他们的忙碌让我心慌,让我不安,我像是被遗忘在某个角落。只有在大雪天,大地都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忙碌的父母才能像别人家的父母一样陪在我们身边。全家人凑齐了围坐在煤炉子前吃顿饭。因为小火炉,这顿饭能吃很久,所有的菜都能放进炉子里煮,青菜、酸菜、豆腐、白萝卜红萝卜,甚至过年的香腸。不断地加汤。最后吃得大家都浑身冒热气了才“罢嘴”。
若干年的若干年,识文断字了,才知道白居易的《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
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太喜欢这首诗了,短短20字,有色彩,有人物,有画面,熊熊的炉火,颜色微微泛绿的米酒。这样一个风寒雪飞的天里,在这样一个暮色苍茫的空闲时刻,邀请老朋友来饮酒叙旧。若干年后,当我长成一副伪文艺女青年时,这首诗终于满足了我文艺女青年附庸风雅的心。红泥小火炉再不是吃得肚儿溜溜圆这一个事了。
故乡的冬天总是跟少年时光分不开的。我们穿臃肿的棉衣棉裤,戴厚厚的围巾,个个像大熊似的,却个个轻盈地在寒风里流着鼻涕奔跑欢悦。我们手提火炉去上学,我们在火炉里埋各种吃食。那时有一种百雀羚的雪花膏,妈妈用完后,我们把盒子洗净弄干,在里面装各种豆,黄豆、蚕豆、豌豆,还有花生,然后埋进火炉。不一会儿功夫,我们就把他挖了出来。我们被烫的从一只手里转到另一只手里,最后雪花膏盒“砰”的一声掉在地上。盒盖崩开了,像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豆儿们散落四处,我们不管半生、半熟还是烤糊了,跑着捡起来吃得嘎嘣作响。如今再也没有吃过那样香的豆儿了。
故乡的冬天总是跟年终岁末过大年有关的。我故乡小镇集市是很有特色的,分冷集和热集。逢单日,做买卖的,赶集的相对较少,谓之冷集。逢双,热集,方圆几十里赶集做买卖的都来了,有三瓜两枣都可以卖,如果赶上周日,还能看到很多同学摊主,他们帮着家里卖一些自家产的蔬菜水果。有一个男同学最有本事,他会卖他自己钓的鱼,甚至有乌龟。每每它都会到学校吹嘘一番。最记忆犹新的是跟着爷爷去牛市,冬天冷,爷爷腰间系着围裙,围裙一直垂到脚面,走起路来很是威风,爷爷是帮着别人去看牛的。不知道爷爷是怎么养成看牛的本事的。爷爷会围着牛转圈圈,看牛的牙口,看牛的蹄子,记忆已经模糊,只是记得爷爷打了好多手势。然后老牛和小牛就被牵走了。请爷爷看牛的人会请爷爷“过早”,我也跟着能蹭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猪肝猪血汤。
再也不能在雪天承欢父母膝下了。再也没有那样的热闹质朴的集市了,再也不能跟着爷爷喝热汤了,我们只有将自己藏进回忆中,回忆那些美好的冬日时光。守着一炉火,可煮茶,可温酒,我们在热气腾腾的雾气中与过往撞了个满怀。希望你我都能够度过一个温暖的、不那么漫长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