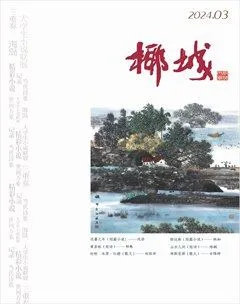迟暮之年(短篇小说)
沈学
嗷——呦——老头披着棉冬衣,颠颠地从卧房出来,打了个长长的哈欠。他的破棉鞋擦在地上发出沙沙声,回荡在冬天的清晨里。这是他一天里力气最足的响动。倘若在以前,老头连续性的起床动静,会被一个妇人的话打破。去厨屋把水烧热!那是来自他床上老伴的指示。但现在世界寂静了,而且快寂静三年了。
此时,外面天已透亮,但屋内还不大清明。老头弓着背,缩着脖,嘴里咝咝吸着凉气。他迈过两扇门来到厨屋,习惯性地拉亮白炽灯。灯泡功率低,才四十瓦,照得房间很暗,兴许是因为冷,房间显得更暗了,可老头常年摸黑,凭感觉避开了所有磕碰。他径直走到火塘边,抄起架子上的黑吊壶,麻溜地驱步至水缸旁,用瓢往里舀满井水。再从墙角掏了把刺杉树叶,抽出火柴呲的一声生出火来。老头褶皱遍布的脸上,这才现出一丝红润的光。忙完这些,老头开始煮饭,将冰箱的剩菜蒸热。流程不多,但动作迟缓,毕竟八十岁高龄了。等他出去喂好窝里仅剩的三只鸡,添好干柴。饭已煮熟,于是他捧着碗靠火塘坐下,慢吞吞地咀嚼起早饭。
老头的牙齿掉了大半,上下颚统共七颗牙齿。当医生的闺女给他装过一副假牙,但他嫌麻烦搁在一旁没戴。他的目光在屋内四处游移,时不时停在某件杂物上,随后盯着一动不动,模糊的印象飞速掠过。老头窝在火堆边,松弛的皮肉塌下来,如同被吸干了水分,骨头也往外突,像是要迫不及待出逃似的。原本瘦削的身形看上去更加干瘪,年纪一大就不抗冻,尽管他穿了四五层衣物,还是冷到不停地伸手烤火。脖颈处的扣子是敞开的,外衣扣子也一多半是扣错的。他很享受这样的随意,又或者是从来无心这样的细节。要说让他感到不快的事,便是胸中那隐隐的落寞,没人再因为衣着天天骂他了。自从老伴走后,老头像是抽空了脊梁骨,啥事都提不起兴趣,地撂荒了,山卖了,牛、鸡、猪也养不动了,如今只打理着几块菜地,和这副日渐衰朽的身体。每天最多的时间就是用来发呆。若是在夏天,有两声蛙鸣,还不至于显得幽清。眼下万籁俱寂的时节,还能发出什么声响呢,无非听听野猫打翻瓶罐,或者冷风扑打窗子罢了。
面前蓬勃着的变幻莫测的火焰,使老头不由想起消逝的往事,他一个劲地唉声叹气,每吸一口气,他的胸腔就塌进去一些。以至于后来家里人同他聊天,他总沉浸在自说自话的世界,不胜其烦地描述起他印象最深的几件事。
对他刚考上大学的孙儿,他跟春天播种一样,不断重复那谆谆告诫,古话说得好,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呢!当年我们乡里有个秀才中举,骑着高头大马经过村里,嗨呀,那个风光唻,啧啧啧……老头每每说到这都眉眼纷飞,面孔显现出一丝与身体极不协调的亮色,刹那间整个人变得容光焕发。但不消片刻,这幅光景便迅速冷寂下来,老头开始倒起苦水。唉,原来,原来我们做了好多好事,到头来还受人欺负。老头说着轻轻摇起脑袋,嘴角塌成一张弓,这里的人呐,一个个坏得很!说罢,老头将目光飘忽地伸向窗户,沧桑的神情停顿半天,干枯的眼睛里似有泪水化开。跟那些上年纪的人一样,老头的耳朵也越来越背,对面的人问东,他答西,直到对面提高了嗓音,他才如梦初醒般拽回话题。片刻后,又开始了他的自说自话,原来我们乡里有个人中举,骑马路过村里……
老伴死后,老头一天里大半时间都坐在家里发呆,按他的话说,赶牛的人没了,干活也没劲了。他不喜欢走家串门,因为三代单传,他在长年的欺侮里变得小心怕事。况且因为耳朵不灵光,嘴巴又碎叨,人家不爱同他说话,索性二门不迈地好。也只有遇上红白喜事,大家才会想起这个活着不多死了不少的老头,迫于需要不得不拉下面子请他出马。老头是村里唯一受过老式教育的人,念过私塾,会写对子。在无可避免的人生大事上,老头像是找到了续命的丹药,他享受着别人低声求他的快感,如同他是当年那个纵马疾驰的举人。
老头正意兴盎然地回味着从前,忽然门外有女人在喊。
海大哥,海大哥,你在屋里没?
海大哥——
女人往屋里走,声音越来越近。老头在烤火,神驰在回忆里,前两声没听到。直到女人走进巷子里第三声喊,老头这才灵醒,他扭过头来,吊着嗓子高声问,谁呀!
是我哦!女人答道。老头仍没辨出是谁,他正疑惑,女人进门,见是村头老杨家的堂客。老头立刻站起身,收起刚才的愁色,递出一副和煦的笑容,哦——是你啊!来坐,坐,有什么事吗?他转身去拿椅子,又给女人倒茶。
我不喝水!您别忙了,有个事想找您老人家帮个忙。老头倒了一杯茶水,递给女人,女人接过水说,太客气了海大哥!是这样,我们家杨鹏月底要娶媳妇,您看那天得不得空帮忙写个对子。我们都没读什么书,又不想请外面人。想想请您最合适了。
老头听明白了个大概,连声应承了下来。问说,这是好事!具体哪个日子呀?农历二十八,您得空的話二十七上午过来,女人喝了口水,利落地回道。那就这么说好了啊!临走时女人又补了一句,那您老人家那天上午记得过来,中午就在我们家吃饭,到时我就不另外来请啦!老头连连点头,说好,跟着把女人送出巷子,人走远后他又回到厨屋,端来椅子坐下,得意的笑容挂在脸上,挂了许久。现在,老头的内心无比满足。这种被人需要的满足,一扫年老力衰的阴霾。他觉着自己还有几分大用。想到这,他感觉火塘里的火苗更加蓬勃了,皱巴巴的脸也随之舒展开了。
老头给村里写对子,不像后生们传的那样性情古怪,可也不是个什么忙都乐意帮的。以前他去别家帮忙,事毕,人家只给了两包差烟,纯属是打发人。这样不懂礼数不知趣的,他帮过一次绝不再帮。但老杨这个忙还是可以帮的。老杨头比他小几岁,多年前两人因田地闹过不愉快,好在他有个堂客明事理,近几年二人关系有所好转,他堂客发挥了莫大的作用。老头打算借坡下驴,能与人为善,何必得罪人呢。活到这岁数,也逐渐想开了,已经半截身子入土,不愿和人去争。火焰在一堆柴火上炫丽地跳跃着,老头开始琢磨起那天该写些什么。他在纸上写写画画打草稿,卡住了,就去电视机柜子底下,找那本《实用对联大全》。
平日里,他没事时就将那本书拿出来翻,翘个二郎腿抱着书,就着太阳啃半天,从白天坐到日落。这是他唯一的爱好。过路的人来来回回,都忍不住甩上老头两眼。每年过年贴春联的时候,两幅大门联都被老头提前写好。不管孙子最后按不按他的意思写,老头总要细细描绘字句背后的深意,让他记住真正的春联是什么样的。说到用心巧妙之处,不免洋洋自得起来。他把邻里的恩怨诉诸在纸上,供外人品议,维护着一个老学究最后的倔强。很快,月底的婚庆对联就出炉了,老头在初稿基础上修改几遍后,誊抄在干净的草纸上,夹在书里。
二十七号这天,老头早早起床,简单吃了个饭,便开始了着装。他取下衣架上的棉帽,换了身像样的行头,把那张写着婚庆对联的纸条揣进兜,还特意用电动刮胡刀磨了磨脸。临出门,没忘捎带上那瓶清风牌墨水,和一支开了叉的羊毫毛笔。外面寒风簌簌,老头佝偻着背走在村尾往村头的水泥道上,左手自然下垂,右手习惯性插在腰间,像一轮移动的纤细弯月。一会,望望沿路人家新建的房,一会又站住脚,望向远处荒芜的庄稼地。拐过几道弯,上下两处坡,很快,老头出现在老杨头的家门口。院子里五六个人乐呵呵地忙着,吹气球的吹气球,挂彩带的挂彩带,老杨头的堂客正在指挥布置,婚礼现场初具雏形。院墙一人半高,砌得很气派,铁门贴了两个大红的囍字。门口两座石狮雕饰威武之极,老头有些好奇,便凑近端详起来。女人抬眼望见老头,忙笑脸上前迎:海大哥来了,辛苦,辛苦。
老头听见女人的声音,这才把视线从石狮子上收回来,晃着身子继续往里走,一边走,一边夸赞,嗨呀,还是你们有本事,这装修的,一看就花了不少钱!女人说,没有没有,喜事,该花还得花,哪能省一辈子。您今后要少干点活,多享享福才是。老头站定,旋即眼神暗淡下来,叹气道,是呢,也想通了,一个人做多了没劲儿!女人扭开头,要一个年轻后生倒水,拿纸,摆桌子。女人又吩咐后生给老头裁纸、镇纸,之后去了别处忙。老头直直走到桌旁,摆弄起他的家伙什儿……
老头一边折纸,一边和女人核对信息,折好纸,老头用毛笔蘸了蘸墨汁,废纸上画了两笔,没啥问题。不一会功夫,地上黑字红纸一张张铺开了。有大门和小屋的对联,有拜天地的流程词。这些红纸黑字将在墨干后贴上对应的墙面,见证一对新人的喜结连理。老头力气的确不比从前了,写完一副联要休息会。他从婚姻的热烈中感到自己强烈的衰老。中午女人看他一人可怜,非要留他吃饭,并嘱咐说第二天不再上门喊他了,直接过来入席,喝酒。做红事执笔者有这点好处,收两包好烟不说,还能管两顿饭,最重要的,是对人一肚子笔墨的恩重。老头不抽烟,只爱喝酒,这顿酒是对自己能力的认可,更是一种尊重。他必须得来。
婚礼这天正午,院子内外都是人,跟沸腾的锅似的。即便出来太阳,还是冷到磕牙,众人在欢笑中,簇拥着新人完成了仪式。而老头像冬天河面的一块浮冰,静静地坐在桌角下,融而不化,有人打招呼就挥手或者点头致意,倒是孩子们的搞怪,令他傻乎乎地嘿嘿笑起。这个时候,他和他的红纸黑字一起被众人忽略了。但老头习惯了这样的忽略,红白喜事一年几趟,无非是笑一笑哭一哭。他见过了太多极端的时刻,在这如戏的人间,老头像个局外人,若有若无地穿梭着。他知道自己喝酒坏事,酒席上只喝那么小二两,点到为止,有人劝也顶多不过半斤。兴许是出于和众人的话不投机,他总赶在大家意兴阑珊前,从乱哄哄的工棚里走出,蹒跚地出现在另一处黑夜。
开席前,老头猛一回头,望见那个胖子杨红也来了。他脸上笑嘻嘻的,看上去油光满面,搁谁都热切地打招呼。老头下巴一沉,立刻黑下了脸,心中又气又怯。三年前,就是他明目张胆砍自家的树示威,也间接导致了老伴的重病。奈何老头斗不过他们四兄弟,只得吃下这个哑巴亏。现在他想躲,懒得和那帮人对眼,本想拣个角落坐下,吃完就撤。谁知被老杨头的堂客瞅见,客客气气叨了一顿,女人领他到堂内坐下,还嘱他等会好生喝酒。虽然他觉得这顿饭值得吃,但杨红的出现让他几乎没了兴致。
桌上,都是自顾自吃饭的人,许多男人女人都眼熟,就是喊不出名字,后生们跟麦子一样,一茬一茬地长得很快,三两年就不认识了。老头分不清谁和谁是一家的,深知自己说话不怎么讨喜,索性自己斟酒自己喝。有懂事的后生站起来给老头敬酒,老头见状会意,拿起酒杯,往桌上顿了顿,送出去又收回来,美滋滋地抿上一小口说,好好好!喝!酒喝到一半,老头听见谁在人群中高声喊,海哥!老头怔了下,循声望去,一个老头笑呵呵端着酒杯,朝这边迈着大步,个子高高的,年纪不小。老头一眼认出来他,手往空中一挥,猛然惊喜道,你啊!你什么时候来的,没看见你。说着两人相拥着坐下,碰起了酒杯。这人是老头的多年旧友,当年私塾的同学,姓张,住城里,一年多没见了。他比老头小几岁,但命好,借老丈人的势谋了一官半职,官位到头退休后,没事写点诗词歌赋,还送过他自印的集册。虽说年纪已过古稀,但那副精气神很好,完全不像七十出头的,老头很是羡慕。闲聊才知道,新娘是他娘家的表亲。
身子骨还健旺吧?我还说等会落你那一趟看看你呢!张老头坐下来,揽着老头的肩膀,贴近他耳朵大声说道。
啊?还可以,就是上次摔了一跤后,做不了重事了。老头有些迟钝,也跟着提了嗓音。
年纪大了,就别往山上跑了,不比年轻的时候。平时你的子女应该经常回来看你吧?
老头皱起眉,苦笑道,看,也给钱,可我哪能要他们的钱,一家一当,都不容易。
是呢,我们都是老骨头不中用了,子女们的事也操不上心,照顾好自己也是给他们省心。张老头听出了老头话中的无奈,知道继续问下去不妥。于是岔开话题,扯起陈年旧事。扯到兴起处,咂摸上两口。一来二去,半斤酒下了肚。老头脸上开始泛起红晕,呼气满是酒味。俩老头酒喝到一两点,都有点喝多了,靠在一起握住手摇来摇去,往事拉来扯去讲不完。这会宾客也走光了,其他桌的残羹冷炙也都收拾干净了,只剩这一桌杯盘狼藉。老头还想拉着张老头要去家里坐坐,尽一尽地主之谊,但被张老头婉言谢绝了,他说这回有事,下次,下次一定。老头抬起眼皮看了看,是有一辆黑色轿车在外面等他。刚刚喝酒的间隙,老张的确接了个电话,听语气不是啥妙事。老头见状也只好作罢,于是两人依依不舍地在村口分別。
刚还比较明朗的天,这会已经转阴了。太阳恢复了原来模样,畏畏缩缩地躲在云层里。山谷有股冷风扑来,有些凉爽。剩下的驼背老头一个人,开始沿着村道往回走。很久没喝这么多了。因为喝了酒,老头浑身燥热。他感觉脚下轻飘飘的,步子摇摇晃晃,像踩在一块猪肉上。视野内偶尔出现一两个不明容貌的年轻人,他老了,很难把他们准确归集到某个熟悉名字的底下。一年又一年的婚丧嫁娶,使得村人模样变化很快。现在,他只觉得这片村庄陌生,陌生不是因为新楼房的建立,而是耕耘一辈子的田土到头来失去了他的控制,自己仿佛是迟早要被驱逐的人。想到这,老头心头泛起阵阵凉意,像是风从口鼻钻进了身体。他朝路边咳了两口痰,路上见谁都没打招呼,以比平时更快的速度回到了家。
他在门口的竹竿里掏钥匙,掏出来拧开堂屋大门后,一把跌坐在竹木椅上,随后神情疲倦地望着客厅内的陈设。电视机因为受潮已经开不了了,沙发被一片防尘布蒙了起来,墙上挂着几幅亲家母送的风水画。这栋偌大的楼房现在只剩下他自己。不,还有墙角那方灵桌,和灵桌上的老伴。老头想起了那个爱絮叨的老伴,她就是在那个东北边的小房间咽气,在那方灵桌的角落被装进棺材,从此老头失去了他生命中最后的热闹。往事如潮水涌上来,特别是在喝了酒后,像开了闸,老头眼眶已经湿润了。
他站起身,关上门,一摆一摆地往那个角落挪。刚挪到桌子跟前,便呜哇一声哭了出来。他用他深陷的眼窝,再次端视起老伴的相片。照片里老伴是灰色的,惨淡的面容勉强挤着一抹笑,眼神凝重地望着桌前的老头。这是她病重之际,儿女仓促给照的。老头在那低垂着头,想起从前两人拼命三郎的日子,为了不落人后,建这房子,两人没日没夜地挖土,挑担。如今大厦建成,她却撒手而去。老头越想心里越堵得厉害,嘴巴里开始自言自语,好人没好报,苦了一世,哎,到头没享到福!你要是没走,日子多么好过哇!香炉里插着三线根芯,香药已经燃烧殆尽。老头将他那枯树般的手臂搭在灵桌上,呆坐良久,不断悲叹。恍神半天,老头才想起,自己吃饱了,老伴还没吃呢,于是他便伸手够香,数好三根,颤颤地用火机点燃,还没等插进香爐,泪水又涌了出来。老头的泣哭让整个客厅有种苦悲的热闹,仿佛又回到了老伴离开的那几天。
老头窝在角落里恸哭,缩着身体像个孩子,直至委屈泄干净了,他才直愣愣抬起眼皮,沉重地看看地上,又看看桌上。泪水已经冻干在脸上。可能酒的降解使他恢复了一部分清醒,他擤了把鼻涕,情绪进入低潮。他回想今天的遇闻,想到精神的张老头,心里生起些许不忿。
当年一起上学,自己都读四书五经了,而他大字不识一个,《三字经》都背不熟,最后硬是靠岳丈起了家。而且生了三个儿子,还都有出息,一个在财政局,一个在教育局,一个在部队,去哪都风风光光。自己的儿子,就这么一个,还没考上大学,复读吧,中途偷摸辍了学,跟人修冰箱空调去了,差点没把家里气死。这些年老头很自责,当年没贷款买个座位。又嗔怪儿子不争气,平日里没事就嘴痒,动不动揭儿子伤疤,儿子自尊心又强,以至于这些年父子俩一见面就吵吵。严重时还因此动了手。三代单传本就受人欺凌,儿子还动不动要挥拳打死老子。作孽啊!我要去喝农药,死了一了百了!老头在一次冲突中,歇斯底里地嚎啕道。那阵仗着实吓坏了小女儿,于是她赶忙上前好言劝慰。
老头有两个女儿,一个摆摊卖水果,一个在乡医院当医生,也就小女儿贴心点,老伴死后,就她时不时回来看看,塞点钱,买两件衣服。比起人家,哎!张老头还邀他去城里坐坐,老头自觉脸上无光,总倔着性子不肯去。
老头低落的情绪消退一些后,起身跌跌地往卧室走,脱下棉衣棉裤躺床上去了。他的确有些累了,只想在黄昏来临前睡上一觉,现在他有这个权力了,没人再揪他耳朵干活。每回喝多了酒,那些业已消失的旧日便重新浮现,令他在虚实难分的世界里苦不堪言。想不通的事还是想不通,不如睡觉。他把那部老年机放在枕头旁边,盖上棉被,棉被即使有三层,但仍旧很冷,他有些发抖。可他还是很快就打起鼾来。
黄昏时刻,老头再次醒来。他坐起身,眯起浑浊的眼,扫视着这张老式雕花大床,望见身边空落落的枕头,老头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无声的悲凉,这种凉并不直接来源于天气。很多次,他和村里老人聊天,半开玩笑地说起,自己倘若哪天一命呼呜了,被人发现尸体都见骨了。事实上,这种担忧不无道理,老头住在村尾,离最近的邻居还要隔上一座土丘,另一边则是没有人烟的野山。平日里没有客人,正屋大门紧闭,侧屋也几乎不起灶火,小巷的门,被邻居建在路边的储物房挡了大半。如果没有人上门特意找,谁也不会关注到老头的死活。
老头心念一沉,忽而头颅一阵晕眩。他东摸西摸,摸来枕头边的手机,毛糙地按了三回才开了锁,点开红色的电话键,摁响了最上头的号码。这是孙子教他的,不会找通讯录就摁最上面的电话。
下午五点多,正在上班的小女儿接到电话。对面传来老头虚弱的声音,秀儿,我,我怕是不行了,你,你回来,我这有点钱,你们拿去,分了吧。听到这小女儿脑袋轰地一声响,像被浇了一盆凉水,浑身湿彻。爸你怎么了,别吓我,我们马上回去,你撑住!她急忙询问道,还差半小时下班,但也顾不得了,她立马打电话给老大和老二,要他们一齐赶回去处理。老大老二接到电话抛下手中事,马不停蹄往回赶。消息来得太突然,老头的儿子脑袋嗡嗡作响,拿着扳手的手下意识地垂了下来,耳朵瞬间什么也听不见了。老头子上星期还能吃能喝,怎么就……虽然有怨气,但说到底是亲爹啊!何况娘走了,屋里头有个人看家,总比空落落的要好,回去还能有点热乎气。几分钟里,老头的儿子原本复杂的心短暂地通透了。父子间此前水火不容的琐事,在死亡面前忽觉轻如鸿毛。
老头的儿子感到喉咙干涩,像被堵住一样,几乎说不出话来,粗粗洗了个手,便快步赶起了路。寒冬腊月,天气本就阴凉,妹妹的这个电话无疑令他雪上加霜。三年前,在娘弥留之际,他从外省出差赶回来,也像这样风尘仆仆,差点没赶上见最后一面。
小女儿离得近,率先赶到家。外面看,屋里面灯是亮的,没一点声音。她着急忙慌停好车,一进门就爸、爸地喊,声音里夹着微微的哭腔,两鬓的散发垂了下来,都来不及拢。当她疾步闯到偏屋的厨房时,只见他那奄奄一息的父亲好生坐着烤火。她的脑子瞬间凝固了,跑过去检查了眼睛,又翻了翻手掌,见老头面色没有异样,穿戴也十分正常,顿时就明白过来,这是老头导演的一场戏。
她如释重负地一阵埋怨,你发什么神经呢爸!把我吓到了。方才的急切化作了一滴泪水。她抬手抹了抹眼角。小女儿恰到好处的怒火,不仅是老头迫切想看到的,更释放了自己内心悬着的胆,也是对死神未至的最强证实。老头健在,胜过一切。老头见小女儿这般手足无措,张开嘴仰头哈哈哈笑了起来,一副阴谋得逞的模样。他摆了摆手说,我现在没事了,刚才我以为要死了。小女儿虚惊一场后抄来把椅子,在老头跟前对面坐了下来,刚想打电话让他们不用来了,但他们已经都陆续赶到家门口。这样的热闹很少见,也就年底有那么两回,但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每年年底,老头都趁天晴把被子拿出来晒,就是为了过年他们回来住两天。原先他们还能住个一晚上,现在日子殷实了,出行过于方便,家里反而成了灼人的热灶。每年吃完晚饭,他们都一溜烟功夫回了城,片刻都不耽搁。
老头的儿子急步跑进来,手里紧紧捏个手机。大女儿也殷殷地喊着爸,神情不安地跟了来。见屋内的老头好端端的,精神抖擞地和小女儿聊着天,都霎时瞪直了双眼,傻愣地呆在原地,额上的细汗里,反射着白炽灯微弱的光。小女儿先开了口,解释说老头没事,他故意这么搞的。又扭过头交代丈夫,把车后座的东西拿下来,等会带老头一起去城里。老头的儿子见老头活着好好的,木了片刻才松下劲来,很快又恢复了上次冷战的模样,继续生起暗气来。老头的无理取闹在他眼里并不新鲜。他本想发脾气来着,莫名忍了下来,他知道这会儿不能言语相激,怕老头真想不开。于是目光旁移向屋内,发现暗得不行,才想起拉亮另一盏更亮的灯。果然,又是一地的碎枝烂叶,桌台上还摆着没洗的碗筷。他的洁癖无法容忍这一切。也是为了避开尴尬,老头的儿子迅速地拾掇起屋内卫生,比以往更加麻利,里里外外扫完地,又将铁桶里冷水泡僵了的衣服倒出来,将竹竿上穿过的衣服拢在一起,丢进洗衣机。大女儿见老头安然无虞,倒也没表现出多惊讶,她打小性子就冷。她大口呼喘着气,叉着腰在那低声嘟囔,真是个老糊涂,没事乱打电话。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件事成了老头的口头谈资,每每说起,他眼睛里都闪烁着晶莹的光。他神秘兮兮地同孙子坦怀,其实当时我是故意那么做的,谁让他们那么久不来看我。孙子知道他的小算盘,于是狠狠白了他一眼,又怜又气地怼他,你个死老头子,喜欢没事找事。
果真应了那句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虽然用在这不甚妥当,但也足够贴切。自打装死事件后,老头所受的待遇就升了级。因为他死活不愿进城,所以隔三差五,只能几个儿女轮流来送饭,洗衣。老伴死后,几个儿女把老头接进城去,换着每家住过一段日子。但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他感慨说住女儿那不方便,女婿不够亲,比不上儿子。可唯一的儿子呢,脾气又不好,在家说话跟打雷似的,嫌老头不讲卫生,老头如坐针毡,也不敢出声,接话就要挨训。后来待着实在受不了了,就吵着闹着执意要回乡下,哪怕吃不上饭也要回去。
儿女们无奈,也拗不过,只好遂了他的愿。但这个倔老头只会逞嘴上功夫,又不會做饭,又不会洗衣,一人在家总归是个疙瘩,于是他们商量好轮着送饭和打扫,谁去了就拍个照片发在群里,省得去重了。起初还有些怨言,直至近年来村里噩耗频起,下乡吊唁的次数明显变多。他们兴许是意识到了某种迫近的事实,开始予以老头更多的宽容和照顾。
因为害怕意外,小女儿花钱在网上买了个摄像头,安在侧屋的外墙上,能对话,摄像,摇头,远程监控老屋的一举一动。客厅坏掉的电视机也换了大屏液晶的,老头喜欢看戏曲节目,但因为不会按遥控器,所以一个人看不了。乡下湿气重,电视很容易受潮,一受潮就死机,修过一次又坏,最后老头索性不看电视了,宁愿坐在外面晒太阳,对着旷野发呆。这种状态一直伴随到他的耳朵完全失聪,而他此前不迭的闹腾,更像是年迈后的某种回光返照。
这天,寂静很久的家庭微信群里突然有了动静。小女儿上传了几张照片,是老头在家的实时录像截图。图像很模糊。群里半天没人吱声。视频画面里,老头裸着那副皮包骨的上身,坐在门外的小椅子上乘凉,和以往没啥不同。黄昏从四下杀出,即将在众人眼皮底下吞没老头。天色暗了下来,而他仍旧不动,视线直直地盯着某处,像是快要肉身成佛的样子。群里的孝子贤孙们无心关注,或者不知道老头到底在看什么,在想什么。只有老头知道,他所望向的那片山坡,是老伴的长眠之地,更是他将来真正的容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