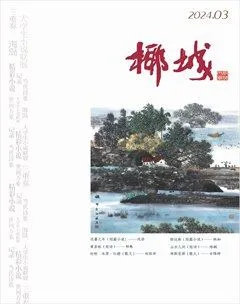小小说四题
作者简介:安谅,上海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经济学博士。发表中短篇小说、微型小说约千篇,著有《阳台上的微笑》《你还有多少童年的朋友》,《安谅微型小说精选》,“明人日记”系列《你是我的原型》五辑及精选本等小说集等,另有多部长篇纪实文学,音乐剧,话剧等作品,作品被广为转载。并有多本英文等译本。获萌芽报告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奖,年度大奖,双年奖,中国微型小说年度优秀作品集,上海作协年度优秀诗歌集奖等数十种奖项。
回返童年
明人和三位退休老友约打“惯蛋”。
老苏说:“那和小时候常打的上游牌玩法差不多呀!”“是呀,当年夏夜在路灯下打,谁输了得脸上画一道墨,有时还得在耳朵上夹木头夹子呢!”明人笑道。那孩童时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
“咦,你怎么想起重新玩起这个了?你之前从来忙忙碌碌,惜时如金的,连和我们吃个饭,喝个茶,都难得一见,来了也是屁股还没坐热,就又告辞了!”老黄诧异道。
“不是现在卸任了,空闲一些了吗?再说,打牌是锻炼脑子的好办法呀!到了这个年纪,不能让脑子太闲了!”明人看着这几位老友说道。
“这倒是,我们邻居老人家当年就爱打牌,打桥牌,所以八九十岁了,脑子还挺好使。”老谢毕竟是位老机关了,开口就显高度。
“哎,我看你看电视,选的都是海外高清原声的片子,你是在学英文吗?”老黄又问明人。
“我也是想练练脑子呀。读书那会学英文,有基础的,也有专业的,可工作三十多年极少用到,现在这样,也是一举两得呀。”明人停顿片刻,又说:“有一种说法,说老年痴呆症,有一种原因,说是曾激活过的脑神经,之后很久不再用了,这部分脑神经,或叫大脑神经元细胞便容易变性和坏死,最后失去正常思维能力。我也未做深入了解。反正,这么回头再学习,总有好处。”
老苏鸡啄米般地点头道:“对,对,对!美国那个里根不就是老年痴呆嘛,年轻时做演员,背台词,到进入官场之后,便用不上了,脑神经就坏得快了!”
“哈哈,这老年痴呆好像有基因突变之故,也与高血压或者缺氧、缺血、免疫力下降有关,非你们所说的这般原因吧?”老黄是大学教授,虽然学的是历史系,但还是他们老友中,属于博学的一位。大家有些哑声。不过,老谢很快驳斥道:“老年痴呆至今还没法治疗,说明还属未知领域,谁能保证那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我觉得明人和老苏所说的说不定是根本。你们没见包括里根在内,那些多聪明的人,不少都患了此病,呜呼哀哉了!与其担惊受怕的,还不如像明人这么预防些,至少也是自己尽力过了!”
老谢还下定决心地说:“明天晚上我就开始讲童话,念古诗,睡前说给小外孙女听。我小时候真是读过不少呢!我也怕这部分神经元细胞,快退化了!”
大家又沉默片刻。只听老黄大声提醒了一句:“好了,别多说了,老苏该你出牌了!”
正愣神的老苏像从梦中惊醒,他哦哦地连忙从手间抽出了一张单牌。
这牌局的一个多月后,他们又凑在一块打牌。这回是在老苏家。老苏的太太是山东女子,家里的大小家务历来都是她张罗的,在圈里有名的贤惠。她很高兴老苏的老友来家。他们唯一的女儿,在澳大利亚定居了。老苏太太忙着给他们沏茶,端水果。大家打着惯蛋,闲聊着。
老谢说,他为小外孙女讲童话古诗的时候,发现自己脑子活络了许多。
老黄说,他在家里做弹弓,叠纸飞机,还制作了一台幻灯机,本来手木木的,一个月下来,灵巧了许多。他说当年就是学校兴趣组的积极分子,玩过航模飞机,他这几天正准备制作呢!
明人惊叹道:“都一朝返回童年了,真可记可述呀!”
他们瞥了老苏一眼。只有他没吭声,理着手上的27张牌,仿佛很投入。
老苏上厕所的片刻,他太太过来坐了一会。她低声但神情不无焦虑地对大家说,她发现老苏最近一段时间行为怪异,她怀疑老苏是不是已患老年痴呆了 。
她刚要详细叙述。老苏已解好手,出来了。她闷闷地走开了。
待老苏坐定,明人似乎是随意地问道:“看来,各人都有各人的招术,咦,老苏,你没有什么行动吗?”
老苏笑了笑,说:“真不好意思说出口。我是半夜爬起,要在院子里淘泥土,捏成一只只圆柱体。再想办法打成几十只孔。堆在院落一角,还用塑料布遮挡着。”
“你这是砌砖吗?像当年备战备荒吗?”老谢猜测道。
“我看,倒像是在做什么苦菜饼,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和家人学做的吧?”老黄又提出了另一个版本。
“煤饼!你是在做煤饼!”明人忽然顿悟,高声说道。老苏的太太闻声,也走了过来。
只见老苏轻轻点了点头:“当年家里用的煤饼,都出自我手,白天上课,半夜里做的,是和我爷爷学的。现在几十年没做了,怕这部分神经痴呆了,就恢复如常吧。可惜找不着煤,家里也早用天然气了,就当是每天的保健操吧。”
“啊,你原来是这个意思,我看得都吓坏了,以为你是脑子出问题了,梦游着,连喊都不敢喊你……”老苏太太手抚自己的心口,喃喃有声。
沉默了好一会,大家都放声大笑起来。那笑声像是童年的气息,欢畅而透亮。
薄薄的楼板
在机关工作的明人,从早忙到半夜,邻居老葛平常见到的少。这天吃了早餐,出了门,在走廊的电梯口撞见了老葛。两人打了招呼,明人问老葛:“这么早就去学校了,上午有课?”老葛在一所高等职业学院任教,平时除了上课,空暇时间多,他的业余爱好有不少,玩得尽心,明显比明人活得滋润。
“上午没课,去二手房市场,想搬家了。”老葛平静地回道。明人倒是被捅了一下腰眼似的,陡地一惊:“怎么,你要将这里卖了?”他至今记憶恍如昨日。好几年前,老葛托朋友找到明人,说他想在这城东找个房,最好是高层的。登高望远呀。他因老宅拆迁,从市中心被安置在了城市边缘的一个新城,多层住宅,上班路途太远,很不方便。城东位置比较合适,而且房价也能接受。
明人听说隔壁正巧有位业主要卖房,当年买房就是为了投资,看架势,这地段的房价也涨到顶了,他就想出售了。房也是一直空着的。明人将这信息告知了朋友。老葛后来就与该业主联系上了,经过看房,讨价还价,老葛以不菲的价格,拿下了这套房。新城的动迁房自然挂脾出售了。老葛还挺感谢明人的,即便他只是及时提供了消息。明人倒觉得这售价过高了,可看见老葛欢欢喜喜的样子,也不多说了,他欢迎他成为自己的邻居。他们偶尔在周末还串串门,聊聊天,也是新邻居,好朋友了。不曾想,老葛竟准备卖了此房,好像还拿定了主意。
随着电梯的下降,老葛说:“这我住得太不爽了,没想到这高层住着,比我那动迁房更磨人! 雨天我在家里客厅跑跑步,楼下就来敲门了,说我蹬蹬蹬地跑,等于踩在他们头顶上,他们被震得头晕,建议我最好到走廊上去跑,走廊就这么点空间,怎么跑呀!还有,您知道,我喜欢听音响,买了一套高音质的音箱,就开了一点点声音,楼下又提意见了,说太吵了。天花板都在抖动。我特地买了避震器,垫在音箱下边,他们还说声音太大,投诉了物业,并让我每天早晚和双休日不要开启。在这时间段一开,物业立马就打来了电话!
还有,你知道的,我在阳台内侧,装了一个养鱼缸。有一回,清洗时,不小心泼洒了一地的水,楼下又来抗议了,说有水渗进了他们的墙壁,我下去一看,是有一摊水珠在他们的天花板上,不时地滴落。我只能找了物业来帮忙,维修费自然是我付的。还把鱼缸干脆撤了。
这楼板太脆弱了。这还是有点档次的楼盘呢!这个不行,那个不能干,我呆在家,越呆越傻了!连我太太都说,这高楼像鸟笼,更像囚房,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家家门户紧闭,却连声响都不能大,多无聊呀!
哦,我还幸亏有您这样的好邻居,好朋友。可您也太忙了,碰不上你呀!”
老葛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出了小区的门口了,他还想继續说着,明人抱歉地说他得赶路了,争取这几天找时间和他再聊聊。他转身时,看见老葛嗒然若失的神情,也有点心情不畅。大概,当初自已就不该提供这房源信息的。他估摸着,这楼板确实薄薄的,应该比几十年前的老公房厚实多了,可老葛他为何还不满意呢?住着还是人情。
工作一忙,他又忘了老葛的事。是几天后周末的一天,他在家,听见走廊里动静很大,家人告诉他,是老葛在搬家。他吃了一惊,咋这么快呢,他走出房门,找到正忙着指挥搬家具的老葛:“怎么,新房已买好了?这么急!”
老葛抹了抹额上的汗说:“我可惜老宅被拆了建高楼了。哦,我将这个屋子租了出去,自己租了近郊老镇的一处农民房子。那里挺像我当年的老宅的,两层楼房,有个小院落,虽然很一般,但安安静静,邻居互相之间也你来我往的,挺和美的,我知道今后怎么放音乐,唱歌,跑步,都没人会有意见。就是离我学院远了,好在有地铁,转两条线,就能直达。欢迎您来做客呀!”
明人向他表示乔迁之贺。心里想,这老葛是回归呀,城里的高楼并不适应他。那一处接地气的简陋的民居,方是他心灵安顿的地方呀!
他得找时间,以一个不合格的老邻居的身份,好好去他那里坐一坐,聊聊这薄薄的楼板和人情冷暖呀!
老郑的司机
老郑是明人的一位老同学,典型的学霸,理工男,从一家国企下海组建一家名曰星空的科创公司,狠命地投入,他头发白了,人消瘦了,但公司的业绩也在同行中崭露头角。他的司机老邱,比他年长十来岁,跟了他好多年,既是专职司机,又兼做各种事务。
说起来,还是好多年前了。那天,两位老同学从外地来出差,特意看望了老郑。老郑就请他们到自己家吃便餐,还叫上了明人。老郑的太太陪女儿去加拿大留学了。掌勺的竟是他的司机老邱。炒西兰花、清蒸鲈鱼、四喜烤麸、红烧素鸡……虽都是些家常菜,但吃得挺入口,特别是一碗红烧肉,一半是百叶结,色香味都很诱人,老同学都咂咂有味。最后上的炒河粉,看着晶莹剔透,放在嘴里既软滑又爽脆,满满一大盘,都被扫荡干净了。
老邱端菜上桌时,大家都不吝赞美之词。都说,老郑找的司机好,两用人才呀!
老郑只是笑笑,也没多说什么。
饭后,老同学吵着要打一会牌。只有四个人,两位老同学说就打惯蛋。这比当年读书时打八十分,要有趣刺激得多。明人前不久写了题为《惯蛋》的小说,之前曾集中操练了一阵,能上场打打。老郑则说他不太会打,你们说说规则,我试试吧。两副牌试下来,证明老郑说的是实话。他看见司机老邱己收拾好了饭桌,便对老邱说:“你来打吧。我没这实力。”他转脸又对老同学说道:“我司机能打,让他替我吧。”
老邱擦洗了手,笑微微地坐在了老郑让出的位置上。他长得粗壮高大,头发乌黑,不薄的眼袋透露了他快奔六十的年龄。他轻快地理好牌,该出手时,果断利落,该相让时,丝毫不动,静观全局,像是把握着自己的方向盘一般稳当。他与从未合作过的明人,配合默契。他们连续几次将对手双双拿下。明人和两位老同学对老邱啧啧称赞。老郑在边上观战,抿一口茶,脸上含笑。
这一晚,两位外地老同学兴致甚高,虽败仍然兴奋。不是明人喊停,说是明天还有会呢,这场牌打个通宵都有可能。
这一天,老邱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不久,老郑公司碰上了一点麻烦事。他的一位客户不讲人情,死乞白赖地纠缠老郑,有一回,还差点大巴掌甩到老郑的白皮嫩脸上,是司机老邱一把箍住了他的手腕,让那客户动弹不得。老邱眼珠子瞪着他,那客户最后还是灰溜溜地走了。
有一阵子,明人碰到老郑,看他是自己开着他的那辆宝马车,便问他,你那位司机老邱呢?
老郑垂了眉,显然有些不悦:“他跳槽了。他觉得他有更大能量,不开车,去做一家私企的行政主管了。”
这对老郑来说,确实可惜了。明人只得劝慰道:“人各有志,不必太挂心上。”他其实知道,老郑对他的司机老邱是薄的,很信任他,视他为亲密伙伴。什么活动都带他参加,或让他出面。给他的薪酬也不低。人心还真是不可测呀。
三年时间总算淡化许多,两位异地的老同学又来沪了。这次是游玩,有点报复性的消费,不止是身心憋闷许久,还有,就是来报数年前惯蛋滑铁卢之仇。
明人想尽地主之谊,做个东。可老郑提出还是在他家,请老同学便餐。明人说:“你那司机不在了,是你自已掌勺,还是叫外卖。”
老郑乐呵呵地说:“放心,没事!”
到了这天,端菜上桌的竟仍是司机老邱。他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厨房客厅来回忙碌着。那些寻常而又好吃的菜肴,又一次让他们吃得津津有味。
又到打牌的环节了,老郑依然让老邱代他出场,他在一旁观战。老邱一如既往地打得行云流水。
待老邱上厕所之隙,明人悄声问老郑:“他又回来了?”
老郑点点头,依然微笑着。
两位老同学则看着他们,茫然无知。
倒是老邱很快回来了,他一坐下来就坦然说道:“我在郑总这儿开过一次小差,我还以为是自己本事足够大,可以出去闯一闯,但干了一阵就知道了,别的老板当我劳工,差我做这做那的,薪水也不高。可郑总当我是朋友和家人,信任又放手,我才有可能露那么几手。”
“你这匹老马,还算识途的。”明人开玩笑道。
“我是马儿要吃回头草,而且,就这么吃下去,到郑总不再要我为止。”老邱决然地说道。
“怎么会不要你呢!你就在这里,我们一起养老了!”老郑也笑着,态度坚决地说道。
明人叫了一声:“好!”
两位老同学似乎也咂摸出点味儿了,也跟着高声喊道:“好,一起养老!”
看 病
会议中,有人正在发言中,老赵忽然递来一张折叠的小纸条,主持会议的明人展笺一看,迅即抬起头,向老赵点点头。又示意办公室于副主任陪送,安排个车。
老赵老胃病,常常会疼。有时吃点药就好了,这回他说胃又疼了,药没了,得赶去医院配一下。 这是一次工作例会,老赵作为业务一处代表,方才已发了言,但发言并不好,明人不点名地批评了几句。估计是给他添了压力。胃疼得治,明人当然得立即准允。
老赵是双手按着肚腹,脸色少了平时的血色,嘴咧着离场的。恐怕老毛病犯得不轻。
一个半小时的光景,会刚散,老赵却在办公室于副主任陪同下,回来了,脸色恢复如初,双手随步幅摆动,神情轻快了许多。
明人主动关心,有些惊讶:“你这么快就好了,吃了什么神药呀?”
老赵苦笑参半地说:“哪吃过药呀,排了一个小长队,给别人做了个心理按摩,就这么好了。”
明人没听明白,目光来回看着老赵和于副主任。
老赵便叙述了刚才在医院的情形。
医院急诊队伍排得很长,幸亏于副主任找了预检医生,又和排队的病人点头打招呼,看到老赵秃着顶,小老头的模样,又捂着肚子,冒着汗,一些病人便默认了,让他稍稍插了个队,提前挂了号。
快轮到老赵看病时,隔着一扇屏风,就听见一位妇人的嗓音,高八度的,还带着尖叫,正和医生叫板。“你摆什么谱,半个月让我跑一次,你当我狗耍呀!”老妇人出言不逊。
医生是位三十来岁的男青年,他反复解释,这医院有规定,一次只能配这些。
可老妇人不服,话愈来愈难听:“你这个医生是太嫩了吧,我看你是胆小如鼠吧!”
“医院规定,我也没办法呀!你吵什么吵!”医生也生气了。
“你让我半月来一次,你以为你是谁,美男子呀!”妇人说得有点损。
醫生没睬她。
“我看你是故意刁难我老太婆,如果年轻美女在你这边一坐,你就不一样了吧?”妇人有点信口开河。
“你别在这里乱说!”医生回道。
妇人不依不饶:“我看你就是这个德行!伪君子一个!我老太婆年轻时,也是美女一枚!”
“你太过分了,对不起,你自己去美吧,我还有病人等着!”医生也加重了语气。
“你这是要赶我走呀!我要到院长室去投诉你,你这个没有人性的假医生!”妇人站起身,声音飙得很高。
“你去,你去呀!”医生也不让步。
“你是个缺德鬼!”妇人吼道。
“你才是个缺德鬼!”医生回击了一句。
这下老妇人更是暴跳如雷,又口出秽语,毫无节制地扔向了医生。
医生也回了她几句狠话。
妇人差点没把屏风给推倒。气哼哼地走了,一路骂骂咧咧的,说是这医生太糟糕,臭男人,不是家离这近,根本不想来这里!
妇人长得倒蛮富态的,有一点半老徐娘的风采。
老赵扶正了屏风,坐到了妇人刚坐的位置上。他见医生脸色很不好看,连忙说:“医生,你别理她,我看是她的错,有点胡搅蛮缠。”
医生不吭声,他在电脑上不知在寻找什么。
老赵又说:“这种人心理就有病,她不是找您岔,就是找别人岔。”
医生心不在焉似的。他抬眉望了老赵一眼,嘴巴仍紧抿着。他正生着闷气呢!
老赵不得不继续说:“现在这类人不少,他们不该来看急诊内科的,而是直接到精神病医院去看才对!”
“你们医生不容易,要面对这么多心精神有疾的病人。”老赵又说。
医生仍不吭声。目光停留在电脑屏里上,显然心里还憋着一肚子气。
老赵继续说道:“其实,您真的一点没错。您对她算是客气的。碰上我,早大声开骂了。”
这位男医生,白净的脸沉郁着,又抬眼注视了一下老赵。
“您根本不用在意她。就当挤地铁,碰上了一个身上发臭的人。您给那么多人治病,绝大多数人都是心存感激的。要不然,这么多人排长队,干嘛呢?”男医生还没从方才与妇人的争吵中走出来,老赵不得不多说几句。
男医生终于开口闷闷地说了一句:“你看什么?”
老赵摸摸肚子,刚说出一个胃字。男医生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把老赵吓了一跳。男医生重重地骂了一句:“神经病!”
稍一会儿,老赵也立马回道:“是神经病,这女人一看就像,她跑错医院了。”
男医生盯视了老赵一眼,目光渐渐活泛起来。片刻后,他轻声而又和蔼地问道:“哦,先生,抱歉,您有什么不适?”
老赵知道他终于走出了刚才的阴霾。他的心理按摩成功了。
但又一次摸摸自己的肚子,会议时比较剧烈的疼痛忽然找不见了。
他一时迷惑了,这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是谁治好了谁的病呢?
明人笑说:“你也别有太大压力,继续踏实干,别多想。”
老赵喜笑颜开:“您这一说,我更舒畅多了,药也不用吃了!”
“那这包药,我就处理掉了。”办公室于副主任提着一小袋刚配的药,开了一句玩笑。
老赵笑道:“这个还得吃。不过,心病,还得用心药 。明人领导,您也是心理按摩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