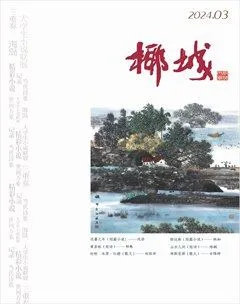卡夫卡与我和亮(短篇小说)
作者简介:富周,原名周富。中国电力作协会员、山东散文协会会员、烟台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获“青未了”散文奖、入围首届“今古传奇”文学奖复评。小说、散文、诗歌发表纸媒、期刊共十余万字。
我注定看不到他的面孔。
他是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下半夜从塑钢窗变形的缝隙挤进来的。我的室友让我把窗缝堵上,她说怕冷。冬天,每天晚上都有冷风吹着呼哨往里钻。我没按她吩咐去做,搪塞说,堵漏的胶水和封条都含有化工原料苯,能够诱发癌症。你是情愿中毒患癌少活几年,还是身体受一点冷而多活几年?室友沉默不言语。真实情况是,她肠胃不好睡下后爱放屁,我经常半夜被熏醒。留着窗缝,在空气浑浊的卧室里,有一丝清冷的风吹进来,总是一件让鼻孔和大脑愉悦的事情。对我这样害怕浊气熏蒸的人,时刻给窗户留个洞也给脑袋留条缝,或许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我还庆幸没有听从隔壁老王的劝说,把过时的塑钢窗换成当下流行的严丝合缝的铝合金系统窗。
正是塑钢窗的缺陷,让这个身体能够变形的人钻了进来。
他钻进来那夜,我床头上价值五元、一个月耗费一角人民币的小夜灯突然不亮了。我摁下小夜灯开关,还是漆黑一片。他说,你跟我来,不要惊动别人。我想脱掉睡衣换上出门的衣服,黑暗中的他立即揣摩出我的心思,说,不用换,我在小区旁边的公园等你,你从房门出去,记住锁好门。我当然要从房门出去,那吹进清风的缝隙我哪能挤得出去,再说这是在十三楼啊。
是夜,我的嗅觉告诉我,室内空气比往日清新许多,如同安装了一台大功率空气净化器。
黑夜里,凭着记忆我摸索着走进公园。没有携带照明工具,直觉告诉我,他不愿让我看到他面孔。他坐在公园石凳上,这是他的身体气息提示的,我距离他估计有六七米的样子。他说,你也坐下吧。他的声音非常柔和,外国人说汉语的腔调。我在他对面炭烧木联椅上坐下来。
他说,你好,小富。跟你探讨个问题吧?我下意识点点头,琢磨怎么回答他。第一次在黑夜听到一个陌生人叫我小富,有些不适应。
他说,你点头了。没理解错的话,你的习惯是点头表示同意。暗夜里我什么都不见,他却能看到我点头。
没容我继续往下想,他说,那我可直接问了,这个公园的名字为什么是大家公园?
这问题简单难不住我。我说,大家,是说这公园属于公共设施,是众人共同拥有的,谁都可以进来,不收费的。
他说,我的理解,公园就是公众的园林场所,已经表达非常清晰了,加上大家两字,是不是复杂啰嗦了?
让他问得头脑有些慌乱。我解释说,大家是个名词,作为公园的名字使用,也能指定方位,起到方便人们的作用。
是这样吗,我怎么看不出有指导方向作用?他说,你的小区前面的大街叫前进大道,小区的门牌是前进大道5号,公园在小区旁边,叫前进大道6号,是不是比大家公园更容易让不熟悉的人找得到?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想来,他说的有道理,可是记忆中,没听说过公园是用数字6号7号命名的。
在我转动脑筋组织语言的时候,大家公园墙外传来雄鸡的叫声,喔喔喔……高亢洪亮,让暗夜里的人们猝不及防。
是谁家成为了这个时尚小区的“一唱天下白”首个拥有者,或者说,前进6号小区第一个打鸣的公鸡是谁的?
要在家里养一只大公鸡是这段日子室友跟我絮叨的主要话题。我说,十三楼养哪儿,养在家里臭不臭?夜里打鸣吵醒邻居怎么办?想吃鸡我去乡下给你买跑山鸡。室友说,你老外吧,哪是吃,现在宠物已经不是狗啊猫啊这些了,要养宠物,最好的就是大公鸡。狗啊猫啊只会发情叫春,只有大公鸡能提醒你什么时候天亮。
转过神来,立刻发现,在我懵懂愣神的那一刻,他悄然离去了。随着鸡叫走了。
这个时刻,是我初中作文本上曾经写到的,天空露出鱼肚白。
我走到他坐过的石凳前,地上有一行字,是他蘸着水池里水写的:人叫不醒装睡的人,公鸡可以。我刚辨认清楚,字迹即刻消失了。
当天晚上,天刚黑,我做的第一件事,把小夜灯的开关打到“ON”,灯亮了。
我问室友,这灯昨天夜里怎么不亮了?她说,不可能,怎么会不亮?我买的可是外国进口的灯,一辈子都不会坏!
我拔下小夜灯,见到灯口上有一串英文字母,Made in China。我努力克制好为人师的欲望,不给她解释。我知道,解释的结果是惹她发怒,不好玩。再说今晚是我们试婚期的最后一天,她说今天通过了,明天就跟我去婚姻登记处办理合法手续。我问,明天5月19号,何不等到5月20日,寓意美好的520?她说,后天人多,明天是空窗期,人少不用排队。
我不知道什么是空窗期,也懒得再问。我继续翻箱倒柜,那盒超薄透明的安全套塞哪儿啦?记得包装盒上画着一只斑斓大公鸡,非常奇怪的图案。
亮见过他。一种坦诚到赤裸裸的相见。
亮是我的朋友,一个处于潜伏状态的作家,未来可期。我搞不明白的事都找他请教。
我说,亮,有天夜里我做个梦,一个外国人从我家的窗缝钻进来了……
亮说,那不是梦,是真事。
我说,真事,我怎么觉得是做梦?
亮说,是你至今没醒。
我还是似懂非懂,问亮,你见过他吗?亮说,见过的。我又问,看到过他的脸,知道他长啥样?亮的回复答非所问但干脆,他说,白天,又补上一句,还光着腚呢。
他是敲门进的亮的家。敲了三下,极其有礼貌的笃笃声。亮感知,他是弯曲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輕叩的门。打开门,他和亮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对视足足三分钟。他保持着宽容温和而又神秘的微笑,亮的表情由羞涩到安然,第三分钟要结束的时刻,也变成了微笑。亮的微笑竟然也传染上几分神秘。
他没有打算进家,轻轻摆摆头,亮即刻明白他的意图,是让亮随他去外面。亮很乐意跟他去空旷的天地,亮的家空间实在不大。出门时,亮随手拿上一个大包,里面是准备祭祀先人的贡品。为什么会拿上贡品随他出门,直到七年后亮去了他的故乡,站在他的塑像前,亮也在琢磨这件事情,没有找到说服自己的答案。
他和亮在月亮山下说话。上午,山头顶着一个蛋黄色太阳。
他和亮面对面。亮从大包里掏出一把白玉嘴乌木杆紫铜烟锅的大烟袋,装好烟丝,双手恭敬地递上去,他接了,把白玉嘴衔在嘴里,亮用火镰打火点燃烟丝。他深深抽一口缓缓吐出烟雾,起初袅袅绕绕,后来清晰成一绳烟线,竖起来仿佛能够挂上山顶的蛋黄日头。亮甚感古怪,一个外国人对古老的中国烟袋,使用起来如此娴熟,让人惊奇。亮听长辈说过,他的祖先技惊乡人的本领就是口吐烟绳。传说,无风的日子,祖先吐出的烟绳能横出十里地。今日见他烟绳够上太阳,亮不再怀疑祖先的本领是吹牛了。亮的脑袋随即闪过一道光,悟到,祖先的烟绳是横着伸出去的,追出十里地就消散了;他的烟绳是竖着的,上升到看不见的高度。
他盯着亮看,看亮闪亮的眼睛。他把烟袋递给亮,示意亮也抽一袋烟丝。亮身子后仰,慌张地冲他摆手。亮哪敢接烟袋,38岁的亮6岁即被家人灌输训诫,抽烟的人是败家子,是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不要说烟袋,亮活到现在连烟卷也没抽过。
推开他递来的烟袋,亮陷入迷惑。先人光宗耀祖的“十里烟绳”技能为什么没有传承下来?假设先人因烟技出现了错失甚或罪过,为什么祭祀先人的贡品还是一把白玉嘴乌木杆紫铜烟锅的大烟袋?
亮没能考上大学,完全怪罪于数学成绩太差,满分150分,亮只考了37分。已经与数学彻底决裂的亮,此刻坠入概念冥想状态。朦胧中,他的“竖向烟绳”和祖先的“横向烟绳”,两根“烟绳”呈十字摆放,形成数学的坐标。如同醍醐灌顶,脑袋开窍了。在坐标上找到原点,然后在X軸上上下爬行,在Z轴左右横行,亮完全进入理想的生活状态。亮一会儿是一只蚂蚁,沿着X轴到达要去的高度;亮一会儿成为一只蟑螂,顺着Z轴来回穿梭。
亮睁开眼睛那一刻,月亮山顶太阳的颜色成为煎蛋去掉蛋黄的蛋白色。亮的眼睛里含着两颗小太阳,左眼有一颗,右眼也有一颗。亮看不到自己眼睛里有太阳。亮能看到对面他的眼睛里的两颗太阳,左眼一颗,右眼一颗,亮从惊奇到震撼,太阳如何钻进了他的眼?
亮的表现是震惊,他的态度是冷静。他静静地盯着亮看,直到亮的呼吸均匀如常态。他伸手入怀掏出一支粗大的雪茄,又从外衣的下口袋掏出雪茄剪修剪两端,然后从上衣口袋掏出银壳打火机点燃,深吸一口。他闭紧嘴唇锁住那口烟雾。他闭合眼帘酝酿那口烟雾。
亮看完他有条不紊的一连串动作,清晰的脑海走进了现代化都市商品街。一条分工明确的商业街道。买工具进五金工具专卖店;买孩子的衣服进童装专卖店;买汽车进汽车品牌专卖店。转过商业街,走上一条泥泞的乡村泥土路。亮的脑海灌入没有进行雨污分流的浑水。亮要打捞不小心落入污水流的身份证,身边找不到顺手的工具,亮跑进路边杂货店。店里商品琳琅满目,杂乱地混在一起。店老板推开簇新的自行车,搬开沉重的瓷质酒缸,挪开头层牛皮皮鞋箱子,拖走两袋化肥,拽出一捆麻绳……亮着急在催,气喘吁吁的店老板说,差不多了,抬走这两块木板,捞鱼的抄网就在下面。你说,活的鱼都能逮得住,你的身份证不是一捞一个准?亮扫一眼手表,四十七分钟过去了。其实二十分钟之前,亮的身份证随着浊流飘进了海里。这内海与公海相通。
亮摇摇头醒了。
他依然闭紧嘴唇锁住那口烟雾,但他睁开双眼不再酝酿那口烟。他见亮睁开眼,慈祥地把雪茄递过来。亮这次不再犹豫,伸手接过来,学他的样塞进嘴里,用力嘬一口。这时,他噘嘴把酝酿许久的烟雾吐向天空。亮依样对空吐出烟雾,两团烟雾首尾相接在升腾。
月亮山顶的太阳更加炽烈,变成耀目的灿白色。他和亮头上大汗淋漓,衣服洇湿,两人开始脱衣服。他们吐出的烟雾已经融合在一起,上升到山崖凹陷处静止不动了。烟雾均匀地散布开来,云锦般在山壁上挂做银幕,太阳灿白的光线投射到银幕之上,一个古老的故事在重播上演。
他和亮都被崖壁上的电影吸引。
故事情节简单明了。森林中的一群原始人在追逐动物,初始猎获的食物很少,仅能维持生存。后来收获多了,果腹之后有了剩余,一个强壮的原始人占有了多余的部分,其他的原始人行事之前必先看他脸色。不久,另一群原始人来到这片森林。于是,两群原始人一边追逐动物一边猎杀对方的原始人。两群人的厮杀很血腥,银幕上是满满的鲜红色。红色暗淡下来的时候,是两群原始人站在壕沟两边在咿咿呀呀地讲和。他和亮对一下眼神,瞬间都理解了对方的意思。他们共同辨别,银幕上的森林像是百万年后的月亮山。当两人把目光转向崖壁确认银幕上的场景是否发生在百万年前的月亮山时,那银幕烟消云散了。
天空在燃烧,仿佛要把太阳蒸发汽化。目光对上亮的眼睛,说,在分别之前我向你提个问题吧,你说,人类到现在最好的发明是什么?
亮眼一闭看到了两群原始人站在壕沟两边讲和、签约的情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规则,或者叫法律。
他笑了,脸上透出与长者年龄不符的神情,伸手抓了抓亮,很快松了手,像调皮的小伙伴之间的玩闹。他跑开了,亮愣在原地。
他回头看亮,说,追我呀!他继续跑。
亮反应过来,听懂了他的话,追上他我也能抓他,我们是平等的。亮开始追他。
……
后来,亮拿来一块从月亮山朝阳南坡捡到的石头,要我在石头上给他画一幅卡夫卡肖像。我说行,等我去互联网搜搜他的画像再给你画。亮说,网上的不传神,都是变形的漫画。还是我给你描述他的形象吧。于是,亮把心目中他的形象说给了我。
一个月后,我把凭记忆画的石头画给亮,亮看了足足十七分钟,说,一个眼大一个眼小,但都有神光。
亮到底也没告诉我,我画的石头画像不像卡夫卡。
亮不说,我也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