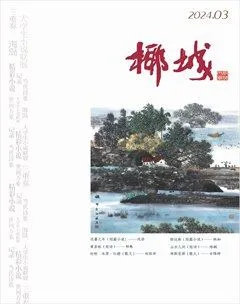转运珠(短篇小说)
班知
一
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我和她,相隔着两个盲道砖块的距离,一前一后,说不清楚谁是谁的影子,反正就这样,一直相安无事,向前方缓步挪动着,没有目的地,没有一个确切的方向,同样,没有人率先开口打破这追逐的局面。
在石桥公园,现在已经很少再看见几对悠闲散步的身影。我随意踢着脚边的石头,把脚后跟像前锋一样抬起,这样拖曳着腿向前摆动,刻意地弄出声响,将自己的脚步放慢,好让身后的女士能够赶上我的步调。
前方的林荫道马上到尽头了,我们慢慢挪向桥边,太阳下落得很慢,但你一不去看它,它又像是很快的坠落,给人带来一种紧迫感,但我心中,此刻,却仍说不清是否还是艳阳高照,或许是吧,我也希望如此。
“你确定想好跟我走了吗,这可不是随便说来玩的。”久违的细语从斜后方响起,来不及做出反应的同时,也暗自松了口气,“啊,啊,是吧,是。”我有点局促地向后转向她,她的眼睛很大,眼睫毛带有一种自然的曲线向上卷曲着,额头未被刘海盖住的部分,渗出细细的汗珠。
“额,算是吧,我想好了。”看见对方没有回答,我又自顾开口,而我的手似乎摆在哪儿都不太合适,于是,只好别到脑后尴尬地挠着后颈的绒毛,左手转运珠的红线从手腕往下滑下一点,耷拉在手上。听到我这番话,她只是抿嘴笑了笑,不再看我,径直从我身边经过。
“可是,算上这次,我们也没见过几面,你就那么相信我吗?”
我迈开大步追上她,和她肩并肩地走在一条线上,风来得很缓慢,轻轻地平铺在我们脸上。
“是啊,刘念,一切都显得太荒谬了,但这就是你想要的不是吗?一场冒险。”不觉间已经到了石桥的跟前,这是一座比較矮的虹式单拱桥,台阶有序地排列到曲线的最高点又随之递减,台阶两侧是供轮椅与婴儿车通行的滑道,一两个穿着凉鞋的小孩坐在顶上,你推我、我推你地争夺先后顺序,像是在进行什么古怪的仪式,再磨磨蹭蹭地滑下来。
桥下的河是死水,已经很久没有换过,它就一直这样站着,缺少流动。已经有一小片一小片的绿色在其中沉浮,在风中,隐隐飘出腐烂的气息,像一位失去心脏的石质巨人,并不知道自己到底为谁而活着,又为何会如此突兀地出现在这。难道我目前的处境就比它好一些吗?
我没有再管刘念的回答,或者她也并没有接下我的话茬,我绕到河岸边,那些河流的体味就越来越近了,河面已经完全看不清东西了,一些鱼或者是石头,都被泥沙和微生物遮盖着。我看着岸边无人看管的小植物,一株株,富有夏天的生命力,我开始想这一天,这一个下午,或者这一件事,是否来得过于突然了,我习惯性地拨动左手腕上的转运珠,它四周的棱角摩擦着我,令皮肤露出不适的红色,再回头看向刘念,她也正朝我这边走来。
她今天扎的是高马尾,肩带跨上黑色皮包,一件合适的T恤和修身的牛仔裤包裹住她年轻的身体,五官端正,嘴巴总是抿成一些不同的形状,看不出喜怒。她会是谁,你真的了解她吗?看着这张离我越来越近的脸,美丽,年轻,却愈发令我感到陌生,刘念,这个名字突然像水葫芦一样,轻易地覆满我的思绪。
而我就像是这片死水。但比它更可悲的是,连将过去与现实连接起来的桥都不复存在,这一切都太过理想了,即使,直至两周前我才第一次听到,并且真正记住这个名字。
二
就把他简称陈吧,初中毕业,我就辍学去技校学修车,陈是我的初中同学,我俩经常扎堆在一起,有时是打电玩,但更多的时候都是厮混,两个人轮流抽一根烟,偷拿些家里的零钱出去上网,我也因此成为了问题学生。但陈的成绩一直比我好,不算拔尖,只能说还凑合,所以毕业后他就去了八中,而我则被我妈安排去学修车。在报到之前,我妈特意送了我一条用红线穿起的转运珠手链,三克多,安静地躺在红绳间,她说就算是提前给我一个成年礼物,就算读不上高中也希望我能够有好运气。于是,它就这样一直陪着我到今天。
两周前,周末,我宅在家打电动,陈叫我去舞厅喝酒,声音嘈杂,叫我务必快到。我也自觉无聊,挂了电话,就洗个脸草草出门。
陈说的舞厅在城区的东部,一个步行街饭店的二楼,店不大,人却夜夜爆满,我在门口锁好单车,上楼,一阵闷闷的鼓声让我心跳加快。厅内昏暗,彩灯射线在墙壁和地面上拐弯,麦克风传出各种调动气氛的说辞,遮盖DJ舞曲的声浪,空气中弥漫着烟草味和汗味的粘腻,混杂着其他各种的香水味,让人头晕。
刚进门,眼睛还受不了突然的冲击,眼前的人群摇摇晃晃地靠拢,之后又像潮水一样的散去,和不同进出的人擦肩或撞在一起,我在厅内尽力寻找着陈的影子,舞厅的布局以舞台为中心朝四周散开,一个大圆桌围绕一圈沙发,由内朝外扩散,最左面进门的位置是吧台,提供散客的座位和酒水,灯光很闪,周围人群不同的话语似乎都被音乐拧成一道共同的尖叫,听不清是什么声调,见状刚想掏出电话的手,又重新从口袋拿了出来。我慢慢地从不同的男女中间穿过,一路向着舞台的方向靠拢,四下找着陈的身影。
在舞台侧翼稍远的角落,一个寸头男性背对着沙发靠在枕垫上,边上几个年轻人或坐着,或站在沙发上跟随鼓点跳起来,我试探地走到跟前,从寸头男沙发的一侧路过,还没回头时,熟悉的语调就从身后响起。
“欸,李,是不是你啊,你过来坐啊,你去哪里,刚还想给你打个电话。”
回头,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一股力将我拉向后方的位置,我顺势坐在沙发上,一个熟悉的笑脸出现在我的眼前。
“你今天怎么搞那么久,都等着你玩呢。”陈把手从我的肩上收回,我则随便找了一个理由搪塞,“这些都是我朋友,有些是同学,反正没关系,大家一起玩就好了,是吧。”陈用手指了指对面和他旁边的几个人,顺手从桌上拎起酒瓶,递给我。
“怎么了,最近在忙啥呢?”
“修车呗,还能干啥。”我干笑一声,一口绿棒子下肚,廉价啤酒的涩味冲入我的口腔里,能感觉到脸上的温度正在逐渐上升,“倒是你,一天天忙啥呢,还是那么潇洒。书还读不读了?”“也就这个时候能开心一点了。”说完,陈像是被抽光了所有力气靠在沙发的枕垫上,握住酒瓶的颈口,耷拉在一旁。
见陈这个样子我也没再好继续搭话,只好正了正身子,四处观望周围的人群,之前在对面聊天的一群人已经走到了卡座的左面,正跟其他几位女生攀谈起来。几位女伴有高有矮,舞厅的灯光昏暗,看不清脸,凭感觉判定应该与我和陈差不多大。长发随着节奏摆动着,透过几人身影的间隙,能够看到一个年轻的侧脸,模糊,在彩灯下衬出下颌的曲线,裙摆是白色,腰身正随着音乐像波浪一般摇动。
似乎是感应般,或者是,那眼神的炽热过于明显了,没有任何预兆,她轻轻地转过身瞥向我,眼睛很大,正向我和陈的方向不经心地探视着,刘海被撇向耳后,露出一小半的额头,听到周围人的俏皮话,她不时挂上微笑,嘴角的弧度微微上扬,梨涡带有浅浅的轮廓。
“欸,我说,你在看啥呢。”一只手掌不合适宜地搭在我肩上,我稍稍一愣神,陈那张棱角分明的侧脸就出现在我的肩后,带着不明所以的笑容,之前的情绪似乎已经一扫而空。
“说吧,喜欢上谁了,这都是我同学,来吧,带你认识一下。”我笑着摇头搪塞,但陈像是因此来了兴趣,直了直腰,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另一只正向着对面来回比划着。
“是这个?还是这个?”
“欸,不是,你是不是有病。”
我把陈比划着的手扒拉下来,挣开另一只手,起身拎起桌上的酒,“不是,李,咱俩谁跟谁,你在哥们面前也那么认生是吧。”陈也从沙发上起身走到我的身后,继续朝着刚才那位女孩的方向比划着。
“你看是她不?”我专心用桌角开瓶盖没吱声,也不知道他指的是谁,或许是她吧,我也不确定到底是希望还是拒绝,下一秒,陈就推着我走到斜对面,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刻,我的手里还时时握着还未打开的酒瓶。
三
只记得她叫刘念,是刘念,而不是留恋。其他的细节则在酒精和音乐中逐渐模糊,细化成时间案板上的一个细小的点。
一阵尴尬之后,我和这位陈口中的刘念,一起被很多双手和粗俗的话语推向卡座的另一侧。这种情况下,刘念并没有什么不满的神色,在同行女生的打趣下,依旧挂着那模棱两可的笑容,用手擦去额头细密的汗珠,见她并未因此反感,我也没有开口,只是学着刘念,一块做出足以回应任何状况的笑。
说是无地自容,但这处境也谈不上如此糟糕,跟陈玩的这些年,我一直不是一个胆小的人,只是相比起陈来说相对寡言一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闷骚。只是感觉这一切都过于迅速和突然了,甚至是荒诞,对,没错,荒诞。我只是盯着这位素不相识的女生看了几眼,我不敢说没有夹带任何私人的情感,但至少,目前对她还说不上喜欢,被如此突兀地坦诚布公,以至于到了独处的时刻,在我心中还是有些忐忑。
“不好意思啊,我朋友他实在,欸,他平时就爱这样开我玩笑,你要是觉得心里不舒服我等会过去骂他去。”我找了个沙发的空角落坐了下来,刘念跟在我后边坐下,隔着半个人的距离,她的手交叉放在翘起二郎腿的膝盖上,不时撩起鬓角的头发。
或许是因为没听清,她没有马上回答,我觉得有些尴尬,望了望她,探起身,拿起子开了瓶酒递给她。
“没事。玩得开心就行。”她接过酒轻声说了声谢谢,声音很轻也很细,在舞池的嘈杂中听得费劲。我向她的周围挪了挪,两个人的距离变得更近了,刘念抬起酒杯,我顺势跟她碰杯,清脆的声响后,口腔内滚动的苦味让人发晕。
“你是陈的同学嘛,还是……”
“对,我和他关系还行,但也不算特别好,就是,能玩在一起吧。”
“噢,这样。那,那挺好的。”話题就这样断了下来,我又独自喝着酒,短暂的沉默后,刘念的声音响起。
“那你呢,你也是他的同学吗,怎么在学校没有印象?”
“嗯,算是吧,至少之前是,但是我已经不读书了,现在在技校学汽修,就是,就是修修车什么的,平时也不算有意思,当然了,和你们可比不了。”我讪讪的笑着,虽然过去了这几年,关于这件事,嘴上总是说着不在乎,但今天跟刘念在这种场合谈到这件事却仍让我喉咙一紧,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那几声笑更像是对我的保护。
“没事,学一门手艺也很好啊,像我还有一年就快高考了,却还是像什么都没做一样,不踏实,没劲。”
“对。没劲,我也觉得,干什么都挺没劲的。”
“都挺没劲的。”
我深深地吐了一口气,靠在沙发上揉着眼眶。手腕上转运珠的棱角蹭着眉毛,我抬眼,刘念已经把啤酒放在一边,两只手按着手机的按键,像是在回着对面的短信,左手无名指的戒指在彩灯下不时地反射出些微的色彩。
“戒指挺好看的。”
“什么?”
“我说,戒指,挺好看的。”
“喜欢吗?我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刘念抬起左手向我挥了挥。
“好巧,我也有。”我也向刘念展示我的转运珠,左右摇晃着手腕。
“这是什么,手串吗?”
“转运珠,也是我妈妈送我的礼物。”
“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吗?”
“我希望是的。”
之后便是短暂的缄默,刘念继续在手机上打着什么,而我靠在沙发上搓着珠子,有不少人已经跑到台上和DJ一同摇着手,现场的气氛已经逐渐被带至高潮,更多的人从各自的卡座出来,朝台边靠拢。我开始感到疲惫,或许是太晚了,一直没来得及看手机,想到这里,我掏出手机,已经快十二点半了,待在这里也有点无聊了,或许我天生就不太适合这些热闹的局面,这只会让我感到在人群中格格不入的孤独,也或许是我太矫情了吧。
我自嘲地笑笑,刚刚喝的几瓶酒已经开始上脸了,能够感觉到脸颊和脖子的热,加上這拥挤又密闭的环境,开始让我有些头晕,突然想抽一支,我伸手掏我扁平的裤兜,才发现今天出门太急忘了带火,所以便起身到正在跟着音乐摇晃的陈的身后,伸手掏他裤兜里的烟和火机。
“你干嘛,这就聊不下去了?”
“这人太多了,我出去透透气。”
“那你就把人家女孩一个人扔那啊。”
我回头,刘念正在沙发上用手机回着短信,手机微弱的光映在她的脸上。我叹了一声,朝原来的方向走去,刘念顺势抬头,露出标志性的微笑,我愣了一愣,像是被什么东西摄住心魄,面对她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对视了几秒,轮到刘念开口打破僵局。
“怎么了?”
“那个,我出去透透气,要一起吗?”
“嗯,好。”
刘念起身扯了扯裙角,一双大眼睛,再度望向我。
“走吗?”她把手机握在手里,脸上重新堆上标志性的笑容。
我点头,侧身,绕过她的肩膀,挤开前方拥挤的人群。我没有回头看她,没有见过她走路,但是我觉得,她应该会像大多数女孩一样,轻轻压住裙边,一步一步,温婉地追上我的背影,想到这我便不自觉地放慢了我的脚步,怕她反悔,也怕她会就此迷失在这浑浊的人浪中,想到这,一种令人心悸的陌生触感便随着手指,逐渐上升至皮肤、脖颈、后脑勺。左手戒指的冰冷隔断着两只手指间温度的传递。算得上是久违吧,这种感觉,已经很久远了,久得我已经忘记了这种触感。在这样一个嘈杂晕眩的瞬间里,她就这样牵住了我的手。
她的手掌不大,皮肤很细,手指像是若即若离的丝带缠住我的五指,冰凉。像一块温润的玉含在手心,一丝丝渗进我的心绪中。如果你在这一刻,突然问我到底喜不喜欢刘念,我会很肯定地回答喜欢,但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次牵手,或许,是因为我在见到她在卡座的第一眼?我也不明白,即便是十年后的我也只能用“一见钟情”这四个字草草概括,或许这就是她说过的荒诞吧。
一出门,空气像是突然松绑一般,释出令人放松的情绪,走出大门,像是就此隔绝了两个不同的空间,我深深地吐了一口气。一抹白色出现在我的侧面,刘念跟在我的身后出了门,两只手本就脆弱的联系就此断绝了下来。往前走下台阶,我蹲在路口,低着头,零星的人从我身边来回走动,深夜,人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归宿。
而突然脱离了高压的环境,周围的一切开始迟钝起来,每一个人的步伐,他们的笑或醉态开始变得很慢,树木正在向我不断靠近,耳朵带有隐约的嗡响。
我摸出刚刚陈的烟,狠狠地抽了一口,刘念在我身后的台阶上坐下,小心地扯着裙边。
“你还好吗?”我看着白色的烟雾向上缓缓地消散,回头看向刘念。
她并没有马上回答我,只是指了指我裤兜露出的半边烟盒。我惊讶于刘念的要求,但还是掏出一根交到她手里。啪一声,火苗从塑料壳中窜出,烟丝在火焰中急速消退,成为情绪的一部分。我看着她,仰起细长的脖颈,下颌,像是那些海滨城市漫长的海岸线,一直延伸至耳后,淡淡的白雾从鼻中流出。
“怎么能不累呢?每一天,都像门里面一样吵,一样拥挤,家人、朋友、陌生人,和那些傻逼,那些虚头巴脑的破事,费了很多劲想走出来坐坐,松口气,但待久了,却并不会改变什么,又该灰头土脸地回去,可悲的选择。”
我听着她的话没作声,不知道该回答些什么,一个只与我相识甚短的人,她的过去,她的伤痛,她那些不与人言的缺口我全然不知,但对于我、陈,或者许多同龄人来说,我们却都有着共同的疲惫。
在这段破碎、语义不全的话外,她看起来安静,有个性,生活优渥,竟也会如此悲观。显然从这方面考虑,我们并不是同一个环境内的人,我们虽然都苦恼,但却始终无法走入同一个隧道中。但她的话确实也是我所想的,也是我最困惑,与最想要与人倾诉的一部分。生活的苦闷与荒诞。我不想再过多地回忆我的原生家庭,不愿再一遍遍细咂他是怎么因为一个碗就将一个折凳草率地摔在我脸上的,但我不再愤怒了,去他的,无所谓,喝多了,管不住自己的脑子。刚刚的酒,烟,和刘念,再一次尝试打开我锈掉的花园,我能感觉到她的渴望,两头失控的小兽。
我把烟头顺手丢在路边,拍了拍裤子起身,回头,刘念还在夹着那半根烟发愣,烟灰慢慢延长像是生命一次次将自己逼向危险的地带。
“去哪?”
“啊?”
“我说,你等会去哪。还进去玩吗,还是回家?”
“不知道。我爸不在家,我在这等花她们出来吧。”
“你怕我吗?要不,跟我走吧。”
四
每次都忘记关掉那该死的闹钟,我在心里咒骂自己,伸手摸索着床头柜的手机,四五个未接通知醒目地出现在消息栏上,心里咯噔一声,宿醉之后迟钝的大脑瞬间变清醒,关于昨天的事很多已经记不清了,酒,烟味,呕吐物,泪水。这些事物互相重合的影子,不带任何规律的轮番或一同冲到我的眼前,即使我们之间已经那么近了,仿佛我只要一伸手,它们就会紧紧攥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到这个房间内的某个门前返回昨天的一切。但它们却也像是丢掉了所有的细节,流水声、拥抱、亲吻,再细一点就完全无法窥视了,像是麦当劳叔叔丢掉了它的鼻子。
我侧过头看向睡在身边的人,窗外亮得很早,空调呼呼的响着,刘念抱着被子的一角,将自己紧紧裹在一起,背对着我看不清脸,白色的被单上散落着零星的几根碎发。我知道我不能再留在这里,待两人都清醒之后,事情便不会一成不变地走向美好,还是让这些都留在回忆中吧,我摸向手腕的转运珠,把它转到中间的位置,摩挲起来,还是一样生涩,类似我猛地咬向一颗青苹果。
回电给陈依旧是关机状态,后来过了几个小时他发短信给我说刚睡醒,嗓子哑了不想打电话,没提我为什么中途走了的事。回家面对我妈,我只能一口咬定我在陈家过了一夜,任凭我一身散不掉的烟酒气息在狭窄空间内散发,也同样任凭她怀疑的目光在我身上上下扫射,也只能让自己强装镇定,来回搓着转运珠的棱角。在紧张的对峙下,最后她还是放过我一次,但也警告我下次要是再这么突然的话就把我送去我爸那。从小到大她就一直用这句话恐吓我,听着很吓人对吧,我觉得也是。
稍晚些时候刘念打电话给我,当时我正在客厅用饮水机泡泡面,在水声下,她跟我说她的戒指不见了,找遍房间也没发现,这明明是件不小的事,但她的语气却仍没有任何急切以及不安的情绪,就像她永远的笑容一般,在电话那头,只是一字一句地说,像听力课上冷漠的女声。我安慰她没事的,总会找到的,可能在自己衣服口袋里,要么就是掉在舞厅里了,不然打个电话去问问。她没说话,我也没说话,用脖子夹住电话,把泡面用铁盆子扣上,我站在桌前,看着白烟从盆沿的四周缓缓溢出,像是我们那晚遥远的烟雾,稍纵即逝。我愣了一会然后开口。
“你怀疑是我拿的?”电话另一端还是没有回应,只能听得清细细碎碎的声音,迟迟等待的回答确没有确定的痕迹。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结束的对话,或许我们还因此争吵了几句?记不清了,反正不好不坏。而发生了这件事后,我开始疯狂迷恋网络游戏,一笔笔钱被我换成虚拟账户上的数字,像是失去了什么本就禁锢在我手上的铐子,在学校的实习也经常旷课,而和刘念,我们又见了几面,我们都心照不宣的没有再谈这件事,有好几次我试图开口去询问她戒指的下落,但看着她沉思的表情还是难以启齿。
在石桥公园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在万福路散步,我牵着她的手送她回家,她说她最近压力很大。我问因为什么,她没有说话低下头,玩她的头发。我说,因为要高考了吗,不着急,你还有一年,总会考上大学的。
这时路上行人已经不多了,秋意慢慢攀上来,一阵阵风从不同的方向吹过,那些最细微之物就被悄然浮动。她并没有回应我的祝福,只是说她想去广州。惊讶之余,我问什么时候,她说这几天,她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想暂时逃避一段时间,好好地生活,好好地呼吸。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和家里人说了吗,学校那边怎么办,休学吗还是……她只是转头用眼神打断我,我盯着她的眼睛,还是一样的陌生、冷静。路上,车辆疾驰而过,而我们都一同站定,像是旧战场中待命送死的兵卒。
“那你愿不愿意和我走?”一阵阵气息扑向我,有她的发香,有空气中灰尘的味道。我能感受到言语间的跳动,一个字一个字地跳上我颤动的心,像是萤火,像是蜜蝶寻蕊前肆意地挥动它的双翼。
五
“在想什么呢?”熟悉的笑容在我视线一角由模糊转为清晰,回过神来,河水依旧静静地,不出声,散出藻类腐烂的气息。我想,确实在这待太久了。
“嗯。没事,想了些之前的事。”
“考虑得怎么样了,明天?”
“明天吗?”
“对,明天。”
我拉着刘念的手从岸边走回石子路,在沙沙的声响中,走向这座矮桥,之前还在玩轮椅道的小孩已经跑入我们来时的林荫中。落日已经快无法辨析了,微弱的,像更加虚弱的病患,只散发出它最后的那些光。我牵过刘念的手,来回摩挲她的掌心,像是每一次心乱之时都会反复摩挲我的转运珠。
我摸上刘念手指空缺的一处,想象那枚有过一面之缘的戒指重新回到这里的样子,淡淡的金色在刘念洁白纤细的指节之间,闪烁动人的色彩。
“好,那我们就东站见。”我松开刘念的手,过了桥,石桥公园的南门如同一道神秘的梭门,似乎跨过去,就会进入截然不同的生活中去。带着一种决绝,我率先向前迈了一步,又矛盾地停在了前方,世事也会有回旋的余地吗?我不确定。
我轻叹一声,又回头走向刘念,我们挨得很近,刘念比我矮半个头,低下头就能嗅到她发间的香。
刘念愣了一下站在原地,她问我怎么了,我没作声,低下头,把手腕上的红绳扯下,在空中扯了扯,比划了下,最后套在刘念的手腕上,两根手指一拉,一条红色的小蛇缠上她白皙的手腕。
“这个送给你,希望大家都能时来运转。”
一夜无眠,电脑屏幕一直亮着,蓝色的光在房间的角落闪烁。我躺在床上,用枕头蒙住自己的脸,却并没想明天的事。我从小便生活在这,没有离开这座县城半步,石桥镇小,十三中,到现在的永福区职业技术学校,我像是被一股未知的力量困在这圈里,囫囵地活着,无法回到母体,亦无法勇敢地前进。而这一次,冒险似乎来得过于轻易,只一句话,似乎就要将我带离干冷的北方。北方,想到这左手指节莫名的生疼,由内向外,像是受过风寒的病根,我习惯性地摸向左腕,但那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那一天早上来得很慢,我像是古老的祈火者,等待着日出。阳光透过窗帘洒在我的床脚,视线由此变得温暖起来,黑屏的电脑,堆在床尾的外套、烟盒、易拉罐。卧室外很安静,还没有听到母亲叮叮当当煮鸡蛋的声音。我似乎感觉不到疲惫,同样也感觉不到任何其他的情绪在我的身上流动,兴奋,惶恐,或是不安。
我甚至快忘了刘念,我发现也没有那么在乎她了,那些执念或者爱,已经很淡了,至少在这个短暂的瞬间是这样。今天似乎与往常的364天相同,早上见不到母亲,起床再去厨房拿出给我留在锅里的蛋,然后睡到十一点,下楼打包一碗炒粉,数一数剩下的钱,藏进衣柜的夹层中,继续打开电脑。
但我也清楚,今天和往常也不太一样,会有不得不做的事情,即使我根本不知道之后会有什么未知的意外发生,也不知道广州到底有多远,不知道我该如何到达我想要去的地方。我像往常一样穿衣、洗漱,来不及看时间,只发现现在母亲的房门很安静,回头掏衣柜夹层里的钱,一百七十八块,把它们叠在一起,塞进牛仔裤的侧兜里。手机已经完全没法开机了,昨晚又忘记充电了,只好把它兜在外套里,拿起鑰匙出门,走到半道又折回来拿身份证,听他们说坐火车和开房一样,冒险,都得证明你是不是你本人。
这座县城有火车站吗?我不知道,我在自己熟悉的路上一路骑着,夏末的清晨很忙碌,我路过自己熟悉的一切。十三中、网吧、舞厅、万福路、石桥公园,我在一个个绿灯和红灯前穿梭,没有目的地的等,等那个熟悉的身影出来,再次将我领出这些熟悉的领域。
石桥公园、舞厅、万福路、网吧、十三中,所有带记忆碎片的场景,将时间片段串联成一个紧凑的闭环,从一头走向另一头,像是我无数次淌过自己成长的湖泊,感受着这一成不变的矛盾。而突然,急促的笛声下,一个硕大的物体正迎面向我冲来,我下意识地拼命拐着我的车头,车轮发出尖锐的摩擦声,车身迅速失去平衡地向前方甩去,我也顺势向一侧滚去,在向前滑行了一段后,刚刚跟我迎面而来的轿车终于停了下来,我躺在粗粝的水泥路面上,像是被掏空了所有气力般蜷在一处。
只能够感觉到脸颊和手掌火辣辣的疼,只能够听到车门开关,各种脚步逼近,各种粗鄙的辱骂声,行人的围观,一阵阵无序又刺耳的笛声。然后有一只手使劲地掰着我的肩膀,或许是那个车主吧,又或许是许多的人或事,无数意念会汇成一只大手,他代表着什么?又会给我带来什么?不愿再深思。我把自己的头越埋越深,好遮住自己的腹部,什么广州,什么戒指,什么转运,什么爱,什么未来,我都无法再清晰地辨认,我只想好好地躺在这,就这几秒,闭上眼睛,不要再叫醒我,好吗?
六
那天最終还是没能去到车站,后来我被几双手拉了起来,用车主的电话拨通了我妈的号码,而我的电话也因此消失,去往了它该去的地方。我和刚起床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的母亲一起,把这个歪把子车推回了家,用酒精擦着我并不光彩的印记,我憋得满脸通红也只是嘶嘶地吸气。坐在窗边一直等到太阳下山,就像曾经在石桥公园的时候一样,看着一切充满生机的事物却依旧死水般呆滞在那,那个下午我没有收到刘念的任何消息,这在意料之中,我也没再去打探过她的处境,其中有愧疚,也有不安吧,反正我还没做好准备再次进入一场梦。
之后陈倒是来了几回,但他好像已经忘记我和刘念认识的事,我也没有再向他打听她,仿佛在我这刘念已经是一个积满灰尘的人,我想伸手揩掉记忆的灰尘,但又怕看清楚之后便舍不得离去,所以那只伸出的手一直停在半空,无法回到母体,亦无法勇敢地前进。
“希望大家都能时来运转。”
在这之后,我像是突然的慢了下来,我不再抽烟,甚至一度戒掉了网络游戏,更加安静地在这个圈里独自打转,从一头走向另一头,行走在自己生活的闭环中,而刘念像是这之间偶然的裂隙,打开了这规律中的一个特殊的点,所以我得以在这规律内暂时出走,但又必要地迅速返回其中。
六月,我提前拿到结业证书,一个红色的小本,上面盖了章写上我的名字,然后就没有了。晚上我妈鼓励我再去考深圳的专科学校,听说现在南方机会很多,哪怕是汽修,也会有很多方向。我没有马上回答她,而只是低头扒饭,露出空空如也的手腕,展示着我所经历的一切。那天下午我走出校长办公室,靠在栏杆上发呆,从五楼往下望去,形形色色的人经过,有的抽烟,有的将头发变成很多不同的造型。我想,刘念也快高考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有没有逃到广州,有没有准备好大学的一切。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哑光的戒指,金色,在阳光下像是重新恢复它的熠熠,像是我们在舞厅的第一次见面,但其中却又微妙的不同。我用它对我的手指比划,从食指到中指再到无名指,最后才顺利滑进小拇指内,这是我第一次仔细看这枚戒指,上面是一朵玫瑰的造型,也像一张素未谋面的镜子,在阳光下,正朝我摊开它的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