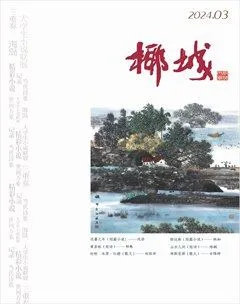自然主义视角下的迟暮再现(评论)
作者简介:石凌,甘肃灵台人,陕西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作品》杂志特约评刊员。在《文艺报》《北京文学》《作品》《奔流》《飞天》《延河》《收获》《野草》等报刊发表评论。散文集《素蓝如瓦》获第五届黄河文学奖、评论集《一川巨流贯风烟》获甘肃省第三届文艺评论奖,长篇小说《支离歌》获第八届黄河文学奖,二篇评论获“傅雷杯”全国文艺评论征文奖。
阅读沈学的小说《迟暮之年》,仿佛推开了一扇门,门里走来一个人——他是我们的父亲母亲,他是不太久远的我们自己,他“牙齿掉了大半……松弛的皮肉塌下来,如同被吸干了水分,骨头也往外突,像是要迫不及待出逃似的。”“他用他深陷的眼窝,再次端视起老伴的相片……将他那枯树般的手臂搭在灵桌上,呆坐良久,不断悲叹。”他“裸着那副皮包骨的上身,坐在门外的小椅子上乘凉,”一坐就是大半天……小说以自然主义笔法,冷静沉实地刻画了一位80岁的耄耋老人的暮年状况,小说对人物神情与心理的刻画达到了纤毫毕现的地步。阅读这篇小说的过程就像拿着放大镜仔细查看我们的父母,甚至是我们自己的暮年现状,冷寂的画面、迟缓的动作、怕死又不得不随时迎接死神的心情……令人不忍卒读。
《迟暮之年》选取的描述对象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他的回忆里没有叱咤风云的过往,没有缱绻浪漫的爱情,有的只是老夫老妻平凡岁月里的厮守与鸡零狗碎的点滴,正是这些看似平淡得毫无光泽的日子编织了我们每个普通人的一生。小说从老人清晨起床写起。在妻子去世后的三年里,再也无人关注老人是如何在黎明的鸟鸣声中醒来,颤颤巍巍地起床、生火、洗漱、做饭,然后坐在门前发呆,“老伴死后,老头一天大半时间都坐在家里发呆……老头住在村尾,离最近的邻居还要隔上一座土丘,另一边则是没有人烟的野山。平日里没有客人,正屋大门紧闭,侧屋也几乎不起灶火,小巷的门,被邻居建在路边的储物房挡了大半。如果没有人上门特意找,谁也不会关注到老头的死活。”冷漠本来是一种城市病症,乡村为何也染上了这种病候?应该从源头上寻找原因。在去乡村化的过程中,城市像一个个巨大的黑洞,不断地吸附着村庄的青壮年,于是,村里只剩下耄耋老人,一个又一个老人把儿女抚养大,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孤零零地守着老屋,悄然离世,无人问津。
如何对待老人,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体现的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做人底线。当一个村子的老人一个接一个地去世后,当一个村子不再冒起炊烟后,这个村子基本上就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审视,《迟暮之年》提出的课题是严肃的,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四十多年的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传统的宗法制结构正在土崩瓦解。当漂泊成为青壮年的人生常态时,老龄化社会已悄然到来,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孤零零地度过迟暮之年的阶段。关心、关注老年人的生存现状就是关心、关注我们自身。一个年轻作者能静下心来观察一位迟暮之年的老人,深入老人的内心世界体察他的心情,需要大情怀。从这个角度审视沈学的这篇小说,社会学的意义尤为突出。在老龄化社会大踏步到来的时候,在养老机构还不够完善的时候,在儿女各自忙着各自的工作生活的时候,每一个老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像小说中描述的那个老头一样,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做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发呆,一个人自言自语,一个人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慢慢地老去。
正如李书磊先生在《现代小说与城市兴起》一书中说的,“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二十世纪以来生活方式最明显也最深刻的变动就是现代城市的兴起。现代城市的興起极大地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组织方式,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经济分布结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这种改变对老年人来说,感受尤其明显。宗法制社会的老人,要么像《红楼梦》中的贾母一样,在耄耋之年仍然统御着一个大家庭,儿孙都要围着她转,讨她欢心。要么像刘姥姥一样,即使穷得揭不开锅,也有孙儿可以绕膝,也可以到其他亲戚家走动走动。然而,今天的老人谁还能回到过去?小说中的老头也曾梦想着能像他的父辈一样儿孙绕膝,有人嘘寒问暖,尽享天伦之乐,生活却以猝不及防的速度撕开了冷冰冰的内核。长久地被家人冷落使老人饱受孤寂之苦,老头不得不向子女撒谎说他不行了,有点余钱需要交代后事。三个孩子接到父亲的电话纷纷放下手中的事,一齐赶回老家。当他们见父亲仍然好好地活着后,抱怨一通又匆匆离开。正是与孩子们短暂的回归,让老人品尝了天伦之乐,以至于后来,“他神秘兮兮地同孙子坦怀,其实当时我是故意那么做的,谁让他们那么久不来看我。”从内心深处,老人渴望天伦之乐。然而,现实中,两代人之间观念冲突,无法和谐地生活在同一道屋檐之下,儿女要到城里讨生活,父母晚年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于是,孤寂就成了老人的常态。“现在,他只觉得这片村庄陌生,陌生不是因为新楼房的建立,而是耕耘一辈子的田土到头来失去了他的控制,自己仿佛是迟早要被驱逐的人。”孩子们不在身边,与他同龄的人一个接一个去世,昔日热闹繁忙的景象不再,在老人眼里,乡村作为他们生身的热土早已变为了冷土,而孩子们生活的城市却没有变成他们眼里的热土。年轻人要想体面地生活,就不得不去往城市,接受骨肉分离。老人在跟着子女去往城市经历了种种不适后,不得不回归乡里终老。老头的儿女像当今社会的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为了生计在城里奔波,在城里置业安家,也曾接老头前去一同生活。然而,在土地里劳作了一辈子的老人看不惯也过不惯拥堵的市民生活,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守老家。
如果不是村里一对新人结婚需要写对子,老头几乎被人彻底遗忘了。邻居找上门来,唤起了老人对过往的热切回忆——老人曾上过私塾,古文功底深厚,老来无事后常常抱着一本书在太阳底下啃半天——学习使老人的生活不那么空虚,也使他在80高龄后仍能继续为社会发光发热。小说重点写了老人为村民写对子这件事,意在提醒老年人,学习是抗拒空虚与无聊的良药。当然,一位老人即使因这一技之长在村民的红白事上能帮上忙,仍有可能被大家忽略,“老头分不清谁和谁是一家的,深知自己说话不怎么讨喜,索性自己斟酒自己喝。” 参加年轻人的婚宴反而给老人的心头平添了一层落寞。
小说是社会变迁的真实历史。因为小说家像解剖麻雀一样,拆解了社会结构,把社会与人性的黑洞赤裸裸地展示给人看。沈学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作者,能够把目光倾注到一个退出社会舞台的耄耋老人身上,是一种大悲悯大情怀。《迟暮之年》中,作者深入到老头的内心,体察他的所想所念,把备受家人与社会冷落的老年人的精神状态一笔一划地描绘出来,既体现了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关怀,也提醒人们应该关注老龄化到来后的社会现实。
在写作手法上,沈学继承了左拉的自然主义与卡佛的极简主义,描写客观,叙述冷静,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一段段描写就像一帧帧照片一样清晰、简洁、真实,一帧帧照片连起来,就是一部色调沉郁的电影,把乡村老人的凄凉晚景展现于读者眼前。语言生活化是这篇小说的另一个看点。生活化的语言源于作者对现实的深入观察与日常积累,“他一个劲地唉声叹气,每吸一口气,他的胸腔就塌进去一些。”“老头说着轻轻摇起脑袋,嘴角塌成一张弓”,这两个“塌”字把老人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生动地再现了老人迟暮之年的精神面貌。小说结尾让家人在摄像头上截取一个片断观察老头,比让老人孤零零地死去更耐人寻味。子女能否从老人久久不动的神情上读懂他的内心?这种开放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当然,从小说的结构来看,《迟暮之年》通篇采用散文笔法,调子沉郁,着意老头迟暮之年的精神摹写,对老人的过往,尤其是与老伴之间的关系着墨很少,矛盾冲突过于弱化,很难吸引普通读者一口气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