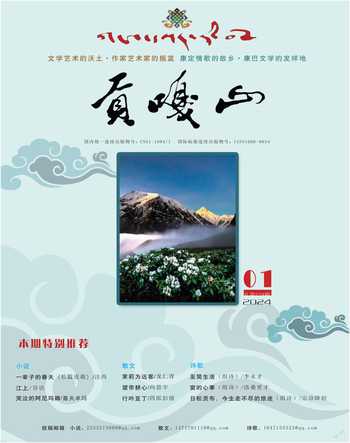哭泣的阿尼玛卿
嘉央卓玛
李想的手在屏幕上反复摩挲,始终没有按下发送键,房间里仅有的光源是他的手机,这光源逐渐熄灭,小西的脸也就逐渐熄灭。然后忽而亮起,和消息提示音一同响起的是李想的动作,一同结束的是李想的期待。
是老夏。
“小李,来活了!”
这片荒原永生永世都是这副模样,不会有任何改变,深秋已有严冬的冷酷,群山是一柄柄雪色的剑刺进天空的心脏。
荒原地是灰鼠皮的颜色,沾着在地上打滚时蹭上的泥灰。这灰鼠在沉睡,皮毛也就一点一点枯落腐烂,等到明年春夏或许会一点一点苏醒。风无法搬动这里的砂石,砂石们一日日孤独,也就一日日沉重,沉重到风无法搬动。
李想倚在车窗上,颠簸让他额头生疼,司机抽着一元一包的烟,劣质烟的味道刺挠他的鼻腔,但李想无路可逃,也無力可逃,车载音响播着他无法听懂的尼泊尔音乐。
多吉不会抽烟,李想跑了大半个县城,从唯一的商店里买到一包微微破损的中华,但当他把烟递给多吉,多吉只是腼腆笑笑,推开烟摇了摇头。
李想的藏语并不流利,结合手势多吉明白他是今天来的记者,没有说话,替李想扛起收音设备,往右边指指,一条极狭窄的小路,离多吉的住处还有四公里余,公路只修到这里。
四公里并没有什么,从李想深山里的家到乡小学有六公里,小小的李想已经学会摸黑走山路,在猫头鹰的呜咽里捕捉月亮,在田蛙鸣唱里追逐太阳。再后来他去了城市,依然习惯在黑暗里出走,不知道哪里是目的地,就随性走。他偶尔会在车流鸣笛里瞬间惶恐,看着绚丽的霓虹灯刹那不安。小西笑他昼伏夜出,他想说什么,但没有张开嘴。
在海拔五千余米的高原,氧气的稀薄挤压他的肺脏,碾弄他的咽喉,他在微微的耳鸣里抬头看天,天色未明,晨星是这顶厚重牛毛帐篷棚顶的缝隙,细小孱弱。多吉停下脚步,拿过李想胳膊上缠绕的包,他走得很重很稳,每一步都能留下脚印。
李想就跟着他,把全身的力气拴在脚上。
现在不必要再走这四公里,去年公路修到了野保站门口,这条公路吞吃掉了脚印,吞吃掉李想肺里尚存的氧气,吞吃他的记忆,有那么几秒的恍惚。他试着跟司机搭话,已经过了十几年了,他还是无法完全听懂这里的牧区方言,这样的方言里流淌着晦涩枯烈的风,如同使用他的牧人。
多吉也是牧场的孩子,李想问起他的家乡,他很认真地说着,李想从他浓重的鼻音和弹舌里读出了阿尼玛卿,他现在也只记得阿尼玛卿,记忆被公路吞没,被风吹落,他已经完全不记得那个复杂的牧村的名字。多吉耐心地重复了很多遍那串词语,然后问李想他的家乡。李想一瞬间想到了很多,想到那条昏暗而陡峭的山路,想到乡小学墙壁上剥落的灰,燥热的夏天总是那么漫长,从他幼年延伸到今天,他想到阿嬷皱巴巴的脸,永远没有洗干净过的泥手,冬天短暂但是阴冷难熬,在每个难以入睡的晚上撕咬他手上的疮印。
然后李想笑笑,说我的家乡在西南的一个小山村,那里不会下雪。
小西是北方姑娘,她的冬天大雪弥漫,李想收到过小西寄来的照片,小西穿着蓝色羽绒服和雪人躺在一起,笑得灿烂。那张照片被李想放在钱包内夹好多年,褪色的速度远远慢于李想的生命。
多吉的住处是非常简陋的牛场棚,棚里除了铺地的彩塑料布,被昏黄的马灯吞掉所有原有的色彩,万物都变得模糊混沌,李想像透过啤酒的酒液在观察这个世界。
但是没有任何一家商店会售卖这样破烂的酒瓶,棚顶棚壁的破洞都用棚底同色的塑料布堵住,堵住寒风的视线,却无法堵住寒风的侵入。
终于到了野保站,就在多吉的牛场棚的旁边,也许是念旧,多吉没有拆掉那个朽烂的棚子,白墙黑瓦的新野保站和身边干枯萎缩的牛场棚像光鲜亮丽的小伙与行将就木的父亲。
李想扛着相机进入了野保站,门没有上锁,也根本没有必要上锁。说是野保站,不如说是安置点,站内只有一个人,只会有一个人。李想要尽可能找到这个人脱离常人的地方,又要去摸索他正常活过的痕迹。
野保站短短的走廊上挂着站长与县长、书记,乃至州领导的照片,李想仔细观察这些照片,觉得想象有些痛苦,他无法想起这张脸,这张经历日晒风吹的黢黑的圆脸。
采访正式开始,因为多吉不会汉语,由李想这个半拉子来采访兼翻译。对于李想一本正经的问题多吉显得有些局促,尤其是面对镜头,他总是好奇地看着这个偶尔会发光的工具。但好在他足够配合,采访顺利结束,李想还要做的是去多吉日常工作的地方。
走出牛场棚,已经是正午时分,多吉从棚子边的角落里拖出一辆和牛场棚十分相配的摩托车。走了四公里的李想快被这辆摩托车气晕,但是真正坐上这辆车,他又庆幸自己是走来的,这辆漏油的摩托除了音响音量足够以外浑身都是缺点,李想的骨头快被抖散,又在抖散前到了多吉的巡视点。
这是真正的荒原,可能是来的季节不正确,这里生长着荒芜,杂草掩盖杂草,岩石雕刻岩石,河流重叠河流,僵硬地卧在视线的尽头。李想不相信这样的地方会有生物存在,多吉笑了:“这里动物多得很,夏天就来了,藏羚羊、野驴,还有野牦牛,我最喜欢的就是野牦牛……”
李想不能从他的描述里看到这样蓬勃的生命力,多吉又拧了油门,在猛烈的颠簸里李想闭上眼睛躲避风沙,等风稍微小些时他睁开眼睛,他们在一匹尚未驯服的烈马背上飞,这烂摩托突然有了生命一样向前横冲直撞,然后再突然停下,突然停下,李想眼前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光景——一具遗骸,看上去有了好几个月,头颅的皮肉已经被剥离,它有一双巨大的角,微微弯曲,像是在死去后还生长了许久。
多吉从摩托车上下去,走到尸骸前细细地抚摸,嘴里不断地重复什么,当他摸到牛角的结尾,话也走到结尾,他对靠近的李想说这头死去的野牦牛只有四岁,马上成年,“成年后还可以长大的,还可以长大的,要是还活着,可以活到它最威风的时候……”
这尸骨那样衰老,却甚至没有活到它的青年。
李想是什么时候第一次遇见小西的呢?是在课后炸串店打工时透过厚厚的油烟,还是在学校永远弥漫塑胶臭味的操场上?其实他们是同班同学,但是李想从来没有认真看过任何一个同学的脸,所有人的脸在他眼里都是陌生的,如果可以,他想活在一个没有脸的世界里。然后小西来了,带着微微上翘的尾音,一张鲜活明亮的脸闯进他的世界,击碎他的生活。没有客人时李想会发呆,他想自己可能已经死在了高三每个昏昏沉沉的午后,带着满眼的血丝和无处诉说的疲倦,现在的一切都是幻觉。
穿过短短的走廊,是一间简单的办公室,档案架上还是单薄地摆着几本册子,办公桌上整整齐齐地码着些书,李想蹲下身看了看书脊,那是几本简单的汉语学习教材,甚至有一本英语书。一支没有盖上笔帽的圆珠笔歪在桌子上,好像主人马上就要回来,或者已经回来过。
“很多人不相信这里会有动物,就像他们不相信阿尼玛卿是世界最高峰一样。”李想第一次听见这种说法,他说:“世界上最高的山是珠穆朗玛峰,你看,你也被骗了,是阿尼玛卿。”
60年代不具备测量水平的时候,也有人提出阿尼玛卿是世界最高峰,但是这个观点在成功测量出珠峰高度后就消失了,李想没有说话,他甚至也有一瞬间的怀疑。他在怀疑什么呢,怀疑用生命堆砌出来的登山路?怀疑现代的测量工具?
李想有時候也会想回到他的童年,他总能在傍晚昏黄的日光里闻到淡淡的血腥味,时间在流血在死去,但是他却好像永远长不大。再后来呢,他会想起自己在雨城暂住的一个晚上,清晨传来小动物的呜咽,楼下的小孩在踢打一只小狗。他下楼时小狗奄奄一息地趴在地上,他想把小狗挪到阴凉的无人经过的台阶上,小狗细短的绒毛下有小小的浅浅的心跳,小小的浅浅的温度,烫到了他的手心。
他很不情愿把自己和动物相提并论,但是那一刻他很可悲地感到这两个弱小生命的相同之处,小狗的心跳慢慢停止,他安静地让小狗的头枕在自己的胳膊上,感到自己的一部分也停止了心跳。然后他放下这具小尸体,去赶他的车,他有很远很远的路要赶。
李想推开野保站卧室的门,没有铺床,墙角摆着两卷卷好的铺盖,上面落了一层薄灰,没有人住在这个房间。
多吉最后一次抚摸牛角,站了起来,说:“我经常巡逻到这里,都会来看看这个朋友,它的脑袋朝向也是阿尼玛卿的方向,是一头幸福的牦牛,来生不会堕畜生道的。”李想不知道有没有来生,阿嬷临死前不停地抽气,一双枯树枝一样的手钳住李想的手,她睁大眼睛,却没有泪水流出,李想一点一点看着这双眼睛彻底变得混浊,在巨大的悲恸中卑劣地产生一种近乎解脱的快感,阿嬷有没有来生呢,她喜欢在闲暇时到村上的破庙去烧香听经,天天混着佛啊道啊给李想讲故事。
“多吉在藏语里是金刚的意思,你也是很有福气,很幸福的人啊。”“嘿嘿,我也喜欢这个名字,你的名字在汉语里有什么意义吗?”“没有意义。”“什么意义都没有吗?”“什么意义都没有。”李想,理想,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
李想的理想里有阿嬷,有小西,还有最难以启齿的他曾经特别向往的文学,他想这个无趣的世界,只有文字有意思,但毕业后选择了去当一个小报社的记者。他没有什么选择,这个世界从来不缺有才华的人,不缺有能力的人,不缺理想。偶尔他在刊物上读到小西的文章,读到一个与自己完全不相同的鲜活的世界的时候,他会停下,望着手上厚厚的茧子发呆。
李想走出了野保站,此行他没有收获什么,想到晚上要赶稿他就头疼,他再次望见那个牛场棚子,顶上的塑料布也已经失去颜色,他轻轻推开木门,光亮的透人让棚内的一切慢慢显露。
“你说外面所有的人都认为珠穆朗玛是最高的山,所以我永远不会离开这里的。”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理由,“我不能理解他们,就像他们不能理解我,我理解这里的四季变化,理解每种动物的行踪,但是我连藏文字母都不认识几个,更不用说复杂的汉文……”“不可能一辈子留在这样的荒地呀,难道在这里待到老,不难熬吗?”
棚内铺着一张牛毛毡子,和十年前一模一样,顶上接了电灯,炉子里有未燃尽的木柴。李想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景象,这个人在这样的地方待十几年,宁愿待在昏暗阴冷的棚子,也不愿意到新建的房间去住。
要告别的时候,多吉像来时一样送李想出去,在夕阳昏沉里李想又闻到了时间的血在流淌,他回头去看,多吉的身影在群山之中慢慢消失,像雪融化在雪里。多吉最后对他说:“其实阿尼玛卿可能一直在哭泣。”李想不太理解这句话。
没有人找到多吉的尸体,就在三天前.他骑摩托车到县上去采购生活必需品,路上遇到抛锚的车,于是下车帮忙,被拐弯的大货车连同他的烂摩托一起扫下山崖,山崖下是滚滚的河水。
李想的一生见过那么多的死亡,在他怀里停止呼吸的小狗,最后一刻眼睛里都还是他的阿嬷,一次他的受访人是一位误服农药的村妇,她在绝望里感受自己的身体机能一点点丧失,清醒着聆听死亡的脚步,他同样采访过抗癌十年的老人,他所有的亲属欺骗他手术结束后他的病就会根除,他充满希望在一个清晨猝然离开。
他终于要离开了,他对司机说能不能载他到那头野牦牛身边。司机豪爽地笑笑,说找对人了。这辆已经快报销的旧皮卡在山路上颠簸,李想再次来到这个朋友身边,它的皮毛已经基本被剥蚀干净,那双角却好像更大了一点。李想安静地看着它,像一场默哀,然后伸手模仿多吉的方法去数角轮,这是多么年轻的生命。它的头颅朝着神山,身躯也就腐烂得更加缓慢。
李想其实去过阿尼玛卿,他终于走到这神山的脚下,正好赶上转山的日子,桑烟煨起,经幡在烈风里翻滚。
山前有溪流,这一定就是这神山的泪水,无数人离开他的身边,这神山一日日哭泣,溪流也就一日日繁盛,在溪流的下方会滋养出新的沃土和牧草,于是有人会迁来,但神山的眼泪会流尽,终于所有的牧草枯萎,所有的牛羊死去,所有的孩子离开他。这神山还是在哭泣,尽管没有泪水。
李想回到狭窄的出租房,敲下最后一个字,看着眼前千篇一律的夸赞和褒扬,看着他用得腻烦的词句被套给其他人,又套给多吉,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反胃。把文稿交给老夏,他的手指最后一次掠过小西的头像,然后扔下手机,尸体一样直挺挺地倒在床上,他没有别的权利,还有什么都不去思考的权利。
眼前是一瓶快枯萎的花,全都来自看似寸草不生的荒原,有一种颜色似铁锈的花,还有一种很特殊的花,多吉说这是糌粑花,她生来就没有汁液,没有眼泪,也就永远没有流泪,不会鲜活,也就永远不会枯萎。
多吉把这瓶花摆在牛场棚里,他的枕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