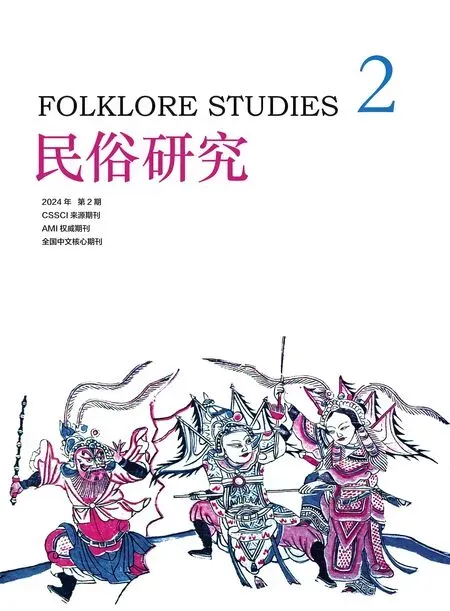技术情境中的国家礼制与地方神明崇拜
张佩国 黄小莉
宋廷分别于元丰元年(1078)、宣和五年(1123)两度派遣“神舟”出使高丽,这两场盛大的对外交往活动不仅反映了明州船舶生产、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情况,还包含了明州地方神明崇拜与国家礼制的互动。前辈学者对两浙神明崇拜的讨论多集中于东海神和妈祖信仰,其中亦有涉及“神舟”出使高丽在地方神明崇拜体系构建中的角色问题。(1)王元林、李华云:《东海神的崇拜与祭祀》,《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王元林:《国家祭祀与地方秩序构建中的互动——以唐宋元伏波神信仰地理为例》,《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陈国灿、鲁玉洁:《南宋时期圣妃信仰在两浙沿海的传播及其影响》,《浙江学刊》2013年第6期;陈国灿、鲁玉洁:《略论宋代东南沿海的海神崇拜现象——以两浙地区为中心》,《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金相范:《北宋和高丽海上外交的另一种面相——宣和五年国信使一行的海上遭难和下赐海神封号的举措》,姜锡东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27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85-100页;蔡相辉:《宋代明州的海外贸易和妈祖信仰的建立》,武世刚主编:《国家航海》第2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11页。事实上,“神舟”出使后朝廷对海上神明的关注,推动明州地区逐渐形成了以东海神为象征、以林氏神女及其他地方神灵为附属的神灵奉祀体系。学界关于明州海外贸易、造船技术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2)学界前辈讨论的话题包括但不限于明州对外贸易、造船技术,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选取部分表达敬意,如叶文程:《从泉州湾海船的发现看宋元时期我国造船业的发展》,《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4期;林士民:《明州港的造船业》,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宁波港海外交通史论文选集》,宁波日报社,1983年;林士民:《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明州》,海洋出版社,1990年;周庆南:《御笔碑和宋代明州造船业及外贸》,《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1期;李军:《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繁荣时期广州、明州(宁波)、泉州三大港口发展之比较研究》,《南方文物》2005年第1期;唐勇、刘恒武:《宋代宁波地区的造船业》,《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为后学理解整体历史实践中的明州社会提供了借鉴。明州造船技术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生产关系层面,它还是一个集物料筹措、船只使用、船户生活、对外贸易和社会意识为一体的整体社会实践,这样的整体实践虽远非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所提倡的“技术世界”(3)鲍辛格提倡的“技术世界”与“民间文化”反映的是现代与传统的辩证对立关系,以机械化、工业化、城市化为特征的“技术世界”与充满传统、民俗、国族元素的“民间文化”无法避免地互相融合。无论是现代化的技术还是前现代性质的技术,都无法与民间文化/地方文化保持泾渭分明的状态。参见[德]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户晓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却能搭建一个技术与民间社会文化相互交融的“技术情境”。
“神舟”出使是宋代明州高超造船技术的表达,褪去“神舟”出使之光环,明州船业是否能持续繁荣?神明信仰是否在船只生产与日常生活之间起到了文化联系之作用?若将话题置于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复杂体系的场域中讨论,明州作为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江南城镇,其与中央王朝并非“礼制下行”或“地方自主”式的简单的控制与对抗的关系。汉学家华琛(James Watson)认为,在“神的标准化”过程中存在一种弹性机制,其本质是国家对民众行为的关注而非信仰表达。(4)[美]詹姆斯·沃森:《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960-1960年)》,[美]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陈仲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92页。沃森通常译作华琛,故本文在叙述时采用后者,特此说明。科大卫(David Faure)认为,在地方社会成员的实践中,存在一种“重要礼仪标识”,这种标识建立在“正统”概念之上。(5)[英]科大卫:《从礼仪标签到地方制度的比较——“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介绍》,[日]末成道男总主编,刘志伟、麻国庆主编:《人类学与“历史”:第一届东亚人类学论坛报告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33-239页。张士闪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指出,地方在制造和使用“礼仪标签”时,普遍存在着以“礼”“俗”为表征的不同话语流向,并且呈现出多主体交互建构的特征。(6)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在明州民间信仰的场域中,国家始终关注地方信仰的正统性、规范化等问题,而正统性对地方信仰的传播、延续也至关重要,因此民间信仰在进行自我表达的同时,也注重贴近国家正统。国家礼制与地方信仰的双向流动,正是一种“礼俗互动”的表达,可视为华琛“标准化”、科大卫“礼仪标识”解释框架的一种深化。本文从“礼俗互动”(7)张士闪:《礼与俗:在田野中理解中国》,齐鲁书社,2019年。视角出发,围绕明州造船的“技术性”和“社会性”两个层面,考察地方神明崇拜与官方礼制之间的互动机制,从而试图理解两宋时期船舶情境下的明州社会结构。
一、物力维艰:“神舟”归来后明州的船舶生产
北宋时期,朝廷在多路设置船场,形成了南北各自为重的造船格局。长江之北以淮南路的楚州船场和陕西的凤翔府船场为代表,长江以南的船场则主要集中在江西南路、两浙路、荆湖路和成都府路四处。在这些官营船场中,两浙路船场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又以明州(庆元府)(8)庆元元年(1195),明州升为庆元府,见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717页。、温州、婺州、台州为主要造船基地。温州、明州擅造巨型海船,“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9)吕颐浩:《论舟楫之利》,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4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56页。,元丰元年(1078)作为国信船出使高丽的“神舟”产自明州,说明其造船技术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梦粱录》亦载:“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10)吴自牧撰:《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1页。然而,人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必然受到技术和知识的调停,“神舟”出使和造船技术一方面推动了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必然与社会传统产生冲突。明州在元丰“神舟”出使高丽后正式取代登州成为两国往来的重要枢纽,来往船只沿明州-定海-外洋-礼成江一线航行,形成了“初高丽使朝贡,每道于明供亿繁夥”(11)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5061页。、“异时高丽入贡,绝洋泊四明,易舟至京师”(12)王庭秀:《水利说》,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4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98页。的盛况。崇宁年间,明州设置了来远局接待使臣,接待之费增加了地方财政负担。出使高丽的“神舟”归来后,明州地方造船业受到官方重视,同时也面临着危机,如木材、灰油等原料的短缺。
徽宗政和七年(1117),楼异注意到明州造船业的发展压力,上疏提出几点建议:其一,将温州的船场迁到明州,以减轻工役往返、船场管理的负担;其二,开垦广德湖,以其田租作为造船和接待使者的经费来源;其三,创建高丽使行馆,作为接待高丽使者的外事场所;其四,完善与高丽交往的船舶系统。任明州知州期间,楼异着手落实谏言中的设计,且徽宗“出内帑缗钱六万为造舟费”(13)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11163页。,支持楼异的船场改革。浙东台州、温州以及明州昌国县出产的金松、松、杉、樟、檀、楠等都是造船的上等木材,其中松木和杉木常被明州船场用来制作龙骨、壳板。温州船场的木料主要抽自木商,“除材植取于客贩抽解,贴买不多”(14)楼钥:《乞罢温州船场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63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4页。,而明州造船所需木材主要从外地购入。在楼异的谏言下,温州船场短暂移入明州,但由于明州船场极易受到波动的木材市场的影响,同年(1117),两浙转运司上奏将温、明船场合并后移到镇江府,不久又移到秀州通惠镇。此外,船场所需的其他物料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物料强取于民,而地方监司、守令乃至廉察使等对这一问题漠然处之,以至“并系敷配于六县人户,逐等第强取于民”的情况愈演愈烈。朝廷不得不明文规定“如尚敢依前抑配取于民户,不还价钱,官并当远窜岭外,人吏配海岛。廉访使者常加觉察以闻”(15)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125页。,才使得情势稍减。另一方面,楼异耗时近一年主持泄湖为田的工程,政和八年(1118)广德湖之湖田竣工,“治湖田七百二十顷”,募民佃租,“岁得谷三万六千”。(16)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11163页。他还修筑西坝,完善了湖田系统。这一年明州财政收入已经能够支持打造百余只高丽坐船(17)楼异:《乞与高丽纲梢工添米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28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7页。,这些新造海船设于招宝山海道口(18)招宝山是出海必经之港口,元丰出使的两艘“神舟”也曾停泊于此。,供高丽使者使用。楼异继任明州后,又用朝廷赐钱建造了两艘“锦帆朱鬛,威耀若神”的海船,且“投赐铁符于定川之宝山,海涛以镇之”(19)王厚孙、徐亮纂:《至正四明续志》,《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6564页。,以铁符祈求平静的航行环境。为了应对日益频繁、规模日趋庞大的高丽使节和商团的到来,官府亟须设立与形势发展相匹配的官僚机构,如建设新的馆舍、提供食宿办公、安置随行人员以及拓展贡赐货物堆放和交易的场地等。因此,楼异主持完善了接待场所,“依元丰故事造画舫百柁,置海口专备丽使”(20)王厚孙、徐亮纂:《至正四明续志》,《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6564页。,以承办与高丽的来往业务。
楼异的治理暂时解决了明州的问题,但实际上明州造船在木植、物料筹措方面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且广德湖的改田措施给鄞县东乡的农田灌溉埋下了隐患。实际上,楼异上任之后,明州接待高丽使节的规格、耗费越来越高,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南宋初年政局初步稳定后,朝廷先恢复了有木植优势的温州船场,继而恢复了明州、华亭两处船场,以应对漕运、边防对船只的需求。但明州船场在木材、物料筹措方面的问题在漕船、纲船、战船打造任务中再次显露。
从官方给明州的造船定额可以看到明州船场生产力的下降。徽宗时期,明州造船每年以六百只为额,其后明州打造船只的数量逐年减少。政和四年(1114),朝廷诏令两浙转运司各打造三百料平底船三百只,江南东西、荆湖南北转运司各打造五百料平底船三百只,供开封使用。(21)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124页。建炎间(1127-1130),温州造船年额为三百四十只,但“近年财赋窘乏,打造不曾及额”(22)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127页。。绍兴元年(1131),朝廷诏两浙路转运司打造二百五十料的纲船三十五只(23)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127页。,楼钥也说南宋初温州船场只“岁造百艘以供漕运”(24)楼钥:《乞罢温州船场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63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4页。,可见打造船只之力胜、数量都在减小。“官舟少而漕运多”的情形在南宋初年屡见不鲜,官府除了“拘收应干例外官司舟船以备漕运”,还另外“因出度牒。即上户市舟。又刷百司舟船应副”(25)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88年,第1659页。,但这些措施都无法供应漕运所需船只,最后调用明州、华亭船场的船只才“足以供转输之用”(26)楼钥:《乞罢温州船场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63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4页。。绍兴四年(1134),两浙船场有所恢复,为了缓解漕运压力,朝廷“欲令两浙、江东西路各造船二百只,专充运粮使用”(27)朱胜非:《乞令两浙等路造船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6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1页。,再次扩大造船之额,但明州船场所需木材等资源已经无法供给,造船年额无法达到规定数额。南宋中后期的明州船场几乎不曾走出过生产困境,朝廷所定船额也很少超过一百。孝宗隆兴元年(1163),令“明、温州各造平底海船十艘”(28)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131页。,这与楼钥描述的隆兴初年的明州船场情形相符,“岁朘月削,每年止造十船”(29)楼钥:《乞罢温州船场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63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4页。。乾道五年(1169),明州依令打造多桨战船五十艘(30)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133页。,淳熙元年(1174)再次裁减两浙路每年造船之额,“温州元额一百二十二只,今减作五十只”(31)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135页。。嘉定十四年(1221),沿海制置司给温州“降下船样二本,仰差官买木,于本州有管官钱内,各做海船二十五只”(32)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139页。,可见原本木植颇丰的温州船场也遇到了生产困境。
此外,船场在役力雇佣方面也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如温州船场船工大多是兵卒、军匠,“官吏五人、兵级二百四十七人”(33)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127页。。为了降低人力成本,绍兴元年(1131),转运司对船场的监官员额进行缩减,“今欲除选留监官一员并兵级一百人在场应副打造外,其余官兵并行裁减,内官员依省罢法,兵级拨归本州,充厢军役使”(34)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127页。。而明州船场则试图通过减少雇佣民间工人的方式缩减开支,如绍兴五年(1135)朝廷采纳李迨谏言,令温、明、虔、吉四处船场“募兵卒牵挽,使臣管押”(35)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11593页。,在减少支出的同时也能减轻造船之于百姓生活的负担。
二、渔陆不得:技术情境中的船只与地方社会
宋廷与高丽、日本的交往在“神舟”归来之后更加密切,对地方造船也愈加依赖,技术与明州社会的关系日趋复杂,这种复杂关系不仅表现为人地矛盾,还体现为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在以船舶生产为中心的技术情境中,除船场、役工之外,船户的生存状态也是重要的考察维度。
绍兴年间(1131-1162),明州船场因木植、灰钉供应等问题再次陷入生产困境,船只生产力急剧下降,但此时江海防重要性日益提高,官舟十分缺乏。在对外贸易发展、造船技术普及的背景下,明州地方以航海为业的船户数量增多。于是,转运司和船场将解决官舟数量不足的出路转向了征调民间船只。绍兴二年(1132),福建路率先征用民船巩固海防,“乞令本路沿海州县籍定海船,自面阔一丈二尺以上,不拘只数,每县各分三番应募把隘,分管三年,周而复始……其当番年分辄出他路,及往海外不肯归回之人,重坐其罪,仍没船入官”(36)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128页。。朝廷对征用船只的大小、征调的时间都作了规定。此外,为了保证按时当番,船户当番前半年只能于本地近海海域活动,期间还要接受官府对船只的检查,有时还需进行集中校阅,这对船户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影响。此后,征调民船成为应对海防舟船不足的惯例。端平年间(1234-1236),庆元府(明州)每年组织本府、温州、台州三郡之民船前往镇江、定海等切要之地增强防御。将三郡数千只民船分为十番,“岁起船三百余只”(37)吴潜:《条奏海道备预六事》,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9页。,分拨在镇江、定海戍守,其中“岁发一百四十只,前往镇江府,防拓江面”(38)吴潜:《奏行周燮义船之策以革防江民船之弊乞补本人文资以任责》,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5页。。宝祐四年(1256),朝廷令沿海制司“起发温、台、明系籍民船,摆布岑江等处,以防外洋之寇”(39)吴潜:《奏论海道内外二洋利害去处防贵周密》,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0页。。征调的民船数量一方面证实了两浙地方具有深厚的船业基础,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船户们日益增长的供船压力。除了承担江海防,船户有时还需要执行额外的差役,“凡遇起发官物和雇舟船,百姓惊惧,如遭驱掳,呻吟怨呼之声所不忍闻,道路不通,商旅断绝”(40)崔敦礼:《代论起发官物雇舟之数札子》,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69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2页。。在承担官府纲运任务时,损坏丢失之物皆由船户赔偿,“监锢禁系,动经岁时,往往破家竭产,终不能偿其一二”(41)廖刚:《漳州到任条具民间利病五事奏状》,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39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4页。。船户不仅要承担物质损失,甚至还面临牢狱之灾。频繁且严酷的船只征调,扰乱了船户的正常生活,甚至出现了凿沉船只逃役的情况。“盖因军兴以后,船户例遭驱虏,民间莫敢置船”(42)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982页。的局面使得从民间筹措漕船、江防战船也越来越困难。若将船只生产任务交予明州船场,则往往因物料和经费短缺而作罢。
此时,明州船只生产的矛盾已经不仅仅在于调度生产原料层面了,船场的问题已经无法再像楼异那般调整治理,加之彼时情境下的朝廷无暇顾及这些问题,因此明州船只征调之弊病持续了一个世纪才被郑重对待。宝祐四年(1256)春,吴潜以观文殿大学士授沿海制置大使、知庆元府(明州)。他上疏描述了庆元、温、台三郡边海百姓对于起发隘船的困扰:“迨至每岁发船,则县道召人,纠举白船,以补欠阙之数,又乘此以为骚扰乞取之计。”(43)吴潜:《奏行周燮义船之策以革防江民船之弊乞补本人文资以任责》,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5页。在征调过程中,不管舟之大小皆被征用,但征调的对象却不包括有钱、有势、有权之人。因此,三郡之民“陆者不得安于陆,渔者不得安于渔”(44)吴潜:《奏行周燮义船之策以革防江民船之弊乞补本人文资以任责》,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5页。,在吴潜的争取和台州漕贡进士周燮的建议下,两浙海域开始施行“义船法”:“其法以一县当出之舟若干只,分乡都之广狭,令凡有舟之家,以大小丈尺,均出钱物,置备舟只,以应每岁当发之额。其有舟而止及七八尺以下者,不在纠率之数。且不待官司之文移,至期则合从应调。船必坚牢,杠具必整齐,人丁必强壮。”(45)吴潜:《奏行周燮义船之策以革防江民船之弊乞补本人文资以任责》,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3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5页。将原来分散到每户的番役集中到乡都,允许以出资的方式替代征调,减少了对民众的普遍征调,这使得沿海两三千里的船户能安心维持生计。
在地方官吏通过政治措施缓解征调船只造成的社会矛盾的同时,地方民众也在自求出路:一是依靠船只和航海经验成为海寇,以逃避征调;二是将希望寄托于神灵,在官府主导构建的神灵体系中寻求慰藉。

面对肆虐的海寇,官府的治理可分为三类。其一,朝廷通过设置巡检寨、建立户籍等方式管控涉海人群,并施以保甲法来严控沿海地区人口的流动。(56)张宏利:《宋代沿海地方社会控制与涉海群体的应对》,《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其二,统一军事行动,展开抓捕。嘉定十一年(1218),“温、台、明、越四郡海道辽阔,盗贼出没不常”(57)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876页。,时任庆元军府知州兼沿海制置司公事的韩元礼认为,这是由于四郡只负责本地事务,在对付贼寇方面没有展开统一的缉捕行动,因此盗贼得以随意出入。此后,海寇的缉捕由沿海制置司统一组织,沿海诸州予以配合。其三,制定新的船舶、航运管理方案,从制度层面减轻民众压力。淳祐年间(1241-1252),时任庆元知府的颜颐仲认为,应该“蠲积赋,减折价,浚河渠,损征额”(58)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5017页。,通过保障百姓生活的基本条件来降低矛盾激化的可能性,“或有违戾,许民越诉,不以荫赎,悉坐违制之罪,庶几海岛之民可以安生乐业”(59)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5017页。。但这些控制海寇的措施收效甚微。实际上,在清剿海寇的过程中,官府的船只根本不足以提供交通支持,往往还得征调民船。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部分不堪重负的沿海之民沦为海寇,而那些能够于重重征调中勉强维持生活的船户又增加了抵御海寇的责任,因此两浙沿海之寇循环滋生,无法肃清。加之,朝廷规定“贾人由海道往外蕃……毋得参带兵器或可造兵器及违禁之物”(60)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4561页。,进一步削弱了商旅、渔船在海上航行的安全感。因缺乏防御武器,一旦遇到海寇,这些船只的安全很难得到保障。海盗跨区域犯案,行踪飘忽不定,围剿的成本、难度都非常高。因此,出海之人大多会在出发前虔诚地祈祷神灵庇佑,甚至举行盛大的发舶祭祀仪式,祈求航行顺利,这影响了民间信仰秩序的建构。
完全不受技术影响的民间文化只存在于构想中,“人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必然受到技术和知识的调停,而技术和知识在根本上是属于人的、社会的范畴”(61)[德]艾约博:《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韩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页。。在以造船技术为联结的整体情境中,地方官府通过宏观手段调控生产,缓解明州造船压力,却收效甚微,以至于用船压力从船场转嫁到船户群体,船户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探索出新的自洽方式,由此产生了新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结构。
三、国家礼制中的神明与地方信仰中的神明
造船技术之于明州地方除了展开纯粹技术性和生产性的解释外,也能成为民间信仰建构分析的重要媒介。明州地方的神明崇拜与船舶、国家礼制间存在多层级的、复杂的互动。明州海神信仰与国家礼制的互动可追溯至元丰元年(1078),该年出使高丽的船队返程,安焘等使臣以“东海之神已有王爵,独无庙貌”(62)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7170页。为由,建议朝廷在明州修筑东海神庙,东海神的祭祀庙址正式从莱州迁移到明州,这是明州东海神崇奉首次获得国家礼制认可。崇宁二年(1103),刘逵、吴栻出使高丽归来,上疏为东海神请封,于是东海广德王庙获“崇圣宫”之庙额,每年度化一名道士供奉香火(63)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45页。,以保证神祠香火绵延。大观四年(1110)六月,王襄出使高丽返回后也为东海神请加爵号,以回报神灵庇佑,朝廷因此封东海神为“助顺渊圣德王”,地方官府则重新修葺了东海神的庙宇,同时在该神两侧增添了风雨侍神。(64)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5238页。宣和五年(1123),路允迪等使臣归来后请旨加封东海神“显灵”爵号,其神祠获“渊德观”之额。(65)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6410页。此时东海神已经获得八字王爵“显灵助顺渊圣广德”,遵循了“赐命驭神,恩礼有序”(66)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2561页。之原则。纵观数次国信海船出航,平安归来的使臣们不仅在内心感谢神灵的护佑,还通过请旨建祠等方式切实地表达他们对东海神的崇敬。此外,明州地方的其他神灵也因宣和出使得到了褒封:林氏神女获得“顺济”之庙额(67)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18页。,鄞县灵应庙鲍郎神获封“忠嘉”爵号(68)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5128页。,定海县昭利庙演屿神得“昭利”庙额(69)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6358页。。护航海上的叙述为东海神信仰的传播提供了故事空间和叙事载体,国家礼制的认可使得地方社会捕捉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空间感和灵活性,加速了神明信仰的地域化传播和地方神明信仰的发明。
建炎南渡所用“明州楼船”再次将明州船舶引入历史分析的视野,证实了技术与社会融合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建炎南渡以明州船舶为技术支持,同时也建立了明州民间信仰和国家礼制的多元联系。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底,吕颐浩、赵鼎等上疏讨论避难海上,“今若车驾乘海舟以避敌,既登海舟之后,敌骑必不能袭我。江、浙地热,敌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复还二浙”(70)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88年,第578页。。于是十一月二十四日,朝廷遣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枢密院提领海船张公裕前往明州募舟。十二月二日,张公裕复旨称已筹集千舟。此时金军已逼近临安,高宗听从吕颐浩建议,准备入海避敌。然而仅明州一地的船只无法承载庞大的南渡队伍,于是监察御史林之平奉命招募闽、广之海舟,“故大舟自闽中至者二百余艘,遂获善济”(71)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88年,第584页。。明、闽、广等多地海舟聚集后,十五日“(高宗)上自州治乘马出东渡门,登楼船。宰执皆从之。诏止亲兵三千人自随,百官有司随便寓浙东诸郡”(72)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88年,第586-587页。。建炎四年(1130)三月,“辛酉,上御楼船发温州”(73)李埴撰:《皇宋十朝纲要校正》,中华书局,2013年,第619页。泛海北上。可见高宗流亡温、明、台所用的海船为楼船。当时的楼船可分为两种:一是精美装饰的高级游船,另一种则是配置于沿海水域的高级战船。由扈从人员构成可以推测,高宗出海御舟应是第一种,即装置精巧、雕梁画栋的楼船。据载,当时随高宗乘船出海的近侍主要有赵鼎等少数人,“于是扈从泛海者,宰执外惟御史中丞赵鼎、右谏议大夫富直柔、权户部侍郞叶份、中书舍人李正民、綦崈礼、太常少卿陈戬六人、而昕夕密卫于舟中者、御营都统制辛企宗兄弟而已”(74)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88年,第589页。,护卫亲兵在其他船只上,百官有司均自行安置,随行近侍为数不多,加上舟师、舵手,推测其数量在五十人左右。按照《武经总要》所说,一人为二石(料)力胜计算,高宗所乘楼船应为力胜一千料左右的游船。作为战船的楼船需放置作战器械,为将士作战预留活动空间,其力胜大致在二千料至三千料。“(杨)么陆耕水战,楼船十余丈,官军徒仰视不得近。”(75)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11721页。作战楼船是一种集装载与战斗于一身的大型海船,军事装备齐全,适合远攻近战,然其船身较高、重心不稳,不适合远航,因此多出现在内河及沿海水域。由于技术、战术等各方面的限制,这种技术水平较高的海船很难普及,因此在水军中尚未普遍装备,“建康战船殊未如法,楼船绝少,惟海鳅稍多,不足以威敌”(76)王之望:《乞招抚司与江东帅司措置建康楼船奏议》,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9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5页。。假设高宗出海御舟是作战楼船,那么百官有司也不用自行安置,至少随船亲卫也不应只有辛企宗兄弟。出海逃亡的船只由温、明、闽、广等地募集,十日内筹集千舟,并且兼具楼船、大舟,可见两浙路有很雄厚的船业基础。
幸得舟船相助,高宗一行顺利逃往定海,进而从海路继续南渡,最终逃过金军追击。御舟途经明、台、温三州海道,在海上漂泊数月。近海海道凶险,有随时触碰暗礁的可能性,两浙路船只多为尖底方尾船,不仅速度快,还能抵御风浪,而且采用水密隔舱技术增强了防渗性,通过灵活多变的船帆设计提高了稳定性。明州地域精湛的造船技术为高宗海上出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持,可以说两浙发达的造船技术在巩固南宋政权稳定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建炎四年(1130)二月,金将兀术自明州北撤,一路纵火焚城,明州、临安、平江府数日烟火连绵,很多前代帝王及五岳四渎、名山大川的神祠庙宇都在这场战火中毁坏殆尽。明州在此次战火中受灾严重,“故庐焚荡,一物不遗”(77)楼钥:《跋先大父嵩岳图》,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6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02页。,呈现出“残破之余,荒芜单弱”(78)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14051页。的衰败景象,东海广德王庙也在这场战火中被毁。金军撤退后,朝廷立即遵照建炎元年(1127)五月敕书“如祠庙损坏,令本州支系省钱修葺,监司常切点检,毋致堕坏”(79)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88页。的要求,令祠庙所在州县筹钱“渐次修盖,如法崇奉。其不经焚烧,或有损坏去处,亦仰依此施行”(80)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89页。。为感谢神灵对社稷安定、航海安全的庇佑,朝廷于建炎四年(1130)四月下诏敕封沿路州郡之神灵,“应神祠庙宇已有庙额、封号处,令太常寺加封;有封号、无庙额去处,与赐额;其未有庙额、封号,令所在官司严洁致祭一次,钱于本路转运司系省钱内支破”(81)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89页。。建炎四年(1130)的加封自然包含了最具正统象征意义的东海神,在其原有封祀、庙额之上,加封“祐圣”,爵号由原来的六字变为“助顺祐圣渊德显灵”八字。朝廷对明州地方的其他神明也都保持了制度层面的重视,比如鄞县灵应庙以“护风涛若平陆”获赐“广灵”爵号(82)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6351页。,定海县越王山麓的演屿神亦获“褒应王”爵号,崇列八宇,其子侄九人皆赐列侯(83)梁克家纂:《淳熙三山志》,《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7864页。。朝廷通过封赐爵号等方式表达对海神的崇奉,这从制度层面保障了以东海神为象征的海神奉祀体系的延续和完善,是国家礼制持续规范明州地方海神崇奉的具体表达。
绍兴二年(1132),定海县组织重建战火中被毁的东海广德王庙,但战争极大地损害了地方经济,很难筹措经费,导致神庙的重建过于潦草、简单,“遂祀神于廊庑,以观为主而神附之”(84)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5239页。。绍兴三十一年(1161),李宝统领水军三千、战船一百二十艘于胶西(今山东胶州)陈家岛大败金军,朝廷在褒扬李宝的同时,也特意下文感谢东海神的襄助。乾道五年(1169),太常寺少卿林栗言:“自渡江以后,惟南海王庙,岁时降御书祝文,加封至八字王爵。如东海之祠,但以莱州隔绝,未尝致祭。”(85)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2488页。这说明在意识层面,南宋士人还是认为东海神的祭祀圣祉在莱州,可见建炎初加封东海神后,其祭祀仪礼主要停留在制度层面,抑或是特殊时期常规祭祀难以为继,使得社会意识远远滞后于制度设计。由于四海海神只有南海神的岁时降御书祝文、祀典如常,于是林栗“请依南海特封八字王爵,遣官诣明州行礼”(86)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2488页。,首次将“东海”二字加封到爵号上,于封赐、祭祀层面将东海神放到与南海神同等的位置。他建议每年立春在明州祭祀东海神,祭祀仪典参照广州祭祀南海神之例,“关报所属请降香祝,下明州排办,差官行礼”(87)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26页。。朝廷强调东海神在岳镇海渎祭祀体系中的有效地位,是国家意识在神明崇拜领域发挥主导性的体现。这也说明明州东海神祭祀在意识领域最终取代登州东海神祭祀,在明州海神信仰中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
元丰“神舟”归来后,明州东海神信仰进入国家祀典体系;宣和“神舟”归来和高宗南渡之后,林氏神女、鲍朗神等地方神明被纳入“标准化”过程。若以“神舟”为明州地方信仰秩序建构分析的关键点,明州地方社会信仰在国家礼制主导下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东海神为尊、以林氏神女及其他地方神灵为附属的地方神灵奉祀体系。需要注意的是,在以东海神为尊的明州,地方神灵奉祀均借“神舟”故事、官方祀典、神祠庙宇等载体传播和延续,不过东海神信仰是由国家礼制推崇建构,而林氏神女、鲍郎神、演屿神则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地方表达。在技术的整体情境中,船只征调、海寇劫掠给船户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民众渴望获得神秘力量的庇护,自下而上的需求改变了明州地方神明的秩序和功能,形成了独特的地方信仰文化,即国家礼制对明州东海神信仰的强调并不总是与地方自身的信仰实践保持一致。实际上,国家和地方社会意识存在一个渐进的联结过程,“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礼’与国家政治结合成为一种文化制度,是有着一个逐渐联结的过程的,‘俗’则在地方生活的运作中呈现出民间‘微政治’的多种社会样态”(88)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明州地方的林氏神女、鲍郎神、演屿神便是明州信仰中“俗”的多种样态之一。
宣和五年(1123),林氏神女获得“顺济”庙额,由民间“淫祠”升格为国家“正祀”之神,在瓯闽地区传播开来。(89)徐松辑,刘琳、刁忠民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18页。绍兴三年(1133),明州市舶司北舶舟长沈法询自兴化分香,修建了第一座神女祠(90)程端学:《灵济庙事迹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3页。,此后神女信仰不仅在明州传播、延续,还延伸出祈雨、捕盗等其他职能。神女新增职能不断获得官方的认可,其爵号日益显隆。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月,林氏神女因救助海上船只、平息风浪等功,被封为“灵惠夫人”(91)程端学:《灵济庙事迹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2页。。此后,林氏神女的职能不断延伸,不仅在缉捕盗贼方面声名远播,而且在抗敌、祈雨方面闻名遐迩。绍兴三十年(1160)十二月,神女因为“海寇啸聚江口,居民祷之,神见空中,起风涛烟雾,寇溃就获”获封“灵惠昭应夫人”。(92)王厚孙、徐亮纂:《至正四明续志》,《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6566页。孝宗乾道三年(1167)正月,因缓解兴化疫病、助捕海寇有功,朝廷封其为“灵惠昭应崇福夫人”(93)程端学:《灵济庙事迹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2页。。淳熙十一年(1184),因帮助福兴都巡检使姜特立捕温、台海寇,神女获封“灵惠昭应崇福善利夫人”(94)程端学:《灵济庙事迹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2页。。南宋中后期的明州深陷技术情境的漩涡——频繁的征调、附加的差役、肆虐的海寇,林氏神女在这样的情势下发展出捕盗职能,这种由地方发明出来的信仰功能逐渐为国家礼制所认可。绍熙三年(1192),林氏神女晋封为“灵惠妃”(95)程端学:《灵济庙事迹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2页。。庆元四年(1198),温、台遇旱,祈之降雨,“封灵惠助顺妃”(96)程端学:《灵济庙事迹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2页。。宝祐二年(1254),福建遭遇旱灾,神女显应降雨,朝廷封其为“助顺嘉应英烈协正妃”,并对其父母、女兄、伴佐进行赐封。(97)程端学:《灵济庙事迹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3页。景定三年(1262),因祷捕海寇显应,林氏神女获封“灵惠显济嘉应善庆妃”(98)程端学:《灵济庙事迹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3页。。国家通过加封神明承认地方社会俗情的同时,也通过推行帝国礼仪整合地方信仰。淳祐十二年(1252),“诏海神为大祀,春秋遣从臣奉命往祠,奉常其条具典礼来上”(99)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847页。,官方组织盛大庆典规范地方神女信仰、祭祀程序,构建地方实际可见的“礼仪传统”。鄞县城外的灵应庙供奉后汉人鲍盖,其被视为鄞县地域守护神。宣和六年(1124),路允迪以“蹈海无虞”奏请为其加“忠嘉”二字(100)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5128页。,楼异亦在“神舟”话语情境下为其请封“惠济”爵号;定海县越王山麓供奉唐时福建观察使陈岩之长子,宣和二年(1120)降神迹于明州,鄞人置庙祭祀,称其为演屿神。(101)梁克家纂:《淳熙三山志》,《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7864页。宣和六年(1124),“(路允迪)与同舟之人,断发哀恳,祥光示现,然福州演屿神,亦前期显异,故是日舟虽危,犹能易他柂”(102)徐兢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下),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131页。。使臣们以护航有功为名为其请封“昭利”庙额,使其进入明州地方的海神奉祀体系。
虽然鲍郎神、演屿神在礼制层面获得了国家的认可,但其信仰内容与崇奉仪式并未像东海神、林氏神女那样“标准化”“礼仪化”,而是充满了地方表达。因其海上护航的功能,鲍郎神、演屿神才得以进入国家认可的奉祀体系,但在地方民众的崇奉实践中,它们主要是作为地方多功能神庇佑域内信众。如面临船只征调、海寇侵袭、水旱灾异等困境时,百姓多向演屿神、鲍郎神求助,以至于二位神灵在史料中主要与祈雨、救疾、抗贼等事件联系在一起。
在百姓的观念里,鲍郎是一位有求必应、关心疾苦的神灵,不仅捍灾御患,水旱、疾疫必祷,还消弭奸芽乱萌:“今雨旸,祷必应;民有疾苦、急难,则呼吁之。歉岁贵籴,神能在海中招客舟使之来。功在鄞,不可殚纪。”(103)梅应发、刘锡纂:《开庆四明续志》,《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5948页。楼异废广德湖为耕田,短时间内田赋收入增多,长期看来却破坏了定海、鄞县的农田灌溉系统。广德湖造田工程竣工不久,农田灌溉水源不足的问题就已经暴露。后来湖区每每遭遇旱灾,百姓认为是鲍郎神显灵抗旱降雨,于是楼异奏请朝廷加封其为“惠济王”(104)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5128页。。鲍郎信奉传统悠久,乡人视之为祥风甘雨,祭祀不绝,“春而祈,秋而谢,牲肥酒香,箫鼓喧遝无虚日,至诞日远近辐辏”(105)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6351页。。嘉定四年(1211)九月,参知政事楼钥上疏,“时和年丰,神有大赐于民,愿显扬其先以及后昆”(106)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6351页。。由此,朝廷对鲍盖的家属进行褒封,封其父为协应侯、其母为协惠夫人、其妻为靖顺夫人、其妾为昭顺夫人、其子为顺助侯。宝祐四年至六年(1256-1258),吴潜在任时对鲍郎神亦关注有加,称赞其竭力为民的神迹,并以其剖决曲直之心自拟,“此心惟鲍君知我”(107)梅应发、刘锡纂:《开庆四明续志》,《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5948页。。吴潜亲自完善庙史,且“择画史之精者,图王之出处事迹于殿壁,若仪从若兵马又绘于门之内外焉,以至廊之屏蔽,门之丹雘,显设藩饰粲然”(108)梅应发、刘锡纂:《开庆四明续志》,《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5948-5949页。。这些地方精英不仅重视制度层面的神灵崇奉,还重视修葺神灵庙址、关注祠宇的装饰。而演屿神职能也从护航海上转向日常庇佑。建炎初,寇犯西闽,百姓将生存希望寄托于神明,奔走于演屿神庙祈祷,“俄顷雨雹交下,盛夏如冬,时平地水尺,贼惶怖而遁”(109)梁克家纂:《淳熙三山志》,《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7864页。。除了这些获得官方封赐的神明,明州地方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神明信仰及其庙宇,比如明州城南三里外的白龙王庙,城西南三里半的水陆冥道院及东距鄞县县城四十里的石庙等。
在官方意志构建的地方神明崇奉体系中,属于岳镇海渎国家祀典体系的东海神稳居首位,林氏神女、鲍郎神、演屿神等地方神明处于从属地位;明州的地方神明崇拜也并非被动等待国家礼制整合,普遍化的神女信仰、鲍郎信仰也通过国家权力而得以“正统化”。林氏神女、鲍郎神、演屿神等民间信仰的“标准化”是国家用“礼”框约地方社会之“俗”,亦将“礼”与地方社会之俗情密切联系起来。
四、讨 论
明州造船的社会实践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技术情境”,明州地方的神灵奉祀和官方构建的神明崇拜即是在特定的社会基础上生成出来的礼俗互动。从国家礼制构建的祭祀和爵号来看,东海神的等级最高,但在明州实际祭祀中却并没有享有最鼎盛的香火。在地方的神明崇拜体系中,神灵有各自负责的领域,百姓往往根据“灵验”的程度来选择自己信奉的神灵。远洋航行时,人们注重对东海神、林氏神女的祭祀和供奉,日常生活中则表达出对鲍郎神、演屿神的虔诚。各路神灵在“神舟远洋”驱动下进入“标准化”的信仰体系,但在南宋末期,这些地方神明作为海神的护航职能已经大为弱化,甚至消失殆尽。由此可见,整体社会中的民间信仰与官方意识主导构建的神明崇奉全然不同。
华琛以帝制晚期中国的妈祖信仰传播为中心,剖析神明走向“标准化”的历程,他认为是国家、士大夫精英和大众联合建构了民间文化被官方统一的文化标准化实践;科大卫把华琛“标准化”体系的“一致性东西”阐述为“礼仪标识”,关注到地方社会成员的主动性;“礼俗互动”的视角既展现了船舶技术情境中的社会信仰结构,还暗示了这些神明信仰的生成过程及基本形态。在明州整体的技术情境中,借助“礼俗互动”的概念,有助于分析统治者与普通民众、国家礼制与社会文化的内在冲突和关联。“神舟”归来后的明州地域信仰秩序的变动是宋廷在“大一统”天下观下的礼仪教化普遍化倾向和对地方文化的高度包容。国家礼制褒封的神明表达了“礼”,明州地方神明职能的转变展现了“俗”,它们既是社会现象也是话语形式,正是“二者之间的互动实践奠定了国家政治设计与整体社会运行的基础”(110)张士闪:《礼与俗:在田野中理解中国》,齐鲁书社,2019年,第1页。。明州船舶生产为考察“礼俗互动”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物料筹措、木材调运、船只征调、海寇滋生等问题展现了一个生动的、复杂的、整体的社会情境。在明州船舶生产的整体情境中,神明崇拜始终贯穿地方民众的生活和集体意志,地方神明崇拜与官方礼制之间的互动展示了技术情境中明州生动复杂的社会-文化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