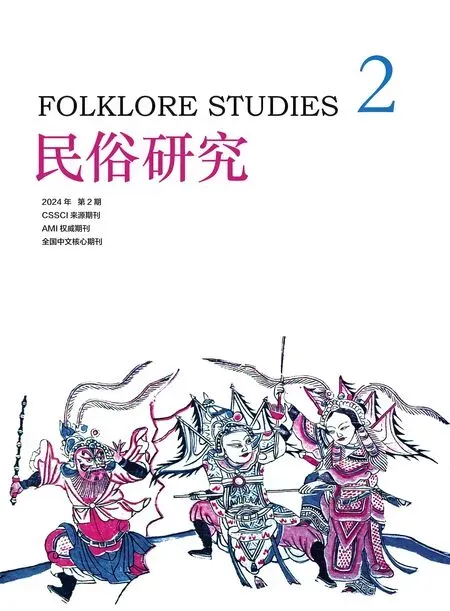禄是遒和卢国祥对中国婚丧、岁时风俗书写比较研究
王海涛 夏瑞芳
“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是欧洲历史上的‘启蒙时代’,这个时代同晚明前清以天主教传教士为主要媒介的中欧交往在时间上大致吻合,也正因为如此,造就了中国与欧洲在精神上的第一次深刻碰撞。来华的各类旅行者向欧洲读者呈现出一个富饶、美丽、强大的中国形象,而耶稣会士的著作更进一步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地理、宗教、儒学、制度。那个富丽的中国形象令所有欧洲人都对美好生活产生向往之情,而被耶稣会士刻意雕琢过的中国文化意象则令启蒙时代的旗手们找到了行动的指南。于是一个走向近代文明的欧洲同一个耶稣会士有意远古化了的中国产生共鸣,仿佛一次时空交错之旅。而当欧洲借助中国肯定了自己的新面貌后,最终还是抛弃了中国。”(1)张国刚:《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06页。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欧洲对于中国的了解只局限于前两个世纪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所做的记录,新一轮探索活动迫在眉睫,非洲协会和皇家地理协会(成立于1830年)成为重要推手,其中洪堡1799-1804年的“重新发现美洲”之旅为此类活动树立了标杆。此时欧洲对域外风俗、社会的记录和文物收藏与其“启蒙时代”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密不可分。德国旅行家和民俗学家走遍世界各大洲,进行记录和文物搜集工作。他们从一开始便对这项工作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认为自己的记录需要为研究工作和专业人员的培养提供服务,以展示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2)[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强朝晖、刘风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5页。此时的清廷奉行闭关锁国政策,除了受聘修订历书的传教士,其他传教士的活动多为秘密活动。据统计,截至1839年共有65名欧洲传教士在中国本部十三省活动,天主教徒共计三十万人。其中部分传教士成为侵略者的耳目,为天主教势力的扩张做准备。(3)Chinese Repository, November 1844, p.59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灾难,在那个时代,西方走向中国,而中国同时也走向西方。(4)[奥]雷立柏:《译者序》,[德]赫尔曼·费希尔:《传教士韩宁镐与近代中国》,[奥]雷立柏编译,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IV页。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大批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作为“实践型的职业汉学家”(5)李雪涛:《德国汉学研究史稿》,学苑出版社,2021年,第43页。,广泛深入中国内陆田野,扎根乡间,以学校、医院、育婴堂等兴办为犁,“疏松土壤,让传教士们得以播撒基督教的种子”(6)[瑞典]安特生:《龙与洋鬼子》,李雪涛、孟晖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58页。。当时的外国传教士想按照自己的梦想建设中国社会。他们认为传播信仰会帮助中国,拯救尽可能多的中国灵魂,使他们远离迷信和无知。为达目的,他们试图利用科学知识、现代技术、文化修养以及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等各种方式,包括支持西方列强向清廷施压。(7)[奥]雷立柏:《译者序》,[德]赫尔曼·费希尔:《传教士韩宁镐与近代中国》,[奥]雷立柏编译,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V页。除传教事业外,他们还记录了观察和收集到的当地民众的生活情况和独特习俗、信仰等内容,让西方了解到中国的真实情况,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也奠定了彼时汉学研究的基础。
一、禄氏和卢氏及其著作
禄是遒(Henri Doré,1859-1931)(8)禄是遒神父生于法国,1884年来到中国,在上海和江南一带传教三十余年,在上海、江苏、安徽等地调查中国的民间习俗,收集大量民俗资料,于1931年在上海逝世。十六卷本法语《中国民间崇拜》汇集其毕生收集,是关于中国民间宗教的巨著。和卢国祥(Rudolph Pieper,1860-1909)(9)卢国祥神父生于德国,是最早到中国的圣言会会士之一,他于1886年抵达山东,1909年7月24日因病逝世于坡里。其著作共两部,分别为本文所引用的《中华苗蔓花》(Rudolph Pieper, Unkraut, Knospen und Blüten-Aus dem Blumigen Reiche der Mitte, Steyl, Verlag der Missionsdruckerei in Steyl, 1900)和《新版中华苗蔓花》(Rudolph Pieper, Neue Bündel: Unkraut, Knospen und Blüten-Aus dem Blumigen Reiche der Mitte, Steyl, Verlag der Missionsdruckerei in Steyl, 1908)。分别作为基督教耶稣会和圣言会(10)圣言会(拉丁语为:Societas Verbi Divini,缩写为“SVD”,英语为: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是1875年在荷兰斯太勒(Steyl,亦译“史泰尔”“斯泰尔”等)创立的传教修会,1879年派第一批传教士到中国,即安治泰神父(Johann Baptist Anzer,1851-1903)和福若瑟神父(Joseph Freinademetz,1852-1908)。的传教士,几乎同时进入中国,二者虽然侧重点和生活区域不同,但都详细记录了婚丧和岁时习俗,具有较高的可比性。以二者为代表的传教士通过对“小人物”的关注和“在野并旁落”的发掘,深描出“历史的掌纹”。他们的作品虽有感情用事之弊,其描述倾向性明显、居高临下、充满偏见,正说明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霍耐特(Axel Honneth, 1949-)所提出的“认可”的重要性,“揭示出不公平的社会对于人间本应有的认可之系统性漠视这一社会病理,导致受歧视、侮辱、排斥等痛苦经验”(11)方维规:《“本真性”:民俗学的知识生产及其多重视野》,岳永逸:《土著之学——辅仁札记》,九州出版社,2021年,第4-6页。,但“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本质上来讲……在于他们能够相互理解,他们都拥有意识、思想和精神”(12)[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2页。。从“认可”的视角对二者的著述进行比较分析,首先可以从不同视角看出“时代精神”在二者身上打下的烙印;其次,可以通过二者“在野、内发、跨领域和世界性”的民俗学研究,深入挖掘汉学的民俗学研究成果,融合中国民俗学与外国民俗学者之中国民俗学的两大天地,重温柳田国男(1875-1962)所倡导的“一国民俗学”,即“一国民俗学”也是“世界的”。(13)方维规:《“本真性”:民俗学的知识生产及其多重视野》,岳永逸:《土著之学——辅仁札记》,九州出版社,2021年,第3页。从“异域”的视角出发分析二者的记录,首先可以为研究近代中国婚丧和岁时文化发掘大量具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因为他们思想上与中国文化的天然距离,使其可以更全面地观察和记录民俗事象;其次,这些记载中折射出的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矛盾与冲突,为理解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想象与建构提供了参考文本(14)彭瑞红:《他者镜像中的中国近代民间礼俗——法国传教士禄是遒对中国婚丧、岁时风俗的书写与研究》,《民俗研究》2018年第4期。;最后,还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西方民俗学、民族志和人类学的求知旨趣,为研究“他者视阈”下的中国近代民间礼俗提供更全面的依据。
“文本体裁”是二者书写的第一个不同之处。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记录主要包含两种体裁:首先是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记录,涉及历史、地理、风俗、宗教、语言等各个方面,此类著述后来在西方被称为“民族志”,如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曾德昭(又名“谢务禄”,Alvaro Semedo,1585-1658)的《大中国志》(1642)、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的《中国总论》(1847)和卢国祥的《中华苗蔓花》(1900)及《新版中华苗蔓花》(1908);其次是通过某个特定视角记录中国社会状况,如高延(De Groot,1854-1921)的《中国宗教体系》(1892)和禄是遒的《中国民间崇拜》(1911-1912)。不同的记录方式源自二者的学术背景、传教经历和研究旨趣,其“建构内部心理表征的过程……不仅涉及结构性的知识,而且涉及大量非结构性的知识”(15)刘学惠:《跨文化交际能力及其培养:一种建构主义的观点》,《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1期。。
二者书写方式的第二个不同之处体现在“文本风格”上:禄氏的著述具有较为显著的“学院派”风格,体现了法国学院派汉学“理性与科学”的理念,又继承了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入认知的传统。他在中国安徽、江苏等地农村传教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调查”材料,并用十余年时间整理打磨,其主要目的乃是“帮助在乡间的同事们,那些新近从西方到达,还不了解中国人宗教状况的传教士们”去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因为它有别于“文明真正起作用”的通商口岸,是“另一个中国”。(16)李天纲:《禄是遒和传教士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岁时习俗》,沈婕、单雪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页。上述因素互相交织,形成一幅奇异而丰富的关于中国民间信仰与风俗的画卷,在法国国内和欧洲汉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其《中国民间崇拜》是一部较全面描述中国区域民间信仰风俗的巨著,为后世学者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间信仰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其中《婚丧习俗》《岁时习俗》两卷通过文字和图片详细记载了中国民间社会的婚丧习俗与岁时节日,其研究融入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少表述已经触及中国民间社会观念的核心特征(17)彭瑞红:《他者镜像中的中国近代民间礼俗——法国传教士禄是遒对中国婚丧、岁时风俗的书写与研究》,《民俗研究》2018年第4期。;卢氏的作品则体现了德国汉学传统中的“实践派”风格,他在1900年出版的《中华苗蔓花》从“基督教中心主义”出发,认为“异教”的中国是所谓“苗”(德语“Unkraut”有“杂草”“野草”之意,此处为转译),应弃之如敝屣;而基督教的中国是神圣教会所开出的“蔓芽”(德语“Knospen”有“蓓蕾”“萌芽”之意);最后所说的“花”(德语“Blüten”)指的是在华传教士,他们以宗教献身精神投入在华传教事业,其中许多传教士去世后都被埋葬在中国(本文所涉及的两位均如此),希望以此彰显其宗教热忱,以获得德国国内对在华传教事业的关注和支持。此书对当时清代中国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介绍,包括生活习性、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记录了自己“从精神的、内部的、不可见的宗教皈依层面与中国人的接触”(18)[英]顾德诺、[英]朱莉亚·库恩编:《西方旅行者的中国书写:1840-1940》,顾钧、程熙旭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40页。历程。同时,其结构设计也体现了当时传教士把中国看作一个宗教问题、宗教谜团和宗教事业的时代特征。
二者书写的第三个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分析具体意象的理念和思路上存在明显区别。禄氏“有意识地把不同文化类型进行对照和比较研究,形成其独特的文化理论”(19)高有鹏:《近代西方传教士视野中的中国社会风俗及其理解——以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系列著述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卢氏更擅长从中国传统出发去解构现实,尊重儒家传统,“将历史研究与活生生地理解当代的发展进程结合起来”(20)李雪涛:《德国汉学研究史稿》,学苑出版社,2021年,第258页。。禄氏在解构过程中除了引用中国典籍之外,还借鉴了多位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如卫三畏、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0)、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1831-1878)、高延、戴遂良、麦嘉温(John Macgowan,?-1922)、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等。另外,他对中国信徒黄伯禄(1830-1909)《训真辩妄》和《集说诠真》的引用以偏概全、杂乱无章,成为其著作中最大的瑕疵。相比较而言,卢氏则继承了德国民俗学传统,尤其是赫尔德(Johann Herder, 1744-1803)的“民歌”“民族心灵”“民族信仰”等理念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的中国史观,以及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欧德理(Ernst Johann Eitel,1838-1908)、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等传教士的汉学研究传统,其所在的圣言会除了尊重儒学,也有记录中国民俗的传统,涌现出三十多位汉学家,在民俗学记录和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卢氏的记录被德国著名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1878-1957)吸收,从而完成其成名作《王伦三跳》,在德国文学界引发轰动,被称为德国“第一部表现主义小说”(21)转引自谭渊:《德布林的“中国小说”与德国汉学——〈王伦三跳〉中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外语教育》2013年年刊,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7页。。卢氏写作的主要目的是吸收捐助用以支持圣言会在华传教事业,因此其著作通俗易懂,趣味性较强。他的分析以引用中国典籍为主,仅在涉及汉语学习部分引用了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这一不同之处充分体现了二者所在的教会以及各自汉学界的研究传统及写作方式的区别。相较于法国耶稣会及其汉学,德国圣言会和汉学在记录中国民俗和相关研究方面起步相对较晚,因此,以卢氏为代表的圣言会传教士的著作学术深度相对不足。
二、禄氏和卢氏对中国“婚丧习俗”的书写
禄氏的《婚丧习俗》是《中国民间崇拜》的第一卷,在“诞生和幼时”部分,禄氏介绍了“出生前”“出生后”“孩童时期的迷信习惯”“过关”四个方面的内容。在关于“祈求子嗣”的描述中首先介绍了向观音求子时的“借鞋”“还鞋”风俗,并指出道教系统“送子天仙”的地域性特征:山东和附近几省崇拜的是“泰山娘娘”;随仕她的“注生娘娘”在南方数省特别受到尊崇;在其他地方,人们更倾向于向“天后圣母”求愿。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女神,一些男神同样也被安排来和蔼地聆听求子者的求愿,如“安徽省繁昌县的‘宴公’”“掌管文运之神魁星”“吕洞宾和关公”“张果老”等。(22)[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婚丧习俗》,高洪兴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3页。最后禄氏介绍了“供奉催生娘娘和葛姑娘娘”“难产用符”“算命先生查看性别”“作为护身符的魔镜”“排八字测命运”“拴娃娃”“将新生儿过继给一个神”等习俗。出生后的习俗包括“洗澡”“七星灯”“桃剑”“偷生鬼”“狗毛符”“钱龙”“杀鸡”“畜名或丫头”“铃铛”“点朱砂”等。(23)[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婚丧习俗》,高洪兴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10页。孩童时期的习俗包括“戴锁”“戴圈”“戴耳坠子”“戴钱”“戴八卦”“留箍”“穿和尚衣(百家衣)”“烧破鞋、挂鱼网”“治小孩病之符”“干亲”“辫子上挂红布”“核桃锁”“床”等内容。(24)[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婚丧习俗》,高洪兴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17页。最后一部分记录了小孩在青少年时期拦截在其生命之路上的每月一次或每年一次的关口。“直到十六岁时通过了最后一个关口,所有危险才过去。”(25)[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婚丧习俗》,高洪兴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7-18页。书中列举了三十个关口的名称。
卢氏在“中国儿童”一节中开篇节选《诗经·小雅·斯干》: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26)Rudolph Pieper, Unkraut, Knospen und Blüten-Aus dem Blumigen Reiche der Mitte, Steyl, Verlag der Missionsdruckerei in Steyl, 1900, p.55.
之后介绍了“剃胎发”“起乳名”“过门”“坐月子”“起丫头名”“认干妈”“抓周”“拜干亲”“虎头鞋”“弃婴”“裹脚”“启蒙”等民间习俗,并从《礼记》中找到了“剃胎发”等习俗的起源。卢氏重点介绍了民间“重男轻女”的习俗,从“弄璋之喜”“弄瓦之喜”“抛弃女婴”“男婴有权在祖祠剃胎发”“一儿顶十女”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同时他表示,其中的原因“并非出于对女孩的厌恶,只是中国残酷的现实让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男孩给家族所能带来的荣耀是女孩给不了的”,且抛弃女婴现象“主要发生在非常贫困的家庭,他们往往无力养活众多孩子,中国母亲也和其他国家的母亲一样爱自己的孩子”。灵活地运用俗语也是卢氏写作的特点,其中包括“严父出孝子,慈母多败儿”“棍棒底下出孝子,娇养造就忤逆儿”“有其父必有其子”等。(27)Rudolph Pieper, Unkraut, Knospen und Blüten-Aus dem Blumigen Reiche der Mitte, Steyl, Verlag der Missionsdruckerei in Steyl, 1900, pp.55-62.
在“红事”介绍中,禄氏借鉴了戴遂良(Léon Wieger)《汉语入门》的内容,但“省略了未在这两省流行的习俗”(28)[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婚丧习俗》,高洪兴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9页。。他详细记录了“订婚”和“婚礼”的仪程。在“订婚”部分,禄氏主要介绍了“婚帖”,包括“生庚”“换贴”“定亲贴”“传庚帖”等;在“婚礼”部分介绍的内容包括“定日子”“下娶贴”“七子礼”“新娘启程”“新娘进新郎家”等仪程,并从婚礼对基督教徒的神圣意义出发,批判了“闹新房”的习俗,认为其“可谓下流、粗俗不堪……在此场合允许头发花白的老人说年少风流的话。异教恐怖如此,甚至连最基本的廉耻观念都被摈弃了”。(29)[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婚丧习俗》,高洪兴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5页。因此,可以发现“他丝毫不理解中国民众的情感表达方式”(30)高有鹏:《近代西方传教士视野中的中国社会风俗及其理解——以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系列著述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也体现了二者书写的第一个相似点:深受“基督教中心主义”影响。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观念深刻影响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和想象,导致二者在材料的选择上有明显的倾向性和片面性。(31)彭瑞红:《他者镜像中的中国近代民间礼俗——法国传教士禄是遒对中国婚丧、岁时风俗的书写与研究》,《民俗研究》2018年第4期。同时,认为“中国人的信仰是迷信”的观点在西方非常普遍,一方面成为其“传播福音的最令人信服的正当理由”(32)[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范丽珠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页。;另一方面导致中国形象被“污名化”,并逐步沦为政治和权力的工具,其影响绵延至今。这是“时代精神”在二者作品中的充分体现。
二者书写方式的第四个不同之处在于,禄氏记录了江苏、安徽等地的大量珍贵“符箓”,为全面深入了解中国民间信仰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和独特的研究视角;而这一部分内容在卢氏的记录中很少看到,他在记录内容上最大的特色在于对“俗语”的记录和灵活运用。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二者对中国民俗研究旨趣的不同。卢氏在此部分开篇借用俗语“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描述中国人的婚姻观,随后介绍了中国婚礼的起源,并引用《国风·豳风·伐柯》以突出媒人的作用,另外还包括迎亲队伍和演奏乐器等。他详细介绍了“订婚仪式”,尤其是“择良辰”。在描写“接亲仪式”时,卢氏引用了《礼记·哀公问》之“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强调了接亲本质是对于新娘的尊重,同时也是对新郎自己的尊重,以顺利地为家族延续血脉,传承祖祀。(33)Rudolph Pieper, Unkraut, Knospen und Blüten-Aus dem Blumigen Reiche der Mitte, Steyl, Verlag der Missionsdruckerei in Steyl, 1900, p.42.他还详细介绍了“开脸”“拜天地”“穿新衣”“坐福”“回门”“做新裤”“住对月”“禁止近亲结婚”“纳妾”“冥婚”“过继”等习俗。对于结婚的意义,卢氏引用了《礼记·婚义》中的“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34)Rudolph Pieper, Unkraut, Knospen und Blüten-Aus dem Blumigen Reiche der Mitte, Steyl, Verlag der Missionsdruckerei in Steyl, 1900, p.52.同时卢氏也记录了订婚和婚庆典礼中的迷信。作为比较,卢氏描述了中国基督教徒的婚礼:
婚礼在中式庆典前一天的清晨安静地举行,通常是在教堂里,大门紧闭,只有证人在场,尤其是当婚姻发生在异教徒分散的家族之间时。一方面,我们必须让年轻人免受“羞辱”;另一方面,必须注意避免在异教徒中出现令人不快的言论。这是夫妻双方都要为之奋斗的真正的英雄壮举!“在神圣教会的见证下,你愿意接受某某成为你的丈夫吗?”没有回答,再问一遍依然没回答。神父严肃地告诫他们,甚至发出威胁,最终才传来一个安静的、胆怯的“是”。在双方握手环节,新郎通常会向右看,而新娘会向左看。对于新郎来说,当他给新娘戴上戒指时,找到正确的手指实属不易;如果神父没有伸出援手,新郎定会将戒指戴错手指。通常需要他的引导才能让这对年轻夫妇正确地完成这场神圣的仪式。(35)Rudolph Pieper, Unkraut, Knospen und Blüten-Aus dem Blumigen Reiche der Mitte, Steyl, Verlag der Missionsdruckerei in Steyl, 1900, p.53.
二者书写方式的第五个不同之处在于,由于生活区域不同,其记录体现出明显的地域化特色,如禄氏在丧葬禁忌中所说的“扣子”在当地方言中有“诱拐绑架小孩”(36)[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婚丧习俗》,高洪兴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7页。之意;而卢氏所记录的“扣子”谐音为“扣住子孙、断子绝孙”(37)Rudolph Pieper, Unkraut, Knospen und Blüten-Aus dem Blumigen Reiche der Mitte, Steyl, Verlag der Missionsdruckerei in Steyl, 1900, p.277.。“这些地方共同的特征表现在普遍的功能模式上,而不是在具体的崇拜方面。”(38)[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范丽珠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页。禄氏关于丧葬习俗的描述分为“白事”“死者之符”“为死者服务的种种迷信”三部分。“白事”部分首先介绍了“死前”的“招魂”和“抬菩萨”仪式以及死者穿戴的禁忌,之后分别介绍了“死后”“入棺”“下葬”“葬后”“葬礼上焚化的迷信纸”“买路钱”等内容。其中,他认为“买路钱”的习俗既源自孔子弟子高柴拒绝对葬妻时损害农作物进行补偿的传说,也受到日本下葬时沿路撒铜钱施舍穷人和乞丐习俗的影响。“孔夫子的追随者,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是因为高柴的事才为送葬付买路钱。然而这一做法既欺骗了单纯的民众,也欺骗了他们自己。”(39)[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婚丧习俗》,高洪兴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5页。禄氏在接下来的两章中记录了大量佛教和道教丧葬符箓,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此外,禄氏在最后一章中重点论述了“木主”和“轮回”两部分内容,对“尸”和“木主”的考据尤能体现禄氏著作的学术水准。禄氏通过分析发现,“因为这些错误的注释,导致公众相信亡灵就住在木主中。因此人们想像通过在其前再三叩头祈祷,就可以得到幸福。同样也认为如果此行为被疏忽或抛弃的话,不幸就会降临”(40)[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婚丧习俗》,高洪兴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6页。。
卢氏在“中国葬礼”一节中首先介绍了“丧前”和“初丧”,包括“寿衣”“寿材”“灵床”“彻裹衣,加新衣”,其中重点描述了寿衣需要用“带子”取代“扣子”,另外还包括“适室”“鸡寐枕”“打狗饼”“吊唁”“长明灯”“指路”“倒头饭”“成服”“拜土地爷”“五道爷”“泼汤”“抬筲”“安灵”“丧葬演戏”“买路钱”“枕金蹬银”“封灵”“过桥”“看风水”“打井”“铭旌”“服丧”“扫墓”等习俗,强调了提供“超越意义”的风水先生的重要性。(41)Rudolph Pieper, Unkraut, Knospen und Blüten-Aus dem Blumigen Reiche der Mitte, Steyl, Verlag der Missionsdruckerei in Steyl, 1900, pp.276-298.此部分最后,卢氏援引《诗经·小雅·蓼莪》《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和《文公家礼·葬礼》对儒家正统丧礼仪式及观念进行了总结,其中尤其强调了《文公家礼》。(42)李红、胡彬彬:《新见清代礼制孤本文献〈文公家礼·丧礼〉的内容与价值》,《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这部书是朱熹的礼学著作,是对冠、婚、丧、祭等礼仪及日常行为的规范整理和汇编,目的是通过这些仪式来体现孝道,将抽象的“孝”的理念进行世俗化推广,从而实现“礼下庶人”,并起到“崇化导民”的作用。此书上承《仪礼》《唐开元礼》,下续《明集礼》《清通礼》,对宗族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有助于重塑门阀制度解体后的家族组织结构。“官家用科举笼络平民,构成上下循环的官吏选拔系统,基层士绅由此形成,使得道德教化变成了一种可以替代行政管理的技术……(从而)节省治理成本。”(43)杨念群:《“大一统”:诠释“何谓中国”的一个新途径》,《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
二者书写方式的第二个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经过长期的“田野调查”,都注意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孔子的儒家思想中加入了释伽牟尼形而上的佛教理论,近代的道教从佛教中借鉴了许多东西”(44)[英]甘沛澍:《英译版序》,[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岁时习俗》,沈婕、单雪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页。,儒家“在葬礼和祭祀中接纳了道教和佛教的神学思想和仪式”(45)[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范丽珠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1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死亡常被看作人生从“阳世”到“阴世”生活转换的节点。“从死亡到丧葬的仪式,即以此种观念为出发点,葬礼被看作是将死者的灵魂送往死者世界必经的手续。”(46)钟敬文:《民俗学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40页。葬礼既是对死者已逝的心理感受的仪式性表达,也是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结构建构的开始。同时,先验中关于另一个世界的观念因在意识中得到了感知的内容而具有了某种真实性,并成为人们的信念意识。引导亡灵前往彼岸的过程表达了仪式主体对古老历史和权威体制的膜拜,加强了传统意象的象征意义,同时折射出其对两个世界的认识,以及能懂得跨越两个生活世界,并对其进行干预背后的心理结构。丧葬仪式作为多面综合体,既是生活中各个部分和元素在时空关联中的形式,也代指社会生活层面的结构,是两个世界整体性转换的节点。(47)黄健、郑进:《农村丧葬仪式中的结构转换与象征表达——基于一个丧葬仪式的分析》,《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4期。卢氏将此部分作为描写的重点,发现“中国庶民所以形成多神信仰,主要反映了人群生存社会需要之功能分殊,不恃万能之唯一真神,而如同人间现实需要,恃不同职司之神,护佑其生活中不同情状之痛苦疑难”(48)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岳麓出版社,2002年,第12页。;另外还展现出“三教融合”的特点,如死后魂灵所去的方向正是佛祖所在的西南方(49)Rudolph Pieper, Unkraut, Knospen und Blüten-Aus dem Blumigen Reiche der Mitte, Steyl, Verlag der Missionsdruckerei in Steyl, 1900, p.279.,触及中国民间社会习俗的核心。与此同时,二者写作的第三个相似点在于,他们都强烈地批判了影响中国民间信仰的佛教和道教,尤其是佛教。卢氏在文中曾明确将以色列异教徒和佛教徒相提并论;禄氏在记录“纸马”的过程中选取的均是与佛教相关的内容,并在文中表达了对佛教在乡村巨大影响力的不满。这与二者的传教士身份密不可分,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是二者在传教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之一,因此二者在精神层面上理解中国文化受到佛教和道教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必须在现实中与之斗争。
三、禄氏和卢氏对中国“岁时节日”的书写
禄氏的《岁时习俗》是《中国民间崇拜》的第五卷,共分为“崇拜仪式”“中国的节庆习俗”“被赋予神奇力量的动物、树木和植物”三章。其中第一章以“招魂”和“中国的神佛圣诞及宗教节日历表”为核心,介绍了与魔法、巫术和妖术有关的各种民间习俗,其中包括中国古老的招魂习俗,宫闱之中的妖术,上海周边地区尤其是江苏北部海洲的道女(道教女巫师)的职业活动,并“向读者展示了一份完整的中国人信仰崇拜的神佛及人文英雄的历表”(50)[英]甘沛澍:《英译版序》,[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岁时习俗》,沈婕、单雪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页。。《中国民间崇拜》英文版译者甘沛澍(Martin Kennelly,1859-?)认为异教组织模仿了基督教会每年公布一整年内宗教节日及圣徒瞻礼日的惯例,“向广大信众提供了对虚假的鬼怪、被神化的圣人和勇士以及民族英雄的崇拜,人们脑海中的错误由此变得根深蒂固”,“中国宗教之树大部分枝干是土生土长的,但在原有枝干上也嫁接出了一支巨大的外国起源的宗教分支”,是三教“互相嫁接与吻合的过程”。(51)[英]甘沛澍:《英译版序》,[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岁时习俗》,沈婕、单雪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二者书写的第四个相似之处在于,他们对于当地的礼俗和民间信仰的认知表现出明显的“碎片化”,没有进行合理的归类排序,并且在逻辑上还有前后矛盾之处,例如,禄氏的著作中多次提到“招魂”,除了为逝者,还包括为生者招魂——“叫魂”。为逝者招魂主要表达了家人的痛苦和不舍,是“人们不愿相信死亡真实性的一个标志,人们对逝者还抱有生还的希望”(52)[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岁时习俗》,沈婕、单雪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页。,其象征意义“建立在活着的亲人坚信灵魂继续存在的事实基础上”(53)[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范丽珠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页。。虽然禄氏引用了《礼记》《陈留风俗传》《后汉书》《晋书》《中国的宗教制度》《中国辞汇》《中国文献记略》《中国近代民间传说》等中外典籍中所记录的为死者招魂的典故和仪规,并加入自己所收集的安徽庐州府和江苏徐州府为生者招魂的民俗,但并未真正厘清“招魂”的历史发展逻辑和两种不同形式的区别,逻辑上略显混乱,在判断上简单地认为“出窍的灵魂经常找不到返回身体的路,偶尔它也会因为太害怕了而不敢返回。这种情况下,必须让它安心,哄它回来,很像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害怕被生气的父母责罚。这就是当今中国人的思维特点”(54)[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岁时习俗》,沈婕、单雪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页。。卢氏此部分的记载相对简单,但同样没有厘清“招魂”和“叫魂”的区别。二者的这一共同点体现出彼时两国汉学界对于中国民俗的认知缺陷。
二者书写的第五个相似之处在于,为增加文本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二者都加入了众多民间传说故事并记录了亲身经历的社会风俗生活,是他们作为传教士“对中国民众思想和情感的观察”(55)高有鹏:《近代西方传教士视野中的中国社会风俗及其理解——以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系列著述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从而保留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从学术价值上看,他们对中国民俗的书写作为“他者的话语,与自我‘群体标记’形成两极结构或曰正反结构:在形象的形成过程中,自我形象与他形象相互照应和相互作用”(56)[德]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形象学》,方维规译,《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3期。。例如,禄氏在第二章记录了中国人的主要节日,尤其是新年期间的庆祝活动,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记录了“乞丐届如何享受新年”,即乞丐利用人们对于鬼神的畏惧心理到富户家拜年并索取礼物,其乞讨手段为唱吉祥如意话儿的“莲花落”段子。(57)[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岁时习俗》,沈婕、单雪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0-101页。禄氏记录的三段唱词为近代民间文化保存了珍贵的样本。在第三章中禄氏表示,此类习俗存在的原因在于“人们渐渐地从表面上的尊敬深入到发自内心且坚定不移的崇拜并希望以此获得神灵特殊的庇佑”(58)[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岁时习俗》,沈婕、单雪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26页。,“要根除这些就需要宗教和科学的力量相结合,当这项工程完成,社会将处处是真理,中国也会比过去更加繁荣昌盛”(59)[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岁时习俗》,沈婕、单雪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0页。。
卢氏关于中国“岁时节日”的描述主要出现在第一部分的《中国的节庆日》一章中,介绍了“春节”“元宵节”“中国的宗教节日”。在春节部分卢氏开篇引用了俗语“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他认为春节是民众相互之间和解的好机会。接下来卢氏介绍了春节习俗的四个重要因素:“烟花”“吃肉”“请门神”“讨(躲)债”。“哪怕浑身上下只剩6分钱,也要拿出2分钱买烟花”;“为了能吃上一口肉,会把自己的床当了,哪怕后悔几个月也值得”;“人们非常重视过年时在门上贴什么,异教徒通常会贴上神像保佑自家平安,基督徒也会贴上宗教标语”;“为了还债,人们不得不把自己的衣物典当出去……传教士经常会在草垛里发现躲债的人。”(60)Rudolph Pieper, Unkraut, Knospen und Blüten-Aus dem Blumigen Reiche der Mitte, Steyl, Verlag der Missionsdruckerei in Steyl, 1900, pp.242-245.在“元宵节”一节中,卢氏记录了“拜佛”“舞狮”“踩高跷”“杂耍”“划旱船”“挂灯笼”“招魂”“开印”等内容,其中尤其提到了“西洋镜”,卢氏认为它利用了中国人的好奇心,“事实上是欧洲的耻辱,不应在任何市场上出现的垃圾商品被卖给了中国人,毫无底线的商贩赚得盆满钵满,损害的是欧洲的名声……不仅对传教工作不利,也阻碍了正常的贸易,包括商品引进”(61)Rudolph Pieper, Unkraut, Knospen und Blüten-Aus dem Blumigen Reiche der Mitte, Steyl, Verlag der Missionsdruckerei in Steyl, 1900, pp.249-250.。本章最后一部分记录了“异教节日”,即中国的“宗教性节日”,包括“祭天地”“供财神”“降圣节”“填仓节”“土地诞”“文昌诞”“道诞”“观音诞”“打春牛”“帝籍”“朔日节”“寒食节”“清明节”“端午节”“火神节”“雷祭节”“中元节”“地藏节”“元成节”“中秋节”“重阳节”“寒衣节”“孔子圣诞”“阿弥陀佛圣诞”“腊八节”“祭灶”“扫尘日”等内容,“异教徒虽然也供奉自己设计并摆放在祭坛上的神,但在这种敬拜中,他们首先要敬拜的绝不是神,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感官冲动。只此一样就能让有思想的异教徒相信其偶像崇拜毫无意义。宴饮、看戏和玩牌是异教徒庆祝的特色内容……不管是膜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人,还是佛教徒”(62)Rudolph Pieper, Unkraut, Knospen und Blüten-Aus dem Blumigen Reiche der Mitte, Steyl, Verlag der Missionsdruckerei in Steyl, 1900, pp.253-254.。
二者书写方式的第六个不同之处在于,与禄氏“居高临下”地批判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相比,卢氏表现出较强的“自我批判”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度更高。“我没看到中国人在春节特别闹腾或者很粗鲁,相反,他们在举行庆祝时充分表现了自己童真而又快乐的一面。同时,我也极少看到有人喝醉。我很钦佩中国人此时还能保持清醒,欧洲人在这一方面需要向他们学习。”(63)Rudolph Pieper, Unkraut, Knospen und Blüten-Aus dem Blumigen Reiche der Mitte, Steyl, Verlag der Missionsdruckerei in Steyl, 1900, pp.246-247.卢氏认为中国人的素养得益于儒家的影响,因为孔子的“慧言仍然像一种雪布遮蔽着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这些格言保护着许多自然的道德的种子,但它们也仍旧阻碍着生命的发展和成长”(64)[德]赫尔曼·费希尔:《传教士韩宁镐与近代中国》,[奥]雷立柏编译,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400页。。这也反映出圣言会尊重儒学的传统。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认为儒家更接近基督教,其经典中很多表述与《圣经》相似。因此,“在山东的德国传教士倾向于区分‘善良的’儒家道德教导和佛寺、道观中那种‘邪恶的’偶像崇拜”(65)[德]赫尔曼·费希尔:《传教士韩宁镐与近代中国》,[奥]雷立柏编译,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397页。,还曾刊印儒家经典。禄氏的“批判性”则代表了当时传教士的典型书写策略,为了迎合读者的心理预期,他们不仅在选材上有所侧重,在论述中也会夸大中国民俗中的所谓“迷信”成分。
四、结 语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来华传教士因地制宜地开展传教工作。他们在这里建一座教堂,在那里建一所学校,仅仅如此就已经令生活区域的外部面貌发生了变化。他们还直接影响(他人的)生活,而不是走世界市场或殖民政府这样抽象的“权力”曲折路线。受他们影响,个别人获得了新的生活机遇,包括在大都市深造的机会;另有一些人在抵抗传教士侵略的过程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传教活动的影响因此远远超出改变信仰者和支持者的圈子。传教士现身其中的本土社会不会就此而自行“现代”起来。“传教士,尤其是原教旨主义传教士,即认为圣经正确无误的信心差会(Faith Mission)所宣讲的西方,与精神行囊中装着改革、科技征服自然的自由派所宣讲的西方完全不同。不过无论以何种方式,这些本土社会都在经历着一种对自我理解的空前挑战。”(66)[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强朝晖、刘风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618页。这一挑战在禄氏和卢氏的记录中都得到了体现。从纯学术角度看,二者代表的传教士学者身处异域,思想上保持了天然的距离,因此能敏锐地察觉到本土学者往往视而不见的民俗事象,因此能较完整地保存民俗资料。(67)卢梦雅:《早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民俗的辑录和研究》,《民俗研究》2014年第3期。本文通过二者的比较研究更全面地介绍了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初衷、他们在华的经历、他们的贡献以及他们思想的局限性,从而更好地呈现出处于错综复杂关系中的传教士的民俗学记录,更深入地了解到他们的心态和思想。
中国有“礼”“俗”结合的社会传统,以此引导和规范民众的言行举止,而不同于讲究绝对法制的西方社会。民俗文化毕竟贯穿着一方民众的生活智慧与集体意志,承载着民间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观念、精神需求、价值体系等,构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群体行为规范。民间自我生成的“规范”力量,与国家权力意志之间既有分立又有合作,既有纷争又有对话,并谋求在对话、合作中从日常规范上升为公共价值。在“礼”“俗”两种话语之间,无论如何都会存在不能或未能通约的一面。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这其实正是中国礼俗互动传统的价值与活力所在。(68)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总之,二者的记录首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礼俗互动”的传统;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以近似现代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探寻中国人的信仰和精神世界;再次,通过文本的互文性分析得出二者都不同程度受到欧洲汉学发展的影响并实现了“文化互化”;最后,“历史背景、社会状况、文化生态”(69)彭瑞红:《近代传教士研究的跨学科实践——以禄是遒及其〈中国民间崇拜〉为中心的讨论》,《2014首届“跨学科研究”博士生学术论坛文集》,中国研究生跨学科协同创新联盟,2014年,第75页。等因素的影响都在二者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