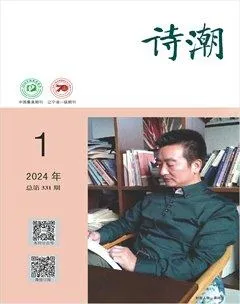猫之歌
草树

它从淘宝来。现在躲在沙发下,像一个羞怯的灵魂。
这一夜我接到了岳母去世的消息。孩子们在悲伤中等来这只猫,这才打破沉默,转而蹲在沙发边,喊着猫咪,用鸡毛掸子逗着它。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猫了。在遥远的乡下,土砖房前,正是冬天雪后的上午,一群人坐在背风的墙脚晒太阳,男人在说笑,女人在纳鞋底,我发现家里的黄猫扑在我的脚尖睡着了,半睁着一只眼。
这是一只布偶,白色的,头顶和尾巴有一抹高级灰,眼睛幽蓝幽蓝的。据说它的祖先是在美国的加州,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不知它是第几代?它和老岳母又有着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在同一个夜晚“来去”?
早上哥哥和妹妹躺在床上从不同房间争着为这只猫命名——“小虎!”“虎皮!”“小虎子!”“虎皮虎皮!”……他们送外婆上山,从乡下归来,因为小猫咪而摆脱了悲伤的负担。
妹妹最终赢得胜利!虎皮!她从床上跳起来,从书房将虎皮抱在怀里,喊着“虎皮”。虎皮睁着它蓝色的大眼睛。
虎皮当然不知道为了它的命名,刚刚发生了一场权力之争,且权力的底色涂抹了爱的色彩。它也不知道“虎皮”和它自身到底有什么关系——给它一顶帽子,或者一件外衣,语言的?
名实对应,意味着存在。哥哥让出命名权,妹妹获得了欢喜,和虎皮并无关系。
外婆徒余其名,永远对应一个坟堆,名实分离,坟堆遂成为存在和虚无的边界。但是外婆仍和我们的生活发生着关系,比如女儿在叠被子的时候,想起了外婆曾经在星期天怎样教她折叠,她再也没有在幼儿园因为不会叠被子而哭鼻子了。
虎皮不再以沙发为庇护所。它走出房间,开始在客厅漫步。家里每个人都撸了它的脊背——当手掌撸过,它微微拱起,显然感觉到了爱抚的温柔,尾巴也稍稍扬起。
我幼年的记忆里,猫总是和人保持着距离,即便是和孩子。白天,它看上去慵懒,慢悠悠走着,或者扑在角落睡觉,夜晚会突然像一道闪电在黑暗中飞奔,伴随着老鼠的仓皇和它的小脚碰触家具的声音,然后是一阵叽叽声。
这是另一种猫。没有老鼠可捉。与我们渐渐亲近。你到浴室洗澡或在厨房做家务,它就静静趴在旁边,陪着你。
当每个人拿着手机沉入自我的世界,虎皮似乎唤醒了一个早已变得名不副实的词:陪伴。是啊,陪伴。岳母临走前瘫痪在床的几个月,很多人来陪伴——进房里问候一声,然后就在堂屋打牌,说笑,嗑瓜子,每天像办流水席一样。
与其说是陪伴,不如说是打扰。
我不由得在过厨房门时撸了它的脊背。它望着我,两只眼睛蓝蓝的,喵呜一声。
夜晚虎皮有时候也会蹿出一阵乱响,仿佛在捉老鼠。
躺在床上听着椅子或地板发出的声音,当你还沉浸在白天发生的矛盾的余绪里,突然就摆脱出来了,为这一阵纯粹的声音和它的余波所吸引。
布偶猫不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里。它独立自足,尤其在夜晚。它在夜晚创造的戏剧性,打破了时间的线性结构。不像过去乡下老家那只黄猫,有时候与一只狗对峙,眼睛冒着黄色的火焰,背脊微微拱起;而狗则发出低沉的吼声,伸着长长的舌头。
人类何尝不是始终处在这样的对峙中:不论关联交易的甲乙,还是官场的正副,抑或国家与国家之间。
或许它是打破囚徒困境的一条道路。
又一阵蹿动声。
虎皮行走无声。当我走向书房,它每次都是悄然走到前面,像一把春草一样缠住你。好几次,我差点踢着它,不得不止住一只脚,身体也就只好瞬间倾斜。
桑德堡为什么把纽约港湾的雾比作猫,现在我明白了。那种无声,那种无处不在,那种轻盈而又含蓄的伴随。
当你停住脚步,它也停止了,然后静静趴着,或者弓着腰蹲着。
“静静地俯视港湾和城市”——那是雾,布偶猫把全部注意力给了它的主人。你在社会上已经受到太多忽略甚至蔑视,从它那里传递过来一种久违的注视——且它的两只湛蓝的眼睛是那么美,带着一种冷美人的矜持。
那时早晨一道阳光穿过树枝,照临阳台。
指纹锁嘀的一声。门打开,虎皮喵呜一声。
这声音的二重奏有着某种欢喜的共振。喵呜——虎皮每日守在门口,迎候主人回家,让我想起孩子们还小,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外面的世界回家的时候——孩子们听到敲门声,争相来开门,他们的声音立即让我有澡雪的清冽感觉。喵呜,细声细气,无比轻柔,不像夜总会两排盛装的小姐齐喊“欢迎光临”的千篇一律,也不像过去时代孩子们手拿纸花跳着舞蹈欢迎某位大员的热闹场面。像一阵清风掠过树枝。
一天夜晚,我坐在沙发上喝茶,吃着一块鲜花饼姑作晚餐,手机里播放着张蔷的《手扶拖拉机斯基》,正想起前天晚上在外面吃饭的不快——在那一桌人中地位最高者,从头到尾掌握着话语权,他仿佛不是在吃饭而是在自我表演或灌输——其他人不过是他的田园里的韭菜。这些韭菜要么附和,要么沉默。居高临下的、垂直灌注的聲音,不是清水从池塘通过水泵抽往田野,更像楼房落水管的声音。刷刷。不是哗哗,或者潺潺。
“越过西伯利亚伏尔加河,穿过施华洛奇的森林,来到迷幻的克林姆林宫……”我可能打起了拍子,虎皮也有些兴奋,跃上茶几。一贯敏捷的跳跃居然带翻一只茶杯,它仿佛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翻身下去,远远站定,喵呜一声。
虎皮跃上窗台,眺望远方。
外面正在下雨,小区支起两顶橙色的帐篷,帐篷下坐着几个“大白”,树篱中一只喇叭循环播放着一句话:同义反复。
虎皮当然不知道楼下那长长的、撑着伞的队伍在做什么,更不知道更远的马里乌波尔正在发生什么。它只是好奇,没有焦虑。雨中长沙城街道空空,没有往昔的繁华。云雾在国金的顶部吞吐:一会儿吞没它,一会儿吐出它。
我的焦虑不知从何而来:不想看书,不想听音乐,一直刷着手机上源源不断的消息,仿佛置身某种世界末日的场景中。
虎皮下来了,想象像一朵走动的蒲公英。它至少暂时让我离开了想象“世界末日场景”一会儿——我打开吸尘器,开始清理它飘飞的“花朵”。
这是一个治愈的时刻。
你走进浴室,它蹲守门口
你走进厨房,它在脚边打转
你躺在沙发上看书,它凑上来
像个孩子时刻跟着母亲
像一阵微风轻轻吹动花朵
那个髋骨骨折的老母亲在呻吟
那些花朵正在割草机的轰鸣中战栗
保姆在卧室里一边抱怨一边忙活
陪伴的人在堂屋一边倒牌一边手往桌上一拍
截胡了。胡低张的那人一脸沮丧
这些场景在叠加,又分离。猫咪的人性化和人类的动物化,一种令人诧异的“双向奔赴”。或许我脸色的“阴晴不定”由此而来。虎皮在脚边缠绕,脸色又舒展开来,就像一个刚刚生过气的大人,低头看见孩子在扯自己的裤脚,睁着一双清澈的眼睛。我进一步发现,阳台上蔷薇又绽开两朵,姿态姣好。
猫咪在飘窗上眺望远方
一声不响,像一个人来到异乡
一动不动,又仿佛在欣赏
我已经多久没有望远
熟悉下面的街道、市声、店铺
不认识南来北往的人
在漫長的岁月中
拿绳子捆绑自身
仿佛困境没有止境
很多年前,在年轻的孤独岁月,每一扇玻璃窗都激起我的梦想。一个面着大理石的飘窗,让我惊异于建筑师的想象力对视野的拓宽。猫咪是否像人类一样会渐渐丧失好奇?是否拥有了就不再热爱,丧失对世界的热情?是什么让人渐渐陷入自我隔离之中?
今天我顺着猫的视野看去
万达的幕墙映着晨光
国金的顶部薄雾缠绕
棚户区的屋顶上
开着大片三角梅
我撸了撸它的背脊:蓬松茂密的白毛,柔韧起伏的脊骨。它反转头,睁着湛蓝的大眼睛。相对无言,却分明有了深刻的交流。
砰的一声。猫咪奔向阳台,重重撞在玻璃隔断上。它迅速撤退,躲在沙发底下,一声不吭。
没有埋怨,没有怒火,而是感到羞涩和耻辱的样子。
我心中不禁升起一股敬意。
人何尝不是常常落入那样透明的或者说看不见的陷阱,可是人撞痛头会怎样呢?小时候撞墙会哇哇大哭,直到大人朝着那墙拍打几下;长大了遭遇陷阱,会满腔怒火去和对手战斗;如果落入更大的、以自身之力无法改变局面的陷阱,就哀叹命运的不公或无常……
敬意和羞愧交织。我倒着头喊“虎皮”,它在沙发下面睁着那双大大的、惹人怜爱的蓝眼睛,怎么也不出来,一动不动。也许疼痛还没有完全消失。
但是就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它又在客厅里“大象漫步”了。
小猫咪快一岁了,能听懂它的名字。你喊一声“虎皮”,它便朝你转过头来;再喊,它迈着优雅的步子走过来了。
如果它没有名字,你喊猫咪,她喊宝宝,它会怎样呢?如果它进入宠物店,与大群猫在一起,那么多猫咪,你喊猫咪它会作何反应呢?
词语就是身份。但是“虎皮”不会进入户口栏,无需身份证,更没有政治面貌或者工作简历,它比人类更少受到语言的限制和规训,因而无疑是一种更纯粹的存在。
对于小虎皮来说,除了爱的观念,它不会再受到其他什么观念的约束,当然它除了给主人带来快乐,不会打乱人类任何秩序。事实上它也十分小心谨慎,即便在摆满东西的茶几上行走,很少碰动什么。偶尔踩在钢琴的琴键上,踩出一个音符,它大吃一惊,立即就跳下来。
我们已经把虎皮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了,没有谁以主人自居。
它何以能够受到年轻一代的热捧?和它相处久了,就连我这样以前十分排斥宠物的人也不得不宠爱它——它唤醒了人类身体里许多渐渐失去的品质,比如温柔、好奇、爱和同情,等等。
我们在虎皮不在的时候谈论虎皮,“虎皮”这个词,唤起万种柔情,就像阳光照耀着湛蓝的大海。
虎皮不见了!
三十二层消防楼梯上的脚步声。虎皮虎皮的呼喊声。在保安岗亭的问询,在小区每一个角落的找寻,在地下车库对每一辆车底部的“检查”,在小区微信群寻猫启事的发布……
虎皮不见了!全家出动。简直是一场精神地震!一家人陷入悲伤。孩子们坐在沙发上落泪,再无心看手机。世界的焦点从中美科技战、俄乌冲突和涿州大水转移到“虎皮”上。像遇到其他所有不可抗力一般,我们唯有祈祷菩萨保佑虎皮归来,祈祷奇迹发生!
这才思考“虎皮”的意义。一个生造的词语,在生活中获得了巨大的意义!
以虎皮为核心旋律主导的生活节奏一下子陷入崩溃后的寂静。但是,寂静中响起敲门声。对面邻居告诉了我们虎皮的下落。她是在电梯里无意中听一个小孩儿说出的。
虎皮在十五楼那户人家像一个失去父母的孩子一样羞怯而恐惧地缩在一个笼子里。那家人也养猫狗,有些犹豫但还是把虎皮归还了。
失而复得!多么富有戏剧性!但是再不能让它的大意和我们的粗心导演这样的戏码了。
它蹲在电视柜旁边,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睁着一双湛蓝的大眼睛。
虎皮以“虎皮”之名进入语言,它在行动中,以它优雅的步态和美丽的毛色激活了人的感觉,于是一些沉睡的词苏醒了,比如“陪伴”“安宁”“独立自足”,等等。它趴在窗台上看世界,刷新了人类的世界观——一种纯粹的看,使得世界的美,重新从屋顶上或者街头远远呈现,是什么遮蔽了人类的眼睛?
当人类陷入自我或虚幻(在手机中),它把你拉进人和人的关联性之中。
当它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静静舔着自己,不是自恋,而是给予“洁身自好”一个新形象。
当它度过长夜,小心翼翼避开你的身体,以它的嘴拱你,你说还要睡一会儿,它仿佛听懂了,就默默等在床头。这不是“耐心”或者“理解”?
当你抱着它,细看它那双湛蓝的眼睛——是否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影子呢?是否骨子里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血液呢?它似乎超越了一切文化观念,就像湛蓝的海水。
现在它跃上写字台,踩在电脑键盘上,踩出一串长长的逗号。我摸了摸它的头,操着它的肚子,挪开它,没等我删除那些它制造出来的“词语”,又来了。我抱起它,看着它。它挣脱。它有自己的尺度或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