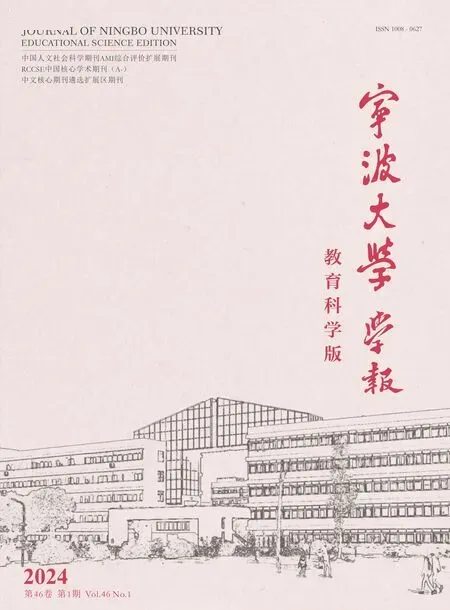具身沉浸倾听语文教科书声音景观的实现路径
杜二敏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当下,人们置身的移动传播时代是一个更加具有陪伴性、开放性、个性化的生活时空,不断消解了视觉至上及其带来的不良影响,进入到了诸感官处于相对均衡状态的“全觉体验”时代,听觉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声音得到关注。近年来,学界开展的“听觉转向”研讨活动旨在提醒人们,“声音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景’,忽视‘声音景观’无异于听觉上的自戕”[1]。语文作为“纸上有声”的学科,其重要载体——语文教科书作为一个声音容器,在本体设计和承纳内容两个维度上,具有丰富的声音景观。
一、语文教科书声音景观的构成
(一)语文教科书本体的声音景观设计
语文教科书的设计受到当代出版理念与实践的双重影响。当代出版行业在理念上不断优化、在实践上持续创新,源源不断地将更为丰富的元素融入出版行业中,成为语文教科书声音设计的参考维度。日本著名设计师杉浦康平指出:“所谓视觉传达是指对信息进行设计的‘建筑’,从多种感官相互联通的角度来看,书籍设计这一平面造型不仅局限在视觉层面之内,一页又一页的纸成为视觉传达的中介物,是有着长度、宽度和厚度,占据三维空间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存在。”[2]123如果将一张纸放在手上,将其进行对折、再对折,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耳畔会传来纸张折叠声,折叠之后的纸张产生了结构,纸张也因此具有了生命气息,获得了独属于它的“生命”,转化为富有存在价值与生命意义的立体性存在,纸张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具有传奇意义的变化。一本本的书就是由一页页的纸有机且富有创意地组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立体构造物。书中蕴藏着的故事在一页一页的纸上写就,铺展开来,其间还具有将完整故事首尾贯穿起来的一条线,由此可以看出,“一本本书就像一部部电影,蕴含着时间元素,是一个个瞬间前后相续的有机衔接。在书中,故事的铺开连绵起伏,此刻是宁谧的平坦原野,下一个瞬间则成为高耸的巍峨群山”[2]163。一本本的书虽然小,但是蕴藏着天地万物发出的多元化声音,从这一角度来看,“书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容器,其中蕴含着的多种元素相互作用,呈现出流动、排斥、膨胀、交融之态,书在不断被‘造型’的过程中,将整个宇宙收纳进来,充满了‘灵性’的力量”[2]181。因此,设计者在对作为视觉传达的书籍进行设计时,不但赋予其文字可运用眼睛进行阅读,以发挥视觉的功能,而且还能够让人们产生大声朗读的冲动,或者进行倾听式阅读的心向,进而发挥听觉的功能,倾听“纸上有声”的文字之美。
从设计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视觉传达,语文教科书主要通过文字、纸张、色彩等丰富的视觉元素,传递出作家盛放在文本中的多元意蕴、传达出语文教科书编写者的编辑意图、传送出教材设计者的设计理念。无论从内容资源的优化整合,还是从形式上的装帧设计,无不是如此,这已经成为人们对语文教科书的一般认知。从移动传播时代的角度进行审视,身处其中的人们不断实现着听觉回归,社会听觉关怀得以彰显,移动的媒体和流动的师生成为语文教学世界的新生景观,为此,“视觉传达设计”正经历着逐渐消解“视觉”霸权地位的过程,凸显出移动传播时代中的人们强调多种感官协同作用下的交互体验,这对语文教科书的设计理念与设计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当下,语文教科书的设计除了满足师生诉求、识别、认知等方面的功能之外,还加入了倾听体验下的信息互动维度,增添了与声音密切联系的情感体验功能。在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与设计过程中,编写者与设计者打开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将色彩、声音、材质、结构等多种元素有机融入语文教科书的设计过程,将语文教科书的信息传达建立在人的多感官协同发挥作用的基础之上,借以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增强了语文教科书设计的叙事性与情感性。
(二)语文教科书承纳的声音景观
语文教科书是“纸上有声”语文学科的重要承载主体,本身就是多元声音共生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存在。从隐喻角度来看,语文教科书就像一个声音容器,承接并容纳着丰富多元的声音形象,创造出不同的声音意象,具有声调美、节奏美与情感美和谐统一的特点。语文教科书承纳的声音景观,由声音与声音的交汇融合而成,声音的来源路径多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大自然是声音的重要来源,在语文教科书中,对自然之声的关注无处不在,比如,水流潺潺、蟋蟀㘗㘗、蜜蜂嗡嗡、笋芽钻土等。不同对象发出的多元化声音,为不同作家敞开的耳朵、敏感的心灵所倾听、所体验,并编织进文本,渗透在不同学段的语文教科书中,成为学生学习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统编语文教科书中,除了关注自然之声,还选入了不少声音意象的倾听型文本,比如,散文《大自然的声音》[3]88-89,意在引起学生关注自然,倾听大自然丰富且美妙的声音。作为大自然的音乐家,风声大合唱、雨声奏鸣曲以及动物音乐会,穿梭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召唤语文教师和学生进行倾听。《听听,秋的声音》[3]22-23是诗人毕国瑛张开倾听的耳朵,细心搜集秋天发出的各种声音,并将其投注到典型的听觉意象之上,形成了黄叶道别、蟋蟀振翅、大雁叮咛、秋风歌吟等富有倾听性的秋之典型声音景观,吸引学生张开倾听的双耳,感受自然之美,这是从小学低年级开始即注重培养学生能倾听、会倾听、善倾听能力的鲜明体现。此外,大自然中存在的声音,包括平淡无奇的声音,甚至还可能是噪音,比如,解牛之声、鸣蝉之音经过作家的艺术化书写,成为蕴藉着倾听之美的文本,具有浓郁的可倾听性。当它们被教材编写者选入语文教科书之后,成为教学文本,同样也构成了语文教科书的声音景观,吸引学生沉浸在倾听活动中。
在语文教科书中,声音景观不可或缺的构成主体是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人,人是一种具有多重人性表现、有着丰富生命体验的独特存在,“每个人都是典型的,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4],因为人是一定的个体,其发声吐字所借助的语音是人分离的身体,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具有个性化的特点,这也正是卡尔维诺在罗兰·巴特观点的基础上向前推进所揭示出来的“语音独一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有力证显。关乎人生命成长、发展及完善的语文教科书的编写者和设计者自然会利用这一资源,充分发挥语文教科书“纸上有声”的特质,让师生在学习过程中借由声音联想与听觉想象产生“如闻謦欬”的生命体验[5]。基于对人及其语音的深刻洞悉,善感敏锐的作家运用生花妙笔将一般人不曾留意、尚未入心的倾听行为记录下来,“作家在倾听行为基础上开展的每一次文本创作活动,既是他个人心灵历史的艺术化书写,又是他对一个时代做出积极回应所进行的有力传达”[6]。语文教科书编写者承担着编写文本的责任,他们选入了鲜活、个性的角色样态,透过个性独特、角色多元的“声音之口”,建构出意蕴丰富的文本之声。语文教科书中的各种角色,在他们所生存的社会大环境及其所置身的生活小环境中,发出了个性化的声音,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与实用类等多种文体中均有着出色的描写。丰富的声音被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语文教科书的声音景观,充分彰显出语文是一门蕴含倾听之美的学科,从不同维度满足了师生对语文教科书声音景观的倾听,有助于语文教师和学生对生命之音的深入理解。
在语文教科书的未来设计过程中,纸质、有声、数字化等多种类型的语文教科书将会更加关注有声的插图设计,形象化的结构逻辑,纸张材质的声音元素,等等,具有可听性、可看性、可读性与可互动性等特点,多种因素协同作用,声音效果动态立体,体验方式多元交互,共同促使语文教师和学生主动打开多种感觉,全身心投入到语文学习过程中,进行“整全感官”共同参与下的“全觉体验”。可见,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与设计是一个多种元素有机联系、前后相续,并且蕴藉着鲜活、具体、形象、独特之人的动态化存在,而非器具化思想的过程。这意味着语文教科书声音设计关注的焦点不再仅仅着眼于物,而是重视师生与语文教科书的交互过程,同时注重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倾听体验。从声音景观的角度加以审视,语文教科书的设计体现出了这样的发展趋势:从关注外在形式的“硬件时代”,经由注重内容的“软件时代”,逐渐发展到兼具内容与形式,同时考虑到移动传播时代中语文学科“人文性”的“人的时代”。
二、语文教科书声音景观选取的尺度
语文教科书充溢着自然之声、人的言说、社会之音、艺术之声,是作家在多种情境中对来自不同路径、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声音进行多维度倾听的基础上,联合多种感官,借助文本呈现出来的。在编写者的共同创编下,连同设计者富有创意的设计,语文教科书发展成为“美声”意义上的存在。语文教科书的“美声”特质既源于书中多元声音的有机共处,又离不开由多元声音共同建构的生态环境。从编写者与设计者的理念与实践来看,语文教科书的声音景观选取遵循三个尺度。
(一)生态尺度
语文教科书选取了丰富的自然声音景观,从根本上还原并保留了自然声音景观的多种样态。雨滴荷花、风吹芭蕉、枝上鸟鸣、叶间蝉声、田里蛙声等声音景观表现出迷人、喜人、乐人的特点,它们“传入”语文教科书,既是作家倾听自然的结晶,又是语文教科书编写者和设计者慧耳听声、慧眼识声以及慧心品声的智慧性选择,还成为语文教师和学生在纸上倾听自然的重要条件,与课堂之上的他们张开耳朵,倾听教室之外的自然而获得的声音相映成趣,共同促使他们更好地认识自然,对理解文本与建构意义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语文教科书声音选取遵循生态尺度的具体表现。
(二)多元尺度
语文教科书中的声音景观取自不同路径,源于多元主体,多元尺度是教材编写者选择时自觉而主动的表现。如果对语文教科书进行审视,从声音景观的角度凸显听觉审美的文本就有不少,比如,彰显自然之声的《听听,秋的声音》(毕国瑛)、《春》(朱自清)、《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辛弃疾)、《秋声赋》(欧阳修),表现艺术之声的《村晚》(雷震)、《口技》(林嗣环)、《琵琶行》(白居易)、《秦腔》(贾平凹)等。从声音的功能来看,丰富的声音景观抵达语文教师和学生的身心,有助于唤醒他们的听觉感官;就倾听的作用而言,语文教师和学生关注意蕴丰富的文本,进入作家营造的文本世界中,丰富了他们的听觉审美体验。除上述具备显性可听性质的文本之外,从广义来看,语文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本,其主要构成元素汉字具有“形”“声”“义”三位一体的特点,汉字所特有的声音之美,赋予了语文教科书浓郁的可倾听性,为语文教师和学生进行倾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三)人本尺度
语文教科书所选择的自然之声、人的言说、社会之音、艺术之声,是作家借助眼耳鼻舌身等感官积极体验,运用生花妙笔,赋予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度中的人们发出和他身份相符合声音的能力,借以塑造出一个又一个“这一个”的典型人物形象。在越来越公正、文明、民主的社会里,语文教科书中不同样态的声音主体,以其独特个性在世存在,无论他们发出多么微不足道的声音,都能够被语文教师和学生所倾听,并得到及时回应。从这一角度来看,语文教科书声音景观的选择、设计与呈现还遵循着人本尺度,体现了对人生命在世存在的倾听、看见、承认与尊重,充分印证了人是语文教科书的创造者、编写者与设计者,同时人又是语文教科书最终的使用者,人本应该作为被关注的焦点。在移动传播时代,人的主体地位不断显现出来,人们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人类自身,提出了“人本尺度”的语文教科书编写理念与实践,以及设计理念与实践。语文教科书声音景观选择的人本尺度,形成了多元而丰富的声音样貌:令人喜欢的与憎恶的共存、积极的与消极的共生、正面的与负面的共在,这些声音进入语文教师和学生的倾听之耳,如果他们的身体能够积极在场,进行具身沉浸倾听,那么,为不同声音所萦绕的生命主体,则能够发展“耳识力”。
三、具身沉浸倾听语文教科书声音景观的生命状态
作为身体自我、智力自我和精神自我的寄居场所,身体具有独特的价值,与人们的精神生命相始终,从初生柔弱到不断强大,再由逐渐衰弱到最终离场,在整个生命成长过程中,身体在每一个生命在世存在的时空中始终积极在场,敏锐地体验着人间冷暖、细腻地品味着酸甜苦辣,是一直处于成长过程中的身体。每一个体自我身体的成长变化过程,既能够为他者目见耳闻,又可以为自我深切感知,毫无疑问,后者的体验感更强,加上可以借助外在工具映射出个体的“镜像自我”,从应然状态来看,身体参与人们的各项活动,对自我身体的积极照看以促使其主动发展,既成为个体不可推卸的分内之事,又有其发生的必然性。不过,受到主客二分、身心二元对立认识论的影响,加之,个体有意或者无意的忽视,与占据主体地位的心灵相比,身体则处于客体地位,在认知过程中,它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缺失了身体的积极参与,特别是离身参与下的诸多活动,人们的活动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不良影响。为了改变身心分离、相互对立的局面,20 世纪80 年代,具身认知得到不断发展,在多个学科领域得到积极回应与实践,如哲学、心理学、医学、音乐学、教育学等。具身认知强调人的心智发展是大脑、身体与外在环境积极共在、相互作用的产物,人的身体并不是盛放心智的容器,环境也不是被割裂出来仅仅作为心智活动的场所。从四者的关系来看,人的心智嵌入大脑中,大脑嵌入人的身体内,身体又嵌入人所置身的环境中。就人的生命整体来看,心智、大脑、身体和环境四个方面须臾不可分离,作为有机统一的整体发挥作用。“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对具身认知的内涵加以理解,第一个方面,身体积极参与人的认知、思维、体验、评价等活动,其表现出来的状态发生变化,对人的认知、思维、体验、评价等活动也会产生不一样的影响。第二个方面,在大脑和身体之间存在着特殊的‘感觉—运动’通道,它们在个体认知活动的启动、发展、完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基于心智、大脑、身体、环境四个方面相互嵌入、彼此交织的关系,既需要将人的心智、大脑和身体,又应该将环境中的相关因素纳入到人的认知、思维、体验、评价等活动过程中。”[7]
沉浸既是一个概念,又是一种生命状态,其意为“浸入、浸泡在水中,在不同的语境中,人们多使用它的比喻义,即人投注时间、精力、情感、智慧于某种氛围或者思想活动中”[8]。在日常生活中,当人们对某种知识学习、情境认知、思想活动产生了身心情意整全生命意义上的投入状态,甚至忘记了身边其他无关的人、事、物,这意味着他进入到了一种沉浸状态[9];从学习的视角进行审视,“‘沉浸’更主要地指人们在学习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积极‘走心’状态,意在凸显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凝神专注状态”[10]。无论从日常生活进行审视,还是就学习来看,沉浸都表现出主体全神贯注的一种生命状态,是更好地进行认知、思维、体验、评价等活动的必备条件。倾听主体具身沉浸,将心智、身体、大脑和环境积极融为一体,沉醉于语文学习过程中,具身沉浸的精髓就在于实现心智、大脑、身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激荡,语文教科书的声音景观,也需要借助师生的具身沉浸倾听,由心智、大脑、身体与环境的积极互动加以实现[11]。
四、具身沉浸倾听语文教科书声音景观体验的三重境界
编写者与设计者植入声音景观的语文教科书呈现在师生面前,在他们的轻声翻阅下,语文教科书这一本体就能够发出“沙沙沙沙”的悦耳声音,声音频率与师生的精神需求相契合,成为语文教科书“美声”特质的本体表现,既是语文教科书鲜明个性的声音标签,又是师生对语文教科书声音体验的最原初形式。身体在场,心入其中,身心情意浑然一体,身体自我、智力自我和精神自我积极共在,师生以手轻轻触摸语文教科书,耳边响起的手动翻阅书本的声音,成为语文学习的前奏曲,开启了他们的语文学习活动,赋予了他们愉悦的心情。这样的声音体验,需要能倾听、会倾听、善倾听的语文教师和学生拥有敏锐善感的心灵,惟其如此,他们才能够感知、体验到语文教科书所发出的细小轻声,并且将它们迎接到主体始终处于敞开状态的倾听之耳内,与之建立起生命的连接关系。相反,如果语文教师和学生的身体缺位、心情烦躁、内心嘈杂,必然导致他们精神涣散、心不在焉、置若罔闻,一则难以听到语文教科书本体传达出来的声音,二来急躁用力翻动语文教科书而产生的“哗哗哗哗”声响,可能不会引起语文教师和学生的注意,或者虽然能够得到关注,但是往往作为一种噪音遭到师生耳朵的拒绝。语文教科书的声音设计之美在第二种情况下作为不美的样态,难以获得师生源于生命深处的积极观照,更无法得到他们的主动倾听。
不管从哪一层面来看,“美声”语文教科书的实现都离不开语文教师和学生的积极参与,需要他们的身体自我、智力自我与精神自我主动在场,身心情意积极共在的具身沉浸倾听,既可以是语文教师、学生所进行的独自倾听,以品味语文教科书的多重意蕴,又体现为语文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倾听,构成了他们共同的声音记忆。师生对语文教科书的声音体验,随着他们的生命成长,倾听能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体现出三种不同的倾听境界。
第一阶段为听而不闻,处在这一阶段的语文教师和学生表现出心不在焉的倾听样貌,他们既听不到语文教科书本体作为兼具物质性与精神性存在而发出的声音,又听不到语文教科书中多元化、个性化的主体所传达出来的各具特色的声音。“纸上有声”的语文教科书,在听而不闻阶段就此沦落成为“无声”的存在。第二阶段为听而闻声,这一阶段中的语文教师和学生身心在场,他们能够倾听到语文教科书的本体之声,以及语文教科书中的人、事、物发出的声音,并且可以从声音中听出意义,品味文本意蕴,“纸上有声”的语文教科书,作为声音传达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存在,为语文教师和学生所听到,并且能够对它们产生反应。第三个阶段为听而享声,无论对语文教科书本体来说,还是就它所承纳的多元化声音而言,这一阶段的师生对语文教科书发出的声音均怀有深深的喜爱之情,基于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他们以身倾听、以知倾听、以思倾听、以技倾听、以心倾听、以情倾听、以德倾听、以慧倾听,倾听诸要素得以充分调动,和语文教科书的声音景观建立起优质的连接关系,展开全景性的多层级倾听,实现了对语文教师和学生生命的积极疗愈,这是他们对语文教科书声音景观具身沉浸倾听的理想状态,登临这一境界离不开倾听主体的具身沉浸,以及声音体验能力的不断提升。师生对语文教科书声音景观具身沉浸倾听的每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见表1。

表1 具身沉浸倾听语文教科书声音景观的三重境界
需要澄清的是,师生“对语文教科书声音景观具身沉浸倾听能力的提升是‘锦上添花’之举,而绝非‘喧宾夺主’之为”[12],它和师生开展其他学习活动所形成的核心素养共同推动语文教学迈向更为理想的境界。
五、具身沉浸倾听语文教科书声音景观的实现路径
(一)热爱语文的心性
具身沉浸倾听语文教科书的声音景观需要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即语文教师和学生发自内心地喜欢语文学科,由此衍生出喜欢语言文字,以及喜欢主要借助语言文字而呈现出来的文本,这也是语文课程性质“引导学生热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13]的重要体现。拥有热爱语文心性的主体才可能会主动开展语文教科书声音景观的具身沉浸倾听活动,其活动样态表现形式不一,既可以是对语文教科书的倾听,以品味语文教科书本体及其所承纳文本的声音之美,感悟文字的节奏韵味,通达作者创作文本的原初意义,在激活倾听主体的知识储备、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唤醒他们情感体验的基础上,建构出文本尚未言说出来的意义之维;又可以开展其他形式的具身沉浸倾听活动,比如,听画解文活动,借由具身沉浸倾听语文教科书中文意画所发出的泠泠之音,赋予静态画面动态化、声音化的意蕴,走近作者,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走近文本,欣赏文本的意义之美。语文教科书的“声音景观既然已经为作家所创作、为编写者所编写、为设计者所设计,那么体验声音景观的活动则聚焦于‘倾听’之上。具备热爱语文学科心性的倾听主体才能更好地发展出‘音景式思维’,这样他们就能倾听到语文教科书发出的多元而丰富的声音景观,无论是积极的、正面的、喜欢的,还是消极的、负面的、憎恶的,均能够进入他们的倾听之耳,丰富他们的生命体验”[14]。
(二)适合倾听的声音
视觉传达的语文教科书本体,越来越注重生态尺度、多元尺度和人本尺度的设计理念与设计实践,不仅在视觉上满足了语文教师和学生的智力发展与心理需求,而且注重纸张品质的优化选择,为语文教科书添加了声音维度,保障了爱上语文的师生在翻阅语文教科书时发出悦耳的沙沙声,成为“美声”语文教科书最为本源性的体现,是适合具身沉浸倾听的声音品质在语文教科书本体中的积极呈现。此外,在语文教科书中,弥漫着经过作家的艺术化加工而呈现出来的富有审美意蕴的声音意象,比如,笛声、琴响、蝉鸣、猿啸、莺啼、雨声、风吹、雪落等,它们构成了适合倾听声音品质的组成部分,为语文教科书增添了“声音轨道”,建构出了语文教科书的声音维度,构成了语文教科书的倾听之美。在语文教科书中,还存在着这样的声音,它们由发展不充分、具有明显人性弱点的人所发出,是作家为了表现特定的主题,在对声音进行艺术加工的基础上写就的,构成了文学长廊中“这一个”人物“语音独一性”的重要表现维度,这些声音从另一个层面为语文教师和学生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促进人更好在世存在的样态。在民主、公正、文明的社会中,人们的不同存在样态得到承认、理解与尊重,多元共生是其基本表现形式,为此,语文教科书编写者与设计者看见、听到、体验着各种不同样态之人的“存在”和“存有”,他们珍视生命的每一种存在样态,将其所发出的宏大声音、细小轻声,连同沉默无言,都收纳进语文教科书这一声音容器中,让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学生看见、听到、体验出不同样态生命的在世存在,映射出社会的进步。语文教科书本体所发出的声音与它所承纳的声音景观,作为适合倾听的声音品质,共同润泽着语文教师和学生的倾听之耳,丰富了他们的生命体验。
语文教科书本体传达出来的声音景观与倾听主体产生精神共振,成为适合倾听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存在,达到悦耳润心的目的,让人乐于倾听。为了更好地实现具身沉浸倾听,还可以从倾听主体更好体验的角度加以优化。从语文教科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可以通过视觉设计达到优化听觉体验的目的,这种做法虽然并没有改变语文教科书的声音景观,不过,在人的感官与感官之间会出现联觉,而视觉与听觉之间产生的联觉能够因“悦目”而产生“动听”的移情作用和增殖效应。另一方面,可以对语文教科书发出的声音,以及声音效果进行优化,具体来说就是优化语文教科书的设计结构,比如,从语文教科书的材质加以考量,改善语文教科书的材质;借助不断发展的语音识别技术,实现插图的有声化与立体化;运用形式多样的声音谱系,乃至各种各样的声码识别图像,为语文教科书植入声音传达二维码,实现扫码倾听名家朗诵,倾听与文本有关的声音景观讲述,等等,都可以成为语文教科书的声音标签,提升了语文教科书的声音品质,增加了语文教科书的“美声”维度。通过为语文教科书添加声音元素,优化的声音传达出了悦耳润心的“美声”,丰富了语文教师和学生的倾听体验[15]。
(三)开启重听学习范式
图像景观与声音景观的交融,图像思维和倾听思维的合一,既是移动传播时代对语文教科书设计提出的要求,又是人们多种感官协调发展的呼吁。语文教科书声音景观的丰富多维需要主体将“重听”作为一种新的学习范式,其功能与俄国形式主义学者为了恢复人的多种感觉而提出的“陌生化”相契合。如梅尔巴·卡迪-基恩所主张的“抛开非语义学层面上的重读,借助声音路径的重听活动,我们寻求到了理解语文教科书的新范式”[16]。阅读语文教科书时,师生聚焦图像景观,运用图像思维,更为充分地发挥了视觉功能,成为图像时代的表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视听失衡现象的发生。为了改变这种情形,语文教师和学生开启重听语文教科书的学习范式,促使“纸上有声”的语文教科书散发出习焉不察的听觉芬芳。
依据语文教科书声音景观的呈现样态,可以分为两种重听类型:一是语文教科书所选文本具有丰富而鲜明的声音景观,为倾听主体重听时所进行的“听声”和“听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有助于师生具身沉浸到语文教科书丰富的声音景观中,借由听声而达意,进而实现听声而构意。二是语文教科书所选文本呈现出来的声音信息较弱,这与声音的品性相关。由于声音无形、转瞬即逝的特点,加之拟声词、感叹词的有限导致了以声写声受到限制,如不能转向以形类声的摹写声音之道,作家对声音景观的书写往往会表现出俭省的特点,不过,声音景观的意蕴却并非因此而变得简约。从广义上的文本意涵来看,重听语文教科书中这种类型的声音景观仍旧具有可能性,因为“就发生机制这一原初意义上而言,作家所创作的文本首先是对声音的捕捉、倾听与记录”[17]。语文教科书中这种类型的声音景观更值得师生具身沉浸倾听,其原因在于第一种类型明显易听,容易得到关注,后者的声音景观隐蔽难察,稍不注意就会与其失之交臂,因此这种类型的语文教科书声音景观更应该获得师生的重听。为了更好地开展重听活动,师生一则对声音进行具身沉浸倾听,二来还需要充分发挥声音联想与听觉想象,从而理解语文教科书声音景观背后的丰富意蕴。师生重听语文教科书声音景观的形式多元,既可以是对语文教科书本体声音景观的具身沉浸倾听,又可以是对单个文本的具身沉浸倾听,还可以依据不同文本书写的不同声音景观进行多文本组合,比如,优选“笛音”“雨声”“禽语”“钟声”等作品展开语文教科书的群文重听活动。在重听语文教科书声音景观的过程中,为了避免“以目代耳”现象的发生,语文教师和学生需要回归吟诵、唱读、讽咏等传统语文学习中的“耳识”之法,重听语文教科书,借由听觉路径细心感受、品味、体验文本,“因为语文学科是一门‘口耳之学’,更好地进行学习离不开‘耳治’之功”[18]。宋代郑樵在《通志·乐略》中向世人发问:“古之诗,今之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可乎?”“郑樵之问”从声音角度强调了对诗歌词曲的吟唱,隐含着重听行为,具有穿越时空的意义,有助于纠正视觉至上仅凭眼睛所进行的走马观花式阅读之弊端。由于声音有稍纵即逝的特点,加上听觉联想的变幻无穷,在重听语文教科书的声音景观时,师生可以运用自由联想的方式,以达到《楞严经》所说的“心闻”之境界。
六、结语
在社会重视听觉关怀背景下,语文教科书仿佛成为一个声音收纳器,蕴含着不同声音主体发出的多元化声音,构成了语文教科书丰富的声音景观,吸引着语文教师和学生以新的姿态投入到学习过程中。在主体重听范式开启之下,具身沉浸倾听语文教科书的声音景观,语文教师和学生需要张开耳朵,积极联通包括眼睛、大脑、心灵等在内的其他感官,充分发挥多种感官的联合作用,在充满听觉关怀的社会语境中,不断发展出“全觉体验”下的语文教科书学习范式。
需要澄清的是,在视觉至上转向听觉关怀的过程中,师生所开展的具身沉浸倾听语文教科书声音景观这一学习活动,既不是将听觉置于视觉之上,又不是以听觉取代视觉,更不是以听觉压倒视觉,而是基于平衡发展人体多种感官的目的,师生充分发挥每一种感官在语文教科书学习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并将它们进行有机整合。借由具身沉浸倾听语文教科书声音景观的活动,开展感官与感官之间的联合共创,实现意义建构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