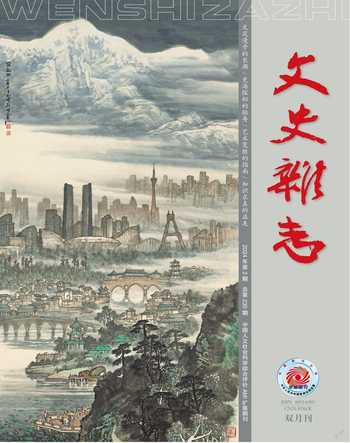武则天时代与蜀道石窟
王洪燕
摘 要:蜀道石窟始于北魏晚期,虽历代均有开凿,实则兴盛于武则天时代。武则天时代奠定了今天蜀道石窟基本格局。其时佛教兴盛,蜀地经济文化繁荣,得以支撑蜀道石窟佛教造像的大规模凿刻。它们与同时代其他石窟如中原石窟相比较,具有独自的地域文化内涵与特色。
关键词:佛教发展;扬一益二;地方特色
蜀道作为联结关中和四川的重要通道,遗存了大量唐代摩崖造像,其气势雄伟、典雅,具有盛唐大气磅礴之风格。广元素有“女皇故里”之称,蜀道与武则天关系密切。武则天时代为蜀道石窟兴盛的关键时期,蜀道石窟于此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本文所指蜀道石窟主要是指蜀道中的金牛道和米仓道的佛教摩崖造像。至于武则天时代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相对比较模糊;学者界定的时间长短和起止年代均有较大差别。从持续时间来看,所谓武则天时代时间最短者,如唐代杜佑在《通典》中所言,乃从武则天登基到神龙政变退位的十五年;[1]时间最长者,则如台湾学者雷家骥所言,自贞观十四年武则天入宫到神龙政变武则天退位,中宗复国这段时间,约六十五年。[2]其他如王涤武、申少亚等学者对武则天时代的界定均有不同说法。陈寅恪先生甚至将武则天时代影响的终点界定在安史之乱爆发之时。[3]本文从蜀道石窟开凿及变迁的角度,认为武则天时代是从武则天之父武士彟在蜀道重镇利州任都督开始,到玄宗先天初年止,即在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至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之间,共约八十五年。
一、武则天时代的佛教发展
初唐时期,唐高祖、唐太宗尊道教祖师李耳,把道教放在儒释道三家之首。武则天掌权后,青睐佛教,将其放在三家首位,佛教从而走向繁荣期。
武则天与佛教的渊源,首先在于武则天的家庭。武则天父亲武士彟资助李渊起义反隋。他成为新贵后,相传又与隋朝宰相杨达之女婚配,其政治地位大大提升。隋朝推崇佛教,作为宰相之女的杨氏也笃信佛教。在武士彟任利州都督时期,她在皇泽寺有礼佛活动。皇泽寺残存的第12号、13号窟有相关题记,现已风化,但《八琼室金石补正》录文之《再修西龛佛阁记》中,明确说明西龛佛阁是由武则天母亲杨氏所造。[4]有学者认为利州都督武士彟夫人杨氏造寺像的活动,客观上对广元初唐时期的石窟开凿有所推动,“使广元的造像活动更加频繁,从而使广元成为四川初唐造像最具规模的地区,广元也因此迎来了石窟开凿史上的第一次高潮”[5]。武则天的家庭对礼佛活动十分重视。赋则天从小得以耳濡目染,遂对佛事活动情有独钟。武则天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入宫。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她即入感业寺为尼,参加诵经、礼佛等佛事活动,对佛教有更多的体验,从而与佛教结下更深厚的情缘。
武则天于唐高宗时再次入宫后,在逐渐走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中,采取一系列推崇佛教策略。武则天在准备登上帝位之际,僧人薛怀义等人译出《大云经》《宝雨经》等,称她是弥勒佛转世为女身当帝王,这就为她改朝换代提供了有利的舆论支持。佛教也因此得到相应的地位。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敕:“释教宜在道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6]。武周时期,武则天大肆修建寺院庙塔,特别是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藏《大云经》;同时,她还热衷于开窟造像,如龙门现存的卢舍那佛像即为大手笔。梁思成先生認为武则天“于佛像雕刻,尤极热心,出内帑以建寺塔,且造像供养焉。就唐初遗物观之,唐代造像多在武周”。长安城中,“武后时期造像尤多”。[7]武则天还热衷佛教经典翻译事业,亲自主持规模巨大的《华严经》的翻译。这一系列操作让佛教成为“国教”,融入到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种大背景下,与武则天有着密切关系的蜀道沿线,其石窟开凿造像即进入繁盛时期。
二、武则天时代的蜀道石窟
武则天时代的蜀道石窟按现有行政区域划分,最具有代表性的为金牛道和米仓道上的广元石窟、巴中石窟;沿线其他区域则少有分布。
(一)武则天时代的广元石窟
广元石窟是指广元境内石窟,共计造像59处,其中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意义的集中在利州区,分别是千佛崖摩崖造像、皇泽寺摩崖造像、观音岩石窟。皇泽寺摩崖造像现存造像57龛,大小造像1200余尊,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凿于北魏晚期。其历经北周、隋代、唐初的不断开凿,到高宗、武周时期达到全盛。千佛崖摩崖造像现存龛窟950余个,其中重要的窟约20个,现存造像约7000余身,题记130余条,始凿于北魏晚期,大多是唐代作品,主要集中开凿于高宗、武周、中宗、睿宗、玄宗时期。
姚崇新将广元石窟分为3期,认为高宗、武则天时期正是唐代造型艺术的形成时期,这个阶段是广元石窟造像开始进入大规模的开凿期。[8]
武则天时代的广元石窟,虽然从贞观年间武则天母亲杨氏在皇泽寺开窟造像开始,但武则天当政后广元石窟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即出现了改造前人龛窟的现象。千佛崖莲花洞(535号)位于千佛崖崖壁中段下层,紧邻古蜀道边上,之前根据龛内有“大周万岁通天年”的题记将该窟开凿的时间下限定为武周万岁通天年间(公元696年)。现存大龛为破坏了主尊前莲花上的大像后重新雕刻,原来大像的头光还残留。窟顶大莲花,与洛阳龙门宾阳洞中的大莲花非常相似。由此推测此窟开凿于北魏后期,但武周时期作了改造,并补写了若干题记。同时皇泽寺中心柱窟(45窟)也有被改造过的痕迹,由此可以推断武周时期,广元有一批北朝窟龛被改造了。[9]改造的目的是突出象征武则天弥勒佛的居中地位,可见广元石窟的政治色彩很浓厚,这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案例。这一时期倚坐弥勒佛造像在广元石窟中也较为流行,如千佛崖493号俗称神龙窟,开凿于神龙二年(公元706)年,龛内雕一尊倚坐弥勒佛像,二地神托起佛座。
武则天掌握朝政多年,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有“政启开元、治宏贞观”之美誉。神龙政变后武韦集团的影响力仍然持续。广元石窟在中宗、睿宗至玄宗开元时期达到繁盛的顶峰。这一时期在广元出现了大批官员开凿的石窟造像。睿宗景云、延和年间(公元710—712年),利州刺史毕重华开凿了弥勒窟(365号)和菩提瑞像窟(366号)。开元三年至开元十年(公元715—722年)剑南道按察使、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韦抗在千佛崖捐资造像,现尚存大云古洞第512号和513号,千佛崖第222、213、421、86号龛以及大云古洞正壁南北大龛等。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宰相苏颋调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在千佛崖捐凿了211号龛。武则天时期的千佛崖开凿龛窟,虽百分之九十龛窟都没有开窟题记,但从造型上看大体都是这一时期作品,基本上是地方官员推动的。
武则天时代广元石窟造像组合出现新的样式,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二天王二神王十一尊像等。题材丰富,有释迦、弥勒、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沙门形地藏、天龙八部、药师佛、神王、菩提瑞像等。龛窟雕造像技艺精湛,出现背屏式镂空雕刻、圆雕等作品,奠定了广元石窟的独特格局。这是广元石窟发展史的繁盛时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武周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十月二十九日,武则天诏令天下两京诸州各立大云寺一所。千佛崖自北魏以后就有寺庙,最早称柏堂阁,武周时期更名为大云寺。大云寺在武周神龙政变后基本上都更名为中兴寺等,唯有广元至今仍称为大云寺;清代乾隆年间广元县令张赓谟还曾重修。这与武则天和利州特殊的关系密不可分。
(二)武则天时代的巴中石窟
巴中石窟是指巴中境内的石窟,位于古蜀道米仓道上。巴中石窟开凿的高峰期在唐贞观到开元初年。[10]巴中、广元两地都跟武则天有关系:广元是武则天故里,巴中是章怀太子被贬之地。[11]巴中石窟共计223处,其中唐代41处,宋代11处,元代2处,还有几处道教造像。其中唐代造像约670龛,造像约8200余尊,其中最具代表性者有南龛、北龛、西龛、水宁寺、石门寺等。南龛石窟是巴中石窟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现存龛窟176个,始凿于初唐,盛唐和中晚唐多有开凿。造像题材有释迦佛、三世佛、弥勒佛、菩提瑞像、双头瑞像等,西方净土变和毗沙门天王题材尤为突出。北龛造像34龛,从初唐到盛唐期间造像居多。西龛现存造像九十余龛,分布在龙日寺、流杯池、佛爷湾三处。大多数龛窟开凿于盛唐。
雷玉华等人将巴中石窟分为七期:隋到初唐、唐贞观到开元初年、开元后期至天宝时期、乾元年间到会昌以前、会昌时期、宋代造像、晚清和民国时期的造像,其中唐贞观到开元初年属于武则天时期的遗存。武则天时代的巴中石窟受到武则天崇佛政策的影响,出现了开凿的高峰。这个时期出现比较大型的龛窟。从石窟题材来看,出现了广元石窟未有的阿弥陀佛与五十菩萨、药师佛与十二药叉大将、双身瑞像等题材。巴中石窟中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佛帐形内龛,雕刻技艺精湛,有卷草纹、火焰纹、云气纹、莲花纹饰等装饰华丽,构成了巴中石窟独有的风格。
武则天时代广元地处蜀道的金牛古道之上,巴中位于蜀道的米仓道(巴岭路)上,都是重要的交通要道。从两地造像风格来看,均受到中原造像风格影响。巴中特有的如双身瑞像等题材可能与巴中与敦煌之间道路畅通有关系,[12]因此敦煌的造像样式可能直接传播到了巴中。这里的造像与蜀道其他地方相比,风格迥异。
(三)武则天时代蜀道上的其他石窟
1.汉中石窟
据统计汉中石窟57处,35处为清代造像,与唐代有关仅3处。最早的是牛头寺及其石窟,是一组寺庙与石窟相结合的石窟寺。牛头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牛头寺石窟原名千佛洞,始凿年不详,清顺治七年(1650年)重修,窟内现存1042尊石造像。该石窟寺是目前汉中地区保存规模最大和数量最多的石窟寺。武关河造像龛位于汉中市留坝县武关驿镇,根据造像风格判断为隋唐时期,现存东、北两龛,造像共计8尊,2号龛有一佛二菩萨、一佛二菩萨二弟子的造像。灵岩寺摩崖石刻坐落于略阳县城南七里嘉陵江畔的灵岩寺,创于唐开元年间,宋时臻于全盛,明、清渐衰。灵岩寺摩崖石刻以摩崖题刻、碑碣名闻天下,属于石窟寺部分仅有金龟洞及罗汉洞两处。两洞及周围遗存唐至民国年间摩崖题刻、碣碑共130余方(通),石造像20余尊。但武则天时代的石窟在汉中几无遗存。
2.绵阳石窟
据统计,绵阳石窟有88处,其中佛教造像隋唐时期43处,明清时期21处,元代1处,宋代1处,风化严重年代不详14处。绵阳唐代石窟总龛300余个,基本上属于规模小、保存较差的中小型龛像点,很多残损经过现代修补、妆彩,造像数量难以统计,无法识别其具体题材和年代。绵阳石窟大致始于隋,其余地区造像大多开凿于晚唐至北宋,[13]如位于绵阳市梓潼县宝石镇永利寺摩崖造像、位于绵阳市三台县塔山镇崇福寺摩崖造像。有题记可查的是绵阳市盐亭县文通镇龙门垭摩崖造像,开凿于隋代至初唐之间,有龛窟24个。
位于绵阳市江油市龙凤镇塔子梁摩崖造像题记有“武德二年”“武德九年”“贞观五年”等重要信息。梓潼县卧龙镇卧龙千佛岩摩崖造像始凿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其中1号窟代表性题材为阿弥陀佛与五十二菩萨。绵阳石窟中题记约50余则,如圣水寺摩崖造像有9则,塔子梁摩崖造像开窟造像题记10则。绵阳石窟造像规模小,有20余个龛窟。其中有唐代造像遗存,但武则天时代的造像很少。
3.阆中石窟
据统计,阆中石窟造像共47处,清代造像25处,隋唐造像15处。阆中石窟造像始建于南北朝时期,如石室观摩崖造像是一处以道教造像为主、佛道并存的造像龛群。慈云村佛耳岩摩崖造像从右到左共开凿4龛,14尊造像。大像山摩崖造像主要开凿于中晚唐和宋代,明清时期也有少量开凿。东门垭摩崖石刻现存龛窟3个,共计25尊像;佛洞坪摩崖造像开凿于隋唐时期,现存共2龛,20尊造像。黑崖湾摩崖造像现存3龛,破坏严重,只剩龛窟形制。雷神洞摩崖造像现有龛窟3个,造像36尊。灵城岩摩崖造像现存龛窟共4个,造像共计75尊,开凿时间为隋唐。此外还有牛王洞、普陀岩、千佛岩村、猪垭槽村等龛窟造像。
综上可见位于米仓道上的阆中在唐代造像规模小、點位分散,有明确年代的大像山摩崖造像有开元年间的造像,没有大规模的开窟造像,可见阆中在武则天时代造像也较少。
4.德阳石窟
统计表明德阳石窟造像较少,共32处,其中有唐代造像21处。德阳石窟造像始凿于唐代,规模小,零散分布,破坏严重;清代改凿、补凿较多。如观音崖摩崖造像开凿于唐代,均为小龛,清代有增补。千佛崖摩崖造像开凿于唐代,后代有增补,现有造像3龛,造像505身,其中唐代造像仅12尊,如第2号龛窟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第3号龛窟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大佛岩摩崖造像开凿于唐代,清代有重修,现有11龛,共31身造像,其中唐代造像26龛。德阳市中江县唐代摩崖造像较多,有彩虹村摩崖造像等17处,造像题材有千佛、阿弥陀佛与五十二菩萨、三世佛、观音,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像的造像组合,有佛道合龛现象如老观音摩崖造像。
德阳石窟造像规模小,点状分散,历史上改凿、妆彩改变了唐代龛窟和造像的本来面目,大多数龛窟只有唐代龛形轮廓,不好界定是否为武则天时代造像,或许会更晚。
综上所述,蜀道沿线其他地区武则天时代的石窟规模较小,分布零散,破损严重,题记较少,这便更加凸显出以广元和巴中为代表的佛教石窟的重镇地位。
三、武则天时代是蜀道石窟造像的全盛时期
武则天时代是蜀道石窟造像的全盛时期。蜀道作为蜀地通往中原的主要通道,是沟通南北文化传播的桥梁。武则天时代蜀道石窟的地方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造像题材丰富,群像雕刻独特。
蜀道石窟造像题材有释迦佛、三世佛、弥勒佛、阿弥陀佛、多宝佛、菩萨像、弟子像、天龙八部群像、飞天、力士、供养人、石狮、观音像、地藏菩萨像、伎乐、经变图、瑞像等,数不胜数,应有尽有。当时长安、洛阳的石窟流行组合样式在广元均有遗存,但又有创新。以武则天时代的蜀道石窟和龙门石窟比较,一是开凿者不同。蜀道石窟大多为地方官员如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韦抗、利州刺史毕重华等推动开凿;而龙门石窟在开凿技艺、规模、题材等方面尽显皇家风范,是皇权的象征,如武则天捐资开凿的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大卢舍那像龛群雕。[14]二是造像题材推陈出新,出现新的组合,如广元千佛崖流行的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二力士二天王二神王的组合,如512、513号窟等一批造像,特别是二神王造像,在其他地方还未出现过类似组合。三是造像组合新颖,出现佛教人物群像,如广元千佛崖86号窟不但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二天王,还有护法天龙八部群像雕刻在菩提树之间,坛前还有一对石狮子。这种组合在蜀道石窟中较为常见,同时巴中石窟中还盛行阿弥陀佛与五十菩萨等组合。
其次是造像分布广泛、规模庞大、造像数量大。
蜀道石窟在金牛道、米仓道上的造像分布范围广,沿途均有分布,造像数量较多。根据蒋晓春等人《嘉陵江流域石窟寺分期研究》的统计,仅四川境内就有“广元造像1241龛,8000余尊;巴中934龛,14194尊;达州161龛,3000余尊;南充644龛,14599尊;德阳125龛,889尊;绵阳406龛,3192尊;遂宁195龛,1737尊”[14]。同时根据笔者走访参加全国石窟普查工作的专家获得的信息,唐代蜀道石窟约有150余处,20000余尊造像。蜀道上石窟造像规模约为龙门石窟的五分之一。
唐代是建造大像窟的高潮,蜀道经济虽较中原落后,造像规模不能与中原地区相媲美,但是蜀地中特有的象征武则天的倚坐弥勒佛则盛行于蜀道石窟,如广元千佛崖535号莲花洞,窟高约4米,弥勒倚坐像高2米;138号窟北大佛窟中的倚坐佛像高约4米;493号俗称神龙窟倚坐弥勒佛像高3.6米。蜀道石窟造像与同时期龙门石窟相比,体量普遍较小(但造像数量并不算少)。这应与蜀道上建造石窟的官吏和信众流动性大,石窟开凿时间较短,能够支撑长时期持续开凿人力物力的供养人较少有关。
四、武则天时代蜀道石窟的雕凿技艺和美学价值独具风采
蜀道石窟寺的选址,大都是背山面水,背靠奇峻险峰,面前流水泛波,景色宜人。广元千佛崖、皇泽寺前就是嘉陵江,庄严肃穆的佛像与优美的自然风光相得益彰,形成一个自然与人文融合的佳构。这与龙门石窟面对洛河的支流伊河相似,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研价值。
武则天时代蜀道的石窟雕凿具有显著的美学价值。首先是广元千佛崖365号和366号双窟雕刻的镂空背屏雕刻,其中365号窟还为圆雕,镂空背屏雕刻立体感强,造像技艺高超,这在其他地方鲜有发现。最具代表性的广元千佛崖365号弥勒佛窟,佛坛上造像,主佛背后的头光及镂空菩提双树直通窟顶,且均为圆雕。此外雕像与背景组合丰富,集立体感、唯美感为一体,如广元千佛崖366号菩提瑞像窟,佛坛上凿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七尊像,主尊座后靠背直通窟顶,形成背屏,背屏两侧及上部为镂空双树;广元千佛崖746号窟,坛上凿出一铺13尊涅槃组像,坛后部二角各雕一棵娑罗树,树干直通窟顶。
这一时期蜀道石窟还出现佛帐形龛,尤其为巴中石窟独有特色。佛帐形龛内顶上多饰重檐,檐下悬帐、铃等物形成龛楣,帐柱即为两侧龛柱,多用忍冬纹、卷草纹、团花、宝珠等装饰,同时龛后壁用菩提双树装饰。这种组合繁琐复杂的装饰,给人视角冲击力特别强,精湛的雕刻水平凸显出立体感。
武则天时期蜀道石窟的兴盛与唐代佛教的发展方向同步。隋唐时期的巴蜀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俨然成为重要的佛教传播中心。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蜀中多寺院(如著名的玄宗所建大圣慈寺、僖宗所建宝光寺),仅唐代成都寺院有记载者就有43所之多。[15]蜀地高僧云集,如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玄奘在成都游学,武德五年在成都空慧寺受戒。玄宗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新罗王子(俗姓金,曰无相)入中国,止于禅定寺,后入蜀欲谒智诜禅师,玄宗幸蜀,迎无相至成都,“并创建净众、大慈等寺,对唐代蜀中佛教禅宗传播影响很大”[16]。咸通年间(公元860—873年),有天竺三藏经过成都,晓五天胡语,通大小乘经律论……隋唐时期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发展,亦促进巴蜀佛教的大发展。
有唐一代,佛教开窟造像遍及巴蜀。特别是从武則天到盛唐中唐时期,佛教的石窟开凿浪潮波及整个四川,成都蒲江石窟、邛崃石窟、大邑石窟、乐山大佛、巴中石窟、安岳石窟、夹江千佛崖石窟等争相形成。不过,武则天时代的蜀地石窟,除广元石窟外,其他大多还处于发展初期,如乐山大佛的开凿,晚于武则天时代约半个世纪。所以广元乃是这一时期蜀地佛教石窟的中心。安史之乱后,随着玄宗、僖宗两代皇帝入蜀避难,石窟宗教艺术重心随之南移,偏安一隅的巴蜀地区为佛教艺术盛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使巴蜀石窟成为中国石窟最后的辉煌。这一时期的蜀道石窟雕刻艺术可以成为唐代艺术的实物标本。如巴中西龛53号龛有唐代雕刻的仿真楼阁2座,各高2米,镂空雕刻,是川渝地区难得的唐代建筑形象。广元石窟中的供养人如皇泽寺12号、13号窟,千佛崖供养人689号窟、153号窟以及千佛崖366号菩提瑞像窟胡人伎乐等遗存都是研究唐代服饰的重要史料。
佛教的重点传播区域,必须依靠发达的经济提供支撑。有唐一代,成都经济文化的发展一直处于上升势头。著名诗人陈子昂曾描述:“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17]。隋末唐初蜀地未经历大规模的战乱,经过长时间发展,到中晚唐时成都经济地位进一步上升,与扬州并称“扬一益二”。《元和郡县志》说:“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蜀地经济文化的繁荣,能够支撑大量寺院的建造与石窟的开凿。而蜀地的独特地域文化,也影响了蜀道石窟造像的风格,从而形成唐代蜀道石窟的独有特色。对这一特色的探索,可以對大蜀道文化的研究起到推动的作用。
注释:
[1](唐)杜佑:《通典》卷五十一:“昔武氏篡国十五余年,孝和挺剑龙飞,再兴唐祚。”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27页。
[2]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
[3]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提出:“综括言之,此一集团武曌创组于大帝之初,杨玉环结束于明皇之末者也。唐代自高宗至玄宗为文治武功极盛之世,即此集团居最高统治地位之时,安禄山乱起,李唐中央政府已失去统治全国之能力,而此集团之势力亦衰歇矣。故研究唐之盛世者不可不研究此集团,特为论述其组成及变迁之概略,以供治吾国中古史者之参考。”(《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4]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七十一《再修西龛佛阁记》,民国14年刻本。
[5][8][12]姚崇新:《巴蜀佛教石窟造像初步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3页,第121页,第299页。
[6]《唐会要》卷四十七《释教议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7]《梁思成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354页。
[9]参见张宁、雷玉华、王婷、李凯:《四川广元千佛崖莲花洞考古新发现》,《四川文物》2020年第6期。
[10]参见雷玉华、罗春晓、王剑平:《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235—245页。
[11]参见苟廷一:《唐巴州章怀太子墓考》,《四川文物》1988年第6期。
[13]参见于春、王婷:《绵阳龛窟——四川绵阳古代造像研究报告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205页。
[14]蒋晓春、雷玉华、聂和平:《嘉陵江流域石窟寺分期研究》,《考古学集刊》第22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15][16]谢元鲁:《成都通史·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8页,第286页。
[17](唐)陈子昂:《谏雅州讨生羌书》,《全唐文》卷二百一十二,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嘉庆本,第2149页。
作者:广元市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