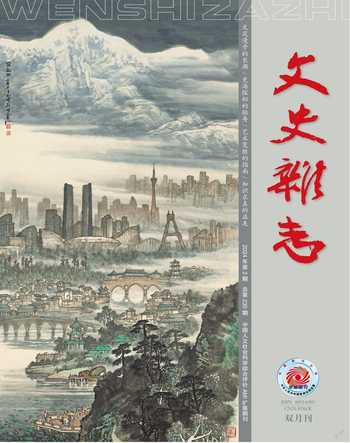李商隐《碧城三首》新诠
宋荻
摘 要:李商隐《碧城三首》释义纷纭,各家解读“各有偏见,互持莫决”,各家之间还偶有“不可通”“未融洽”“援据支离”的相互指摘,诗歌的阅读诠解尤有隐晦不明之处。联系唐代仙道文化语境与诗人自己的生命经验,《碧城三首》所咏,当是诗人关于修习仙道的所感所思。此诗首章幻想仙界场景;次章写仙界神妙,令人神往;末章借汉武帝故事表达对于求修仙道的疑虑与困惑。三首主旨统一,情感流畅,逻辑自洽。从诗中情感与意识看,组诗可能作于诗人早年学仙玉阳期间。
关键词:《碧城三首》;神游仙境;好仙慕道;《汉武帝内传》
一
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
对影闻声已可怜,玉池荷叶正田田。不逢萧史休回首,莫见洪崖又拍肩。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鄂君怅望舟中夜,绣被焚香独自眠。
七夕来时先有期,洞房帘箔至今垂。玉轮顾兔初生魄,铁网珊瑚未有枝。检与神方教驻景,收将凤纸写相思。武皇内传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
千百年来,李商隐《碧城三首》释义纷纭,“莫定其解”[1]。这些解读所依循者大致三种径路:朱鹤龄、冯浩为代表的比兴寄托派,纪昀及梁启超所代表的不求甚解派和苏雪林所代表的索隐派。三者之中,不求甚解固非文学阅读审美可以满足的境界,索隐也因其邻于穿凿附会而难得学者首肯,[2]惟比兴寄托作为此诗诠释的主流路径成就最丰富。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所搜汇的如“志不得伸”(朱鹤龄)、“君门难近”(姚培谦)、“幕府失意”(徐德泓)、“青楼望郞”(胡以梅)等十数种诠释,[3]多在古典文学香草美人的隐喻传统中展开,不断地以超文本与再生文本的形式,丰富着诗歌的感性内容,开拓着诗歌的意蕴空间。但是另一方面,各家解诗或重于兴,或本于赋,“各有偏见,互持莫决”[4],始终为读者的诗歌阅读与审美体验带来困惑。这里以诸说中影响较广的朱彝尊、王士禛、钱良择“讽明皇太真”与胡震亨“刺贵主为女冠”二说为例。对朱、王、钱的“刺李杨”说,不仅张宗柟表示对第三章“尚不能无疑”[5],冯浩也说“首章总不可通”,其余“亦未融洽”。而胡震亨的“刺贵主为女冠”说也遭到纪昀“既无本事,难以确主第”、只是“各就所见领略”的批评。此外,纪氏还批评众人解诗大都“援据支离,于诗无当”[6],因此他自己剥落种种猜测臆想与过度诠释,而回头主张不求甚解说,承认《碧城三首》为“所寓之意”“不甚可知”的“寓言”(这一主张后为梁启超所继承)。
上述诸说之外,也有人摒弃比兴寄托,单从诗歌语汇、境象、事典出发而主张“游仙”之说,如黄周星“非仙境安得有此”[7],陆鸣皋“(《碧城》)三首泛作游仙”[8]。惜二氏立论之余,皆无更进一步阐说。文学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外化,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关。联系诗歌文本中与神仙世界相关的语汇,结合晚唐仙道文化语境与诗人早年修习仙道的真切生命体验,二氏将三首主旨归于“游仙”的说法颇有意义。根据诗人自述,他早年曾“学仙玉阳东”(《李肱所遗画松诗两纸得四十一韵》)、“习业南山阿”(《安平公诗》),经年修习仙道之学。晚唐诗人之中,李商隐的道教文化修养最为深厚,因此元代茅山道士文人张雨称美他说“消得羊权火浣布,诗中唯數玉溪生”(张雨《李商隐学仙》)。李商隐诗歌中不仅表白自己一度“心悬紫云阁,梦断赤城标”(《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对于道教神仙世界有过真诚的向往,而且还记录自己“戏掷万里火,聊召六甲旬”(《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二十韵》)的入静实修体验。在唐代仙道文化环境与诗人生命经历的整体视野中考察,李商隐《碧城三首》极可能是他早年关于仙道信仰、情感与认知的组诗书写。
二
此诗首章首联“十二阑干”“辟尘”“辟寒”诸语,摹写“碧城”的宫观规模与整体氛围。“碧城”,朱鹤龄引《太平御览》“元始天尊居紫云之阙,碧霞为城”之说,[9]以为元始天尊所居。依《元始上真众仙记》,元始天尊所居,“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10]。唐人诗中,“天上白玉京,五城十二楼”(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玉京十二楼,峨峨倚青翠”(孟郊《长安旅情》),“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李商隐《无题》),“十二(阑干)”不仅是玉京规模的传统语汇,也泛写神仙居所。又《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载,玉京山“在三清之上,无色无尘”[11]。三清之上的大罗天,是道教“三十六天”最高天界,这里不染尘俗,使人联想起博物神话中“其角辟尘,置之于座,尘埃不入”的海兽“却尘犀”;[12]而凡人想象中最高天上的玉京山恐怕要“高处不胜寒”,需以玉辟之方能“温润而泽”。颔联“书附鹤”“树鸾栖”,是对仙界虚拟境象的呈现。“阆苑”,传说为西王母所居,此处有玉楼十二;“女床”,是《山海经》所载的殊方之山,此山有鸟“状如翟而五彩文,名曰鸾鸟”[13]。仙道文学的异世间叙事,不惟景观与人间不同,时空结构方式也相迥异。在这里,仙人以鹤传书,鸾凤为驾,是精神逍遥自虞的重要外在表征。但是,“山兄望鹤信”(李洞《赠王凤二山人》),“鹤探丹丘信”(褚载《赠通士》),鹤信并非总是情书。“鸾音鹤信杳难回,凤驾龙车早晚来”(罗隐《淮南高骈所造迎仙楼》),仙人凌虚蹈空,乘龙跨凤,闲弛时鸾栖于树,这也是仙境叙事对情境细节的合理想象。前人对此二句的种种解说,在“书凭鹤附,树许鸾栖,密约幽期,情状已揭”(冯浩)[14]、“鹤书皆得上达,鸾鸟皆得栖止,无不弹冠相庆,如增州县官三百八十三员之类是也”(姜炳璋)[15]之类隐曲迂远或拘狭泥实的索解之外,陆昆曾“仙境自然无尘埃,无寒暑。而鸾鹤往来,非人间世之所得同”[16]的解说算得上明白晓畅。
首章颈、尾两联“星沉海底”“雨过河源”“晓珠”“水晶盘”等语汇,进一步写想象的天上景观。上古宇宙神话叙事中,羲和浴日,常羲浴月,日月星辰皆住于海,故魏武观沧海而生日月“若出其中”,星汉“若出其里”的感慨(《观沧海》)。两汉以后的文学想象,在“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案:浑天说)[17]等天文学认知的支撑下发展出天上人间混一的世界作为仙话叙事的空间结构。张华《博物志》的“八月槎”在“天河与海通”的天地结构中讲述了海渚之人乘浮槎访天河牛女的仙话。[18]到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这个仙话进一步演绎出张骞“寻河源”登天河而得“天上织女支机石”的故事。[19]天河不仅与海相通,还与(黄)河源相通。唐人赵璘批评前辈诗人用典“张骞槎”者“相袭谬误”之“不足据”[20],正说明“天河与河源通”已然成为唐人共享的普遍空间意识。李太白诗“黄河之水天上来”中浪漫瑰丽的文学想象,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唐人空间意识的自觉流露。李商隐此诗写“星沉海底”“雨过河源”的天上景观,并未超出这一空间意识的框架,只是观察视点的转换,导致“当窗见”“隔座看”这一景象的奇特呈现方式。视点是叙事者发现、记录与叙述场景的眼晴,视点的位置同时是场景叙述的立场。随着观察者视点向最高天界的提升,“星沉海底”“雨过河源”这些在地上为凡人目力所不能及的宏大景观遂成为当窗可看、隔座可见的平常景象。“晓珠”“水晶盘”是想象在天上所见的日月。道家谓“日为流珠”,如“西摩月镜,东弄日珠”(皇甫湜《出世篇》),是文学修辞与教义譬喻的结合。在虚构的现实中,从最高天界看,太阳就像一粒“明又定”的宝珠,而月亮晶莹通透像一个水晶盘。末二句的仙境想象叙事在视点上保持了与全诗的整体统一性。
三
次章写存思所现仙境神妙,油然神往而生修仙之志。“存思”(或谓“存神”“存想”)是道家(尤其是李商隐所修上清派)流行于六朝唐宋间的静功修持技术。《真诰》:“存五神于体……则去仙近”[21],存即“存思”。存思的方法,如礼太微天帝君:“存己身如在太微天帝玉阙下”,礼太上玉晨道君:“存己身如在太上玉晨道君玉阙下”(《登真隐诀》)[22],入山却邪:“闭眼思五色之云奄冠一山,及我身在云气之中,良久,见五岳仙官及山形林中,草木禽兽万物悉来朝己……”(《上清修身要事经·玉清消魔道士游行山泽祝法三十》)[23],其中包含着极力设想身临其境的想象力思维训练因素。存思过程中,除了存想神灵境象(“对影”)之外,有时常常伴随特定的声音元素(“闻声”),如存白元君:“呼玉房神名,呼之耳象闻如人应声,或有诵经音,则其应”(《太上洞房内经注》)[24]。对于熟谙上清存思技术的李商隐,我们有理由相信,此诗首句所言“对影闻声”,即使不是对于某次存思静修的记录,仅是作为一种文学想象,也与存思活动紧密相关。下文中的仙境美景(玉池荷叶正田田)、仙人活动(“萧史”“洪崖”)以及乐舞场景(“紫凤放娇”“赤鳞狂舞”),都通过这种与存思活动有关的想象呈现出来。
颔联“萧史”“洪崖”二句,在二位仙人之间结构出一种明显的选择关系,历来为解诗者聚讼。根据胡以梅的说法,此二句“言止可与郎依恋,切勿更与他人相亲,妨猜而丁宁,痴情之毕露”,陆昆曾则认为这两句是说“(明皇太真)神人道殊,未明促别,岂复能回首拍肩,时时相遇”,而姚培谦又将二句释读为“若使逢萧史而回首,遇洪涯而又拍肩,则专一之志荒”[25],分岔衍义,不一而足,正所谓“各就所见领略”。考“萧史”“洪崖”为唐诗熟典,但此联选择语境设置了一个对二仙差别进行索解的问题,需要联系六朝以来的道教神仙品级观念来解决。东晋之时,葛洪提出了神仙三品之说,谓“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26],初步建立了道教神仙等级体系。到唐五代,神仙之中,“冲天者为优,尸解者为劣”[27],尸解仙“是仙品之下第”,“应得尸解之仙者,或禀受使然,或志行替败,或学寻浅狭,情向颓住”[28],早已成为修仙道者的普遍认知。萧史“善吹箫……日教弄玉作凤鸣……一旦,皆随凤凰飞去”[29],是白日“举形升虚”的神仙之上者。洪崖“吞琅玕之华而方营丘墓(其墓在武威姑臧)”[30],他死后受《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镇墓,“百廿年墓开,尸形飞腾”[31],是典型的尸解仙。在道家神仙等级体系的文化语境中,二仙的不同品级必然代表不同的两种修仙技术途径。诗中“不逢萧史休回首,莫见洪崖又拍肩”二句,表达了立志择修上仙的决心与有志修成上仙的信念。后“紫凤”“赤鳞”一联,状存思所见之热闹非凡的仙境乐舞场景。“紫凤放娇”“赤鳞狂舞”,既是对湘灵鼓瑟之音乐效果的渲染,也是仙境乐舞合一的场景呈现。其中“赤鳞”句,不光如杜诏、杜庭珠所说“暗用瓠巴鼓瑟,游鱼出听语”[32],同时赤鳞者,赤鲤也,也是对干宝《搜神记》琴高能鼓琴、后成仙乘赤鲤鱼出这一仙传事典的变形运用。唐诗中以虚构增补的“赤鲤听琴”来烘托音乐效果的写法,时亦已成为常典,如顾况之用“两声赤鲤露鬐鬣”(《郑女弹筝歌》)来写郑女琴艺的高超。
尾联“鄂君”云云,典出刘向《说苑·善说》。楚国襄成君始封日,立于流水之上,楚大夫庄辛希望能“把君之手”以“渡王”,却引起襄成君的不悦。于是庄辛向襄成君講述了鄂君子皙的故事:一日,鄂君子皙“乘青翰之舟”,“泛舟于新波之中”,音乐结束的时候,一位榜枻越人“拥楫而歌”,为他献唱“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的越人歌,鄂君大受感动,“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与榜枻越人“交欢尽意”。听完故事,襄成君“奉手而进”,向庄辛表示“愿以壮少之礼谨受命”[33]。对于这一句的诸种诠读,或谓诗以“鄂君”之典“极写其放荡”(程梦星)[34],或称鄂君“独自眠”为“尚有欲亲而未得者”之“怅望”(冯浩)及“今之凄凉”(屈复)[35]的托喻,大多着眼于鄂君“绣被”这一语言符号的色情属性。在刘向《说苑·善说》鄂君叙事的整体话语中,鄂君是“亲楚王母弟”,又“官为令尹,爵为执珪”,他的个人魅力还为他赢得世人的慕恋,因此是一个典型的世间成就者形象。而鄂君对榜枻越人“拥之”“绣被覆之”的举动,实在是他满足于这种令人艳羡的人间福份而拥抱并享乐于现世生活的象喻。诗中在仙界境象整体呈现之后,再写及鄂君中夜怅望而焚香独眠——对“鄂君”一典如此反其意而用之,盖欲表达仙境美景、活动、乐舞等的整体场景感染力之大,使得曾经如此满足于现世享乐的鄂君也觉歉然,不由生求仙慕道之情,何况是他人呢?
四
第三章全诗用《汉武帝内传》典,包含诗人对于修习仙道的复杂情感与认知。《汉武帝内传》载,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四月戊辰,武帝闲居承华殿,王母侍女王子登来与武帝约定:“从今百日清斋,不闲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暂来”,武帝于是“登延灵之台,盛斋存道,其四方之事权委于冢宰”,清斋百日,至七月七日,武帝又“修除宫掖之内,设座殿上,以紫罗荐地,墦百和之香,张云锦之帐”,燃灯,设枣,酌酒,盛服“以俟云驾”,二更后,王母果至。王母向武帝传授了长生之术与《五岳真形图》等,上元夫人(召青童小君)授武帝“五帝六甲左右灵飞”等十二事。王母及上元夫人去后,武帝不能从诫,于是仙真遂不复来,武帝求仙不得。[36]此诗首联“七夕来时”“洞房帘箔”两句,述王母下降之前先遣侍女与武帝有清斋百日之约,以及汉武帝七月七日为王母下降修除张设等盛礼。颔联“玉轮顾兔初生魄,铁网珊瑚未有枝”,述七月七日王母降真,但武帝“实非仙才”,因终未能修成正果。句中“玉轮”“顾兔”“月魄”,皆为写月之语。严格说,三词本有差别,“玉轮”为满月,如“素娥睡起,玉轮稳驾”(卢炳《水龙吟·赓韵中秋》)的中秋月;而“月魄”,据“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37]之说,当是农历十六之后渐亏之月。但是唐人作诗,多数不拘细义。李商隐诗,以“常娥照玉轮”(《七夕偶题》)写七夕新月,“顾兔飞难定”(《赋得月照冰池》)写“似镜”的“皓月”,“扇裁月魄”写团团圆月(《无题·凤尾香罗薄几重》),语用亦不囿于特定的月象。此句即以“初生(魄)”一词,指义王母七夕降真时的上弦新月。《海中经》载:“取珊瑚,先作铁网沉水底,珊瑚贯中而生……因绞网出之,皆摧折在网中,故难得完好者。”[38]以铁网采集珊瑚,常摧折而无获,合为“铁网珊瑚未有枝”之谓。《汉武帝内传》说,初,王母以武帝寻道精勤,“有似可教者”,因而见降,可惜武帝“形慢神秽”,“每事不从王母之深言,上元夫人之妙诫”,因此王母“遂不复来”,武帝求仙无果,直若以铁网采集珊瑚而未有所获。下句“检与神方教驻景”,述王母始降,为武帝讲说养性之道,向传授可以“后天而老”的“太上所服”、可以“后天而逝”的“天帝所服”、可以“白日升天”的“飞仙所服”,以及可以延年益寿“得为地仙”的“下药”各种仙方,并“敕侍笈玉女李庆孙书出,以相付”一事。武帝“收将凤纸写相思”,述王母与上元夫人去后,武帝将二仙所教延年之诀、致灵之法、乘虚之数、步玄之术等诸要妙辞,撰为一卷,与二仙所传真形经书、六甲飞灵之事等“盛以黄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安着桐梁台上”,以为“神真见降,必当度世”的见证,以安慰自己的慕仙之情。“凤纸”,为道家青词用纸,帝王亦用之。行文至此,末句“武皇内传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总言众仙真降会武帝一事,已见录于书,历历可见,此事人间应知。但《汉武帝内传》的仙传故事,究竟要传递怎样的信息,是寻道精勤终将感会仙真下降?抑或若非仙才终不能修道成功?终究迷离含糊,总不真切。但是,联系全诗整体话语氛围,此句或似劝谕人们若肯勤修仙道,则能感至真仙降会,或表达自己对于如何修道成仙的疑虑与困惑,而总不似全为讥讽武帝求仙之虚妄而说。
《碧城三首》为总写诗人对于修习仙道所感所思的组诗。三首之中,首章幻想仙界场景;次章写仙界神妙,让人神往;末章借汉武帝故事表达自己对于修习仙道的反思、疑虑与困惑。如此一来,不仅对于语汇与诗义皆无需借由更多的臆测与想象来深曲索解,而且三首之间主旨统一,情感流畅,逻辑自洽。以此为基础,把握诗中自然流露的情感与意识形态,又可进而推知此诗当大约作于诗人早年学仙玉阳前后。对比李商隐后期诗歌创作中神话场景表现的系统意象运用,诸如“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谒山》)、“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无题》)、“兔寒蟾冷桂花白”(《月夕》)等,都偏向择用寒色系的语汇营造无温度的孤冷氛围。[39]惟此诗“犀辟尘埃玉辟寒”一句构设的天宫仙界,洁净而不失温润,一反诗人情感常态,其中蕴含的对于天上仙界的真诚向往之情,大概率只能发生在诗人早年学仙期间。此外,本诗末章借汉武帝故事所传达出来的对于学仙的疑虑困惑之情,或许与不久之后李商隐弃道学儒的人生选择相关。李商隐后来频频感伤于自己“我本玄元胄,禀华由上津。中迷鬼道乐,沈为下土民”(《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二十韵》)的歧路厄途,又一再称说自己“上清沦谪得归迟”(《重过圣女祠》)、“沦谪千年别帝宸”(《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的“沦谪”之恨。倘若他当初的弃道学儒真有理由,此诗所传达出来的疑虑与困惑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一个。李商隐弃道学儒固然可以为出仕或为“稻粱谋”计,但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开设了以道家学说课试取士的“道举”科,到晚唐一直沿袭,所以李商隐早年的学道并非仅是出世之选。当然,这已经是另一个问题。
注释:
[1][4](清)冯浩笺注,蒋凡标点《玉谿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73页,第136页。
[2]蒋寅:《李商隐〈无题〉与中国诗歌诠释传统》,《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3][6][7][9][12][13][14][15][25][32][34][35][37]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2004年重印版,第1850—1864页,第1862页,第1856页,第1848页,第1848页,第1849页,第1860页,第1861页,第1853—1857页,第1850页,第1859页,第1860页、1858页,第1851页。
[5][8]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编《李商隐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6年重印版,第352—353页,第466—467页。
[10]《道藏》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页。
[11]《道藏》第3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625页。
[16](清)陆昆曾:《李义山诗解》,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51—52页。
[17](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上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18](晋)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2014年重印),第111页。
[19](南朝梁)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
[20](唐)赵璘撰,黎泽潮校笺《〈因话录〉校笺》,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21][30]〔日〕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朱越利译《真诰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页,第459页。
[22][23][24]《中华道藏》第2册,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267页,第378—379页,第84—86页。
[26]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页。
[27](唐)杜光庭:《墉城集仙录叙》,(宋)张君房:《云笈七签》,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526页。
[28]周作明點校《无上秘要》,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064、1067页。
[29]王叔岷:《〈列仙传〉校笺》,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0页。
[31]李德范辑《敦煌道藏》第2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版,第1055页。
[33](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7—279页。
[36]《道藏》第5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47—57页。《汉武帝内传》记王母、上元夫人下降于武帝的时间,前后有元封元年、元封二年两种不同说法。
[38](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卷四,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82年版,第116页。
[39]欧丽娟:《李商隐诗歌》,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03页。
作者:哲学博士,西藏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