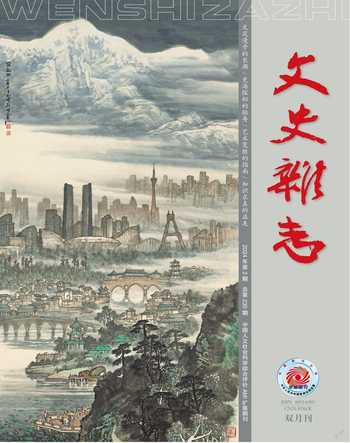司马迁的“蒙太奇”
张昊苏 陈熹
摘 要:《史记·刺客列传》描写“荆轲刺秦王”一段,具有丰富的动作细节,犹如电影的“分镜剧本”,给人极强的画面感,可以视为文言写作的“蒙太奇”。司马迁如果生在当代,当是善于营造镜头场面的电影大师。
关键词:《刺客列传》;动作信息;长镜头;原始面貌
在162分钟的电影大作《荆轲刺秦王》(1998年陈凯歌导演作品)中,陈凯歌以9分半的长度表现荆轲在秦庭的刺杀经过——这也许可以代表多数人的认知:“刺杀”本身固然是《刺客列传》“荆轲传”的高潮,但因为太过耳熟能详,反而可以用简省的方式来讲述。于是,司马迁在文本原作描写这一段时所运用的文章笔法,就容易在一般阅读时被忽略。
让我们重返《史记·刺客列传》那刺杀高潮时刻的现场:
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
这一段描写千百年来为世所称道,今天重读,仍然有如在目前的“即视感”。在司马迁细致而富于节奏的笔调之下,我们仍能明白地理解彼时的来龙去脉,感受到一时的紧张刺激。《史记》的善于“讲故事”为人所熟知,然而在流传两千年的文字背后,我们需要更细致地考察,它“生动”的秘密何在?
我们今天所谓“描写”,本来就是指用语言指引读者还原事件,是文学写作的基本手段。《史记》的时代并没有摄录机,这些生动描写当然多少有赖于历史叙述者的主观想象。从这个角度推想早期著作中“文”“史”之边界,追究细节描写是否有确据可能未必重要(也缺乏操作性),关键是理解特定描写令人想来逼“真”的原理。
重读荆轲刺秦王的描写,一个鲜明的特色是连续的细碎的动作。“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这一连串的描写,都是连贯细致的动作。《史记》前的中国史书虽然有丰富的叙事实践,但《史记》似乎对叙事中的动作有更深入的理解。
不妨粗略借用哲学分析中讨论人的动作的框架來观察《史记》叙事。围绕一个动作事件有很多因素:有施行动作之人,有动作的意向,有具体动作,有动作效果,还有动作的因果。《史记》前的传统史书记事,在关注语言对话之外,主要给出事件中动作的效果,关注人物在事件中的作用。而《史记》区别于传统史传之处,正是提供了更丰富的动作信息。且看《刺客列传》接下来一段——
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不中,中铜柱。
如果只从效果事件出发,那么这几句的描述重点应该是“秦王负剑”和“荆轲掷秦王不中”两个结果,不影响事件结果的信息如第二个“负剑”可以删去。但在司马迁的笔下,整个事件中动作信息异常丰富完整:左右发出提醒的声音后,我们看到了击杀荆轲中间的重要一步,“负剑”(动作);而秦王做出负剑动作的因由,是因为有左右提醒(因果)。荆轲向秦王投出匕首(动作),马上给出“不中”的效果,以及“中铜柱”的余响。正是通过提供这些看似细碎但丰富连贯的动作要素,司马迁仿佛直接为读者提供了一份“分镜剧本”,予人极强的画面感,也是后世“叙事文学”多从《史记》借鉴的重要原因。
《史记》的动作特色还可以在其他篇目中发现。以有名的《李将军列传》中李广出猎一段为例(括号中字是笔者所标示的动作要素,下同):“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意向)而射之(动作),中石没镞(效果),视之(动作),石也。”若纯就笔法简省这一角度看,“视之,石也”甚至“以为虎”都可以删去,因“见草中石,射之”已经将整个故事的结局呈现出来了。围绕事件提供丰富完整的动作要素,这正是司马迁叙事的高明。读者借由完整的动作要素还原情景,由此得到生动的体验。
我们不妨拿出和《史记》所叙内容有重叠的两部书——《左传》和《汉书》,作为参照。《左传·桓公十八年》记载鲁庄公在齐国被彭生杀害于车上,直接写事件的结果:“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效果)”。根据同样的材料,《史记·齐世家》则给出了更多的动作细节:“使力士彭生抱上(动作)鲁君车,因拉杀(动作—结果)鲁桓公。”《鲁世家》则用互见笔法写成:“因命彭公折其胁,公死于车”,这里的差异正是《史记》的特色。《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记有李广行军战阵的场面,司马迁写道:“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汉书》则写成:“广令曰:‘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仅从此句看,班固的处理方式当然更加雅洁,且未损失任何核心信息,但读者却更容易从《史记》的描写体验到事件中的情景——仅仅一字之差,语言之“前”与动作之“前”的动作就如在目前。
明代茅坤《汉书评林序》中对《史记》有一段精彩的评价。他说《史记》的描写:“指次古今,出入《风》《骚》,譬之韩、白提兵而战河山之间,当其壁垒、部曲,施旗怔鼓,左提右挈,中权后劲,起伏翱翔,倏忽变化,若一夫舞剑于曲旃之上,而无不如意者,西京以来,千古绝调也。”这确实是千百年来读者对《史记》的阅读体验,其中的“动作”正是奥秘所在。在此之外,如果说传统史传叙事关注事件的结果,使人明白地看清历史现场的意义,《史记》对动作的还原,则是将历史事件根植于日常经验之中,关注于事件中的人身上。
正如叙事电影和纪录片不同,不以再现线性时间下的动作为目的,《史记》也不是单纯地再现动作要素,而以更高超的手段调节动作进程的展示。这里不妨细玩《史记》荆轲刺秦王那段(见前引)的文意:荆轲左手把袖、右手持刃——司马迁行文的语气相对舒缓;而“未至身”以下连续的二三字断句却节奏极快极密,富有跌宕起伏之美。这种疾、徐的对比间,荆轲的刺杀似乎给人以慢动作的感觉,秦王的一系列躲闪却是反应迅捷。这一段中更有镜头景别的变化。如果用电影的分镜语言来诠释,先是近景特写荆轲与秦王的近身动作,凸显紧张的快速切换;忽然拉远呈现殿中人群像的远景镜头,乃至“而秦法”一句,又将画面切换到殿下。司马迁在不知不觉中引导着读者想象这一事件的情境,让读者感知的并非荆轲与秦王的实际搏斗时间(或曰故事时间),而是《史记》为这一段搏杀提供的叙述时间。最激烈的打斗在一瞬间交换了大量动作,随后则进入到秦王占据主动、重创荆轲,又异常简练,一瞬之间“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
再往前回溯,在荆轲怒叱太子丹,不待“客”到而入秦一段,司马迁给世人留下一段记忆永恒的送别: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伉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短长句式的交错,变徵、羽声两种音乐更替对送行者(或曰“观众”)情绪的直接冲击,以及“就车而去,终已不顾”的告一段落,这一连串动作事件不间断地涌来,可以称之为是一组古文中的“长镜头”。在这样的展示之下,司马迁给读者留下了绵长的“叙事时间”,带来异乎寻常的艺术震撼。
电影剪辑中的蒙太奇(Montage)手法,宽泛而言,指的是不同镜头重新组合可以生成新的含义,常常以视觉形象的象征性代替事件自身的因果邏辑,这也是电影从机械记录变为艺术创造的重要技术依凭。这类表现手法在文章写作中则更易实现。按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的讲法,《史记》属于文人之史;“《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传统批评中的“事为文料”,也许可以看作是文言写作的蒙太奇——仅从技巧本身来说,文章家的剪裁与当代的影视剪辑颇为同调。
在所有动作、时间、景别、蒙太奇之外,必须认识到,我们在司马迁笔下事件中读到的生动,离不开《史记》本身的史学框架。《史记》中几乎出现在每篇结尾的“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相当有标志性的个人书写,有些细节看似闲笔,却有相当深刻的史学属性。《刺客列传》最后的“太史公曰”探讨了荆轲故事的史源——“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曾亲用药囊击打荆轲的夏无且,将这段故事讲给了公孙季功(弘,公元前200—前121)与董子(仲舒,前179—前104),随后又传递到太史公(司马迁,约前145—?)处,使这段记载区别于“世言”(大抵是《燕丹子》同类的小说家言)。从别人那听来故事,这似乎符合本雅明所谓讲故事的传统之一,即远方来人讲述传奇;然而不同的是,《史记》总是通过“太史公曰”以严谨的态度检视这些传奇的源流和可信程度,这就脱离开生动的“故事”,而回到严肃的“史学”。比如,在记叙战国四公子跌宕起伏的传奇之后,太史公谈起他的追索:“吾尝过薛”(《孟尝君列传》),“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魏公子列传》),“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春申君列传》),甚至是援引理论的批评:“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太史公曰”算是一段结尾旁白,也可说是每段故事后“史学”的压轴登场,把传奇拉回到历史书写的框架中。后来的历史学家,以及试图用“实”饰“虚”的小说家,都深深受益于这一框架。
在荆轲刺秦王这一故事的尾声中,假如把《史记》原文里比较中立的“秦王不怡者良久”,改换为《战国策》中的异文“秦王目眩良久”,则其文学性愈发地显豁起来:故事业已讲完,只有一段秦王头昏目眩的空镜。考虑到今存《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一段大概率是依托《史记·刺客列传》而加以删削的文本,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假如没有“史”之客观性的限制,司马迁完全有能力写出更富有传奇性的故事。区别于记载了更多道听途说传闻,但仍兼具杂传文体特征的《燕丹子》,《史记》的笔墨显然远胜之。文章可读性的高低,并不必然地与所记录事件是否“传奇”挂钩;严肃地表明史学的谨慎立场,反而能给传奇以现实参照,更增大传奇的震撼力。
当然,面对古代文本展开细致解读,可能时常要面对是否“原本”的问题。考虑到今本《史记》的文字远少于司马迁自称的“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则或许今本《史记》已被钞者作了大量删削,而原本《史记》的繁复程度可能远超今本。从今本中的长篇文章本身所呈现的效果来看,《史记》的风神是相当鲜明而特出的,且正存在于易为忽略的“闲言碎语”之中。《史记》的原始面貌或许展示了更为生动复杂的历史场面。
最后,我们不妨下一带有文学色彩的总结评论——对于太史公,人周知其乃“史家之绝唱”,是“小说之教父”;同时也应该相信,他如果生在当代,必然也是熟谙口头文学技艺的评书家,是善于营造镜头场面的电影大师。前人批评太史公之好奇,其“奇”不在于“增益怪诞”,而在于叙事引人入胜,所谓“于起灭转接之间,觉有不可测识处,便是奇气”(刘大櫆《论文偶得》)。这些表现技巧至今仍然具有艺术教科书的意义。
作者 张昊苏:南开大学文学院教师
陈 熹: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后
——以《山河故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