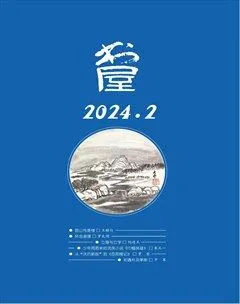少年周恩来的武侠小说《巾帼英雄》
朱天一
一
很少有人知道少年周恩来还曾写过武侠小说。当时周恩来在天津读中学,师从韩慕侠等武术名家习武,组织“敬业乐群会”锻炼体魄,同时也想借小说移风易俗,改造社会。1914年10月和1915年4月,周恩来以飞飞为笔名在《敬业》杂志第一、二期上发表了《巾帼英雄》。今天只能看到前两期的连载版本,该刊第三期已佚,亦无法考证是否写完。目前能看到的版本虽是一篇插叙、倒叙相结合的短篇小说,但主角明确,故事线清晰,主线“远行”的叙述铺垫似为长篇做准备,很像是晚清长篇侠义、公案小说的开篇。以女侠、书生与老仆三人在外的行程为线索,似为后续章节做准备,而此行沿途艰险,多匪寇威迫。少年书生每每“如堕愁海中”“趑趄不前”;老仆则每每夸下海口,内心实怯;只有青衣侠女面对艰险面不改色,一路保护书生。用周恩来自己的话来说,他写了一个“书生无胆,少女多能”的故事。
中间还插叙了女主人公洪飞影疾恶如仇,劫狱救走张氏翁媪的故事,有古大侠风,最后交代青衣侠女即是保护书生前行的洪飞影,用以补充关于侠女的性格、事迹方面的叙述。故事中出现的男性角色如书生、老仆、县令、张翁、梁生等皆寡力而胆薄,或缺少自我保护的能力,或本身就是恶人。在颠倒性别地位的表达中,唯有洪飛影堪称“英雄”,如此“阴盛阳衰”的情节架构既是当时侠义、公案小说的流行写法,也反映出周恩来对中国当时承担社会重要职能的男性精神力量、人格气禀的不满。
周恩来写武侠小说并不是突发奇想,其背后有着很扎实的文化准备,中学时代的他酷爱读《史记》,尤其是《游侠列传》《刺客列传》。1914年冬季,在作为作文习作的《拟刘厚传》中,周恩来又通过同学一家为侠士所救展现刚猛好义的精神追求,而只在结尾提到一位名为“冯极”的侠士,与其说是写人,不如说是对这种精神表达崇慕之情。此文并未写完,也只留下一个关于武侠世界的充满悬念的肇启。
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巾帼英雄》所写本事,及本事背后反映的写作观念问题。洪飞影“一身青衣”的装扮,让人想起后来鲁迅《铸剑》中的眉间尺和金庸《越女剑》中的阿青。而向前追溯亦有发现,先秦两汉至魏晋之史传和文人笔记中也有侠女形象,且多隐踪吴越之间,如《吴越春秋》中记叙了“越女试剑”以及干宝的《搜神记》、陶潜的《搜神后记》等书中都有涉及女侠客形象。此外唐人小说中的红拂女、聂隐娘,明代凌濛初《拍案惊奇》中的韦十一娘,王世贞《剑侠传》中的越女等,类似形象不胜枚举。侠女的文学形象为中国文学所独有,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上有典型意义。而周恩来的小说具体本自哪部小说,则须结合文本来判断:
首先我们可以结合文本做一些推断:周恩来在原文中写道,青儿(洪飞影)出自淮阴拳师之家,而当地“俗尚强悍”,其家保镖于齐鲁至淮阴一路。周恩来幼时在淮阴家乡热衷于听长辈讲“奇闻怪事”,经常绕膝不去,在《射阳忆旧》中即写道“淮郡人民,素称强悍”。周恩来曾见过公差绑缚的杀人越货的强盗悔悟的场景,也见过本地百姓群情激奋的画面,这些生活经验都成为他写小说的重要现实促因。而彼妇女“声震齐鲁间”,让人想起《水浒传》中的一丈青。“一丈青”最初本为齐鲁间武人家女子的通名,并非专作扈三娘绰号,亦是这一文学形象的来源之一。缺名笔记载“女而为盗者,障其面目”,相谓曰“一障青”。著名学者李拓之先生在《水浒绰号解》中指出,所谓“一丈青”,为旧时奇女子在“齐鲁一带草泽通名”。故洪飞影的形象或也本自对往昔话本小说口口相传的“奇女子”的一般想象。除上述侠女形象的远宗之外,《巾帼英雄》或近宗当时影响力巨大的鉴湖女侠秋瑾的形象,小说中与诬告者同谋的腐朽政府与民间侠士的矛盾激化,实际上也是晚清革命和旧有司法机制崩溃的象征。
第二个推断:纵观以往旧小说,参而考之,周恩来这个故事的底本或脱胎自清代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同是侠女牢狱救人,故事同样发生在淮阴,同样是书生“末路穷途幸逢侠女”的主线。文康写十三妹搭救书生安骥,二人后来喜结连理,侠女放下以往的行侠仗义,变得温柔体贴,辅助书生考取功名。周恩来似乎对这个结局颇为不满,连载两期的叙述都丝毫未写到少女与书生的感情线,反而破天荒地以隐含作者口吻加上了一句冷峻的批语“胭脂虎又岂甘雌伏哉”。另一个反传统小说书生侠女爱情模式的线索是洪飞影形象的高度男性化:其打扮的色调为“青”,青色在旧时的布艺染烫中泛指黑色,洪飞影从小“天生丽质”,却“不束足”“不曳裙”而好“作男子装”。作者还插了一句很重要的批语:“吾华俗尚早婚,闻之必当咄咄,至在欧西,则无足怪矣。”侠女之怪,是在一定的文化体系内,性别表现的颠倒,在当时为怪,而放诸现代文明话语体系中,则无足怪也。
这也从根本上否定了旧武侠小说侠义加爱情的模式,故周恩来自言其构设的“光怪陆离”,都在二人关系的微妙上,又言明二人既非兄妹,亦非夫妇,仅仅是搭救与被搭救、解放与被解放的关系。故书生因无胆而配不上多能之侠女,隐含着对民国初期社会转型中男权话语的批判,呼吁的是男性的自强,更反思以往旧小说中文人基于对女性的美好想象,毫不自愧地以个人期待去规训女性。这也体现出少年周恩来对传统文化的反叛精神。
二
1914年春季,周恩来邀友人游山海关的经历是其创作的重要动机,他在与友人的信中曾抒发自己想要“观察燕赵之习俗,复有昔日所谓慨感悲歌之士者乎”的打算,而本校同学“多束装归里”,信中隐含着无人与共的孤独情绪。
待游览古代燕赵之地后,周恩来曾写过《春日偶成》二首,其一有“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的句子,前句用典为《史记》中的“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后句的“博浪”则是张良曾荐力士行刺秦始皇的地方,充满了豪放壮阔的侠客精神。而第二首则极为婉约,句曰“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抒情主体更具女性气质,以女性视角等待“相思”中年年不见之人,亦是对自己此时挚友难觅的遗憾。其对“侠”精神的追求,与对女性抒情主体的设置也是并行的,故《巾帼英雄》里女侠要伴书生远行,对侠精神的追索,也要超脱于周遭人际现实的桎梏外进行。
同年,周恩来还写了一篇《春郊旅行记》,斯文除对良辰美景的玩赏之外,更时刻提醒侪辈“国步之艰难”,对当时北洋政府“奔走于权门”的官员颇有针砭之意,认为彼等尚不如“乡堡之农夫村女自食其力”,自己立志为“学者出以济世之才,以槃国家于累石之安”。这个不寻常的春天也成为周恩来自我革命的开始。次年春假,周恩来又约友人同行,并指出欲“砥柱中流自任”而不能“仅限于课本中”,自我锻炼的根本途径是追溯以往民间侠士的可贵品格:“齐鲁义丐,洙泗遗风,燕赵屠狗,秦晋旧俗,皆吾人所当顾问及之。”这种对地方彪悍民风、古侠士气禀的追溯成为少年周恩来自我锻炼的根本方式,也为自己的武侠小说写作提供了重要的肇发条件。
在燕赵、齐鲁等古代侠客之乡寻根,周恩来所寻找的是一种富有力量、自我锻炼同时改造社会的人格气禀。因此,周恩来“求友”的本意是侠的再造和群的复现,言彼之所有,是因此时之所无。小说包含了周恩来的审美期待,国民性改造诉求,也体现了一代人共同的精神世界和对未来生命状态的期待。
天津南开学校开学时,周恩来在开学感言中即说“勤学立品,煅身炼心”,而仅仅两个月后又与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共同起草了《敬业乐群会简章》(周恩来的武侠小说也是这一阶段写作的),“凡同志者,盍兴乎来”。这让人联想起毛泽东1915年曾在长沙街头张贴的《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在敬业乐群会成立后,周恩来还曾撰《爱国必先合群论》,进一步解释“求友”的目的乃是合群而爱群,以团体之众力推动国家革命,并率先指出:“阶级不除,无平等之望;人群不合,无爱国之理。”周恩来当时在校内组织的社团还曾演出《五更天》《一元钱》等文明新剧,号召同学组建足球队锻炼体魄。而行之于文学,则是以武侠作为群体进步的榜样。在《本会成立时之宣言》中,周恩来强调“舍在学时代极力锻炼身心增进智能而奚求”,首先强调了身与心的锻炼,这与毛泽东在《新青年》上的表述“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的观念颇为吻合,也反映出那一代最为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具有集体性、时代性的思想特征。
故“侠”的呼吁,成为“体”的外在显现,而性别上的女性的特别标出,更凸显了周恩来对当时男性欠缺“体”之锤炼的体认,在心理上是以一种代偿机制去安设女侠这个角色的。侠女形象的兀现,是为了激励身边男儿当知耻而自强。“求友”是新文化运动到五四前夜新青年的群体性姿态,暗含着个人声音微弱,亟待产生更大影响的潜在目的。“闻鸡鸣而起舞,无忘雪耻之志”成为一代新青年的精神写照。故侠与书生同行,成为“自我革命”的象征。
三
周恩来的武侠小说,应该放在晚清民国之交的文化浪潮中进行认识,这是抛开简单的情节和人物关系,回到历史现场,认识周恩来在小说中寄寓之主旨的关键。
晚清民国之交,武侠小说中的侠女形象书写是作为一种浪潮出现的,在当时影响较大的作品如叶楚伧的《古戍寒笳记》、钱基博编《武侠丛谈》中的《清江女子》、蒋景缄《侠女魂》等,这些作品大抵都出现在1910年前后,1912—1917年则是此类中篇小说写作的高峰期。这个潮流中既包含着诸多后来声名鹊起的政治人物,暗寓革新理念,也包括不少海派文人在旧小说影响下的创作,但总体趋势已不再是古代公案侠义小说本着情节之离奇,趣味性之突出,而有了近代主题的更易。周恩来亦是得风气之先,比其他小说写作者动手更早,年纪更轻。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夜,周恩来借武侠小说传递出来的思想是变革社会的预先展望。
周恩来之所以在小说中表现出如此鲜明的性别意识,凸显女性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位置,也基于当时“缺少什么就呼唤什么”的社会心理结构。男女社会地位何者为先,与如何解释侠客精神,只是周恩来少年写作的表层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際上是新与旧对立层面的文明社会结构的找寻,以及对哪些传统精神成分有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的探究。
虽然早在1844年,埃尔德赛等西方传教士就在宁波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学,但影响毕竟较小。直到1898年,戊戌维新时,经元善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学会书塾,这是第一所中国人自己办的女学。1900—1910年,国内女校多有停止招生的情况,起起伏伏,总未形成潮流。据薛文彦研究:清末女学多设于私塾,无论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资办女学的能力都有所不足,加之固有观念和守旧势力的阻挠,造成“女子学校教育服从于政治的附属地位”。
1913年教育部颁行的“壬子癸丑学制”中,“初小四年”男女同校,此后男女分校,此前的“癸卯学制”中并未规定女性就学地位,而蔡元培主持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则明确规定了普通中学、中等实业学校、师范院校都要设有女校,作为民国第一个学制,有着很强的探索性,仍带着顾及男女大防的传统观念。
周恩来上中学时积极组织社团男生活动,而看到女性就学率仍然非常低,故“求友”也是“求群”“求平等”,求更好实现自己改造社会抱负的机会。南开中学时期,周恩来还曾亲身参演《茶花女》中的女性角色。追求男女平等的前提是受教育机会的平等,之所以当时需要男性角色演女性,也反映出社会转型期内,男女分校教育制度本身的保守性、滞后性。因此,周恩来笔下的洪飞影有英雄气,然而周恩来却并未提到她的受教育水平,大抵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不似秋瑾那般文武兼备。而书生胆气的不足,更是当时一些中国男性在面对外侮畏缩不前的缩影。其所留下的空白正是对中国教育平等的希冀,在少年周恩来的观念中,只有男女互补,侠义精神得到贯彻,才能实现文化自新。到1919年,周恩来、邓颖超组织的觉悟社则已经广泛吸纳男女同学。他们后来更倾力支持女权运动同盟会,筹办《女星》旬刊、《妇女日报》等报刊。周恩来夫妇在积极社会革命的同时,也真正促进了一代书生的自强和女性的解放。
解放女性也契合周恩来早期“阶级不除,无平等之望;人群不合,无爱国之理”的思想,在艰难发展中,女性逐渐浮出历史地表,成为社会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周恩来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才尤其重视这一问题。而数年后胡适发表《终身大事》,《新青年》上讨论女性问题的“易卜生专号”,都是这一诉求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周恩来的武侠小说更像是新文化运动到来前,借用旧文学形式,传递革新思想的尝试,其与陈独秀办报时的“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思路相仿。所不同的是,少年周恩来希望借中国传统史传、公案文学中的侠义精神与政治革命相结合,通过改造国民性促进精神界的焕新,其中也包含着对传统文学形式、思想观念的冷峻反思。周恩来武侠小说的写作,可以看作新文化运动前夜一次“借旧为新”的思想操练,是他走上革命道路前重要的历史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