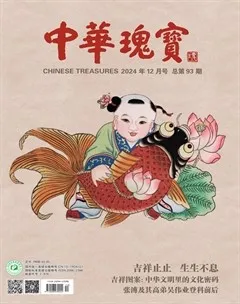天机织贝 冰蚕失文






唐代螺钿工艺技艺超凡,以此工艺制作的螺钿器精美绝伦、绚丽夺目,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螺钿镶嵌工艺是集贝类装饰、木艺镶嵌、髹饰工艺之大成而发展起来的髹饰工艺,以漆之坚牢、贝之绮丽融合而成,其制品绚丽奇幻,流光溢彩。在唐代,螺钿工艺超凡,螺钿器大放异彩。
何为“螺钿”
螺钿又称螺甸、钿嵌、陷蚌、坎螺等,螺钿工艺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门类。“螺”,即体外包有硬壳的软体动物;“钿”字取镶嵌之意。其制作过程一般是以螺、蚌、介类之壳为材料,将其磨制为薄片并镌刻成形,最后再依据图案设计,将薄片镶嵌于器物表面。螺壳天然绚丽,视觉效果强烈,故被广泛应用于家具、乐器、盒匣等物的装饰工艺中。
螺钿与漆艺相伴相生,商、周之时,将螺贝、蚌壳作为装饰的技法已不罕见。殷墟商代王陵遗址出土的漆器上就有蚌壳镶嵌,北京琉璃河遗址西周墓出土的彩绘兽面凤鸟纹嵌螺钿漆罍,其兽面纹上亦镶嵌有蚌贝片。屈原《九歌·河伯》中“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朱宫”的“贝阙朱宫”指用贝壳珍珠装饰的宫殿。
贝壳装饰、髹漆工艺的发展,促成了漆与贝的结合,造就了螺钿器对比强烈、妙相纷呈、色泽熠熠、光华可赏的美感,使其成为中国工艺美术的瑰宝之一。
极盛的唐代螺钿艺术
唐代的手工业空前繁荣,螺钿工艺也不例外。经过东周至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螺钿镶嵌工艺在唐代日趋成熟,其中,螺钿漆工艺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并蓬勃发展,而木地螺钿镶嵌工艺的发展更为迅速。唐代的螺钿工艺,在漆艺形态上有所转变。六朝时,螺钿工艺深受当时宗教艺术氛围的影响,装饰内容长期以神兽为主。至唐代时,螺钿工艺的装饰内容开始以花鸟等充满生机活力的题材为主,展现了开朗舒放的精神面貌。唐代白居易的《素屏谣》诗云“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织成步障银屏风,缀珠陷钿贴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正是当时螺钿器的华贵气象之体现。
唐代螺钿器的螺片都较厚,属“硬螺钿”范畴,其加工形状概括,细节以毛雕刻画,表现出气质大方的时代特色。硬螺钿漆器的制作分为选材磨片、贴稿、锼片、垫色、搛坯、刮浆灰、磨灰、糙漆、开纹、涂漆、磨显、推光等十余道工艺程序。其主要制作工具有手弓、手锉、切样板、切样刀、拉弓板、开纹刀、錾子、镊子等。最终,采用螺钿镶嵌工艺的图像呈现出文质齐平、光华可赏的特点。
唐代螺钿器有一定遗存,其中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收藏有约20件唐代螺钿传世作品,含木底、漆底、树脂底、玳瑁底四大类,包括9件铜镜、7件乐器、2件棋具、2件器盒,多为圣武天皇旧藏,堪称稀世遗珍。日本奈良时代正值中日文化交流频繁的中国盛唐时期,大唐赠送的宝物多被日本较好地保存至今,为我们认识唐代艺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日本正仓院藏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是目前仅存的唐代五弦琵琶,堪称大唐乐器活化石。该琵琶长108.1厘米,最大腹宽30.7厘米,造型隽朗端庄,其髹饰工艺将唐代螺钿镶嵌技术发挥到了极致,在美术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乐器装饰工艺的经典之作。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的正反面螺钿片总计达1300余平方厘米。由于琵琶背板、侧板、转手、琴头等处是谐振部位,故其作为主装饰面被大量施以螺钿等工艺,而对主要承担共振功能的面板装饰节制。琵琶正面的玳瑁捍拨是主装饰带,其上骆驼载胡人琵琶弹奏图案呈现出鲜明的西域风格,人物上方五只祥鸟绕树而飞,琴声弥漫,意境高妙。该琵琶的螺钿选材精良,光色统一,传承千年仍保留完好,玲珑润泽的质感和耀眼的光辉彰显出极度奢华。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是迄今所见最华美的唐代螺钿器,让世人得以见识到盛唐精湛的木地螺钿工艺。
唐代螺钿铜镜
目前国内出土的唐代螺钿约15件左右,以螺钿铜镜居多。盛唐时期的螺钿镜非常精美,如1955年河南洛阳16工区76号唐墓出土的花鸟人物螺钿镜,直径23.9厘米,平贴螺片的物象细部如人物面容、衣纹、飞鸟、树木、山石和花草等,均有精细的毛雕,形象栩栩如生。又如1956—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1914号墓出土的云龙纹嵌螺钿铜镜,是盛唐时期的作品。此镜直径22厘米,工艺精湛,刀法娴熟,镜背用白色螺片拼嵌成一条盘旋飞腾的巨龙,其形象肥硕而不失夭矫之势。龙身云朵均有毛雕,生动异常。此两件螺钿镜螺钿花纹繁密,宛如星辰,是唐代螺钿器的代表作品。
日本正仓院亦收藏有9枚唐代螺钿铜镜。这些铜镜保存完好,纹饰各异,但基本样式相同。从规格和工艺的复杂程度来看,这9枚铜镜在复合镶嵌和细密镶嵌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在镜背用琥珀或玳瑁进行复合镶嵌,在蚌片间则用绿松石、青金石等细小宝石进行细密镶嵌。
一直以来,唐代螺钿铜镜背面采用漆底几乎成为国内学界共识。但日本正仓院收藏的螺钿铜镜不是漆底,而是使用了虫胶。虫胶也称紫胶,是紫胶虫吸取树液后分泌出的天然树脂。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胡健认为,螺钿铜镜皆为漆器是中国学界的一个认识误区。唐代螺钿铜镜可分为漆底镜背和树脂底镜背两种,后者受萨珊波斯文化影响。国内出土的螺钿铜镜多数应为虫胶树脂底。
萨珊波斯艺术是对唐代螺钿工艺影响很大的域外文化,唐代螺钿奢华富丽的镶嵌风格正是受其影响。很多螺钿器的图案采用了中西亚特色的连珠纹、胡人骆驼、对鸟对兽纹等纹样。萨珊王朝在北魏时就与中国有往来,在唐代时文化交流更为紧密。萨珊王朝的宝石镶嵌技艺举世闻名,尽人皆知,而唐代螺钿工艺的突出特征就是螺钿同其他宝石进行复合镶嵌。
藏于国外的螺钿铜镜多与正仓院样式相类似,唯有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圆形双凤花卉纹铜镜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能明显看出漆底的螺钿铜镜。从这枚铜镜实物来看,漆底上纯用蚌片组成花鸟图案,虽有部分镜背漆底脱落,但基本保存完好。这枚铜镜蚌片上没有复合镶嵌,蚌片间也没有其他宝石碎片的细密镶嵌,装饰风格端庄质朴。
饰威饰荣
唐代螺钿工艺,是在先秦以来的漆器和木器的嵌装技术基础上,受中西亚玉石工艺法影响而形成的。鲁迅曾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侯,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今天,我们仍能透过唐代螺钿器感受大唐盛世之瑰丽。
《考工记》中“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工艺美学原则,对中国古代工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以螺钿器为例,螺钿器在古代已是极为珍贵的工艺美术品,一器之成,往往是工精料细,縻费工本,只有上层统治者和富贵之家才能持有,但它的制作者都是智慧的劳动人民。总而言之,古代“饰威饰荣”的政治文化主张是中国古代髹饰工艺繁衍生发的沃土,而螺钿镶嵌工艺的成熟和辉煌正是得益于中国古代髹饰工艺的进步。
唐玄宗之后,朝廷曾多次下诏,禁绝奢华工艺品制造,钿镂便在其列。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诏:“珠玉、宝钿、平脱……之类一切禁断。”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敕曰:“朕思素俭敦……宝钿、杂绣等一切禁断。”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诏:“不得造假花果及金平脱、宝钿等物。”但终唐一代,螺钿器未能禁绝。直至今日,螺钿仍是髹饰工艺中最重要的装饰品。
在乌黑的漆地上,精工细密地镶嵌的螺贝薄片,如暗夜的繁星般闪烁着迷人的异彩,光映宫阙,令传说中的冰蚕锦也失去光彩,可谓是“天机织贝,冰蚕失文”。
张超越,深圳市致理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