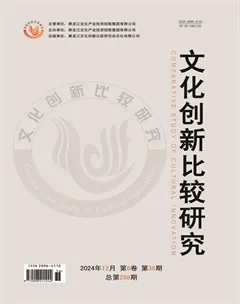从“学”论看子夏与荀子之间的思想联系
摘要: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虽称“子夏氏之儒”为“贱儒”,然而这实质上仅是对子夏后学末流生活细节之批评。对于子夏,荀子评价其为“古之贤人”,推崇备至。事实上,子夏与荀子之间的学术还存在着紧密的思想联系,从“学”论来看尤其如此。对于为学之目标,荀子继承了子夏“学”为君子的思想,并进一步提出君子要“学”为圣人;对于为学之态度,荀子接续子夏之“学”注重积累的特色,明确主张要通过“积”以成“学”;对于为学之次第,荀子沿袭子夏论“学”重实践、重力行的特点,以“行”作为“学”的最终目标,提出“学至于行之而止”的观念。可见,从“学”论来看,由子夏至荀子的思想发展,确乎是先秦儒学发展的一条重要进路。
关键词:子夏;荀子;“学”论;君子;积;行
中图分类号:B222"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12(c)-0051-05
The Connection Between Zixia and Xunz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ing\"
CHEN Shengzhe
(Confucius Institute of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273165, Chian)
Abstract: Although Xunzi calls the Zixia's Confucianism low Confucianism in Fei XII Zi, this is in essence a criticism of the details of the life of Zixia's later scholars, who were at the bottom of the hierarchy. As for Zixia, Xunzi regarded him as \"a sage of ancient times\" and held him in high esteem. In fact, there is a close intellectual connection between Zixia and Xunzi, especial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theory of learning. For the goal of learning, Xunzi inherited Zixia's idea of \"learning\" to be a gentleman, and further proposed that a gentleman should \"learn\" to be a saint; for the attitude of learning, Xunzi continued Zixia's characteristic of \"learning\", focusing on accumulation and emphasising the importance of accumulation. For the attitude of learning, Xunzi succeeded Zixia's \"learning\" by focus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cumulation, and explicitly advocated \"learning\" through \"accumulation\"; for the order of learning, Xunzi inheri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ixia's \"learning\" by focusing on practice and action, and advocated \"learning\" by focusing on practice and action, and further proposed that a gentleman should \"learn\" to be a sage. As for the sequence of learning, Xunzi followed Zixia's character of \"learning\" which emphasises practice and action, and took \"action\" as the ultimate goal of \"learning\", and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learning to the end of ac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theory of \"lea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 from Zixia to Xunzi is indeed an important path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 the pre-Qin era.
Key words: Zixia; Xunzi; \"Learning\" theory; Gentleman; Accumulation; Behaviour
清人汪中《荀卿子通论》言:“荀卿之学,实出于子夏、仲弓也。”从子夏到荀子在学术上具备思想联系,荀子作为先秦儒学之殿军,系统性地吸纳并发扬了子夏的学术思想。然长期以来,由于荀子在其《荀子·非十二子》中批评其为“子夏氏之贱儒”之缘故,部分学者凭此点认为荀子对于子夏其人、其说持否定之态度[1]。实则不然,这一表述并不意味着荀子对于子夏学术思想的否定。清人王先谦《荀子集解》中便已引郝懿行之说对所谓“贱儒”问题做出回应:“此三儒者,徒似子游、子夏、子张之貌而不似其真,正前篇所谓陋儒、腐儒者,故统谓之贱儒,言三子之门为可贱,非贱三子也。”当代学者高培华先生进一步明确指出:“至于在百家争鸣中,荀况所批评的‘子夏氏之贱儒’‘子张氏之贱儒’应当是儒学发展到战国末期,荀子所看到的子夏、子游、子张之后学末流,而非三子本人。因为他批评的生活细节等表现,只能是他看到的同时代的人。”[2]陈来先生亦指出:“子张、子夏、子游都是孔门的高弟子,荀子却攻击他们的学派是贱儒,这显然是不公允的。然观其所用,这里的批评都未涉及子张、子夏、子游的思想,其所批评的都是这些学派的衣冠饮食等生活方式。”[3]
“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食则饘粥不足,衣则竖褐不完;然而非礼不进,非义不受,安取此?子夏家贫,衣若县鹑。”事实上,对于子夏,荀子评其为“古之贤人”,对其推崇备至。在论“学”的问题上,两人的学术还存在着重要的思想联系。众所周知,重“学”历来是儒家的重要精神传统。荀子同孔子、子夏尤重“学”,其全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子夏的“学”论,使其成为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荀子》一书以“劝学”作为开篇,足以看出“学”论在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从孔子到子夏,从子夏到荀子,儒家的“学”论通过这种代序传承,对后世之儒的治学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4]。
1 以“君子”论“学”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自孔子至荀子,儒家皆主“为己之学”,认为学习的目的在于成就自己的道德人格。然而,“为己之学”中的道德人格具体指什么呢?就理想人格的境界而言,儒家从高到低有圣人(仁人)、贤人和君子等。在孔子及其弟子看来圣贤是“自诚明”,乃本性使然;普通人是“自明诚”,方有教育可言[5]。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故《论语》中强调为君子,以君子作为普通人通过后天的“学”可以达致的理想人格。《论语·雍也》中孔子告诫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教育子夏应当以“为君子儒”作为人生追求。子夏承继孔子之教诲,将“学”与“君子”相结合,以“致道”、成为“君子”作为“学”的目标。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正像工匠长日在肆中要做出器物以证明自身的才干一样,君子为学亦是如此,应当以“学”为天职,不断通过“学”以求“道”,以锤炼君子的道德品性。因此,在君子人格的养成上子夏十分重视“学”的作用。这里子夏所言君子“学”以所求之“道”,或为孔子、儒家最为看重的“仁道”,并非局限于某一“小道”。其言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小道”虽有可取的地方,但“君子”不应拘泥于此。“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所谓“君子”,唯有通过“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的努力,才能求得“仁道”。子夏还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他看来,“学”成君子的具体表现就是自身能够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做到“敬而无失”“恭而有礼”,在行为、言语方面合乎礼节,符合“仁道”。
在子夏与荀子之间,荀子继承了子夏“君子学以致其道”的思想主张。其言曰:“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这里,荀子把礼义总结为中正之道,认为它不是天地运行规律,而是君子所要遵循的大道。“出于‘法先王’的历史意识和价值导向,荀子指明君子向往和推崇彰显中庸特质的仁义之道”[6],这同子夏“仁在其中”所要求取的“仁道”正相发明。“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同样与子夏“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的观点相符。荀子认为,“君子之学”不应局限于某个方面,应以多方面“全而粹”的学问作为“君子之学”的追求。“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所谓“君子之学”在于将所“学”内化于主体自身,以达致“全而粹”的完美人格境界,而不是将所“学”当作家畜之类的礼物去赠献他人。
相较于子夏,荀子在“化性起伪”观念下更加强化了后天之“学”(伪)对于理想人格养成的重要性。他说:“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性情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在荀子看来,人若想成为君子需要重视后天的积累磨炼,通过不断地“学”以成就内在德行,最终才能成为君子;反之如果放纵性情不注重后天之“学”(伪),便会沦为小人。“性者、本始材朴也”,君子与小人、圣人与凡人“其性一也”,于荀子而言,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君子、圣人,其根据不在先天之“性”,而在后天的“伪”(积学)。“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也就是说,人之成为“君子”或“小人”,关键在于其后天是否能够心肯意肯地去通过“学”的修为以努力成为君子。故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另外,从二者所认为的为学最终目标来看,子夏继承孔子“得见君子斯可矣”的观念,认为“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在他看来,“学”应追求“君子之道”,能“有始有卒”的圣人是现实中绝大多数人所望尘不及的。故他将“学”之目标主要聚焦于养成君子人格,主张“学”为君子。荀子继承了子夏“学”为君子的思想,并进一步提出君子要“学”为圣人,以“成圣”作为为学的最终目标。“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非特学无方之民也”,其认为主体自身应当要通过后天不断地“学”(伪),在“化性起伪”的工夫中,达致圣人的理想人格境界。为此,他特别提出了“积善而成圣”“行之而为圣”等观念。总而言之,在荀子“学”论中,“成圣”是为学的最高目标,而为学本身就是引导人走向“成圣”的途径。此可谓荀子对孔子、子夏“学为君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2 以“积”论“学”
子夏论“学”已注意到了“学”所具有的过程性特点,他提倡“博学”,注重广泛地积累知识对于“成学”的作用。于子夏而言,为学当中注重慢慢积累是不可或缺的。他认为,所谓“好学”就是每天不断学习新知识,并且保持对于旧知识的掌握,对此其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此即孔子所谓“温故而知新”。这一为学态度在他与子张的对话中亦能反映出来:“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面对子张对其学术“舍本逐末”的批评,子夏回应道,学术只有种类之分而无本末之分,若把本末全然分开看待,或许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孰先传焉?孰后倦焉?”即使是在不被人所看重的细微之处,仍然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唯有如此去“学”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收获,即其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
与荀子相比,子夏之论“学”,虽已有注重积累的特色,可他并未明确提出“积”以论“学”的主张,因此,对于“积”以成“学”未能给予充分论证和展开。从为学之态度上看,荀子继承了子夏笃实的学风,主张“积”以成“学”。“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积”是荀子在讨论为学工夫时反复出现的关键字,荀子通过列举“积土成山”“积水成渊”,以自然界事物的演变来论证人成就德行同样需要通过“积善”来实现。“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荀子较子夏更进一步地提出“积善而成圣”的观念,将“积”的为学态度贯穿于“成圣”的过程中。在“积”以成圣的过程中,荀子提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以此强调“学”的延续性和不间断性。荀子认为,在“学”的过程中,唯有通过不间断地“积”从而保持“学”的延续性,对所“学”做到“全之尽之”,最终方能成就“圣人”这一理想人格。
那么,何以保障“积学”的终身延续和不间断呢?在子夏的“学”说中就已经提出,“学”的过程中要做到“博学而笃志”。汉末文学家徐干《中论·治学》亦记载:“子夏曰:‘日习则学不忘,自勉则身不堕,亟闻天下之大言则志益广。’”子夏认为,广泛积累学习的同时,有笃定之心、坚定之志同样重要。以“积”之态度为学是个艰辛的过程,为了达到预期,人们在学习中必须有着坚定的志向,从而得以保障“学”的不间断性。荀子的“学”论继承子夏,他提出“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强调人们在“学”的过程中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其言曰:“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此之谓也。与子夏几乎完全一致,荀子也认为,坚定的志向对于人之为学十分必要,若无坚定之志,学有所成则无从谈起。荀子将此坚定的态度,形象地形容为“一”的精神。他说:“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这就是说,在“积学”的过程中若做不到“一”,即“集中”与“专一”,难免会学无所成,沦为街巷之中的普通人。
此外,荀子还在人性论的层面对保障“积学”的延续性提供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论证。荀子主张“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尽管人性先天缺乏内在德行,但是先天之“性”是可塑的,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后天不断地“化性”以向善。“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在这一“化性”过程之中,唯有通过外在持续不断地“积伪”(积学)才能够使其得以贯彻,最终方能“积善而全尽”,使人性由恶向善。
3 以“行”论“学”
孔门论“学”,以成德为重。“学”不仅是知识论意义上追求知识、发展智性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价值论意义上修养人格、涵养德行的过程[7],因此“学”不仅要重“知”,更要重“行”(人伦实践、践行礼义),这是儒家一以贯之的观念。作为孔子高足的子夏深谙此道,不同于曾子等强调“内省”工夫的弟子,子夏之“学”注重对现实之“礼”的学习、践行。《国语·鲁语下》记载:“子夏闻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谓之不幸。’夫妇,学于舅姑者也。”在这里子夏所强调应向长辈学习的即如何学习与践行现实生活中“洒扫应对进退”之礼节。又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说明子夏所谓的“学”着重通过现实中的“行”来践履各类礼节,包括对父母孝,对国君忠,对朋友信。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能遵道而行,其人虽或自谦说“未学”但也被子夏认为是“好学”。朱熹引吴氏之言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辞气之间,抑扬太过,其流之弊,将或至于废学。”[8]诚然,子夏对“学”所表明的这种重力行的特点,并非对“学”之作用的低估,也并不如吴氏所认为的这会导致出现废“学”的倾向。李泽厚曾指出:“整个讲来孔门更强调的是广义的‘学’,即德行优于知识,行为优于语言。”[9]儒家所谓的“学”不能仅停留在对于经书的诵读掌握之上,而是要践行到现实人伦生活中去。换言之,唯有在现实人伦日用中成为能够笃行之人,才可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学”。当然,由此可以说,子夏之“学”自然带有鲜明的政治实践性,比如他就明确提出了“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10]的主张。子夏认为,想要“仕优”必须去“学”,“学优”方可出仕,“仕”(行)与“学”之间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开的。
从为学之次第上看,荀子继承了子夏“学”思想重实践、重力行的特点,以“行”作为“学”的最终目标,提出“学至于行之而止”的观念。在荀子看来,只有最终落实到“行”上,才能将所“学”之“礼”贯彻到实际生活之中。“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从为学次第的角度来阐明“行”对于“学”而言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他认为,外部所“学”的礼仪知识最终应“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贯彻到个人的身心当中,最终通过“行”表现出来。荀子说:“礼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颠蹶陷溺。”他认为,唯有在日常生活中践履“礼”,才能不断完善自我,成就理想人格。荀子重“行”(实践)的原因正在于此,“学礼”若仅限于知识讲求的层次,而不能将之付诸于行,那它便没有修身的意义可言,更无从谈起对于为政的意义。“学莫便乎近其人”,在荀子看来,亲近现实人伦生活中的人格典范,不断日积月累,耳濡目染,乃是“学”的最佳途径。
与“积善而成圣”相一致,荀子同样将“行”与“成圣”相结合,提出“行之而为圣”的观念。其曰:“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杨倞注曰:“行之,则通明于事也。”对于这句话,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理解认为若把此处杨倞的“通明于事”,理解为“知通统类”“知通贯、统摄一切事理之理”,那“圣人”就是由“知”来规定的,这便与荀子所要表达的“学止于行”的原意矛盾[11]。实际上,《荀子》中“知”存在同字异义的问题。荀子的“明”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知”,而是需要通过“行”以成就政事方能得以展现,是圣人所独有之“知”,代表了个人认知的最高境界。《荀子·儒效》:“知之,圣人也。”杨倞注曰:“知之,谓通于学也。于事皆通,则与圣人无异也。”依杨倞,此处“知”与“通明于事”之“明”意正相合。《荀子·解蔽》中同样出现“知之,圣人也”,杨氏亦注:“知圣王之道者。”[12]依此可见,此“知”(明)非为学之次第当中的“知”,而是圣人境界的彰显,“圣王之道”的指代,是通过“学”以达致“成圣”目标之后自发的显露。因此,想要“学以成圣”,唯有通过“闻见”“知”“行”的为学次第来实现,以“行”作为“学”的最终目标。故韦政通言:“‘明之为圣人’即能笃行之人。”[13]“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14]荀子将最终能否付诸“行”(人伦实践、践行礼义)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之学的标准,至此不难明矣。
由上可见,在为学次第上,无论是子夏还是荀子论“学”均以“行”作为“学”的最终目标。子夏将日常生活中能够遵道而行称作“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到荀子时提出“学至于行之而止”的观念,由“知”到“行”,通过“行”来实现对于所“知”的落实,并在“行”中不断完善先前所学,最终达致“明”的境界[14]。
4 结束语
由于受限于“道统说”的影响,学界往往侧重于关注由孔子至“思孟学派”之间的思想脉络,相比之下对于孔荀之间的思想发展则缺乏相应的关注。通过以上关于子夏与荀子“学”论的探讨,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荀子对于子夏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子夏作为孔子的高足,力图全面如数继承孔子的为学思想,因此其“学”论基本是对孔子思想的“照着讲”,属于对孔子为学思想的进一步丰富以及归纳总结。而荀子论“学”则属于在全面继承子夏“学”论的基础上的“接着讲”,对“学”论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发展。其明确提出“积”“行”以成“学”,将为学之目标由“为君子”提升至“成圣人”,并在“化性起伪”的观念下,进一步强化了后天之“学”(伪)对于理想人格养成的重要性。因此,无论是否存在一个同“思孟学派”平行发展的“夏荀学派”,从“学”论上看,荀子思想深受子夏影响是十分明显、毋庸置疑的。由孔子至子夏,从子夏至荀子,这确乎是先秦儒学发展的一条重要进路。
如果说“思孟学派”的思想观念对后世宋明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那么荀子继承子夏发展而来的“学”论则对汉学之儒的治学理念产生了深刻浸染。《荀子·尧问》中已记载汉初荀子后学称:“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特别是在宋明理学向清代汉学的转型过程之中,其对汉学之儒的影响表现得尤为深刻,“从顾炎武以‘日知’名书,到惠栋提倡治学重积累,再到钱大昕以‘驽马十驾’自许,倘若追溯其义,无疑都源自子夏、荀子”。可见以“积”“行”作为治学的观念在清代汉学家的治学理念中普遍存在,故汉学家普遍尊奉子夏和荀子为“家法之祖”和“汉学之源”,将其视为自身学术传统之起源,由此从“学”论上看,由孔子至子夏、从子夏至荀子的儒学发展进路在很大程度上贯穿了中国儒学的发展始终,值得对其进行更进一步的研讨。
参考文献
[1] 李冬君.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2.
[2] 高培华.卜子夏考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83.
[3] 陈来.“儒”的自我理解:荀子说儒的意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19-26.
[4] 赵四方.孔门传经弟子的形象重塑与清代经学转型:以子夏为中心[J].江海学刊,2022(4):190-199.
[5] 郭齐勇.中国儒学之精神[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263-267.
[6] 涂可国.儒家人学视域中的荀子君子之学[J].东岳论丛,2024,45(1):165-173,192.
[7] 郑治文.荀子论“学”[N].光明日报,2022-09-24(11).
[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50.
[9] 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36.
[10]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
[11]何淑静.由“成圣”看荀子的“为学步骤”[J].鹅湖学志,2012(2):1-35.
[12]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3]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22:37.
[14]张觉.荀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陈圣喆(2001-) ,男,山东东营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儒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