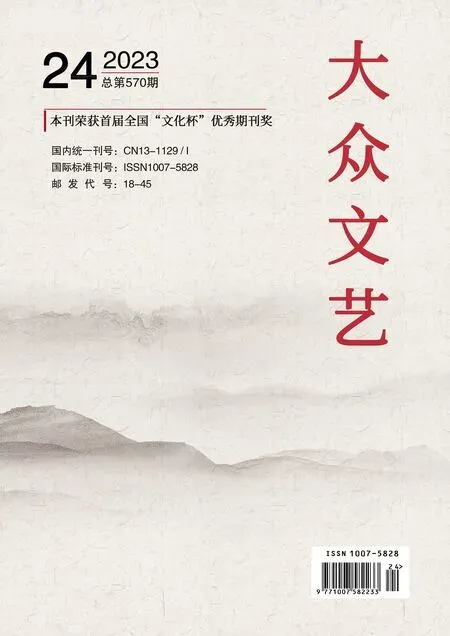先秦至南北朝:七夕节的起源、成型与发展
杨 宇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开封 475000)
一、相关研究评述
关于七夕节的起源,自20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探讨,笔者在此择要列举部分代表性成果。张君认为,七夕产生于战国时期的楚国,脱胎于“汉之游女”的神话,织女的神性和七夕乞巧祈愿的习俗与楚地的少司命信仰关系密切。[1]吴天明认为,七夕文化源于夏人的原始宗教和夏代历法,牛女传说的本质是对华夏诸族青年男女七月七日夜祭祀先妣、月神、织女神时放纵野合习俗的反映。[2]刘学智、李路兵认为,牛女传说和七夕早期节俗均产生于西汉初的长安,七月七日是因牛女传说融入方成为“七夕”并作为一个纪念性节日而存在。[3]隆滟认为,七夕节的存在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其名称和节俗都跟农耕习俗息息相关。[4]赵逵夫认为,七夕节诞生是受牛女传说影响,而牛女传说早在先秦就已经出现。[5]萧放认为,七夕经历了从凶时恶日到良辰吉日的历史变化,这背后隐藏着古代社会民众时间观念的重大变迁,汉代以前七夕就已经出现,只是不一定在七月七日,可能在七月朔日。[6]刘宗迪认为,由于历法不够精确,七夕节在西汉末王莽时期之前日期并不固定,是东汉才固定为七月七日并因之成为一个节日,而七夕节所依托的织女崇拜则早在先秦就出现了。[7]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出发对七夕的起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尽管在一些观点上有出入,但基本有一个共识,即七夕节虽然大致在汉代才完全成型并正式成为一个节日,但早在汉代之前七夕文化及部分节日元素就已经存在。
关于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七夕节研究,根据主题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研究从民俗学、历史学角度入手,重在对七夕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和对七夕节俗进行考证与释读。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陈连山的《论七夕节的源流》、赵逵夫的《七夕节的历史与七夕文化的乞巧内容》、萧放的《七夕节俗的文化变迁》、刘宗迪的《七夕的历史与神话》等等。这些论文论证充分、考证翔实,但大都主要论述汉代部分,关于魏晋南北朝的论述相对简略。此外,山东大学马莹的硕士论文《北朝七夕风俗与西域文化》详细考证了北朝七夕讲武驰射的风俗之由来及其特殊性,弥补了学术界关于北朝七夕研究的空白。
另一类研究主要是从文学角度入手,以七夕诗歌、牛女传说为主题进行的文学文本研究,且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的牛女传说和诗歌中的七夕书写。其中属于学位论文且较有代表性的有青岛大学王爱科的硕士论文《牵牛织女神话传说与七夕节的起源》、中南民族大学邱绮的硕士论文《传统七夕节演变历程与现代转型》等。学位论文以外,也有一些期刊论文值得关注,比如徐传武的《漫话牛女神话的起源和演变》、郑慧生的《先秦社会的小家庭制与牛郎织女故事的产生》、杜汉华与华汉文的两篇同名论文《“牛郎织女”流变考》、刘宗迪的《七夕故事考》、赵逵夫的《牛女传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播与分化》与《由秦简<日书>看牛女传说在先秦时代的面貌》、傅功振和樊列武的《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考证与民族文化内涵》、赵依的《“牵牛织女”传说的起源与流变》等。以上论文均对这一时期的七夕节有所涉及,但皆非以七夕节为主要研究对象。
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史料和文学文献资料对隋唐以前的整个七夕节发展史做一个梳理,分阶段论述七夕节从孕育到形成再到初步普及的整个历史过程,并突出其在每个阶段、每个时代的发展变化和主要特点,以期探明源流、从整体上把握七夕节的早期发展历程。
二、秦汉之前:七夕节的起源与节日元素的孕育
一个节日的诞生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既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特殊的契机,又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七夕节虽然在汉代才正式成为一个节日,但是促使七夕节产生的文化元素早在秦汉之前的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七夕节的起源,主要是受以下因素影响:
第一,周秦之际,“农业革命”的发生确立了以耕织为中心的新的生产方式,并催生出日渐精密复杂的历法体系。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传播,铁犁牛耕代替刀耕火种成为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逐渐确立,与此同时,自西周起“一夫一妻”逐渐成为主流的婚姻模式和主要的家庭建构方式,单个家庭逐渐取代原始部落或族群等集体单位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组织单元,这种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革新彻底改变了周秦时期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使得中国古代先民们产生了新的更为复杂的生活需要,正是这些新的生活需要催生了封建社会日渐精密庞大的历法系统和节日体系,七夕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刘宗迪认为,节日的诞生有赖于天文学的进步和文字的使用,需要有成熟的历法系统确立其日期,乞巧习俗和织女崇拜可能早在“观象授时”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但七夕节迟至汉魏时期才正式诞生,这是更为发达的“按月计日法”代替“干支纪日法”因而把七夕确定在“七月七日”这一天的结果。[8]
第二,古老的星辰崇拜也对七夕节的形成和发展影响重大。一般认为,对七夕节来说影响巨大的牛女传说便来源于原始先民的星辰崇拜,是先民将星辰形象化、拟人化以后产生的结果。这种星辰崇拜起于何时已难以考证,但不会晚于西周,因为牵牛、织女并列出现最早见于《诗经•小雅》中的《大东》篇。此外,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也有关于二者的记录。有学者据此以为牛女传说大致产生于周代。比如蒋明智认为,西周时已有天孙织女与牛郎结合却因违背天帝意志而为天河所阻隔、只能一年一度鹊桥相会的传说,他明确指出这正是西周“一夫一妻专偶制”确立的结果。[9]在对秦简《日书》进行考证后,赵逵夫认为牛女传说“在战国时代已大体形成同后代基本相同的情节,主要人物的身份特征也基本确定”。[10]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熊钿认为,仅凭《诗经》和睡虎地秦简中语焉不详的片段记载无法证明牛女传说在周秦时期便已形成,但是她也指出,就算《诗经》和秦简并不能直接证明牛女传说已经形成,二者对其形成过程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二者关于星象的拟人化记载和情感化表达以及将“牵牛”“织女”并列对举的做法,极易给人造成一种“门当户对”的印象,激发人们的浪漫联想。此外,星象本身也为民间故事的创作提供了素材。[11]
第三,先民对数字“七”的崇拜也值得注意。钟年在梳理汉族及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后发现,在与女性相关的描述中数字“七”大量出现,钟年据此认为是初民在观察女性生理周期或生命发展节律后发现女性的基本生理现象往往与“七”有关,从而形成了对数字“七”的信仰。[12]这种信仰既然在神话中有所反映,毫无疑问,其早在文明初期就已经存在。而《黄帝内经》在“上古天真论”中确实存在这类说法:“女子七岁肾气实,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13]该书对男女生理规律进行总结,认为女子每七年发生一次生理变化,男子则是八年。此外,关于数字“七”,万建中认为,一般来说在中国传统时间观念里单月单日都是不吉利的、非凶即恶的,像三月三、五月五、九月九莫不如此,然而数字“七”则是时间观念中的“一个圣数”,因而在单日里,只有逢“七”才具有吉祥的象征意义,而这种现象是在《庄子》《周易》等先秦典籍里已经有所体现的。[14]由此可知,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对数字“七”已经产生了特殊的认识,这对七月七日在历法体系中被凸显出来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太平御览》中也确有“七月七日为良日”“七日为阳数”的记载。[15]可见数字“七”与众不同的神圣性使得七月七并不像五月五、九月九一样被视为恶日,而是一个吉日,其带给民众的情绪体验和心理暗示也偏向积极或中性,后世七夕节祈福乞巧的主题和喜庆欢乐的氛围可能就与先民对七月七的偏爱有关。不同的是,萧放认为七夕节早期的节日主题也与“分离”“禁忌”有关,西汉中期以后才逐渐由凶趋吉。[16]笔者以为,这与数字“七”被视为圣数并不矛盾,或许正是因为数字“七”意义特殊,才促使七夕节很早就完成了由凶趋吉的转变。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也有说法认为,七夕节在战国时就已经出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明代。罗颀《物原》云:“楚怀王初置七夕。”[17]亦即七夕节可能在战国末期的楚国就已经存在。但是这个说法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物原》一书虽为更订北宋高承《事物纪原》而作,但是《事物纪原》全书并无这一说法,此说当为罗颀增补,除罗颀《物原》外,此说别无材料可供印证。二是罗颀为明代人,距离战国远甚,不知其材料出处。三是书中较多提及神话人物,有“伏羲初置元日”“神农初置腊节”的说法,混杂神话与历史。[18]因此,此说的真实性成疑,孤证不立,故而“楚怀王初置七夕”也只是一种可能,尚无足够的材料支撑。
三、两汉时期:七夕节的成型与相关传说的发展
汉代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伴随着政治统一和经济繁荣,文化也出现了大发展。作为汉帝国的首都,长安的文化更是引领时代风潮,在汉代终于发展成一个正式节日的七夕节便诞生在汉都长安。汉代七夕节情况如下:
第一,西汉时,七月七日可能已具有了节日的属性,至迟在东汉,七月七日已然成为一个节日。据笔者考证,“七夕”一词可能最早出现在西汉。《西京杂记》中有“七夕穿针开襟楼”这一条目,这是现存古籍中关于“七夕”一词的最早记载。此外,其书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19],又引戚夫人侍女贾佩兰之言云:“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受”[20]。这些记录虽然简略,但却是现存古籍中关于七夕节俗的最早记录,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只是,《西京杂记》为西汉刘歆所作、东晋葛洪辑录,成书时距离西汉已十分久远。如所载属实,则说明西汉初七月七日已然成为一个节日,有登楼穿针、临百子池、作于阗乐、羁五色缕等多种节俗。不过,这仅限于皇宫之中,是宫廷中人的专属活动。到了东汉,七夕节已正式诞生。据崔寔《四民月令》载:“(七月)七日遂作麹。及磨。是日也,可合药丸及蜀漆丸;曝经书及衣裳;作干糗;采葸耳也。”[21]作麹即制酒,蜀漆丸据传有给书或衣服防虫蛀的功效,干糗即干粮、粮食,葸耳可制蜡烛。可见在东汉,七夕节已经有了酿制酒、做防虫丸、晒经书、晒衣服、制干粮、采葸耳的节俗。这些记载是关于七夕已然成为一个节日的有力证明。
第二,牛女传说也在汉代逐渐成形。司马迁在《史记》中讲解星宿时明确指出,“织女,天女孙也”[22],可见司马迁时代有织女为天孙的神话流传,司马迁有所了解,只惜未详加记述。但在东汉古诗《迢迢牵牛星》中,已有关于牛郎织女分隔银河两岸不得团圆的描写。此外,东汉班固的《西都赋》也明确指出,在“昆明之池”旁,“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23]可见牵牛织女的形象已经形于建筑之中。由以上材料可知,至迟在东汉,牛女传说就已经出现。只是此时,牛女传说尚且还不能算作七夕节的传说,二者尚处在各自独立发展的阶段。
第三,七夕节适应汉代人追求长生、仰慕仙道的需要,变成了一个具有神异色彩的节日。汉代人普遍渴望修仙得道、长生不老,他们将这种期待与七夕结合起来,演绎出一系列具有神奇色彩的传说。据《太平御览》载,《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中有关于汉武帝与西王母七夕相会的传说,《列仙传》中有关于王子乔七月七日驾鹤飞升、陶安公七月七日乘龙飞升的传说,此外梁代文献《荆楚岁时记》中也有关于窦太后七夕遭遇神迹的传说。[24]从这些传说可以看出,在汉代,七月七日被视为可以偶遇神迹、结交仙人、飞升得道的吉日。正如前述,牛女传说虽在东汉已经存在,但尚未完全融入七夕节。而汉至南北朝文献中记载的这些关于七夕奇遇的传说,却是真正属于七夕节的传说。另外,这些故事的主人公皆为贵族,可见七夕节此时还主要在上层社会流传。
汉末三国历时较短,史料有限,未能发现关于七夕节的记载。但曹丕《燕歌行》“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25]的千古名句明确点出了牵牛织女,并以此比拟人间不得团圆的夫妇,很可能便是对牛女传说的化用。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七夕节的发展与初步普及
魏晋南北朝时期,七夕节的发展情况则比较复杂。一方面,由于社会屡遭动荡,民众无法长期安居乐业,正常的社会生活难以持续进行,这必然对七夕节的发展和普及有所阻碍。但是另一方面,在两汉的基础上,这一时期七夕节也并非毫无进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至汉末魏晋,牛女传说终于彻底融入七夕节。关于七夕节何时开始与牛女传说发生联系,学术界尚无定论。赵逵夫通过释读《周易》中《复卦》与《既济卦》后指出,卦爻辞中“七日来复”“七日得”等描述与牛女传说的情节符合,牛女传说可能早在先秦就与七夕发生了联系。[26]陈连山在对秦简《日书》进行释读后也认为牛女传说在先秦便与七夕关系密切,秦简中牵牛织女结婚的日子大概在正月或七月。[27]萧放认为七夕自汉武帝时期开始由凶日向吉日转变,而汉武帝与西王母故事中青鸟的存在为汉代人将乌鹊引入牛女传说发展出鹊桥相会的情节提供了依据,他进一步指出,七夕由凶到吉的转变与牛女传说的成熟是大致同步的,七夕这一转变在汉魏初步完成,而牛女传说也在汉魏基本成熟。[28]刘宗迪的观点前文已有陈述,他在释读《夏小正》等文献后认为织女崇拜及相关神话传说先秦时已经出现。[29]综合考量以上研究,可以发现虽然学者们对于牛女传说与七夕建立联系的具体时间意见不一,但基本都认为早在先秦时期二者就已有关联,传说与节日都经历了一个由粗疏简单而变得细密成熟的过程,而且基本同步。《淮南子》逸文中也有“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的记载。[30]但更直接的证据则是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该书在描述七夕节时,记载了某人乘浮槎见牛郎而客星犯牵牛、牵牛为娶织女借天帝钱下礼不还、汉窦太后少时于七月七日看织女而神光照室等三则传说,并引用傅玄《拟天问》等典籍对“乞巧”的仪式流程进行了讲述,这些记载都明确指出牛女是于七月七日相会、民众有七月七日向织女乞巧的习俗。[31]由此可知,至迟在南北朝时期,牛女传说已经彻底融入七夕节。
第二,在节俗形式方面,魏晋南北朝的七夕节继承汉代并有所发展,魏晋士人佯狂傲世的风气和南北朝士人诗酒风流的传统均在七夕中有所表现。魏晋南北朝的七夕节继承了汉代七夕的主要节俗,包括穿针、祈牛女、晒书、晒衣服等,并将之发扬光大,以至于留下了许多典故。比如《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了阮咸晒衣、郝隆晒书的故事,尽显狂人风范。汉代七夕虽有穿针、祈牛女的节俗,但并未言明有乞巧,到了魏晋南北朝则非但明确提出乞巧,更发展出乞福、乞寿、乞子的新节俗,向牛女祈愿的内容更加丰富了。据《太平御览》引西晋周处《风土记》载,“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酺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织女”,“乞富乞寿,无子乞子”,此外,还要吃“汤饼”。[32]《荆楚岁时记》载:“是夕,妇人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33]可见,汉代的穿针节俗被发扬光大,有七孔针,还以金、银等贵金属为针,奢靡浮华之风可见。此外,蛛丝乞巧此时也已经出现。晋张华《博物志》中甚至有关于海外岛民“其俗常以七夕取童女沉海”的记载。[34]此说可能是对当时海外岛民基于某种信仰而产生的人祭习俗之记载。
第三,在魏晋南北朝,七夕节较之汉代在上层社会更加盛行,在南朝民间和北朝也都有了一定的传播。这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果说在汉代诗赋中七夕及牛女传说只是偶尔出现的话,随着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的兴盛,七夕题材已经频繁出现在上层文人的诗文中。经笔者考证,魏文帝曹丕,西晋陆机、潘尼,南朝宋颜延之、谢灵运、谢惠连、谢庄、鲍照,南朝齐谢朓,南朝梁庾肩吾、刘孝仪,南朝陈江总等人,均有以七夕或牛女传说为主题的诗歌流传于世,如谢灵运《七夕咏牛女》诗等。而南朝梁君臣更把七夕作为御前创作的主题之一。南朝君王中,宋武帝、梁武帝、简文帝、陈后主等人均有七夕诗传世。这些诗人及其作品的存在标志着七夕节至少在当时的上层社会已经是颇为重要的节日,以至于那些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均要以七夕及牛女传说为主题或素材进行诗文唱和,尤其是在七夕节这一天。此外,《太平御览》引顾野王《舆地志》载,“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世谓之穿针楼”[35],足见穿针之俗在南朝宫廷十分流行。
在南朝民间,七夕节及牛女传说此时已经有了一定范围的传播。乐府民歌中已有关于牛女传说的内容。《七日夜女歌九首》中有“春离隔寒暑,明秋暂一会。两叹别日长,双情若饥渴”的诗句,全诗都围绕牛女传说展开,表达了对牛女一年一会的无奈和双方的相思苦恋之情。[36]《月节折杨柳歌十三首》之《七月歌》更是明确点出牛郎织女:“织女游河边,牛郎顾自叹。一会复周年。折杨柳,揽结长命草,同心不相负。”[37]这两首民歌均讲述牛女故事,并明确指出牛女相会是发生在七月初秋时。
在北朝,七夕节也拥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逐渐被北朝贵族和文人所接受。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受南朝七夕文化及游牧民族传统影响,北朝发展出七月七日讲武驰射的习俗,二是北朝文人也有写作七夕诗的行为。据《魏书》载,北方拓跋氏政权素有七夕骑射的传统,早在北魏追封的高祖、十六国代国君主拓跋什翼犍时就有“秋七月七日,诸部毕集,设坛埒,讲武驰射,因以为常”[38]的习俗。马莹指出,北魏拓跋氏坚持本族文化,将七夕讲武驰射之风世代延续,以至于成为北朝定制,每年都必须举行,形成了具有北朝特色的七夕节俗,成为史上仅有的一例。[39]此外,受南朝影响,北朝文人也有七夕诗流传,比如北齐邢邵的《七夕诗》,其中“盈盈河水侧,朝朝长叹息”“不见眼中人,谁堪机上织”等句明显是以织女为写作对象。[40]这说明牛女传说在北朝文坛也较为盛行,该诗哀婉凄美的风格更是明显习自南朝宫体诗,南朝对北朝影响之深可见一斑。除邢邵外,现存的北朝七夕诗尚有魏收《七月七日登舜山诗》、温子昇《捣衣诗》与庾信《七夕诗》及《七夕赋》等。魏诗主要抒发怀抱,内容与七夕无关。[41]温诗中有“七夕长河烂,中秋明月光”等句,明指七夕。[42]庾信的《七夕赋》也有“睹牛星之曜景,视织女之阑干”“针鼻细而穿孔”等句,描述了七夕观星、穿针的习俗。[43]
五、结语
七夕节从萌芽孕育到正式成型再到初步普及,每一步均跨越了漫长的历史阶段。通过系统梳理七夕节早期的演变历史可以发现:古代七夕节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兴的过程,其虽然在汉代才正式成型,但却在秦汉之前便开始酝酿,是受多元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七夕节的性质、主题及其早期节俗也都处于动态演变之中,七夕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喜庆的、以乞巧为主要节俗的节日;七夕节的诞生与牛女传说和织女崇拜有关联,但其发生联系的确切时间和内在的互动机制尚不确定,可以确定的是牛女传说是在魏晋南北朝才彻底融入七夕节。
据此可以判定:七夕节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从一而终的所谓“传统”,其节日性质、节日主题、节俗形式和节日传说甚至节日日期都是在文明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动态演化出来的。七夕节早在魏晋时期就因牛女传说而拥有了浓厚的爱情元素和浪漫色彩,其在当代向情人节转化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据的,从乐府民歌和南北朝七夕诗中的七夕书写可以发现,七夕节及牛女传说早就建立了歌颂爱情、抒发相思的文学传统,早就在人们心中打下了以男女情爱为作为节日主题的心理基础,只是古代中国并无情人节这种说法,但是到了当代,部分民众受西方情人节刺激和启发把七夕节当作中国情人节也就顺理成章了。
节日发展有它自己的逻辑线索和独特的生命历程,忽视节日的发展逻辑和文化基因去审视其动态演变是不客观的。对节日演变过程和发展逻辑的揭示,无疑会对我们看待和处理当下及未来的现实问题有所帮助。对于七夕节来说,只有厘清其历史源流和演变过程,方能理解其如何发展为当下的状况。在这方面还有待更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