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来自大漠的修行者
何映宇

雪漠要让现代人的心静下来。
2023年12月29日下午,著名作家、甘肃省作协副主席雪漠受邀与上海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上海市妇联一级巡视员翁文磊女士,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妇女学学会副会长郑长忠先生相约“下午茶”,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圆桌对话,围绕“爱不落下”“世界是心的倒影”“心定气闲·迎接2024”等主题畅谈创作体验、阅读人生。
第二天,他又来到上海图书馆东馆举办跨年演讲:“大变革时代如何安住?”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千名读者闻讯而至,与线上近万名读者共同见证了雪漠精彩的演讲。
从大漠走来的雪漠留着大胡子,典型的西北大汉的模样,说话却是低声低调的。
2000年,他以河西走廊为背景,描写以老顺一家为代表的西部农民物质匮乏、精神贫瘠生活画面的长篇小说《大漠祭》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
这部写了整整12年、几易其稿的作品,为雪漠赢得了“第三届冯牧文学奖”“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等十多个奖项的肯定。
迄今为止,雪漠已经创作了“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白虎关》《猎原》),“灵魂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故乡三部曲”(《深夜的蚕豆声》《一个人的西部》《野狐岭》)以及《羌村》等浓厚西部风味的长篇小说,还创作了《爱不落下》《老子的心事》《佛陀的智慧》《空空之外》《世界是心的倒影》等非虚构作品。他的作品被译为英、法、德、西班牙语等20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发行。
这些年来,雪漠越来越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智慧。当代人面临生活的压力,战争和瘟疫等不确定因素对每个人的生活造成积压,导致人们容易焦虑、缺乏安全感。因此,现代人更需要人文精神的照亮;需要修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走出心灵的困惑。
雪漠,他是来自大漠的修行者。
小时候,您家里很穷。您曾是个牧童,每天牵着村里的枣红马到湖湾里放牧。是这样的吗?
我的祖上都是农民。小时候,为了减轻父母的生活负担,我就出去放马,可以挣工分,挣点钱。
上小学时,您便显露出出色的记忆力,开学不几日,便能将所有课文背得滚瓜烂熟。家乡流传的凉州贤孝成了您重要的精神食粮。这些民间曲艺是不是对您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
小时候,我的记忆力很好,过目不忘,每天记个一两万字是很容易的。一直到三十多岁之后,有一天突然失去(强)记忆力,现在完全不行了。但是用啥,啥就来了;不用的时候,就没有了。就是没有任何念头。如果让我死记一些东西,我是记不住的,记住马上就忘掉了。
小时候,我们村里基本没有书,所以我除了课本之外,没有其他的书看。但是,我们那里有一些瞎仙会弹唱贤孝,这属于民间艺术的一种。我从小就听贤孝,自己也会演唱贤孝。贤孝的内容很丰富,有历史故事,有传说故事,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教科书。我从小就是在它的熏陶下长大的,慢慢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后来,我写了长篇史诗《娑萨朗》,主要基调就是按照凉州贤孝说唱的那种方式写的,非常精彩。
1988年,您是怎么会写作处女作中篇小说《长烟落日处》的?
1988年的时候,灵感突然找到我,我也很奇怪。现在看来,那个时候写的东西仍然很成熟。其实,那时候我刚刚学会写作,突然有一天就被一种巨大的灵感裹挟了,作品自己就流淌出来了,整整流淌了一个礼拜,最后就流出了处女作《长烟落日处》。
刚开始是灵感找我,后来我就训练着如何控制灵感,就是任何时候都有灵感。但刚开始的时候做不到,忽而有灵感,忽而没有灵感,然后通过一点一点地训练,最后任何时候都有灵感,随时能进入写作状态。其实,它是一种可控的流程。后来,我就用这种方式教人写作,叫“雪漠创意写作”,大家通过短期训练之后都能做到这一点,都能流淌出文章来。
我一般都是早上写作。晚上写作的话,往往写不太好。白天又有各种信息的干扰,所以写作效果也不是很好。而早上起来之后,大脑就好像被格式化了一样,非常清醒,这时候写作是最好的。我认识的很多作家,都是早上起来写作。早上写作和晚上写作,文字里的那种气场是不一样的,晚上的写作有种疲惫的、芜杂的味道,早上的写作非常干净、纯粹。
您写完您的处女作《长烟落日处》之后,投给《飞天》杂志,就很顺利地发表了?
是的。写完之后,甘肃的《飛天》杂志很快就发表了,于是甘肃文坛就发现了我。那时候杂志的发行量很大,有几万或几十万册,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般刊物也就发行几百本或几千本,算很好的了。而且,80年代的文学还处于热潮,人们的关注度很高。但是,发表之后,我觉得要通过修身的形式去训练,因为灵感找你的时候,那是不可控的。可控的时候,你找灵感,然后将灵感变成你的生活方式。当然,现在已经不是我找灵感,或灵感找我,我就是它,它就是我,我和它是一体的,所以写什么都很好,就始终在它里面写,不会跳出来写。
1988年,您是怎么开始创作《大漠祭》的?这部小说修改了无数遍,一开始您对自己不满意在什么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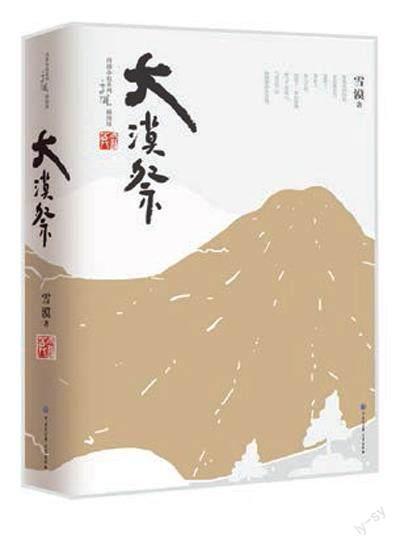
左图:雪漠作品《大漠祭》。
刚开始,因为欲望控制着你,是一种欲望性、情绪性写作。后来,我就进行训练,一边写作一边修身,这个过程整整用了五年。到三十岁的时候,心就能进去了,所以,三十岁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写作。在练笔的那个阶段,写了一遍不满意,然后再写一遍,反复不断地重写,最后达到没有“写作”概念的时候,也就是说,把写作的架势忘掉,不要那个东西,你才能写出好东西。当我一有那种写作的架势的时候,我是写不出好东西的。在技巧上下功夫的时候,看起来技巧很好,但人一看就知道你想把他抓进去,然后人就不想看了。为什么?没有真心。就好像现在搞营销的人,销售技巧非常成熟,但人一看就知道他在营销,根本就打动不了别人。好的写作,最后没有写作的概念,没有技巧,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颗真心在跳动,在喷涌。巴金就很了不起,他的东西看不出什么技巧,只有火热的激情在喷发。我的写作有点像巴金的写作,那种激情的东西自己就流出来了。
那时候,没有住房,没有写作空间,一家三口,只有10平方米的一间单位宿舍。写作条件很恶劣,怎么克服的?
刚开始调入城里工作的时候,我没有自己的房子,一家三口就住在教委的一间宿舍里。上班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写作,但人来人往,声音很嘈杂,我没有办法写作。当我请求给我分一间工作室的时候,办公室主任说,哪里惯的这种毛病?为什么有人就不能写作?他这么一说,一下子点醒了我,那么我就开始专门训练,有人的时候也能写作,也不受干扰。现在,不管是有人无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都能写作。甚至,和别人聊天的时候,我仍然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能写作。有人就说,你这时候怎么还写作?我说,我一直在写作,从来就没有走出来,一直安住在自己的世界,自然就会流出东西来。每个人只要训练,其实都能做到这一点。有时候,我讲课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它自己就在说,不是我有意地说,而是话自个儿在流,类似于脱口秀一样。西方的一些学者,将这种写法称为心流写法,它不仅是意识流,而且是智慧流,就是训练到后来的时候,任何时候都可以流出来。
在这种状态下,是不是有时候写作会很快?
是的,喷涌式的。有时候,那种喷涌跟不上思维。跟不上也不要紧,让它流去,流完之后,再慢慢修改。进入那种喷涌状态的时候,写作是非常快乐的,就是在享受生命本身,根本不会在乎写不写文章,就像马拉多纳踢足球一样,他踢足球的时候是很快乐的。
《大漠祭》《白虎关》《猎原》构成了您的“大漠三部曲”,您用这三部长篇小说构筑了自己对西北大漠的观察和思考。有评论家说您是“写大漠与人的第一人”,您怎么看?
有人甚至认为,在全世界的作家中,没有人像我那样写《大漠祭》的,我自己也坚信没有。其实,我的很多东西,放在世界的格局中,也是很独特的,这就是很多海外的翻译家喜欢我作品的原因。他一看就觉得和别人的东西不一样,生活不一样,内容不一样,技巧不一样,思想、境界也不一样,承载着东方智慧独有的最精髓的东西。它不是被别人影响的东西,而是能够影响别人、能够改变别人的一种东西。

雪漠与骆驼。
“大漠三部曲”描写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单调的社会环境,更注重自然环境的描写,而后面的“灵魂三部曲”是不是更关注内心的一种思考?
“大漠三部曲”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很喜欢。直到今天,写农民最好的是赵树理、高晓声,但很多学者认为,雪漠远远超过了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大漠三部曲”一百多萬字,定格了一个时代,那个渐行渐远的农耕时代。它不受任何标签的影响,纯粹就是一种生命的东西。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大漠祭》和《白虎关》,影响都非常大。上海有第一流的读者。各个城市的读者中,上海的读者群是非常厉害的。为什么?上海有这么多的高校,有非常好的批评家,培养了这么多有眼光的读者。很多城市没有这样的读者。一个城市的群体阅读力,超过上海的很少。所以,在上海《大漠祭》一出来,首先火了。上海读者的眼光很厉害,只要你有好东西,读者们就会认可你。其他城市有眼光,但声音太大,喧嚣太多,人静不下来读书。有些城市能静下来读书,但鉴赏力不够。所以,上海人既能沉静地读书,又有很好的鉴赏力,而且人数多,有一大批读者。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群体。
您的小说里也有大量的动物,您对动物观察细致入微,《大漠祭》里的鹰,《猎原》里的狼和羊,《白虎关》里的豺狗子都令人印象深刻,对动物的热爱,是不是也因为您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野生动物?
我小的时候,人与自然是非常和谐的。鹰、骆驼、马等,都是生活中常见的动物,它们就像伙伴一样,和你生活在一起。西部有两种东西,在上海不一定能见到,一是动物,二是神鬼的故事。像一些动物,除了动物园之外,在上海很难见到它们。但在西部不是这样,人和动物是一样的,随处可见。另外就是神神鬼鬼的故事,在上海可能听不到这些故事。所以,动物和神鬼故事,是西部文学创作中非常重要的素材。

雪漠作品《羌村》。
我尤其喜欢动物,所以在我的小说中有很多关于动物的故事。当你通过特殊的训练,真正做到“天人合一”之后,你和动物是一体的,你能感受到动物的生命,感受到土地的生命,感受到自然的脉搏。所以,“天人合一”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哲学,包括政治哲学。几千年中,像祭天祭地的仪式,像对社稷的祭拜等,这些与大自然有关的礼仪,其实都是国家非常重要的教化方式。礼仪代表着一系列的文化系统。
2023年7月,您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羌村》,这是您第一次在小说中写到居住在高山的西部中国人的世界。怎么会写这样一部小说的?
我能进入一般西部人进不去的世界。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想象力,但它不仅仅是想象力,更多的是智慧的东西。羌村那块土地,我采访了二十年,一有机会我就去那里收集素材。前幾年,在藏区我还集中生活过一段时间,我的胡须就是在那个时候白的。在那里可以睡得很好,但醒来就像没有睡过一样。有一天,一个记者采访了我,在报纸上刊登了我的照片,报纸出来之后,我的一个学生就说,您的胡子白了。我一看,才知道自己的胡子白了。因为那块土地海拔太高了,生活条件不是很好,所以住上一段时间之后,人是很容易衰老的。
后来,我写《羌村》的时候,已经收集了很多资料,大概有几千万字,那真是一个文学富矿,像大海一样深邃。《羌村》里用的只有一个故事而已,那里还有很多很多不为世人所知的故事,是我一辈子也写不完的。那么,这时候我就创造一种新的文体,才能写出我感知到的世界,并能够写活它。这个时代的作家可能会编一个故事,编得也很好,也能畅销,但是我的那个世界一般作家进不来,所以我只能创造一种新的文学叙事来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
我能进入一般西部人进不去的世界。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想象力,但它不仅仅是想象力,更多的是智慧的东西。

雪漠在相约“下午茶”活动中演讲。
您写了好几本关于老子的书。从什么时候开始读《老子》的?
十九岁的时候,我就背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逍遥游》,但那时候读不懂。后来我发现,现在读懂《道德经》的人仍然不多,包括那些所谓的解读者,也没有真正读懂老子,根本不知道老子的心事是什么。老庄的文字像电脑屏幕上鼠标的那个箭头,点一下的时候,其实是背后的程序在运行,我觉得(那些解读者)只能看到那个箭头,看不到后面的程序。但我解读《道德经》的时候,一定要将文字背后的程序写出来,这时候就和一般作家不一样了。现在的学者,大多是将《道德经》翻译成白话文,然后再进行诠释、训诂,里面的程序他也不知道,所以他写不出来。
去年,我讲了《黄帝内经》,也是讲它背后的程序。我注重道的层次,而不是术的层次。中华文明最高的是道的高度,它远远超过了西方哲学表达的很多东西。虽然一些西方哲学家也达到了道的层次,但它不是主流,而在中华文明中,道一直是人们追求的主流,是中国人向往的目标。虽然他做不到,但可以向往。如果你只在术的层面去诠释,不从道的层面去体悟的时候,那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根本性的东西,你是不知道的。其实,它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个根。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根上下功夫,从道的层面来解读老子、庄子、孔子,抛弃一些次要的东西,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根本,能够作用于心灵,作用于生命。
在现在这个时代,您觉得该怎么修身?
现在的修身要符合这个时代的特点。过去的修身可以整体化、系统化、长期化的训练,像我那时候,一天要有八到十二个小时的训练。但现在不需要了,现在需要碎片化,像卡巴金的正念冥想,就只有十五分钟。现在,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训练,坐车的时候,上下楼梯的时候,任何时候都可以训练,就是将这种生活碎片化跟修身一体化结合起来。行为上可以碎片化,精神追求上要一体化。也就是说,在一种稳定的精神状态中,可以做一系列琐碎的事情。通过专门的训练之后,这是可以做到的。
2023年12月5日,您刚刚度过了60岁生日,回顾这60年的人生,您是不是可以说已经参透了人生的道了?
我没有年龄的概念。当你达到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一种境界时,时间和空间都消失了,只有一片朗然光明的东西,这个世界仿佛消失了。所以,在这种状态中,我是记不起时间的。
我六十岁的精力比我十八岁时还要好,为什么呢?因为心属于自己了,没有杂念,生不起任何念头,只要生命存在,抓紧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别的就不管了。但是,我清醒地知道,哪些是我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因为我知道喧哗的世界都在不停地消失,沉淀在生命中的人也不多,自己该做的事就那么多,所以要珍惜自己最该珍惜的一切。现在,我每天都会在直播间和读者见面,因为我发现读者最重要。无论这个世界上有怎么样的喧嚣,属于自己的只是与生命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就消失了。
什么是人生最值得珍惜的事?赶紧写作。什么是人生最该做的事?将心中那种感悟性的、对别人有用的东西分享出去,同时培养一些优秀的孩子,此外我啥都不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