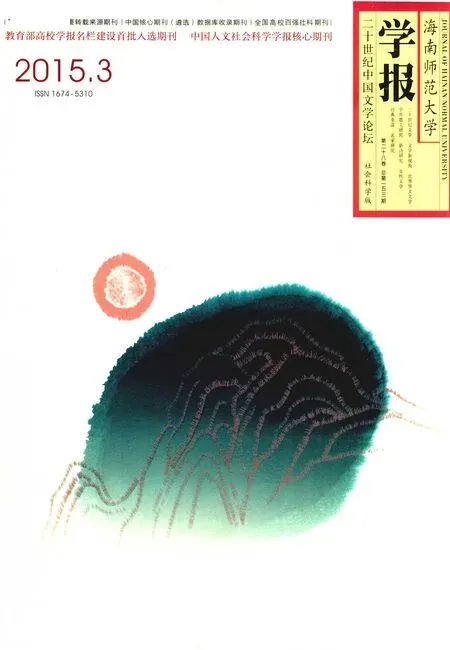雪漠及其两次“超越”
宋登安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雪漠的小说一方面展示了凉州地区的现实生活和家乡人顽强的生存意志及坚韧的生活态度,他们总是低着头进行一次次的“轮回”。另一方面,雪漠还在宏观层面上追寻西部的千年历史,其实雪漠是在追求生命的永恒,追寻历史的神性与超越。如果说阎连科的“神实主义”写作是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仰仗于神灵、精神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意思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1]那么雪漠的“神性写作”,则可称之为“佛性写作”,就是在人格的升华与超越之后对历史性神性色彩的追寻,而并非指特定的人格化存在。[2]而且,雪漠具有超越后反观现实的普世情怀,亦如觉世的苦行僧关照现实社会。雪漠从现实主义转向神性写作,进而升华至现实与神性有机融合后再对现实进行反观,这是雪漠写作手法上的两次转型,更是雪漠精神的两次超越。
一、定格农业文明的“残阳”
雪漠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他是为了真实地记录一代人的生活境遇。当一个时代随风而逝时,他抢回了几撮灵魂的碎屑。雪漠的小说,没有简单地诠释鲁迅的国民性思想,没有生硬地迎合某种声音,也没有用官僚化的思想诠释农村的生活。它只是写了河西走廊农民一年四季的艰辛生活。这种生存被写得非常鲜活:他们存在着,他们沉默着,他们已经习惯了几千年的这种生活。[3]雪漠对农业文明的描写在“大漠三部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老顺一家人的生活被雪漠呈现在了读者眼前,其中许多人物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如《大漠祭》中的老顺,《猎原》中的猛子、豁子女人,还有《白虎关》中的莹儿、兰兰等。其实老顺一家是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更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另一方面,雪漠也在关注着农村女性的命运,雪漠说,凉州的女人大都不是他心目中满意的对象,作品中的女人是作者理想化了的女性形象,她们勤劳质朴、温柔贤惠,既有柔情的一面,更有坚强的一面。她们中的这种坚强是忘记性别的坚强,是一种坚韧的坚强,一种忘我的坚强。这是生活赋予武威女人们的生命特性。《白虎关》这部小说可谓是把当代的西北妇女的苦难写得最为深刻的作品。[4]作品中的兰兰,一个美丽的人儿,被生活磨砺得如男人般坚强,在沙漠里遇到豺狗子,她毫不犹豫地抓起枪杆进行生命的搏击,一次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之后,她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这就是生命的超越,灵魂的超越。《猎原》中的豁子女人,那更是一个提得起放得下的女汉子形象。虽然平时的生活中她浪里浪气、妩媚风韵,但是豁子在井底受伤之后,她毅然担起了生活的重担,尽了一个“媳妇”该尽的责任。
雪漠的作品也涉及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家乡巨变的内容。中国作家在处理乡村生活时已经提供了很多写法,如《受活》《秦腔》《金屋》《泥鳅》等等,但比较而言,雪漠的写法更为内在,增加了一些新的东西,更具内在性,它不是一般的心理描写,而是企图揭示一些灵魂的痛苦和困惑。[5]每个人都在现实的困惑和痛苦中寻找新的出路,如走出去寻找新世界的灵官,再如与猛子一起开金窑的白狗,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新的思想意识,他们在“观望”之后也在现代化的浪潮中留下了自己尝试的痕迹。而且,雪漠更多的是描写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恶吏横行的现状,原有的农村道德的坍塌以及现代化建设对环境的破坏,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改变,对人性的扭曲等等。《大漠祭》中孟八爷向大漠伸手要钱,《猎原》中许多牧人因土地沙漠化而不得不进入沙漠求生,而他们在沙漠中与动物争夺生存资源,不免要与动物发生厮杀;《白虎关》中现代化的步伐使白虎关千疮百孔,猛子也觉得家乡慢慢地变得陌生了。雪漠对此类现象的叙述和思考,表现了一个作家的现实主义情怀和对即将消失的农业文明的惋惜。
“大漠三部曲”中,许多人在现实的逼迫下背井离乡,寻找新的出路。这种寻找的过程也是精神蜕变的过程,是对生命本质的一种叩问。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在质问自己,人活着究竟图啥?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于是作品中的主人公们不得不在现实中寻求新的出路,他们也是在寻找人生的出路。莹儿和兰兰无奈之下穿越沙漠去盐池驮盐,最后却是九死一生到达目的地,但是盐池也并非清静之地,生存的境遇还是很残酷,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迫使她们早早地离开了是非之地。如果说老家和盐池是人不让她们安稳地生活,那么两次穿越沙漠则是大自然对她们生命的拷问。在经历磨难之后,虽然对生命的意义无法界定,但是她们对世界有了新的“打量”。她们一直徘徊在生死之间,每一次的死,每一次的生都是生命的一次次升华。这也是雪漠本人对现实的深刻反思,对灵魂超越的一种追求。雪漠在《大漠祭》扉页上说:“我不想当时髦作家,也无意编造离奇的故事,我只想平平静静地告诉人们:我的西部农民父老就这样活着。活得很艰辛,但他们就这样活着。”①见杨光祖《雪漠:良知和文学的大漠》,《甘肃日报》2002年11月4日。作家的这种创作心态,是值得赞许的。
雪漠还对贪官污吏的卑鄙勾当进行了揭露,写到黑暗的现实把部分人逼入了“歧途”。如《猎原》的中的鹞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在贪官的压迫下一步步走向了犯罪的道路。但他却是一个有血性、有担当、有骨头的男人,比起“软蛆”一类的人物,他活得坦坦荡荡。同样,在《西夏咒》中,雪羽儿在经历生死之劫之后,她本想给官府反映“人吃人”的社会现状,不料却看见另一个反映者的悲惨下场。但是“老天能给,老子就能受”这种武威特色的俗语却表达了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也正是这样“韧性”的人生姿态反映出武威人不为生活所奴役的精神品格,才使武威人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子引孙”,延绵血脉。
《大漠祭》主要描写家乡生活的苦难,《猎原》涉及沙漠中的生存与死亡,《白虎关》展现了现代化进程中家乡的“变异”。“大漠三部曲”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写作,这也凸显了雪漠定格农业文明的写作姿态。雪漠在努力留住在现代化浪潮中消失的农业文明、民间文化,如“捋鹰”、凉州“贤孝”、花儿、驼队、驼道、木鱼歌等逐渐消失的民间文化和手艺,定格即将消失的农业文明。当然这里包含着雪漠本人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和关怀。
二、追求灵魂的超越
雪漠关注西部的现实社会,其作品取材于西部,既关注现实生活,也对西部未知世界进行了挖掘。“灵魂三部曲”就侧重于对西部未知世界的挖掘以及宗教教义对人的教化作用的叙写。《西夏咒》中对许多灵异现象的描写,《西夏的苍狼》中紫晓对苍狼、黑歌手的寻觅,黑歌手对娑萨朗的追寻,都是典型的神性写作。而无论是现实的武威还是神性的武威,雪漠关注的就是自己的家乡,就是大漠、农村、驼队,也就是那些即将消失的农业文明、历史和因环境恶化而不断失去的家乡。正如雪漠所言:“中国有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我们的小说为它留下了哪些东西?我只想努力地在艺术上‘定格’一种存在。当然,我的所为,也许跟堂·吉诃德斗风车一样滑稽。”[6]
许多作家常常被文学理论或是“主义”紧紧地束缚,单调地对自己的文学理念进行叙述和复制,他们无法实现对自我的突破,但雪漠是一个“异类”。他不再关注主流话语,也抛弃了所谓的“主义”,他仅仅是在书写自己的心灵,叙述地地道道存在过的历史现实。雪漠说他的写作本身也是一种修行,他要用他的生命,建立一种岁月毁不掉的价值……[7]“大漠三部曲”是现实主义的写作,生活的苦难,生存的境遇,人与动物的紧张关系,现代化建设对家乡带来的改变以及人们精神的动摇、人性的迷失和幡然醒悟等都有所涉及,这里面带有部分乡土的神性色彩。在“灵魂三部曲”中,这种神性的描写愈加强劲,这是雪漠对生命的本质发出无数次叩问后的结果。我们能捕捉到主人公对生命的责问,但更多的是一个“觉醒者”对世人的教化。雪漠在传播佛教救世、醒世的大智慧,从“人”的自我打碎走向“佛”的普度众生,这也是雪漠追求超越的必然结果,更是雪漠从小与佛结缘的必然趋势。而且,雪漠除了对乡土的描写外,也试图描写现代化的都市生活,《西夏的苍狼》就是一个范例。该作品既有凉州地方特色,也有岭南都市生活的描摹,更有对西夏国神性色彩的追寻。这是雪漠将武威文化和岭南文化相混合而进行的一次写作尝试,作者将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和寻找古老的苍狼结合在一起,现代中带着悠悠的古老气息,古老中透着神秘色彩,使得作品别有风味。这是雪漠的第一次超越。
从文学现象来看,世界范围内的魔幻题材的复兴便是其中一个表征,其实很多作家在乡土书写中往往也有返魅的一面。[8]雪漠在“灵魂三部曲”的写作中一改现实主义文风,而进行神性描写。《西夏的苍狼》中,黑歌手在追寻西夏历史和生命的超越,字里行间渗透着神性色彩、历史神秘和藏传佛教思想。雪漠在还原消失的西部历史,更是追寻生命的超越。《西夏咒》中存在三个叙述者,雪漠、阿甲以及一个“上帝”式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这种人神共语、横跨历史,将现实生活和“神”眼里的世界进行对比叙述,更具神性色彩。这是雪漠写作的创新,也是雪漠精神超越的结果。作为“灵魂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无死的金刚心》以对“信仰本体”的探索和演绎,成就了“灵魂三部曲”建构的信仰的诗学体系。很明显,这是一部信仰的寓言。[9]在写作手法上,正如雪漠所说,他是在“反小说”,在形式上寻求新的突破。如《西夏咒》的故事时间跨度加大,叙述人物复杂,情节多变,而且还有作者与作品中人物的互相问答,整部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透着十足的“神味”。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祛魅”,在现代化过程中去除神秘化和神圣化。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很多人没有了信仰,这是一个信仰与对生命敬畏缺失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需要重新“返魅”,重新建立信仰。雪漠的历史性的民间神性叙述正是自然赋魅的一种方式,或许雪漠本人认为这是一种天然的存在。诗意也好,孤独、灵魂、超越、永恒这些“雪漠关键词”也好,莫不与信仰有关。信仰,才使雪漠成为雪漠。在这个意义上,雪漠不但是个诗意的作家,更是个朝圣的作家。[10]《西夏的苍狼》中人们对苍狼的敬畏,《西夏咒》中村人对神的崇拜使人们心生畏惧和敬仰。有了心灵对自然、生命的敬畏和敬仰,人们才有所畏惧,有所收敛,人与自然才能和谐共处。最难能可贵的是,雪漠的写作不是单纯的虚构,而是经过实地调研、访谈后才动笔,“大漠三部曲”如此,“灵魂三部曲”亦是如此。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才成就了雪漠一部部的经典之作。一个真正关注灵魂领地和内心精神生活的作家,其与生俱来的气质和触机而动的灵性,经过深沉痛苦的内在磨砺,就会显示出动人的光芒。雪漠的写作历程也正说明了这一点。[11]
三、对自我的再次“打碎”
从“大漠三部曲”到“灵魂三部曲”,再到新作《野狐岭》,雪漠打碎了自己的现实主义和神性写作,这是雪漠在追问生命的本质,实现灵魂超越之后,反观现实、引导众生的人生转变。试想,一个被现实打磨雕琢,被佛教教义“腌透”后的雪漠,反观现实生活时那该是怎样的一种视野和胸怀?雪漠曾说:“我不再是作家,不再为文学所累。我之所为,就是悠然空灵了心,叫他们从灵魂里流淌出来。”[12]雪漠在观察世界,他发现了真善美,也窥探到了假恶丑,他想做的仅仅是通过自己的文学修养、佛教修为,将“善”的理念转化成文字,感染和影响世人,给世人带来快乐、安静、清凉。雪漠站在现实的对面,用自身的“所有”做一面超越现实的镜子,以此“倒影”世界,这就是雪漠。
雪漠修炼佛法,深谙佛教教义,能将佛教的教义与救世精神融入作品。新作《野狐岭》将宗教、神性、现实、哲理、智慧、推理融为一体,在写作上进一步升华。雪漠超越了现实,超越了灵魂,以一个经受了现实考验的“神”的姿态与灵魂对话,这一次雪漠又打碎了“神性写作”,将现实与神性有机融合。超越的过程最为艰辛,《野狐岭》基于现实,但又超越现实,实现了现实与神性在人物形象中的结合。作品按照作者与灵魂的对话形式展开(二十七会),每一次的对话都是按照念咒、招魂、对话、散会、总结的形式进行,这也是形式上的突破。雪漠由现实主义转向神性写作,从历史的追寻转向灵魂超越后对世人的说教,这是内在超越后的回归,雪漠回到了大漠,回到了现实;但又不仅仅是叙述现实,而是在思想升华、灵魂超越之后,继而反观现实生活的一种神性写作。犹如经历了生死之后的幸存者一样,雪漠在经历了现实的打磨、灵魂的超越后,再次回到源头,反观现实社会。这是一种博大、神圣、崇高的写作情怀。
《野狐岭》中雪漠以一个经历了现实考验、灵魂超越后的“神”的形象与世人对话,这是在经历了“大漠三部曲”、“灵魂三部曲”后的本真结果。如果说,雪漠的重心一度向宗教文化偏移,离原来意义上的文学有些远了,那么《野狐岭》走出来了一个崭新的雪漠。不是一般的重归大漠,重归西部,而是从形式到灵魂都内在超越的回归。[13]笔者认为这里的回归就是回归现实主义,回归雪漠熟悉的大漠,回归“大漠三部曲”中的真实世界,但是这种世界却是灵魂口中叙述出来的,这就延续了“灵魂三部曲”中的神性写作。更让我们惊奇的是这种神性恰恰是整部作品的结构方式。这就雪漠的再次回归,用神性组织结构,用灵魂叙述现实,用宗教反观世人。这是雪漠的第二次超越,他实现了从灵魂到“神”的再次超越。这里雪漠仿佛一个苦行僧,在恶劣的环境中寻找自己,并一次次地叩问自己的灵魂,才实现了生命的超越,追寻到了真实的自己。
《野狐岭》包罗万象,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以自己的视角叙述历史,包括骆驼一类的动物。其实,每一个人物都是雪漠,又都是读者。雪漠在作品中寻找自己,每一个灵魂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读者亦然,读者在读雪漠也是在读自己,每一个人物都是象征性的读者,每一个读者都在寻找自己,所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野狐岭》。野狐岭就是一个世界,进入野狐岭的道场就是进入人类灵魂升华的“法门”,在道场里许多人都在上演人生、寻找人生。齐飞卿在寻找革命,马在波在寻找超越,沙眉虎在寻找生存,陆富基在寻找正义;而木鱼令却是给人们带来希望和精神慰藉的“明灯”,它预示着希望,在沙尘暴来临后给人活下去的理由和信心。但是逃出野狐岭的人又能怎样呢?除了马在波和木鱼妹远离世俗躲入野狐岭外,其他的人却都不得善终,或被砍头或被批斗,这是雪漠对那个时代的叩问,也是雪漠对美好、安静生活的一种向往。雪漠希望自己是作品中的每一个人,最好是马在波,但最好别是豁子、祁禄或是蔡武,这恰好印证了雪漠作品中一惯的道德要求。文学一直与道德有不解之缘,文学总是被指称为提升人类精神品质的有效手段,这就使文学既把道德作为一种目标,也作为一种动力,甚至转化为一种标准。[14]“灵魂三部曲”中对世人的教化与此不谋而合。在《野狐岭》中,雪漠回来了,带着现实主义、神性色彩、灵魂超越、教化世人、还原众生的面目。雪漠再度回归西部,回归家乡武威。而且在经过“大漠三部曲”、“灵魂三部曲”的历练之后,在写作风格、叙述手法、布局结构上都有了新的突破。
结 语
《大漠祭》是完全的现实叙述,在《猎原》和《白虎关》中这种现实叙述发展为更高的层次,基于现实,超越叙事。雪漠着眼于人类的关爱,关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文明的消失。雪漠既有扎实的写作功底,更有超凡不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贡献了别的作家不一定能贡献的另一种东西,包括灵魂的追问、信仰的求索、形式的创新、文本的独特。[15]在“灵魂三部曲”中,雪漠在对生命本质的叩问下追求灵魂的超越。如果说“大漠三部曲”中雪漠是“人”,那么在“灵魂三部曲”中,雪漠则以一个“神”的角度反观世界。而在《野狐岭》中,雪漠再次“打碎”自己,以一个“人”的身份回来了,回到了现实主义与人文关怀,以此来还原世间众生态。但是雪漠的回归是在经历了现实中“人”的磨难和“神”对世人的洞悉和教化之后的回归。
[1]阎连科,张学昕.当代文学中的神实主义写作[M]∥我的现实我的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06.
[2]雪漠.文学朝圣:下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216.
[3]雷达.雪漠小说的意义[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06-18.
[4]陈晓明.西部叙事的美学气象与当代机遇:雪漠的《白虎关》[J].小说评论,2009(1).
[5]陈思和,等.让遗漏的金子发出光辉:“复旦声音”雪漠长篇小说《白虎关》研讨会[J].文艺争鸣,2010(3).
[6]雪漠.写作的理由及其他——《白虎关》(代后记)[M]∥白虎关.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516.
[7]陈彦瑾.雪漠关键词[J].当代作家评论,2011(3).
[8]刘大先.文学的共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6.
[9]陈彦瑾.信仰的诗学与“灯”叙述:解读雪漠“灵魂三部曲”[J].飞天,2014(4).
[10]陈彦瑾.朝圣的雪漠[N].中华读书报,2011-05-11.
[11]彭岚嘉.乡土风景与乡村情感:关于雪漠的小说创作[J].飞天,2002(4).
[12]雪漠.我的文学之“悟”——《猎原》(代后记)[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400.
[13]雪漠.野狐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封底.
[14]陈晓明.批评的旷野[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179.
[15]雪漠.杂说野狐岭(代后记)[M]//野狐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417.
——评野狐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