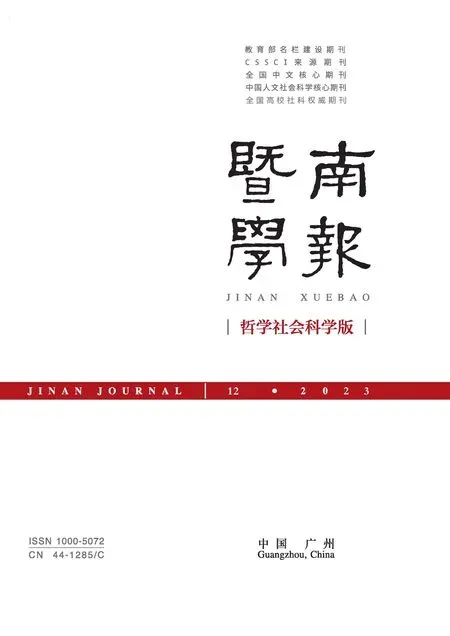中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中的制度变迁与多重逻辑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中国经验
汤 瑜,刘 哲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述评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探索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1)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几代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的基础上,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系统谋划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从生态文明思想到生态文明体制,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经验,对加强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研究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令在必信,法在必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执法体制作为确定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与环境执法部门、不同环境执法部门间职能设置、隶属关系和权力划分的具体体系和组织制度,逐步建立完善,对规范企业排污、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绿色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环境保护和环境执法提出许多新的要求。然而,以块为主的环境执法体制在落实地方政府环保责任、规范基层环境执法方面存在制度性困境,环境执法职能和力量碎片化、地方保护主义干预 、跨域联合执法滞后以及基层环境执法队伍薄弱等制约了环境制度的落实。基于此,大量体制改革指向环境执法。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在漫长的时空场域中,我国环境执法体制经历多次调整与变迁,从70年代初期的萌芽探索,发展至今已初步建立起统分结合的环境执法体制。那么,总体上我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这一过程中呈现出何种样态特征?制度演进的发生机理又是什么?深入梳理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历史轨迹,把握体制变迁的发展规律与多重逻辑,既有利于深化我国环境监管制度发展历程的认知,也有利于明晰未来环境执法体制演进的方向。
纵观已有研究,学界围绕环境执法体制改革展开了丰富讨论,并主要聚焦于两个层面。第一,价值理论分析。环境执法体制是环境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执法机构的科学设置关系到环境立法能否得到有效实施。(2)贺思源:《论我国环境执法机构的重构》,《学术界》2007年第1期。从法学角度出发(3)郭大林、张富利:《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的生成逻辑与法治构造》,《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环境综合执法改革的现实逻辑源自碎片化的执法困境,理论逻辑在于符合职权法定的正当性。从政治学(4)杨志云:《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一个组织结构整合机制的阐释》,《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和管理学(5)龚宏龄、吕普生:《环境执法权为何“逆流而上”?——基于环保案例的质性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10期。出发,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本质在于结构整合和执法权的再分配,遏制属地保护主义、协调跨域府际合作、抬高位阶强化监管权威构成了环境执法改革的理论逻辑。第二,实践应用分析。通过大量的田野观察,研究人员发现环境执法体制发挥成效的同时仍存在一些典型问题,如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权责失衡(6)张国磊、张新文:《垂直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环保部门的权责对称取向》,《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不同环境监察执法部门间职责界定交叉和职责模糊(7)刘之杰:《我国环境监察执法的现实困境与对策思考》,《环境保护》2014年第20期。;环境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不强、执法力量薄弱和法治观念淡薄等(8)聂德明、张仲华:《我国环境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S2期。。为此,学者们从法学(9)黄锡生、王江:《中国环境执法的障碍与破解》,《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和管理学(10)孙畅:《地方环境监察监测执法垂直管理体制改革:利弊争论与改革方向》,《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12期。出发,从提升权力层级、整合执法职能、强化法制保障、重塑条块关系、充实执法资源等维度,提出了破解环境执法障碍的系统性建议。当然,也有部分文献从历史角度梳理我国环境执法体制的发展过程,如刘明明(11)刘明明:《改革开放40年中国环境执法的发展》,《江淮论坛》2018年第6期。从环境执法理念、模式、体制、手段、监督与责任等角度出发,总结回顾了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环境执法的发展。杜辉(12)杜辉:《生态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法理与进阶》,《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从本体论、运行论和方法论出发,立足于政法体制和法治机制的双轮驱动,总结分析了环境执法体制的变迁逻辑与再发展的总体进路。郑石明(13)郑石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6期。从提高政治站位、推进机构改革、拓宽监管主体、完善政策法规、提高监管费用和加强监管手段等方面系统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体制改革的内容、成果与经验。
综合而言,既有文献对环境执法体制的讨论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启迪,有利于在理论与实践上加深对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理解,但仍存在进一步的拓展空间。第一,既有文献对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困境分析较多,缺少对我国环境执法体制发展现状的整体把握,缺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执法体制改革演进轨迹的系统性思考。第二,虽有部分文献对我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展开历史性分析,但侧重于经验总结与法理阐释,对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演进阶段与演变逻辑的深层次剖析不足。鉴于此,本文以政策网络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为基础,进一步结合我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构建“社会情境—参与者网络—制度系统”的分析框架,系统梳理我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政策及实践,旨在揭示其演进轨迹、特征与逻辑。
二、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一)政策网络理论的分析范式
20世纪70年代,作为解构复杂政策过程的分析手段,政策网络理论在美国兴起,并逐渐流行于欧美学界。在此之前,政策研究围绕政府官员、利益集团和国会议员构成的“亚政府”和“铁三角”展开,他们在政策制定中结成利益联盟并影响政策走向。1978年,赫克洛(14)Hugh Heclo,“Issue Networks and The Executive Establishment”,in A. King ed.,The New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Washington,DC:AEI.1978,p.104.提出议题网络的概念,强调政策决策过程中除了稳定封闭的铁三角外还存在数量众多的公众、专家以及大众传媒等松散社群。同年,卡岑斯坦(15)[美]彼得·J.卡岑斯坦:《导论:国内和国际力量与对外经济政策的战略》,彼得·J.卡岑斯坦主编,陈刚译:《权力与财富之间》,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版,第28页。在《权力与财富之间》中首次提出规范的“政策网络”概念。此后,政策网络研究逐渐丰富、成熟。简单地说,政策网络是分析政策制定过程中多元主体复杂关系的一种工具,其功能在于解构政策制定各阶段多元主体的互动、博弈和妥协行为。目前,西方政策网络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分别是基于资源依赖的政策网络、共同价值的政策网络和共享话语的政策网络。(16)范世炜:《试析西方政策网络理论的三种研究视角》,《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4期。虽然上述研究视角认为组成政策网络的链接纽带不同,政策过程中主体的行动资源和互动策略也存在差异。但相同的是,它们均认同政策变迁是网络主体互动博弈的结果,并且这一过程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和约束,外部环境将通过政策网络的中转和调节影响政策结果。其实,政策制定的过程也是政策变迁的过程。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环境的改变,政策网络中平衡的利益格局会被打破,这将引发新一轮的博弈、冲突和妥协,直至新政策的产生。
总体而言,政策网络理论对多元利益主体的关切跳出了国家中心主义与社会中心主义、法团主义与多元主义的理论争论,为重构国家—社会关系、解构政策制定过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但政策网络理论在聚焦成员互动过程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原有制度安排的结构分析。具体而言,政策网络理论强调网络联盟(网络子系统)与外部环境互动博弈对制度变迁的影响(17)[美]保罗·A.萨巴蒂尔、[美]汉克·A.简金斯—史密斯:《支持联盟框架:一项评价》,保罗·A.萨巴蒂尔主编,彭宗超等译:《政策过程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10页。,但它却缺少对制度历史和制度结构的讨论,即忽略了现行制度安排的制度惯性对维持制度动态稳定的作用,同时也忽略了现行制度内部结构失衡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进路
历史制度主义被认为产生于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直接批判,其核心是强调制度变迁中国家、政府和其他组织对个体行为的影响。(18)杨光斌:《政治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历史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指的是那些对行为产生构造作用的正式组织与非正式规则及程序。(19)凯瑟琳·西伦、斯文·斯坦默、马雪松:《比较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它既包含宏大的国家结构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秩序,也包含组成国家的具体制度和微观组织。(20)G. John Ikenberry,“Conclusion: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1,1988,pp.219-243.关于制度变迁,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要点集中于结构观和历史观。在结构观上,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的结构性安排对政策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任何一项制度的生成或调整都在特定的制度场景中发生,是特定阶段制度结构的产物。不同制度之间的排列方式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制度结构,其中一项制度的调整可能会导致与之相关制度的变迁,不同制度之间的结构不匹配可能会引发制度结构震荡。在历史观上,历史制度主义重点关注维持制度长期稳定、阻碍制度变迁以及推动制度创新的历史性因素,它们分别对应了历史制度主义中的路径依赖、路径锁定和关键性节点。具体而言,历史制度主义强调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即过去的历史事件或政策选择会影响当前的政策方案,传统越重,路径依赖越强。一旦选择某种制度模式,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制度模式会愈发稳固,从而陷入锁定状态。(21)汤瑜、于水:《项目下乡为何总陷“精英俘获”陷阱——基于苏北S县的实证研究》,《求实》2021年第5期。要想实现制度变迁,需要技术创新、政治力量冲击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等创造制度断裂的关键节点。
总的来说,历史制度主义通过对旧制度主义和行为主义的继承和吸纳,构建了以制度为基础的中层理论,弥合了微观行为分析和宏观制度分析的间隙。然而,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因素的强调多少有些制度中心主义和制度决定论的意味。尽管它并不忽视个人偏好以及多元主义的团队动力,但它认为个体偏好的形成和选择、团体互动的方式和结果由人所处的制度环境构造和决定。(22)杨光斌:《政治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23)凯瑟琳·西伦、斯文·斯坦默著,马雪松编译:《比较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这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多元行动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决策者偏好的影响,同时忽略了偏好变化导致的制度变迁。
(三)一个整合的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制度变革引起了学者广泛讨论,其中政策网络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采用较多的理论视角。然而,如前所述,既有理论在深化制度变迁认识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水土不服”,即上述理论视角似乎都解释了我国制度变迁的某一界面,但难以廓清制度变迁的完整形态。因此,吸收不同理论的学术要点,构建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具有理论上的必要性。经验表明,我国环境执法制度的建立离不开官厅水库污染事件、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等历史事件的推动。同时也难以摆脱财政分权体制和考核晋升机制的影响,遏制地方政府的“逐底竞争”一直是新世纪我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除了外部情境的影响,环境政策决策系统的内部博弈也是影响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和财税增加是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此时地方政府与钢铁、冶金、焦化等工业企业的关系较近,即使出现环境污染,环境执法也多以事后处罚为主。尽管中央政府(部委)已经意识到这一时期环境执法属地管理的弊端,但调整环境管理体制仍然困难重重。随着社会舆论、环境参与以及领导注意力的持续走高,政策系统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调整,环境执法体制出现大的调整。当然,环境执法体制的制度系统自身也是影响制度变革的重要力量。例如,环境、城建、国土、水利、农业等职能部门环境执法制度的不匹配便是“小环保”变成“大环保”的重要动力之一,而长期实行以费代税、以罚代管、属地执法的制度惯性则使得环境执法体制的调整限定在较小范围内。

图1 环境执法体制变迁的分析框架
综上,本研究以政策网络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为基础,结合我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构建“社会情境—参与者网络—制度系统”分析框架,以厘清中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发生机理。如图1所示,社会情境既包含相对稳定的基本政治制度、基础社会结构、自然资源和文化特质,也包含波动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公共舆论、环境质量)和历史事件;参与者网络包含政策过程中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专家、公民、媒体和社会组织等主体,多元主体的互动、冲突、联合会影响政策变迁的方向和结果,也会引发社会情境和制度结构的变化;制度系统包含初步成型制度的制度惯性,也包含不同制度间的结构匹配度。总体而言,三种理论元素既独立驱动环境执法体制改革,同时也相互联系,以组合叠加的方式共同推动环境执法体制调整。
三、历史轨迹:中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
历史地看,从1972年我国建立以各级卫生防疫站为中心的环境监测网络与监测制度到2018年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五十余年里我国环境执法体制从摸石头过河逐渐向扩权增能完善。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24)王刚、高启栋:《地方政府何以跟进中央的机构改革?——基于海洋机构改革的组织学分析(2018—2020)》,《中国行政管理》2023年第1期。,本文从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管理体制三个维度出发,将中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划分为探索起步、继承发展、渐进调适以及创新完善四个阶段(见表1)。

表1 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历史轨迹
(一)探索起步时期的三废管理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环境执法工作发展缓慢,这一阶段政府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主,环境保护和环境执法较少进入政策议程。随着西方环境公害事件的密集爆发,1970年前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开始研究我国工业发展中的环境公害问题。据曲格平统计,为了唤醒各方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从1970年到1974年,周总理围绕环境保护至少发表31次讲话。(25)于勇、李焱:《周总理“逼”出了新中国第一代环保人》,《经济日报》,2015年1月12日。1972年初,官厅水库污染事件爆发,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逐渐开展“三废”管理,并初步建立了“三同时”制度和环境监测体系。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的环保工作拉开序幕。1974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主要聚焦环保政策、计划和方针的制定。1979年9月,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环境保护“32字方针”确立。1982年,国家建委和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等五部门合并,组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并内设正厅级的环境保护局。1985年,国家环保局成立征收排污费管理办公室,统一管理全国排污费征收工作,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执法开始出现。此间,各地区政府相继成立由本级政府领导的三废治理办公室和环境保护办公室,探索三废监督管理工作。但总体来看,环境监管要求不高,力度不大。
(二)继承发展时期的环境监理
1986年5月,国家环保局开始第一批环境监理试点工作,推动排污收费队伍向环境执法队伍转变。1988年7月,环境保护局从城乡建设部分离,正式成为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职能部门,其内设的开发监督司(1994年2月更名为监督管理司)负责三废管理工作,政策法规司负责环境立法与执法指导。1989年12月,正式的《环境保护法》出台,明确了环境规制中的属地管理原则。1998年6月,国家环境保护局升格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为国务院正部级直属机构。具体到地方的环境执法工作,1991年,国家环保局颁布《环境监理工作暂行办法》,排污费征收职能由环境监理机关继承,同时进一步承担监督、检查和处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事件的职责。根据政策规定,各地区环境保护局相继内设排污收费监理站或环境监理所,主要负责排污费征收,并辅之以环保处罚职能。1996年11月,《环境监理工作制度(试行)》和《环境监理工作程序(试行)》颁布,对环境监理机关的工作规则、监理程序、职能职责和上下级关系等做出确切规定。1999年,国家环保总局发布通知,要求统一规范省市县三级环境监理机构设置,进一步强化环境监理职能。在这一时期,环境监理机构在各级政府领导下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环境监理人员的管理权限在同级政府,业务上接受上级监理机构的监督和指导。
(三)渐进调适时期的环境监察
为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树立执法权威,2002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印发通知,要求将各级环保局(厅)所属的环境监理机构统一更名为环境监察机构。2003年3月,国家环保总局决定开展环境监察试点工作,旨在建立生态环境监察执法机制,使环境违法案件得到有效查处。同年10月,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成立。2008年,国家环保总局从国务院直属机构调整为国务院组成部门的环境保护部,政治地位大幅度提升。在这期间,为进一步强化上级监督,减少地方政府干预,2003年至2008年国家环保总局先后成立六大区域督查中心。2010年1月,《环境行政处罚办法》颁布,规定环境监察机构在环境主管部门委托下实施行政处罚。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2016年,伴随着中央环保督察的全面展开,省以下环保机构垂直管理改革于9月启动试点,旨在增强环境监测监察执法的独立性、权威性和有效性。总体而言,为了扭转地方领导发展理念,减少地方环境保护主义,这一阶段环境监察工作的整体趋势是渐进增强中央政府的监督和约束。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时期环境执法体制属地管理的特征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管理体制上仍表现为“以块为主、条块结合”。即使部分地区如大连市1994年、安康市2006年、汉中市2006年、沈阳市2008年开展了环保垂改,但均局限于市级以下环保部门,同时部分区县环境监察大队的人财物管理仍归属县级政府,针对环境执法体制的垂直管理并未彻底完成。(26)赵琳、唐珏、陈诗一:《环保管理体制垂直化改革的环境治理效应》,《世界经济文汇》2019年第2期。
(四)创新完善时期的环境执法
2018年1月,《环境保护税法》正式施行,沿袭多年的排污收费制度改为环保税,环境监察部门的排污费征收职能相应剥离。2018年3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发布,提出整合分散的环境保护职能,统一行使环境执法职责,组建生态环境部。同年8月,生态环境部“三定”方案出台,国家环境监察局改为生态环境执法局。3个月后,《关于统筹推进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发布,各省环保垂改工作全面推开。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整合相关部门环境执法职能,统筹环境执法资源和执法力量,将县级环境执法机构转变为市级派出机构,由市执法支队统一管理人财物资源,市级环境执法支队由“双重管理、以块为主”调整为“双重管理、以条为主”。在这一时期,环境执法体制从属地管理变更为垂直管理。2020年3月,生态环境部印发《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明确了248项环境执法事项的职权类型、责任部门与第一责任层级。2021年6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重点推进环境执法队伍现代化、专业化和制度化建设。目前,环境执法体制改革“后半篇文章”稳步推进。
四、演变特征:中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样态呈现
回顾中国环境执法体制五十余年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随着不同时期社会环境和政府工作重心的调整与转换,环境执法体制始终处于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中。虽然环境执法部门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管理体制几经调整,但环境执法体制却能在变与不变之中维持平衡,并在改革主线、改革过程、改革模式和改革趋势上彰显独特的演变特征。
(一)强化监督与推动综合执法的改革主线
通览环境执法体制改革轨迹,始终围绕强化上级监督和推动综合执法的主线双轨并进。两条主线犹如硬币两面,没有主次区别,同等重要,二者统一于实现更好的环境执法这一目标。一方面,针对基层环境执法的上级监督持续增强。从环境监理时期开始,上级环境监理(监察)机构便承担对下级环境执法行为的指导、检查和监督责任,定期开展环境稽查。此后相继成立的六大区域督查中心和中央环保督察办公室,也是中央政府持续加强上级监督,遏制基层政府和环境监察机构不作为的有力举措。当然,除了强化对基层环境执法行为的直接监督外,中央政府还逐渐增加对企业生产、排污和用电量,以及区域气水土质量的数据监测,减少信息不对称,强化间接监督。另一方面,历次机构改革中不同部门的环境执法职能持续集中。总体上,环境保护机构经历了七次机构改革。在这过程中,核污染防治、机动车污染防治、农村生态保护、生物技术安全、地下水污染防治、流域水环境保护、排污口设置管理、海洋环境保护等职能逐渐向环境部门集中,环境部门职能从“小环保”变成“大环境”。与之对应,农林水利海洋国土交通科技等部门的环境执法职能也逐渐向环境执法部门集中,执法职责、力量和资源的配置向整体、综合迈进,多层执法和多头执法行为逐渐减少。
(二)改革过程中呈现“间断—均衡”演变
历史地看,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过程通常表现为一种稳定和渐进主义的态势,但偶尔也会出现不同于过去的重大制度变迁。(27)[美]詹姆斯·L.特鲁、[美]布赖恩·D.琼斯、[美]弗兰克·R.鲍姆加特纳:《间断—平衡理论:解读美国政策制定中的变迁和稳定性》,保罗·A.萨巴蒂尔主编,彭宗超等译:《政策过程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版,第125页。就长期均衡而言,环境执法体制经历大的变革后通常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即使经历制度调整,也发生在较小范围,大的制度方向不会转变。另外,虽然政策均衡期内会出现制度调整,但制度调整的过程是缓慢的,常按照“试点—反馈—修改—推广”的路径渐进发生。以执法机构的管理体制为例,长期以来一直为属地管理模式,在这过程中虽然通过区域督查、环保督察、巡视、数据监控等手段一步步强化上级政府监督,约束地方政府权力,但是彻底的体制转变直到2018年才发生,此前还经历了多轮改革试点。就短期间断而言,环境执法体制有时会受到社会环境、突发重大事件、制度结构失衡以及新的行动者等单一或综合的影响,一旦这种影响形成足够的压力,中央政府便舍弃原有的制度设计并对其做出重大变革。但是变革发生后,制度会重新变得保守,从而维持政策的稳定和连续。从1970年至今,在5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环境执法体制仅发生过四次大的制度跳跃,每一次变革后环境执法体制又保持了长期稳定。
(三)改革模式上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结合
制度变迁模式包含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前者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代替,或者新制度安排的创造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与实行;后者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制度变迁。(28)Lin Justin Yifu,“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Induced and Imposed Change”,Cato Journal,Vol.9,No.1,1989,pp.1-34.从改革模式看,中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实践既存在政府主导政策供给下的强制性变迁,也包含由社会需求、技术进步引导下的诱致性变迁。以环境执法体制初建为例,70年代初期,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环境污染,工业污染只在资本主义国家有。虽然此时工业三废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但环境执法体系建设存在较大阻力。因此,这一时期环境执法体制的探索和起步,依赖于党中央自上而下的领导、组织和协调,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令主导着这一时期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但是,中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阶段演进并不局限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革,而是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革相结合。以环境监理为例,在《环境保护法(试行)》指导下,排污费收费工作逐渐展开,但执法不力、执法不严现象大量存在。原因之一是缺乏专职的环境执法队伍。因此,各地环境执法部门积极探索,以排污收费监理、环境监察、消除烟尘大队以及城管大队环境监理分队等形式探索环境执法。1986年,自下而上的改革需求得到回应,中央政府开始环境监理试点,以排污费征收队伍为基础打造环境执法队伍。
(四)专业化、独立化与法治化的改革趋势
第一,改革趋势上的专业化。从表1可以看出,环境执法体制改革过程中环境执法机构的职能从排污费征收,到排污费征收为主、辅之环保处罚,到排污费征收与环保处罚并行,再到专司环保处罚,机构职能经历整合、调整与剥离后逐渐清晰专业。第二,改革趋势上的独立化。在中央层面,环境执法机构历经征收排污费管理办公室、开发监督司和政策法规司、监督管理司和政策法规司、环境监察局、环境执法局五次机构调整,逐渐从环境保护局的内部科室演变为机关司局,机构的主体地位逐渐清晰。在地方层面,环境执法机构的管理体制经历属地管理向垂直管理转变的过程,县级环境执法机构从县级职能部门转变为市级派出机构,市级机构从上级指导转向上级主管,基层环境执法机构逐渐脱离基层政府控制。第三,改革趋势上的法治化。环境执法从起初依据《环境监理工作办法(暂行)》到《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再到《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环境执法的法律依据逐渐清晰完善。同时,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法治化特征还表现为依法执法和违法必究,环境执法过程中的外在干预受到持续压制,自由裁量权的使用逐渐清晰规范。
五、多重逻辑:中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发生机理
总的来说,我国环境执法体制经历了探索起步、继承发展、渐进调适以及创新完善四个时期,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管理体制出现不同程度的调整和转型。此间,社会情境的外部干预、参与者网络的内部博弈以及制度系统的结构性影响,构成了我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演进变迁的多重逻辑,三类元素单一或综合地形塑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和结果。
(一)社会情境的外部干预
社会情境是制度变迁的背景与底色,既影响行动主体的行为和选择,又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和结果。在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重大历史事件、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经济和社会环境、文化特质等深刻影响着制度变迁。新中国成立初期,受经济发展战略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影响,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存在环境问题。因此,这一时期政府部门并未开展环境保护和执法活动。1972年,官厅水库污染事件爆发,该事件直接促进了“三同时”制度、环境监测体系以及跨域环境监管机制的建立。同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环境污染问题逐渐引起中国政府重视。2001年7月26日,《焦点访谈》曝光南水北调水源地旬阳县铅锌矿企污染汉江的问题,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2天后,旬阳县13个铅锌选矿厂全部关闭,相关设备被拆除。为遏制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冲动,改变环境执法部门的弱势地位,2002年陕西省出台《市以下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意见》(简称《意见》)。《意见》指出陕西省环境部门实行市以下垂直管理,县级环境部门的人事权和财政权上划,改为市环保局的派出机构或直属机构。可以说,国内外重大的历史事件直接推动和加速了我国环境执法体制的形成及其变迁。
此外,外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也是影响制度变迁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企业因缺少经营自主权和投资决策权而不具备独立法人地位。因此,虽然企业的生产活动造成了环境污染,但涉事企业并非责任主体。虽然70年代初期我国已经成立三废管理部门,但这一时期的环境监管系统却并不能进行现场监督执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全面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成为独立法人,现场环境监督执法具有现实需要,1986年环境监理应需而生。改革开放以来,在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宏观制度性约束下,官员晋升的“GDP锦标赛”催生了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单极发展逻辑,“逐底竞争”和地方环境保护主义问题屡禁不止。表现在生态环境上,我国水污染、空气污染和土壤污染事故密集暴露。根据《中国环境年鉴》数据,从1993年至2010年,中国各地区共计发生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30 349次,年平均1 597次。(29)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环境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而得。密集的环境污染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雾霾更是成为2013年年度关键词。鉴于此,环境执法体制进一步调整,在职能配置上进一步增加环境监管执法职责,在管理体制上进一步强化上级监督和约束。此后,随着市场、交通、农业等六部门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以及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实施,环境执法体制与其他制度匹配均衡的状态被打破,环境执法体制迈出新的改革步伐。
(二)参与者网络的内部博弈
制度是创造出的制度,制度的生成和变迁无法脱离政策主体而独立存在,它是多元行动者互动博弈的产物。在中国环境执法体制的演进过程中,涉及的行动者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排污企业、专家、公众、环保组织以及大众传媒等,可以划分为政策社群、议题网络、专业网络、生产者网络和府际网络五类网络联盟(图2)。就我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参与者网络的影响。

图2 环境执法体制改革中的网络互动关系
第一,政策社群内的价值理念存在分化并且随社会情境动态调整,继而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在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演进历程中,政策社群内的行动者包括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发改、财政、城建、国土、农林、水利、海洋、环保等部委。环境执法体制改革涉及环境部门政治地位和执法职权的调整,严重影响其他部门利益。因此,环保部门单一主体很难推动制度变迁,需要高层权威的首肯和支持。(30)郭哲、曹静:《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历程与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湖湘论坛》2020年第2期。改革开放初期,政策社群的主要价值理念是经济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环境部门的地位相对处于弱势,环保工作为“小环保”,环境执法为“虚位执法”。十八大以后,随着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布局,政策社群的主要价值理念转为发展与环境并重,这为环境执法体制改革提供了观念支持和政治支持。
第二,由于情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行动者的有限理性和自利性,网络联盟间的关系是动态调整的,从而影响制度变迁的结果。政策社群是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关键力量并发挥决定性作用,随着外部环境以及内部力量的调整,政策社群时而摆向府际网络和生产者网络,时而摆向议题网络和专业网络。相应地,环境执法体制在“事后处置、被动应对为主”和“全链条监管、积极作为为主”之间动态调整。具体而言,2000年以前,中央实质财政能力较为薄弱,实现财税收入的增加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期待,此时中央政府摆向地方政府和工业企业,环境执法偏向事后监管,处罚为主。新世纪以后,中央实质财政能力大幅度提升,对财税收入的迫切度有所下降。此外,频繁的污染事件提高了环保意识,也扩大了环境参与。根据《中国环境年鉴》数据,2003年至2015年间,年均公民环境来信39.3万封,来访5.7万批次。(31)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环境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而得。面对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调整,政策社群向议题网络和专业网络倾斜,环境执法体制向强化监督和严格执法转变。
第三,在制度调整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行动者拥有足够能力决定其他行动者的行动策略,所有行动者都有各自的目标与偏好,各行动者根据资源和力量的多寡能动的影响制度变迁。(32)朱春奎等著:《政策网络与政策工具:理论基础与中国实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在环境执法体制改革中,府际网络和生产者网络凭借前期积累的巨量资源和科层制的信息优势,在环境执法体制改革中具有重要发言权,从而维持了长期的属地管理体制。专家、媒体、公众和社会组织构成的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资源和力量相对匮乏,主要通过社会舆论影响环境执法体制变革,作用较小。但重大历史事件是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影响制度变迁的契机,他们通常借环境危机和政治事件,如淮河水污染、太湖蓝藻危机、2011年北京雾霾等,影响政策社群,进而影响环境执法体制改革。
(三)制度系统的结构性影响
制度是历史的制度,既有的制度安排在历史演变中具有黏性和惯性。在报酬递增、自我强化、学习效应、协同效应、沉没成本的作用下,旧有的制度、经验、资源都会对体制变革产生影响,使得制度变革呈现动态稳定性。所谓动态稳定性,指的是既有的制度安排或制度系统在受到外部干预或内部博弈影响后,在制度黏性和制度惯性的作用下能够通过微小调整使制度变革保持在较小范围,不出现大的波动。在环境执法体制的演进历程中,排污费征收制度的调整较为明显地体现了这一逻辑。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首次提出“按规定收取排污费”。1982年《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中正式确立排污收费制度。2003年,国务院废除此前的暂行办法,出台《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及配套管理办法。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颁布并生效,排污收费制度正式取消。虽然排污费制度长期存在执法刚性不足和地方政府干预等问题,两会代表也多次提出关于征收环保税的议案,但环保税从“研究开征”到正式颁布历经12年。此间排污费征收标准虽有所调整,但征收机关和征收形式却并未发生变化。
环境执法体制是一个大系统,环境执法体制内部制度的结构匹配或失衡均会引发制度变迁。(33)王智睿、陈纪:《中国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脉络与发生机理——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的考察》,《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9期。其中制度结构的匹配(耦合协调)可以阻隔外部冲击和内部博弈产生小的扰动,使得制度系统不发生持续震荡,而制度结构的不匹配或失衡则会引发制度变迁。以环境保护和城乡建设制度结构失衡为例,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决议》。根据文件要求,成立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将国务院原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撤销,其办公室并入城乡建设环境部并调整为环境保护局。然而,这一调整却间接剥夺了环境管理机构的独立监管权。同时,由于取消了国务院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层级较低的环境保护局又无法有效统筹跨部门的环境保护工作。鉴于此,1984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成立,同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内设的环境保护局改为国家环保局,前者领导协调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后者作为前者的日常办事机构。经过此番调整,环境执法体制内部制度结构不匹配问题有所缓解。但由于国家环保局仍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下属的国家局,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职能分野问题仍然存在。因此,1988年环境执法体制再次调整,国家环保局独立于城乡建设部,成为国务院直属部门,至此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制度失衡问题解决。
六、结论与讨论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单纯的环境立法并不能显著抑制污染排放,环境立法的有效性有赖于环境执法的严格度。(34)包群、邵敏、杨大利:《环境管制抑制了污染排放吗?》,《经济研究》2013年第12期。法贵在行,也难在行,基层环境执法中的政企合谋、变通式应对和运动式执行屡禁不止。推动中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建立统一、独立、权威、有效的环境执法体制有利于遏制地方环境保护主义,严格环境执法。长期以来,中国环境执法体制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稳步推进的历史进程中得以发展完善。通过对其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管理体制演变规律的梳理总结,本文认为环境执法体制改革总体上经历探索起步时期的三废管理、继承发展时期的环境监理、渐进调适时期的环境监察以及创新完善时期的环境执法四大阶段。此间,环境执法体制在改革主线上呈现强化监督与推动综合执法特征,在改革过程中呈现“间断—均衡”演变特征,在改革模式上呈现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结合特征,在改革趋势上呈现专业化、独立化与法治化特征。通过建立“社会情境—参与者网络—制度系统”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中国环境执法体制变革是社会情境的外部干预、参与者网络的内部博弈以及制度系统的结构性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实,就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历史演变而言,历史制度主义、政策网络理论、政策范式理论、支持联盟框架、间断均衡模型、多源流理论以及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似乎都可以回答环境执法体制变迁的发生机理是什么这一问题。但这些“都可以”正反映了西方制度变迁理论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35)张翔:《城市基层制度变迁:一个“动力—路径”的分析框架——以深圳市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的发展历程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18年第4期。因此,本研究没有拘泥于采用单一理论来解释中国环境执法体制为何历经调整,而是立足于中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具体的实践经验,通过吸收既有理论中的关键元素,提炼出社会情境、参与者网络、制度系统三个分析要点。在强调国内外重大历史事件、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经济环境、文化特质、社会环境(社会舆论和生态环境质量等)等外部影响的同时,充分关照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工业企业、公众、大众传媒、社会组织、专家智库等政策主体的内部博弈过程及其作用,同时肯定制度系统本身的惯性以及结构匹配度对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影响。这一分析框架统合了既有理论中情境、参与者、制度分析的分野,有利于拓展中国场景下制度变迁研究的知识边界。
回顾环境执法体制改革历史,我国环境执法体制正朝着机构更加独立、执法更加严格、府际合作更加协调的方向发展。鉴于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压力叠加和环境质量根本好转尚有差距的现实挑战,未来我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仍需进一步完善、巩固和提高。首先进一步完善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方案,优化顶层设计,强化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和环境垂直管理改革的制度衔接,加强日常执法、专项执法和督查巡视的有机协同,推进环境、海洋、国土、农林、水利部门执法人员编制划转。其次进一步加强环境执法基础能力建设,加强环境执法队伍思想建设和专业能力建设,补齐环境执法装备配置短板,推动环境监测执法信息数字化与信息整合。然后进一步明确不同部门、不同辖区环境执法职责配置,减少水资源监管职责交叉界面,增强地下水、各级支流、跨域断面的监测执法,推动重点区域府际合作执法常态化。最后,进一步强化基层环境执法监察机制和行政相对人申诉机制建设,构建社会力量参与污染防治和污染监管的程序化平台通道,发挥环境治理多元主体的实质性作用。
总体而言,中国环境执法体制演进过程曲折复杂、宏大独特。本文虽然在政策文件和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演进轨迹、演进特征和演进逻辑做了些许补充完善,但在规律把握和理论拓深方面仍力有不逮,例如对历史事件的前后过程和复杂关系摹刻不足;对多元主体互动过程的分析仍稍显简单,可能影响机理分析的丰富度,未来需要结合问卷资料和访谈资料做更深入、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