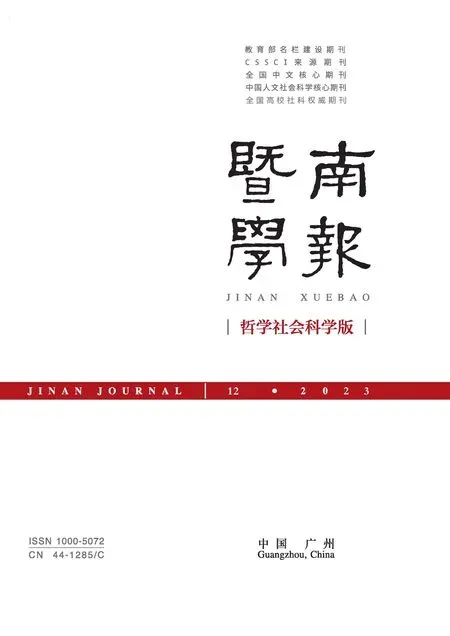国际法视域下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模式转型与中国贡献
冯 帅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在人口剧增、陆地资源被大规模开发利用之后,海洋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后空间。但是,随着人类活动增多,海洋的环境压力日渐加大,并超过自身净化与修复能力,由此引发一系列海洋生态环境问题。通常来说,这些问题包括两类:一是海洋生态破坏;二是海洋环境污染。前者表明海洋资源因不合理或超强度开发利用而导致原有平衡被打破,包括生态系统紊乱、生物多样性锐减、部分物种灭绝等;后者指海洋空间因不当使用而导致海水质量明显降低,包括陆源废弃物入海、大气污染物沉降、近海富营养化加剧等。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制定“区域海洋计划”以来,该问题确实得到一定缓解。不过,在全球风险社会,这一方案逐渐“失灵”。换言之,在风险泛化且高度复合的现代社会,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与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因素交织在一起,逐渐走向“失控”。2019年,联合国发布《世界海洋评估》(WOA II),强调,2012—2017年海洋渔业捕捞数量增加了30%,且70%以上为过度捕捞。(1)United Nations,The Second World Ocean Assessment (Volume I),United Nations,2019,pp.163-171.2021年10月,UNEP发布《从污染到解决方案: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全球评估》,指出,目前海水中约有0.75亿~1.99亿吨塑料垃圾,占垃圾重量的85%,若不采取有效行动,到2040年,每年将新增0.23亿~0.37亿吨塑料垃圾,增幅达200%。由于这些塑料持久性强,且能通过浮游生物来改变碳循环,故它们一方面对海洋生物和人类健康与福祉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也深刻影响着世界气候。不仅如此,考虑到经济和市场因素,到2040年,海洋资本损失额将达2.5万亿美元/年——显著加大了全球经济隐性成本。(2)UNEP,From Pollution to Solution:A Global Assessment of Marine Litter and Plastic Pollution,Nairobi,2021,pp.38-43.固然,这些为人类活动的累积性后果,但从根源上来看,应归于现有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具言之,现有模式无法满足治理需求,导致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乱象丛生,并在“问题—治理”逻辑下陷入“恶性循环”。是以,要有效纾解这一问题,还需基于系统论视角,对现有模式予以反思。
对此,有学者提出了“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概念,并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在使用语境上,强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普遍性,并将其作为一种规范表达;(3)全永波、叶芳:《“区域海”机制和中国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Harris P. G.,International Equity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Power and Principles in U.S. Foreign Policy,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7.二是,基于功能主义,以协作机制的构建作为优化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突破口。(4)李昕蕾:《全球海洋环境危机治理:机制演进、复合困境与优化路径》,《学术论坛》2022年第2期。Vatn A.,“Environmental Governance-from Public to Private”,Ecological Economics,Vol.148,No.3,2018,pp.170-177.诚然,这些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但它们既没有从结构上揭示海洋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也未能在逻辑上深入分析现有模式的滞后,更没有就模式转型给予充分关注。故而,本文坚持问题导向,在“理论—制度—实践”的研究框架下,以模式分析为主线,系统考察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两种选择,并据此还原出两种模式——在解读区域治理模式的法律安排并澄清其体制困局之时,论证全球治理模式的基本逻辑、价值期待及其功能预判,同时理清中国的贡献范围与作为空间,以期重塑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运行机制,通过全景式、统合性治理体系的构建,促进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之实质改善。
二、海洋生态环境的区域治理安排
区域是一种社会历史单位,而区域治理是基于世界地理特征和族群分布而以区域为单元、以善治为目标的社会实践。(5)张云:《东南亚区域安全治理研究:理论探讨与案例分析》,《当代亚太》2017年第4期。故海洋生态环境区域治理是通过区域内国家权力的部分让渡,推动治理从“分散”走向“集中”,从“碎片化”走向“条块化”,以避免国家竞争带来的“裂解性服务”弊端——在区域内取得“共容系数”的治理形态。(6)全永波、叶芳:《“区域海”机制和中国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当下,海洋生态环境以区域治理为行为模式。
(一)区域治理分布
1974年,UNEP成立,并将“区域海洋计划”作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最重要机制——旨在通过政府间框架,解决区域层面的海洋退化问题。目前,该计划在区域治理下设置三种模型,涵盖146个国家:一是,“UNEP管理”型,即在UNEP主持下建立区域公约和行动计划(RSCAP),并由UNEP提供秘书处、财务管理和技术援助等机构——加勒比地区、东亚海域、东非地区、地中海、西北太平洋、西非地区和里海等7大海域治理即如此;二是“非UNEP管理”型,即虽在UNEP主持下建立RSCAP,但由其他组织提供秘书处、财务管理和技术援助等机构——黑海地区、东北太平洋、红海和亚丁湾、ROPME海域、南亚海域、东南太平洋和太平洋地区等7大海域治理便如是;三是“独立”型,即整体脱离UNEP,注重与其他RSCAP的合作——北极地区、南极地区、波罗的海和东北大西洋等4大海域治理即如此。这些模型将世界海域分为18个“区域海”(regional seas),并通过RSCAP,推进区域合作和区域共识之形成,进而为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基本情况大致如表1所示:(7)该表根据UNEP统计数据制作。参见UNEP网站,https:∥www.unep.org/explore-topics/oceans-seas/what-we-do/regional-seas-programme,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1月12日。

表1 海洋生态环境的区域治理模型及其分布

(续上表)
(二)区域治理结构
区域治理为解决单一国家难以触及的超国家和跨国家问题而存在,牵涉多国利益。因此,相较于国家治理而言,经“区域海”而形成的区域治理模式有其优越性。一则其跨越了国家边界,形成的空间范围介于国家与全球之间,意在对“共域性”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予以治理——为国家治理的延伸;二则正是因相关问题具有“跨界性”,故在传统的“垂直”“央—地”关系之基础上,其拓展了“横向”的“央—央”关系,即区域内的政府间联系——渗进国家治理内部,为国家治理的让渡。是以,区域治理由区域成员共同参与和投入,治理成果亦由它们共享。进言之,区域治理衍生于地缘政治之下,倡导沿岸国的“点—点”合作——通过海域分布来定位参与主体,要求同享一片海域的国家基于可能的利益而加入治理阵营。这一模式存在较强的工具属性——通过区域整合,处理特定范围内的公共事务。换言之,它建立了以国家为节点的“立体空间结构”,蕴含更加显性的现实主义权力框架,并以行为体、身份及利益塑造为权力来源,(8)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316.存在“区域连接”、“区域建制”和“区域大国”之内在逻辑。(9)张云:《国际关系中的区域治理:理论建构与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由此,海洋生态环境区域治理形成了“水平+垂直”的网状结构,并以“中心—边缘”的权力配置为主要特征——既有“大国强制主导+小国无奈跟随”或“大国主导+小国积极配合”的国家互动,(10)储新宇:《区域合作秩序的建构与中国的策略选择——历史与现实维度的经验分析》,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4页。也有“政府主导+非政府有限参与”的社会互动。不过,这两种互动均不以协调“国家—国家”、“政府—非政府”利益为重心,而是偏向于现实主义下的危机管理,以“任务+项目”为驱动,具有强封闭性——既不主张政府角色的扩张,也不关心“区域”外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11)Wallis,Allan D.,“The Third Wave:Current Trends in Regional Governance”,National Civic Review,Vol.83,No.3,1994,pp.290-310.究其本质而言,这与区域治理以塑造区域规范、维护区域秩序的价值定位相吻合。
应当说,这一结构有其重要性——在权力流散的背景下,通过国与国之间重新整合,稳定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区域善治。亦即,它深化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的治理范式——对国家治理“做加法”,丰富了公共事务的处理路径。在其项下,海洋生态环境区域治理以“区域协调”、“区域管理”和“区域监测”为三大侧重。其中,区域协调以区域共识为目的,通过区域对话来建章立制;区域管理以区域决策及其执行为偏好,经成员国授意,通过区域机构行使区域行政、区域立法和区域监督等权力;区域监测以追踪和反馈为基本内容,意在对治理进程予以系统评估。(12)张云:《国际关系中的区域治理:理论建构与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在此过程中,区域组织的建立是最常见的方式,即在国家自愿和平等参与下设立有关机构,并赋予其超国家或跨国家治理职能——在汇聚共识和推动议程之时,促进海洋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是故,这些机构往往以组合形式而存在。以加勒比地区治理为例:协调机构为四大区域活动中心——“加勒比地区海洋污染应急信息和培训中心”(RAC REMPEITC-Caribe)、“古巴交通运输与环境管理研究中心”(RAC CIMAB)、“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海洋事务研究所”(RAC IMA)、“瓜德罗普岛特别保护区和野生动物区域活动中心”(SPAW RAC);管理机构是1986年成立于牙买加金斯敦的“加勒比地区协调单位”(CAR/RCU);(13)现已作为《卡塔赫纳公约》的秘书处。监测机构则以2019年“加勒比海洋保护区管理网络与论坛”(CaMPAM)为主。
然而,区域治理虽是国际治理的重要内容,但其本身为“去全球化”的治理形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发挥之作用受到限制。换言之,由于国际治理无法“亲力亲为”地处理所有公共事务,因此,它只能将目标分解到各区域,并期望以区域治理来实现治理目标。但是,正如区域仅为全球的子单元,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亦有“子系统”和“整体系统”之分——前者的兴起意味着后者功能的萎缩。是以,在整合全球多层次利益诉求时,区域治理很快便陷入困境,既无法回应全球公域的治理需求,也加剧了国际法的“大范围”碎片化——在“专门化”与“自主化”之间形成“全球化悖论”,导致国际法愈加不成体系。(14)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https:∥legal.un.org/ilc/reports/2006/english/chp12.pdf,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1月12日。申言之,区域治理位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中间地带,虽推动产生了超越国家边界的社会空间,但不足以在国际社会中普及共同的规则和制度,虽试图以制度互动来解决海洋生态环境问题,(15)郭培清、闫鑫淇:《制度互动视角下北极次区域治理机制有效性探析——以北极地区传染病治理为例》,《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但“国际机制—预期效果”的线性结构并未出现,反而使区域治理陷入是否有效的“泥淖”。在此基础上,海洋生态环境问题的恶化,亦得到了合理解释,即这一现象的出现意味着UNEP在建构区域治理时未能实现其应然功能,导致国家与UNEP在“互动链”中出现某种程度的断裂,彰显出全球公域治理在“权威性”的塑造和权力运行上面临着结构性难题。根据UNEP数据显示,2009—2018年,全球约14%的珊瑚消失,尤以南亚、太平洋、东亚、西印度洋、澳大利亚、海湾和阿曼湾最为严重;未来几十年,除了珊瑚以外,超过100万种动植物将濒临灭绝;(16)UNEP,“Life Below Water”,https:∥www.unep.org/interactive/status-world-coral-reefs/?lang=EN,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1月12日。红树林和海草面积正以每年1%~3%、2%~5%的速度减少——与19世纪后期相比,1/4以上的红树林和近30%的海草面积已经消失。(17)UNEP,“Why Protecting &Restoring Blue Carbon Ecosystems Matters”,https:∥www.unep.org/explore-topics/oceans-seas/what-we-do/protecting-restoring-blue-carbon-ecosystems/why-protecting,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1月12日。基于此,以解决“当下”问题为重心的“临渴掘井”式的区域治理必然难以为继。是以,如何赋予其所承载的国际社会意志以普遍性和体系性,应是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之根源所在。
三、海洋生态环境的全球治理面向
与“区块格局”有别,全球治理内含整体性思维,属于更高治理形态,本质为“领域”治理而非“区域”治理、“国际社会”治理而非“民族”治理,并以大国协调、国际组织管理和国际法治为核心。(18)郭树勇:《区域治理理论与中国外交定位》,《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12期。具言之,它将全球海域作为基本场域,在尊重自然规律之时,倡导多边协作。(19)Weibin Zhang,“Dilemma of Multisubject Co-Governance of Global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ustainability,Vol.13,Issue 20,2021,https:∥www.mdpi.com/2071-1050/13/20/11145/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1月12日。
(一)旨在破解当下治理“赤字”
由于海水具有动态性,且与水体中各种物质构成海洋生态环境,故而,因海洋生态环境问题而受影响的主体不局限于某一或某几个国家。比如,微塑料虽经河流进入沿海,但在水流运动下,亦会走向其他海域(尤其是毗邻海域),并对后者造成不利影响。(20)Joanna Vince,Britta Denise Hardesty,“Plastic Pollution Challenges in Marine and Coastal Environments:From Local to Global Governance”,Restoration Ecology,Vol.25,Issue 1,2017,pp.123-128.与此同时,海洋生态环境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比如,有数据显示,2022年3月16日至20日,南极平均气温较同期高出许多,导致大量冰架坍塌,(21)UNEP,“Record Heat Sends Sea Ice into Retreat,Worrying Scientists”,https:∥www.unep.org/news-and-stories/story/record-heat-sends-sea-ice-retreat-worrying-scientists,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1月12日。但海洋亦是最大的碳库,储存了全球碳总量的93%,且每年吸收近20亿吨二氧化碳(CO2),占全球排放量之1/3左右。(22)Post,W. M.,Peng,T. H.,et al.,“The Global Carbon Cycle”,American Scientist,Vol.78,No.4,1990,pp.310-326.因此,在全球化迅速发展、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度加大、各种风险共振叠加的当下,衍生于国家治理理念和制度安排的区域治理,表现出明显滞后性。换言之,“区域海”机制已然无法独立肩负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使命:一方面,海洋流动性、一体性及其边界模糊性,使得区域治理难以应对国家和“区域海”之外的环境威胁;另一方面,海洋生态环境问题的影响之广、产生原因的复合程度之高,超越了国家和区域界线,使得国家治理和区域治理难以触及。
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成为破解这一“赤字”的必然选择。首先,海洋生态环境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本身难以分割——具有全球属性。(23)张卫彬、朱永倩:《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构》,《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5期。因此,将其划为“区域性”公共产品,将极大地限制受益者范围,从而有损全球可持续发展。其次,全球治理可以理解为区域“间”治理或跨区域治理,即打通18个“区域海”的界限,强调“区域治理+区域治理”之融合,以达到“1+1>2”的效果——本质是通过树立“全球权威”,加强国际合作,以优化治理成效。最后,全球治理覆盖了区域治理不足以触碰的领域,重视“需求—供给”下的制度平衡,并以公平、公正为导向,一方面囊括海洋生态环境之不同问题的综合性、联动性治理,另一方面将国家治理和区域治理的互补逻辑引入,在包容、普惠、高效的基础上,实现海洋生态环境之国际法治。
事实上,全球共治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和全球公民社会理论亦为此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全球共治理论既强调“东—西”共治,也主张“国家+非国家”共同参与,并以全球主义为视角,(24)Kooiman J.,Bavinck M.,“The Governance Perspective”,in Kooiman J.,Bavinck M.,et al.,eds.,Fish for Life:Interactive Governance for Fisheries,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05,p.11.通过“政府—市场—社会”三边互动,形成当今世界之基本场域。它要求“以国家为中心”让位于“以国家合作共治为中心”,秉行的是“弱冲突逻辑+强和谐逻辑”——既凸显国际交往中稳定的互信模式,也承认国家因各自情况不同而存在利益差异,(25)高奇琦:《全球共治:中西方世界秩序观的差异及其调和》,《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4期。引导主体从“被动配合”转向“积极参与”,进而形成海洋生态环境的利益与责任共同体。“新区域主义”在传统区域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既不限于“政府间主义”,也不提倡“上—下”式指导,而是基于“政府—市场—社会”而建立一种“区域泛组织”。(26)罗小龙、沈建法、陈雯:《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的管治尺度构建——以南京都市圈建设为例》,《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9年第7期。它淡化了“国家—中心”,主张共同利益约束,强调自愿协作,虽重视国际公共事务中固定联盟的建立,但以主体多元、协商对话和公众参与为优先,(27)袁政:《新区域主义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2期。重视主体行动的外部性与海域流动性,以及主观的价值认知与文化渗透,而非客观的海域空间结构——旨在拓展合作领域及范围,走向深度一体化与全球化。全球公民社会理论希望通过世界公民人格和全球公共价值的确立来建立协同,以谋求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28)袁祖社:《“全球公民社会”的生成及文化意义——兼论“世界公民人格”与全球“公共价值”意识的内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在动员治理资源并确认公共利益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且在代表被边缘化的主体立场上,更为公正。它在赋予国家以自主治理能力之时,以民主性和有效性为体系构建的向导,一方面融入了“自下而上”的治理元素,另一方面引导多元主体科学评估治理绩效,并借由公民社会力量而建立海洋生态环境新秩序,使之符合民主治理与国际法治的要义。
(二)存在有效的国际法指引
在现有国际法框架下,海洋生态环境全球治理有其规范性起源,并于国际硬法和国际软法中加以呈现。其中,前者指约定各方权利义务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规则,如国际条约、国际习惯等;后者指各方权利义务模糊且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规范,如国际指南、国际宣言、国际建议等。(29)骆旭旭:《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法律工具选择——以国际软法与硬法的互动为切入点》,《国际经济法学刊》2013年第2期。
首先,国际硬法。一般来说,海洋生态环境全球治理在国际硬法层面区分了海洋生态与海洋环境两部分。在海洋生态部分,《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作了较多考量。比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条表示,“生物”包含来自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构成的生态综合体;第8条、第9条继而要求各国尽可能地并酌情对生物多样性进行就地保护或移地保护;第18条倡导缔约方之间直接或通过国际/国家机构开展科技合作,并促进人员培训和专家交流;第19条进而主张将生物技术的成果与惠益分享给世界各国。(30)See article 2,8-9,18-19,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1992).从立法目的来看,该公约对“各国”和“缔约方”的表述,为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随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14条更是强调双边、区域和多边治理安排——允许缔约方以此为基础,与其他缔约方或非缔约方订立双边、区域和多边协定。(31)See article 14,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 (2000).其中,多边协定即全球治理的直接法律依据。在海洋环境部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行了仔细布局。比如,第192条、第193条指出,各国拥有开发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及保全海洋环境之义务;第194条、第195条表示,为了防止、减少并控制海洋环境污染,各国应于适当情形下联合采取必要措施。在第197条至第201条,它继而区分了“全球”和“区域”两种合作——分别对应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随后,第207条至第212条根据污染源对国际规则的“全球”与“区域”属性作了进一步阐述。(32)See article 192-237,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总的来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并重,为海洋环境问题提供了基本解决思路和方法。除此之外,《国际捕鲸管制公约》、《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等亦对海洋生态和海洋环境的全球治理予以了关注。
其次,国际软法。相较于国际硬法而言,海洋生态环境全球治理的国际软法众多,并可分为一般性国际软法与专门性国际软法。一般性国际软法包括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1982年《内罗毕宣言》、1992年《里约宣言》、2015年《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等——一方面要求各国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并进行合作,另一方面提议保护和恢复地球生态系统之健康与完整,本质是通过统一安排,倡导国家和非国家层面的互补与合作。(33)See Rio Declaration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92).专门性国际软法涵盖1995年《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2002年《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全球行动纲领》等——针对性地对具体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予以维护。尽管这些软法在效力上远不及国际硬法,但由于它们根源于国际主体的“内在理性”,且符合国际社会在特定时期的利益需求,故其通过“共同身份感”的塑造,与国际硬法相配合,共同指引主体的行为方向(34)何志鹏、孙璐:《国际软法何以可能:一个以环境为视角的展开》,《当代法学》2012年第1期。——是海洋生态环境全球治理的内生动力。
(三)探索全球治理新路径
海洋生态环境全球治理既有“陆海统筹”的理性思考,也有从“区域”合作转向“全球”合作的利益之维,即只有形成合力才能面对风险社会下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本质是协调不同利益冲突,实现“人—人”、“人—自然”关系之和谐。因此,从区域治理转向全球治理,需基于利益逻辑,在“权力—权利”框架下,转变现有治理结构并整合当前国际法机制,以实现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
1. 基本逻辑:区域利益让位于全球利益
区域治理以区域利益为考量,形成了区域整体利益高于区域内个体利益之基本逻辑——是国家理性与区域理性在治理过程中的博弈,亦是治理价值所在。具言之,国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寻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并防止他国利益扩张,此为国家个体理性,但该行为或将导致区域行动非理性,即区域治理的效果并不能自动实现。由此,区域理性通过弥合区域竞争,实行区域规划、构建区域分工,以形成稳定的区域合作,进而体现区域整体利益。但是,在全球治理下,“区域”这一利益实体作为“全球”的一部分,必然存在区域利益与全球利益的位序之分。与前者有别,全球利益衍生于全球意识,既摒弃地理局限,也超越阶级属性,是人类群体利益的最高位阶。故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比如,地中海治理为“区域海”机制的典范,因此,当沿岸国恪守现有标准时,是区域利益的体现,但当其提升治理标准时,则是出于全球利益的考量。当然,冲突亦在所难免——若基于区域利益,则22个参与方可降低行动积极性,但海洋生态环境的全球治理却要求所有主体参与,由此引发了区域利益与全球利益之博弈。在此背景下,全球理性通过行为解释和整体主义方法论,为二者的调适与融合提供互动逻辑。该理性超越了纯粹国家理性与区域理性,但并非对后者予以全盘否定,(35)郭树勇、于阳:《全球秩序观的理性转向与“新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基础》,《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4期。而是立足于多边主义,强调行为体对国际伦理、国际责任的共同认识,并在“全球—区域—国家”层面,进行“长期—短期”的利益布局,以形成全球利益关照下的区域利益与国家利益观。
2. 内部结构:从“中心—边缘”走向“去中心”
区域治理结构的本质为“中心—边缘”式——大国“中心”与小国“边缘”、政府“中心”与非政府“边缘”。在其项下,大小国基于治理权力而生成相应规则和制度,一方面将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另一方面将区域描绘成“圆形”结构,赋予其平面性,区分“中心国”与“边缘国”,认为后者依附于前者。与此同时,政府与非政府之间虽然存在先赋的博弈结构,(36)刘祖云:《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博弈、冲突及其治理》,《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但基于治理经验而呈现出主次角色之分,即政府为中心、非政府为补充。换言之,区域治理架构为“自上而下”的“政府—非政府”互动——本质即“政府主导”型的权力资源配置。而海洋生态环境全球治理旨在从外部治理转向深度治理,故主张“去中心”的“圆柱”结构,强调立体性——打破经济、政治和权力视角下的大小国划分,凸显“权利本位”而非“权力本位”意识,推动治理“等级性”转向治理“平等化”,进而实现多方共治。在该模式下,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彰显,“利益相关方”的界定更加科学,遵循“规则治理+关系治理”,以形成真正的全球伙伴关系。在此过程中,“能力”为重要的驱动和衡量因素,即能力较强国与能力较弱国同为基本主体,但责任有别——属于多方共治中的“多边共治”,即以民族国家为主体。不过,多方共治尚存在另一含义,即国家之外的行为体角色之发挥——政府与非政府共同治理海洋生态环境——从科层制转向合作制,二者既在各自领域发挥专业优势,又相互支撑,以形成统合性的治理格局。
3. 法律支撑:基于多边主义的规则再造
既然全球治理涵盖“全球—区域—国家”层面,那么,其规则体系必然在现有国际法基础上统筹区域治理规则,以形成完整的法律系统。具言之,其进路主要有四。一是坚持多边主义,尊重不同国家的话语诉求,在共商共建共享之基础上,坚持可持续发展,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体系内容,探索专门条约之构建——基于整体性框架,将海洋生态环境的一切问题纳入议题范畴,通过跨部门、跨地区合作,实现治理责任均衡,继而有效应对公海等留白领域的治理无序及不稳定,确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二是将海洋生态与海洋环境并重,通过“预防”与“整治”相结合,在国际法治的向导下,寻求体系化治理范式——将系统思维融入全球治理,明确海洋生态环境与气候议题之耦合、共振,进而推动全球公域治理的“权威性”回归。三是以整体、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强调海域的不可分割性,通过目标设置,集合各方力量。不过,考虑到海洋生态环境全球治理并非单一维度或单一领域治理,而是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议题挂钩,故它还存在非生态环境领域的维度衡量。四是在制度衔接上,构建全球规则、区域规则与国家规则的联动架构,通过规范利益关系和秩序价值,减少治理成本,以匡正失衡的环境正义,(37)王芳、毛渲:《特殊的主体与普遍的诉求:环境正义的多维张力与进路》,《理论导刊》2021年第3期。进而推动“海洋生态环境命运共同体”之形成。
4. 合作秩序:从单向指令走向双向互动
区域治理遵循单向指令逻辑——“区域—国家”和“政府—非政府”的指令接收与政策实施。换言之,主动或被动的权力社会化在削弱国家意识形态之时,重塑着区域治理的权力系统,因此,区域性组织与国家之间形成单向的线性联系,亦即,区域性组织发出指令后,国家通过利益计算和政策偏好,将区域规则转化为国内法,强调“中央—地方”政府职能,并基于“政府—非政府”的地位差距,呈现“单轨”整合。而海洋生态环境全球治理强调主体角色及其功能,意在形成“东—西—南—北”共治格局,以及“政府元治理+非政府微治理”的行动框架。(38)全永波:《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多层级治理:现实困境与未来走向》,《政法论丛》2019年第3期。申言之,由于这一模式不再借由经济等因素来区分大小国,因此,在治理角色上,各方目标一致,故,在坚持UNEP等国际组织的“权威性”时,国家既是指令接收者和政策实施者,也是规则制定者、影响者和完善者。此外,在多方共治下,非政府角色得到极大提升,(39)Susan Keen,“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in Policy”,in H. K. Colebatch,ed.,Beyond the Policy Cycle:The Policy Process in Australia,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20,pp.27-41.因此,政府与非政府之间亦形成双向型互动关系,后者既是前者的指令和政策的作用对象,也能通过规范扩散和具体行动影响指令与政策的作出。(40)冯帅:《次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功能定位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换言之,这些主体形成了一种共同认知结构,通过相互配合,凝聚共识,以避免治理层次分裂和治理体系缺失。由此,在海洋生态环境全球治理中,“全球—区域—国家”与“政府—非政府”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从“领导型”合作秩序转向“协调型”合作秩序。
四、海洋生态环境全球治理下的中国贡献
应当说,海洋生态环境全球治理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新的机遇,并助力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方面可以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国际规则制定能力,另一方面有序推进“海洋强国”建设。不过,区域治理有其存在的特定背景,在转型时具有路径依赖性。因此,从区域治理到全球治理,除了内部驱动,还需外力作用。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定将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推动“海洋生态环境命运共同体”之构建
海洋生态环境全球治理与中国诉求具有高度契合性。据统计,2013—2018年,中国与世界主要海洋国家签订了23份政府间海洋合作文件,建立了8个合作平台,在推动海洋综合管理及生态环境保护上取得重大进展。(41)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网站,http:∥www.mnr.gov.cn/dt/hy/201801/t20180122_2333429.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1月12日。与此同时,中国先后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首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随后,在2021年4月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他进一步规划了构建框架及整体思路,明确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要求。(42)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1年第13号,第7—9页。该理念突破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主张人与自然共生共荣。而海洋生态环境全球治理亦寻求“人—自然”关系之平衡。换言之,人与自然并非“主—客”关系的二元对立,而是包含“和解”之道与可持续发展旨趣。在此期间,各主体通过广泛合作,实现自然社会化和社会自然化的统一,进而在“人—自然”的“和解”中,走向“人—人”、“人—社会”之“和解”。(43)穆艳杰、于宜含:《“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当代建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3期。其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习近平主席强调,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有力抓手,只有各国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共同增进海洋福祉,才能促进海洋发展繁荣。该理念创新了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价值,重在树立合作与可持续的安全意识和互联互通的治理观——虽非仅提及海洋生态环境,但在范围上应可覆盖这一内容。(44)姚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意涵:理念创新与制度构建》,《当代法学》2019年第5期。
从逻辑上来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延展,前者将海洋作为“陆海空”生态环境治理的一部分,后者将生态环境纳入海洋治理之下——二者含有“海洋生态环境命运共同体”之义,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向引领。由此,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转型将受益于这一命运共同体之构建。事实上,由于海洋生态环境凝结着人类共同利益,故其通过寻求治理的“最大公约数”,以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为核心诉求。就目前来看,中国可从“观念—规则—行动”上进行考量,同向发力:在观念上,既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向全球,又在绿色发展上输出生态文明的思想指引,以增进各方互信、凝聚共识;在规则上,既在相关谈判和治理方案上基于全球治理模式而推出“中国方案”,又在制度衔接上加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以“良法”促“善治”;在行动上,既坚定多边主义,拓展国际合作方式,又在“区域—国家—地方”层面加大治理力度,以构建新型海上关系,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不仅顺应了人类发展潮流,应和了国际社会期待,(45)张宇燕:《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9期。而且符合中国的一贯作风及其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二)充分发挥国际规则引领者作用
“海洋生态环境命运共同体”之构建是基于“人海和谐”,本质是推动蓝色伙伴关系的塑造。(46)Amrita Jash,“China’s ‘Blue Partnership’ through the Maritime Silk Road”,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2017,pp.1-8.因此,在国际层面,主要路径有三条:
其一,大力弘扬并践行多边主义。作为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中国在坚持多边主义、改善全球治理上肩负重任。(47)杨洁勉:《中国应对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挑战的实践和理论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3期。因此,在模式转型下,需率先维护以UNEP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确保既有多边进程不停顿,(48)有学者曾提出构建“世界海洋组织”(world ocean organization),应当也是此种考量。参见杨泽伟:《新时代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变革:理念与路径》,《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并以双边合作、区域合作为突破口,凝聚共识——一方面倡导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另一方面寻求多边合作支点,为海洋生态环境全球治理提供现实支持。事实上,“一带一路”从倡议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已然注入多边主义的正能量,故通过这一平台,可推动相关议题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在全球伙伴关系之下深化蓝色伙伴关系,在夯实国际合作基础之时加大治理多边性。进言之,中国可以自身为“纽带”联结全球——既在“南—北”国家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弥合各方分歧,又在相关议题中引导海洋生态环境的正式与非正式讨论,推动治理朝着更加普惠、均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其二,主动参与并引领国际规则再造。尽管中国曾因“体系外国家”心态而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上较为被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其已逐渐融入国际法,并成为“体系内国家”。(49)徐崇利:《“体系外国家”心态与中国国际法理论的贫困》,《政法论坛》2006年第5期。针对海洋生态环境全球治理的规则“赤字”,中国将顺势而为、主动参与,不再“单纯地对他国方案进行简单修修补补”,而是从理论汲取营养,以实践幻化制度(50)仇华飞、孔维一:《国际法的中国理论:现状与构建》,《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贡献“中国方案”。不过,由于规则为制度的起点,因此,在制度竞争日渐普遍化之际,这一规则再造,或将面临隐形的权力争夺。(51)李巍、罗仪馥:《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故“中国方案”既要体现利益交汇,又要秉承正确的义利观。以《世界环境公约》为例,该公约意在整合全球环境与资源领域的治理方案,以形成国际环境法的一般原则。因此,其达成必然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全球治理规则产生重要影响。是以,在该公约陷入困顿之际,可以基于2018年《关于联大迈向〈世界环境公约〉特设工作组的评论意见》,借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体系,凝练共同但有区别责任(CBDR)、惠益分享、能力建设、资金支持、技术转让、危机应对、影响评估等内容,并经由“一般—具体”逻辑而在海洋生态环境全球治理中加以体现。事实上,这亦彰显了中国从“被动接受”国际法到“主动塑造”国际法之立场转变。(52)王阳:《全球海洋治理:历史演进、理论基础与中国的应对》,《河北法学》2019年第7期。
其三,有效传递中国声音,维护全球利益下的区域利益与国家利益。全球治理模式虽然主张区域利益与国家利益让位于全球利益,但主权理论的扎根、国家概念的形成和理性主义的存续表明,三者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共生共存。亦即,区域利益和国家利益无法被全球利益所取代。事实上,由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以国家利益和区域利益为基柱,因此,一方面,国家利益依然是最基础、最核心、最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较长的一段时期有存在之必要;另一方面,区域利益承载了区域协调,亦是全球利益下的特定组成部分。故而,在海洋生态环境全球治理下,中国宜推动三者“相向而行”:一方面,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合理表达自身诉求;另一方面,坚持以发展为目的,反对霸权,既强调主权平等,也注重增强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并以各国能力差距为显现,主张“国家—区域—全球”利益之平衡——在实现发展中国家集体利益之时,维护本国利益。此外,宜将全球利益、区域利益引入国家利益语境——推动国家利益从“国内”驱动型走向“国际+国内”驱动型,(53)刘贞晔:《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与国家利益分析》,《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9期。通过三者交融,形成最大“向心力”。
(三)深入推进国内治理体制改革
海洋生态环境全球治理作为一种范式变革,除了从国际上积极推动,还需在国内深度融入。申言之,在“全球—区域—国家”治理结构下,一国的法律和政策与国际法律、政策之间存在显著联系,即该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立场通常是其国内偏好投射至国际层面的结果。(54)Grigorescu A.,Baer Ç.,“The Choice Between Intergovernmentalism and Nongovernmentalism:Projecting Domestic Preferences to Global Governance”,World Politics,Vol.71,No.1,2019,p.88.亦即,一国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实践可通过传导性、渐进式途径而影响全球治理成效。故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分别对应各自层级的治理问题,只有共同发力,并经由二者持续互动,才是海洋生态环境全球治理之全貌。目前,在国内层面,中国可在三个方面推进:
第一,优化治理结构,加强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建设。针对地方治权强势、政府职能垄断和权力内卷化等实践,(55)杜辉:《环境公共治理与环境法的更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124页。中国宜将“政府+非政府”作为治理主体,明确“政府‘掌舵’、市场‘配置’、社会‘划桨’”的治理模型:一方面,清晰界定不同部门的工作范围,使之从功能重叠走向分工明确;另一方面,发挥政府调控职能,引导市场以资源配置为目标,主张社会畅通参与渠道——通过主体协同,避免治理“碎片化”和“政出多门”,并防止“条块联合执法”及条块主义泛滥,禁止利益合谋或利益俘获,以增强国家治理的体系性、科学性与有效性。与此同时,宜加强当前治理能力建设。一则,秉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56)人民日报评论部:《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我们的美丽中国》,《人民日报》,2020年8月13日,第5版。在涉海治理中,重点考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并以“陆—海”互动为基础,(57)张耀军、高又壬、郑霖豪:《区域协调发展视域下的陆海统筹:关键环节与实现路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确保海洋空间规划合理,以提升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环境保护之能力。二则,将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划分为“硬能力”和“软能力”——前者从人、财、物等方面同步切入,后者以体制优化和业务培训为落脚点。故,一方面宜充实执法队伍,加大资金支持,并引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最新科技支撑;另一方面,宜对现有立法体系予以修正,建立海上综合执法体制,并加强对专业人员之培训。
第二,对相关法律加以补充、修订和完善。参与海洋生态环境全球治理,意味着将围绕统筹协调、管理执行、科学咨询与评估、公众参与,建立平行且相互联系的“制度群”或“制度丛”(regime complex)。(58)R. O. Keohane,Victor,D. G.,“The Regime Complex for Climate Change”,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9,Issue 1,2011,pp.7-23.其中,统筹协调由生态环境部承担,管理执行以部门分工为重点,科学咨询与评估重在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公众参与以“市场—社会”互动为导向。(59)张丛林、焦佩锋:《中国参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优化路径》,《人民论坛》2021年第19期。与此同时,在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之基础上,可有针对性地进行补充、完善。比如,推动塑料垃圾入法,转变“以污染防治为主”的立法设计,明确“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之立法目的,并深化海洋污染联动整治、海洋生态系统修复、海洋生态环境数字治理等基本制度——推动《海洋环境保护法》走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此外,需明确不同主体的参与路径,通过法制手段强调“政府+非政府”合力,并以责任制度压实主体义务。具体来说,主要侧重点有二:一是,在纵向上基于海洋督察制度,强化“央—地”立法逻辑,细化对相关主体的考核评价;二是,在横向上基于湾长制,通过主体的自主压力传导,严格化奖惩配套措施。(60)崔野:《新时代推进海洋环境治理的难点与应对》,《海洋环境科学》2021年第2期。当然,在此过程中,《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需与近年来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有关内容加以协调,并兼顾碳中和目标,以最大化地发挥治理功效。
第三,构建关联机制,实现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衔接。尽管理论上可以理清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内在关联,但一般来说,只有将该联系固定于法律机制中,才能强化目标与行动的一致性。因此,在参与海洋生态环境全球治理时,中国宜将其作为行动的价值基础,从观念、规则和行动等方面强调治理共融——在人本化的治理中心下,明确“全球秩序—国家秩序”的紧密互动与相互支撑。事实上,这一关联机制亦可推动治理成果的分享,为全球治理提供实践范本,进而助力于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目标之达成。
五、结 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中国将积极参与,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6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年第30号,第4—27页。目前,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国际上仍以区域治理模式为总体架构。这一模式基于区域理性而产生,以区域合作、区域联动为重要手段,超越了单边和双边机制,以回应区域“公地悲剧”(62)G.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Vol.162,Issue 3859,1968,pp.1243-1248.和“集体行动的困境”。(63)M.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5-15.由于该模式照顾到沿岸国利益,弥补了国家治理的缺陷,并与“面向海洋”之吁求一致,故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主流范式。但是,这一依托于特定海域范围的利益集团,在对抗结构性风险时,不仅难以解决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更可能带来主体之间的关系紧张。换言之,在面对复杂性、综合性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时,区域治理陷入困境,既无法体现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不能回应日益增长的人类共同利益诉求。基于此,全球治理成为新的模式选择。事实上,不论是从全球共治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全球公民社会理论来看,还是从现有国际法规范来考察,海洋生态环境均有全球治理之面向。不过,由于二者在基本逻辑、内部结构、法律安排和合作秩序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转型时,区域利益需让位于全球利益,“中心—边缘”的治理结构需走向“去中心”。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将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海洋命运共同体”为理念指引,推动“海洋生态环境命运共同体”之构建,并基于“国际—国内”的双阶构造,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