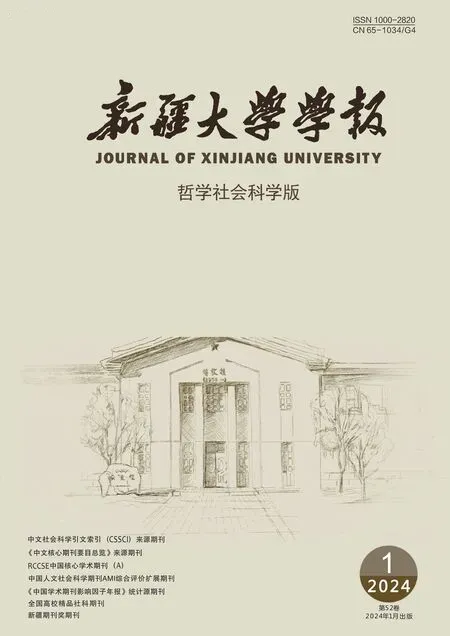交融互鉴:高昌国、唐西州各族民众社会生活研究
——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曹利华,张 磊
(攀枝花学院文学院,四川 攀枝花 617000)
季羡林先生曾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1]吐鲁番位处丝路要冲,该地区的民族关系历来备受重视,研究成果也较为丰硕。不过,以往的研究多从政治、军事等角度进行,较多关注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更为宏阔的视角关注民族关系,如马雍、周伟洲、荣新江、裴成国等代表性研究成果。①参见马雍《西北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第146-153 页;周伟洲、李泰仁《公元三至九世纪新疆地区的民族及其变迁》,《西北民族论丛》第5辑,2007年,第96-110页;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4-14页;裴成国《论5—8世纪吐鲁番与焉耆的关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127-132页。
而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系统考察各民族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并进一步论证民族关系和民族交往的则较为少见。孟宪实等从基层军政体制运作、宗教与社会信仰、西域历史与粟特人、知识技术与社会变迁等,展示了中古时期吐鲁番社会的诸多方面,但未从民族交往交融的角度进行论述。②参见孟宪实、荣新江、李肖《秩序与生活:中古时期的吐鲁番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邓小南利用出土文书阐释了6—8 世纪吐鲁番地区下层妇女的社会生活,重点在她们因生计所迫走出家门参与借贷、租赁、诉讼等活动的情况。③参见邓小南《六至八世纪的吐鲁番妇女——特别是他们在家庭以外的活动》,载季羡林、饶宗颐、周一良《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5-237页。李方论证了粟特人史玄政在唐西州的各种活动,关注点不在民族交往而是所承担的各种杂税徭役以及西州的地方特色。④参见李方《唐西州胡人生活状况一瞥——以史玄政为中心》,载季羡林、饶宗颐、周一良《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5-285页。本文试图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从居住、生产、婚姻、信仰等方面考察各族民众的社会生活及民族交往交融情况,再现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民族共同体的西域图景,为新疆地区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文化认同资源和文化心理支撑。
一、高昌国、唐西州的民族构成与民族主体
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吐鲁番地区的居民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土著车师人;二是西域、中亚地区迁入的胡人;三是汉人。
吐鲁番地区是车师人的故乡,车师人原政权虽不复存在,但建立该政权的民族不会随政权实体的覆灭而立即消失。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出现的车姓人,一般就是土著车师人之后裔。马雍先生《略谈有关高昌史的几件新出土文书》分析了吐鲁番阿斯塔那50 号墓出土的五件族谱,指出其中的“夫人车氏”应属旧车师国的王族。①参见马雍《略谈有关高昌史的几件新出土文书》,《考古》,1972年第4期,第46-64页。《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引》列“车庆元”“车不六多”等车姓人名24 个②参见李方、王素《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14-315页。,除人名外,吐鲁番阿斯塔那99 号墓所出《高昌延寿某年(631)勘合行马、亭马表启(八)》(1-439)③吐鲁番出土文书用例,参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的于文书标题后采用“(册数—页码)”的格式注明出处。这里的“(1-439)”,表示该文书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1 册第439 页;其他用例随文注明来源。详见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全四卷),1992—1996年。还出现“车寺”等车师人的家族寺院。
除车师人外,吐鲁番地区来自中亚、西域的胡人也非常复杂。我们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引》对文书所见的非汉族人口按姓氏初步统计,计有翟姓90 人,浑姓7 人,安姓99 人,康姓341 人,曹姓287 人,米姓11 人,何姓63 人,龙姓47人,白姓106 人,鄯姓9 人,车姓24 人。可见,吐鲁番地区有昭武九姓,有浑氏铁勒部族后裔,有车、鄯、龙、白等西域诸国王姓,还有卑失、栈头等突厥人部族姓氏。说明吐鲁番地区曾存在过车师、匈奴、突厥、吐谷浑、柔然等游牧民族,还有龟兹、焉耆、鄯善等西域诸族,再有粟特、波斯、天竺等异域外族,民族构成非常复杂。
汉人在张骞通西域后主要通过屯田、家族迁徙、徙民实边等方式,移居西域和高昌地区。
汉族是高昌国主体民族基本已成定论。陈国灿先生《从吐鲁番出土文献看高昌王国》细数了汉民族融入高昌的历史,并断定:“一批又一批汉人的到来,逐渐构成了高昌王国居民的主体。”[2]同时,还从政权基础、语言文字、文化风俗、宗教信仰方面予以佐证。黄文弼先生亦指出:“吐鲁番盆地自汉宣帝以后,已为汉人屯田之所,自汉至唐很少变化,故上文称高昌国人为汉族略杂胡人者此也。”[3]另外,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各姓氏出现的频次比率看,“在高昌人口中,汉族是高昌王国的主要民族,约占人口的70%至75%,而少数民族居民占25%至30%”[4]。
所以,我们肯定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时期的吐鲁番地区汉族是主体民族的同时,必须强调汉族主体民族地位的确立是一个动态过程:由车师国时期的土著民族,到汉族人的进入,再到汉民族主体地位的确立。同时,还要强调其他民族虽然在数量上不占绝对优势,但其作为土著民族或作为迁入定居的外族对该地区语言、社会、文化的影响是重要而深远的,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是不容忽视的。“如果无视这一点,就不能正确把握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的吐鲁番社会。”[5]
二、高昌国、唐西州各族民众的社会生活
(一)各族民众交错杂居
1.田地相接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记录田地四至的主要有“勘田簿”和“授田簿”。“‘勘田簿’就是唐平高昌后,为了解西州高昌县民户实际占有土地状况以推行均田制而作的”[6],集中反映了高昌国时期各族民众田地占有及使用情况;“授田簿”即唐平高昌建西州后将高昌三郡五县二十二城的8 046 户、37 738 人列入户籍中实行均田制,授予田亩的记载。④参见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701-1702页。
吐鲁番哈拉和卓1 号墓出土的3 件“勘田簿”集中反映了高昌国时期的情况:《唐西州赵相憙等勘田簿》(2-16)记汉族百姓赵相憙、孙大牙等与粟特人康波□、康嘿仁田地相接。《唐西州高昌县顺义等乡勘田簿》(2,12-15),残存可知共勘田28人,其中“何佑所延”为粟特胡人,其勘田一亩,“东田、西道、南□□□、北邓女憙”,与汉族民众田地相接。《唐西州张庆贞等勘田簿》(2-17)记汉族百姓张庆贞,北临粟特人何相憙,他们又与焉耆人龙不符麻子田地相邻。
唐灭高昌置西州后实行均田制,同样详细记载了授田者及田地四至。如吐鲁番阿斯塔那42号墓所出《唐西州高昌县授田薄》由29 个断片组成,其中断片(九)(3-129)所记的田地四至情况保存较为完备:
2(缺)城南五里白地渠 东左保西李鼠 南麹者 北渠
由文书可知粟特人“康乌破门铊”和汉族人李鼠、史伯、郭知德等同时被授予田亩,并且田地相接。可见,不管高昌国还是唐西州时期,吐鲁番地区入籍的各族民众都分得田地。不同民族、不同家庭田地相接,生产劳作中必然有交往交流,可以想象各族民众共同劳动、相互协作,在田间地头临时歇息、亲切交流的场景。
2.邻舍相望
定居高昌国和唐西州的各族民众不仅田地相接,而且邻舍相望,这在吐鲁番出土文书有很好体现。阿斯塔那10号墓所出《高昌延寿八年(631)孙阿父师买舍券》(2-206)记载其房舍:“东共郭相憙舍分垣;舍南诣道,々南郭养々舍分垣”“北共翟左海舍分垣”。据文书所记汜愿佑的房舍,东面、南面均和汉族民众有一墙之隔,北与粟特人翟左海的房舍仅一墙之隔。可见,当时散居的各族民众互为友好邻里,非常密集的聚居在吐鲁番地区。
这一点《唐宝应元年(762)六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4-329)也能很好反映,择录于下:
1 男金儿,八岁
2 牒:拂郍上件男在张鹤店门前坐,乃被行客
3 靳嗔奴家生活人将车辗损,腰以下骨并碎破
9 女想子,八岁
16 靳嗔奴扶车人康失芬年卅
17 史拂郍男金儿,曹没冒,女想子
18 问史拂郍等状称,上件儿女
19 在门前坐,乃被靳嗔奴扶车人辗损
该文书交代的事实经过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粟特人史拂郍的两个8岁的孩子,在汉族百姓张鹤店门前开心玩耍。粟特人孩童在没有大人看管的情况下,自由地坐在汉族百姓门前玩耍,可推测两家相居不远,或为近邻,同时足见当时各族杂居民众交往之密切,关系之融洽。第二个阶段,两个孩子被驾车的粟特人康失芬误伤辗损。文书载康失芬乃“处蜜部落百姓”,康姓粟特人为何是突厥部落百姓,应该是粟特人加入了突厥部落,或者非粟特人使用了粟特人的姓,①参见荣新江、华澜、张志清《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1页。可见该地区民族交往交融之密切和深入。
(二)各族民众共同从事生产劳作
1.农业生产
定居高昌国、唐西州的各族民众邻舍相望,田地相接,在农事耕作、田间管理、行水灌溉等农事活动中互相协作。吐鲁番出土文书真实记录了当时各族民众共同生产劳作的情景,如《唐开元二十二年(734)西州高昌县申西州都督府牒为差人夫修堤堰事》(4-317),本件盖有“高昌县之印”五处,共15行,兹择录数行如下:
4 右得知水官杨嘉惮、巩虔纯等状称:前件堤堰
5 每年差人夫修塞。今既时至,请准往例处分
6 者。准状,各责得状,料用人功如前者。依检案
7(缺)例取当县群牧、庄坞、底店及夷胡户
由该文书可知,唐西州高昌县要求按照惯例组织人力维修堤坝,“知水官”杨嘉惮、巩虔纯,从姓氏看为汉族人;按照前期制度规定本次修塞堤坝的工人应该是“当县群牧、庄坞、底店及夷胡户”。这里的“群牧、庄坞、底店”三类人不宜明确族属,而“夷胡户”为少数民族无疑,一般认为具体指西州领地内居住的伊朗系胡人和游牧部落为主体的人们。②参见〔日〕荒川正晴《唐代吐鲁番高昌城周边的水利开发与非汉人居民》,沈玉凌、平劲松译,《吐鲁番学研究》,2013 年第2期,第122-131页。该文书记载了各族民众共同修筑堤坝,共同劳作。
另外,入籍的各族民众共同担负调薪、供鞍等各种税收、杂役等责任,在同一个账目中出现不同种族民众缴纳赋税账目和具体额度,表明不同民众在同一个生产生活单元从事生产活动,过程中他们必然相互协作。如《高昌传用西北坊鄯海悦等刺薪帐》(2-41),记各族民众交纳调薪:
1(缺)贰人传用西北坊鄯海悦刺薪一车
2(缺)保壹车,刘阿尊壹车,刘济伯一车
3(缺)车,刘善庆壹车,左养胡壹车,贾法相壹
4(缺)青守壹车,龙德相壹[车]
文书中的“西北坊”是高昌县的一个“坊”,“坊”是“一级城镇基层行政单位,……高昌城至少有四坊,东南坊、西南坊、东北坊、西北坊”[7]。文书中“鄯海悦”当为鄯善人,“龙德相”为焉耆人,他们和汉族民众一起承担供给“刺薪”的任务。
又《高昌延昌三十四年(594)调薪文书(一)》(1-316)记调薪者姓名清晰可辨者共84 人,至少来自4个民族,其中“史元相、康世和、康师儿、史养儿”等粟特“昭武九姓”9人,“白保儿、白神救”等龟兹白姓4 人,“竺□儿”等天竺人1 人,另外还有“令狐得养、令狐众贤”等具有民族色彩而不宜区分族属者2 人,其余为汉人。大谷文书4910 号《唐天宝元年(742)七月交河郡纳青麦状》载“浑孝仙”“浑定仙”等“浑”姓吐谷浑人,和汉族百姓吕才艺同时交纳“屯田地子”,《唐开元二十二年(734)西州都督府致游弈首领骨逻拂斯关文为计会定人行水浇溉事》(4-315)记载西州突厥人从事定居农业生产活动等,各族民众在当地共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当地农业生产生活贡献力量。
2.手工劳作
吐鲁番阿斯塔那153 号墓所出《高昌入作人、画师、主胶人等名籍》(1-282)能很好反映各族民众集中从事手工劳作的情景①有学者研究认为该文书所记作人从事窟寺营造活动,具体参见苏玉敏《西域的供养人、工匠与窟寺营造》,《西域研究》,2007年第4期,第74-83页。。文书所记不同日期入作人、画师、主胶人姓名清晰可辨者共80 人,去其重复者计54人,至少来自8个民族,详见表1:

表1 阿斯塔那153号墓所出《高昌入作人、画师、主胶人等名籍》统计
由上可知,该文书所记作人、画师、主胶人中有“王辰虎、张明海”等汉族34 人,“康善憙、何相胡”等粟特“昭武九姓”8 人,“浑善相”等吐谷浑2人,“竺阿堆、竺沙弥”等来自天竺印度等地2人;另有龟兹白姓4人,高车翟姓1人,焉耆龙姓1人,“员头六子、张资弥胡”等具有民族色彩而不宜区分族属者2人。总体来看,该文书记载的作人、画师、主胶人等手工业者至少来自8个民族,汉族和非汉族的比例约为17∶10。并且,每一批作人都来自几个民族,如“五月廿九日入作人:刘胡奴、浑善相、李佑宣、白希憙、张石儿”等三十五人中,共涉4 个民族。同为画师的不同民众、同为主胶人的不同民众,长期共同参加艺术创作或手工劳作,互相借鉴,互相影响,书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个片段和缩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粟特等入籍高昌、西州的外来民族,不仅仅是普通的生产者建设者,他们在生产生活中得到广泛认可,部分还担任管理者,甚至立功受勋。《高昌计人配马文书》(1-281)记有巡逻人员石智信和康申保,《高昌付官、将、兵、人粮食帐》(1,314-316)记有“虎牙康婆居”“将石子正”,《高昌诸臣条列得破毡、破褐囊、绝便索、绝胡麻索头数奏二》(1-430)记有“虎牙史元善”,《高昌某年传始昌等县车牛子名及给价文书》(1-428)“康虎皮”已官至“洿林主簿”,《唐开元二十年(732)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4-275)粟特人石染典官至“游击将军”。这些都是汉族以外民众担任生产生活组织者、管理者的记录。可见,各族民众共同生活,融洽相处,不同的思想、信仰、风俗以及社会实践的交光互影,使不同的民族更好地认识了“他者”和“异域”,并且借助与“他者”的来往和与异域的交流更好地认识自己发展自己,以主人翁和建设者的姿态为该地区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三)各族民众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是民族交融的重要形式。关于吐鲁番地区的民族家庭问题,杨际平、郭锋等《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略有涉及,为论证敦煌的家庭结构关系,对吐鲁番出土户籍手实中家口情况较完整的45户家庭按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等作了分类统计。①参见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30页。董永强博士论文《四至八世纪吐鲁番的多民族问题探索》从家庭的民族构成角度,对所检90 余件唐代户籍、手实中的352 户家庭从胡人家庭、汉人家庭角度进行统计,并制成《唐代西州家庭类型统计总表》,②参见董永强《四至八世纪吐鲁番的多民族问题探索》,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37页。其中128户存在胡人,定义为胡人家庭,胡人家庭占可统计总数的43%;汉人家庭170 户,占可统计总数的57%。可见,唐西州这个移民社会虽以汉族为主体,但定居西州的胡人及胡人家庭亦不在少数。
那么,该128 户胡人家庭中胡汉通婚、胡胡通婚又占多少比例,我们利用董永强所列姓名齐全的18户胡人家庭统计表,③参见董永强《四至八世纪吐鲁番的多民族问题探索》,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24页。作表2并进一步分析:

表2 吐鲁番出土文书18户胡人家庭族际通婚情况统计
由表2 可知,18 户胡人家庭中,胡汉通婚家庭11户,焉耆粟特通婚1户,高车粟特通婚1户,不同民族间通婚共12 户,占67%。照此比例计算则128 户胡人家庭中,不同民族间的通婚约85 户,占统计总数的28.5%。也就是说,从当地家庭的民族构成看,约三分之一的胡人家庭为不同民族间的通婚。当然该数字只是部分统计,不具有绝对性,不过通过以上材料足见当时的吐鲁番地区民族间相互通婚组建的十分普遍,以及民族交往交融程度之高。
(四)各族民众宗教信仰相互影响
该地区各族民众在长期杂居相处、民族通婚等过程中宗教信仰也相互影响,不管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在部分民众中都出现了宗教信仰的改变转移。
1.汉族民众宗教信仰受其他民族影响
高昌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大量的汉族是从内地或河西走廊到此的,所以最初普通汉族民众部分信奉本土宗教道教,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箓以及随葬衣物疏中道教信息的记载能很好说明这一点。如吐鲁番阿斯塔那303 号墓出土551 年道教符箓一纸④参见黄烈《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箓”》,《文物》,1981年第1期,第51-55页。,有朱书符文四行,最后几字为“急急如律令”。《北凉真兴七年(425)宋泮妻魏仪容随葬衣物疏》(1-28)有“如律令”,《高昌章和五年(535)令狐孝忠妻随葬衣物疏》有“急急如律令”,《北凉缘禾六年翟万随葬衣物疏》(1-85)记“时见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这些都体现了道教在高昌国以及高昌郡时期的流行。即使佛教盛行时期,汉族民众的随葬衣物疏中仍然有道教的痕迹,如《高昌延昌七年(567)牛辰英随葬衣物疏》(1-198)出现“佛弟子”等佛教词语,最后仍是道教用语“急々如律令。”王启涛先生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指出:“当时的人们无论是取名,还是生活和丧葬习俗,以及官方的祭祀活动,都不乏道教的气息,特别是唐西州时期,由于唐王朝奉道教为皇家宗教,道教在丝绸之路的传播达到高峰。”[8]
高昌国时期汉族民众的佛教信仰更为普遍,这和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尤其是麹氏高昌时期礼敬佛教尤为虔诚,玄奘法师停留高昌期间,每将讲经麹文泰则“躬执香炉自来迎引,将升法座,王又低跪为隥,令法师蹑上,日日如此”[9]21,及别高昌,厚礼相赠,“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每一封书附大绫一疋为信”[9]21。统治者对佛教如此虔诚,普通民众的佛教信仰从姓氏、随葬衣物疏、功德疏也可见一斑。从姓氏名籍来看,汉族民众以“佛、僧、佑”入名的很多,如《僧尼财物疏》(1-97)载有“孙佛保”,《高昌赵阿六头举钱券》(1-284)载有证人“杨僧和”,高昌残名籍(1-372)中有“秦僧贤”,另外还有“僧忠”(l-303)、“佛奴”(2-89)、“僧佑”(1-136)、“僧保”(1-282)等。高昌国、唐西州汉族民众的“随葬衣物疏”,基本都称墓主人为“佛弟子”并评价其“持佛五戒,专修十善”。另吐鲁番出土文书还有一批“功德疏”,详记墓主人生前造佛像、布施、抄诵佛经等敬佛礼佛情况,如《唐咸亨三年(672)新妇为阿公录在生功德疏》(3-334)“请廿僧乞诵,并施马一疋与佛”。《唐咸亨五年(674)儿为阿婆录在生及亡没所修功德牒》(3-259)“阿婆文軏法师边讲《法华》一部。敬道禅师边受戒。写《涅槃经》一部,《随愿往生经》一卷,《观世音经》一卷”等,足见民众对佛教的虔诚。
除了道教和佛教之外,部分汉族民众还信奉了粟特人带来的祆教。该教崇尚光明、火和日月星辰,善恶二元分立。《魏书·高昌传》载:高昌“俗事天神,兼信佛法”[10]2243,《北史·高昌传》《隋书·高昌传》均有此记载①参见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12页;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7页。。陈垣先生认为“天神”信仰五世纪传入我国,至唐初缩写“天神”二字始创“祆”字,认为“不称天神而称祆者,明其为外国天神也”[11]304。唐长孺、姜伯勤、王素等先生也曾进一步论证②参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第235 页;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168-177页;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上海:三联书店,1955年,第416页。。
《高昌传》所记“天神”应是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言之“胡天”③参见王启涛《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2年,第444页。。如《金光明经卷第二题记》有“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下”[12],《高昌高干秀等按亩入供帐》(1-200)有“十二月十五日,一斛,付阿(缺),祀胡天”。《高昌众保等传供粮食帐》(1-238)有“面六斗,供祀天”,《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1-400)“祀天”字样六见。
从语言学角度看,“胡天”一词具有典型的外来特征。“胡本匈奴(Huna)专名,去「na」著「Hu」,故音译曰胡,后始以之通称外族。”[13]“胡”在指称民族及相关事物时是音译外来词,“胡天”一词是“胡”作为语素和汉语固有语素“天”构成新的胡汉合璧词。早期中原典籍也常在“天神”“天”之前冠以“胡”字,指称祆教之“天神”。如《魏书·灵太后传》称“胡天神”[10]338,《晋书·石季龙载记下》载“龙骧孙伏都、刘銖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14],《隋书·礼仪志》载“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儛,以事胡天”[15],两部史书均称“胡天”。从民族交往的视角看,“胡天”这个汉语词是汉族民众使用的,以汉族为主体视角对外来宗教的一种称呼,是对外来事物的标识,也体现出汉族民众对外来宗教的接纳和认可。正如陈垣先生所言:“在西域传曰天神……在中国人祀之则曰胡天,或曰胡天神,所以别于中国恒言之天,或天神地祇之天神也。”[11]306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直接记录汉族民众从事祆教活动的材料很少,但是部分汉族民众的姓名却很好体现了其对祆教的信仰。很多汉族民众取名“奣”或“”,如阿斯塔那1 号墓所出文书《某人条呈为取及买毯事》(1-6)记“杨奣从刘晋取官四斛,为丝十三两。”哈拉和卓91号墓所出《无马人名籍》(1-81)记无马者17 人,其中两人分别是“汜”“王”,汜姓、王姓当为汉族百姓无疑。祆教崇拜光明,敬奉日月天神,“奣”“”能很好表达此意,“当时高昌人偏爱以‘奣’字为名……意在表明自己是火祆教徒”[16]。
可见,汉族民众本信奉自己的本土宗教,随着民族交往的加深部分民众信奉佛教或祆教等外族宗教。“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精神信仰,从外族传来而为当地百姓所认同和接受,并最终在语言文字中沉淀,期间的民族交往和认同是不言而喻的。”[17]
2.其他民族宗教信仰受汉民族影响
这里我们以高昌国、唐西州外族人口占比最高的粟特人为例①据《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隐》胡姓人名共1 086个,其中粟特人名880个,占比达81%,推知高昌地区人口最多的外来种族当为粟特人。参见李方、王素《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隐》,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468页。,考察其他民族受汉民族信仰的影响及渐变发展。
粟特人是典型的商业民族,是丝绸之路上最为活跃的民族。他们组成规模浩大的商旅队伍,商队首领同时担任宗教首领,整个商队在丝路沿线城镇留居,形成粟特聚落。高昌国、唐西州时期中亚到中国的陆上丝绸之路基本被粟特人垄断②参见荣新江《波斯与中国:两种文明在唐朝的交融》,《中国学术》第1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6-67页。,而吐鲁番地区当时的商业地位决定了其为粟特人的重要聚居地。大规模的商队带来本民族的祆教信仰是很自然的。
“祆教不仅被粟特人随着他们庞大的商队带入吐鲁番地区,同时还被带入西域的于阗、鄯善,带给了北部的嚈哒、突厥等民族。”[18]186“在民族交往中敬奉天神的祆教不仅在高昌国盛行,在于阗、焉耆等更大范围内的西域地区也比较普遍,甚至影响了草原民族的信仰。”[18]186我们必须肯定粟特人在民族交往史上对宗教传播所起的积极作用。
但是随着粟特人长期定居高昌,编户为民,与汉族民众房舍相邻、田地相接,共同从事生产劳作,甚至通婚组建家庭,部分粟特人逐步接受了佛教。尤其是麹氏高昌时期,佛教颇为盛行,粟特人定居高昌而兼信佛教,非常自然。粟特人信奉佛教在姓氏名籍中也有很好体现,如《高昌计人配马文书》(1-281)有“曹佛儿”,《唐何延相等戸家口籍》(2-33)有“曹僧居尼”等曹姓粟特人,《高昌元礼等传供食帐》(1-265)有“康佛保”,《高昌重光三年(622)条列虎牙泛某等传供食帐》(1-377)有“康禅师”等信奉佛教的康姓粟特人,另有安僧迦(2-42)、史佛住(2-107)等,以上姓名佛教特征非常鲜明。另外,敦煌文书中的50余种粟特语文献,主要是佛教经卷,时代已到晚唐五代,③参见吉田丰《敦煌胡语文献》,《讲座敦煌》卷6,东京:大东出版社,1985年,第187-204页。亦能很好说明佛教在粟特人中流传之广。
部分粟特人信奉道教,如《唐西州道俗合作梯蹬及钟记》(4-335)载:乡官折冲张无价等12 名道教领袖,其中一位是曹姓粟特人“曹玄仲”,《唐开元四年(716)籍后勘问道观主康知引田亩文书》(4-109)载粟特人“康知引”为道观观主。这些都能很好反映对道教的崇信。宗教信仰属一个民族的观念层面、意识层面,一般不会轻易改变,粟特人宗教信仰的改变,除粟特人适应能力极强之外,只能解释为该地区民族交融程度之深。粟特人作为文化的传播者,同时也是文化的接受者,同化其他民族的同时也受到影响,民族间的交往交流是双向的,互鉴的。
总之,吐鲁番地区的民族信仰是多元的,在长期的交流交融过程中相互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汉族民众在本土宗教道教基础上不仅接纳了祆教,还接纳了佛教、祆教等其他民族宗教;粟特民众信奉祆教,部分转而兼信佛教、道教,这些都只能在民族成分复杂、民族交往频繁、民族交融深入的区域进行。
三、小 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高昌国、唐西州时期吐鲁番地区的民族交往已经达到了民族融合的程度。各族民众沿着丝绸之路,汇聚吐鲁番,在吐鲁番长期杂居相处,房舍相望、田地相接,共享道路水渠,共同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劳作,甚至族际通婚。长期交往中他们的语言、思想、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相互渗透,相互涵化,情感上相互亲近,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民族关系长期发展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实现了区域性的民族融合。他们亲如一家,以主人翁和建设者的姿态在古代吐鲁番的舞台上尽情展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当地兴旺、大唐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高昌国、唐西州时期吐鲁番地区的民族交流融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缩影。当今时代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出土文献等文献典籍中寻求历史渊源,挖掘文化认同资源和文化心理支撑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