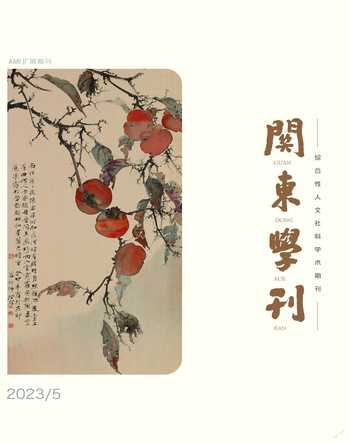中西音韵对称形式交融下的现代交响
[摘 要]音韵对称作为新诗形式建构的重要方面,是诗歌审美的重要元素之一。卞之琳注重从诗艺角度重新思考新诗中的音韵对称问题,主张借鉴、融合中西方诗学资源中的音韵对称形式。这一方面体现在他“化古化欧”“入出”之间的现代音韵对称观中,另一方面也呈现于其中西融合下繁富的韵式安排,及内外交融下精致的韵律效果中。可以说,卞之琳的新诗音韵对称实践为现代音韵对称诗学开拓出更加丰富、现代的审美效果。
[关键词]卞之琳;音韵对称;新诗;中西交融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新诗对称形式研究”(19CZW039)。
[作者简介]高健(1990-),女,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讲师(扬州 225000)。
自新诗尝试之初,音韵对称就成为诗人们论争的核心问题之一。具体而言,韵,作为构建诗歌节奏的重要元素,“是歌、乐、舞同源的一种遗痕,主要功用仍在造成音节的前后呼应与和谐”。(朱光潜:《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从具体建构方式来说,诗歌中“所谓的‘押韵’,就是用音色去表现音律的一种方法。也就是把同一音色的‘音节’间隔多少时间就让它重复出现一次,使这种‘重复出现’显得相当的规则化”。(谢云飞:《文学与音律》,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8年,第23页。)由此不难看出,以一定音质(或称为音色)为基础的对称安排,是押韵成立的重要方法之一。在具体建构中,音韵借助不同位置及多样的对称形式,在诗歌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音韵类型和艺术效果,不仅为诗歌带来了和谐的音乐性,其本身所具有的修辞意义,也能起到强化诗歌内容的作用。无论在汉语诗歌还是在西方诗歌中,音韵对称都是诗歌审美的重要元素之一,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传统汉诗判断诗体成立与否的关键因素,这从古人常以“韵文”来指称诗歌就可见出一斑。不过,随着新诗的革新与发展,音韵对称在诗歌中的建构不再具有强制性,胡适就曾指出:“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2页。)。但作为一种诗艺手法和诗美方式,无论在胡适等的白话新诗中,还是在以郭沫若、艾青为代表的现代自由体诗歌中,以及新月派诗人的新格律体诗中,音韵对称的建构仍然是他们探索新诗形式建构的重要方面。朱自清先生就曾表示:“新诗开始的时候,以解放相号召,一般作者都不去理会那些旧形式。押韵不押韵自然也是自由的。不过押韵的并不少。到现在通盘看起来,似乎新诗押韵的并不比不押韵的少得很多。”(朱自清:《诗韵》,朱喬森编:《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402页。)
卞之琳被称为“上承‘新月’(徐、闻),中出‘现代’,下启‘九叶’”(袁可嘉:《略论卞之琳对新诗艺术的贡献》,《文艺研究》1990年第1期。)的现代诗人。当他登上诗坛时,有关新诗音韵对称争论的高潮已经基本过去,在对待新诗音韵对称问题上,卞之琳一方面拥有相对理性的建构空间;另一方面前人所积累的相对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也为他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诗学资源。在此背景下,音韵对称在卞之琳的诗中,呈现出更加自由、成熟的形态。李广田曾称赞卞之琳现代诗歌中的音韵对称艺术,表示:“他(卞之琳——笔者注)在格式与韵法方面也许贡献得更多,更可贵”(李广田:《诗的艺术——论卞之琳的〈十年诗草〉》,《李广田全集》第4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9页。)。卞之琳自己也表示:“押韵是古今中西诗歌的较为普遍的要求”(卞之琳:《谈诗歌的格律问题》,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37页。)。而在现代音韵对称的具体建构中,卞之琳注重结合中西方诗学资源,不仅在诗歌中营造出精巧别致的音韵对称效果,也为现代音韵对称诗学开拓出更加丰富、现代的审美效果。这一方面体现在他“化古化欧”“入出”之间的现代音韵对称观中;另一方面也呈现于他中西融合下繁富的韵式安排,及内外交融下精致的韵律效果中。本文以最能代表卞之琳艺术成就的现代诗作(即卞之琳在1930-1939年间的诗歌创作)为对象,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具体考察卞之琳现代诗歌的音韵对称艺术。
一、“化古化欧”“入出”之间的现代音韵对称观
为进一步加深对卞之琳的音韵对称理论观点的理解,这里有必要简要回顾从白话新诗派到新月诗派的音韵对称观点,对现代诗歌音韵对称的诗学脉络作简要梳理。首先,作为新诗的早期开拓者,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新诗派诗人,在面对来自传统的巨大阴影时,主要采取背逆的姿态。音韵对称作为古代汉诗的重要文体特征之一,其在律诗中所呈现的逐步趋于固化的对称形态,受到白话新诗派诗人们的一致反对。刘半农就曾提出,诗歌革新的首要步骤在于“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鲍晶编:《刘半农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9页。)。除此之外,胡适、康白情、俞平伯等也分别提出相应观点,旨在以“自然的音节”破除传统汉诗音韵对称的僵化。不过长期的古典文化滋养却让白话新诗派很难在创作中完全摆脱旧诗音韵对称的影响,呈现出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状态。其次,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现代自由体诗人认为,“拘于因袭之见的人,每每以为‘无韵者为文,有韵者为诗’,而所谓韵又几乎限于脚韵。这种皮相之见,不识何以竟能深入人心而牢不可拔。最近国人论诗,犹有兢兢于有韵无韵之争而诋散文诗之名为悖理者,真可算是出人以外。不知诗的本质,不在乎脚韵的有无。”(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309页。)从理论上否定了音韵对称在新诗文体中的主导地位,强调应当以“内在的韵律”打破传统诗歌以外在音律为主的节奏建构方式,对新诗文体的更新有着较为积极的帮助,但对于音韵对称的态度却略显偏激。第三,以新月派为代表的新格律体诗人则认为:“主张自由诗者以为音韵是诗的外加的质素,诗可以离开音韵而存在。这种说法完全是没能了解诗的音韵的作用。”(梁实秋:《诗的音韵》,徐静波编:《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1页。)“它(韵脚——笔者注)就好比是一把锁和一个镜框子,把格调和节奏牢牢的圈锁在里边,一首诗里要没有它,读起来决不会铿锵成调。”(饶孟侃:《新诗的音节》,王锦厚、陈丽莉编:《饶孟侃诗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9页。)在否定的基础上开始重新思考音韵对称在新诗中的价值。
面对前期新诗创作者们在新诗音韵对称问题上较为明显的分歧,卞之琳没有拘执于一方,而是根据自身的创作经验以及对新诗文体独立性的清醒认识,辩证地指出:相较于传统诗歌“无韵不成诗”的创作方式,“今日写白话新诗不用脚韵是否行得通,其实关系不大:我国今日既习惯于有韵自由体,也习惯于无韵自由体,和外国一样”(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55页。);并进一步表示,在新诗中音韵对称与平仄声律规则一样“已不属格律范畴而纯属诗艺范畴了”(卞之琳:《人事固多乖:纪念梁宗岱》,《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这一观点既综合了前期诗人在分歧中的潜在统一,从文体特点的角度否定了音韵对称在新诗中的主导性地位,又从实际出发明确了音韵对称在新诗诗艺建构方面的作用。而作为一种诗艺技巧与审美要素,在具体建构过程中,深受古典与西方诗学滋养的卞之琳,主张打破古今中外的诗学时空界限,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兼容心态,大胆探索新诗音韵对称的建构方式。
从古今中西诗学的多重角度出发,卞之琳虽然指出在不同诗学背景中音韵对称的具体建构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押韵方式(或者脚韵安排)中西有所不同,一般说来,西方的较为复杂,我国的较为单纯”(卞之琳:《谈诗歌的格律问题》,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37页。)。不过在新诗整体包括音韵对称的具体建构过程中,卞之琳从自身的创作经驗出发强调“化古”与“化欧”的双重结合,在《〈雕虫纪历〉自序》中,诗人写道:“我写白话新体诗,要说是‘欧化’(其实写诗分行,就是从西方如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那么也未尝不‘古化’”。并进一步指出:“如果我写白话新体诗,写得不好,不就是因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用得不好或者不对头而已”(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59、461页。)。正是在这样的建构心理与思维方式下,相较于其他现代诗人,卞之琳更注重从诗艺本身出发,发现古今中西诗学间的融通之处,这也明显体现在他对待诗歌音韵对称的态度上。
首先,卞之琳注意打通中西音韵诗学间的壁垒,强调二者间的相融相通。例如卞之琳指出,诸如换韵、交错押韵以及阴韵等西方诗歌中较为典型的音韵对称方式,在传统汉诗中并非杳无踪迹。他指出:“我国旧诗较多一韵到底,换韵也不稀罕”,并进一步指出,“交错押韵,在我国也是古已有之,只是稀有,后来在旧词里,特别在较早的《花间集》里就常见”(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55、456页。)。除此之外,卞之琳还深入挖掘了“阴韵”这一特殊音韵对称方式在中国传统诗学中的应用情况,“阴韵(Feminine rhyme),我国《诗经》里就有(就是连‘虚’字‘兮’一起押韵,例如‘其实七兮’和‘迨其吉兮’押韵),后来就少见了”(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55-456页。)。其次,卞之琳也主张从诗艺角度吸收与借鉴中西方诗学技巧,无论是传统汉诗还是西方诗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音韵对称方式都是卞之琳主张新诗人们革新与尝试的对象。
卞之琳之所以注重以“化古化欧”的方式,打通古今中西音韵诗学间的壁垒,其目的在于以更加现代、自由的方式建构白话新体诗中的音韵对称形式。他认为,诸如换韵、交错押韵以及阴韵“这些韵式虽则在过去因时代变化而废弃不用了,今天在又变化了的时代,在借鉴我国古典诗律以及西洋诗律的基础上,再拿来试用到新诗上”(卞之琳:《今日新诗面临的艺术问题》,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96页。),并不是一种不可行的方式。可以说,卞之琳有关新诗音韵对称建构的基础,在于通过诗人的不断融合与革新,改变新诗读者倾向于传统的、单一的听觉习惯。
在对现代诗人吴兴华的诗评中,卞之琳指出:“不论‘化古’‘化洋’,吴诗辞藻富丽而未能多赋予新活力,意境深邃而未能多吹进新气息,……尽管做了多大尝试的努力,似乎在一般场合终有点‘入’而未能‘出’。”(卞之琳:《吴兴华的诗与译诗》,《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86年第2期。)由此可见,在“化古化欧”的建构思维下,卞之琳还要求新诗人们不仅要熟悉、灵活掌握(“入”)多种诗学资源,还需要根据新诗自身的艺术特点(“出”),合理吸收与改进古今中西诗学资源,以去芜存菁的方式,在借鉴与继承中葆有大胆创新的现代诗学精神,为新诗开创出更加自由、多样、现代的音韵对称形式。
在具体建构中,卞之琳从新诗自身的文体特征出发,对新诗音韵对称提出了以下建构原则:
第一,作为增加新诗音乐性的重要因素,卞之琳认为新诗音韵对称在具体建构过程中,应当尽量避免单调和涣散。卞之琳不主张直接借鉴传统汉诗中较为普遍的一韵到底的音韵对称方式,认为这样既会造成单调的倾向也不合诗情的变化(卞之琳:《新诗和西方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503页。)。根据新诗的语言特点以及以“顿”(音节)为基础的形式建构方式,卞之琳还进一步指出新诗中的音韵对称应当避免变化过杂和间距过长等问题,他指出:“应该承认,由于语言本身的性能不同,脚韵交错得太复杂,间隔得太远,在我们新体诗里大致不大行得通。”(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56页。)这主要是“因为白话新诗里,脚韵隔得太远,不易起押韵作用”。在对中西方格律体诗歌的借鉴中,卞之琳也提出应以新诗自身的文体特征为依据,如对于七言律诗的借鉴,他就表示“像七言律诗的新格律八行诗也是大可写的,只是需要排除老一套对仗方式,并采取较有变化的押韵安排”(卞之琳:《吴兴华的诗与译诗》,《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86年第2期。)。同时,他也对十四行体的借鉴提出了一些建议:“十四行体,特别是它的现代变体,在中国新诗里,实践证明是可以引进来应用的,只是因为韵脚安排关系,每行最多不能超出五拍,愈短愈能见效。”(卞之琳:《吴兴华的诗与译诗》,《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86年第2期。)在“入出”之间,卞之琳为新诗音韵对称探索出更加多元的诗学可能。
第二,卞之琳强调了轻重音对音韵对称效果的影响,他指出:“既讲轻重音,押韵就得押在重音上;而我们口语里两个字一顿的,重音不一定在后一个字上,要押韵就得大部用三字顿收尾。”(卞之琳:《哼唱型节奏(吟调)和说话型节奏(诵调)》,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28页。)不过,在此基础上,卞之琳也从新诗的特点出发,指出“脚韵押在重音节或强音节上,在中西诗中共属当然。但是在我们的语体新诗行尾以孤立的单音节(单词)押韵,也不宜过分,……偶用以分别和下行孤立的单音节词相协,固然会显得脚韵嘹亮、铿锵,多用则反成单调、刺耳。”(卞之琳:《奇偶音节组的必要性和参差均衡律的可行性》,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573页。)
可见,在现代音韵对称的建构中,卞之琳既主张以“化古化欧”的方式积极融合中西方诗学资源中的音韵对称形式,也强调在“入出”之间尊重新诗文体独立性,探索符合新诗文体规律的现代音韵对称形式。卞之琳诗歌艺术的重要研究者江弱水先生,曾从音韵对称的角度称赞卞之琳是“新诗人中最富于音乐性的极少数人之一”(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在“化古化欧”“入出”之间的现代音韵对称观下,繁富、精致的音韵对称是卞之琳现代汉语诗歌的重要特色之一。在具体建构过程中,卞之琳善于以中西融合、内外交融的建构方式,探索音韵对称形式的现代交响。
二、现代音韵对称实践路径之一:中西融合下繁富的韵式安排
卞之琳诗歌中繁富的音韵对称形式一直为人所称道,卞之琳多年的知音好友李广田先生就曾表示:“一接触到《十年诗草》中的格式与韵法问题,我们就面对着了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大致说起来,在全书七十六首诗中,實在只有很少的诗是不大讲究格律的,而那些格式与韵法的变化又是那么繁富,几乎每一首诗都看出作者在这方面的工夫,也几乎是每一首诗都有它特有的格式与韵法,我们简直很难得把它完全说出。”(李广田:《诗的艺术——论卞之琳的〈十年诗草〉》,《李广田全集》第4卷,第238-239页。)具体而言,卞之琳诗歌中的音韵对称形式之所以呈现出繁富的样态,其中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卞之琳善于融合变化多端的中西韵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新诗创作思维使他的诗歌中既可见传统汉诗的音韵对称形式,也不乏西方韵式以及中西方音韵诗学的交集韵式。
首先,卞之琳在一些诗歌中大胆使用了传统汉诗的音韵对称方式。如《归》《第一盏灯》以及《给修筑飞机场的工人》就使用了与七绝较为相似的aaba的传统韵式。以《归》为例:“像一个天文家离开了望远镜·,/从热闹中出来闻自己的足音·。/莫非在自己圈子外的圈子外?/伸向黄昏去的路像一段灰心·。”除第三行以ai为元音结尾外,第一、二、四行均以in、ing协韵(王力在《汉语诗律学》中表示:“在汉语里,象en和eng押韵,in和ing押韵,an和ang押韵,可认为协音;又象in和en押韵,in和ün押韵,eng和ong押韵,都可认为协字。”参见王力:《汉语诗律学》增订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873页。)的方式,形成较为和谐的脚韵对称。不过,客观而言,卞之琳虽然以“古为今用”的态度,并不刻意规避传统汉诗的格律效果,但直接套用古典汉诗音韵对称的方式,在其诗歌中仍然较为鲜见。在借鉴传统汉诗的音韵对称形式时,卞之琳一方面注意以四行体为主,尽量以篇幅的短小避免密集重复带来的单调感,如《归》《第一盏灯》。另一方面也注意以诗节为单位的换韵方式规避单调感,如在《给修筑飞机场的工人》中,诗人首先在第一节中以元音ing为韵,形成了aaba的脚韵对称形式,而在第二节至第五节中则分别换以元音ü、ang、an、i为韵,搭建出不同的aaba的脚韵对称效果,在重复与变化中使传统汉诗的音韵对称形式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其次,卞之琳也十分关注西方诗体中的音韵对称形式。一方面是对西方十四行体诗歌音韵对称形式的有意借鉴。卞之琳曾表示:“实际上我全部直到后期和解放后新时期所写不多,存心用十四行体也颇有几首,只是没有标明是十四行体,而读者也似乎很少看得出。这可能说明了我在中文里没有达到这样诗体的效果,也可能说明了我还能用得不显眼。”(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61页。)不过,根据学者统计,在《十年诗草》(1930-1939)诗集中,《望》《淘气》《灯虫》《给一位政治部主任》《给委员长》《给〈论持久战〉的著者》《给一位集团军总司令》《给空军战士》等8首诗歌都是较为严格的十四行体(李广田:《诗的艺术——论卞之琳的〈十年诗草〉》,《李广田全集》第4卷,第239页。),《影子》《几个人》《音尘》《长》等则使用了十四行变体形式。这些诗歌虽然大多采用彼特拉克式即意大利十四行体,但在具体建构中,卞之琳并没有简单套用,而是匠心独运地使每首诗歌的韵式都不完全相同,如《给一位政治部主任》采用了“abba//abba//cdc//dee”的音韵对称形式,而《给一位集团军总司令》则使用了“abba//cbbc//dee//dff”的形式,呈现出繁富的音韵效果。另一方面,卞之琳还有意识地借鉴了西方诗歌中较具代表性的音韵对称形式,如诗歌《白螺壳》就借鉴了法国诗人瓦雷里《棕榈》(Palm)一诗中的复杂韵式,全诗共4个诗节,每节10行,每节的韵脚排列为ababccdeed,兼用了“交韵”(abab)、“随韵”(cc)和“抱韵”(deed)等多种韵式,展现出繁富工巧的一面。
再次,卞之琳还擅长使用中西融合的韵式。在前文有关卞之琳现代音韵对称理论的梳理中,我们已经了解到,在精通古今中西诗学的基础上,卞之琳认为换韵、交错押韵以及阴韵等音韵对称形式,在中西音韵对称诗学中都有所表现,属于二者的交集部分,“至于押韵,我国旧诗词以至今日真正的民歌里,换韵是常用的,也有交韵和抱韵,西方格律诗更常如此,只是更复杂一点”(卞之琳:《新诗和西方诗》,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503页。)。对这些中西融合韵式的巧妙使用为卞之琳的诗歌增加了更加现代、繁富的音韵效果。第一,换韵是卞之琳诗歌常用的音韵对称技巧之一。随着诗行、诗节等崭新诗歌单位在新诗中的应用与普及,换韵的使用为新诗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声音效果。诗行之间可以以换韵方式,形成音韵的交错对称,为诗歌提供多元化的听觉效果,这一点我们在稍后的交错押韵中具体论述。除此之外,诗节间的换韵在卞诗中也较为普遍,除了前文的《给修筑飞机场的工人》外,在诗歌《对照》中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设想自己是一个哲学家,/见道旁烂苹果得了安慰,/地球烂了才寄生了人类,/学远塔,你独立山头对晚霞。//今天却尝了新熟的葡萄,/酸吧?甜吧?让自己问自己,/新秋味加三年的一点记忆,/懒躺在泉水里你睡了一觉。”全诗共2个诗节,在每节诗歌的内部诗人虽然都使用了abba的抱韵形式,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在具体建构中,诗人采用了精巧的换韵方式,如第一节诗人分别以a和ei作为第一、四和二、三行的韵脚,形成抱韵。但在第二节中,诗人则将尾音换成ao和i,进而完成诗节内部的音韵对称形式。其他如《寂寞》《奈何》《远行》《傍晚》《大车》《无题二》《无题三》《水分》《白螺壳》等诗歌,也都采用了以诗节为单位的换韵方式。使诗歌在整齐中蕴含着变化,在变化中又潜藏着和谐,为诗歌带来繁富的音韵对称效果的同时,也为诗人们提供了更加自由的韵律选择,同时也从技术操作层面增加了诗韵与诗情间相融相通的可能。
第二,在古今中西诗学的融通中,卞之琳认为交错押韵在传统汉诗中虽然鲜有,但在旧词特别是早期《花间集》中却较为常见,因此,不可以简单地将其纳入到西诗行列,“至于韵式,随韵(aabb)、交韵(abab)、抱韵(abba)、还有阴韵、复韵,也并非西诗的独创,我一再说过,我国上至《诗经》,下至《花间集》(和一些宋词慢调),今至一些地方民歌,也就早用过或还在用”(卞之琳:《奇偶音节组的必要性和参差均衡律的可行性》,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573页。)。而对于其在新诗中的应用,卞之琳则表示:“今日我们有些人,至少我自己就常用,甚至用很复杂的交错脚韵安排”(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56页。)。具体而言,在卞之琳的诗歌中,交错押韵主要以“交韵”(abab)、“随韵”(aabb)、“抱韵”(abba)以及多种音韵对称方式相交织的形式呈现。先看交韵(abab)。在卞之琳的诗歌中交韵的音韵对称形式较为普遍,有全诗都使用这一韵式的诗歌,如《水分》《远行》《大车》《旧元夜遐思》《给地方武装的新战士》《给一位刺车的姑娘》《给西北的青年开荒者》《雪》《足迹》等;有在部分诗节或诗行使用这一韵式的诗篇,如《淘气》《长途》《无题三》《白螺壳》《给一处煤窑的工人》《给委员长》《给一切劳苦者》《噩梦》等。这里以《水分》的第一节为例:“蕴藏了最多的水分的,海绵/容过我童年最大的崇拜/好奇心浴在你每个隙间,/我记得我有握水的喜爱。”在这里诗人以诗行为单位,并利用跨行的手法,分别以元音an和ai作为第一、三行和二、四行的韵脚,形成交错对称的形态,使诗歌在重复与变化间完成了和谐有致的音韵建构。再看随韵(aabb)。在卞之琳的诗歌中,《酸梅汤》《傍晚》《落》《无题三》《给抬钢轨的群众》等诗歌或整体或部分地采用了随韵方式建构诗歌内部的音韵对称形式,以诗歌《酸梅汤》为例:“可不是?这几杯酸梅汤/怕没有人要喝了,我想,/你得带回家去,到明天/下午再来吧;不过一年/到底过了半了,快又是/在这儿街边上,摆些柿、/摆些花生的时候了。……哦,/今年这儿的柿,一颗颗/总还是那么红,那么肿,/花生和去年的总也同。”在这首诗歌中,诗人使用了较为自然的口语,并且以连续跨行的方式建构起和谐有致的随韵形式,有效地串联起了整首诗的情绪,为诗歌带来了较为谐畅的韵律节奏。最后看抱韵(abba)。《对照》《灯虫》《给〈论持久战〉的著者》《给一位集团军总司令》等诗歌中都使用了抱韵来搭建诗歌的脚韵格式。除此之外,在卞之琳的诗歌中,还有以现代手法处理完成的多种音韵对称方式相交织的音韵形式,如《无题三》就以交韵和随韵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诗节间的音韵对称,《过节》《黄昏》中的音韵对称则是抱韵和随韵的结合,给诗歌增添了更加丰富的音韵对称效果。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在卞之琳的诗歌中,诗人善于以自由、多样的现代化手法,组织营构符合新诗文体特征的交错音韵对称形式,为新诗提供了更加丰满、立体的听觉效果。不过,在具体建构过程中,卞之琳也十分注意结合新诗自身的语言及文体特性,对交错音韵对称的建构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他指出:“由于语言本身的性能不同,脚韵交错得太复杂,间隔得太远,在我们新体诗里大致不大行得通。”(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56页。)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卞之琳认为过杂或过疏的对称形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交错音韵对称的诗学效果产生消极影响。
第三,随着现代汉语虚词在新诗中的大量使用,阴韵,这一独特的音韵对称形式,重新受到诗人們的关注。何谓阴韵?王力曾表示,在诗歌中“韵脚如果只有一个音节,叫做阳韵;如果含有两个或三个音节,叫做阴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在汉语里,适宜于外加律的字不多,只有‘了’‘着’‘的’‘呢’‘吗’(么)‘儿’‘子’等字。有些诗人便用这些字来造成阴韵。”(王力:《汉语诗律学》增订本,第883、884页。)卞之琳从古今中西诗学融合的角度,在新诗创作中也大胆启用了这一音韵对称方式,为诗歌带来了更加繁富工巧的韵律效果,从其创作来看,《傍晚》《黄昏》《月夜》等诗歌都使用了这一手法。以诗歌《月夜》为例:
月亮已经高了,
回去吧,时候
真的是不早了。
摸摸看,石头
简直有点潮了,
你看,我这手。
山是那么淡的,
灯又不大亮,
看是值得看的,
小心着了凉,
那我可不管的,
怎么,你尽唱!
——卞之琳:《月夜》
全诗由2个诗节组成,在具体建构中,诗人以诗节为单位,以换韵的方式在诗歌中形成了两组ababab的交韵对称形式。而在交韵的建构中,诗人又分别以“了”和“的”为外加律,在诗行与诗节间形成了有规律的阴韵对称形式,使诗歌的音韵对称效果更加多样、精巧。不过,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阴韵在汉语新诗中若用之不慎,容易造成谐谑甚至滑稽的感觉。《尝试集》中就不乏这种误用的例子,以至被人讥称‘好了歌’。”(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第158页。)因此,阴韵的音韵对称方式虽然可以为诗歌增加更为丰富的韵律效果,但在具体使用中必须谨慎。值得一提的是,在阴韵使用的基础上,卞之琳也进一步关注到内韵即复合韵在新诗中的作用,他指出:“至于由阴韵发展到复合韵。例如我在《叫卖》这首小诗里用的‘小玩艺儿,/好玩艺儿’,那是过去从北平街头叫卖人口里如实捡来,……这种情况外国也不是没有。”(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56页。)内韵的对称方式,在卞之琳的新诗创作中还有很多,既能够为诗歌带来诗行内的音韵和谐,也有助于从声音的角度营造与契合诗歌的情绪,在下文论述卞之琳诗歌中的音韵对称与诗情的巧妙融合时还会对这一音韵方式有进一步介绍。
三、现代音韵对称实践路径之二:内外交融下精致的韵律效果
卞之琳对中西方音韵对称形式的巧妙融合与应用,造就了其诗歌繁富工巧的韵式特点。不过,相比较纯粹自足的音响效果,卞之琳更加关注外在韵律与内在诗形及诗意间的照应与配合。在具体建构过程中,卞之琳善于以精巧的音韵对称形式呼应诗歌的视觉直观效果与情绪,这使得其诗歌的音韵对称效果在繁富之余又充满了微妙与精致之感,不仅进一步丰富了音韵对称的诗美内涵,也在内外交融中使诗歌达到了整体的有机统一。
Elizeabeth Drew在《现代诗的诸方面》中表示:“格式有两层意义——视的格式与听的格式——它的目的是通过了目与耳之精微的内在引导而服事于诗的主题。诗的主题与情调就在格式中被启示,被解释。格式并不只是一种装饰的或和谐的安排,它乃是一种机构上的引导。”(Elizeabeth Drew:《现代诗的诸方面》,转引自李广田:《诗的艺术——论卞之琳的〈十年诗草〉》,《李广田全集》第4卷,第246页。)从这一论述可以看出,视觉与听觉间既有着天然的审美关联,二者的交互融合也有助于诗歌主题与情调的有效传达。传统汉诗虽然具有和谐的外在声律之美,但竖行直写的方式却极大地遮蔽了汉诗的视觉效果。不过,随着分行形式在新诗中的大量应用,诗歌的“建筑美”即视觉直观效果也逐步受到新诗创作者们的注意,再加上汉语一字一音的语言特性,更为视觉与听觉的融合提供了丰富的可能。以新月派诗人为代表的新诗人就曾从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维度为新诗指出了新的审美路径。卞之琳也十分注重视觉与听觉间的审美关联,从音韵对称的角度来看,在诗歌创作中,诗人试图以独特的音韵对称方式与诗形的视觉直观效果形成巧妙的呼应,在诠释诗歌主题的同时也为诗歌提供了精巧别致的诗美效果。以诗歌《黄昏》为例:
闷人的房间
渐渐,又渐渐
小了,又小,
缩得像一所
半空的坟墓——
啊,怎么好!
幸亏有寒鸦
拍落几个“哇”
跟随了风,
敲颤了窗纸,
我劲儿一使,
推开了梦。
炉火饿死了,
昏暗把持了
一屋冷气,
我四顾苍茫,
像在荒野上
不辨东西,
乃头儿低着,
酸腿儿提着,
踱去踱来,
不知为什么
呕出了一个
乳白的“唉”。
——卞之琳:《黄昏》
从诗歌的视觉直观效果来看,全诗共由4个诗节组成,每节6个诗行,但在具体安排过程中,诗节内部的诗行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在两个诗行的连续对称后,第三个诗行一律采取缩进2个字节的方式,形成视觉上的参差变化之感,而在变化与重复之间,也诞生了新的视觉对称,即每节诗歌内部的三、六两行也在视觉上呈现出均衡的对称之感,进而形成了整首诗独特的视觉对称效果。与此同时,诗人也在诗歌中积极建构出与之相应的音韵对称形式,在为诗歌增添听觉和谐的基础上,形成视觉与听觉的巧妙融合。如在诗歌中视觉上连续对称的诗行,诗人一律以随韵(aa)形式为其安排韵脚,如首节的第一、二行就以元音an形成连续的音韵对称形式,而在第三、四节中,诗人更以阴韵对称形式配合诗歌的视觉对称效果,如第三节的一、二行与第四节的一、二行就分别以元音i+“了”与元音i+“着”的方式形成了严密的阴韵对称形式。在此基础上,为了配合第三、六行在视觉上的参差对称之感,诗人以换韵的形式在诗歌中形成了三、六行分别押韵的形式,而在多重音韵对称的配合下也逐步形成了与诗歌的视觉直观效果极为相称的aabccb的随抱相杂的较为复杂与和谐的音韵对称效果,以精巧别致的方式为现代汉语诗歌带来了崭新的诗美体验。
除《黄昏》一诗外,《胡琴》《一块破船片》《傍晚》《一个和尚》《夜风》《古镇的梦》等诗歌在建构中,也十分注意韵律与视觉直观效果间的呼应和配合。如《夜风》一诗就以abab的随韵方式配合了诗歌长短相间的参差交错的视觉直观效果;在《古镇的梦》第二、三两节中,诗人又以诗节间参差均衡对称的方式完成了视觉与韵律的双重建构:
敲不破别人的梦,
做着梦似的
瞎子在街上走,
一步又一步。
他知道哪一块石头低,
哪一块石头高,
哪一家姑娘有多大年纪。
敲沉了别人的梦,
做着梦似的
更夫在街上走,
一步又一步。
他知道哪一块石头低,
哪一块石头高,
哪一家门户关得最严密。
——卞之琳:《古镇的梦》(节选)
在此诗中,外在韵律与内部诗形间的巧妙融合,不仅带来了集视觉与听觉于一体的多重美感,也在精巧与严密之间,进一步扩大了新诗的审美维度,为新诗音韵对称增添了新的诗美效果。
在对卞之琳诗歌艺术的研究中,有学者曾发现卞之琳诗歌中的韵律节奏与诗意传达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非常重视诗作为意义与声音的有机结合体在声音层面的重要性”,“他对声音层面的关注,是以对意义层面的关注为前提的。每个字的音色和音质以及它们在诗中呼应、对比、变化的效果,总是服务于诗人表情达意的需要”(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第156页、166页。)。注重外部韵律与内在诗意间的熨帖融合,以不同音质的韵式传达、呼应诗歌的情绪,也是卞之琳诗韵效果呈现出精巧别致的原因之一。这里以诗歌《一个和尚》为例。这首诗歌虽然是一首十四行体诗,但在诗形的安排过程中,诗人并没有简单套用4433的常规结构,而是利用韵律与诗形的巧妙融合,搭建出独特的诗形效果,如第一节就以“天”“梦”“踪”“片”为韵脚形成了abba的抱韵效果,与此相应在外部诗形上诗人以第二行与第三行的缩进为标志,呈现出视觉上的环抱形式,有效提醒了读者视觉与听觉上的双重注意。从诗意传达的角度来看,在这首诗歌中,诗人有意借“钟声”这一核心意象展现一个和尚困倦、无聊的日常生活,进而传达出一种厌倦的情绪。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形神兼备地描摹出古寺钟声沉闷悠远的听觉效果,诗人不仅精心选用了元音ong(或与ong相协的eng)作为诗歌脚韵的音质基础,如“梦”“踪”“中”“衷”“重”“钟”,还有意识地在诗行内部选用大量以元音ong(或eng)结尾的字,如“撞”(“一天的钟儿撞过了又一天”“他又算撞过了白天的丧钟”)、“梦”(“昏沉沉的,梦话沸涌出了嘴”)、“空”(“头儿木鱼儿一样空,一样重”)既形成了丰富的内韵效果,也进一步增加了钟声在诗行内部的回响,形成了全诗范围内钟声的交替回响。除此之外,诗人以元音ong为基础形成的诗歌内部较为密集的声音重复,其在韵律上所具有的单调之感,也契合了诗歌以困倦为主的主要情绪,从音响角度增加了诗情传达的有效性。卞之琳曾表示:“《一个和尚》是存心戏拟法国19世纪末期二三流象征派十四行体诗,只是多重复了两个脚韵,多用ong(eng)韻,来表现单调的钟声,内容却全然不是西方的事物,折光反映同期诗作所表达的厌倦情调”(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60页。)。由此可见,卞之琳对于诗歌音韵的择取十分注意,如果换成别的韵,诗人在这首诗中想要传达的困倦之感,可能就不会如此妥帖了。
选用与诗情较为契合的音质为韵,进而从声音角度促进诗情传达的有效性,这一精巧的音韵对称方式在卞之琳的诗歌中还有很多,如《夜风》就以一系列的in为韵脚,在诗行间营造出夜风清冷凄切之声。而除了脚韵对称外,卞之琳也善于选取恰当的音质作为内韵,在由内而外之间借声音的营造契合诗情。如在《白石上》一诗中诗人就写道:“用颤抖的手儿/揉揉酸溜溜的倦眼”以一连串的ou音呈现出游移不定的踟蹰感,又如《淘气》一诗的第三节:“我这八阵图好不好?/你笑笑,可有点不妙,/我知道你还有花样——”用一长串ao音的绵延交错,使诗歌充满了轻松活泼的情调和氛围,很好地配合了稚气十足的“淘气”之感。《灯虫》的第二节的起始两行:“多少艘艨艟一齐发,/白帆篷拜倒于风涛,”则以“艨”“艟”“发”“帆”“篷”“拜”“倒”“涛”等音节,“使我们听到了海上的声音”。《大风》也从声音上“给了我们一种洪荒玄远的感觉,也仿佛就听到了那大车的工东之声”(李广田:《诗的艺术——论卞之琳的〈十年诗草〉》,《李广田全集》第4卷,第245页。)。《倦》与《古城的心》也都以不同的音质完成了音韵与诗情间的巧妙融合。再如《长途》一诗的第二节,其中“几丝持续”“牵住西去”等形成了以元音i为主旋律的韵律节奏,较为传神地模拟出蝉的声音,卞之琳自己也曾指出,“几丝持续的蝉声”与瓦雷里《海滨墓园》中同是写蝉声的名句颇为相像(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江弱水、青乔编:《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60页。)。李广田曾将卞之琳诗歌中音韵对称与诗情较为融洽的诗歌称为“形声诗”,江弱水也曾从谐音、拟声的角度论述过卞之琳诗歌音韵对称的这一特征,这些称谓也从侧面透露出卞之琳在诗歌声音与意义融合方面的匠心独具。
江弱水在论述卞之琳诗歌中的音韵对称时曾表示:“以上这些押韵技巧,既出于表达某种特殊的情味的需要,也是对现代汉语音乐性上之种种潜在可能的探索。从主观上说,卞之琳有一种因难见巧的心理,有意识地在诗中设置并克服一些困难的条件,从中获得艺术的满足。”(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第160页。)在音韵对称的具体应用中,卞之琳突破了“无韵不成诗”的强制性规范后又适当纠偏了“无韵自由诗”的矫枉过正。在他的诗歌中,音韵对称成为纯粹的诗艺建构方式,既获得了较为自由的建构空间,可以积极采纳古今中西音韵诗学中多样丰富的诗学资源,还进一步打破了韵律节奏的外在装饰作用,为音韵对称增加更为丰富的诗学内涵,在内外交织中,形成更為精巧别致的音韵对称效果,为现代音韵对称诗学开拓出更加丰富、现代的审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