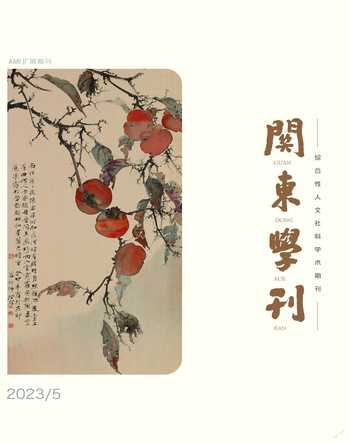马克思与爱因斯坦的会通
[摘 要]本文在简述牛顿系统思想后,探讨了康德、黑格尔两位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系统思想主要内涵及他们与近代物理学的关系,分别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角度梳理了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与爱因斯坦相对论两个方向论题之间的关系,据此阐明马克思主义、爱因斯坦相对论哲学在唯物主义观上一脉相承而殊途同归。
[关键词]近代物理学;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相对论;唯物主义
[作者简介]李节(1969-),经济学博士,男,成都体育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成都 610041)。
一、引论
英国物理学家、科学史学家斯诺(C.P.Snow)于1959年提出了“两种文化”(Two Cultures)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分为“人文文化”和“自然科学文化”两个大阵营,这两个阵营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隔阂和互相不理解的问题。人文文化强调人文关怀、情感表达和艺术审美,重视人类自身的哲学、文学、历史等领域的研究。而自然科学文化则注重数理推理、数据實证和技术创新,尤其是物理、化学、生物等领域的研究。一些文化人士对科学技术缺乏理解和兴趣,同时,一些科学家对于人文艺术也缺乏兴趣和理解,这导致了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他强调,消除两种文化的隔阂和构建一种综合的文化视野,是当代社会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他认为,唯有通过促进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才能够实现人类智慧的最大化,推动科技和人文发展的和谐统一。但这种和谐统一是一个复杂问题,需要涉及科学、人文、社会等多个学科才有望解决。
就在斯诺提出“两种文化”观点的前后,从二战前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应运而生了系统科学、系统哲学、系统工程三种形态的现代西方系统思想。现代系统思想是文理相通最为成功的一种思想。系统思想强调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分析和思考,因此,人们可以在整体性或系统性的视野下,超越传统的学科边界和分割,避免陷入局部性的思考和对立的观念,缓解“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和矛盾,更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和应对复杂问题,促进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沈小峰、王德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的趋势和问题》,《哲学研究》1986年第5期。)。
众所周知,在古代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不分家的。西方若干年前几次评选了千年思想家或哲学家,马克思与爱因斯坦常占据着前两名。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人文社会科学,而爱因斯坦物理学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代表自然科学;如果以20世纪中叶的现代系统科学为桥梁,初步论证了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物理学会通(李节:《马克思经济学的现代系统范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年。),那么,很自然地会引出一个新的问题:假定现代系统科学是西方“两种文化”会通之“流”,我们能否不需要现代系统科学作为中介,在20世纪前叶甚至更早的时间,从近代西方系统思想发生之处,从西方“两种文化”之“源”处,直接找到马克思与爱因斯坦的会通之处?(本文是应2019年底杜永明同志和海藤壶同志要求所作的。)有人说:人文与科学在康德那里汇聚,又从康德那里分叉(牟宗三:《中西哲学会通之十四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9页。),那么,康德会是马克思与爱因斯坦分别之前的“两种文化”会通之“源”么?
一般认为,康德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文革”中的钱锺书先生从认识论的角度指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开宗明义说,知识一定是从经验开始的,却不一定完全从经验出(钱锺书:《管锥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91页。)。那么,康德哲学是从什么经验开始的呢?又出到何处呢?
我们先来看康德哲学之“出”。列宁在1908年指出了两个方向:“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康德在承认空间、时间、因果性等等的先验性时,他就把自己的哲学引向唯心主义。”(列宁:《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4页。)于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与彻底的唯心主义从左右两边都批判它,也就形成了后来的两派:向右的唯心主义、向左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学派,从康德那里向左走,走向完全否定一切唯心主义和一切不可知论”(列宁:《列宁全集》第18卷,第211页。)。一战前夕,列宁指出: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思想来源之一(列宁:《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2页。)。又过一年,列宁更明确地说:写博士论文时的马克思是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8页。此外,参见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7页。)。由于《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直接批判马赫主义,也在批判康德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受此影响,从1949年到1978年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年间,中国学界一直重黑轻康(丁东红:《百年康德哲学研究在中国》,《世界哲学》2009年第4期。)。由于《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也评论了很多物理学家,由于马赫与爱因斯坦之间的关系,加之“文革”中批判爱因斯坦(周培源1936年曾参加过爱因斯坦主持的关于相对论的研讨班。文革时他是这样说的:“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已被事实证明,批不倒。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议,可以讨论。”见胡大年:《“文革”中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中国科学院“相对论批判组”再考》,《自然科学史研究》2018年第3期。),中国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前要客观完整再现德国古典哲学原貌是有难度的。因而才会出现80年代初如饥似渴的一幕:1981年初《哲学研究》要刊登康德专稿,齐良骥先生誊好一页拿走一页,即看即送印厂(丁东红:《百年康德哲学研究在中国》,《世界哲学》2009年第4期。)。
再看康德哲学之“入”。20世纪80年代哲学传统教科书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德国古典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等辞条,主要是根据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来阐述马克思的时空理论的(俞吾金:《马克思时空观新论》,《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反映了当时学界对现代物理学的理解与马恩时空观关系的认识。为了寻求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突破,90年代初刘奔先生较早地提出了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问题。他指出:“人类的发展与自在的自然界的发展速度有着巨大的差别,因此,仅从自然科学角度理解时间是不够的,物质运动的社会形式也有自己特有的时空结构……还应从人的社会本质、社会实践的本质、社会运动的规律性来理解时间问题的重要性”(刘奔:《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社会时-空特性初探》,《哲学研究》1991年第10期。)。文中从马克思关于“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著名论断入手,提出这样一条进路:物质时空-社会(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时空-社会实践-劳动-劳动的时间结构和空间-(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论(辩证因果性)。俞吾金教授由此进入并展开了更为一般的马克思时空观(俞吾金:《马克思时空观新论》,《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他从社会时空的特征、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意义、马克思时空观的发展阶段等多个角度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批评了传统教科书“在强调时空的客观实在性时,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撇开了来自人、人的经验和人的实践活动方面的主观性因素,从而把时空绝对化、抽象化了”。他认为,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存在一种与人的实践相脱离的“自然时-空”。而传统的哲学教科书的失误正是撇开人的实践活动,从所谓的自己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或自然界本身出发去阐述马克思的时空观,形成所谓自然时空,这样就把马克思的时空观二元化了。传统教科书把人归结为高度进化的自然,笼统地说人与自然本质是统一的,以此来说明马克思自然时空观与社会时空观统一为马克思时空观,当然是不够的。
那么,究竟是从自然时空进到社会时空,还是从社会时空进到自然时空?应该怎样克服二元论,是不是像俞吾金教授所说的:“人们仍然借用传统哲学教科书中关于时空问题的表述,试图对马克思哲学的整个体系做出新的说明。这种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只有在时空观上彻底摆脱传统哲学教科书的束缚,进入到马克思本人的时空观的视野中,才能真正进入实践唯物主义的原创性的境界中。”如果说传统教科书在这个问题上偏重于科学认识论,由此得出的可说是科学时空一元论,而俞吾金则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由此得出的是不是人文社会科学时空一元论?这个进路的变化会不会有矫枉过正之嫌?是不是也走向另一极端?由于时空与因果性的密切联系,他后来很自然地探讨了康德的两类因果性(俞吾金:《康德两种因果性概念探析》,《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可以看到,真要彻底解决刘奔提出的问题,势必要追本溯源探讨康德哲学所“入”,也就是德国古典哲学所“入”。从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开篇把时空看作先验感性的最初形式,到马克思首次在完整的著作即1841年《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称《博士论文》)中论述时空问题,到后来《哲学的贫困》、1859年《资本论》开篇把价值量归结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因而作为价值形态的资本也最终可以归结为劳动时间量,再到1905年狭义相对论关于时空的认识,需要做一完整的梳理。
由此,一系列有关的问题似乎也可以做深究:由“扬康抑黑”“扬黑抑康”引出的康德与黑格尔究竟谁是马克思的精神源头?(张盾:《康德与黑格尔:谁是马克思的精神源头》,《哲学动态》2011年第2期。)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康德化、马克思的黑格尔化、马克思的费尔巴哈化?德国古典哲学整体与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何关系?(俞吾金:《论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如果1841年时的马克思没有任何唯物思想的准备,为什么能在毕业短短三四年后很快接受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转向唯物主义,并进而转向经济学研究?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上,社会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马克思自然时空观、社会时空观、马克思前后期时空观的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科学思想之间有无差异?马克思主义究竟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实践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作为中国式科学哲学或科学技术哲学,已经从恩格斯的遗著变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门学科(曾国屏、王妍:《自然辩证法:从恩格斯的一本书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门学科》,《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第9期。),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哲学并行。但从近年研究马克思主义的1515篇博士论文抽样分析看,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角度去探讨的微乎其微(胡洪彬:《从博士论文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基于1515篇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论文的抽查评估》,《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8期。)。
总之,30年过去了,目前鲜有把康德、马克思、爱因斯坦三人的时空观联系起来研究的(国内学者陈冠玉有文章《时空观念——从康德、恩格斯到爱因斯坦的发展》,《中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西方学者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如近来的阿德里安·巴登关于时间哲学、历史哲学的研究,没有提及马克思。虽然他引用了霍金的《时间简史》,提到了时间之矢、热力学箭头、心理学箭头,也提到了光锥,但没有鲜明地点出时-空是物质展开的一体两种属性。此外,对于作为人的主体时间与人之外自然的、客观的时间两者的关系思考并不深入,更不要说思考中国思想里是否有关于时间或空间的认识。因此他没有注意到普里高津的成果。见阿德里安·巴登:《解码时间:时间哲学简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由于时空问题也关乎因果观、物质观,因此,把三人的“三观”联系起来的研究就更少了。
二、康德系统思想的牛顿力学渊源及“两种文化”会通
仅仅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换言之,仅仅从《纯粹理性批判》去理解康德、理解德国古典哲学是不够的。要理解这部书并理解康德之“出”及“出”之后的影响,就不能不了解康德之“入”,了解康德思想的发生,就要联系到牛顿(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关于康德哲学、康德哲学与后来的德国古典哲学诸人的关系以及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认识,既完整又达到相当的高度。他认为:牛顿和卢梭是康德思想的两个来源。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2页。),从而立之年作为天体物理学家的康德说起(严锋:《好天》,《万象》2003年第2期。)。
(一)基于万有引力之上的康德宇宙系统演化说
近现代东方落后于西方,而西方近代最重要的事件是教会的影响力下降、科学的影响力上升([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页。),而基于科学技术之上的西方现代化深深影响了东方的历史进程,因此,科学史上最大的事件可说是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出版([英]W·C·丹皮尔著,李珩译,张今校:《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0页。)。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三编宣布发现了万有引力。由于宇宙间万事万物彼此都有引力,引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把世界看成是统一的整体即宇宙系统,上升并归纳为宇宙系统概念,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牛顿的系统思想却少有人关注。第三编主要是运用万有引力定律研究太阳系不同天体之间的运动。
第谷建立的丹麦汶岛天文台、牛顿观察彗星所在的剑桥大学([英]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赵振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610-612页。)与康德所在的哥尼斯堡,纬度只相差2-3度,都是高纬度地区,冬天晴朗的天空使人能有更长的时间看到星星、银河系。不难猜测,想象力丰富的康德会如何接着牛顿说。
康德给《宇宙发展史概论》起的副标题就是“或根据牛顿原理试论整个宇宙的结构及其力学起源”([德]康德著,全增嘏著/译,王福山校:《西洋哲学小史、宇宙发展史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1页。)。一方面,康德运用系统的同构思维发展了牛顿的系统思想,从日月系统扩大到太阳系、银河系、整个宇宙做了这样的论述:“实际上,所有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行星和彗星,由于它们都围绕一个共同中心体运转,已经组成了一个‘系统’”,“各个恒星都联系在一个共同平面上,从而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这是许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人们看到,在无限远的距离上还有着更多这样的星系。在这个无限辽阔的范围中,造化处处都是有规则的,它的各个成员都是相互联系着的。还可以进一步猜测,这些更高的世界系统也不是互不相关,而是通过相互联系又构成了一个更加广大的系统。我们确实看到,这些椭圆形的云雾状星体,如德·莫佩尔蒂(即莫培督,此时正任柏林科学院院长。见许良:《莫培督——一个被遗忘的天才》,《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2期;《一个应受到重视的法国启蒙思想家——莫培督的科学与哲学思想评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所提出的那样,都同银河的平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德]康德,全增嘏著译,王福山校:《西洋哲学小史、宇宙发展史概论》,第73、79页。)这里康德明白无误地把宇宙看成不同等级、层次的系统([苏]阿尔森·古留加:《康德思想今论》,《哲学译丛》1981年第5期。黄小寒:《世界视野中的系统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15頁。)。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康德研究天体本身是如何在引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下形成并演化的,也就是提出了星云演化思想。学界对此、对恩格斯的评价多有论述,此不赘述。
(二)康德哲学对牛顿经验主义与笛卡尔理性主义的调和
速度是连接空间与时间的直观形式,通过叠加可以不断增大(中国古代也有描述。荀子《劝学》篇中说:“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伽利略总结成叠加原理,牛顿在他发现的加速度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总结出牛顿第二定律。对在大学执教长达41年的康德来说([苏]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贾泽林、侯鸿勋、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9页。),这些可谓滚瓜烂熟。
人总是从后往前思索的。57岁已近耳顺之年的康德开始对物理学经验做哲学层面的总结,天体物理学家康德由此而成为哲学家康德。经过长达12年的思考,厚积而薄发,康德写作《纯粹理性批判》时间并不长。他说:“没有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在这里没有得到解决,或至少为其解决提供了钥匙。”([德]康德著,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休谟否认因果关系,把思维带进了死胡同([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第196页。)。笛卡尔虽然生在休谟之前,但从逻辑上看却在休谟之后。当他把“我在怀疑”当成一个确定的、不能怀疑的事,并提出“我思故我在”时,朝着世界是可知、可认识的方向走出了积极的一步。如果继续追问:肯定“我在”这个事实的“我”又在何处呢?当一个人说“我和这个世界”时,这个“我”与“这个世界”是什么关系呢?这个“我”是不是“在”“这个世界”里呢?既要总结哲学,总结笛卡尔,又要总结数学与物理,总结牛顿的时空观、系统思想,总结自己年轻时的星云演化说中的系统思想,像几何学那样确定几条公理然后演绎出整个哲学体系,换言之,给理性确立何种最初的、可靠的前提,而又不倒退到休谟。那么,康德是如何解决的呢?解决的钥匙就是:肯定时间和空间具有“经验的实在性”,“我”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的,因此,“我在”与时间、空间的同在,都是无可争议和确定的事实。经此处理,“我在”之后的科学就可以继续演绎下去了。也就是說,先有时间与空间的存在,才有“我在”。先有牛顿的时空,后有笛卡尔的“我在”。这就形成了《纯粹理性批判》的开端即在先验感性论中定义“感性”:通过我们被对象所刺激的方式来获得表象的这种能力(接受能力)([德]康德著,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第23页。),紧接着展开论述空间和时间(事实上,牛顿影响的不只是德国哲学,还有德国文学,因而,一定程度也影响了德国的启蒙运动。比康德小5岁、同处一个时代的莱辛,在其名著《拉奥孔》里就运用了时与空的关系来把握雕塑,见钱锺书:《读〈拉奥孔〉》,《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3页。)。不过,“先验感性”一词充分反映了康德的纠结:先验既然是先于经验的,是纯粹的,那就应该百分之百与经验无关,而感性又是与经验有关的,“先验感性”不是矛盾吗?
我们今天能很容易地把主客观、主客体截然分开、先分后合,可对要调和笛卡尔理性主义与牛顿经验主义成份的康德来说,这种挣扎不可避免。而正是康德的这个贡献,使康德之“出”并不只是列宁所说的哲学内部的一分为二——一路向左走向唯物主义,一路向右走唯心主义,而首先是哲学与物理学的一分为二,他对物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包括音乐(赵鑫珊:《贝多芬的音乐创作与康德哲学》,《文艺研究》1983年第3期。))两线并行的影响也由此开始。德国古典哲学不仅如马克思所说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版,同时也是牛顿力学的德国版。
三、奥斯特电流磁效应实验及其德国古典哲学背景
如果说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李节:《马克思经济学的现代系统范式》,第129页。),而光合作用是新陈代谢的重要部分,光是电磁波的一种形式,那么,统一了光、电、磁的电磁学正是从奥斯特电流磁效应实验开始的,英法德物理学由此开出了一片新天地(许良:《德国现代物理学和康德哲学》,《哲学分析》2015年第3期。)。这个实验不仅在物理学上开创了电磁学,继引力之后发现了新的相互作用;而且在哲学上,上承康德、下启爱因斯坦。影响了奥斯特的正是康德(学界长期存在一个误解:奥斯特是在偶然间发现了电流磁效应。有关内容见[美]弗·卡约里:《物理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0-171页;宋德生:《奥斯特和电磁相互作用》,《自然杂志》1981年第6期;黄亚萍:《奥斯特的预想与电磁效应的发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2年第3期,黄文还特意提到了谢林1832年评法拉第新发现的文献;杨建邺:《伟大的科学家、教育家H.C.奥斯特》,《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6期。)。
1799年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Hans Christian Oersted)在博士论文《论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廖祥勇:《对奥斯特实验的再认识——纪念电流磁效应发现200周年》,《物理通报》2021年第2期。
)中阐述了康德哲学在自然哲学中的重要性和应用,相信“电与磁是有关系的”。1801年奥斯特到柏林结识了逃离耶拿的费希特,开始读谢林的书并听自然哲学讲座。
1799到1803年,奥斯特身处柏林,在这短短4年间,德国古典哲学正经历着最灿烂的一幕。康德还健在,只是人在普鲁士王国的哥尼斯堡。而在萨克森-魏玛公国,围绕在教育和文化部长歌德周围,形成了一个耶拿大学的艺术、学术团体——康德的学生也是歌德的老师赫尔德,后来的第一任柏林大学校长洪堡,文学家席勒,哲学家谢林、黑格尔、荷尔德林都在耶拿大学。1799年8月费希特与康德决裂,三十而立的黑格尔完成《基督教精神及其命运》,在伦理学中萌发了黑格尔辩证法([苏]阿尔森·古留加:《黑格尔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4页。萧诗美虽是国内不多的注意到古留加这个观点的,但他的解读变成了另一个方向。见萧诗美、蒋贤明:《从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督教神学起源重新理解西式辩证法的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3年第1期。)。1801年黑格尔转到耶拿大学后,为了获得在耶拿大学的无薪讲师职位,他写了《费希特哲学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异同》,并在次年公开支持谢林反对费希特哲学。但刚过一年,1803年黑格尔开始不赞成谢林哲学,而形成了自己的哲学。
这一时段,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时空同在、师徒关系辗转相生,完成了德国古典哲学质的变化。概括地说:从康德的主体与客体两分的二元论,演变成费希特基于“主观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并进而演变成谢林的“基于客观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谢林认为客体因素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统一的体现者,使德国思维转向自然科学,甚至有唯物主义色彩([苏]阿尔森·古留加:《黑格尔传》,刘半九、伯幼等译,第30-31页。汝信:《德国古典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139-142页。)。而黑格尔哲学也开始萌芽。
就在1803年,奥斯特就断言:“我们的物理学将不再是关于运动、热、空气、光、电、磁以及我们所知道的各种其他现象零散的罗列。我们将把整个宇宙容纳在一个体系中。”(转引自陈晨星:《这个发现猛然打开了黑暗领域的大门》,《中国科学报》2021年1月14日。)物理学和德国古典哲学都在酝酿一个新的时代。
1806年10月13日,拿破仑大军攻下耶拿时,《精神现象学》杀青。10月27日拿破仑大军继续向柏林进发,费希特被迫先从柏林跑到哥尼斯堡,而后又于1807年6月到哥本哈根找奥斯特避难(梁志学:《费希特哲学体系简评》,《现代德国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07年。)。费希特与奥斯特谈了什么,有待考证。就在费希特与奥斯特会面前,1807年4月《精神现象学》刚出版不久。因此,黑格尔不大可能影响奥斯特。
经过16年的探索,奥斯特于1819-1820年间在课堂上做了实验,发现了电流磁效应,把电与磁两种现象联系起来。他的论文发表两个月后,法国安培和毕奥萨伐尔在他的基础上发现了用两人名字命名的定律,我们今天的5G时代由此开启。
四、黑格尔的系统思想
(一)感性确定性中“这一个”与“这一位”体现的系统时空观
德国古典哲学的范畴及思想的发生与正式呈现并不总是同步的。黑格尔1801年到耶拿后,虽然与康德本人没有直接的来往,但此前已读过《纯粹理性批判》,加之与德国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赫尔德同处一校,赫尔德提出现象学思考,对黑格尔是有启发的(贺麟:《译者导言》,[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7页。)。歌德是赫尔德的学生,对耶拿时期的黑格尔也有帮助([法]雅克·董特:《黑格尔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2页。)。黑格尔已经从康德的好几位杰出学生处了解了康德。
《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首部正式出版的著作,有着“作为逻辑学的导言、作为意识发展史、作为一个自身的全体”三位一体的特征。但另有很多想法,还不成熟,也来不及展开。《导论》一章,就是接着康德讲的。因此,首个面世的哲学范畴“感性确定性”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那么,它与时间、空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黑格尔以“这一个”为例,把“这一个”分解为“这时”与“这里”,即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存在形式([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译,第65-66页。)。反过来说,就是把“这一个”事实上看成“这时”与“这里”的综合体,他用的术语是“共相”。“这一个”与“那一个”、此事物与彼事物、此共相与彼共相,换成今天的话,就是此时空体与彼时空体的对立(邓晓芒:《对〈精神现象学〉“感性确定性”章的现象学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可惜的是作者虽然已经意识到对黑格尔的解读应该从头开始,但却从现象学角度入手,而没有从相对论视角入手,割裂了时间与空间的一体性。作者认为:“对象的‘这一个’则首先是在时间中的‘这时’,其次才被‘我’这一位确定为‘这里’。‘这时’比‘这里’要优先,因为‘这时’涉及对象,而‘这里’则取决于‘我’(这一位)的位置”。失去了引入并联合自然科学的绝好视角。不过这比张一兵笼统地说“黑格尔是从感性确定性(sinnliche Gewissheit)复归主体观念的精神现象学”还是要精细多了。见张一兵:《否定辩证法:探寻主体外化、对象性异化及其扬弃——马克思〈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要〉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邓晓芒把主体的“这一个”也就是“我这一个”译为“这一位”,保留了贺麟关于对象、客体的“这一个”的译法(邓晓芒:《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6页。),把主客体分得更清楚了。但不论是“这一位”还是“这一个”,都纠正了康德时空二律背反的论证。康德假定世界不存在时,还有虚空时间存在,用今天的话说,在时间的零点时刻之前还有负时间。而我們知道,根据广义相对论,当时间为零时,空间也变为零。可以看到,黑格尔是接着康德在讲时间与空间,但不像康德那样,把时间和空间作为感性的最初形式,而是把主体的“这一位”和客体的“这一个”的时空体作为感性的最初形式,也就是黑格尔哲学的首个前提。两者都具有感性确定性的特征。把从外在于人的时空置于主体之后,已经暗含着黑格尔后来把时空看成绝对精神的外在体现的做法,这在后面1817年出版的《哲学全书》第一版的第二部分,也是第二个理论环节《自然哲学》中可以得到佐证。黑格尔鲜明地引用了康德的原话:“空间和时间是感性直观形式”([德]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薛华、钱广华、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0页。),也预示了《逻辑学》把时间和空间作为量的规定性之一种([德]黑格尔:《逻辑学》,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199页。)。这是因为,如果说“界限就是事情终止的地方,或者说,界限就是那种不复是这个事情的东西”([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贺麟译,第2-3页。),那么,不同事情的界限就转换成不同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也就是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大小的差别,也就是数量差别。独立于人身之外的自然时间和空间,就可以作为自我之外的“有”展开它们的“量”。
综上,牛顿的时空概念被康德抽象概括为感性直观,接着被黑格尔改造成“感性确定性”,变成了自己的绝对精神的最初环节。“感性确定性”于是成为黑格尔通向“实体即主体”的绝对唯心主义的秘密和起点(章忠民:《黑格尔的“感性确定性与真理性”——通向“实体即主体”的绝对唯心主义的秘密和起点》,《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8年第6期。),这里的主体即绝对精神。黑格尔不再是简单地重复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而是经历了康德对笛卡尔、牛顿的调和,紧跟着“感性确定性”首次提出了“辩证法”([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译,第65页。)。黑格尔唯心辩证法首次在正式出版物中面世,萌芽于伦理学时期的痕迹消失了。经过如此改造,时空概念的自然痕迹大大淡化了。
(二)“力与知性”的牛顿力学渊源与哲学改造
对《力与知性》这一章,学界论述不多(姜勇君:《知性辩证法——〈精神现象学〉中由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过渡》,《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黑格尔在具体阐述“力”之前,在导言性质的论述中说:“这两个环节表面看来最初呈现出,一方面是许多持存的质料之普遍媒介,另一方面则是自身反思的一。”邓晓芒认为:“自身反思的‘一’就是实体本身,质料有许多,而实体只有一个,整个宇宙只有一个实体,那就是一,那就是自然本身,这个‘一’是不可分割的,也是无所不包的。”(邓晓芒:《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第378页。)这里继续体现出了黑格尔的系统整体思想。
但究竟如何理解“力与知性”这个环节呢?事实上,只要知道黑格尔想把万事万物都纳入到一个体系里,我们就能明白,黑格尔把“力与知性”放在“意识”这个大环节之下,而放在“自我意识”之前,是把物理现象改造为哲学的一个环节。这也意味着,具有客观性的物理现象,在“自我意识”之前,或者说,客观性先于主观性而存在;并把力的本质界定为超感官世界、现象界,而规律是现象界的真理等等([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译,第100、102页。),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特征发端于此。我们也因此知道,黑格尔之后的任何哲学,都不可能再倒退回极端的主观主义。
黑格尔的具体论述是:“那些被独立地建立起来的东西直接过渡到它们的统一性,而它们的统一性直接过渡到那种展开,而这种展开又再返回到那个归结的做法。但这种运动就是那被称之为力的东西;力的一个环节,其力之作为那些在其存在中具有独立性的质料之扩散;就是力的表现。但是力作为这些质料的消失了的存在便是从其表现中被逼回到自身中的力或本来意义上的力。”(邓晓芒:《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第388-392页。)在物理学中今天已知的四种基本相互作用里,当时对万有引力的认识是成熟的,对电的认识还很不成熟,因此,黑格尔就是在这样的物理学基础上,把万有引力和电作为现象,再进一步抽象为“力”和“力的表现”这两个范畴,然后很吃力地展开论述力与力的表现的关系,也就是一与多、统一与展开、吸引与排斥的关系。此外,还提出“物质”范畴的雏形——“质料”范畴。之所以说黑格尔论述得很吃力,是因为今天的物理学已经把他所涉及的这些范畴界定得很清楚,如有静止质量的物质,与没有静止质量的光、电,引力可以看成自旋为2、自身没有质量的引力子,而物质之间的吸引就可以看作是交换引力子等等([英]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许贤明、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73页。)。不过我们还是能看到黑格尔从矛盾统一对立的哲学层面对物理现象令人惊叹的把握:“……黑格尔把一切事物、一切质料归结为力,这个思想是很前卫的。”(邓晓芒:《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第411页。)
(三)黑格尔关于奥斯特电流磁效应实验的摘录
奥斯特做电流磁效应实验的时间,正值黑格尔到柏林大学任教不久。黑格尔《哲学全书》在1827年和1830年分别做了两次修订,其中的《自然哲学》部分提到了奥斯特的实验([德]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薛华、钱广华、沈真译,第315页。)。如前所述,当时只对引力一种相互作用有了较成熟的认识,对电磁相互作用的认识刚刚露头于奥斯特实验,因此,黑格尔还无从意识到奥斯特发现的伟大意义和法国物理学家随后的发现。
五、马克思主义蕴含的“两种文化”会通思想
仔细考察,我们会发现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中,从马克思到列宁,存在一条不那么连贯、不那么明显的科学与人文互动影响的思想线索。
(一)《博士论文》里的时空观——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的自然哲学发端
从1841年的《博士论文》到1859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的18年里,马克思先后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态》《共产党宣言》等重要著作出现,学界越来越意识到,应该联系马克思前后期和所处的环境做深入研究(聂锦芳主编:《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5页及见该书下篇。)。笔者以为,如果把马克思从1841-1845年的思想演变看作一个整体,就能看到:康德、马克思、爱因斯坦三人的时空观、物质观、因果观的发端一脉相承,而时空观是需要首先关注和重点关注的。
内田弘可能是为数仅有的学者,认为应当联系康德来研究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他指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主题就是对康德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对《纯粹理性批判》全面系统的批判。另外,《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包含了批判康德哲学的含义……马克思从写作博士论文的1840年前后到1883年逝世为止始终在阐释同一个问题。”(内田弘、由阳:《〈博士论文〉作为〈资本论〉形成史的起点》,《晋阳学刊》2017年第6期。)但是,应当联系年轻时天体物理学家的康德还是晚年哲学家的康德来研究青年马克思呢?
马克思1830到1835年就读于特里尔中学时,他的历史老师是被歌德称为“康德哲学专家”的校长胡果·维滕巴赫,那么,当时60多岁的老师会向10多岁的中学生马克思讲康德吗?目前似乎没有文献支持。不过至迟到1837年马克思读柏林大学时,在写给父亲的诗作中最早提到康德。同时,他已经在通过黑格尔的学生们读黑格尔。在关于黑格尔的两首讽刺诗和幽默小说中,马克思提道,“我把洛克、费希特和康德的著作推往一旁”,更明白无误地提道,“休谟对因果关系的存在始终持怀疑的态度……在哲学家康德之后是骑士克鲁格”,“在莱布尼茨天国之后是沃尔弗教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0、825页。)。有理由相信:马克思此时的关注点已经转向德国哲学思想发展,但关注康德到何种程度不得而知。
《博士论文》阶段的马克思与哪个阶段的康德关系更密切呢?马克思是否直接读了《宇宙发展史概论》暂不可考。《宇宙发展史概论》前言如下:“现在我可以放心地把上述的一切应用于目前我这个冒险的探讨。我假定整个宇宙的物质都处于普遍的分散状态,并由此造成一种完全的混沌,我根据给定的吸引定律看到了物体的形成,又看到了斥力改变物体的运动。我不需要任意的虚构,只要按照给定的运动定律,就可以看到一个秩序井然的整个系统产生出来,这使我感到欣然满足,这系统与我们眼前所看到的那个宇宙系统如此相似,以致我不得不把它们当作同一个东西。在大范围内自然秩序的这种出乎意料的发展,起初也使我怀疑这种正确的相互配合,怎么竟会建立在如此简单而淳朴的基础之上……但是人们会说,你为你自己的理论体系辩护,也就是在为伊壁鸠鲁的意见辩护,他的看法和你的体系极为相似,我不想完全否认我与伊壁鸠鲁的观点有一致的地方。许多人就是以这种论据为借口而变成了无神论者。但是,仔细考虑这种论据仍有使他们深信至高无上确实存在的可能。对无可非议的原理做颠倒的理解,也往往可以得出非常错误的结论。伊壁鸠鲁的结论就是这样,虽然他的设想不失其为大思想家智慧的表现。因此,我并不否认卢克莱修或他的先驱伊壁鸠鲁、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理论与我的理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德]康德著,全增嘏著/译,王福山校:《西洋哲学小史、宇宙发展史概论》,第58页。)这里康德把自己与伊壁鸠鲁、德谟克利特等做了类比。《博士论文》以这两位古希腊哲学家为对比对象,可以看到《博士论文》与作为天体物理学家的青年康德、与《宇宙发展史概论》存在间接的联系。
而《博士论文》与作为哲学家的晚年康德、与《纯粹理性批判》的关系就鲜明多了。《博士论文》所提到的“偶性”这个范畴,《纯粹理性批判》是这样定义的:“一个实体的诸规定无非是该实体实存的种种特殊方式,这些规定叫做偶性。偶性在任何时候都是实在的,因为它涉及到实体的存有。”([德]康德著,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第152页。)国内学者中,孟氧略早于刘奔和俞吾金注意到这一点(俞吾金认为:“在我国哲学界,最先对马克思的时空观作出富有创新意识的理解和解释的可能是刘奔”。孟氧:《经济时间与经济空间》,《河南财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他指出:《博士论文》体现了作为起点的马克思时空观。“马克思所使用的时间概念最先并不是取自牛顿力学,而是来源于古代希腊科学,在某种限度内还与英国古典经济学有关。”“它(指德谟克利特哲学)没有看到,当它把实体当成时间性的东西时,它同时也就把时间变成实体性的东西了,从而也就取消了时间概念,因为成为绝对时间的时间就不再是时间性的东西了……伊壁鸠鲁却不是这样。在他看来,从本质世界排除掉的时间,就成为现象的绝对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1页。)。孟氧进一步指出,当马克思把时间看成是相对性的东西时,事实上他是把时间当作有限事物的变换,并深刻地揭示了伊壁鸠鲁的时间规定:“时间被规定为偶性的偶性”。孟氧从语源的角度指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偶性”(德语Akzidenz),是指区别于实体(Substan)的变体,而不是指偶然性。当它是偶性时,时间也就发生了。马克思得到了一个认识:“事物的时间性和事物对感官的显现,被设定为事物本身的同一个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4页。)。
孟氧难能可贵地把视角拓展到了自组织系统学,把马克思自然时空观、社会时空观放到宇宙大爆炸理论、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现代物理学的语境下讨论,但并没有继续向前追溯马克思的思想来源。因此,需要更细致入微地辨析一下。事实上,此时马克思的时空观并不完全来源于古代希腊科学,而是引用了康德的认识。马克思意识到德谟克利特把实体与时间分开,并进而相对性地反思:时间不也就成为另外一个与原子实体平行的“实体”了吗?那么,这个不是时间性的绝对时间、这个与实体平行的“实体”到哪儿去了呢?马克思说:“从本质世界中排除掉的时间,被移置到进行哲学思考的主体的自我意识中,而与世界本身毫不相干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1页。)时间既然从外部进入到人的自我意识中,自然,康德就应该登场了。马克思随后说:“正因为时间是感性知觉的抽象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3页。),作为前提去评价伊壁鸠鲁。而康德认为:“时间……是感性直观的纯形式”,“不过是内部感官的形式”([德]康德著,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第31、33页。)。而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所引的是:空间和时间是感性直观形式,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用自己的语言转述的是:“时间和空间是感性事物本身的共相,照康德说来,是感性的先天形式。空间和时间就它们直接的性质说,并不属于感觉本身。我有这个或那个感觉,这感觉永远是个别的;作为共相的空间和时间只属于先天的感性。”([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64页。)对比黑格尔引用康德的话,可以看到,马克思没有通过黑格尔而是直接引用康德关于时间与空间的认识。
以上可以看出,《博士论文》时的马克思有转向唯物主义观的自然哲学或者说物理学思想基础。
(二)成形和成熟于宗教批判、政治和社会批判的马克思唯物主义观
那么,马克思后来的思想环节是怎样的?或者说,通过谁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转折?其中之一就是与马克思过从甚密的布·鲍威尔——黑格尔的学生、青年黑格尔派的首领。据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是在鲍威尔的建议和指导下写的。欧洲反犹太主义时间很长,如果说《博士论文》阶段的马克思没有清晰地剥离时间与内化的自我意识,那么,到1843年端倪出现。作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初步批判鲍威尔时指出:“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而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离出来,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基督教是犹太教的思想升华,犹太教是基督教的鄙俗的功利应用,但这种应用只有在基督教作为完善的宗教从理论上完成了人从自身、从自然界的自我异化之后,才能成为普遍的”。民族利己主义不过是一个略微放大了的“自我”,马克思对犹太民族利己主义的批判,也是对“自我”的批判;而这种自我意识的根源在于市民生活,因此,对犹太精神的批判,还是对以高利贷者犹太人夏洛克为代表的金钱或者货币的批判,“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他顶礼膜拜”。既然彻底批判了“自我”,那么,自然就会出现它的对立面“社会”,人就由“个”人变成人“类”,人的“类”本质就是人的社会性,人的解放就是社会的解放,而社会的解放,就意味着要批判地上的货币和天上的宗教。因此,“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4-198页。),整个人类社会都要从货币和宗教中解放。批判犹太教、基督教,从而批判一切宗教还是在批判人“类”一段时间占统治地位的“自我”意识。可见,批判鲍威尔后往上溯源,批判黑格尔呼之欲出。
正是这一年,马克思同时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他指出:“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9页。)马克思开始从宗教批判转向了政治批判。
回到地面的政治批判后,马克思很快就转向了经济批判。在稍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不仅把人“类”作为整体的社会学批判(李节:《马克思经济学的现代系统范式》,第30-32页。),还扩大到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批判:“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的因而是非现实的本质,——是外化的因而是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抽象出来的思维,即抽象思维”(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7页。)。货币是要被批判的,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那就意味着逻辑学也是要被批判的。“自我”本身是作为实体的自然界、世界的一部分,对“自我”意识的清理,也就是对内化为自我意识的时间意识的清理,因此,时间就不再是《博士论文》中所说的另一个平行的“实体”,也就连同“自我”回到实体,回到真实的世界,不再是异化的存在、抽象的存在、不存在的存在。我们有理由猜测:马克思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绝对知识》一章笔记中把黑格尔《逻辑学》的范畴都简单地列出来,事实上是对自己一段思想历程的总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7页。)。至此,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就完成了。旧的已去,新的当立。《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威尔及其伙伴》《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提出了唯物史观。
(三)《资本论》中时空一体的时空观
马克思指出:并存性是继起性的一个,把空间并列的资本看成同一个资本时间上先后的阶段。他把资本的生产过程分成了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建立了资本的时间结构,“不过把现成产品的各部分同时并存的空间变成了它们依次出现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8页。),在生产过程中,资本的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是交织运动的,“资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劳动力付出的体能,以产品形式出现,而产品分成了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即产品的数量结构。资本的时间结构又重新生成为产品数量结构,“并列存在本身只是相继进行的结果”(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120页。)。可以看到,这里的时空观坚持了《博士论文》阶段的时空一体观,而且进一步在经济学中具体化了。
(四)马克思关于奥斯特电流磁效应实验的摘录
《资本论》一卷用了长达近160页来说明机器大工业,占了一卷近1/5的篇幅,不可谓不重要,但长期以来学界似乎重视不够。张一兵是为数不多的从“两种文化”相通的角度做深入研究的(张一兵:《工艺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深层构境——马克思〈伦敦笔记〉中的“工艺学笔记”研究》,《哲学研究》2022年第12期。)。他提出:在《伦敦笔记》的第15笔记本(Heft Beft)共计44页摘录中,“工艺学笔记”的重点关注对象是波佩(波珀)对工艺学和工艺学史的研究;考证马克思的“工艺学笔记”,大约完成于1851年9月到10月之间,并且指出,这些笔记后来转换到了《1861-1863经济学手稿》中。他认为,对马克思的工艺学研究,也将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的深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里需要补充一个很重要的细节。马克思写“工艺学笔记”期间,1851年5-10月间在伦敦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展览会,马克思参观过这个展览会。1855年伦敦出版的著作《各国的工业》第二部就是根据对这届展览会展出展品的分析而写成的。马克思对《各国的工业》第二部做了如下摘录:“[XIX—1214](即第19本笔记第1214页)电磁学。电流通过绕在铁上的铜线圈时,铁就获得磁性。厄斯特德教授第一个发现,放在电流影响范围内的磁针,当电流通过线圈时立即产生向一旁偏离的倾向。这就是英国使用的普通型号的电力电报机原理。接着,厄斯特德发现,一个软铁棒在电流绕着它环流时,就感应出磁性。这样一来,用磁力的产生和消失的方法就可以向任何距离传送一系列信号。美国的电报机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制造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17页。)厄斯特德是奥斯特(Orsted Hans Christian)的另一个中文译名,这里所说的就是奥斯特实验(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
第634页。)。这段摘录之前的内容是:“[XIX—1213]鼓风机、磨房”,之后的页码和内容是“联合王国工厂中在业儿童、男子和妇女人数比例表[XIX—1215]I.棉纺织厂”,摘录与前后的关联性不强,显得相当突兀。虽然《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有小标题“3.相对剩余价值……(γ)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续)]”(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0页。),这表明马克思想论述机器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也试图论述以电力作为动力的机器的作用。但关于电的科学进展,全书引用的只有这一小段,其他只有个别的概念。可见,当时电磁学和技术发明与应用还不成熟,不足以给马克思提供充分的论据。正式出版的《资本论》中只有与机械动力有关的机器论。
(五)恩格斯对电磁学的局部认识
电磁学真正成熟是在1873年。此时的恩格斯已经移居伦敦,他于1873年5月30日写信给马克思谈了写《自然辩证法》的意图,最初的目的是批判毕希纳(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把《自然辩证法》的内容既按照写作的时间顺序日,也按照内容分门别类列出目录,这就既给了我们比较《反杜林论》与《自然辩证法》之间的关系的线索,也对恩格斯写《自然辩证法》的意图和过程做了提示,可以看得更清晰了。)。马克思是否赞同恩格斯從事自然辩证法研究呢?(王庆丰:《恩格斯为什么要研究“自然辩证法”》,《长白学刊》2015年第5期。)1876年,恩格斯开始写《反杜林论》,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也在同步进行,但目的相应有所变化。对比《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可以看到:一方面前者的相当部分内容取自后者的笔记;另一方面,1878年6月《反杜林论》完成时,两者的内容和篇幅是有差别的。《反杜林论》与《自然辩证法》从哲学与自然科学双重展开。《反杜林论》第一编“哲学”部分的第5至第8节“自然哲学”,显然是接着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阐述,结合新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做出新的总结与概括并有所批判。他曾向马克思念过《反杜林论》,可见马克思是赞同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
《反杜林论》与《自然辩证法》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重要差别之一在电磁学。《自然辩证法》中文版共300页,有关“电”的一节就达到了50多页,占了约1/6的篇幅,分量不可谓不重,而这一节基本上是马克思去世后才形成的。联系到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注意了1882年慕尼黑电气展览会上法国物理学家马赛尔·德普勒展出的第一条实验性输电线路(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可以推测,很可能是恩格斯写《反杜林论》时对电磁学内容积累的材料不够,也就是他说的自己要在自然科学知识上“脱毛”。当然,退一步讲,即使材料不够,已有的自然科学知识内容已经足以支持“自然是辩证的发展”这样的基本认识。因此,《反杜林论》里关于电的论述不多。而这部著作完成后,恩格斯继续搜集和学习关于电、磁的文献,《自然辩证法》里新补充的内容主要来自德国物理学家维德曼1874年的著作。维德曼比麦克斯韦大5岁,但没有注意到1873年的麦克斯韦创立的电磁理论。奥斯特电流磁效应实验做于恩格斯出生的1820年,到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引述这个实验,再到《自然辩证法》笔记,时间已过去了50多年。可能是《自然哲学》对这个实验一带而过,《自然辩证法》的电学笔记没有提到奥斯特实验,自然也就没有提到安培、欧姆等的实验发现。但奇怪和不得而知的是,马克思《1861-1863经济学手稿》对奥斯特实验的摘录,为什么没有反映在《自然辩证法》的电学笔记中。
(六)电磁学的创立与列宁的认识
麦克斯韦在大学期间读了《纯粹理性批判》,受到康德的影响,于1873年创立了电磁学,一举统一了电、磁、光三种物理现象,并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和光的电磁波本质,继牛顿之后对新的相互作用的认识成熟了([美]弗·卡约里:《物理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不久之后,亥姆霍兹(费希特的小儿子与亥姆霍兹的父亲是好友,亥姆霍兹受到了费希特的影响。许良:《亥姆霍兹:罕有的全才》,《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5期。)在德国大力宣扬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受其影响,亥姆霍兹的学生、助手赫兹于1887年实验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同年,亥姆霍兹的另一位学生迈克尔逊与莫雷还做了证明以太不存在的实验。列宁对赫兹的贡献做了哲学总结,补充了具体知识:“光的电磁理论已经证明,光和电都是同一物质(以太)的运动形式”,“红色的感觉反映每秒频率约为450万亿的以太的振动。天蓝色的感觉反映每秒频率大约620万亿的以太的振动。以太的振动是不依赖于我们的光的感觉而存在的”,紧接着评论道:“我们的光的感觉依赖于以太的振动对人的视觉器官的作用。我们的感觉反映客观实在,就是说,反映是不依赖于人类和人的感觉而存在的东西。自然科学就是这样看的。”(列宁:《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6页。)《自然辩证法》出版于列宁去世之后的1925年(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33页。),列宁看不到有关的电磁学摘录,令人惊叹的是,他敏锐而及时地补充了《自然辩证法》关于电磁现象的认识不足,虽然还不大可能注意到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意义,但还是用最新的电磁学成果论证并坚持哲学的唯物主义原则,批判“物理学唯心主义”。
六、广义相对论的唯物主义观
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不仅在物理学和哲学上既有联系,也有一定差别。
在爱因斯坦自述因果性与宗教信仰时,他说自己12岁时从信仰宗教到怀疑一切,14岁还是中学生时,他就开始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6岁时的爱因斯坦想:人追上光会怎样?通过读亥姆霍兹,产生了“时间是可疑的”看法。因此,狭义相对论本质上是一种运动学理论而非动力学的理论,并不追究运动的原因。在哲学上解决了因果性这个认识论中最核心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物质问题(乐传新:《狭义相对论并未揭示时空依赖于物质及其运动——兼与我国哲学界的几种观点商榷》,《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如果说狭义相对论是“在”空间“中”的思考,那么,广义相对论就是对空间本身的思考。我们把牛顿第二定律改写成a=F/m,左边加速度是伽利略“在”我们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中”得出的空间对时间的二阶导数,是对运动的概括,而右边是力与物质,毕氏虽然是《自然辩证法》最初的批判对象,可他的《力和物质》却影响过爱因斯坦。如果力与物质也是可疑的呢?也就是取消右边力及物质的实在性,也就是颠覆牛顿以来根植于人们脑中的观念,思考空間本身会有怎样的结果?具体说,把万有引力公式G=mg=KMm/r^r两边消掉m,可以得到g=KM/r^r,把万有引力中的引力加速度g与一般时空中的惯性加速度a做类比,想象人在引力场中顺着引力线运动会怎样(关于物体的引力质量等于其惯性质量,爱因斯坦用文字是这样表述的:“按照牛顿运动定律,我们有(力)=(惯性质量)×(加速度),其中‘惯性质量’是被加速的物体的一个特征恒量。如果引力是加速度的起因,我们就有(力)=(引力质量)×(引力场强度)其中‘引力质量’同样是物体的一个特征恒量。从这两个关系式得出。(加速度)=(引力场强度)×(引力质量)/(惯性质量).如果正如我们从经验中所发现的那样,加速度是与物体的本性和状况无关的,而且在同一个引力场强度下,加速度总是一样的,那么引力质量与惯性质量之比对于一切物体而言也必然是一样的。适当地选取单位,我们就可以使这个比等于一。因而我们就得出下述定律:物体的引力质量等于其惯性质量。”见[德]爱因斯坦:《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杨润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1页。)?可以看到,爱因斯坦两次思考很类似:前次是想象在电磁场中追上光会怎样,后次是想象在引力场中追上引力会怎样?因此,广义相对论本质上是引力理论(LIGO 2015年9月14日探测到首个引力波信号之后,2016年6月16日凌晨,LIGO合作组宣布:2015年12月26日03:38:53(UTC),位于美国汉福德区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利文斯顿的两台引力波探测器同时探测到了一个引力波信号;这是继人类探测到的第二个引力波信号。2017年10月16日,全球多国科学家同步宣布人类第一次直接探测到双中子星合并的引力波,并同时“看到”发出的电磁信号。)。
广义相对论的结论之一是:时空是物质或者能量分布的后果,引力并不是像前面说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引力同样不能超越光速,同样需要时间才能从一物到一物,把万事万物联系起来,或者说,物质与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需要宇宙铺满物质,也就是宇宙必须是连续的。如果没有物质,有引力波和光,不需要介质,世界也可以萬物互联。由此我们可以推测,爱因斯坦必然会这样写:“从事件存在的因果关系中消除了心理因素,这种心理因素从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构成因果关系中的一个独立环节。目前‘唯物主义’一词无疑正是指的这种观点,亦即认为完全用‘类空’要领来理解一切关系在原则上是可能的。(因为‘物质’已失去了作为基本概念的地位。)”([德]爱因斯坦:《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杨润殷译,第111页。)也就是说,事物的因果关系是真实的,而不是想象的。为此,海森堡总结道:“能量实际上是构成所有基本粒子、所有原子,从而也是万物的实体,而能量就是运动之物;能量可以称为世界上一切变化的基本原因……它可以称为一切变化的原始原因,并且能量能够转化为物质、热或光。”([德]W·海森堡:《物理学和哲学》,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8页、第34页。)
牛顿第一次集物理学之大成,开创了几百年来的一个小传统,作为这个小传统的结果,二战前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两大物理学革命,所描述的世界模式依然是关于时间对称的,而生命演化以及人类演化却不是时间对称的。二战期间及其随后产生的现代系统科学,特别是普里高津等创立的耗散结构论等自组织理论的出现,有了这些理论环节,天体物理界、系统科学界对引力作用的认识也大大加深了。霍金说:“现在我们知道,由于引力总是吸引的,不可能存在一个无限的静态的宇宙模型”([英]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许贤明、吴忠超译,第16页。),法国物理学家卢米涅说:“黑洞正是弯曲时空中很深的、或许是无底的引力阱”,“总之,在恒星演化的旅途上,黑洞的出现标志着引力在恒星一生中的控制作用取得了最后胜利”,“引力最终胜利了”([法]约翰-皮尔·卢米涅:《黑洞》,卢炬甫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1、104、106页。)。这也意味着对牛顿力学的认识也在变化。由于相对论加入了引力,把时空与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自然界联系起来,形成了宇宙演化的认识,而现代系统科学把宇宙演化与我们人类自身联系起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也就联合起来。普里高津认为:大约从人文科学的开创时起就呈现出来的几条思想线索汇合到牛顿的综合之中,相反,牛顿的综合是表达应用与理论认识之间的系统同盟的。在不断膨胀的宇宙中,地球引力场以及磁场等那样的外部场可能在自组织的选择机制上起着主要作用,形成了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并进而形成了有机体、形成了生命,进化出有自我意识、有精神世界的我们([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7页。)。
七、结语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牛顿物理学的时空观念改造成哲学范畴的感性直观形式,而黑格尔又把时空总结成“我”的“这一位”和对象的“这一个”,并进而对“力”做了哲学概括,近代物理学基因就此进入哲学,不论康德以后的哲学如何反复、如何否定、或否定之否定,关于事物的任何观念:神、大大小小的、各种孤立形式的“我”,如国家、民族、阶级、种族等等自我,都终究要被放“在”时空中,并引发“我”或“我们”与时空的关系思考,因此,康德以后的哲学都不可能再倒退回到神、倒退回不“在”时空中的“我”、倒退回极端的主观主义了。而是一方面沿奥斯特-麦克斯韦-亥姆霍兹-赫兹-爱因斯坦,即沿着物理学形成一条越来越坚实的进路,最终指向爱因斯坦的观点:在人之外即在“我”“我们”之外“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另一方面,沿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即沿着人文社会科学形成另一条进路: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条进路殊途同归,到唯物主义。因此,马克思与爱因斯坦会通的意义在于:在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思潮中,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意识形态中无论有多少神的或唯心主义的色彩或成份,甚至一段时间会有一定反复,但只会越来越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