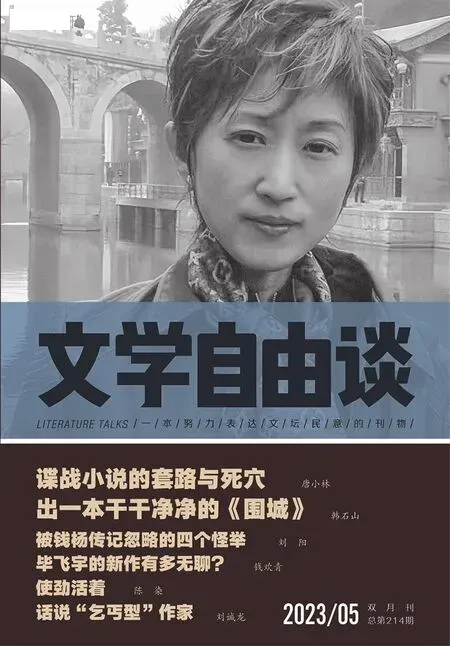被钱杨传记忽略的四个怪举
□刘阳
钱是钱锺书,杨是杨绛。“钱杨”已是当代文坛上一个醒目的符号,就像“苏张”除在极个别场合下指苏轼与张怀民,一般只专指苏秦和张仪那样。万人如海一身藏的钱杨伉俪,著作至今在印,传记至今在出。不过读遍这些存世材料,我仍然感到,他们的若干显得奇怪的举止,没有得到必要的留意,而成了身后之谜。出于对现有钱杨传记在观照这些谜、揭示传主立体面目方面的不满意,我将这些怪举中最令人感到困惑的四个,写出来向大家求教。也怀着抛砖引玉的心情,期待今后新出的钱杨传记能从正面来解这些谜。
本着对两位先生令名的钦敬,我仿照学术体例,在逐一提出四个怪举的同时,分别以注、鉴、评三层结构展开。这或许也能在目感上显得清楚明白些,更便于列位看官浏览和裁断。四个怪举里,钱杨各占两个。女性优先,先谈杨的两个,再说钱的两个。
怪举一:担心小说被后人随意续写,自己提前写出续书并出版。
【注】因为偶然听到一个读者令她“嫌恶”的故事走向猜测,杨绛先生便自行了断故事的结局,匆匆忙忙地出了薄薄一册《洗澡之后》。看前言:“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这样呢,非但保全了这份纯洁的友情,也给读者看到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我把故事结束了,谁也别想再写什么续集了。”书最后不忘再强调一句:“谁还想写什么续集,没门儿了!”可见戒备之深。小说问世后,反响平平,甚至颇多批评意见,和当初《洗澡》在读者中的深入人心不可同日而语也。
【鉴】在我有限的见闻中,一个健在的作家因怕自己的小说被后人“糟蹋”,而赶在生前亲自锁定续书结局者,只此一例。续写,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形:一、作家没把故事写完便去世了,比如《红楼梦》;二、作家已把故事写完并去世,但后人意犹未尽而对原故事续貂,且另有寄托,像陈忱的《水浒后传》、张恨水的《水浒新传》以及佚名的《后西游记》;三、作家已把故事写完并去世,后人借题发挥,以续书形式讲今天的新故事,有童恩正的《西游新记》等为证;四、夺胎点金,李清照的《如梦令》,便是对唐人韩偓《懒起》(“昨夜三更雨,临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的创造式续写,褚同庆的《水浒新传》也可视为此种类型。唯独闻所未闻,有作者活着时给自己作品写好续书的,难道不叫人奇怪?
【评】作家珍视声名,连带爱惜自己的作品,本无可厚非。但为防止后人续写不合己意的结局,急着自己封死情节,分明流露出“我的东西你碰不得”的心态,和杨先生激赏的兰波诗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自相矛盾——不仍在斤斤计较,和后人“争”吗?谈不上做人的大透彻。请原谅我拟于不伦,油然想到前尘梦影里那个拿《富春山居图》陪殉的故事。复再寻玩“我们仨”这个被人津津乐道的书名,觉得个中的独尊情绪和意味,也真蛮有意思的。
这是一层。另一层是,以为作者提前写毕续书,就保证了后人老老实实夹紧尾巴、不再打这部作品的主意,未免也让人哭笑不得:创作时间的终点不代表故事的终点,作者能一厢情愿地“把故事结束”?忘了接受美学的原理吗?古人云,“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别说续写是正常的文学史现象,就算流露出翻版必究的用意,大浪淘沙,作者自家的续作良可备一格,却不妨碍别人同样可从自己的角度继续平等往下写,焉能赋予自己垄断文本意义的特权?
至于杨绛本人仓促杀青的这个带有大团圆俗套色彩的续书结局,是否成功,倒在其次了。熟稔中西戏剧理论的她不会不知,中国戏剧对团圆的看重,归因于中国文化的“一分为三”特征,较之于西方文化重视“一分为二”、擅长形成矛盾与争论,我们一上来笃信人之初、性本善。固然不能由此简单判定两种戏剧观孰优孰劣,我感慨的只是,期颐之年的杨先生太心急了,观念上,艺术上,都未能将这件事处理得更漂亮——本来岂非可以更大气些不是?
怪举二:在预感远行前亲手毁去自己的日记。
【注】从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得知,杨绛在年事渐高之后,“亲手毁了写了多年的日记”。这倒给了好奇如我者一个意外的收获:原来杨先生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
【鉴】对照两年前问世的皇皇十二册《夏承焘日记全编》,真不知该对这类老来自毁日记之举作何评骘。一名有高地位的文化人,日记里会涉及有价值的人和事,客观上可以为后代留下信史,作为作者就真没隐隐考虑过这些文字将来的用途?带着这个疑问,与作家韩石山海侃,极力鼓动也坚持记了半个多世纪日记的老韩,择机出版自己的完整日记,至少可仿效今人对清代李慈铭日记的整理,从中清理出涉及读书的部分,先勒为一编《越缦堂读书记》。满以为这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盛业,是文人乐见其成的,不料此议被老韩断然拒绝。碰了一鼻子灰后犹自在想,到得杨绛的岁数,韩石山总不会也舍得一把火,将自己堆积成山的日记本烧个干净吧?那到时又会如何区处呢?
【评】如何处理私人日记,本无须外人置喙。此中透露出杨绛对隐私的维护,矜持和孤高仍旧一贯。然而,不是只有杨绛才在记日记,钱锺书不也在记日记吗?不错,杨绛说过“他开始把中文的读书笔记和日记混在一起。一九五二年知识分子第一次受‘思想改造’时,他风闻学生可检查‘老先生’的日记。日记属私人私事,不宜和学术性的笔记混在一起。他用小剪子把日记部分剪掉毁了”。但后来影印出版的《容安馆札记》里,不仅不乏记“苗介立”等生活内容的日记,而且有着多少口不择言、臧否时人的言论啊。不恤出版丈夫对人的私下评议,却不惜销毁自己的日记,是否让人感到有两套彼此打架的标准,在左右着杨绛的内心?
实际上,出版笔记手稿是钱先生生前不会认可的事情。硬着头皮公之于世,固然不失为一种保存方式,避免了让数量巨大的笔记从此湮没于天壤间,但潦草的字迹影印推出,可能带来误读误识和以讹传讹,这种毁不如存、存暗含毁的矛盾,是永远无法调和的。看透了这层后,用火攻之法对待自己的日记而片纸不留,委实就显得没太大必要了,反容易引发后人不尽的猜疑。倒莫若从容坦诚地留下它,庸何伤?
怪举三:对甲说“你正确”,转身对乙说“甲不正确”。
【注】先看钱先生当年的同事、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者追溯:
我一到那里,他就说,刚才××到这里,认真地说,《性格组合论》是符合辩证法的,肯定站得住脚。文学主体性也值得探索,他支持你的探索。钱先生显得很高兴。……那一天,他留我在他家吃了饭,然后就主体性的争论,他谈了两点至今我没有忘却的看法。……他说,“批评你的人,有的只是嫉妒,他们的‘主义’,不过是下边遮羞的树叶子。”……就以“方法论变革”一事而言,我被攻击非难得最多。但钱先生也支持,只是提醒我:“你那篇《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是好的,但不要让你的学生弄得走样了。”(《纪念钱锺书先生》)
如上表明,钱锺书对这位朋友甲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以这一理论为观念指导而写成的畅销书《性格组合论》、以及推动了全国“方法论热”的《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一文,都持肯定态度。再听钱氏在同一时间对当年同事乙所说的话:
先生说:我看到一些文章,错误太多,一知半解。我看你们研究室(我当时在文艺理论研究室)很活跃,就一篇关于主体性的文章说了不少意见,真是,文章经不起推敲,这可是不行的呢!(《“我们这些人实际上生活在两种现实里面”——忆锺书先生》)
此处“就一篇关于主体性的文章说了不少意见”云云,指刊于《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后收入《文学主体性论争集》的《自由地讨论深入地探索》等文章。被提“意见”的,就是上面甲的文章。鉴于批评意见占了很大比重,这又显示,钱锺书迅速收回了刚才对甲的肯定,转而埋怨其“文章经不起推敲”——你看得懂这种态度上的一百八十度转弯吗?
【鉴】前面的赞语是不是钱先生的客套?会不会后面的批评才体现了老人家的真实心声?比较一下类似的情形,会发现并非如此。钱氏之赞语,发生在书信往还中,尤其是对不熟的通信者。其身后大量披露的信札告诉我们,对这些人,钱锺书往往不吝溢美之辞,鼓励居多,确也给不少写信的崇拜者带去了受宠之乐。可在当面场合,钱氏褒贬起人来,不见得有那么多虚套。上面两个片段都涉及熟人,谈不上口是心非的虚与委蛇,其间的矛盾便令人由不解而骇怪了。
【评】就此抱以“阳奉阴违”之讥,是容易的却也是平庸的。我感兴趣的是这一怪举表现出来的钱锺书的深层性格:自己对自己的矛盾不甚敏感,自我反思不够。有时,我们觉得他对矛盾似乎很敏感,比如为钟叔河主编的丛书作序时说:“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但有时我们又觉得,他的说法颇有矛盾,比如口口声声“打通”——“通”的就不需要刻意去“打”,靠“打”出来的“通”,那还是真“通”吗?
或许也正因对矛盾不够敏感,钱著在整体上,便缺少一种以自我反思为核心的哲学深度,放眼望去尽以平行铺排为主,缺乏正反交错、展开辩证驳难的深入哲思。迄今哲学界罕有谈他的,没什么研究者将他的书作为学术研究的必需取径,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往深处窥探,其实也很少有某个专题的研究者,把钱著奉为绕不过的参考文献。他的书可看可不看,看了自可增添些知识的兴味,不看,对研究专业问题也没啥损失。随着时日的推移,我以为钱氏治学的某种局限恰恰就在这里。这和他重广度明显更甚于重深度,不能说没有联系罢。
怪举四:送客时忽然发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注】事见刘永翔怀想近四十年前拜谒钱府的文章。前面都正常,有点古怪的一幕发生在宾主告别之际:
最有趣的莫过于临别之时了。先生突然问我:“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我知道,这是钟会去见嵇康时嵇康问钟会的一句话。若照抄钟会原话“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来作答,岂但拾人牙慧,不是还自比陷害嵇康的钟会了吗?因此我笑而不答。(《受知记遇——回忆与钱锺书先生的缘分》)
这里钱氏驱遣的典故并不陌生。三国时钟会不认识“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邀人同去寻访。正巧碰上嵇康在大树下打铁,并不停下,旁若无人。待钟会起身要走,嵇康才问他:“听到了什么才来?看到了什么才走?”钟会只能回答:“听到了所听到的才来,看到了所看到的才走。”各种钱锺书访问记中,记叙钱家大门难进的很多,鲜见描写辞别之际细节的。这段文字难得地为之留下了风采。只是这样一种辞别语,怕够客人猜详一辈子而不得其解了。
【鉴】在这个场景用这个典故,要表达什么意思?用钟会欲害嵇康,比拟于刘对钱的“拜之倒”?把远道而来的后学说成加害自己的钟会?但自己热情相待的行为迥异于嵇康,又无修辞上的对应性,缺乏相似点,比喻不当,好像也不能说是想反讽什么。这算钱氏幽默?
溯自十余年前,我曾研究过钱氏幽默的几种类型,发现多数幽默效果是运用比喻实现的,如形容汉赋的“板重”为“以发酵面粉作实心馒首”,嫌唐朝和尚拾得论禅啰嗦有如“老婆舌”,称韩愈老是话刚出口便反悔,“匹似转磨之驴”,梅尧臣的以文为诗“尚不足方米煮成粥,只是汤泡干饭”,清人钱载的诗则像“肥老妪慢肤多褶”,如是等等。少数幽默效果则来自反讽,像抗议医院里吵闹的小护士:“你把我的病都吓跑了!”唯独吃不准,这从原文里掐头去尾截割出来的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唱的是哪出幽默?思来想去,也只能叫它“断章”了。淡化上下文语境而“断章”为我所用,事实上正是钱锺书特有的说话和为文方式。
【评】“断章”本身不是没有可取点。《左传》就总结了春秋时“赋诗断章”的文学传统。再联想到漫漫科举制长河中那一道道试题,譬如“维民所止”,每每也在断章中截搭,对钱锺书这份癖好,自可见怪不怪。卞之琳还有名诗《断章》呢。将之用于日常生活,开开玩笑则可,可是钱锺书把它大剌剌地用到学术研究上去,窃以为却是问题很大,甚至充满了危险的。
举个例子。对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名文《艺术作品的本源》,钱锺书“断章”截取出一句“真理即非真理”,然后用“亦见亦隐”四个字,联想式地迅速打发了它。这不但没有诠释清楚海氏原文之意,只同义反复了一下,而且在“断章”的拼接中造成了三个不良后果:其一,把哲学本体论问题偷换成“见/隐”的日常生活经验问题,简化了思想语境;其二,海氏原文讲的是“有”和“无”这对范畴在本体论上的关系,“无”在此是绝对的,钱锺书却用“见”和“隐”置换两者,没有考虑到,“隐”只是相对于“见”的暂时遮蔽状态,把一样东西藏起来让人看不见,这样东西仍在,并没有趋于哲学上的“无”,以此类比,便从根本上导致了对这句哲学表述的义理曲解;其三,“亦见亦隐”在切换频率上的稳定性,又逐渐凝固成不变的同一性实体,那种形而上学嫌疑,恰是海德格尔此文试图避免的,他要还原的“无”乃是一种非同一的差异——大道从中涌出的事件性发生源。你看,仅仅基于这三点,靠“断章”搞研究的短板不是已历历可辨吗?
因为“断章”毕竟是前现代的文化现象,若据此信心满满地把治学当作聪明有余、实绩有限的跳跃式变奏和诗性活动,是容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难以长久的。乍一看五湖四海、满目琳琅,一旦穷形极相,却到底说出了什么呢?它不能和现代学术精神对话。从现代学术精神看,符号需要置身于符号关系中,在和所有其他符号的区分中才有意义。一句话的意义,因而无法脱离它所处的整部作品,孤立地把这句话拎出来去和别的话拼接,便失去了对这句话刨根问底的专业化深研姿态,成为漂浮于话语效果水面上的自指游戏,真理便要打个折扣了。
于是可以理解,同样是对疑难字词作解释,虽然钱锺书的《管锥编》知名度大于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今天的人们却似乎相对淡化了对于前者的热情,而正在给予后者越来越高的评价——“永垂不朽,堪称万世楷模”(鲁国尧语)。个中奥妙,我想在于钱氏在“断章”中连类比附,思维上是横向辐射的,百科全书式面面俱到,却难免东点一下、西点一下;蒋氏则咬住每个对象本身深钻细锥,思维上是纵向一竿子通到底,更趋专精的,其书终成敦煌学领域人人案头必备之书。时过境迁来衡量,更为彻底、对学界更有助益的是蒋著而非钱著。据蒋夫人回忆:“我和云从(按:即蒋礼鸿)对钱锺书先生有些‘微词’,……如果他确是中文系的,那就确是有点‘杂’了!……他的博是惊人的,我老伴对他有些‘微词’。”(《蒋礼鸿与钱锺书鲜为人知的交往》)具体有何“微词”,后人已不得而知,但估计和蒋对钱“断章”的、东鳞西爪的治学方式的看法,多少有关系吧。热衷于学界佚闻的有心人,何妨沿此来做做钩沉的妙文?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