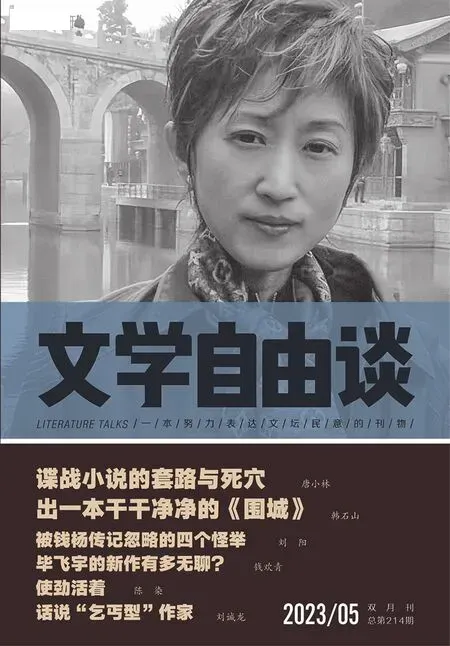谍战小说的套路与死穴
□唐小林
前些年,凭借影视的助推和众多大牌明星的加持,一些谍战小说暴得大名,竟堂而皇之地走进纯文学殿堂,甚至受到某些文学大奖的青睐。但事实上,许多谍战小说并没有谍战本应有的严谨而复杂的故事逻辑,以至于会让读者产生智商被侮辱的感觉。
我们知道,许多读者在阅读这类小说、观看这类影视时,都是为了消遣,没谁会把它当成真事。但被誉为“谍战之父”的麦家,却坚信他小说中的故事是真实发生的。他说:“小说中任何一个失真的物件、反常的细节都可能是致命的,因为赋予它虚构的特权就是要高保真,杜绝虚假。”道理讲得很对,但他的不少作品还是出现了各种虚假。比如《暗算》,从故事到人物,都是不可思议、极不真实的,读起来就像是一部神魔小说——
三岁还不会走路、五岁还不会喊妈的阿炳,高烧昏迷了三天三夜,眼睛烧坏了,但能张口说话了,还拥有了惊人的记忆力和异常灵敏的听力。由于身怀绝技,他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也被特招到701这个从事窃听和破译工作的保密单位。701里有很多他这样的“怪人”“高人”,他们虽然有生理缺陷,却在听觉方面有异能,有点《庄子·德充符》中人物的意思。阿炳是其中的佼佼者,本领更强,工作更出色,也因此,组织上为他“安排”了乡下女人林小芳做老婆。他们不久就有了儿子。但在短暂的幸福之后,阿炳凭借自己的“神功”,从婴儿的哭声中发现了问题——他断定这孩子不是他的,而是医院药房那个山东人的!阿炳不愿被别人戴“绿帽子”,要和这个无法理解的世界和丑恶的人间告别。他录了一段音,告诉世人,他的老婆是坏人、儿子是野种。然后,趁人不备,伸手去捏电源插头……
一部谍战小说,竟被麦家写成了“西游记2.0”!连神通广大的孙悟空都没有的特异功能,却在阿炳身上出现了:现代科技都必须通过基因检测才能判定血缘关系,他仅仅通过婴儿哭声就给解决了。
麦家一面强调小说的真实,一面又在违背生活和艺术的真实。《暗算》最大的“梗”,就是701这个神秘机构,是由一帮“怪人”组成的。有才的怪人在这里可以不受约束,只要能破译出敌方的密码就行。小说中的另一位“高人”“怪人”,是被称为“有问题的天使”的黄依依;她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理学博士,学成回国。而“我”名义上是远赴苏联的留学生,实际上却是有着秘密身份、收集当时苏联破译的美国军事情报的间谍。在回国的前一天,“我”突然接到妻子遭遇车祸的噩耗,但因为工作需要,“我”没有去看望妻子的遗体。回国后,“我”在701受到重视,并很快被擢升为副院长。在一次招聘中,“我”破格录用了结过两次婚、与多个男人有过云雨情的黄依依。而黄依依进入701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崇高的理想、破译敌人的密码,而是一厢情愿地爱上了“我”这个留学归来、成为副院长的“钻石王老五”。但无论丰满貌美的黄依依怎样不管不顾、死心塌地,甚至有失尊严地死缠烂打……
黄依依是个罕见的数学天才,但除了在破译密码方面能力超群,其他方面的每一根神经似乎都不正常,以致被认为是“神经病!十三点!疯子!”她对“我”发起一次又一次火辣辣的撩拨和“强攻”,简直到了丧心病狂、寡廉鲜耻的地步,但“我”绝不动摇,始终不答应她。追求无果,黄依依居然与701另一位有妇之夫、机要员张国庆滚起了床单,并且意外怀孕。不幸的是,她最终在生产之后意外死亡……
我搞不懂的是,麦家在塑造黄依依这个性欲超级亢奋的女人时,思路究竟依循着怎样的逻辑链条?他是不是在故意夸大女人的性欲,以此作为小说的“新突破”和“新看点”?越是有生理缺陷和心理缺陷的人,越是具有特殊的才能?难道谍战小说是专门写给那些有着奇葩脑回路的读者看的,故而不需要正常的逻辑?
固定的套路,雷同的题材,让谍战小说走进一条死胡同。许多情节和桥段,读者几乎都能猜得到——出于斗争需要,为了麻痹敌人,总是有一对假夫妻;必定会有叛徒出卖同志,组织必会紧急应变、设法锄奸;遭遇出卖或情况危急时,首先想到的是把消息送出去;外出参加会议或联络接头,必定有人盯梢,让会开不成,让接头泡汤;遇到突然检查,必定能化险为夷;遇到特务合围,必定能神奇脱身;敌人抓捕开枪,总是打不准,地下党总能逃过一劫;总是有一个秘密联络点,以老字号的药铺、饭馆、书店做掩护;走上革命道路的漂亮女性和大学生,往往都是大户人家出身,甚至干脆是敌方核心人物的子女;组织上给予或大家筹集的经费,通常都不是钞票,而是金条;越是得到敌人信任的人物,往往越是潜伏最深的革命者;故事通常都发生在上海、南京或重庆……
我们再看看另一部谍战新作——《千里江山图》。这是一部被誉为“现象级的文学事件”,实际上却又是非常平庸的谍战小说。尽管各种大奖拿到手软,形形色色的赞扬无以复加,但丝毫不能掩盖作者的写作短板。或许是因为在蓄意摒弃故事的“先锋小说”里浸淫太久,孙甘露已经不会讲述故事、刻画人物了。《千里江山图》的人物个个无血无肉,让读者搞不清谁是张三、谁是李四。它没有塑造出有鲜明个性的典型人物形象,更没有必要的心理描写,和对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的展现。
《千里江山图》处处流露出对“红色经典”,尤其是《红岩》的模仿——《红岩》里,地下组织的联络点是沙坪书店,在《千里江山图》中,则变成了兴昌药号;《红岩》里的江姐和华蓥山纵队政委彭松涛曾经是一对假夫妻,而《千里江山图》居然再一次玩起了假夫妻这个“梗”……可以说,《千里江山图》中几乎所有的“谍战元素”,都可以从《红岩》等小说中找到出处。《千里江山图》中的人物,个个都像作者的提线木偶,而《红岩》中的每一个人物,却都是个性鲜明的文学形象:自私固执、心高气傲的银行职员甫志高,卓越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许云峰,在酷刑面前坚贞不屈的江姐,名震一方的双枪老太婆,“疯疯癫癫”的情报传递者华子良,在狱中出生而从小就失去自由、从未看见过外面世界的小萝卜头……
笔者几十年前上中学时读过的《红岩》,其人物形象早已经牢牢镌刻在了大脑中,再也不会忘记。仅以叛徒甫志高为例,他叛变这一情节构思,是通过令人信服的心理描写和行动描写来支撑的,其逻辑链条非常清晰——为了显示自己的工作水平和组织才能,他未经组织许可,擅自发展成员;在受到许云峰批评之后,又非常委屈,连连抱怨;当他发展的成员中出现了探子,使党的组织遭到破坏,许云峰命令他和其他同志迅速转移的时候,他又在心里抱怨许云峰疑神疑鬼……
《红岩》对甫志高的描写,并没有脸谱化、妖魔化,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细节,使其在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永久地立了起来。甫志高并非天生就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坏人,而是一个拥有理想、怀着私心投身到革命队伍中的试水者和投机者。他也曾想在革命队伍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展示自己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并且非常满意党组织为他安排的银行会计主任兼沙坪书店经理这样一份既体面又收入颇丰的工作。他好不容易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所以,当许云峰要求他迅速转移时,就意味着他将从此失去这来之不易的一切。这为他接下来的叛变,做了天衣无缝的铺垫。甫志高对上级的指示和命令,虽然不愿服从,却又不得不服从。在转移之前,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妻子,知道这悄然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于是,他违反了组织规定,把许云峰叮嘱他的话抛在了脑后,并且决定在第二天向老许汇报时,谎称自己没有回过家。小说写道:
出了咖啡店,夜风一吹,甫志高的头脑清晰了些。不远处亮着一盏红纸小灯笼,那是有名的地方风味“老四川”牛肉摊。那种麻辣牛肉,妻子最爱吃。在这临别的晚上,应该给她带点回去。甫志高买了一大包牛肉,转身向回家的方向走去。
就在这个时候,自以为不会出事的甫志高偏偏出了事,一支冰冷的枪管,抵住了他的背脊。
翻开《千里江山图》,我们实在找不出一个稍微像样的细节描写,看不到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反而遭遇了许多古怪,比如,接头暗号本应越简单、越容易记忆越好,但在《千里江山图》中,地下组织的接头暗号却是:“涅克拉索夫,这些年你读了吗?”对方必须回答:“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更为可笑的是,上级派来的人,在与当地人员联络时,必须拿出一对特别的骰子,以验明真伪。地下工作本身就够紧张、繁忙了,却还要他们在深夜敲门时,隔着门缝互对这种“准文学青年”风格的接头暗号,万一记不住、说不全怎么办?岂不是有可能将对方当成敌人?惊心动魄、危在旦夕的地下工作,怎么会被写成如此搞笑的“行为艺术”?
作为一种类型写作,谍战小说之所以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恰恰在于其惊险刺激、出乎意外、悬念不断、精彩迭出。但我读《千里江山图》,翻不了几页就想打瞌睡——难道作者给它添加了安眠药?
早些时候,一位著名的谍战小说家说,由于题材的固定化和写作的模式化,谍战小说已越来越难写,他也正在寻求新的突破。孙甘露另有“突破之道”,他从别人的作品中寻找到“灵感”,以大量植入谍战小说元素却又未经消化的写作,使《千里江山图》呈现出大量幼稚可笑、似曾相识的情节,甚至出现一望便知的硬伤。这种全靠输血、缺乏造血的写作,恰恰是这种谍战小说致命的死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