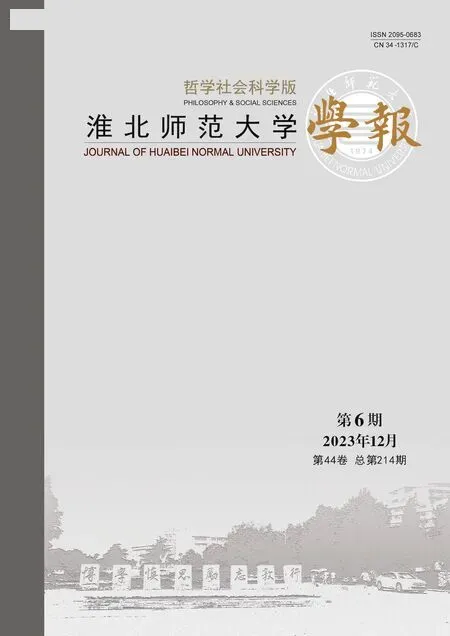《龙眠风雅》的编撰及其地方文化权威的建立
张会会,查思扬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潘江(1619—1702),字蜀藻,号木厓,桐城文坛盟主,极善诗文,性淡泊好交友。马其昶称其为:“生而天才隽妙,十岁试文郡邑,群士推为圣童。后益博极群书,历游齐、岱、京、楚,与海内名流相结,主盟坛席者三十余年。”[1]219潘江作为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在古文和诗词上均有建树,且热衷于乡邑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他于顺治五年(1648)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编撰的《龙眠风雅》分为正、续两编,合计92 卷,共收录桐城乡贤553 人及其诗作,共14874 首。目前,对于《龙眠风雅》的研究,主要针对其诗歌选本主张、文学特色,或是在潘江的藏书著述等人物研究中略有涉及。《龙眠风雅》一面世,便受到同乡张英、戴名世、方孝标、方东树等一众文人的推重,这固然有潘江与桐城诸文人交流广泛、兴趣相投的原因。但是,《龙眠风雅》能在桐城户习家传,奠定了经久不衰的文化权威,它非因人而显,当有其特殊的文化意义。且桐城一地的乡贤文献是一个连续性的编撰过程,从万历年间(1573—1620)方学渐编撰《桐彝》《迩训》开始,终于光绪年间(1875—1908)马其昶所编的《桐城耆旧传》。《龙眠风雅》的编撰正处于明清交替之际,在体裁、收录与内容上,不仅与地方家族的权力变动相结合,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后世乡贤文献的编撰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此书理应放在桐城乡贤文献编撰的整体脉络中,并结合当时的地方权力变动以及桐城学术变迁的背景作立体考察,见微知著,才能明确桐城士人对《龙眠风雅》推崇的真实含义。
一、明末清初桐城的文化氛围与乡贤文献的编撰
桐城在明代以前,声名不显,其文化一直处于比较落寞的状态。明清以降,桐城异军突起,据《桐城县志》记载:“桐,仕国也。人文秀出,炳炳麟麟。或列名容台,或观光上国,以至韬略素娴、奋迹鹰扬者,代不乏人。”[2]其地人文之盛让人叹服。然而,桐城一地自明以来屡遭兵燹,史籍载之不详,文献缺失,让一地之风俗盛美、文人义士,湮灭沉沦。因此,为了发扬桐城一地优良的人文传统,书写乡贤,成为地方士人自发的责任意识。明万历年间(1573—1620),桐城人方学渐“自郡邑志以及父老之口,征所见、征所闻、征所传,闻有一言可采、一事可表者,悉笔而藏之,久乃成帙。”[3]编为《桐彝》《迩训》二乡贤传。作为桐城最初的乡贤文献,此两部乡贤传记的编撰在桐城一地有开拓之功。入清以后,以桐城诗学和古文创作为中心的地域文化发展日渐繁盛。戴名世称“江淮之间,士之好为诗者,莫多于桐。”[4]方孝标言:“吾乡重名教,耻轻肥。父兄之教子弟,不仅制艺,自其初学,即训以音切对偶,为诗赋古文之学。故自城邑以达,乡里虽妇人童子,多能操觚吟咏。”[5]13可知,桐城上自朝廷大员,下至普通文士,乃至闺阁女子,无不追慕风雅、不废吟咏。可谓“其以诗古文词,闻于艺苑者尤多。”[6]而《桐彝》《迩训》仅为单独的人物传记,姚永朴称:“虽收录甚简,然吾乡正嘉以前之文献,实赖是而仅存。”[7]可见,此二书虽有保存人物之功,然而对于文化昌盛的明末清初时期的桐城来说,收录甚简,体例不详,并不符合入清以后的桐城士人希望表彰地域乡贤的初衷。钱谦益曾编选反映明代文学与历史的《列朝诗选》,影响广泛。然而,该书在桐城士人眼里“龙眠诗登载寥寥。”[8]5桐城钱澄之曾与钱谦益论及《列朝诗选》对龙眠诗作收少且不精:“选之不足以尽诗明矣。”[9]299钱谦益认为“子乡有佳诗,而无传本,吾乌乎得而选之?”[9]299在此提到了桐城一地仅有人物传记,却没有地域性的诗集传本,才是流传受阻、文化不显的原因所在。
清朝顺治五年(1648),方授曾和潘江一起编选《龙眠明诗选》一书,未及完成,方授便撒手人寰。于是,钱澄之毅然和姚文燮合作续编《龙眠诗选》《龙眠诗传》二书,此二书也是将人物与其著作合编的大型地域乡贤文献。然而,未能付梓,原因便是其编撰者钱澄之和姚文燮对于诗编命名取义的分歧:“姚曰《诗传》,盛推昔人著作;钱曰《诗存》,严持一己权衡。”[8]16两人对于“宽选”和“严选”的分歧其实有迹可循,钱澄之与姚文燮曾共同在建宁县任职,主修建宁县志。钱澄之寄长文与姚文燮详谈修史事宜:“今天下修郡邑志者,类取于学宫之诸生领其事,往往一二无籍者禄窜入其中,惟上是奉,惟势是趋,惟贿是求,黑白倒置,致令真正节妇、义士皆以与民其书为耻。”[9]77因此,钱澄之编史志首要原则便是“据之以纪实。”[9]74而姚文燮却希望其“委曲以从当事之意指。”[9]74认为对于人物收录,理应尽收以示表彰之意。因此,在《龙眠选传》的编撰中“姚子主宽,欲更加广焉。”[9]299事情因而搁置,合作未成。不仅如此,康熙十二年(1673),桐城县令胡必选主修《桐城县志》,潘江曾参与编修《桐城县志》,并将钱澄之的亡妻编入了邑乘,钱澄之因此称:“故虽纪有未详,诚以足下乡邦名宿,得一字褒称,足以不朽。”[9]82而潘江晚年自述:“常怊怅于邑志之役,以牵于共事,不得行其志。”[8]10钱澄之的亡妻方氏最终被从方志《节烈传》中削去,合邑多为不平。这便显现出潘江无法左右县志人物的去留,以至于被胥吏操控舞弊。钱澄之因此称:“吾邑志书不数年一修,无关重轻。独怪乡称节义,邑有缙绅,而以宗族乡党素所不齿、至俗无文之人,居然司笔削之任,岂不羞龙眠而贻四方之笑乎?”[9]83充分体现了清初方志的编撰遵循国家统一的编撰原则,内容施教化而失史实,编选时又受制于庸吏,桐城士人几乎无法左右地方史的书写,完全处于一种“地方失语”的状态。
《龙眠诗选》与《龙眠诗传》均未付梓成功,可以说钱澄之和姚文燮的主观立场,都是要为桐城乡贤前辈保留文献,而钱澄之所谓的“严选”之论,受到其家族在地方失语的不公正对待和其自身修史观的影响。然而方孝标谓:“吾乡自有明三百余年来,诗人林立,其专稿、选稿行世者多,而汇而集之,则自《龙眠诗传》始。”[5]13其合集文献的编撰行为确实代表了清初桐城士人保存地域文化的初衷。因此,潘江接续地域乡贤文献的编撰活动,筹措编撰了《龙眠风雅》一书。潘江云:“昔邑治迁徙靡常,宋元以前,湮没莫考,断自洪永,渐有闻人……而先正鸿儒,著书满家,又皆耻钓浮名,只用自悦,坐是流传益尠,全集罕闻。”[8]1表明了为已故乡贤搜罗遗文,保存文献的初心。《龙眠风雅》以人物传附诗歌作品的方式,共收录桐城诗家553 人,作品14847首,是一部真正将人物与作品合二为一的大型乡贤文献总集。因此,吴道新、汤日父在为《龙眠风雅》作序中提到:“吾乡方明善先生师此意,撰《迩训》诸书,桐先哲之芳规懿绩,粲然彪炳。予惜其未附以诗文……诗文之遴梓,可以萃众甫而播之广远也。”[8]3而后,潘江又编撰了《桐城乡贤实录》,并协助李雅、何永绍编撰了《龙眠古文》,也对应着桐城古文创作的传统。马其昶因此称:“乡先辈诗文不得泯者,潘、李、何三先生力也。”[1]220可以说,清朝初期潘江乡贤文献的编撰,实是为了应对明末清初桐城文化急速发展而文献缺失、地方失语的尴尬处境。
二、承宗祧、继嗣续:《龙眠风雅》的编撰与乡族参与
如前文所述,钱澄之与姚文燮的争论之处,便是“严选”和“宽选”。其实就是乡贤文献中人物收录的问题。桐城一地家族众多,乡贤传记作为一乡的地方文献,人物入传可以说是莫大的荣誉,因此收录往往是一大难题。早在明末,方学渐《桐彝》一书就招来读者“滥收与不尽收”[10]之疑。方氏后裔在《桐彝续》中有如此辩解:“春秋之作笔甚严,故能为衮斧于邦家。”[10]《桐彝》作为桐城第一部地方人物传记,其采用“严选”的收录方式,虽然其人物传记的书写做到了详实有序,但正、续二编仅收录桐城54 人。而后,《迩训》一书虽然收集600 余人次,但却涵盖安庆一府六县,未能将重点关注在桐城一地,且“取节执中,简汰华实”[3]的书写排列和以“训吾儿曹耳”[3]的家训性质,决定了其内容导向带有方学渐明显的家学传承,更似是一种理学通俗读物。并且这两编书均只收录到明正嘉年间(1506—1566)以前的桐城人物。但明中叶以后,桐城地方家族的权力结构逐渐发生变化,方东树称:“中叶以后,乃遂有吴氏、张氏、马氏、左氏数十族,同盛递兴,勃焉濬发。”[11]304据徐雁平统计,“清代桐城21 个家族643 次联姻中,有526 次皆为桐城家族内部联姻。”[12]桐城地方社会已不再是方氏一家独大,诸多家族通过联姻、交友、师生等关系,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交流网。
因此,潘江《龙眠风雅》的编撰,除了基于人文昌盛的地域文化氛围的考量外,还必须兼顾桐城一地家族众多,联姻密切的现实基础。他毅然采取“宽以收之,严以选之”[8]10的采择方式。正如前所述,《桐城县志》对于前贤事迹多有遗漏,为桐城士人所诟病,私修人物传往往以补邑志收录人物之缺为主要目的。因此,《龙眠风雅》人物后列小传:“于各姓名下叙其爵里,檃其事实,凡以阐扬当代,近而易稽;美行嘉言,均无攸伏。”[8]16小传对于乡贤传记的史料来源,通常遍采史传、志乘、诸家文集、笔记和口耳相传的乡评舆论,具有“考据典核,予以补邑志之阙”[8]10的明显目的。潘江选人、选诗秉持“姚子所欲传者俱传,钱子所欲存者俱存。”[8]5此编选方式,不仅满足了姚文燮“主表彰”的理想,也追承了钱澄之“据之以纪实”的修史原则,并且潘江采用了“选本以著合集”的方式,施润章说:“盖全集繁而易失,选本合而易行也。”[13]58潘江此举不仅是为了方便流通,更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在人物上广泛收录,以求尽显乡族,所以《龙眠风雅》呈现出明显的以家族为中心的收录特点。现以桐城的主要家族为对象,考察他们在《龙眠风雅》中被收录的具体情况,详见表1。

表1 《龙眠风雅》收录桐城家族人物与诗作的统计
由表1 可知,桐城诸多家族在《龙眠风雅》中,不论是人物还是诗作收录,均累计占据了超过半数的篇幅。例如,《龙眠风雅》全编以桐城方氏的五世祖方法开篇,共收录方氏人物96 人,诗作共3143 首,居全书之最。陈正璆在阅读《龙眠风雅》时,便提到:“潘木崖先生手订诗也,前编以断事公始,太史公终,其论定方氏不綦重哉。”[14]方孝标也对潘江将其族人放置于卷首、收录甚多,表示了肯定:“首以先断事之忠贞,终以家密之苦节,于衰宗先后能诗者网络略尽,而以先君子与先兄环青、亡弟子留各为一全卷,且云此家国之光,不徒桂林之盛。”[5]14可知,方孝标认为,方氏以忠孝节义传家的家族文化通过《龙眠风雅》的传承早已上升为一种足以标榜地域的“家国之光”。除此以外,像桐城望族诸如姚氏、张氏、吴氏家族,都在《龙眠风雅》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如姚氏家族,自姚希濂子侄辈开始,由其子姚自虞至姚之騏、姚之蘭兄弟,再至姚文然、姚文燮兄弟辈等,共收录诗作1000余首,一门人才之盛,彰显备至。马氏家族在明代声名不显,然而,九世祖马之瑛与其叔伯、兄弟六人,在其祖父的别业“怡园”互相唱和,诗酒风流,称“怡园六子”,盛极一时。所以,马氏家族虽只收录重点人物8人,却总收录诗作471首。齐氏家族的齐之鸾善作诗,钱澄之认为,他遂“开吾乡风气之始。”[9]218潘江也誉其为桐城诗学的开创性人物,其家族也被冠以重要地位,共收录诗作555首。左氏家族的左光斗为明天启年间(1621—1627)反阉党的忠臣,《龙眠风雅》录其诗106首,其曾筑别墅于龙眠山口,其子国柱、国棅、国林、国材也先后居此吟诗作赋,称“龙眠四杰”。此四人诗集均已没有流传,所存诗歌也仅见于《龙眠风雅》。为了表彰乡族人物,《龙眠风雅》中还有很多家族之人只收录诗作一篇,对于一些小姓,或数姓一卷,或一姓一人一诗。据统计,《龙眠风雅》中仅存诗一首者,共达78 人。人物小传中除对乡贤本人列传外,兼附其兄弟、子孙,家族世系亦清晰明了,源流自具。
桐城宗族发达,地方士人的宗族意识极强。他们认为,“凡拾人遗编断句,而代为存之者。比葬暴露之白骨、哺路弃之婴儿,功德更大噫。”[15]77且《龙眠风雅》又可比肩地方志,是构建地方历史的重要文献并具备广泛的流通性。张会会指出,“乡贤传与地方志虽然立意相同、内容相近,但因为地方志所具有的官修性质,只是作为存史及为政参考,而被束之高阁。乡贤传作为私家撰述,作传除有补充地方志人物之缺失,防贤者久而湮灭的意义外,更加强调为乡贤著书立传以此兴起后学的功用,因此具有广泛的流通性”[16]。所以,能在《龙眠风雅》这部地域文献中被广泛收录,弥补了桐城家族在方志中收录不足的遗憾,他们均希望能在流传性广泛的乡贤传记中公开记录自己亲属的美德学行,以为他们今后获得官方认同奠定基础。这种为先祖保存文献,以备流传的责任感与孝亲感便连为一体。因此,《龙眠风雅》便具有“贤裔扬扢前人,义旧表襮亡友”[8]17的现实意义和广泛流传,以备史志采择的文化价值。作为桐城一地最大的乡贤文献,其“承宗祧、继嗣续”的编撰目的,配合“宽选”的收录原则,满足了桐城士人“子孙表章父祖”的现实需求。也正因为如此,《龙眠风雅》的编撰与《桐彝》《迩训》等乡贤传记编撰的独立操持不同,其受到桐城乡族的广泛支持。关于初编的编纂过程,在资金筹措方面,潘江自述:“前集之刻,实赖姚端恪公龙怀、程太常公立庵,轸念桑梓文献散佚多年,慨然捐资首倡,共节俸入襄梓,仆始敢任事开局。”[17]6而在后期的史料搜集和校对中,“至友人方子尔止、杨子古度、方子还青、邓子颠厓、陈子子垣……皆曾目击收缉,各出家笥,广为搜罗,相与昕夕扬搉者也”[8]19。姚氏家族的姚士塖也数次“邮其诗稿,贻书諈诿”[17]5,促成了潘江“遍征戊午后新逝诸公雅什,汇成巨观”[17]5,维系了表彰乡族的功能。可知,桐城乡族通过“尽发夙藏”“广为搜罗”和“捐资开局”的方式,广泛参与到《龙眠风雅》的史料搜集与刊刻过程中,表现出对于《龙眠风雅》成书的绝对支持。
在多方努力之下,经过从顺治五年(1648)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长达四十多年的搜集整理,《龙眠风雅》正、续两编终于完成,并刊刻92卷,共收录桐邑553 人的诗作。书成后,其书、其人受到同邑文人的广泛推戴。方孝标首先将钱谦益《列朝诗选》与《龙眠风雅》相比,认为《列朝诗选》“体裁颇与足下此书合,但其客气未除,宅心未厚,于索般隐刺之言则详,敷扬盛美则略。”[8]13而《龙眠风雅》则“传贤贵者既详悉有度,而于隐逸之老、穷约之儒尤加扬诩,访咨遗迹极备,而又皆芟繁辨伪,扢善阐幽。”[5]13充分体现了桐城一地文人墨客的风采,阐幽发微,表彰了桐城的诗学成就。吴道新也称:“潘子阐扬乡先哲之功,不既大矣哉。”[8]5许来惠为了表达潘江在《龙眠风雅》编撰过程中搜罗甚广、成人之美的成书之功,称“潘子之功于维桑梓者大也。”[8]9顾有孝、钱澄之、戴名世、张英等人皆与潘江交往密切,且多次给他的诗文作过序,均将《龙眠风雅》的编撰作为其才学品行的一大标杆。大学士张英甚至称:“吾友潘子蜀藻,海内所称!”[18]这类文字的表达倾向,虽然有某种文学写作套式的推促,但是也不乏士人借编撰文献之际自我标榜的意图。乡贤传记由乡邦士人撰写,总序作为一种副文本,也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同乡之手。他们悉数桐城人文兴盛,如数家珍式地陈列地方著姓望族、忠臣孝子、文学传承,以显示桐城一地人文荟萃、同盛递兴。因为这种叙述策略,序文中所关联的桐城家族及士人典范,便被置于地域范围内。看似主次之分,实则在彼此映照。一些桐城士人或小族就算隐晦未彰,经此推扬,也能融入桐城“文化节义之邦”这一固定的历史记忆中。由此可知,康熙年间(1662—1722),《龙眠风雅》的地方文化权威是在桐城众多家族的内部支持与外部宣扬中被初步建立起来的。
三、追溯风雅:《龙眠风雅》与清中期桐城地域认同的建立
《龙眠风雅》在清中期时流传受到一定限制,主要源于康熙五十年(1711)的《南山集》案。主犯戴名世,安庆府桐城人。因其文集《南山集》中,多有引用同乡方孝标《滇黔纪闻》中载南明桂王史事的永历年号,且多忌讳之语。案发后,其文集遭禁毁,牵连桐城士人甚多。而潘江为戴名世师,对其多有教导,马其昶称:“戴编修名世,初未知名,先生奇其才,悉发藏书资之,卒传其学。”[1]219由于这层特殊的师承关系,再加上南山集案中主犯之一的方孝标曾为《龙眠风雅》作过序。因此,在乾隆朝(1736—1796)焚书期间,《龙眠风雅》被列入禁毁书籍,此书被禁毁,流传也十分困难。许结先生因此认为,“《龙眠风雅》在桐城诗学中的地位远不及《桐旧集》影响之大。”[19]可是,嘉道时期(1796—1851),桐城兴起了第二轮乡贤文献编撰的高潮,在士人的议论和文献的编撰中,能显而易见地发现桐城士人对于《龙眠风雅》一书的推崇和体例的借鉴延续。如周成强曾考察清中后期桐城乡贤文献对于《龙眠风雅》的采择,认为“《龙眠风雅》依旧以残本的形态在桐城地区流传,凡是辑录桐城诗之选家,都对其非常重视,并多所引用”[20]。而《龙眠风雅》之所以能在文字狱后的桐城,依然起到极广泛的影响力,就不得不考察当时的社会与学术背景。
在清前中期,“汉学”不断发展,“宋学”呈衰退之势,而桐城家学以崇尚“宋学”为主,姚永概在《童氏宗谱五修序》中说:“盖吾邑盛自前明,仕于朝者立气节,官于外则多循吏,居家则重理学,一时风气尚然也。”[21]因此,桐城学者大都笃守宋儒遗说,主张“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22]906-907。与此同时,以古文为主场的桐城派开始大显于世。桐城古文大家姚鼐在《古文辞类篆》的选本中,就有意构建“桐城文派”,姚鼐将桐城人方苞、刘大櫆置于唐宋文学传承的继承人之列,向天下表明桐城文士为古文正统之传人。清代文人李慈铭便指出,“《古文辞类篆》……自唐宋八大家外,唯有《国策》《史》《汉》、骚赋,后及明之归有光、国朝之方苞、刘大櫆,余不入一字,盖一家学也。”[23]桐城学者所编选本如《国朝古文所见集》《国朝文录》《国朝古文正》,均竭力铺陈桐城士人与桐城三祖之间的师承关系,推尊其为学术正宗,均是为之进入桐城文统的张目。像这些涵盖一朝的通行选本却也只偏向桐城文人,这种看似画地为牢的自我封闭,实际代表了此时桐城地区户习家传、师承紧密、互为姻亲的学术传承。
因此,在受到“汉学”打击时,桐城士人才迫切希望恢张门户,既是为了抵制“汉学”,也是为了桐城学者建立一种地域显学。而像《龙眠风雅》这种地域性的乡贤文献,与涵盖一朝的合集通行选本不同,其以乡人为收录主体,以弘扬地域文化为核心主旨。所以,桐城的乡贤文献在编撰时,不仅少去了道德攻讦,也在无形中增加了桐城士人的地域认同。作为桐城第一部付梓成功的大型乡贤文献《龙眠风雅》,方东树就曾言:“吾始读《龙眠风雅》,固以叹桐城人文之盛。”[11]318方东树是嘉道时期(1796—1851)桐城著名的古文大家,也是桐城派的中坚人物,他在为《古桐乡诗选》作序时,就首次提到“为学者,不以地域,方能推之古今、上下、百世而无间。”[11]317他认为,桐城学术不可囿于一乡,而应将其推至天下。萧穆也曾言:“吾邑自明以来,词章最盛。乡先辈如钱田间、方嵞山、姚羹湖、潘蜀藻、马湘灵,诸先生各有选本。然而,所谓诗选四十家诗,《诗传》《诗钞》皆就散逸,独潘氏《龙眠风雅》一书稍类于世,年久亦渐渐漫,其后王悔生学有《枞阳诗选》、方拳庄明经有《方氏诗辑》、马公实通守有《马氏诗钞》,此三书颇为精核,然或只及一隅或为一族而设,皆不若《龙眠风雅》一书之能包一邑之人才。”[15]78上述或为一族之家集,或为桐城县下一乡镇之诗歌总集。因此,萧穆认为《龙眠风雅》作为能包揽一邑人才、恢弘一地学术的大型合集文献,应是后世桐城乡贤文献效法的范本。可知,在“汉学”逐渐兴起,桐城家学衰落的大背景下,清中期的桐城士人已然萌生了由“表彰宗族”转向“地域认同”的思想趋势。陈焯《龙眠风雅序》早在清初就已提出“以地著者,又因以派分矣”[8]6的明确观念,宣城早在明隆万年间(1567—1620),梅鼎祚便著有合集乡贤传记《宛雅》,康熙时期(1661—1722)施润章续编为《宛雅续》。然而,施润章却评价《龙眠风雅》:“所谓罗遗文于既坠,发潜德之幽光。虽限以韵语,不过一邑之书,而知人论世,殆与《汝南先贤》《襄阳耆旧》相伯仲矣。”[13]59在攀附桐城文化的同时,也标榜其乡宣城诗派,称潘江“独以《风雅》张龙眠”[13]59,显然是将《龙眠风雅》的成书作为桐城地域文化流派建立的典范。
继《龙眠风雅》之后,嘉道年间(1796—1851)桐城第二部大型乡贤文献的《桐旧集》的编撰,便追承《龙眠风雅》称:“吾桐之诗,康熙间木厓潘氏曾辑之。今岁二百年,诗家辈出,而卷帙浩繁,或有选辑一乡一族之诗,而合邑通选,未有续其事者。”[24]5于是,“广为征采,合潘本而并选之。”[24]7在编撰时,例溯源流:“齐蓉川廉访,以诗著有明中叶,钱田间振于晚季,海峰出而大振,惜翁起而继之。”[24]1徐璈不仅历数桐城诗学的发展,最后更直接言道:“海内诸贤谓古文之道在桐城,岂知诗亦有然哉!”[24]1与清中期桐城士人开宗立派的学术潮流相呼应,在桐城古文派大出于世的同时,赫然树立了“桐城诗派”的概念。嘉道年间(1796—1851)至光绪年间(1875—1908),《桐旧集》《桐城文录》《龙眠丛书》《国朝桐城文征》《国朝桐城文征约选》等大型桐城乡贤文献层出不穷,其收录方式均采用“宽选”,总序书写中也明显具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特点。古文收录“以有关于义理、经济、事实、为主。”[25]这些桐城乡贤文献在编撰过程中,都明言此举是对《龙眠风雅》的赓续传承。可以说,在清中期,桐城士人逐渐将地域与文学流派契合起来,这在桐城地域文化观念认知的层面上,是一个莫大的进步。正因为如此,《龙眠风雅》《桐旧集》《桐城文录》《桐城古文约选》《桐城文征录》等桐城地方文献的编纂历程,与桐城学者开宗立派的形成路径基本呈现出并行的轨迹,表现出了强烈的地域意识。
其次,清朝嘉道年间(1796—1851),桐城士人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宋学”的道德建设与经世致用方面。《龙眠风雅》也是桐城第一部具有独立选本价值观的地方文献,其“清真雅正”的选本观,也让桐城士人对其多有追溯。近代刘声木言:“实则桐城文学兼言程、朱之学,大体皆言行足法,不独文章尔雅,堪为师表。”[26]作为乡邑文献总集的《龙眠风雅》,虽受到南山集案的影响流传受阻,但其选本精神符合这一时期桐城士人发扬“宋学”道德重建的目标。桐人认为,“纂次郡邑之诗,必学深识明,始得品第公允,去取精当也。”[24]5这便是要重视乡贤文献编撰者的选本观。缪荃孙在重刻潘江《木厓文集》时,便溯源桐城文脉传承并称:“近世之言散体文者,必曰桐城。师桐城者,必曰方望溪侍郎,一得而刘,三传而姚,凡读书人,无不知之。然方氏之友,文名颉颃者,曰戴潜虚,而潜虚则师事潘蜀藻先生。”[27]戴名世主张古文要立诚有物,率性自然,提倡道、法、辞并重,精、气、神合一,纵横百家而成一家之文,奠定了桐城古文理论的基础,被尊为“桐城派”之先驱。而缪氏此言不仅认可了戴名世是为桐城派先驱,而且指出戴名世的治学思想源自潘江,肯定了潘江的学术立场属于桐城正统派。这为清中后期桐城乡贤文献继承《龙眠风雅》“清真雅正”的选本观提供了理论支撑。
早在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文献编撰者就对诗歌选本的“风雅”标准多有关注,以“雅”命名的就有《皇明风雅》《友雅》《国雅》《梁园风雅》《四明风雅》等。《毛诗序》定义风雅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28]潘江以风雅命名其书,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摛词之家,取法乎上,风雅二字,尽之矣。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亦曰:此吾龙眠之风雅云尔。”[8]16可知,潘江取名《龙眠风雅》之义,便是追承“宋学”的道德教化目标,以“革风俗,正人心”为要旨,这让《龙眠风雅》具有了极强的“宋学”编撰理念。宋实颖认为,桐城“人尚实学,不竞浮名。”[8]6故有明三百年来诗体三变,而龙眠之名卿学者,则“坚守朴学,一以正始为归者。”[8]7桐城人在诗歌内容上重“学理”,在审美上尚“雅正”,均来源于对“宋学”的坚守。对于女性,《龙眠风雅》为女性列传,收录诗篇,也是为了配合儒家传统的列女旌表,其中提到方维仪搜集古今名媛诗作,删定编辑成《宫闺诗史》一书,全书分正、邪二集。潘江认为,此书“主刊落淫哇,区明风烈,录正摈袤,尤裨风教。”[8]18,展现出女性明忠孝节义,睦族亲情,淡雅和美的诗歌特点。吴道新因此认为,《龙眠风雅》“观其命篇,则知以操选之旨:浑而正,公而平”[8]4。方苞作为桐城的古文大家,一直视诗歌为“小道”,但其也认为“诗之用,主于吟咏性情,而其效足以厚人伦,美教化”[22]605。就诗歌来说,他们推崇儒家的诗教观,强调诗歌“助流政教”的功能。桐城派虽为古文派,但他们在思想上也多为“阐道翼教”;在文风上力求“清真雅正”。光绪年间,萧穆编撰《国朝桐城文征约选》是一部古文选本,以“清真雅正、文从字顺者为宗”[15]49的选本观,选录清初至同治年间(1616—1875)桐城作者57 家、文580 余篇。桐城的古文选本观便与诗歌的“风雅”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谓的“风、骚、乐府,户习家传。”[8]6也正是《龙眠风雅》赖以编纂的乡邦文学氛围与文化基础。因此,作为第一部大型乡贤文献的《龙眠风雅》,其“清真雅正”的选本观,始终未脱离桐城士人崇尚“宋学”的价值理论范围。
桐城士人既有维系儒学正统、传承家族文化的宗族使命感,更有教化世风人心、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心与理想。《龙眠风雅》作为一部大型乡贤文献,其虽不具有像姚鼐、刘大櫆“熔铸唐宋”并以“文法通诗法”的独特的诗学理论,也并非像《昭味詹言》是一部专门阐论桐城学术的著作,更不是《历朝诗约选》《明诗别裁》《国朝诗别裁》等涵盖一朝的大型选本,其“风雅”选本观也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但是,其以崇尚“宋学”为基本理论指导的编撰理念和“宽征恕取”以乡人为核心的收录方式,符合这一时期桐城地区的学术变迁和建立地域认同的现实需求。因此,命途多舛的《龙眠风雅》虽然受到南山集案的影响,流传受阻。但其编撰精神的传承,也让桐城后续乡贤文献的编撰逐渐勾勒出一个脉络清晰的地域流派。
结语
明末方学渐编撰的《桐彝》《迩训》收录甚简,体例不详。康熙《桐城县志》又款类不符,被置于清廷的统一控制下。《龙眠风雅》编撰于明清易代之际,正面临着兵燹频发,桐城文献不足而让“地方失语”的的尴尬处境。所以,《龙眠风雅》使用合集的编撰体例,将人物传记与诗文著作合二为一,以烘托桐城的诗学文化成就,其“宽征恕取”的编选方式,也满足了清初桐城士人“表彰父祖,显亲扬名”的现实情感,具备“传乡贤文献,以备国史采之”的巨大文化意义。因此,康熙年间,《龙眠风雅》的背后受到集整理、保存、刊刻于一体的乡族文化网络的广泛支持。清中期,“汉学”的兴起,桐城作为文化重镇,其赖以生存的“宋学”理论传统受到破坏,此时桐城士人乡贤文献的编撰目的已然由“宗族竞赛”转向“地域认同”。《龙眠风雅》这种地域性乡贤文献合集的编撰行为,符合这一时期桐城地区的学术变迁和建立地域认同的现实需求,其“雅正”的选本理念,也始终未脱离桐城崇尚“宋学”的价值理论范围。因此,清中后期《枞阳诗选》《古桐乡诗选》《桐旧集》《国朝桐城文录》《桐城耆旧传》赓续传承了《龙眠风雅》用书籍构建地域文化的书写传统,在书写中考证学术源流,在选本中传承桐城文脉正统,彰显桐城“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的文化特质,以此达到确立其乡里传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