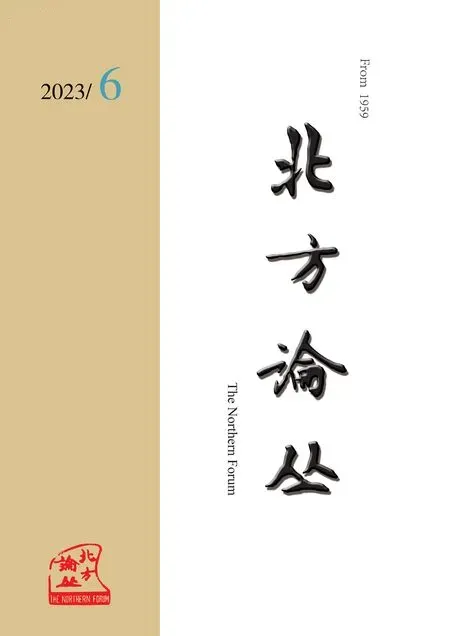微言何以相感:春秋赋诗的内在理路及辨体观念
崔德全 任竞泽
春秋赋诗,又称赋诗言志,是指春秋时人在外交宴享朝聘盟会之际,借赋诗来言说自己或自己国家的意志。《汉书·艺文志》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概括性描述:“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这段话为历来研究者引述,但学界对这段话的阐释似不够深入:何谓微言,为什么要“微言相感”,怎么样才能做到“以微言相感”,“微言相感”的言说效力若何,这一“微言相感”的言说方式对后世中国文学、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在学术界尚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本文即尝试着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索。
一、“微言”释义
《汉书·艺文志》开篇即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1]1701,又于“诗赋略”后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1]1755-1756。这两处的“微言”含义深微,颇值得玩味。检视同时期其他文献,“微言”盖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微言是委婉曲折之言,甚至隐语、密言,而非直言、明言。《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七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杜预释“微而显”曰:“微词而义显”;释“志而晦”曰:“志,记也;晦,亦微也。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又释“婉而成章”曰:“婉,曲也。谓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2]1913杜氏认为,“微”与“晦”“婉”义同,均为婉转曲折地言说,而不直言其事的意思。
“微言”甚至可以指隐秘之言,藏匿之言,不可告人之言。这种“微言”与直言、明言相对。《春秋左传正义》卷六十:“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杜预注曰:“微,匿也。”[2]2178《尔雅·释诂下》云:匿,“微也”。[3]2575《说文》:“匿,亡也。”段玉裁注“匿”曰:“《广韵》曰:藏也,微也,亡也,阴奸也。”[4]635微、匿互训,有藏匿、隐蔽之意。又,《汉志》李奇注曰:“微言者,隐微不显之言也”。[1]1701张舜徽先生在《汉书艺文志通释》里引顾实语曰:“微言者,隐语之类也。”[5]231《吕氏春秋·审应览》之“精谕”篇曰:“白公问于孔子曰:‘人可与微言乎?’”高诱注曰:“微言,阴谋密事也。”[6]222“隐微不显之言”“隐语”“阴谋密事”云云,都是在说“微言”是隐秘之言,不能明说之言。
第二,微言是精微要妙之言。《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谓屈原曰:“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7]2482微,含有精妙之意。辞微,即言辞精妙,寓意深远。
第三,微言即简言、少言、略言,但在简略中包蕴大义。细细玩味“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二句,“微言”与“大义”互文成意,意谓微言中包含大义,大义就在微言之中。孔子之言,言近旨远,语浅意深。《史记·儒林列传》云:“(仲尼)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7]3115在《春秋左传注》中,杨伯峻先生注“微而显”曰:“言辞不多而意义显豁”。[8]870宋林希逸《庄子口义》曰:“绪言,微言也,谓其略言而未尽也。”将“微言”看作简略而未尽之言。[9]640
第四,微言还是指叙述中寓褒贬之言。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0]273孔子的《春秋》为什么会对乱臣贼子具有如此巨大的震慑力,这个问题须从春秋时期的史官说起。春秋时期的史官,其职责不仅在于记事记言,更在于通过史笔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惩恶扬善,以为后王法。正如蒋伯潜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史官书史,“其旨不在记事实,而在借事明义,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11]296皮锡瑞也曾深刻地指出,“《春秋》是孔子作不是钞录”。在《经学通论》四“论《春秋》是作不是抄录是作经不是作史杜预以为周公作凡例陆淳驳之甚明”条中,皮锡瑞论曰:“作是做成一书,不是抄录一过。又须知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后人不知经史之分,以《左氏》之说为《春秋》,而《春秋》旨晦。”[12]2皮氏又于“论《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微言在改立法制孟子之言与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条论道:“《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讨诛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12]1他又在“论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后世无乱臣贼子而能使乱臣贼子不能无惧”条中继续申论曰:“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后世无乱臣贼子,而能使乱臣贼子,不能全无所惧。自春秋大义昭著,人人有一春秋之义,在其胸中,皆知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虽极凶悖之徒,亦有魂梦不安之隐,虽极巧辞饰说,以为涂人耳目之计,而耳目仍不能涂,邪说虽横,不足以蔽春秋之义,乱贼既惧当时义士,声罪致讨,又惧后世史官,据事直书。”[12]25
从史官的职责出发,孔子作为史官,其作《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所惧怕的与其说是他们的罪恶行径将被公诸于世,倒不如说是“惧怕自身行为受到宗教和历史的双重审判”。[13]149“《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7]3297(《史记·太史公自序》)对这些“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7]3298(《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人,孔子都从礼义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了历史的裁决和审判。这正是刘勰所云“《春秋》辨理,一字见义”“《春秋》一字以褒贬”之义。
总之,“微言”有多方面的含义:简略而暗含深意或具言外之意的言辞,蕴含大义的言辞;由于外在条件的制约,无法直说或不能直说的言辞,隐晦的言辞,暗地里的、秘密的言辞;精妙的言辞,曲折而具有策略性、技巧性、艺术性的言辞;寓褒贬于叙述之中的言辞等。
二、以微言相互感化:春秋外交赋诗的事理逻辑
“春秋时代是以礼为核心的人文世纪”[14]54,但春秋又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王室衰微,诸侯崛起。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诸侯国之间也学着周天子的模样,于行朝聘礼时赋诗。古代诸侯朝见天子,亲往曰朝,遣使曰聘,合称朝聘。春秋时期,政在霸主,诸侯朝见霸主,亦曰朝聘。“诸侯僭用天子诗乐以享来宾的礼仪场景变得越来越普遍,……春秋赋诗正是在这种礼乐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用诗机制。”[15]15我们来看几个典型的事例。
(1)《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九下:
冬,公如晋,朝,且寻盟。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公还,郑伯会公于棐,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2]1853
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3年),郑国国君在棐设宴款待鲁文公。郑大夫子家赋《鸿雁》。《鸿雁》,《诗·小雅》篇名,此诗以鸿雁哀鸣喻亡民流离失所。子家赋此,显然不是说孤雁哀鸣,也不是说流民可怜,而是把自己和郑国比作孤雁、流民,希望鲁文公能可怜他们,救救他们,再到晋国为其请和。(按:此前,晋郑已结盟,而郑背晋,有二心于楚,晋欲发兵攻之。)但鲁文公已往返晋国两次,实不欲再往。子家更赋《载驰》之四章,把郑国置于“控于大邦,谁因谁极”之绝境。这样,鲁文公就实在无法拒绝如此恳切之请了,于是借赋《采薇》表示愿意再为郑国跑一趟。
(2)《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七:
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国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恤其患而补其阙,正其违而治其烦,所以为盟主也。今为臣执君,若之何?”叔向告赵文子,文子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叔向曰:“郑七穆,罕氏其后亡者也。子展俭而壹。”[2]1990
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46年)秋七月,齐侯郑伯到晋国去请求晋侯释放卫侯。晋侯设宴款待他们,并于席间赋诗言志。当齐侯、郑伯的意图被晋国君臣故意曲解后,齐侯、郑伯又搬出《辔之柔矣》和《将仲子兮》两首诗。《辔之柔矣》,逸诗,有“柔辔之驭刚马”之意,齐大夫国景子赋此寄望晋侯能“宽政以安诸侯”。《将仲子兮》,《诗·郑风》篇名,郑大夫子展赋此,以“众言可畏”警示晋侯“众人尤谓晋为臣执君”。这样,齐郑二国大夫通过赋诗设喻的方式,从正反两面,软硬夹攻,既让晋侯沉浸于自己作为霸主的崇高和喜悦之中,又让晋侯感受到人言可畏的恐惧。在这种既喜悦又恐惧的氛围里,晋侯也悄然改变了主意,答应齐郑之请,释放卫侯。
春秋赋诗作为一种话语行为,实际上是赋诗者的意图在对话过程中曲折穿行并寻求实现的过程。首先,赋诗者会选择与自己或自己国家的意志具有象征或譬喻关系的诗,并将“志”悄悄地隐藏在诗中。其次,赋诗者在宴会上吟诵自己选择的某诗或某诗之某章,并借此渲染、建构起一种情境或氛围,使对方不自觉地沉浸其中。最后,在建构起的情境里,赋诗者悄悄地、隐蔽地将自己的意图迂回曲折地、优游不迫地传递到观诗者哪里。而在诗情氛围的熏染下,观诗者也被悄悄地融化,于不知不觉间理解并接受了赋诗者的意图,最终瓦解了起初可能要拒绝对方请求的决心。尽管最后观诗者会看穿赋诗者的别有用心,但在诗情的感染下,观诗者往往会原谅赋诗者的良苦用心。在这一过程中,诗起到了很好的中介作用。是所赋之诗,巧妙地隐藏了赋诗者的真正志向和意图;是所赋之诗,建构起了生动可感的氛围或情境;同样是所赋之诗,引导了观诗者理解、领会并最终促成了赋诗者的真正意图、目的之实现。“开头只是‘诗’,在听者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它并不造成对双方关系的危害;而听者一当意识到说者的目的,他又往往已经转变了自己的立场或者原谅了说者的苦心……”[16]72。在这场辞浅义深的对话中,包含着极高深的策略:言说渠道的挖掘,情感氛围的建构,譬喻关系的设置,听者心理的侵入、掌控等。
这是一场双向互动的对话,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充满了张力,充满了歧义,有时和风细雨,有时剑拔弩张。这里有妥协,有对抗,有问候,有试探,有请求,有拒绝,谈吐间体现着春秋时人的智性和诗性。这是“真正的会谈:会谈中,只需凭借所引诗句的调解,一方就能够使另一方改变意向,使之符合自己的利益”[16]71。表面上看起来,这种会谈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他不能直接作用于意志”[17]85;但其实际效果还是很令人震撼的。据笔者统计,在被记载下来的春秋时期的30多场外交赋诗活动中,赋诗者的意图或目的成功实现的比例在90%以上。所以,张舜徽先生说:“《诗》教主于温柔敦厚。深于《诗》者,则可使于四方,折冲樽俎。相与言谈之顷,不直截言之而比喻言之;隐约其辞,情文相感。大之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小亦可以登礼让于衽席。辞令之美,关系甚大。”[5]231
三、春秋赋诗的完成条件
春秋赋诗,表面上是为了酬酢,实际上是为了交涉。那么,赋诗者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意图顺利实现呢?这需要一些条件。
第一,赋诗双方熟习《诗三百》。《礼记·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18]1342西周时期,学《诗》习礼是上层贵族必备的基本能力或文化素养,而学诗又处于学习的第一个阶段。孔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2]2487学诗的最终目的在于用诗,内则参与国政,外则应对诸侯。学而不知用,不能用,不会用,则学亦同于未学。孔子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2]2507那么,为什么诵《诗》三百能达于为政呢?钱穆先生对此做了详细解释:“《诗》实西周一代之历史。其言治闺门之道者在《二南》。言农事富民之道在《豳风》。平天下,接诸侯,待群臣之道在《大、小雅》。《颂》乃政成治定后始作。而得失治乱之情,则《变风》《变雅》悉之。故求通上下之情,制礼作乐以治国而安民者,其大纲要旨备于《诗》。诵此三百首,便当达于为政。”[19]332孔子又尝对其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19]439意谓“诗有比兴,答对酬酢。人若不学诗,无以与人言语。”[19]440。对《诗》的熟知、熟用是春秋列国卿士大夫的最基本技能。诸侯间朝聘盟会赋诗见意,正是他们展现他们高度的文化教养的重要机会。所以,余英时先生指出,“春秋时倘非深于诗书之教的人是不敢在国际宴会场合出现的”。[20]18
笔者曾做过统计,据《左传》记载,自僖公二十三年至定公四年,在春秋列国间的赋诗活动中:就赋诗篇次来看,《诗》中的《大雅》被赋8次,《小雅》35次,《郑风》8次,《召南》6次,《鄘风》3次,《卫风》2次,《秦风》、《唐风》各1次,《周颂》1次,逸诗2次。
数据显示,赋诗者所赋最多的是《雅》。这或许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雅”的性质。《毛诗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21]272雅,是周天子在王都、宫廷宴享各地诸侯及四方来使时所唱的乐歌,通行于全国。而“就地域分布来说,鲁、晋、郑三国赋诗之风最盛,其次已发展到宋、卫、小邾等中小诸侯国和楚、戎等蛮夷地区。”[22]92这说明“雅”传播的地理空间已经相当广了。其次是《郑风》和《召南》。《郑风》被赋篇次仅低于《雅》,但赋《郑风》者皆是郑人,无一例外。郑人熟习《郑风》,自不待言,而他国观诗之人应也熟习郑风。不然,晋人何以知郑人之志,又能未卜先知郑人之命运哉?这或许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郑国乃诸侯之大者。缪钺尝言:“甲国之诗,乙国大夫赋之,而丙丁诸国士大夫亦均能解其义,此例甚多。苟非王朝辑录各国风诗颁布诸邦,不能有此现象。”[23]13
然而,到了春秋中叶以后,礼崩乐坏,《诗》教渐衰,就断续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赋诗而不见答。在《左传》所记载的春秋外交赋诗活动中,因不知《诗》而不答赋的情况只有两次,下面分别叙述。
《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八: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5年),齐庆封聘于鲁,“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2]1995庆封衣着、车马装饰非常华美,与其仪容殊不相类。叔孙豹为其设宴,庆封不敬。叔孙豹赋《相鼠》以讥刺庆封。《相鼠》,《诗·鄘风》篇,诗中有云:“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庆封竟不知道叔孙豹在讽刺自己。
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夏,宋国华定聘于鲁,昭公享之,为赋《蓼萧》,华定不知,又不答赋。《蓼萧》,《诗·小雅》篇,诗中有云:“既见君子,孔燕岂弟。”昭公赋此,意在赞美华定,以联络鲁宋交谊,而华定却不明白。随后,昭公预测说他将来必定会逃亡。果然,十年之后,也就是鲁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华定逃到了楚国。经云:“二十有二年春,齐侯伐莒。宋华亥、向宁、华定自宋南里出奔楚。”[2]2099
上述两次“观诗不而见答”现象的出现,皆是由于观诗者不了解、不熟悉《诗》。
二是赋诗的频次逐渐降低。刘生良把春秋赋诗的发展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可以叫做起始期,以僖公到成公年间,共6例“赋诗”;中期为兴盛期,在襄公、昭公年间,共26例,几乎占到《左传》所载赋诗例的 80%;后期为衰落期,仅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师,秦哀公为之赋《无衣》和定、哀之际鲁公父文伯之母(敬姜)欲为文伯娶妻,飨其宗老,而为赋《绿衣》之三章2 例“赋诗”,“且均非庄重场合”。[22]91
可见,春秋赋诗在鲁襄公、昭公年间最为兴盛,此后赋诗频次逐渐降低,直至最终消歇。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5年),申包胥如秦乞师救楚,秦哀公赋《无衣》。这是史书记载的最后一次赋诗活动。至战国年间,礼乐文化彻底崩坏,诸侯争霸,相互间合纵连横,背信弃义,攻城略地,无暇顾及礼义,更别说赋诗以见意了。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条云:“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24]749
第二,“得体”的表达方式。我们把适合不同语境的需要,采用恰当的方式,说出的话交际效果最佳,叫作得体。在赋诗时,赋诗者会选取符合自己身份、地位和当前处境的诗,以求准确妥帖地表达自己的情志和善意。用春秋时人的话来说就是“歌诗必类”。学界对“歌诗必类”的解释分歧较多。
俞志慧在《君子儒与诗教》一书中认为:“类有品物相随,统类,知统类等义项,具体到赋诗活动中,赋诗之人与所赋之诗也当各有统类,也就是说,具体的诗必因赋诗者与接受者双方的身份、地位及所处场合有着不同的适应性(即规定性和相似性),‘不类’也就是说违反了适应性。”[25]83康宁在《“立象尽意”思维下的“兴必取象”与“歌诗必类”》一文中认为:“‘歌诗必类’有‘从义类’和‘取恩好之义类’等意思。”[26]59战学成则在《宾礼与春秋时代赋〈诗〉风气》中认为:“歌诗必类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唱诗必须与舞蹈音乐相配,不能乱其节奏;另一方面,要求诗的内容,必须准确明白表达赋诗之人的恩好之义,以符合当时的场合、气氛、宾主身份以及谈话主旨等,是赋诗必须遵循的原则。”[27]26
笔者认为,杜预和孔颖达已把“歌诗必类”解释得很清楚了。在《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三“歌诗必类”下,杜预注云:“歌古诗,当使各从义类。”孔颖达疏曰:“高厚所歌之诗,独不取恩好之义类。”[2]1963根据这两条注释,“歌诗必类”概有二义:一为,类,善也,谓赋诗表达善意;一为,类,相似也,谓赋诗必须符合当事人的身份、地位及其所处情境,赋诗必与音乐、舞蹈之节奏相似,既相配。绝大多数情况下,赋诗者都能够做到赋诗得体,“歌诗必类”;而在极个别情况下,赋诗者赋诗不得体或失体,即“歌诗不类”。这样的事例很少,据笔者统计,只有3例。因关系巨大,兹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全录如下:
(1)文公四年: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2]1840-1841
这件事发生在鲁文公四年(公元前622年),鲁文公“有意”为前来朝聘的卫宁武子赋《湛露》及《彤弓》。一般而言,有赋必有答。而宁武子不辞谢鲁文公,又不答复他,这颇使我们疑惑。对此,孔颖达作了非常精彩的解释:“此时武子来聘,鲁公宴之,于法当赋《鹿鸣》之三,今赋《湛露》《彤弓》,非是礼之常法……此二篇,天子宴诸侯之诗,公非天子,宾非诸侯,不知歌此何意。盖以武子有令名,歌此疑是试之耳。”看来,文公是故意赋诗不类。宁武子知鲁人失于所赋,“辞则章主之失,答则以当其宠,故不辞又不答赋,佯若不知,其所为如愚人然”。
(2)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焉”。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2]1963
这件事发生在鲁襄公十六年(公元前556年),在晋平公主持的宴会上,齐国高厚唱的诗没有向晋侯表达善意,惹得晋大夫荀偃发怒并认为他有二心,高厚惧,逃归,诸大夫都发誓说要讨伐他。
(3)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2]1997
这件事发生在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3年),赋诗的郑国诸臣,除伯有外,都在赞美夸奖赵孟,表达善意,以巩固晋郑同盟之谊。赵孟对于这些夸赞,有的谦而不受,有的客套一下。而伯有不一样,他所赋的诗是《鹑之贲贲》,其中有“人之无良,我以为君”二句,言外之意是说他的国君是一个无良之人。外交场合,宴享聘问之间,伯有既没有向客人赵孟表达善意,又在外国使节跟前说自己国君的不是,这显然很“不类”了。正是因为伯有赋诗“不类”,在不恰当的时间、不恰当的场合说了不该说的话,所以才招致了后来的杀身之祸。三年之后,即鲁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0年),郑国因伯有和子皙争权而发生内乱,在这场内乱中,伯有被杀死在大街上。
可见,赋诗类与不类,得体与不得体,关系甚大。赋诗得体,大可以化解战争,小可以结为盟好;若赋诗不得体或失体,轻则会遭对方嘲讽或批评,重则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
最后,对彼此情境的深刻了解。春秋赋诗中,赋诗与听诗双方大都非常清楚对方的身份、地位、需求及其所处情境,也谙熟《诗》意。但是,如果赋诗或观诗其中一方佯装不知或故意误会赋诗之意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文公四年,宁武子不辞又不答赋属于第一种情况,双方都在假装或试探;襄公二十六年,齐郑二国大夫各赋《蓼萧》和《缁衣》而被晋国君臣误解,则属于第二种情况。
四、“微言”大义:春秋赋诗的象征与影响
春秋赋诗的意志表达方式的间接性和隐蔽性,使其成为中国人言说方式的普遍象征。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曾说,中国人拥有一种“迂回表达的能力”,中国人“更多的是从侧面,通过迂回的方式间接地暗示某种不能够、不应该说的东西”[17]6。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
中国人发怒时会互相谩骂,但是拥有巧妙骂人的语言才能的人乐于用最精微曲折的词语表达进攻的意义,他们使用隐喻的方法,在吵架时,对方抓不住其中真正的含义,因为这样的隐喻像裹着糖衣的苦药,需要对方消化才能体味。[17]7
作为中国人言说方式的普遍象征,赋诗言志之间接、隐蔽的表达方式对中国后世的文学、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民歌中“比兴”手法的大量运用、诗歌的“讽谕”功能、卿士大夫们“主文而谲谏”的规劝方式等,都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这一言说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人的劝谏艺术,它增强了古代臣子劝谏的艺术性、趣味性和实用性。《说苑·谏诤》云:“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孔子曰:‘吾其从讽谏矣乎!’”[28]206《初学记》谓:“讽谏者,智也,知患祸之萌,睹其未然而讽告焉”。又云,“讽也者,谓君父有缺而难言之。或托兴诗赋以见乎词,或假托他事以陈其意,冀有所悟而迁于善。”[29]437讽谏可一举两得:既能劝谏帝王,又能保护自我身家性命之安全。《毛诗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2]271“谲谏”谓“咏歌依违不直谏”,“不直言君之过失”。白居易也是主张以“歌咏”的形式讽谕君王,“救济人病,裨补时阙”。[30]962后世臣子劝谏君王,大多是以婉谏或“主文而谲谏”的方式进行的,而像唐室魏征那样直言极谏、以死相争的臣子及其做法则寥寥无几。
其次,迂回曲折、意在言外的表达方式也深刻影响了古人的诗词创作,为古典诗词增添了丰富的情趣、韵味。中国古典诗词讲究言不尽意,讲究余味悠长。当然,古典诗词余韵、趣味的产生,既与汉字与语意的关系紧密相关,又受诗歌创作的比兴传统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深刻影响。刘勰的“隐秀”观,钟嵘的“滋味”说、司空图的“韵外之致”说以及明清时期王士禛的“神韵”说、王国维的“境界”说等理论术语的提出,以及历代批评家对古典诗词曲赋言外之意的批评阐释,足以见出迂回曲折的言说方式之深远影响了。
最后,我们来谈谈“歌诗必类”与后世文章辨体理论的内在关联。《说文解字》云:“辨,判也。”又释“判”曰:“判,分也。”段玉裁注曰:“朝士判书,故书判为辨。大郑辨读为别。古辨、判、别三字义同也。”[4]180“辨”,包含着古人对事物进行分别、分辨的意识。
“作为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理论核心,辨体范畴及其理论批评在中国古代文体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基本起点,对于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31]122中国古代文章辨体理论内涵非常丰富,它大体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辨文体的体制类别;二是辨文体的体貌风格;三是辨文体的源流演变。
如果说,文章辨体是辨析文章的类别、风格、高下和源流的话;那么,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则包含着辨析诗歌的内容、风格、作用及其适用场景等内涵。所以,从更深层次的思维方式上来讲,“歌诗必类”与后世的文章辨体是相通的。而思维方式的研究,也应该成为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基本内涵和对象。
另外,春秋时期,赋诗的“类”与“不类”也与后世文章写作的得体与失体、尊体与破体等现象,在逻辑上也有着同构的关系。“歌诗必类”,即赋诗得体,是春秋赋诗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是实现赋诗者利益最大化的有力保障;而文章辨体、为文“得体”也是文章写作的首要之事和基本原则。于是我们看到,赋诗的类或不类与作文的得体或失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相似性。换一个角度来看,赋诗得体,是一个人明礼、懂礼、讲礼的标志;赋诗不得体,是一个人在有意或无意间突破周王朝礼乐文化的表征。为文得体,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而勇于破体又是一个作家才胆识力的展现,是推动文学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歌诗不类”,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礼乐制度的坍塌;同样的,为文失体也往往标志着特定文体规范的失效。总之,“歌诗必类”与文章“辨体”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或许还值得我们做更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