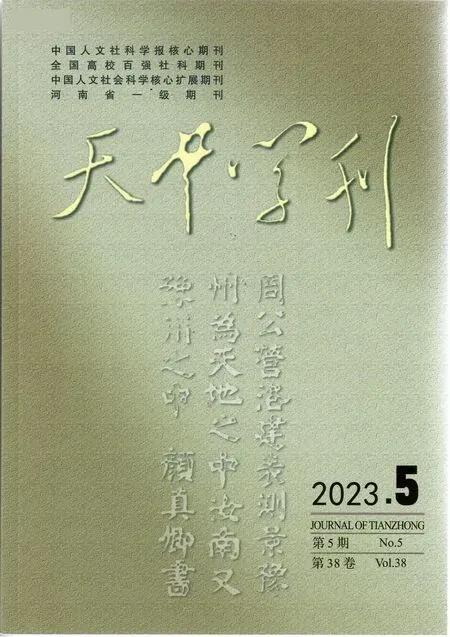逻辑曲解与思想误读:叶适对荀子批判之平议
姚 海 涛
(青岛城市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266106)
荀子与叶适,一为先秦学术集大成者,一为南宋永嘉事功学派集大成者,生活年代相距约1400 年。虽然二人思想上都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但在宋代荀子及其思想受到质疑、否定、打压的大背景下,叶适也对其进行了全面审视与无情批判,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中一桩独特事件。
《习学记言序目》一书以读书札记的形式评鉴诸书,所涉典籍极为宏富,经史子集无不包罗,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叶适对诸书的真实看法,也映照了叶适的思想。叶适于书中专辟读《荀子》札记,以犀利到近乎苛刻的视角与言辞对荀子进行了批判。由于立场差异与思想冲突,叶适的批判多属无的放矢,且充斥着不少的误读与曲解。之所以如此批判,既有时代之原因,也有个体思想差异之因由,体现着叶适思想的“一贯之道”。叶适的荀子批判具有鲜明的逻辑曲解与思想误读特点,可惜学界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尚属凤毛麟角。张涅从叶适与荀子相通之处立论,着力于二人思想之相通[1]。朱锋刚则对二者的差异性进行了客观还原,认定二人并非“思想盟友”[2]。两位学者的研究虽然各有其侧重,却终是未达一间。对叶适的荀子批判进行再审视,并作进一步的正面关切与适切回应,对于深化叶适与荀子的相关研究无疑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曲解误读多偏见,欲抑先扬全批判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44 对荀子的批判,涉及《荀子》32 篇中的13 篇。具体言之,所涉篇目有《劝学》《荣辱》《非十二子》《仲尼》《儒效》《君道》《议兵》《天论》《正论》《礼论》《解蔽》《正名》《性恶》,并于卷末撰一《总论》,共计14 篇。由此可见,叶适所论及者皆为《荀子》重要篇目,且基本上是学界公认的荀子本人所作之篇目。叶适评荀子,多用《荀子》语词,如“陋儒”①“狂惑”②“基杖”③,此正符合读书札记的创作特点。但囿于读书札记的篇幅与体例,加之叶适对荀子抱有的极深成见,故所论多为指责性的直接评论,而缺乏有信服力的分析论证。易言之,叶适论荀,极为偏颇,绝非客观。
首先,叶适对荀子的不少批评,并不贴合荀子本人的思想,纯属个人主观偏见,且有不少歪曲误解之论。如他认为,荀子不应进入秦国,更不应于秦昭王面前辨析“儒有益于人之国”,因为“秦以夷狄之治,堕灭先王之典法,吞噬其天下,别自为区域。孔子力不能救,不过能不入秦而已,子孙守其家法”[3]648-649。荀子打破了“儒者不入秦”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背离了孔子。然而,儒者不入秦既为儒者旧法,岂能死守不放?秦国随着商鞅变法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天下的实力,为何不能入秦推广儒者之说以利天下世人?即使秦国真的是夷狄之治,孔子尚有“欲居九夷”之念,况且真正的儒者应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与行动,为何荀子不能有入秦而教化之的担当与作为?当时,天下统一的形势趋于明朗,故荀子遵循了儒者救世治民的本分,有入秦之见,并与秦昭王答问论辩。同时,荀子批评秦国治理存在“无儒”之弊,也并无任何不当。后来秦用李斯,以法家思想治国,二世而亡,即是明证。退一步讲,荀子岂能逆料后来秦不能自反之事?此正如孔子见互乡童子后所言:“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4]96因此,切不可将后来秦不能自反,乃至生出残暴政治之过,与当时荀子入秦传儒者之道相联系,认为此为荀子不明智之举,甚至将秦亡责任记在荀子头上。
叶适对荀子的评述,以道统为基底与总纲,总体态度是贬大于褒,基本方法是欲抑先扬。如叶适认为:“后世言道统相承,自孔氏门人至孟、荀而止。”[3]654道统之说,始自韩愈。韩愈将道统的终点定为孟子,认为“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不曾将荀子列入其中。后世更无将道统附之于荀子者。所以,叶适所言后世将孟、荀并列入道统之论,实在是突兀和蹊跷。其后,叶适又评荀子为“先王大道,至此散薄,无复淳完”[3]654,并以“辞辩之未足以尽道”为理据,将荀子视为诸子辩者之流,评为无体道之弘心。叶适还言:“自后世若荀卿、司马迁、扬雄,皆不足以知圣贤之言。”[5]711此等言说,更为谬论。叶适本想以欲抑先扬手法批驳荀子,结果却自缚手脚,甚至出现了逻辑的前后矛盾。
综上可见,叶适不仅从根本处否定了荀子对孔子思想的传承,否定了荀子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还将荀子与司马迁、扬雄归为一列,认为其“皆不足以知圣贤之言”。由此观之,在批评、贬抑荀子这一点上,叶适与程朱理学一道站在了贬抑立场,共同形成了“反荀”的历史浪潮,对于荀子历史地位的迅速下滑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将叶适对荀子的误读与曲解略呈如下,并以荀子观点随文剖析与答对,以见叶适之谬、还荀子公道。
二、孔子三语成圣功,荀卿累言反害道
《荀子·劝学》历来推崇者众,而贬斥者鲜。然而,叶适的批判并未放过此篇,认为其“比物引类,条端数十,为辞甚苦,然终不能使人知学是何物”。紧接着,他又点出荀子“全是于陋儒专门上立见识”[3]645。如此批驳《荀子·劝学》,实属亘古未有。
叶适在批驳中将《论语·学而》与《荀子·劝学》相比对,以孔子之高明反衬荀子之浅陋,认为“孔子以三语成圣人之功”。其所指称的“三语”,结合《习学记言序目·论语·学而》可知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3]175叶适对此“三语”推崇备至:“前乎孔子,圣贤之所以自修者无所登载,故莫知其止泊处;若孔子成圣之功,在此三语而已,盖终其身而不息也。”[3]175孔子论学三语为后学提供了“止泊处”,自然可以成为终身效法的经典语录。《荀子·劝学》辞采华丽、逻辑谨严、神思高妙,多受称颂,荀子也因此被称为“学宗”④。《荀子·劝学》首句“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岂不包含学而时习之意?学者杨明照曾对“君子曰”这一用语进行了详细研究,指出:“荀卿之学,原出孔氏。《劝学》首篇,仿自《论语》。是其为学有所祖述,立言有所模拟也。且祭酒传经巨子,躬授《左氏》。故于劝学之始,即假君子之称。正明其渊源有自,非偶然已。”[6]其所言《劝学》是否仿自《论语·学而》虽可商榷,但其从荀子传《左氏春秋》的角度论证孔、荀传承关系,则有一定道理。《劝学》开篇言“君子曰”,其实大有深意。君子一词,实有多义,以政治地位而言,可与庶人对应;在道德修养层面,则与小人对应;此外,还可指特定的人。此处之“君子”,必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志学向道、学有所悟的前代君子。
叶适认为,中国言学之传统可从《尚书·说命下》傅说所言算起。傅说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惟敩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惟说式克钦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7]140傅说所言,句句经典,学于古训、效法贤人、学以逊志、道积厥躬等皆是宝贵的学习名言。朱熹亦将“学”追溯到傅说:“自古未有人说‘学’字,自傅说说起。他这几句,水泼不入,便是说得密。若终始典于学,则其德不知不觉自进也。”[8]大体而言,傅说只是言学之大略,而孔子讲论则更加详尽,此皆能从《尚书》与《论语》中查证。
依叶适之意,前有傅说,后有孔子,论学要略兼备。同时,由于孔子言学于《论语》中历历可见、句句可法,故荀子《劝学》纯属狗尾续貂,且所论亦颇有偏失。叶适认为,孔子论学之本统为合内外、一生死、不厌倦的圆融之事,而一旦打破这种圆融状态,则必有其一偏,而失却本旨。荀子《劝学》之失,正在于此。实际上,孔荀之道,本为一道,言学之道,更是如此。孔子自言“述而不作”,在对文化传统的传承中寓作于述。战国末季,世异时移,学术大坏,荀子注重与时迁徙,应物变化,岂能不调整学习之思想?岂会不调适学习门径入路?荀子长期于稷下学宫董理学务,对于学习有所阐释,理所当然。坦率地讲,人之才性不同,起点有异,勤惰有别,即使同学于一师,所获必有不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若固守前人方法,不深入探究,则学术必不能进步。
叶适所谓陋儒专门之讥主要针对荀子“学数有终,义则不可须臾离”[3]645之言,又联系扬雄所言“学,行之上,言之次,教人又其次”[3]645,一并讥之。叶适对于学习的先后次第、节目规程似有排斥之感,其认为节目法度往往使人进退失矩、得外失内、顾此失彼。因此,叶适注重学习对于内在的改变。但过分追逐内在,会让“学”变得神秘而陷入不可知境地。初学者,必得一定之规,方能学之有得。叶适认为,道无内外之殊,“学”当内外交相发明,不可如荀子般分别出“学”的外在境界。叶适所论固然是一种浑融的讲法,但不注重程序与节目,必然失却可操作性。紧接着,叶适由对荀子的批评转为对当时学界的批评。可见,叶适批荀子论学,有发抒胸臆、批评时学的目的,由是言之,荀子《劝学》篇属代时人受过耳。
荀子隆礼义、贬诗书,将六经分为不同等第,但正如叶适所言,人有良莠不齐,岂可教以同样内容,教法岂能不加区别?从学习本身来看,学无内外之别;从学习者来看,无生死壮老之别。荀子对“学”进行了相当广泛而深刻的探讨,绝不是狗尾续貂、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在孔子基础上对“学”的进一步规范化和系统化。
三、止斗鄙暴不近理,谬戾无识非诸子
叶适在评《荀子·荣辱》时,指出“止斗一义,莫晓其故”[3]646。依叶适之意,只有教授的弟子粗猛,才能教以止斗之法,故荀子论止斗,不可理解。事实上,粗猛的不是荀子弟子,而是那个战国乱世。荀子所处的战国末期,诸侯国之间战斗不已,人人倾轧不休,止斗之教,“训导于戈矛陵夺”,正是对症下药之举。叶适不明荀子所处时代特点,不能了解同情而妄下结论,实不足取。叶适认为,若如荀子讲论,“仁义道德安从生”?实际上荀子认为,仁义道德并非如孟子所言“仁、义、礼、智根于心”,而是化性起伪,导之以礼义道德;是一个外铄内化的过程,而非由内而外的发用;是礼义伪起、师法之化的结果,而非自发自觉就可达成。叶适在批评时还述及有子“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的论点,认为荀子属于过论。若论荣辱,止斗岂可诬妄?荀子之学为实学,为经验之学,为通本达用之学,人岂能仅学仁义道德,而不知非仁非义之事?善恶本相对而生,岂能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是不知其非?
在对《非十二子》的评判中,叶适虽然肯定了荀子“法后王”即是“法周”之意,但却认为“法周”并不可行。在叶适看来,孔子时代,周道尚能行之,而至荀子之时,周法尽灭,暴秦之势已起,于此时“法后王”,则“徒以召侮而不能为益也”。他先举《论语》中的晨门、荷、楚狂接舆以证孔子之道行不得,又举后世鲁两生、梁鸿隐而不为事类比荀子之世。果如叶适所思,则荀子之时,不法后王而又法何王?又有何人能有所作为?又当有何种作为?显然,叶适全是负面解构,而无正面建构,全是消极反对,而无积极策略,此决非儒者所应为。真正的儒者当迎难而上,知难而进,如孔子般“知其不可而为之”,虽“天下莫能容”,“不容然后见君子”[9]。叶适又言孟子排杨墨而害道,实为大诬妄。孟子自言:“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4]252百家争鸣,辩说横行,儒者因不平而发声,本为除害而为,又岂能生害?叶适所言,实不可解。按照叶适“杨墨岂能害道”的逻辑,荀子所非十二子何能害道?真实的情况是,彼时不非十二子,则属同流合污,肯定会损害正道之行。作为真正儒者的荀子,岂能无动于衷、无所作为?
叶适对子弓的认知比较有“创意”,竟然破天荒地提出了三种可能性假设:其一,子弓本无其人,是荀子之妄称;其二,怀疑子弓是仲尼之别名;其三,荀子假立名字以自况。此三种假设,可依次称之为子弓为妄称说、仲尼之别名说与荀子以自况说。三说新则新矣,实皆为无稽之谈。荀子作为一经验主义者,不喜造作假名,亦无假托之寓言,故所言皆信而有征,《荀子》一书所言人物,亦大多可考。在事关重大且严肃的学术文章《非相》《非十二子》和《儒效》中,荀子岂会列子弓虚假之名与孔子并列?孔子又何尝有子弓这一别名?之所以子弓无立言行事之考,是资料散失、本人名声不显等造成的,而不能由此得出世无此人的结论。故叶适对子弓的推断,皆为妄自揣度的无根之谈。如今学界关于子弓是仲弓、馯臂子弓的讨论还在继续,但叶适从根本上否定了此人存在的真实性,确非从事学术研究当有之态度。
四、管仲九合未可轻,儒效夸毗君道非
叶适在对《仲尼》篇的批评中,对于“言羞称乎五霸”之事,引证《孟子》中曾西不屑与管仲同比之言,认可了儒家“羞称”之事的真实性,并认为这对于初学的童子成长立志有所助益。但其否认孟子本人会与管仲相比较,认为孟子作为“大人”,决不会如此幼稚地与管仲论长道短。叶适从功利主义的视角出发,引证孔子之言,嘉许管仲九合之功。在评价管仲的态度上,叶适对于荀子所言“羞称”给予了实事求是的批评,但其并未从全幅思想的角度去审视荀子对管仲的态度,因此又有偏颇。总体来看,荀子王霸论所秉持的固然是王道优于霸道的观点,不过其对霸道并不排斥,甚至有些认可或者企盼,如荀子将国家分为王、霸、安存、危殆、灭亡五等,霸虽居于王下,但排名第二,地位并不低。
荀子对管仲的真实态度是“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10]106,是“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虽非王道,但其是“为政者”,虽属霸道,但是“为政者强”[10]152。“齐之管仲,晋之咎犯,楚之孙叔敖,可谓功臣矣。”[10]244管仲属“圣臣”下一等,是功臣。荀子又引用孔子言论,认为“管仲之为人,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10]484,在功与智方面大有成就,在仁与义上则有所亏欠,甚至居于功用之臣晏婴与惠人子产之上。由此可见,荀子对管仲的评价极高,并未违背孔子对管仲“如其仁,如其仁”的总体评价。
在对管仲的评价问题上,叶适与荀子实质上并无太大分歧,都将其定位为“霸”的级别:
王政之坏久矣,其始出于管仲。管仲非好变先王之法也,以诸侯之资而欲为天子,无辅周之义而欲收天下之功,则其势不得不变先王之法而自为。然而礼义廉耻足以维其国家,出令顺于民心,而信之所在不以利易,是亦何以异于先王之意者!惟其取必于民而不取必于身,求详于法而不求详于道,以利为实,以义为名,人主之行虽若桀、纣,操得其要而伯王可致。[5]705
在叶适眼里,管仲是在王政大坏之后才变先王之法,是不得已而为之,其辅佐的是诸侯,具有行霸道之资,其施政方法简单易操作,注重功利,借托仁义,即使是桀、纣之主,在其辅佐下也可以达到“霸”的层级。若硬要分辨荀子与叶适对管仲评价的区别,那就是叶适不吝言辞,更加热情地讴歌管仲罢了。
而当荀子赞美大儒之效时,叶适却笔锋一转,认为属于“夸毗飞动之辞”,完全忘记了自己对管仲的夸赞。当然,荀子决非谄谀取媚大儒,而是有其真知灼见。叶适从周公、孔子成就事业与道德的全过程立意,认为长路漫漫,相当艰难。众所周知,周公、孔子以一生的努力成就德业,当然绝非易事。而荀子出于游说、答对秦昭王之需要,并未强调其过程之“难”,而突出其成果之“效”,完全在情理之中。成圣成贤,皆非易事,荀子岂能不知?荀子从周公、孔子德业的效果证明儒者决非无用,其有改变社会之实效,正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10]120。叶适则指出,后世学者将儒者之效引以自神,将周公、孔子代入自身以证己之所能,纯属狂惑之举。此说可能是叶适出于点中当时儒者只讲心性、不重践履的弊病之目的,而不仅仅是评论荀子,荀子算是再次代时人受过了。
在《君道》篇中,叶适批评荀子所言为战国之事,而非帝王之治。叶适将“事”与“治”区分开来,固然有其道理。其所谓“事”,指历史上他人之史事;其所谓“治”,指自治,即帝王用己说、凭己智成就治世之局面。显然,叶适是以政治实效来检验荀子学说,认为其所论皆为“事”,“荀卿论治,多举已然之迹,无自致之方,可观而不可即也”[3]648。叶适之批评,肯定了荀子的道德诚意,而批评了其实践功效不足以支撑、证成其理论之宏规。此虽符合历史事实,但正如《荀子·尧问》篇末为荀子鸣不平之后学所言,“方术不用,为人所疑”,“不得为政,功安能成”[10]536。既然荀子因时代限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其政治学说未得到充分施展,如何能映显实效?如何能完成理论与实践的合一?
荀子论治倚重卿相辅佐,认为卿相为“人主之基杖”,叶适对此颇有微辞。他认为,君主当有其自主、自治之权力与能力,而不可倚重臣下,否则“用人之道狭矣”,最终会失掉在政治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叶适所处时代,天下一统,政治决断权隶属于皇帝一人,故其对卿相共享专制权力有所顾虑。而荀子所处的战国后期,周天子权威扫地自不必言,就连一众诸侯国君的权力也被分化,而集中于卿大夫之手,故其时的权力分配有独特的背景与考量。因此,在《荀子》中可以看到荀卿子说齐相,有对齐国“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众庶百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10]290的时政评价,又有与应侯范雎关于秦“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以及“无儒”[10]296-297长短的对答。
五、以人灭天自是偏,物道关系同诸子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对重要关系。荀子《天论》高扬客观之天,区别了天人之职分,纠正了既往对天人观的扭曲认知,打击了宗教神学,彰显了人在天人关系上的主动性与创造力。然而,就是荀子这一科学、客观的天论,仍然没有逃过叶适过分挑剔的眼光,有色眼镜看到的必然是荒谬变形的景色。叶适对荀子天论的批判便体现了这一点。
叶适否定了荀子“天行有常”的观点,认为“尧之时则治,是为尧而存也;桀之时则乱,是为桀而亡也”[3]649。此处其严重误解了荀子原意。荀子认为,天道运行及其规律自有其常道,不会因为尧、桀等帝王个人因素而存亡。而叶适则单纯讨论“治”,认为治乱由人,尧治桀乱,皆由其人,而不在于天,其特别注重在实际政治统治中帝王个人能力对政局的把控。可见,叶适的讨论已经从天人关系转向了政治统治的范畴,叶适与荀子所论天人,分别隶属于不同论域:一指向政治统治中的帝王,属政治哲学;一指向天人关系中的天道,属天人关系。如果从天与人的关系来看,荀子谈的是“天”,而叶适谈的却是“人”。
至于荀子所论“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中的吉凶治乱之“应”是人之应,即人应之以治或乱,并非叶适所指责的神秘且不可思议的“无常”之应。易言之,人若顺遂规律治之,则吉;反之,则凶。叶适批评荀子以人灭天,更是未当。荀子之天为自然之天,是不知其然而然的存在。天的存在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在这一点上,荀子既不以人灭天,也不以天灭人,而是在天人之间保持了适当的张力,维系着双方存在的合理性限度。
叶适也未能恰当理解荀子的“圣人不求知天”。他居然认为,清天君、正天官、养天情与不求知天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实际上,此矛盾在荀子思想体系中压根不存在。荀子认为,圣人是治世的主体而非知天的主体,所以“圣人不求知天”。荀子“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10]304一语清楚地说明了,守天之主体为官人,而守道的主体是“自为”者,即圣人。圣人志于天、地、四时、阴阳,知其所当为者为期、息、事、治四者,也就是说知其然而不求知其所以然。“圣人不求知天”主要从不务求知其所以然的角度而言。
荀子主张“天地官而万物役”,提倡人的主观能动性,却被叶适以古圣人未尝自大到如此地步而否定之。“物畜而制之”“制天命而用之”则因尧、文王从未如此而被叶适批评之。叶适抬出古圣王的只言片语来否定荀子,实属无风起浪式的批评。人役使天地万物,是因为“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10]173,此既与荀子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最为天下贵”[10]162的观点一致,也与现实中人利用天地万物的客观事实相符。
叶适以孔子之言“惟天为大,惟尧则之”[3]650来否定荀子“以人灭天”,并发出了“人能自为而不听于天,可乎”的质问。这是叶适对荀子天人关系的误判。荀子指出,“君子大心则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其中的“天而道”,当依王念孙,依《韩诗外传》作“敬天而道”,与“畏义而节”对文[10]42。荀子的“敬天”观念自然不是“灭天”一语就能解释,荀子也并未有“以人灭天”之想,而只是将天人区割,认为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天人关系中对天的过分依赖,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思想后果,如发展出了宗教神秘之天,给人类生存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困扰。荀子虽然赞扬天人关系中人的价值,却并未否定天的作用,反而是拨正了天人二者的关系。天人关系并非永恒不变的绝对关系,而是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程度不断调适,是在天人进化中不断变动着的相对关系。
可见,叶适对荀子天人关系方面的批评皆不契合荀子本意,属不相干的自说自话。荀子天人观立意于天人相分、天人不与,将天道与人事区分为两个领域,天道不预人事,厘正了传统的天人关系,将人从天的笼罩和统率下解放出来,是人文主义的一大进步,达到了先秦时期天人观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
在万物与道的关系上,叶适评价荀子为“吾未见其能异于诸子也”[3]650。荀子的物道关系观与道家有些类似,认为物为道之偏,道为物之全。而从荀子思想看来,他更加重视的并非物道关系,而是人与人、人与群的关系。故荀子从“中”与“偏”的关系角度,论列评价诸子。荀子追求中道,这在对诸子的批判中亦有体现,他指出“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埶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10]380。荀子在用与文、欲与得、法与贤、埶与知、辞与实、天与人之间尽量保持着类似“中”的动态平衡。换言之,荀子的评价是以先王之道为基准,不断寻求着不偏不倚的中道,“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10]121-122。荀子所谓中道,是礼义之“中”,是“仁知之极”,是仁智合一之“中”,是不偏不倚且不易之“中”。
另,在对荀子《正论》的批判中,叶适又提出,荀子视天子“居如大神,动如天帝”与秦始皇“朕”相类比,实为胡乱比附。这亦属于不相干的议论。一则,这是荀子在驳斥世俗之说“尧、舜禅让”时所言,故大神、天帝所指代者为尧、舜;二则,这里尧、舜是大神与天帝并非实指,而是如大神、如天帝,是在以比喻意义使用此二词;三则,在荀子思想体系中,天帝、大神有其特殊化的含义,早已失去了神秘化、神圣化的意义。
六、解蔽治心亦非是,论礼正名不关事
叶适认为:“荀卿议论之要有三,曰解蔽、正名、性恶而已。”[3]652此评仅将解蔽、正名、性恶三大思想要点拈出,而忽视了荀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两大关节:学与礼。荀子既是“学宗”,又是“礼宗”,是先秦论学、论礼之集大成者。
由于大多数人“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10]374,当百家争鸣之时,各守其说,便不能不有蔽。之所以暗于大理,内在心术与外在万物之差异构成了两大主因,即所谓“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10]376。蔽主要是心术所致,故荀子多从此方面展开论述。叶适不知,见其论心即驳之。其举舜、箕子古圣先贤只言片语,证明圣人不止于治心,以反对荀子论心、治心之说,实在奇怪。叶适属事功派,并不太强调“心”,而注重“事”,思想大端与心学内圣之学相抵牾。叶适有反对宋代心学的思想倾向,在此,他更多地出于门户之见的“思想迁移”,“迁怒”于荀子,早已溢出批荀之事。
《礼论》是论礼名篇,而叶适仅盯着此篇中的“礼者,养也”这一说法不放,且武断地认为,“礼者,养也”与“礼者,欲也”意义相同。需要讨论的是,荀子论礼,以礼养耳、目、口、鼻、体,与“制礼以为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礼固然可以养口体,但决不意味着礼仅有“养”之一面。制礼的目的绝不是止于“养”之一端而已。
礼具有多面性,荀子在《礼论》中既讲“礼者,养也”,也讲“既得其养,又好其别”[10]338。叶适只见其“养”,未见其“别”,忽视了“礼别异”这一重要功能。《礼论》篇中荀子还讲“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10]348,又讲“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10]353,礼之多面性一览无余,叶适不察,反诬为“礼者,欲也”,实在可怪。而通观《荀子》,所论礼更为繁富。兹仅罗列其要者如下:
礼者,所以正身也。(《修身》)
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大略》)
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人伦尽矣。(《儒效》)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富国》)
程者,物之准也,礼者,节之准也;程以立数,礼以定伦;德以叙位,能以授官。(《致士》)
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议兵》)由上可见,荀子之礼,具有修身、为政、定伦等多方位的功用。即使从“欲”这一角度言之,荀子之礼亦统摄了礼以养欲与礼以制欲两大方面。后世宋儒天理人欲之说部分地贬抑人欲,所以同时代的叶适对荀子养欲之说亦不能同情地理解,仅从“养”的角度言之,且进一步以“欲”释“礼”,实际上对荀子之礼形成了误解。
叶适继续以先扬后抑、名扬实抑的手法对荀子正名学说进行评论,先是认为“其于名可以为精矣”,承认其有殊异色彩;又以“正事不正名”,名事一体为论据,贬评荀子法后王之说。叶适认为,荀子法后王是“舍前而取后,是名因人而废兴也”[3]653,显然曲解了荀子之意。荀子认为,先王与后王相比,自然具有时间上的先在性,但就时空距离而言,先王离时人较远,其事不可详知尽知,而后王之于先王虽有所损益、变通,但本质上是同条共贯之道。同时,由于后王之迹灿然于目前,我们反而可以法之有据、法之有物、法之可行。
叶适评荀子正名,亦引孔子正名之说。孔子正名之说借与子路论卫政之事阐发。叶适认为,孔子正名重视名以正事,名正而事从,值得后人效仿。此说固然深得孔子之旨。对于荀子正名之说,叶适却视之为战国群谈,仅是辩说之言,未能行之于事、得之于实,因此和孔子正名不可同日而语。此论有失偏颇。名与事本为一体,名为事之名,事为名之事,二者岂可割裂?只是荀子受时代影响而未能将正名学说大展于政事,此非荀子之过。
进而言之,战国百家争鸣,亦不可被简单地视为“无类之言”,“姑为戏以玩一世”[3]653。如此,则将争鸣百家于乱世中提出的有价值之论当作一场话说,将中国学术黄金时代的价值全盘抹杀,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严重低估了诸子百家的学术诚意与政治立意,泯灭了政治学说的时代价值与历史影响。至于将荀子正名之说置于否定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而否定之,并隐讳地将六国灭亡、暴秦有作、焚经坑儒怪罪于荀子,更是一大历史诬枉。中国历史大势浩浩汤汤,岂是一荀子所能救者?岂是十二子所能救欤?荀子与十二子只是各尽其本分而已。荀子正名学说,岂能为后来之历史背锅?
七、善恶论性何可非,世易时移费思量
叶适通过对比的方式来评价子思与荀子,有将思、孟与荀子同观的意味,如他说:“子思言理闳大,而分限不可名;荀卿言事虽张皇,而节目犹可见也。”[3]648叶适认为,子思之言理闳大,与荀子《非十二子》中所批评的子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10]93之义略同。
对于荀子的性恶论,叶适着墨不多,仅用较小篇幅进行了简单而直接的评论。他将孟子性善与荀子性恶并论同观,“皆切物理,皆关世教,未易重轻也”[3]653,肯定了二者的价值,并认为不可以轻重论,这自然是公允之论。表面看去,叶适对荀子的性恶之说进行了同情地理解,但他又指出:“则是圣人者,其性亦未尝善欤?”[3]653可见,其所理解的荀子性恶,并非荀子所论性恶。荀子性恶之说,非性本恶,而是认为,性若顺从自然条理、欲望流向,易归于恶而已。圣人之性与常人之性本无差别,皆是如此。荀子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可以通过师法礼义,化性起伪,修正自我,不断进步,而成就圣贤人格。圣人之性皆为化性起伪之后的纯然之伪性,与其初生时之性已然不同。
叶适又将孟、荀观点与伊尹“习与性成”和孔子“性近习远”之说进行了对比,认为古人不以善恶论性,而孟、荀以善恶论性,则去古人远矣。荀子以生之所以然者为性,重视后天的习、伪、积等对人性的改塑作用,此与孔子不殊。叶适没有看到,人性论有其自然的、逻辑的发展历程,世殊时异,古人论性与时人论性自然会有所差异,不可一切以古人为标准,抹杀后世论性的价值。
叶适对荀子的批判,确实是一值得反思的学术现象。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被宋代反荀思潮裹挟的事功派代表叶适,亦不能免于学术流俗,竟然在批判荀子这一点与程朱理学之儒达成了合意、实现了合流。与其他宋儒大多专批荀子“性恶”不同,叶适在较为系统地研读了《荀子》文本后,对荀子进行了全面系统、不遗余力的批判,然而其批判既没有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也并非以同情理解为基础,其以充满贬抑与歧视的挑剔目光审视荀子,使其对荀子的批判达到了吹毛求疵、歪曲误解的程度。这既对荀子思想不公,使荀子的历史地位雪上加霜,又对中国学术发展健康不利。叶适的荀子批判也给当今学人提供了一面镜子,若置学术的客观性于不顾,缺少独立思考,缺乏了解同情,一味任由学术观点顺着时代思潮漂流,则会离真理愈来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