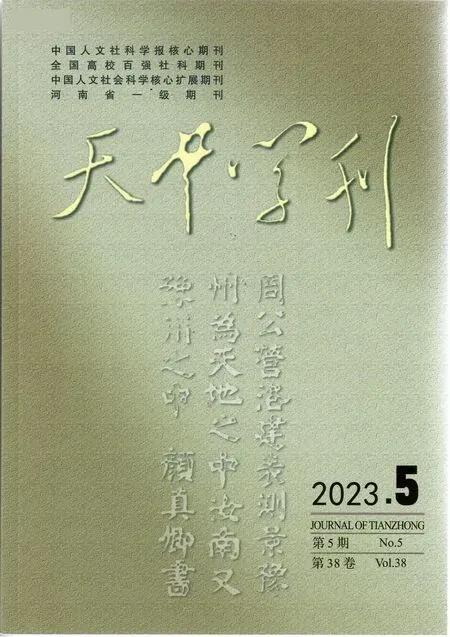由《松漠纪闻》看洪皓的思想与学术进退
刘 师 健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410003)
建炎三年(1129),洪皓(1088—1155)奉宋高宗之命出使金国,却被羁留10 余年,其间坚贞不屈,艰苦备尝,终于绍兴十二年(1142)被释归宋,授徽猷阁直学士。《松漠纪闻》乃其为记金国杂事所著,因篇幅短小、叙事简略,向来少被关注。而涉及该书的论著,多局限于其史学价值的考察①,或致力于其文本内容的考述②。其实,《松漠纪闻》不仅在写作上有着鲜明的史鉴特色,而且书中饱含了作者的政治见解。本文拟在探究《松漠纪闻》写作特色的基础上,梳理洪皓由历史进入理学纵深的学术思想体系,进而揭橥其别样的在世方式及其思想在当时理学弥漫境况下的特色。
一、《松漠纪闻》的成书过程与史鉴的写作自觉
《松漠纪闻》系洪皓卒后,绍兴二十六年(1156)由其长子洪适(1117—1184)刻于歙越③(今安徽省歙县),由于其羁留地冷山在唐代松漠都督府以北,故名。全书分正续两卷,其中正卷记31 事,续卷记27 事。乾道九年(1173),洪皓次子洪遵(1120—1174)补增补遗21 事④,重刻于建业(今南京市),至此全书共记79 事,约14000 余字,详细介绍了金国的山川地理、历史沿革、科举制度及社会风尚等。南宋目录学家陈振孙(1179—1261)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如此著录该书:“《松漠纪闻》二卷,徽猷阁直学士鄱阳洪皓光弼撰。皓奉使留敌中,录所闻杂事。”[1]语言虽然简略,但从“奉使留敌中”一句可知,对于南宋读者而言,《松漠纪闻》的价值就在于其所叙录的金国生活内容。《松漠纪闻》对宋高宗一朝政治的记录与描述,表现出了强烈的以史为鉴的写作自觉,但也注定了其成书过程的复杂曲折。
洪适在跋记《题松漠纪闻》中详细记录了该书曲折复杂的成书过程:
先君衔使十五年,深阸穷漠,耳目所接,随笔纂录。闻孟公庾发箧汴都,危变归计,创艾而火其书,秃节来归。因语言得罪柄臣,诸子佩三缄之戒,循陔侍膝,不敢以北方事置齿牙间。及南徙炎荒,视膳余日,稍亦谈及远事。凡不涉今日强弱利害者,因操牍记其一二。未几复有私史之禁,先君亦枕末疾,遂废不录。及柄臣盖棺,弛语言之律,而先君已赍恨泉下。鸠拾残稿,仅得数十事,反袂拭面,著为一编。[2]
从材料中可知,《松漠纪闻》在洪皓拘留金国期间即已写成,只是作者为了顺利归宋,被迫焚毁了书稿。归国后,又为秦桧所嫉,接连被贬饶州、江州、濠州,因此“不敢以北方事置齿牙间”,直到被安置英州(今广东英德市东),洪皓方凭自己博闻强记,在不曾涉及今日强弱利害关系的前提下,“操牍记其一二”。然而,世事难料,后又遭遇“私史之禁”,加上身患重疾,被迫搁笔。据《宋史·高宗本纪》载,十四年四月“丁亥,初禁野史”[3]560,可知《松漠纪闻》的重新写作时间应为绍兴十四年(1144)前,当是洪皓安置英州的前后一二年间。
《松漠纪闻》成书过程的曲折艰难,自有时局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与其记录内容紧密相关,由跋记可知,写作虽为“耳目所接,随笔纂录”,但所记内容关涉政治、军事、文化诸多方面,体现着鲜明的为抗金大业搜集情报的目的。归国后,面对残酷的政治环境,洪皓在写作中虽“不涉今日强弱利害”,但由于其有着写作一部私家史书留给世人的强烈愿望,希望该书“可广史氏之异闻”,因此,他在书中既记载了女真人羞见的先祖部落遗风与女真贵族的残暴,也肯定了女真人为反抗辽国压迫而起兵的义举以及金国大臣爱民护教的德行,全书本着善恶必书、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依据事实,恰如其分地褒贬史事人物,呈现出比肩正统史书的庄重样貌。诚如《四库全书总目》对该书的评价:“皓所居冷山,去金上京会宁府才百里。又尝为陈王延教其子,故于金事言之颇详……盖以其身在金庭,故所纪虽真赝相参,究非凿空妄说者比也。”[4]
《松漠纪闻》偏重于对金国宏观历史的叙述,其开篇即奠定了这一宏大叙事的基调:“女真即古肃慎国也,东汉谓之挹娄,元魏谓之勿吉,隋唐谓之靺鞨。”[5]115实际上,从洪皓写作的现实处境来看,以宏大叙事的方式隐藏自我、淡化个人色彩,也能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书中三处对洪皓流放之地冷山的记叙就体现着这一写作特色:“宁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5]122“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国所都二百余里,皆不毛之地。”[5]129“长白山在冷山东南千余里,盖白衣观音所居。”[5]132以上对冷山的描写客观冷静,虽凸显了其地理位置的偏僻、自然环境的苦寒,但读者从中很难捕捉到洪皓曾在此生活的痕迹,因此,也不会为冷山停留注目。
客观宏大的叙事基调也使得全书很难寻觅到作者洪皓的身影。书中明确表示洪皓亲历之事共有7 处,就叙事角度而言,可分个人视角与宏观视角两种。其中,从个人角度叙述的有:“嗢热者,国最小”一事:“族多李姓,予顷与其千户李靖相知,靖二子亦习进士举,其侄女嫁为悟室子妇。”[5]119“渤海国去燕京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里”一事:“有赵崇德者,为燕都运……竹林乃四明人,赵与予相识颇久。”[5]120“合董之役”一事:“予过河阴县,令以病解,独簿出迎。”[5]123“西瓜形如匾蒲而圆,色极青翠,经岁则变黄”一事:“予携以归,今禁圃、乡囿皆有。”[5]132从以上记录可知,洪皓在流放期间与不少金国上层官员都有着密切联系,诸如千户李靖、渤海人赵崇德等人,也正是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洪皓获得了诸多关于金国军事动向以及女真、契丹民族历史的情报和资料,为《松漠纪闻》的撰写积累了素材。
此外,书中部分宏观叙事中“我”的显现,有着特意强调的意味,流露出洪皓强烈的史鉴意识。如在叙及契丹为巩固对女真的统治,“自宾州混同江北八十余里建寨以守”的情形时写道:“予尝自宾州涉江过其寨,守御已废,所存者数十家耳。”[5]115看似不经意的一笔,既表达出了面对时事变迁时的沉重心情,又向南宋统治者说明女真也曾臣服于契丹,只要把握时机、出奇制胜,战胜女真不无可能。辽金战争期间,金廷令山西、河北筹运军粮,洪皓过河阴(今河南荥阳)时,亲见县令因“馈饷失期”,“被挞柳条百,惭不敢出”[5]123。这里洪皓通过第一视角向读者描述了北宋降臣在金国的悲惨处境,表明俯首称臣只能苟安一时,惟有坚持抵抗才能保全尊严。书中还提及金人对“赦”的慎重:“北人重赦,无郊霈。予衔命十五年,才见两赦:一为余都姑叛,一为皇子生。”[5]128这里对“赦”次数之少的强调,似乎在为自己羁留金国多年寻找一个合乎情理的原因,以消除南宋朝廷对其忠心的疑虑。
洪皓在《松漠纪闻》中,一边仔细审视着女真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将其种种面相真实记录在案;一边又刻意地疏离其民众,在心理上与他们保持着极为遥远的距离,刺探敌情的自觉深藏在写作之中,“以史为鉴”的写作初衷也于记录中若隐若现。
二、《松漠纪闻》曲笔书写的写作用意
《松漠纪闻》虽着眼于社会历史大事的记录,但宋金和战与徽、钦二帝被俘绝对是洪皓要避开的话题,书中也确实未对此做明显记录,惟有念念在心,时刻不忘,将其深埋心底,隐约寄于笔触。由此,在南宋朝廷苟且偷安、投降派甚嚣尘上的状况下,洪皓只能以曲笔方式隐藏自我,秉着以史为鉴的写作自觉,记录相关重要信息。
(一)详述金国历史与军政现实,复兴汉人精神与华夏骨气
《松漠纪闻》首先记述了女真人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历程:“女真,即古肃慎国也。东汉谓之挹娄,元魏谓之勿吉,隋唐谓之靺鞨。”随后又记录了隋开皇年间靺鞨使者献舞一事,“开皇中,遣使贡献,文帝因宴劳之。使者及其徒起舞于前,曲折皆为战斗之状。上谓侍臣曰:‘天地间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这里借隋文帝之口,表明女真前身靺鞨即为好战民族。紧接着,作者继续叙述了唐太宗征讨高丽时坑杀三千靺鞨兵的史实,“唐太宗征高丽,靺鞨佐之,战甚力。驻跸之败,高延寿、高惠真以众及靺鞨兵十余万来降,太宗悉纵之,独坑靺鞨三千人”。言外之意,对于好战敌人,只有积极备战,给其以狠狠地打击,方有可能实现“开元中,其酋来朝……讫唐世,朝献不绝”的长治久安局面[5]115。这里也在暗示南宋君臣,一味卑躬屈膝、不战而退、谋求和议,是难以满足女真征战欲望的。
关于女真崛起的历史,《松漠纪闻》更多记述了契丹统治者对女真人的残酷压榨和非人凌辱,深刻揭示了女真叛辽是民族压迫下的官逼民反。如“大辽盛时,银牌天使至女真,每夕必欲荐枕者。其国旧轮中下户作止宿处,以未出适女待之。后求海东青,使者络绎,恃大国使命,惟择美好妇人,不问其有夫及阀阅高者,女真浸忿,遂叛”[5]121。还有契丹统治者对女真经济剥削的记录:“宁江州去冷山百七里,地苦寒,多草木……每春冰始伴,辽主必至其地,凿冰钓鱼,放弋为乐,女真率来献方物,若貂鼠之属,各以所产量轻重而打博,谓之打女真。后多强取,女真始怨。暨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驯致亡国。”[5]122-123残酷的剥削激起了女真人强烈的怨恨,也是其起兵反抗的重要原因。这些记录虽语言平实,却言深旨远,深刻表明契丹统治者的凌辱与压榨,是导致女真人反辽灭辽的重要原因。
《松漠纪闻》还记录了双方战争中的情况。如起兵之初,“女真有戎器而无甲,辽之近亲有以众叛,间入其境,上为女真一酋说而擒之,得甲首五百……既起师,才有千骑,用其五百甲,攻破宁江州。辽众五万,御之不胜,复倍遣之,亦折北,遂益至二十万”。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女真内部虽出现了“以众寡不敌”而“谋降”的情况,但阿骨打虚心接受粘罕、悟室、娄宿的建议,攻坚克难,迎难而战,“以死据之”,领兵三千,“连败辽师”,从而“器甲益备,与战复克”。与女真的士气高昂、连战连捷相比,辽方则是军心涣散、众叛亲离、不堪一击。“天祚乃发蕃汉五十万亲征,大将余都姑谋废之,立其庶长子赵王。谋泄,以前军十万降,辽军大震。天祚怒国人叛己,命汉儿遇契丹则杀之。初,辽制,契丹人杀汉儿者,皆不加刑,至是摅其宿愤,见者必死,国中骇乱,皆莫为用。女真乘胜入黄龙府五十余州,浸逼中京。”[5]121-122至此,辽国大势已去,不久遂为金灭。文字虽然简单,但将两个民族与政权的兴亡交替过程及其内在原因表达得非常清楚明白。
女真在契丹统治之下虽饱受凌辱和压榨,然而,在其夺取政权后,对治下百姓却极为残暴,这在《松漠纪闻》中多有记载。公元926 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国,为了安抚与治理渤海遗民,对渤海遗民采取了比较温和的统治政策,“徙其各帐千余户于燕,给以田畴,捐其赋入,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有战则用为前驱”。后来,“金人虑其难制,频年转戍山东,每徙不过数百家”,最后则“尽驱以行”[5]119-120。又如黄头女真“其人憨朴勇鹜,不能别死生,金人每出战,皆被以重札,令前驱,谓之硬军。后役之益苛,廪给既少,遇卤掠所得,复夺之,不胜忿。天会十一年(1133)遂叛”[5]120。对待辽国降人,金国统治者十分歧视。如契丹贵族大实林牙降金后,因与粘罕双陆发生争执,导致粘罕对其心生杀机。“大实惧,及既归帐,即弃其妻,携五子宵遁。”天亮后粘罕不见大实,召其妻“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贱者。妻不肯屈,强之,极口嫚骂,遂射杀之”[5]123。文中“大实”,即为《辽史》所记“耶律大石”,又称“大石林牙”,天庆五年(1115)进士,先在朝中任翰林应奉、翰林承旨,后外授,先后任泰、祥二州刺史、辽兴军节度使;延庆元年(1132),在叶密立称帝,后向西推进,迁都八剌沙衮,成为威震中亚的强大帝国。洪皓从民族压迫的角度,揭示了耶律大石降而复叛的原因,丰富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内容。
《松漠纪闻》亦叙及金朝的职官制度及其实际运作。依据金制,御史中丞作为御史台副长官,协助御史大夫行使监察职责⑤,但在制度的实际运行中,中丞却“唯掌讼谍”,对朝廷内外大小官员的丑恶行径视若无睹、置若罔闻,导致“官吏赃秽,略无所惮”[5]140。金朝转运使虽有监察地方的职责,却从不检举奸恶,使得地方官吏贪赃枉法,民终不堪其苦。书中即记载了一桩吏治腐败导致的冤案:在金国,译语官掌控着重要的话语权,以致“上下重轻,皆出其手”,经常收受贿赂、颠倒黑白、无恶不作,由此“得以舞文招贿,三二年皆致富”,民众对其苦不堪言。一位留守燕京的译语官,名叫银珠,战功显赫,家室显贵,但昏聩无能,不谙民法,且与汉族百姓语言不通。数十户人家欠一富僧六七万吊钱不还,富僧因此告官,欠钱者相继贿赂银珠,以求暂缓审判,银珠为勒索钱财,甚至为欠钱者献计:“汝辈所负不赀,今虽稍迁延,终不能免,苟能厚谢我,为汝致其死。”富僧呈递讼状后,本想着静候结果,却不料银珠将状纸换成富僧因“久旱不雨”,“欲焚身动天,以苏百姓”的请愿书,并随即在请愿书上签字同意,富僧还未明白怎么回事,即被数十个欠债者拥上早已准备好的柴草堆,“竟以焚死”[5]127。金国时政之混乱可见一斑。
(二)详录金国落后风俗与制度,激活宋人文化自信
《松漠纪闻》在记载女真风俗时,突出了其“强效华风”的表征[6]。“女真旧绝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纪年,问之,则曰我见草青几度矣。盖以草一青为一岁也。自兴兵以后,浸染华风”[5]125。女真政权建立初期,保留着浓郁的氏族部落制的遗风,“法制简易,无轻重贵贱之别”[7],甚至有乖风化之处:“胡俗旧无仪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虽杀鸡,亦召其君同食,炙股烹脯,以余肉和藄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吴乞买称帝亦循故态,今主方革之。”[5]127书中还记叙了金粘罕保全曲阜孔庙孔墓的故事:“初,汉儿至曲阜,方发宣圣陵,粘罕闻之,问高庆绪人曰:‘孔子何人?’对曰:‘古之大圣人。’曰:‘大圣人墓岂可发?’皆杀之,故阙里得全。”[5]131借金国大臣尊重儒学圣人,说明金国对汉文化的倾慕和模仿,从而激发宋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在政治上,金国也积极效法中原王朝的多项制度。金熙宗时,数兴大狱,通过铲除宗室元勋重臣,促成了政权从宗室共治到皇权独尊的转变。天眷元年(1138),颁行“天眷新制”,废除勃极烈制⑥,开始全面采用汉官制。皇统三年(1143),颁行《皇统新律》,“大氐依仿中朝法律”[5]127。书中在记叙《皇统新律》的具体施行时,强调该新律的推行并未取得理想效果,执法过程仍是“率皆自便”[5]127的状态,可见,金人在“中朝制度”外表下仍是野蛮贪婪的残暴内核。作为家长的父亲视妻妾、子女如奴婢,甚至有生杀鬻卖之权,《松漠纪闻》言及太祖阿骨打次室所生之诸子云:“自固以下,皆为奴婢。”[5]117一般女真人家也是如此,甚至“殴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5]127-128,丈夫徒手殴打妻妾致死,竟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可见金国妇女地位之低下。金朝自太宗天会元年(1123)始即推行科举,至天会十三年(1135),熙宗即位后,又大刀阔斧改革科举制度,促进了金朝对汉文化的接纳吸收。《松漠纪闻》载:“金人科举,先于诸州分县赴试,诗、赋者兼论,作一日;经义者兼论策,作三日,号为乡试,悉以本县令为试官。”[5]117此处记载的科举方式即为熙宗改革后的制度,在考试内容与制度方面均承袭唐、宋。在洪皓看来,金人虽学习唐宋之制,但学而不精,甚至混入许多部落遗风,形成了一套胡汉混杂的体系。
作为羁留金国的南宋使臣,政治对于洪皓而言是一个敏感话题。他的身份、处境注定其在写作时要避开一些尖锐问题,但他的职责与使命又驱使他为宋朝搜集相关情报。事实上,洪皓曾向徽钦二帝传送过南宋的消息,还多次搜集金人政治、军事情报,并暗中传递给南宋朝廷⑦。在这种现实与责任相矛盾的情况下,洪皓以曲笔方式,记录金国种种实情,旨在告诉他的同胞,令他们畏惧的金人内部其实也存在着激烈的权力斗争,各种势力相互倾轧,政治争斗异常残酷,朝政已是危机四伏,只要抓住有利时机发起攻击,并非没有克敌制胜的可能,洪皓的忠贞之心在这朴实隐晦的记录中昭昭可见。可以说,《松漠纪闻》虽然没有明言写作目的,但其从历史视角探讨宋金关系、记录金国内部种种现状,已经明确表达了作者的政治见解。
三、士人的别样在世方式
《松漠纪闻》在直笔与曲笔的交替中,呈现出含意深微而又致用的史学特征,也体现了洪皓自成一体的思想格调与士人心态。在学术极为繁荣的宋代,洪皓在思想上建树有限,并没有创立独立的学派,也不曾精深开拓某一学术传统,但如果就余英时所谓的“历史世界”而言,其却有着独特的展拓。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中指出,“历史世界”并不仅仅局限于朱熹的个人生活史,而是一个联系着更为广阔的时代社会,包括朱熹生活所处的政治世界,以及与其紧密关联着的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外在表征着宋代士人群体的政治关切、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8]。在此一层面上,洪皓义无反顾地投身政治,滞金之时亦不忘贯彻自己的历史主张,可以说,相比一般宋学家,洪皓的历史世界是一个深入有所作为的实践领域,是一个更为开阔、具体的历史世界。
(一)“以道进退”与士人主体意识
洪皓“少有奇节,慷慨有经略四方志”[3]11557,始终执着地追求“致君行道”,坚持自身的政治理想与见解,不以功名利禄为转移,视“忠孝节义”为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应当遵循的重要道德准则,认为明君应是“道”的代表,君只有自守尽礼,臣才能竭忠辅佐,具有十分强烈的“以道进退”的士人主体意识。
建炎三年(1129),“苗刘兵变”刚被平息,杭州时局未稳,宋高宗打算由扬州迁往建康。当时,洪皓为朝散郎,官秀州司录,听闻此事后,不顾自己位卑言轻,上《谏移跸疏》:“言今内难甫平,外敌方炽,若轻至建康,恐金人乘虚侵轶,宜遣近臣先往经营,庶事告办,鸣銮未晚也。”[9]474张浚对其胆识钦佩有加,将其举荐给高宗。在获得高宗的接见时,洪皓极言:“天道好还,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晋训楚也。”[3]11557历史上,秦将白起趁楚国边备废弛之机,积极防御,取得了攻楚的战略主动。这里,洪皓借邲、郢之战,劝慰高宗积极备战,选择合适时机攻打金国,也能战胜金兵。高宗听后大悦,赞其“议论纵横,熟于史传,有专对之才”[9]474,立即擢升其为“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为大金通问使”[3]11558。但其后,洪皓却以“母老父丧”予以推脱。关于洪皓拒绝升迁的原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线索:“起复朝散郎洪皓为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为大金通问使……而以武功郎龚为右武大夫,假明州观察使副之。上谓左副元帅书:‘愿去尊号,用正朔,比于藩臣。’上令皓与宰执议国书,皓欲有所易,颐浩⑧不乐,遂罢迁官之命。”[10]洪皓本希望高宗能卧薪尝胆,而不是“去尊号,用正朔,比于藩臣”。对于洪皓来说,这般摇尾乞怜的国书使得此次使金成为一种莫大的耻辱与讽刺,与他积极备战的思想背道而驰。然而君命难违,加之宋金形势紧迫,洪皓“告一日,归别”[9]474,在一日之内即告别家人,远赴金国。洪皓处处以时局为重,因国家危难,毅然使金,不愧为忠正之士。
洪皓留金15 年,期间虽备尝艰苦,但不惧贬谪危险,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绍兴元年(1131),完颜宗翰(1080—1137)迫其仕刘豫,洪皓毫无惧色,严词拒绝:“万里衔命,不得奉两宫南归,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愿偷生鼠狗间,愿就鼎镬无悔。”[3]11558-11559洪皓自视南宋使者,坚决不仕伪齐政权。绍兴十年(1140),面对高官俸禄诱惑,洪皓再次毅然予以拒绝:“初,皓至燕,宇文虚中已受金官,因荐皓。金主闻其名,欲以皓为翰林直学士,力辞之。皓有逃归意,乃请于参政韩昉,乞于真定或大名以自养。昉怒,始易皓官为中京副留守,再降为留司判官。趣行屡矣,皓乞不就职,昉竟不能屈。”[3]11560洪皓的南归之意,为已降宋人韩昉(1082—1149)所察,当时,韩昉出任金国宰相,欲任洪皓为翰林直学士,洪皓呈《上韩相昉辞换官书》,以为母尽孝为由,“忧极肠回,泣尽目肿,于亲有害,在义当辞”[11],其不辱使命、为国尽忠的决心一目了然。
洪皓“以道进退”主体意识的另一层面则体现在对“治道”的强调上。关于社会政治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洪皓总能切中肯綮,提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的见解。南宋时期,关于“和战”问题的讨论异常激烈,甚至逐渐由政见之争上升为人事恩怨,成为朋党之争的源头。但洪皓不曾介入其中,而是理性观察时局,冷静分析局势,审时度势,当战言战,当守言守,当和言和,一切以达成抗金胜利这一目标为中心。
作为南宋使臣,议和与探访被囚禁的徽、钦二帝是洪皓的主要职责。至南宋绍兴年间,至少在岳飞遇害的绍兴十一年(1141)之前,宋金局势实际上在逐渐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发展⑨。洪皓虽身在金国,却始终对南宋情况保持关注,多次不顾个人安危,收集情报,传回宋朝。绍兴十年(1140),他认为北伐中原的时机已到,“因谍者赵德,书机事数万言,藏故絮中,归达于帝”。其《密奏机事书》中有言:“顺昌之役,虏震惧丧魄,燕之珍器重宝悉徒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王师亟还,自失机会,今再举尚可。”[12]言明了抗金将领刘锜指挥的顺昌之战,使金军遭受了南下攻宋后的最大惨败,这一战斗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城邑防御战争。整个战争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140 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一日,历时6 天,经过三次战斗,击溃金军的前锋部队;第二阶段从六月七日至六月十二日,历时6天,刘锜率全城军民与金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决战,取得了顺昌保卫战的最后胜利。顺昌之役过后,金国统治者惊恐万分,大有放弃幽燕等地的念头。洪皓认为,这实为向金国发起进攻的良机,不宜错失。绍兴十一年(1141)冬,洪皓再次上书,并献六朝御容、徽宗御书,其在书中曰:“虏已厌兵,势不能久,异时以妇女随军,今不敢也。若和议未决,不若乘胜进击,再造犹反掌尔。”[3]11560向宋高宗描述了当时金国内部普遍厌战的情形。身处金国,洪皓虽无法完成使命,却便于收集金人情报、分析宋金双方的政治军事形势,其以超人的胆识和机警,将情报与形势分析传回南宋朝廷。
在冷山生活期间,洪皓亦时刻不忘使命,利用一切机会向金国贵族传播和平思想,其在金国尚书完颜希尹家中教书时,努力向其传播儒家“仁爱”思想、阐述弭兵道理:“悟室锐欲南侵,曰:‘孰为海大,我力可干,但不能使天地相拍尔!’皓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自古无四十年用兵不止者。’”[3]11559寥寥数语,向完颜希尹解释了金向宋连年发动战争对宋金双方均有伤害。洪皓还经常劝导希尹施行仁政、发展文化,潜移默化间影响其思想和决策。
(二)“保民而王”与基本价值目标
洪皓在政治上总体趋于保守,但在对“保民而王”主张的坚持上却表现得十分坚韧执著,他虽未曾从理论上对“民贵君轻”思想做过系统阐述,但这一思想在其价值观体系中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并贯穿其学术和政治活动始终,甚至可以说,洪皓在践行“施仁政于民”、奉行“民贵君轻”方面,达到了中国古代官德的至高境界。
宣和六年(1124),洪皓为秀州录事,“秋大水,田不没者十一”,民多失业。洪皓主动向郡守请缨,请求承担救灾重任。其先是紧急搜集秀州境内存粮,并以平价出售,但不久钱粮耗尽,情况危及,不容刻缓。此时,正好“浙东纲米过城下”,洪皓请求郡守截留以用于赈灾,郡守不可,洪皓表示“愿以一身易十万人命”,坚持截留纲米,秀州百姓因此得以度过饥荒,“前后所活者九万五千余人”,为表达对洪皓的感激,百姓称其为“洪佛子”[3]11557。羁留金国期间,洪皓更是竭力帮助靖康之变中被俘至金国的北宋王公贵族们。如赵伯璘夫妇于悟室家充当劳役,洪皓为改善他们贫困不堪的生活,拿出仅有钱财给予救济。大将刘光世(1089—1142)庶女为奴后,被迫给金人养猪,洪皓得知后,为其赎身,并将其嫁给当地读书人。张侍之身死云中,洪皓在荒废寺庙中发现其棺材后,带回燕山安葬⑩。在被金人软禁的十数年中,洪皓虽然自身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仍对身陷苦难的同胞伸出了援助之手。
综上,《松漠纪闻》虽为见闻记录,但书中议论精当,明确呈现了作者极强的儒家正统思想与追效前贤的思想意识,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感与经世致用特征。从其杂家式的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洪皓在学术上虽然没有表现出当时理学家对体系性理论的追求,但其以兴致和实用为取舍,力图在实学功夫中探求历史、社会之理,有着以学术杂家化建立新儒学的动向。在这戋戋两卷书里,洪皓的思想与学术进退贯彻得颇为全面。洪皓在《松漠纪闻》的记录中,以隐晦方式表达了以史为鉴的写作自觉,也昭示出其自成一体的思想格调与士人心态。洪皓在进退之间始终践行自己的经略之志,审时度势提出“和战”策略,始终坚持民为邦本,秉持恒定的处世原则与价值标准。洪皓虽然没有建构起系统的思想和学术体系,所学所思所行也不出宋学视域,但较一般宋学家,他的历史世界却是一个更为开阔、具体而又有作为的实践领域,其由历史进入理学的理论纵深,未必为一般理学家所能至。凡此种种表明,《松漠纪闻》杂家化的写作对于认识洪皓学术思想具有独特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