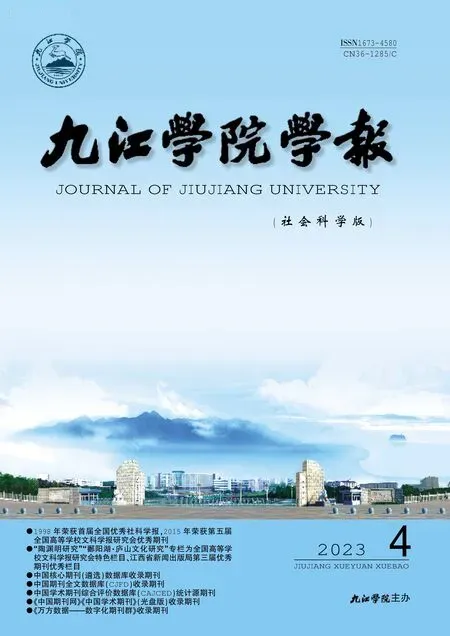论赵孟頫“桃花源”山水图式建构的特征及意义*
舒瑜欣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陶渊明是中国历代文人热烈追慕和歌颂的对象,钱钟书有言:“渊明文名,至宋而极。”[1]由于元代文学艺术是在不断吸收与融合汉族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继承了唐宋文化的元代文化也延续了慕陶情结。潘天寿在论元代绘画时说:“然当时在下臣民,以统治于异族人种之下,每多生不逢辰之感,……故从事绘画者,非寓康乐林泉之意,即带渊明怀晋之思。”[2]元代有许多文人画家由于遗民身份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不得志,面对自身尴尬境遇,他们通过寄情书画来表达其内心与陶渊明的共鸣,故以陶渊明为主题的诗文画作在元代并不罕见。生于宋末而在元初出仕新朝的赵孟頫便是当时创作陶渊明题材诗文书画的大家之一,他对陶渊明有“文采陶彭泽,丹青顾虎头”[3]之赞誉,并自述日常生活乃“闲吟渊明诗,静学右军字”[4]。可见赵孟頫对陶渊明的喜爱之深。
赵孟頫对陶渊明的推崇与接受首先表现在其诗文对陶诗的化用,如《和子俊感秋五首·其三》中“归休何不早,胡为受形役”[5]化用了《归去来兮辞》中的“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6]。《和子俊感秋五首·其四》中“天气政尔佳,抚己徒自伤”[7]化用了《饮酒·其五》中的“天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8]。其次,赵孟頫还在诗文中直接歌咏陶渊明,如《五柳先生传论》中以孔子的“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远其道”[9]高度评价陶渊明的理想人格,《咏逸民诗·其十一》通过重现陶渊明诗文中描写归隐生活的场面表达缅怀赞赏之情,并在众多诗句中提及“陶彭泽”“渊明”等。此外,赵孟頫作品中更有众多陶渊明题材的题画诗,如《题四画·桃源》《题四画·渊明》《题归去来图》等。在书画方面,赵孟頫除了有行草《陶渊明五言诗页》、行书《桃花源记》、楷书《五柳先生传》等,还绘制了陶渊明肖像图及其作品题材的画作,如《陶渊明故事图》《归去来辞图》等。
纵观中国“桃花源”图绘模式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桃源图像由最初的仙境山水转向了“人世化”,最终转向了隐居山水图式,这也是文人画中最流行的山水主题。石守谦称“桃花源”意象与文人山水画的互动“一方面进一步淡化与《桃花源记》的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抛弃了原来仙境传说的母型,加强了‘人世化’的理解,甚至开始展现‘实地化’的现象”[10]。而在文人画与题画诗大兴的元代,“桃花源”意象与隐居山水画的结合在南方文人圈中显示了一种普遍化倾向。赵孟頫“桃花源”建构总体上呈现为隐居山水图式,同时具有“人世化”和“实地化”双重特征。故本文将从赵孟頫的桃源题材艺术作品入手,试揣摩赵孟頫“桃花源”建构的“人世化”特征与代表隐居山水图式的“实地化”特征,进而窥探其心中的桃源世界,明确赵孟頫“桃花源”建构对于桃花源意象建构史乃至中国艺术史的意义与价值。
一、赵孟頫“桃花源”建构的“人世化”特征
有关“桃花源”的故事传说在各地区文化中屡见不鲜,最早将“桃花源”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的便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篇文章描写了有关“桃花源”理想社会的众多场景与物象,使“桃花源”成为重要的语言符号乃至图像符号出现在大量艺术作品中,为人们提供心灵的安歇之处。对“桃花源”进行“人世化”的诠释,在11世纪后期的中国士人文化中逐渐形成风尚。基于对桃源仙境本质的质疑,“人世化”即文人雅士于作品中建构“桃花源”时尝试拉近桃源与人世间的距离,营造出的世俗化生活景象。而渔人、隐士形象用于表达在其中生活的无拘无束。赵孟頫“桃花源”建构的“人世化”特征是通过对山野生活的描绘和对回归现实的纠结来表现的,在传达归隐之意的同时,也寄予了自己的理想抱负,生发出奋发昂扬的生活态度。
其一,赵孟頫“桃花源”建构通过展现丰富的村居生活来诠释“人世化”的理想世界。如赵孟頫的题画诗《题桃源图》,题画诗是诗、书、画在同一介质上的和谐统一,因此从题画诗入手可以间接看到桃源图式的建构。从内容上看,诗中前半部分艺术再现了《桃花源记》中的村落生活,诗篇开头交代了人们为了躲避战乱寻至与世隔绝的桃源重新生活,“艰难苟生活,种莳偶成趣”[11],虽勉强苟活但也在躬耕间暂得乐趣;“西邻与东舍,鸡犬自来去”[12]与“阡陌交通,鸡犬相闻”[13]遥相呼应,描绘了居住在桃源中的人民闲适安逸的生活状况。又如赵孟頫的纸本墨笔《重江叠嶂图》(见图1)以逶迤群山和辽阔江水为主体,其中有村落隐于山水之间,整幅画卷营造了一片祥和、遗世独立的桃源生活图景。赵孟頫用略带乾笔的勾皴加之渲染,勾勒出连绵起伏的山石纹理,清冽江面水平如镜,波澜不兴,天水相接,使得画面显得愈加朴野苍茫。在画卷中部有一双层楼阁隐于山腰间呈半露状态,阁楼左方有一座小桥将峦坡与对岸低缓小丘下的平地联结起来,上有行人正在过桥,在小丘平地上也有几所屋舍相互掩映,画卷左方有三人奋力拉拽着江中的渔船,似是在辛勤作业,右方也有一叶小舟闲泛江中。由此看来,赵孟頫通过描绘自在悠闲的乡野生活来实现“人世化”的“桃花源”建构,使这个原本求仙问道方可得访的理想化空间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息。

图1 《重江叠嶂图》局部
其二,赵孟頫“桃花源”建构以寄隐与不隐于一体来表明“人世化”的终极抉择。如赵孟頫《题四画·桃源》中“桃源一去绝埃尘,无复渔郎再问津”[14],同样述说桃源不易寻的实况。“想得耕田并凿井,依然淳朴太平民。”[15]一个“想”字直接抒发作者对桃源恬淡生活的向往,耕田取水自给自足的生活只存在于太平盛世,“民”字则暗含作者归隐之心,宁做太平世道的小民自由自在,不为官,不为世事所羁绊,即使桃源不复,但日子简单平淡,也宛若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又如《题桃源诗》中的一句感叹:“虽怀隐者心,桃源在何许?”[16]引发后人无限惆怅落寞。在诗歌后半部分赵孟頫对“桃花源”意蕴进行了新发,他一改诗歌前篇因桃源难觅产生的悲伤落魄之感,笔锋一转称赞当朝统治者的圣明和太平盛世:“况兹太平世,尧舜方在御。干戈久已戢,老幼乐含哺。”[17]结尾点明不必再问询桃花源在何处。显然,赵孟頫如此书写是有作为南宋遗民出仕新朝的顾虑的,隐逸之心难以满足,同时也希望可以通过积极入世改变自身处境。赵孟頫只能在歌颂当权统治者与太平盛世时,极为隐晦地表达对陶渊明回归田园,纵享山水之乐的生活的艳羡与渴望,由此可以清晰感知赵孟頫心中“仕”与“不仕”二者心态的交融。可见,“桃花源”之于赵孟頫相当于精神上的休憩之处,在这里赵孟頫可以任意构想理想生活,借以自我宽慰一番,但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现实生活中去。面对隐与仕这样的二难抉择,赵孟頫并未将二者对立起来,而是选择“桃花源”这样一个意象空间,加之“人世化”的处理,使之成为一个融坐穷泉壑的林泉之意与积功兴业的士人之志于一体的心灵居所。
综上,赵孟頫“桃花源”建构的“人世化”特征的呈现一方面是通过描绘山村悠然自乐的恬淡生活使“桃花源”理想空间充满民俗风情;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寄予入仕的纠结为“桃花源”理想空间增添了一份对人生理想的执着。赵孟頫对“桃花源”的“人世化”建构重在表达“隐逸”这一主题,但其真正传达的思想要旨是豁亮,起初赵孟頫因贰臣身份为官境遇并不如意,他何尝不知其苦,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像陶渊明一样隐退,而是依旧选择坚守心中出仕为官实现自身价值的汉儒思想。“桃花源”在空间上的隐遁使人苟且生存,但心灵和精神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是无处遁逃的,故只有在不隐不匿中直面生命的存在,在当下的生命体验中感悟永恒,才是赵孟頫建构“人世化”桃源的真正意义所在。
二、赵孟頫“桃花源”建构的“实地化”特征
巴赫金认为在文学作品中由空间与事件相互交织构成叙事。《桃花源记》中以渔人在桃源的历时性经历为线索,加之桃源中自然景观的变幻共同构成“桃花源”空间叙事结构,这种空间化叙事呈现出了文学与绘画相通的表现状态。文字叙事中对渔人所见所闻的描述和在空间中的上下、远近、内外的位置布局引发了后世绘画作品对桃源的再创造。赵孟頫以题画诗和桃源诗意图两种艺术形式完成对“桃花源”的“实地化”建构,虽然他并未有直接绘下《桃花源记》相关场景的画卷,但赵孟頫其他山水画中的景观已经初呈桃源“实地化”取向,所谓“实地化”即置“桃花源”于一处人世居所,意味着仙境在人间的高度再现。赵孟頫通过对不同地方山水的刻画,塑造理想化的淡雅宁静山水意境,显示赵孟頫隐逸山水间享受平淡宁静之追求。
从赵孟頫题画诗看,有一首观元代画家商琦《桃源春晓图》所作的题画诗《题商德符学士桃源春晓图》,《桃源春晓图》绘出了天台山的桃源春景,而浙江天台亦是出名的桃源现场,这里有相近的巧入仙境之奇景,阮肇、刘晨的故事便发生于此。诗文开篇“宿云初散青山湿,落红缤纷溪水急”[18]点明画中桃源清净安宁的环境;全诗对“绿萝”“飞泉”“瑶草”“长松”诸类自然景物的描写,表明此处鲜有人迹,同时赋予静谧山谷之动感活力;“鸡鸣犬吠自成村,居人至老不相识”[19]反映此地民风质朴,生活安逸。接着作者联想有“瀛洲仙客”知至此地的仙路,但自己却不知如何前往此地,便不禁发问:“何处有山如此图?移家欲往山中住。”[20]赵孟頫在这首诗中大肆描摹画中世外桃源之境,虽原画已无处可寻,但仍可使今人感受到画中万物勃发、春意盎然的景境,给人以闲适平淡之感。赵孟頫借“瀛洲仙客”这一人物形象寄予了欲携仙遨游至秘境的愿望,一方面有对商琦画作的称赞之意,另一方面实则暗含画中“桃花源”于现实之中无处可觅的无奈。
从赵孟頫桃源诗意图看,诗意图是语言和图像两种符号的组合,赵宪章称之为“诗歌的图像修辞”,即为诗语填补空白,使诗歌意象具象化。而诗意图的模仿并非是对诗意的完整再现,因为完整的诗意始终保留在诗篇中,诗意图是一种“间性艺术”——取意于语言艺术的图像艺术。故本文认为桃源诗意图,是在理解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基础上,通过诗意的绘画语言描摹“桃花源”中众多意象事件的理想式山水画卷。赵孟頫山水画中极富“桃源诗意”的代表性画作便有《水村图》《鹊华秋色图》和《洞庭东山图》。
首先,《水村图》(见图2)营造的桃源意境呈现为幽远恬静的江南水乡。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纸本墨笔《水村图》描绘的是赵孟頫前往水村居士钱德钧隐居处拜访时的所见景色,画面以横亘在薄雾中的平缓山峦为远景,山脚下参差坐落着呈条带状分布的林木,中近景以浩渺无边的水面为主体,四周被山水环抱的汀渚之上,几所农舍掩映在茂密树丛下,间有渔舟穿梭,数棵柳树错落分布在空地或民居旁,姿态婀娜。画卷中的水村背靠青山,四周水波环绕,如此独到的地理环境造成了此处与外界交通来往的不便,颇具“桃源难觅”的意味。幽林下的民居显示了村民专注自己生活、不为外界纷扰所动的态度,他们正如《桃花源记》中不知朝代更迭的村民一般过着怡然自乐的生活。赵孟頫在此画中多用披麻皴表现秀灵山水,以清润笔墨横拖纵扫,绘下水村恬淡安逸的生活图景,营造出与世隔绝、宁静闲适的桃源意境。

图2 《水村图》局部
其次,《鹊华秋色图》(见图3)描绘的桃源则是故土上的一隅安身之地。此画乃赵孟頫为好友周密绘下的记忆中的北国故里风光。画卷左端如《桃花源记》所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21],一片开阔的平地上坐落茅屋数间,其周有松柳杂树相伴,有山羊四五于屋舍间的空地啮食,一渔夫正在水边辛勤劳作,还有几叶渔舟于汀渚间穿梭往来。画面中的人们在忙于眼前生计的同时,也享受当下的宁静祥和。《鹊华秋色图》画境清旷悠远,具有十足的田园风味,大好山河秋色定格在此刻,红黄树叶纷飞而下寓示季节更迭,人类在万变之中显得如此渺小。赵孟頫在画中以故乡山水传递羁旅之愁的同时,也流露出于万变中找寻片刻宁静之意,故土就是他心中那片没有战乱纷争,人民安居乐业的“桃花源”。

图3 《鹊华秋色图》局部
最后,《洞庭东山图》(见图4)所绘桃源之景为江南烟雨山水,取景于苏州吴中。画面远处的东山圆浑平矮,层峦叠嶂,山间林木丛生,植被丰茂,山后烟雾笼罩,给人以迷离梦幻之感,深得桃源意境。近处水面的小丘上生长的是些许矮小的杂树,树影交叉错落倒映在湖面上,画作中部是寥廓无垠的太湖,湖面波光粼粼,几叶扁舟行于湖中,营造出静谧深远的氛围感。此图刻画山峦时削弱其层叠之势,用柔缓明润的笔法勾勒山石坡脚,以含蓄内劲的线条细描湖水波纹,表现出江南山水的朦胧和怡人。

图4 《洞庭东山图》
从以上的几幅山水画中,不难看出这些作品在构图上皆采用“一江两岸”的方式,即画面近处为岸或坡,其后以辽阔水面为主体,远端为环水的山石峰峦,这种画面布局在现实地理空间中是具有非连续性和阻隔性的,藏匿于隔岸山水中的世外桃源似乎正是赵孟頫心中所存的可望不可及的理想空间。
由此,赵孟頫对“桃花源”意境的“实地化”再创造向世人展示了赵孟頫对悠然雅静的隐逸世界的向往,同时构建出一个平和素静的精神归宿。赵孟頫在“桃花源”的“实地化”建构中隐晦传达出对故土的思念的同时,也表露出摒弃世俗对自我生命的一切束缚和由此带来的苦楚的心态,这与赵孟頫对待宋、元的矛盾心理是暗中契合的。
三、赵孟頫建构隐居山水图式“桃花源”的意义
“桃花源”的理想是一种中国士人传统文化理想。宗白华曾评价陶渊明“从他的庭院悠然窥见大宇宙的生气与节奏而证悟到忘言之境”[22],而陶渊明笔下的“庭院悠然”恰如“桃花源”中的山川、溪流、良田、村舍等物象,在后世文人的诗画空间中显现出容纳百川之生气。“桃花源”题材的创作盛行于唐代,唐人画笔下的“桃花源”是一个空灵飘渺的神仙世界,到了宋代,桃源大多表现为恬静烂漫的乡村世界,而到了元代,桃源图从仙境、世俗生活逐步转向了隐士的独处之地。对于元人来说,士人们往往是无法真正做到隐逸的,故元人的隐逸是社会性的,或隐于官,或隐入尘烟,如陈传席在《中国山水画史》中所言:“正因为元隐逸者和世俗混在一起,为了表现自己,为了把自己和世俗分开,就须特别强调脱俗。脱俗的口号喊得愈高,愈说明他们和俗离得很近。愈是近于俗,则愈是强调脱俗。”[23]赵孟頫的家乡霅溪(今湖州市)以桃花盛名,他对“桃花源”有自己的理解,赵孟頫“桃花源”建构的隐居山水图式较之前人来说,并未有完全藏匿于山林之意,而是抱有对世俗生活的期待,换句话说,赵孟頫“桃花源”建构中的“人世化”与“实地化”特征并不是分开对立的,而是相互交融的。
首先,赵孟頫隐居山水图式的桃源建构对于赵孟頫个人而言,是使其内心“仕”与“隐”矛盾得以交融的良策。赵孟頫在隐居山水图式的“桃花源”建构中,表露出对“道”的执着追求、对生命的重视和对林泉幽壑的向往。赵孟頫仕元后的矛盾心态与早已根植于他潜意识中的儒家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赵孟頫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加之母亲的鼓舞,发奋读书,渴求做出一番功绩来。奈何南宋政权覆灭,祖业中断,赵孟頫被迫隐居。在隐逸的数十年间,他深居简出,专注研究诗文书画,从未放弃精进才能。但出于“学而优则仕”的文人集体认知、改善家庭状况和提高名誉的原因,身为宋宗室后裔的他在元朝统一后选择了出仕。纵观赵孟頫的为官经历,他才华出众深得元世祖赏识,官位晋升顺利,身居高位,却难免遭朝中人忌恨,为此深陷困境。在这种境遇下,赵孟頫在其艺术作品中对桃源的建构可以说是一种自我调和行为,通过山水画表露其身在朝而心在野的心志。
其次,赵孟頫“桃花源”建构的隐居山水图式“人世化”特征为传统文人山水画创作注入了现实因素,这是赵孟頫入世思想的体现。赵孟頫艺术作品中的桃源建构呈现了与《桃花源记》中相同或相似的物象与景观,但并未如《桃花源记》一般留给后人一个桃源可寻的开放式结局。而是以桃源不复寻,要在现实中开凿或桃源不复寻,唯与仙同往的结局告知读者。前者结局实现的先置条件就是需要一个太平盛世,而太平盛世的出现得益于明君贤才,因此其中既包含赵孟頫对当朝统治者的赞美歌颂,又有对百姓社稷的关心,是赵孟頫入世思想的体现。后者结局则如大梦初醒之前夕,携仙遨游带来的是精神上的享受休憩,桃源成为了精神向往,现实里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是无法前往的。如此看来,赵孟頫是极具雅儒风尚的,内外兼修,他仕元更多是出于实现学者理想。虽然他无法像陶渊明一样摒弃官场,纵情山水之间,但他却将自己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融入他的艺术创作中,在桃源之中展现追崇陶渊明隐逸之意的同时,也表露了在官场中积极进取的决心。
最后,赵孟頫“桃花源”建构的隐居山水图式“实地化”特征为中国传统山水审美观念注入了人格力量,反映出赵孟頫对当下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有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24]南方山水钟灵毓秀,滋养了文人高雅的审美意趣和洒脱自由的人格精神。赵孟頫长期居于江南使其在此处江山河川的助力下构建出了题画诗和山水画中韵味十足的桃源地理空间。又因赵孟頫一生多半时间忙于南北驱驰,使其熟识北国风光,故赵孟頫山水画卷中又多了些许苍茫辽阔。李天道谈到文人画家“总是怀着各种强烈的失落感与忧患意识走进自然山水,通过对自然景物的关照,情感渐渐趋向淡泊,最后直至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完全融会进山水自然生生不已的生命韵律中”[25]。赵孟頫选取江南水乡和友人北方故土实景为素材,塑造了他心中的“桃花源”,“归去来”的归宿即是桃源,桃源在何处——隐没山水间,远离尘世喧嚣,居住在此的人们只专注此生康乐。庄子云:“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26]庄子言下的理想社会乃万物共生,民生安乐,受老庄思想影响极深的赵孟頫在桃源建构中何尝没有营造这样一个理想社会呢?赵孟頫桃源诗意图选择村落、畜群、渔夫等物象组合,加之村民自顾自地忙于生计、渔夫泛舟等事象推展画面,再结合“一江两岸”的构图方式,在自然空间、社会空间与生活空间上构建了一个安逸祥和的“桃花源”。赵孟頫在山水作品中呈现出一种无求于世的高逸,他提倡“云山为师”,强调自然写实,体会山水意境,于山水中表达对生活的感悟,将生命寄存于山水之间。这种独立超拔的精神使得赵孟頫进行桃源建构时在传承陶渊明塑造的“桃花源”隐逸主题基础上又多了些风骨气概。
总之,赵孟頫“桃花源”建构在整个桃花源艺术建构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上承前代桃源“人世化”建构,后启桃源隐居“实地化”建构,使桃源成为一个集朝堂理想与山野之乐于一体的理想化空间,桃源也继而化为赵孟頫坚守本心的表征。赵孟頫的内心始终没有停止找寻能够使精神得以皈依的桃源,可幸的是他在多年于世俗和追求精神自适的痛苦挣扎中选择了一套适合自己安身立命的方式,并最终有所成就。
四、结语
赵孟頫“桃花源”建构的隐居山水图式通过对“人世化”与“实地化”双重特征的呈现,使赵孟頫对“仕”与“隐”的纠结痛苦得以暂缓,既表现了他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又寄托了他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赵孟頫在对桃源的“人世化”建构中以塑造充满烟火气的山居生活来表达对乡野的眷恋,并暗抒在现实生活中积极进取的心态。赵孟頫在“实地化”桃源建构中,将桃源落实到实地景观,即使桃源之于赵孟頫从地理空间层面上来说并无固定所指,可以是宁静的江南水乡,也可以是故乡的一片净土,但桃源所指向的心灵归旨始终如一。
在赵孟頫建构的桃源世界中,仕与不仕,隐或不隐并不是绝对矛盾的,而是互相交融的,为赵孟頫的本心提供一隅栖身之处聊以自慰。赵孟頫进行桃源建构的同时,也对陶渊明重视生命即时体验而超越世俗的生存智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领悟到了“隐”的另一层含义,即积极豁达地直面当下生活的苦难,才能自由抒发超越物我束缚的自适之乐,这也是陶渊明生存之道的内核。
赵孟頫对“桃花源”这一文学母题的频繁摹绘属于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上重要的“语图漩涡”现象(赵宪章语),具有开先意义,并启发王蒙、赵奕等人的桃源诗意图创作。总的来说,赵孟頫笔下的桃源世界不再局限于抒发荷锄畎亩之趣,更有一种于隐匿中迸发出来的豁达乐观的向上之势,这使得“桃花源”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所体现的人生追求与美学理想更为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