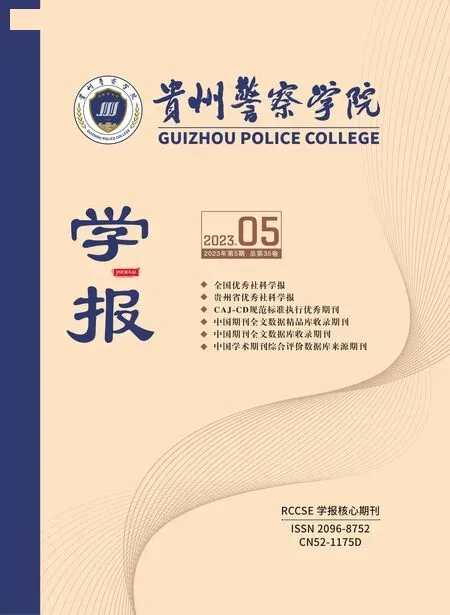关注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研究
——吴家麟留给我们的思考
郑天祥,金承光
(1.扬州大学,江苏 扬州 225127;2.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追忆吴家麟时,人们必誉其为“新中国宪法学的泰斗”。[1]事实上不仅如此,吴家麟亦是为新中国逻辑学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新中国法律逻辑学的泰斗”。1961 年,吴家麟的宪法学研究逢难,开始在宁夏大学教授形式逻辑课程。自此逻辑学便成为了其教学、科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改革开放后,吴家麟首先大力普及逻辑。1979 年,他通过对故事进行逻辑分析的新方式来普及形式逻辑,广罗古今中外的逻辑学故事编著完成的《故事里的逻辑》一书倍受读者好评,至今仍多被效仿。1982年,吴家麟还出版了《破案、审案与逻辑》一书,该著作专门探讨形式逻辑在破案、审案和辩护中的运用技巧,并结合法律知识与逻辑学知识给法律工作者提供了一些法律方面的实际思维材料。1990年,吴家麟又针对中学生听众,与夫人汤翠芳合作编著了兼具知识性、实用性和趣味性的《与中学生趣谈逻辑》,为中学教育阶段的逻辑普及做出了宝贵探索。此外,吴家麟更是中国法律逻辑学界的早期负责人和领军人物。1983 年,中国法律逻辑研究会(1993年更名为中国逻辑学会法律逻辑专业委员会)成立时,吴家麟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副会长。①中国法律逻辑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仅设2 名副会长(另一副会长为北京政法学院杜汝楫),会长为刑法学家李光灿先生,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先生任名誉会长。1989年至1993 年,任中国法律逻辑研究会会长,其间全国法律逻辑领域正式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和学术活动日渐增多、学会不断发展壮大,同时,其学术思想对中国法律逻辑学的建立及早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2 年,吴家麟最先论证了建立法律逻辑学的必要性及其研究内容和方法。[2]1983 年,主编了我国第一本以“法律逻辑学”命名的教材,即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法律逻辑学》,实现了我国法律逻辑学教材由“法律专业逻辑学”到“法律逻辑学”的转变。该书经1986 年修订后一直再版至今,影响了一批又一批中国法律逻辑学者。而由吴家麟执笔完成的两版《法律逻辑学》“引论”作为全书的引领,也集中反映了他对法律逻辑基本问题的思考,在其法律逻辑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在“引论”中,吴家麟提出,“法律逻辑学是一门应用性质的形式逻辑分支学科”,“并不是法学的一个部门,而是形式逻辑的一个部门”。[3]该观点贯穿其主编的两版《法律逻辑学》,既是吴家麟法律逻辑思想的核心观点,也代表了中国法律逻辑学研究第一阶段的基本模式[4]。尽管目前来看该思想仅仅是众多关于中国法律逻辑学性质探讨的观点之一,但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法律推理领域中亦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5]。吴家麟在中国法律逻辑学建立初期即重视形式逻辑对法律逻辑的作用,无疑为中国法律逻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形式逻辑基础。另一方面,吴家麟的这一观点也符合当时法律逻辑学者队伍主要由逻辑学者构成的局面,为法律逻辑学的发展凝聚了一批骨干人才和核心力量。此外,在两个版本“引论”修改中,也动态展现了吴家麟对于法律逻辑学的不断深入思考,而关注中国法律逻辑思想研究就是其中的显著变化之一。
一、吴家麟关注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研究的历程
吴家麟之所以在新中国法律逻辑事业的开端就关注到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研究,这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其自形式逻辑普及工作以来持续关注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和立足中国国情对法律逻辑学基本问题不断深入思考的结果。
(一)形式逻辑普及中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视
中国是逻辑的三大发源地之一,具有丰富逻辑资源。吴家麟认为,“无论古代人也好,现代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都在经常地用形式逻辑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6]从表1《故事里的逻辑》各章节使用的中国古代故事之出处可见吴家麟在形式逻辑的普及工作中对中国古代逻辑资源之重视,及其挖掘中国古代逻辑资源的广度和深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吴家麟在滥觞于先秦的广阔中国古代逻辑视野中,从概念、判断、推理、证明、逻辑规律多层次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逻辑故事的深入挖掘和剖析。这不仅拉近了我国听众与逻辑的距离,有利于形式逻辑的普及,也在逻辑普及的进程中树立了中国文化本位意识,有利于增强中国听众的逻辑文化自信。同时,吴家麟中国逻辑故事视角的研究,也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扩展了文献视野,将《史记》《世说新语》《古今谭概》《红楼梦》《梦溪笔谈》等众多史学、文学、科学文献纳入到了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范畴,丰富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
(二)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的发现
在法律逻辑学的研究中,吴家麟亦十分重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研究。他指出,“古代希腊、中国和印度,都有一批学者结合哲学、政治、语法和修辞,从事思维方面的研究,并且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逻辑学说。”[3]6所以,吴家麟在初版《法律逻辑学》中论述“形式逻辑的产生和发展”时,不仅介绍了西方形式逻辑发展史,更阐释了中国古代逻辑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首先,吴家麟指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在百家争鸣中,建立了我国古代的逻辑学说。”[3]10以惠施、公孙龙、荀子、韩非子等先秦各派代表人物的逻辑思想和逻辑著作《墨经》展示了先秦逻辑的成就。其中,《墨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逻辑,“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逻辑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指出先秦逻辑思想具有“形式化程度比较差”和“把逻辑问题作为独立学术问题来研究的不多”的局限性[3]12。
紧接着,吴家麟又梳理了“先秦逻辑学‘亡绝五百余岁’”后,魏晋鲁胜著《墨辩注》及《形名二篇》,唐代玄奘助力古印度因明传入中国和明末西方逻辑传入中国等中国逻辑发展的重要历史事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新中国形式逻辑的发展问题,他强调发展形式逻辑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条是吸收现代数理逻辑的研究成果,使形式逻辑现代化”;“另一条是建立和发展各种应用逻辑学科,使形式逻辑普及化”。[3]14所以,在初版《法律逻辑学》中,吴家麟是通过总结中国古代逻辑和西方逻辑发展规律,来揭示建设中国法律逻辑学等应用逻辑学科必要性的。这在肯定中国法律逻辑事业重要价值的同时,也将其放在了逻辑学发展的历史脉流中,为中国法律逻辑学建设探明了来路,打下了坚固的学术基础。
随着吴家麟法律逻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1986 年修订《法律逻辑学》时,吴家麟进一步加强了对建设法律逻辑学科必要性的论证。他不仅从逻辑史角度强调建设法律逻辑学顺应了形式逻辑科学发展需要,还指出法律逻辑学是法学研究和法律工作迫切需要,有助于培养和提高法律专业学生和法律工作者应用逻辑的能力。而且,吴家麟强调“中国历来有逻辑知识与法律知识相结合的优良传统。”[7]8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是其论证建立和发展法律逻辑学有助于培养和提高法律专业学生和法律工作者应用能力的主要论据来源。一方面,吴家麟强调“中国古代的法家人物有的就是逻辑学家”[8]8,以“中国律师的祖师爷”邓析子和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的逻辑应用,阐明了逻辑对诉讼和法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善于使用内涵、外延的概念逻辑可能是邓析子承办案件多能胜诉的缘故;“古代法家的逻辑思想,基本上是从‘刑名法术’之学对逻辑的应用中总结出来的。”[8]9另一方面,吴家麟以唐代制判“文理优长”,富有逻辑性,进一步肯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与逻辑应用结合的逻辑传统。
因此,在修订版《法律逻辑学》中,吴家麟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已经走上了与法律相结合的方向,更确切地说,吴家麟开始以其法律逻辑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发现了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研究的新课题。然而,若没有广泛探索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经历和专业的法律逻辑学研究基础,吴家麟难以如此精确地发现邓析子、韩非子实践中的法律逻辑思想和唐代制判实践中的逻辑应用。吴家麟通过两版《法律逻辑学》动态变化展示出的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课题,是其对逻辑学和法学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极具研究价值。
二、吴家麟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研究的特色
逻辑对法学的必要性是法学家们反复强调的重要事项。民国时期,法学家孙晓楼在探索法律教育问题时即指出,“论理学(即逻辑学——作者注)是一种理智的科学,即用以探求真理之学。凡是要整理思想以探求真理,皆不可不从论理的方法来着手,尤其对于法律方面,无论于法律事实应如何推定,证据应如何采纳,律师应如何辩护,法律应如何编制,都应当以清晰的头脑,作有条理有系统的研究,然后论断事件,不致有所谬误。”[8]美国霍姆斯大法官强调:“法律人受到的训练就是逻辑思维的训练。”[9]英国法学家麦考密克和奥地利法学家魏因贝格尔强调:“在法律人的技术当中,主要的就是进行正确的推理和有力的论证的技术。”[10]德国学者普珀在其法学思维著作的开篇也强调:“法律人的技艺,就是论证。”[11]当代,我国法学家舒国滢“以欧陆法学(尤其是欧洲私法)的发展作为考察法学知识谱系的‘素材’,再次强调“没有哲学、逻辑学、修辞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教养其实并不适合从事法学研究”[12]。
当然,创造了辉煌法律文明的古代中国亦不是逻辑对法学发展必要性的反例。早在“轴心时代”的先秦就孕育出了丰富的法律逻辑思想。墨学大家栾调甫在探讨孙诒让对《鲁胜墨辩注叙》“刑名”一词的训诂时,就展示了重法之法家与重逻辑之名家的密切关系。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可谓清及其前墨学研究的大总结”[13],使原本难以卒读《墨子》文字得以理顺,为后世中国古代逻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基础。而且,孙诒让本身也对《墨经》的逻辑思想已有深刻认识。一方面,“孙诒让在校勘诠释《墨经》的过程也运用了一些逻辑知识”[14]。另一方面,他在《与梁卓如论墨子书》指出,《墨经》之微言大义,如欧洲亚里士多德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和佛学之因明论者。而以批梁启超之《墨经校释》一鸣惊人的栾调甫则认为,孙诒让对《鲁胜墨辩注叙》中“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一句的“别”之字训诂提出了不同见解。他认为“别”应为“刑”,“以正别,名显于世”即应是“以正刑名显于世”。
首先,在版本上他强调:“《间诂》附录《鲁序》,虽标题《晋书》,其文实出《通志》。考《晋书胜传》,此文本作以正刑名。《通志》之别,显系误字。仲容未检《晋书》,又不悟讹脱,注谓孙星衍校改,已极疏陋。襄见梁任公《墨子之论理学》竟删刑字。”[15]而后,他指出孙诒让和梁启超之错误在于不理解刑名意思。栾调甫说:“似两君均不识刑名二字之义,而以法家刑名,非惠施公孙龙辈所能正,致生此曲失。不知法家别称刑名,而名家亦号刑名。如《战国策》‘刑名之家’,《抱朴子》‘刑名之学’,均指名家言也。陈诗瑚论申韩曰:‘申韩刑名之学,刑者形也,其法在审合刑名,盖循名责实之谓。今直以为刑罚之刑,过矣。’陈说当否,姑置弗问。若《鲁序》刑名之为形名,读本可通。而‘以正形名,’语子可解,不烦删改,强为傅会矣。”也就是说,“刑名”本来就是法家与名家在一定情况下可共同使用的名称。孙诒让和梁启超以为“刑名”仅为法家的称呼,看到惠施和公孙龙则不敢使用“刑名”与之搭配,或改“刑”为“别”,或直接删去,均是没有必要的。事实上,法律与逻辑的关系也一直是中国法律史和逻辑史学者探索其学科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称名学、辩学为中国古代逻辑学的法律史学家高恒主张,名学是中国古代法学的理论基础,并以“类”“故”“譬”“效”等名学的重要范畴理论对法学的深刻影响为该观点提供了辩护。他认为,“它(名学——引者注)醒示立法者制定法律必须遵循逻辑学理论,名词概念确切、条文符合逻辑、体系严密,以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实行。”[16]法律史学家张中秋在中西法文化的比较视野中即指出,借鉴西方法学发展经验,逻辑学的缺少是传统中国法学的难产的原因之一。[17]但他进一步补充到,“将这一问题置于春秋战国和魏晋时期来阐释就不甚合适,因为古中国恰恰在这两个时期并不缺乏逻辑思辨:前有名家和墨家的辩学,后有玄学的思辨之风;只是在总体上,它们未能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流。”[18]换言之,中国古代法学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有体现逻辑与法学相互关系的反面教训,也可能有正面的经验,而先秦、魏晋等中国古代逻辑的繁荣期则是发现这些正面经验的畛域。法律史学家武树臣在法家法文化研究中即指出,先秦名辩思潮与“成文法”的问世及成熟有着直接的关系,[19]为中国古代逻辑与法的发展提供了正面实例。
胡适于1917 年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申请博士学位而完成的《先秦名学史》是第一部断代中国逻辑史著作,其英文版和中文改写、扩充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分别于1919 年和1922年在我国出版。胡适以哲学史的写作方法介绍了从孔子到韩非子等先秦诸学派的逻辑发展,他认为“没有从孔子时代以来发生的逻辑上的逐渐变化,像韩非子那样对法术哲学的明白、确切的阐述是不可能的。”[20]176因此,他指出“法理论基础的逻辑方法研究,似乎可以被认为是这篇先秦名学史论文的恰当结论”[20]176,首次在先秦逻辑史的语境内提出了“The logic of law”即法律逻辑,并专辟一章对其进行了阐述。[20]174胡适在先秦逻辑史研究中提出法律逻辑概念,不仅凸显了法律逻辑思想在先秦的重要性,更实现了法律逻辑学概念在中国的首次提出,具有重要意义。
继胡适揭示逻辑发展对于韩非子法家学说提出的必要性。逻辑史伍非百进一步从法律发展的角度解释了逻辑在先秦的繁荣。伍非百指出名家与形名家乃异名同实之称,“‘名家’之学,始于邓析,成于别墨,盛于庄周、惠施、公孙龙及荀卿……与印度的‘因明’、希腊的‘逻辑’,鼎立为三。”[21]3而且,他认为邓析子之所以在郑国始创名学,与郑国铸刑书,即我国首次公布成文法有关,强调“‘形名’与‘刑法’是相待而生的伴侣。”[21]4伍非百指出未公布成文法前的周朝礼治时期,“当官者以意断事,上无成例可援,下亦无所据以责难辨核。”[21]4而郑国子产铸刑书后,“科条章明,著之文字,与众共守”,促进了“辩”的产生。所以,伍非百的形名与刑法“相待而生”应理解为两者的相互依靠,刑法的公布促进了形名的发生,孕育了“辩”,而形名的发展也为刑法的运行提供了工具。伍非百在源头处揭示了法的产生与逻辑产生的关系,胡适则是在先秦逻辑发展的晚期看逻辑发展与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法家学说的提出,两者相互补充发挥了先秦法律逻辑思想研究的优势。
郭湛波的先秦逻辑思想研究与胡适、伍非百均有相通之处,他认为形名学就是中国逻辑学,乃中国治学的方法,先秦“形名学”与“刑名学”乃同一概念,“法家所谓的‘刑名’,就是名家所谓的‘名实’。”[22]3而且他认为,“刑名”与“法术”虽然常常连用并非因为刑名学是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等为代表的法术学,而是由于“讲法必讲刑名”。也就是说,郭湛波从“刑名法术”的先秦逻辑入手揭示了法律与逻辑的关系,即法学研究必然离不开逻辑。对于中国逻辑的诞生郭氏亦认为与法的产生相关,认为郑国“礼的观念最先破坏,法治观念最先发生。所以形名学始于邓析子,申、韩源于郑学。”[22]6所以,郭湛波的法律逻辑思想研究认为,中国法的产生孕育了中国逻辑思想,而中国逻辑思想的诞生为申、韩法家学说的诞生提供了治学的方法。
先秦逻辑史研究与法律史研究共同关注到法律与逻辑研究课题,以及胡适能够在先秦逻辑史的研究中首次在中国提出法律逻辑,都说明了先秦法律逻辑思想研究的重要价值。但应当注意的是,包括明确提出了法律逻辑概念的胡适在内的以上学者,虽然都以先秦法律逻辑思想研究为代表探索了中国古代的法律逻辑思想,也取得了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他们都是以中国逻辑史或法律史研究为径开展的,并没有专以法律逻辑视角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进行审视。直至吴家麟才真正开启了以法律逻辑视角进行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的工作。
一般认为,新中国“法律逻辑”或“法律逻辑学”这一名称最早是在1981 年9 月全国形式逻辑讨论会(屯溪会议)才由一些学者提出的。而吴家麟从1982 年率先对建立“法律逻辑学”的必要性及其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证,到1983 年主编《法律逻辑学》,再到1986 年修订该教材讨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时,其法律逻辑观点已逐步走向稳定。所以,无论是从总体上吴家麟对中国古代逻辑知识和法律知识相结合传统的关注,还是具体对邓析子在诉讼中运用的概念逻辑和唐代判词所作的逻辑性分析,其修订版《法律逻辑学》的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始终是在其法律逻辑观的指引下开展的。也正是吴家麟这种目的明确的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为其探究广阔的中国古代逻辑提供了指针,一方面,使其在丰富的先秦逻辑资源中发现了邓析子、韩非子等法家代表人物的法律逻辑思想;另一方面,也指引其走出先秦在中国古代广阔的逻辑应用中发现了唐代制判法律实践的逻辑应用问题。因此,吴家麟的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研究,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其学术成果,更是以当下法律逻辑学研究成果为基础发现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的方法。
三、吴家麟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研究的启示
(一)注重中国逻辑史研究应用逻辑视角
吴家麟在反思中国古代逻辑发展时指出,“把逻辑问题作为独立学术问题来研究的不多”[3]12是其局限性之一。日本学者末木刚博在中国、印度和日本的东方逻辑思想比较中指出,先秦逻辑的建立始终是由于实践的必要,“几乎没有见到把以纯粹的形式抽象出来加以研究的尝试。”[23]然而,当先秦名辩学与西方逻辑相遇后,两者的求同研究却首先成为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徐复观曾指出:“自从严复以‘名学’一词作为西方逻辑的译名以后,便容易引起许多的附会。实则两者的性格,并不相同。……逻辑所追求的是思维的世界,而名学所追求的是行为的世界。”[24]也就是说,以西方形式逻辑来比附先秦的“名”,忽略了先秦逻辑思想的实践指向,缺少对先秦逻辑思想重实践特征的关注。
但重实践一直是逻辑史学家强调的治中国逻辑史不可忽略的重要特征。温公颐认为:“逻辑理论的提出,不是逻辑学家主观自生的东西,它和逻辑学家的实践密切相关。有的逻辑学家的理论是从他的逻辑运用中,特别是在他和不同派别的论辩中,或从政治斗争中或从自然的探索中总结出来的,这在我国先秦时期很突出。”[25]3崔清田也分析道:“求同的学术取向,多出于无视或不关注文化对逻辑的制约,因此也难以发现在不同文化下生成并受其制约的逻辑的特殊性,致使过分强调了不同逻辑传统的同一性。”[26]在此分析之下,崔清田尤其强调中国先秦文化环境的实践面向。他指出:“在中国,先秦文化不同于古希腊文化。它的核心是伦理政治与社会人事,它的主要内容是伦理尺度与治国纲纪的构想、建立和实践,它的基本思维取向是现实的需要以及实践的中国经验。”[27]刘培育在《中国古代哲学精华》中亦强调:“中国名辩史是关于中华民族名辩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这项研究工作既要以极大的注意力去探讨各个历史时期的名辩著作中的基本理论,也要十分注意散见于政治、科学(包括医学、农学、军事学、数学等)乃至文艺学中的名辩理论。这样做不仅符合一般的史的研究规律,而且是从中国名辩史的实际出发的。”[28]
“应用逻辑就是面向特定领域系统探究逻辑因素在该领域的作用机理,以及逻辑因素与非逻辑因素的相互作用机理,以把握方法论‘模式’为研究核心,旨在形成关于该领域的逻辑应用方法论。”[29]法律逻辑作为应用逻辑之一,吴家麟以法律领域为典型,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探究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既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现提供了分析法律实践的应用逻辑方案,也为认识邓析子、韩非子等人逻辑思想和中国古代判词说理逻辑提供了更贴合其法律领域的专业路径。这不仅立足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多未脱离实践的现实,也将先进的法律逻辑学研究成果运用到了中国古代逻辑的解读,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全面发现引进了新工具。所以,吴家麟从应用逻辑视角探究中国古代逻辑的方法是极具启迪意义的。
当逻辑史学家李廉受邀为法律逻辑学著作《司法应用逻辑》一书作序时,法律逻辑视角再次于先秦逻辑领域迸发了活力。李廉认为,“逻辑理论在中国的形成,从一开始就同司法的实践和理论血肉相连,司法实践必须遵循逻辑的规律,逻辑的规律和思维形式则总是比较明确地体现于司法的理论和实践。”关于先秦法律逻辑思想李廉指出,“司法与逻辑密切联合的观点,不仅表现为‘刑名之学’,表现于先秦时期的法家理论,儒家、道家、墨家也都有相同的或近似的观点。”他从法律逻辑中的司法应用逻辑视角出发,广泛考察先秦诸子的逻辑思想后发现,“中国逻辑史上最早的逻辑学家如邓析、宋钘、尹文等,都是‘刑名’(或‘形名’)之家,邓析作《竹刑》,‘循名,察法’,结合刑与名反对周的‘礼制’,宋钘、尹文‘以物为法’,‘名’‘法’同论”;法学家商鞅为“绝对刑名主义”者;管仲“对于‘正’名、‘察’名与国家治乱的关系,特别重视”;韩非既是法学家也是逻辑学家,重视逻辑与司法的关系;儒家孔子指明概念(名)的明确与否对办事、刑罚等等的成败关系;道家庄周的“刑名”要“明”的思想是可贵的;墨家“对‘辩’(逻辑学)下的定义中,有这样的断定:‘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
就具体案例而言,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在法律领域的应用逻辑思想已受到中国逻辑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汪奠基在韩非的逻辑思想研究中发现了韩非“刑名参验”的“实用逻辑”思想,他认为,“韩非是在封建统一的法权政治需要之下,提出了‘循名责实’与‘参验法式’的唯物论者。……他总结提出实用的逻辑思想,体现了他对当时墨辩逻辑的运用,特别是推进了荀况名实唯物论逻辑的发展。”周云之认为,韩非是一位“出色的逻辑实践家”,“用法术改造逻辑学是韩非逻辑的一个特点”。[30]何应灿认为,韩非的“逻辑思想的主要特点是逻辑在刑名法术上的应用”。[31]温公颐则指出:“有人称韩非的逻辑是实质的逻辑、应用的逻辑,这是因为韩非不象名、墨或荀子等发挥逻辑的理论,而着眼于逻辑在形名法术上的应用。”[25]315
因此,吴家麟开启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研究契合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重实践的特征,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的现实需求,为中国逻辑史研究打开应用逻辑视角提供了范例。尤其是在科学逻辑、决策逻辑、语言逻辑、法律逻辑等应用逻辑学科蓬勃发展的当下,中国逻辑史研究开启应用逻辑视角,将打开中国古代逻辑实践历史与当代应用逻辑理论互通的大门,这不仅可以使重实践的中国古代逻辑获得应用逻辑视角的认识,也将从不同专业领域角度大大丰富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内容,为新时代实践提供古老的应用逻辑经验。故从法律逻辑学视角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进行开掘,不只打开了法律逻辑学研究的新视域,更为中国逻辑史研究树立了新范式,启示当代中国逻辑史研究需注重应用逻辑的视角,多层次、多领域地全面阐释中国古代逻辑思想。
(二)发挥中国古代法律逻辑研究的独特价值
吴家麟的法律逻辑学研究始终重视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中汲取营养,该研究路径既可以发挥法律逻辑学的特殊价值,为认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提供新视角,有助于破除西方对我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偏见,同时也是探明我国法律逻辑学研究传统文化根基,赋予我国当下法律逻辑学研究本土的经验的必由之路。
1.破除中国法律“无逻辑”的偏见
基于逻辑的求“真”价值及其与法律实践的密切关系,逻辑常被作为评价法律文化的重要指标。古代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华法系”,法律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当中国法律文化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法学的逻辑学研究范式介入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后,中国法律文化却被贴上了“无逻辑”的标签。如韦伯认为,“逻辑、定义、与推理的力量,尚未为中国人所理解到”;“由希腊城邦首先发展出来、作为达成政治与诉讼目的的理性手段的辩论术,是不见之于中国的。”[32]因而他认为中国法律是“实质非理性”类型的典型,与现代西方“形式合理性”的法律类型截然对立。[33]又如,原惣兵卫认为中国人只知演绎逻辑,不知归纳逻辑,无法培育出科学与法律。[34]而且当下,我国司法改革和法律逻辑学研究也存在通过批评中国传统司法实践“无逻辑”来揭示法律逻辑学对我国的重要性的现象。这使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无逻辑”的偏见被进一步加深。然而,回到我国法律逻辑学研究之初,吴家麟不仅重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逻辑思想的挖掘,而且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与中国逻辑史和法律史相关研究结果亦高度契合。虽然其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说明中国古代法律实践的角度证成逻辑思想对法律工作的意义,但实际上更起到了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正名的作用,即通过呈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有法律逻辑思想内容,有力地驳斥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无逻辑”的谬误,展示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理性的一面。特别是吴家麟采取的以形式逻辑基础的法律逻辑学研究路径,更加强调形式逻辑思想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运用,直接从形式逻辑层面对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古代法律实践“无逻辑”的谬误进行驳斥,更加契合西方学者提出该命题的现实语境,有利于增强论证效果。
2.为当下法律逻辑学研究和法治建设贡献本土资源
随着法律逻辑学研究和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对法律逻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越来越多的相关域外研究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当代法律逻辑成为一门学问始于西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古代法律逻辑思想研究。一者我国法律逻辑学研究从起步就有其独立性的一面;二者无论是从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还是逻辑学的研究,均没有采用完全抛弃本国传统的方案。所以,在新时代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的研究也不应缺失。一方面,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研究的精髓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借鉴。如当代我国当下法律编撰常面临着逻辑失范的批评,[35]是我国当下法典化进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但反观中国古代立法技术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创造出了《唐律疏议》等立法典范。并且,孔子关于“正名”的论述亦被西方法理学者视为“法律与语言”问题的题记。又如当下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改革,亦注重借鉴中国古代判词“天理国法人情”共融的说理方法。再如,从战国后期的《封诊式》到宋慈的《洗冤集录》,其中呈现出的中国古代侦查逻辑思想,亦对避免冤假错案具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的缺陷也是当下法律逻辑学研究和法治建设需要关注的内容。首先,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从繁荣到衰落的历史进程,有助于法律逻辑学获取本土经验,为自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其次,厘清我国当代法治建设中传统逻辑思想内在支撑的不足,更有利我国法律逻辑学研究聚焦中国问题,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吴家麟作为中国法律逻辑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关注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研究既体现了其对法律逻辑学问题思考之深邃,也展现了我国法律逻辑学研究从起步时就具备的独特中国文化视角。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我国当下法律逻辑学研究亦应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延续吴家麟的中国古代法律逻辑思想研究。这不仅有利于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全面认识和中国优秀法律逻辑思想的传承,为我国当下的法治现代化建设贡献本土经验,同时,也有利于破解西方法学对中国误解,揭示中国传统法文化的逻辑理性,提升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