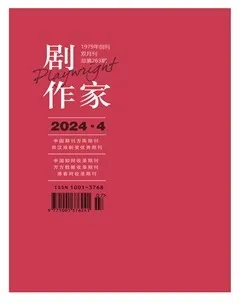明代中后期《西厢记》女性接受者研究
摘" 要:本文主要考察明代中后期《西厢记》女性接受者的情况,说明在明代中后期社会环境中的女性对《西厢记》的两种接受途径,探讨《西厢记》对于女性接受者的影响,并简单阐述了女性接受的局限性。
关键词:《西厢记》; 女性接受;局限性
通过解读昆曲《西厢记》的女性读者叶纨纨、叶小鸾姐妹的生活和黄淑素、刘丽华的戏曲评点发现,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的女性,对于《西厢记》的阅读接受体验是共同的,往往会有强烈的情感共鸣,并由此萌发了朦胧的女性意识,却也仅仅止步于此。
一、《西厢记》的上层女性接受者研究
(一)接受途径
有关上层女性的接受途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途径是文本阅读。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特别是江南一带,刊印业发展繁荣,“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1]P687。而《西厢记》作为对照物被用来对比体现《牡丹亭》的火爆程度,也就是说,在《牡丹亭》问世之前,《西厢记》拥有非常可观的市场。并且,像《雍熙乐府》这类收录《西厢记》的书籍也被大量刊印。由此可见,《西厢记》得到了批量生产并迅速传播。此外,据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统计:“不管读者大众群的发展有多快,它一定不会超过总人口的 10%。”[2]P39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能够有资本和能力接受文本版《西厢记》的女性主要限于读书识字的女性,而这类女性通常集中在社会上层。
晚明著名文人叶绍袁的女儿叶小鸾就是《西厢记》的读者。虽然并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明叶小鸾曾读过《西厢记》,但她曾为《西厢记》《牡丹亭》题诗十六首。而且,叶小鸾年幼时曾被送到舅家寄育,舅舅沈自征是明末戏曲大家,舅母张倩倩也是一代才女,在这样的环境里生长,《西厢记》也应当是读过的。并且在叶绍袁的家中也藏有坊刻本《西厢记》与《牡丹亭》,母亲又是闺阁诗人,由此推测叶小鸾也是《西厢记》的女性读者。
同理,与叶小鸾一样的上层女性读者还有黄淑素,因评点《牡丹亭》时与《西厢记》做了对比,可知,黄淑素也是《西厢记》的读者。
“《西厢》生于情,《牡丹》死于情也。张君瑞、崔莺莺当寄居‘萧寺’,外有寇警,内有夫人,时势不得不生,生则续,死则断矣。”[3]P338
除了上文提到的文本接受层面,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途径——舞台演出。
第一种舞台接受途径是代表最上层的宫廷演出。“(崇祯)五年(公元 1632 年),皇后千秋节,谕沈香班优人演《西厢记》五、六出。”[4]P122既然是在皇后的生日宴会上请戏班前来演出《西厢记》,那么宫廷女性可能为其受众。
第二种途径便是家班演出。明朝有蓄养家班或宴请之时请戏班演出的风气,米万钟家班以演出《西厢记》见长,又以武戏著称。而热衷于串戏的也有很多,如《玉华堂日记》里就记载了万历年间潘允端在有家班的情况下仍然要同家人一道扮戏娱乐。另外,崇祯时期的包耕农曾经与家人合演《西厢记》。由此可见,家班并不完全避讳女子,有时甚至是一种合家娱乐的活动。既有家班,《西厢记》又被排演,由此推测,士大夫阶层的女眷可能接受到舞台演出版本的《西厢记》。
(二)对女性接受者的影响
《西厢记》引起了上层女性的情感共鸣。叶纨纨是叶小鸾的姐姐,也是叶绍袁的女儿,生于文人家庭,也配得一段门当户对的姻缘,但笔下的诗词却被“愁”字笼罩,年仅23岁便香消玉殒。亲友将其归咎于不幸的婚姻生活,而她的父亲直指七年婚姻有名无实:“汝以七年空名,目愁心事。”[5]P116叶纨纨自小便在诗词歌赋的熏陶中成长,这样的环境赋予了她敏感细腻的心性。《西厢记》《牡丹亭》等作品对于爱情的描写太过于理想,家中又有姐妹相互分享感悟,使她对于婚姻抱有过高的期望,但有名无实的婚姻生活却并不如意。而叶纨纨因为从小深受女德教育,即使婚姻生活不如人意,也选择忍耐,除了用手中的笔来排解心中的苦闷,再无他法。长此以往,对于美好爱情和幸福婚姻的向往与冰冷的现实差距过大,便失去了生的希望。
自然,彼时的门当户对是避免遇人不淑的好方法,同为精英阶层,能规避大部分的婚姻风险,但婚姻终究不是简单的阶层匹配,更多的是两颗心灵的契合。因此,即便是身处社会上层,许多人也难逃“盲婚哑嫁”的宿命风险。上层女性养在深闺,她们内心的情感和精神需求便显得尤为重要,而《西厢记》这类戏曲作品,让她们在虚幻的世界里寻找到了情感的出口。当这些深闺女子为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而感动时,她们或许也在默默期盼着自己的未来能够如此美好。然而,现实往往与理想背道而驰,当现实的惨淡和戏文中的团圆同时出现在面前时,那种巨大的落差感让她们难以接受,精神的象牙塔也就随之崩溃。
二、《西厢记》的下层女性接受者研究
(一)接受途径
除有着先天优势的上层女性外,下层社会中也有接收到文本的女性。邹枢《十美词纪》中《如意》一节记载母亲为自己买了一个婢子,一年之后如是说:“余偶于书中得《西厢》,有红硃评点。余笥中有《花间集》,亦以朱笔批阅。余疑此处更无人到,出自谁手?乃呼女问之。女笑不答。”[6]P23《西厢记》的评点便是买来的婢女所作,但因为后来母亲发现诗词之作,该女子被遣作他人妾,没有留下《西厢记》评点的文字记录,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惋惜的结局。
明末刘丽华题词王实甫的《西厢记》很幸运地被记录下来。刘丽华为南直隶应天府的金陵富乐院市妓,富乐院是市妓的集中地。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使商人的地位提高。在当时纵欲享乐的社会风气下,不仅是富乐院这种官营场所,社会上的名妓也大多都是才貌双全,熟读诗书,颇有文采。富乐院原本就是地方乐户的转变之所,市妓所习技艺多为戏曲,刘丽华自身所处南京,更能接触到《西厢记》这类书籍,说不定也曾经出演。只可惜据文献记载明中后期只此一例《西厢记》的下层女性戏曲评点。
第二种途径便是舞台演出。据何璧《西厢记序》记载:“自王侯士农而商贾皂隶,岂有不知乎?然一登场,即耄耋妇孺,痦瞽疲癃皆能拍掌……”[7]P12《西厢记》在民间的吸引力可见一斑。广大下层女性接触戏曲的方式主要是观看演出,而演出的场合又主要有三种:迎神赛会、四时节庆及婚嫁丧葬。迎神赛会多出现在神庙舞台,多为宗教信仰或民间风俗,例如李日华记三月三日秀水濮院镇迎神时,市中景象是“远近士女走集,一国若狂”[8]P98。由此可见,在神庙之类的场合中有女性观看演出。四时节庆多由官方举行,也属于公共观演的范畴,对观众不做限制。
(二)对于女性接受者的影响
下层女性大部分将观看演出作为娱乐消遣的方式,而《西厢记》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引起广大妇女强烈的情感共鸣,以至于传统的卫道士们见《西厢记》如临大敌。
“至于妇女,未尝读书,一睹传奇,必信为实,见戏台乐事,则粲然笑,见戏台悲者,辄泫然泣下,得非有感于衷乎?”[9]P301
在《西厢记》的舞台上,那些熠熠生辉的女性形象与寻常下层女性的生活轨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们被束缚在家庭的方寸之地,不仅仅是家中琐碎事务的管理者,更是家庭的支柱,扛起了生活的重担。而《西厢记》中的女性角色,仿佛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古代女性内心深处的渴望与挣扎。中国的戏曲,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想象的舞台。当这些女性形象在戏台上展现爱恨情仇时,下层女性会代入崔莺莺的情感,跟随着她的悲喜起伏,感受那份来自心底的共鸣。
除此之外,前文所提及的女性戏曲评点者刘丽华所代表的则是地位更为低下的女性对于爱情的向往。
“长君曾示余崔氏墓文,乃知崔氏卒屈为郑妇,又不书郑讳氏,意张之高情雅致,非郑可骖明矣。崔业已委身,恐亦未必无悔。迨张之诡计以求见,此其宛转慕态,有足悲者,而崔乃谢绝之,竟不为出,又何其忍情若是耶?不然,岂甘真心事郑哉?彼盖深于怨者也。董解元、关汉卿辈,尽反其事,为《西厢》传奇,大抵写万古不平之愤,亦发明崔氏本情,非果忘张生者耳。”[10]P671
刘丽华本是娼妓,身处烟花之地,内心却渴望着像崔莺莺那样真挚、纯洁、勇敢的爱情,然而现实生活却并不允许。也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在了解崔莺莺被创作的形象及真实状况之后,更能触动她与崔莺莺的共鸣,于是用笔将崔莺莺的内心想法描绘出来。既已做他人妇,便是事实无法改变,可内心却未必不曾后悔,而拒绝张生的求见,则是因为无法接受看到希望又毁灭,无法接受眼看着心爱之人却只能遥遥相望。刘丽华对于崔莺莺的解读可谓是细致入微,她不仅理解崔莺莺内心的挣扎与痛苦,更体会到了崔莺莺那份对真爱的执着与勇敢。
刘丽华不仅能看到女性形象的内心活动,在以男性文化为主的桎梏中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事实上,崔莺莺最开始被男性塑造的形象便是“尤物”“妖孽”,元稹心安理得地以此作为自己负心的借口。这表明,女性已经意识到了,在男性为掌权者的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形象并非真实写照,而是男性文人根据自身的想象所塑造的。刘丽华的题词,不仅是对男性文人笔下女性形象的不满,意图反抗男性文人对于女性形象的任意塑造,更是女性性别意识的萌动,对于男性文人这一举动的质疑就是对于男性话语权的挑战,是女性自身价值和尊严意识的觉醒。
三、女性接受的局限性
不得不说的是,在《西厢记》的接受过程中,教育是不可避免的一环。下层社会的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少之又少,接触《西厢记》的机会几乎只有通过舞台表演。接受过教育的名妓碍于身份,更容易产生不一样的感情。上层女性所受的教育更多是女德和诗词歌赋,诗词歌赋又最容易催发对男女之情的浪漫想象,时人评价王实甫是写爱情的大家。在《西厢记》出现之后,女性更多的是对于作品的认同和情感的代入,而此时的女性意识还处在朦胧阶段,这就导致婚姻与爱情不可兼得的困境,也造就了更多如同叶纨纨、叶小鸾一样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生。并且无论是属于哪个阶层的女性,对于《西厢记》的接受都只集中在情感层面,没有一个完整的评价体系,对于戏曲理论评点方面是缺失的。
而《西厢记》归根结底是男性所创造的作品,崔莺莺形象历年来的改变几乎都是贴合每一个时代的男性对于女性的构想。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崔莺莺这个形象在其中的存在感并没有杜丽娘那么强,她的形象并不真实立体,而且不算是绝对的女主角,更像是男主生活中的配角,对于女性的描写并不突出,并且大部分的戏份也是依附于男性的,也因此对于女性意识的崛起并没有很强的动力,仅仅起到了萌发的作用。从女性接受的角度来说,如杜丽娘一般至情至性的角色更能唤起女性意识的觉醒,而崔莺莺总是差了那么一点,所以这也是作品角色本身的一种局限性。
参考文献:
[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填词名手”)》,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2]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2004年版
[3]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4]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
[5]邹弢:《三借庐笔谈(卷八·三“优癖”)》,上海:上海进步书局
[6]虫天子:《中国香艳全书(第1册)》,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
[7]王实甫著,何璧校:《何璧校本北西厢记》,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
[8]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二)》,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9]汤来贺:《梨园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卷七)》,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
[10]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卷6)》,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
责任编辑 姜艺艺 王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