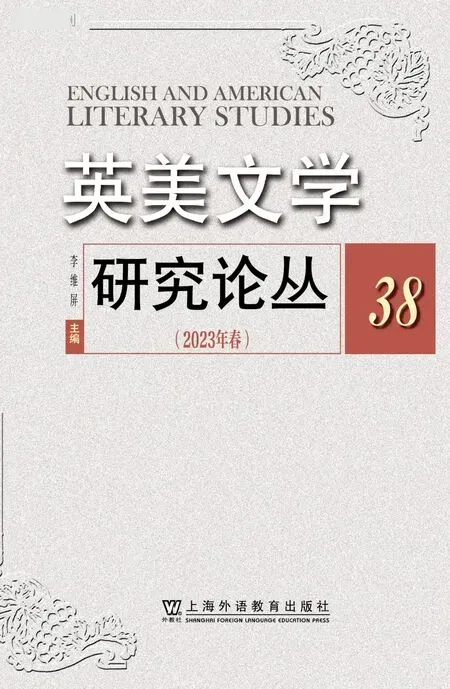论查尔斯·赖特“重彼岸、善超验”的诗歌艺术*
甘 婷
内容提要: 美国桂冠诗人查尔斯·赖特的诗歌存在大量以基督教教义为主题、以基督元素为铺垫的作品,其诗歌的灵性与神性受到评论家的广泛关注。但赖特一方面承认“神性及神性之冥思”是其诗歌重要的主题,另一方面又否认自己是虔诚的基督徒,并撇清其诗歌创作具有传教目的。本文围绕赖特在诗歌创作中展现的对基督教教义的核心问题“受难-复活”“罪与原罪”“死亡意义”的探寻,从“徘徊的信仰”“怀疑的忏悔”“死亡的超验”三个维度来勾勒他“重彼岸、善超验”的诗歌图景,从而印证他将诗歌艺术化身为与上帝沟通的桥梁、灵魂建构的工具的诗学理念。
桂冠诗人查尔斯·赖特(Charles Wright,1935—)被认为是美国现代诗歌领域中最重要的诗人之一(Giannelli xi)。他的诗歌常给人留下灵性冥思的印象。多年潜心研究赖特诗歌的大卫·杨(David Young)曾惊诧“无论有多少评论家以何种不同的角度、以何其精妙的论据分析赖特的诗歌,其浓郁的宗教色彩是大家共同关注的重点”(Wright&Young 1995:122)。不过,悖谬的是,赖特本人一方面承认他的诗歌创作充满“神性”基调:“我在宗教氛围中成长,所以我(诗歌)的参考点、我的语言触点都是基督教式的”(同上);另一方面,他坚决否认其创作具有传教目的,坚称“与其说宗教是他诗歌艺术的燃点,不如说是它的光环”(同上),甚至质疑基督教信仰:“你们知道的,我不是一个传教士。我既不确定,也不信服。我一直在追问,一直在探寻。我所有的断言都是问题式的”(同上125)。为什么赖特在诗歌创作中热衷于宗教主题却又撇清传教目的?赖特笼罩着团团宗教迷雾、袅袅灵性冥思的作品究竟展现了什么样的诗歌艺术?这样的诗歌艺术又反映了他什么样的诗学理念?我们将从赖特诗歌中呈现的“徘徊的信仰”“怀疑的忏悔”“死亡的超验”三个维度来勾勒他“重彼岸、善超验”的诗歌图景。
一、徘徊的信仰
查尔斯·赖特具有深厚的基督教背景——他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自小就被父母送到教会学校接受教育:1948—1950年,赖特在“天空谷”教会学校(Sky Valley School)学习;此后,赖特又被送到另一所名为“基督学校”(Christ School)的圣公会寄宿学校完成高中学业(Friebert et al.279)。成年后赖特还曾担任圣公会的教士助手。在这样丰富的宗教经验浸润之下,赖特的作品蕴藏着各式各样的宗教元素: 既有欧洲著名教堂的再现,如《致敬埃兹拉·庞德》(“Homage to Ezra Pound”,1973)中的圣塞巴斯蒂安教堂①圣塞巴斯蒂安教堂(Saint Sebastiano)是意大利米兰市中心一座晚期的文艺复兴风格的教堂。、《奥斯卡·王尔德在圣明尼亚托教堂》(“Oscar Wilde at San Miniato”,1973)中的圣明尼亚托教堂;也有宗教节日书写,如《链接链》(“Link Chain”,1975)中的圣枝主日(Palm Sunday)①圣枝主日是基督教节日,指复活节前的星期日。棕榈叶在西方文化象征着胜利,该节日为纪念耶稣基督胜利进入耶路撒冷,人们在路上撒上棕榈叶以纪念这一功绩。、《复活节,1974年》(“Easter,1974”,1975)和《升天节》(“Holy Thursday”,1981)中的复活节、升天节等;更有许多宗教主题的诗歌不胜枚举。不过,赖特在诗歌中展现的并非虔诚的信仰,而是真实地再现信仰道路上的困惑与徘徊。《升天节》再现诗人围绕“受难-复活”为冥想主题的踟蹰就是典型例子。该诗共有五节,第一节通过互文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的同名诗歌《升天节》直入主题:
哀鸽开始咕呜咕呜啼叫
胡椒木上,断裂
山丘顶闪过一道蓝色而分离的光,
我独自穿过南瓜花丛来到圆盘形的田野,
布莱克的孩子们仍蜷缩着身子睡觉,一团
噩梦与来世。
圣歌如潮水般从滴血的心中涌出。
大教堂在水雾中若隐若现。
我磨蹭着光滑的土坯,一只眼
惊奇地探索,一只眼盯着结果。②本文中所引查尔斯·赖特的诗歌皆为本文作者自译。(Wright 1990a:14)
“升天节”又称“神圣星期四”,是新教教派之一英国国教(安立甘宗)庆祝耶稣升天的日子。布莱克曾创作两首《升天节》的同名诗歌,分别收入在诗集《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1789)和《经验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1794)中。《经验之歌》中的《升天节》以升天节里孤儿悲痛的口吻描绘了一个充斥着贫困、疾病和战争的世界:
这是神圣事情一桩?
本来富庶的土地上,
婴儿陷入悲惨境况,
竟让那冰冷的放高利贷的双手喂养?
那颤抖哭喊可称之乐章?
那能变成欢乐之歌?
成千上万的孩子陷入饥荒?
那原来是个贫瘠的地方!
他们的太阳永远不会发光。
他们的田野遍地荒凉。
他们的道路荆棘丛生。
那里的天气是永恒的寒冬。
因为只要哪里有阳光普照
只要哪里会降下甘霖:
婴孩不再饥肠辘辘
贫穷也不会威吓心灵。①该诗翻译参考了杨苡翻译的《天真与经验之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和“爱吾词诗”网站的翻译〈https://www.52shici.com/posts.php?clearlocalStorage=57703&id=276862〉。
再来看收入布莱克另一本诗集《天真之歌》中的《升天节》。尽管布莱克在这首《升天节》描绘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但他依然以升天节中的孩童的衣着、行为、生存状况等作为诗歌的主要刻写对象:
升天节天真的孩子们洗净了脸庞
他们都两人一排穿着鲜艳的服装,
前面走着灰发执事拿着雪白手杖,
河水般的长队走向保罗穹顶教堂,
伦敦城的花儿遍地开放斗艳争芳!
相互簇拥在一起焕发出迷人容光。
那里所有的众人都是上帝的羔羊,
数千的孩子将虔诚的双手伸向上方。
洪荒之力将赞美的歌声送上天堂,
抑或是震动天椅的和谐雷声轰响,
上面端坐的智慧老人是穷人保障,
珍惜怜悯以免在门前把天使错伤。②同上。赖特在他的《升天节》中以“布莱克的孩子们仍蜷缩着身子睡觉”互文布莱克的两首经典同名诗歌。布莱克笔下的孩子们一方面在现实的世界中“陷入悲惨境况”“让那冰冷的放高利贷的双手”喂养;另一方面却在信仰的世界中穿戴“鲜艳的服装”整齐地走向“保罗穹顶教堂”,并使用“洪荒之力将赞美的歌声送上天堂”。布莱克通过将“孩子们”悲惨凄苦的现实世界与“体面美好”的信仰世界强烈对比,表达他对基督教控制的精神世界的质疑和批判。赖特在他的同名诗《升天节》中借用“布莱克的孩子们”,并指出他们“仍蜷缩着身子睡觉”,说明他与布莱克的信仰认知一致。他强调纵使孩子们“将虔诚的双手伸向上方(的上帝)”,纵使历史的车轮已碾过布莱克的时代,今天升天节里的孩子们依然贫穷得需要蜷缩着身子睡觉。“噩梦与来世”似乎是诗人喃喃自语的感叹,也再次呼应布莱克对现实与信仰的理解与诠释。如果“噩梦”是布莱克描绘的“孩子们”生存的凄惨世界,那么“来世”是基督教信仰指引我们摆脱痛苦的出路。问题是,赖特是否完全相信基督教的“来世”论呢?赖特以徘徊与迟疑来回答。“圣歌如潮水般从滴血的心中涌出”再次与布莱克的“洪荒之力将赞美的歌声送上天堂”互文,形象地刻画了基督徒忍受着现实的残酷,虔诚地仰赖上帝恩典的形象。因为无论是布莱克诗中的“洪荒之力”还是赖特文本中的潮水般的圣歌应该都是人们向上帝展现的“善功”,但“大教堂在水雾中若隐若现”却暗示赖特对上帝的恩宠能否降临、来世能否获得救赎的困惑,而这也恰恰是“滴血的心”形成的原因。“我磨蹭着光滑的土坯”,“磨蹭”(scuff)——“用双脚来回蹭地的动作”凸显赖特迟疑、犹豫的内心,最终诗人一边继续神性的追索——“一只眼惊奇地探索”;一边静待恩宠的降临——“一只眼盯着结果”。从这后两句诗可见赖特的宗教观远不如布莱克决绝。该诗的第二节以自白的口吻进一步为信仰的徘徊寻找出路:
总有生锈的时候,
为了俯瞰大地和这横链。总有长草的时候,遍布
四周的四角形紫色小花,
光芒四射地装扮着。
总有沾染灰尘的时候。
缓一缓,缓一缓,苍蝇嗡嗡,它们的翅膀
在玉米丝上越来越炽热。
无可回应,四只乌鸦
立在桉树的枝干上,以舌言语。
它们也无以回应。(Wright 1990a:14)
三个排比“总有生锈的时候”“总有长草的时候”“总有沾染灰尘的时候”,以自然界的基本规律比拟信仰上的犹疑与反复。这似乎是诗人的自我宽慰,或许在赖特看来,尽管清教徒强调信仰上的虔诚,但虔诚并不意味着不假思索的笃定。赖特用“生锈、长草、沾染灰尘”等这些自然现象说明身为自然人的清教徒对基督信仰产生困惑与疑虑是自然规律。赖特进而得出“缓一缓,缓一缓”的结论,即使“无可回应”甚至“无以回应”在诗人看来也是可以宽容的。该诗的最后一节再次回归“复活-救赎”的主题:
棕榈树上海浪的声音,
沙沙声,风
从西部大肆而来,
孩子们又睡着了,他们的第二个自我
开始骚动,月亮
倾斜着,他们的梯子滑倒了。
从翻滚的死尸下,从他们湿漉漉的双手和救赎的恩典,
孩子们开始移动,角度磷光闪闪
沿着山脊。
天使们
数着节奏,他们那空洞的歌曲啊
赞美诗说了什么,第一页和最后一页。(同上15)
“孩子们又睡着了”与诗首节“布莱克的孩子们仍蜷缩着身子睡觉”呼应。但这里的“睡着”却不单指物理睡眠,因为从下文“第二个自我”“翻滚的死尸”“救赎的恩典”等词互相关照来看,“睡着”还含有死亡的意义。孩子们从苦难的深渊——“翻滚的死尸下”“湿漉漉的双手”在救赎恩典中开始缓慢移动,这似乎预示着孩子们正等待着走向天国。但他们真的能重生并走向幸福吗?诗歌的最后两行诗“天使们数着节奏,他们那空洞的歌曲啊”、完全不知赞美诗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说了什么,暴露了诗人对基督教“复活-救赎”说的质疑——“空洞”直接揭露高唱圣歌的意义是值得商榷的;“布莱克的孩子们”是否真能获得救赎也是值得怀疑的。统观全诗,赖特的信仰经历了从“怀疑-宽慰-判定”的过程。围绕着基督教教义中极为重要的“受难-复活”主题,一位在信仰中“迟疑-释然-接受”的清教徒形象逐渐清晰。或许这正是赖特否认“传教士”身份的原因,因为他所展示的不是信仰中的虔诚与笃定,而是信仰中的踟蹰与接受。
二、怀疑的忏悔
围绕“受难-复活”主题,赖特还在《复活节,1974年》《晨曲》(“Aubade”,1970)等多首诗歌中从不同的角度冥想与吟唱。不过,他对“彼岸世界”的迷恋还表现在他对基督教教义其他一些基本问题的探究上。他对“罪与原罪”的诠释秉持着一种“追寻问题”式的怀疑精神。追溯基督教“罪”的概念史,“罪”说诞生于基督教母体教派犹太教。犹太教的宗教经典《旧约》记载了世人耳熟能详的罪罚故事: 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被蛇诱惑,违背神的旨意偷食禁果。不过在犹太民族中,尚未将始祖的犯罪故事升华为深重的“原罪”意识,直到基督教才将“原罪”观与“受难-复活”的赎罪意识统一起来。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人们此生此岸实现不了的幸福可在天国实现于复活的灵魂中。但人类因祖先犯下“原罪”,并不具备上天国的资格。耶稣基督通过“受难而死”承担“原罪”打通了选民通往天国的道路,而要成为上帝的选民,就必须虔诚地信仰上帝、信仰基督才有可能蒙获圣恩,接受上帝的拣选。正如学者赵林总结的“在基督教神学中,‘救赎’与‘原罪’构成了一对最基本的辩证范畴——基督向死而生的整个过程无非是为了完成对亚当所犯‘原罪’的‘救赎’”(赵林57)。“罪”(sin)作为基督神学的基本概念以诗歌元素或诗歌意象出现在赖特的诗歌作品中并不鲜见。不过,要论能集中阐释赖特独特“罪观”的诗歌应属《2035年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in 2035”,1977)和《罪说》(“Peccatology”,2000)。《2035年的自画像》全诗如下:
他化身为根,路碾出车辙
那是细粉光下的筛子和谷物
重铸他,下沉他的骨架,
毛毯,爬起来,还好,还好:
虫粪和枕虱;头发
他的胳膊刺痛,黑色鞋子灰尘扑扑
无链无边,模糊不清的他的脸
朽木中,过去暂停……
黑暗,抹去这些线条,遗忘这些文字。
蜘蛛记诵他的一宗罪。(Wright 1982b:113)
该诗开篇勾勒100年后长眠于地下的“他”。第一、二小节的重点描绘生命的物理消亡:“他”的头发沾满“虫粪和枕虱”,肢体一点点腐化——“胳膊刺痛,(随葬的)黑色鞋子灰尘扑扑”,骨架不断下沉,脸也变得模糊不清。不过,肢体腐化正是一种大自然的有机化,所以诗歌尽管描述的是死亡,却没有营造阴森恐怖或悲观消极的氛围。第一句“他化身为根”(“The root becomes him”)中“变成”(“become”)是双关语。一方面树根蔓延占据了诗人的墓穴;另一方面,他“化身为根”是生命的复归。所以“变成”这个词,既可能是树根变成“他”、也可能是“他”变成“树根”。这与下文中“还好,还好”呼应——尽管肉体消亡,但生命以另一种样态复现不禁令人发出“还好”的感慨。最后两句为全诗的诗眼: 即使黑暗抹去这些线条,遗忘这些文字,蜘蛛仍记诵他的一宗罪。“黑暗抹去线条”互文首句“路碾出车辙”;“遗忘这些文字”与“过去暂停”互相关照。死亡分为物理性死亡和社会性死亡,通常社会性死亡才被认为是绝对死亡。那么,什么是社会性死亡呢?社会性死亡简而言之是指任何有关此生命的相关记忆、记录都消失殆尽,比如记得此人的亲友也死亡,世上再没有人记得你的名字,这就是社会性的绝对死亡。如果说前两节诗描绘的是诗人的物理性死亡,那么,最后一节诗描绘的正是社会性的绝对死亡。但即使生命达到绝对死亡的状态,“蜘蛛记诵他的一宗罪”却不能灭亡。蜘蛛记诵的是什么罪呢?为什么是蜘蛛记诵的罪呢?尼采曾在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1883—1885)中描述过“毒蜘蛛”。该文“毒蜘蛛”的隐喻闪现着上帝的影子。尼采眼中的毒蜘蛛比喻“灵魂眩晕之人”“平等的说教者”“最好的世界之诋毁者与异教徒之焚烧者”(尼采176—180)。他还将毒蜘蛛的洞穴所在之地描述为“高高耸起一片古代神庙的废墟”(同上)。显而易见蜘蛛记诵的“罪”内涵基督教的“原罪”。赖特正是借用尼采“蜘蛛-上帝”的意象: 即使长眠于地下,肉体消亡重归自然,上帝却永远记得他的这一宗罪,并世世代代传承下去。那么赖特在这首诗中呈现的原罪观是怎样的呢?如果说他像尼采一样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他却将“毒蜘蛛”替换成“蜘蛛”;如果说他完全信仰“原罪”论,他选择“记诵”(recite)这个词又带有鲜明的讽刺意味。“记诵”这个词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辞典》中有两个释义: 一是“在记忆的基础上的大声朗读(尤指向听众)”、二是“列举”(霍恩比1245)。无论用哪一层意思去诠释上帝“记诵”原罪的行为,都颠覆了上帝“全知全能全善”的形象。因为,“全知”的上帝何须记忆“原罪”?“全能”的上帝又何必(向信徒) “列举”“原罪”?上帝以“原罪”为条件施与的恩典和爱又可称为“全善”么?“记诵”这个动词暗含着赖特对基督教原罪意识的嘲弄。可见,赖特的“原罪”观裹挟着浓郁的怀疑色彩。
或许正因为赖特对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存有疑虑,他在《罪说》这首诗中再提及“罪”时,“罪”的含义就更加立体和丰富:
正如卡夫卡告诉我们的,
罪总是堂而皇之地出现:
它随根移动,不必连根拔起。
它是多么容易在感官上消逝,
然而,印第安的夏天①“印第安的夏天”是用来描述加拿大与美国的交界处,魁北克和安大略南边,一种很特别的天气现象。这种天气发生在深秋时节,冬天来临之前忽然回暖,宛若回到温暖的夏天。,
常春藤树篱的星脚
踩踏着死去的云杉和铁杉刺,
那落叶到最后就像燃烧的煤块
远远地堆积在院子的角落,
阿拉伯数字排列的蝗虫豆荚,从右到左。
它变得多小的一个东西啊!神经紧绷
一半充满刺激,
一半被根除,快乐满满。(Wright 2000:42)
《罪说》开篇就互文卡夫卡之“罪”,因此,要理解《罪说》中“罪”的内涵,首先要厘清卡夫卡认知体系中“罪”的内涵。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是一位罪感意识极强的作家,他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日常生活中都渗透着浓浓的罪恶意识,甚至可以说“我有罪”就是卡夫卡的人生格言。概括而言,卡夫卡的“有罪”观不仅指“原罪”,还囊括日常生活中的罪感。他曾在随笔中对“罪”与“原罪”做过详细地阐述:“我们为什么要为原罪而抱怨?不是由于它的缘故我们被逐出了天堂,而是由于我们没有吃到生命之树的果子所致。我们之所以有罪,不仅是由于我们吃了知识之树的果子,而且也由于我们还没有吃生命之树的果子。有罪的是我们所处的境况,与罪过无关”(11)。卡夫卡所谓的“有罪的是我们所处的境况”是指什么呢?谢春平等认为“在原罪大背景下产生的现代人之罪,是在现代社会法权系统中产生的现代人之罪。卡夫卡之罪是法权系统强加于现代人身上的莫名之罪,是处于法权系统中的现代人因‘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而给自己带来的罪,是弱者面对强大的法权系统产生的恐惧不安心理衍生而来的悖谬之罪”(20—21)。本文认为赖特开篇提及卡夫卡之“罪”正是借用其丰富内涵。首句罪“堂而皇之”(openly)地出现,“openly”这个词的词义是不隐藏、明目张胆。什么“罪”可以毫不隐藏、堂而皇之地出现呢?能毫不隐藏的罪只能是人人皆有之罪,因为只有每个人都有,才不需要隐藏。那么什么罪是人人皆有呢?那只能是基督教世界中人与生俱来的“原罪”。接着,赖特将“罪”比喻为“可随根移动却不必连根拔起”的植物,再次强调原罪伴随人一生的状态。诗歌的第二节,“它是多么容易在感官上消逝”说明在日常生活中,原罪带来的忏悔之感并不是那么牢固。接着赖特以一系列的自然意象隐喻生命的周而复始:“印第安的夏天”“常春藤树篱的星脚”“云杉和铁杉刺”“蝗虫豆荚”。为什么“常春藤树篱的星脚”会踩踏死去的云杉和铁杉刺?认真观察常春藤的植物特性发现常春藤的根形似星星,因此所谓的“星脚”指代常春藤的根;而显然“踩踏”(treading)这个动词生动再现常春藤树根的生长替代死去的云杉和铁杉刺,从一个侧面刻写了生命的传承与生生不息。在这样的生命延续中,最后一诗节发出这样的感慨:“它变得多小的一个东西啊!”——在绵绵不绝的生命反衬下“原罪”的意义被缩小了。原来总让人神经紧绷的“罪”感,一半被根除,一半充满刺激,却让人“快乐满满”。可见,赖特的“罪”观,既没有完全否定基督教世界对“原罪”认定,但又怀疑它被过于强调了。概而言之,赖特的“罪”观是在怀疑中的忏悔。
三、“死亡”的超验
其实,无论是徘徊的信仰还是怀疑的忏悔都说明赖特深深地依恋彼岸世界,因为这种“徘徊”与“怀疑”恰恰说明他一直走在探寻“神性”的路上。不过,诗歌艺术之于赖特来说,不仅是构建信仰的殿堂,更是安放灵魂的家园,因为在他的诗歌艺术中,诗歌不仅是诗人与上帝沟通的桥梁,更是将俗世经验赋予超验深意的工具,而这集中体现在他通过赋予死亡以积极意义来实践死亡的超验。以《致敬保罗·塞尚》(“Homage to Paul Cézanne”,1981)为例,该诗的前半部分是从被动的角度把握死亡的意义,比如通过赋予死者以生者的行为动作和情感思维来打破生死区隔,以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的绘画技巧来借喻多维度的死亡存在的形式和空间。但是,所有这些对“死亡”的理解与感受都是“死亡”作为客体的认知,即完成“死亡”是什么、“死亡”在哪里、“死亡”以什么形式存在等问题的追问,却没有回答“死亡”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功能。如果说“死亡”是什么、“死亡”在哪里、“死亡”以什么形式存在是站在生者的角度来理解“死亡”,那么反过来“死亡”之于生者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呢?这是赖特在该诗后半部分试图探索的问题。且看第五章从细微的日常琐事着手:
他们随身携带他们的彩色线团和一篮子丝缎
为我们缝补衣裳,让我们看着得体,
修改,缝合,更换纽扣,补齐一个裂口。
他们就像我们宽松袖口里平躺的褶皱,他们将我们紧紧聚拢。
(Wright 1990b:7)
赖特运用“缝补”衣服这件日常生活中最平常不过的小事来隐喻死者对生者的影响。在赖特的描述中,“死者”不仅像至亲长辈一样对生者充满慈爱和关切——为了“让我们看着得体”甚至随身携带“彩色线团”和“一篮子丝缎”来为“我们缝补衣裳”,而且还能像“宽松袖口平躺的褶皱”将“我们紧紧聚拢”。缝补衣裳是一件日常小事,但诗歌却令缝补衣裳这件小事不容小觑,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得体与否”。缝补这个动作本身暗含“补救”“修补”之意,诗人借“缝补衣裳”这个意象说明“死亡”之于生者的价值恰恰在于能让生者反思、修正、整改与弥补。《旧唐书·魏徵传》记载了一个典故: 直言敢谏的重臣魏征病死之后,唐太宗非常难过,他流着眼泪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赖特在此处运用缝补衣裳的隐喻与唐太宗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死亡”的经验能为生存带来反观的功效。如果从死亡的角度看待生命,我们的确是更能明白生命的缺口与裂缝,更能了解如何缝补生命的遗失与缺憾,更能体味死亡之于生命的意义。此外,“宽松袖口平躺的褶皱”将“我们紧紧聚拢”则演绎死亡与生存的另一重关系。第三诗章中,“死者”害怕被生者遗忘,一遍又一遍讲述自己的故事,似乎二者的关系完全取决于生者;但其实“死亡”对生者的关系也有能动作用——它能将生者凝聚。有些读者可能会产生疑问: 死者的生命已终结,他们又怎么能够帮助生者凝聚?认真回顾历史经验,才恍然大悟赖特捕捉到生命的深层次含义: 比如,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可能会在一位长辈的葬礼上重聚;仇恨已久的死敌可能会因共同在乎的生命逝去而和解;涣散蒙昧的民族可能会因一位民族英雄的牺牲而凝聚开化。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并不鲜见,只是我们经常遗忘了“死亡”并不只代表生命的终结,它也有让生命重聚的力量。
当然,诗人并不满足于“死亡”之于世俗生活的能动作用,他还将“死亡”的功能延展到灵肉分离的世界,且看该诗第六章:
他们经常会向下伸出一只手,
或说些话,将我们的身体解放出来加入他们(的世界)。
在床上我们回忆另一个自己。(同上)
诗歌多次呈现死者位于生者的上方,他们总是“向下”伸出手来。从方位上看,“死者”的位置与地狱相较更似在天堂,而且打破了前文附属的、被动的角色地位。“他们”向下伸出一双手或用一些言语“将我们的身体解放”。身体为什么要解放?它被什么禁锢了呢?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西方经典哲学史中去寻找答案。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最早提出的二元论论述的就是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只不过在二者关系中柏拉图强调灵魂主导支配肉体,而肉体对灵魂的发展作用是消极的,人的堕落恰是肉体的欲望超越了理性灵魂的外在表现。柏拉图认为“如果我们想获得关于某事物的纯粹知识,我们就必须摆脱肉体”(柏拉图64)。在西方经典哲学体系中,灵魂的本质是理性的、思维的,而肉身则是追寻真理、知识与智慧的障碍与桎梏。基督教中也大量“使用”肉体一词,但基督教中的肉体与柏拉图的“肉体”相较则更具有罪恶本源的能动性。圣经《罗马书》7章14节中记载“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新旧约全书》174);8章3—4节说,神“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同上)。可见,不管是柏拉图的二元论还是基督教的身体观,都一脉相承地对身体持否定态度,如此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在西方传统文化浸染中成长的诗人赖特“将我们的身体解放”的愿望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柏拉图二元论中战胜肉体的是人的理性灵魂,基督教的世界里能够帮助我们摆脱肉体束缚的是神性,而在这首诗歌中将“我们身体解放”的是死者——“他”伸出的双手、“他”的言语能够拯救被禁锢在生者身体里的(灵魂),即生者通过死者看到了另一个不受约束的自己。我们不能确定“死亡”是不是具有几乎等同于“上帝”的功能,但我们感受到赖特强烈的追寻死亡超验意义的热忱。赖特本人接受卡罗尔·埃利斯(Carol Ellis)专访时也强调:“死亡是我能想到的最可接触的抽象之物,大部分的人知道死亡的物理意义,但如果你读了(这首)诗歌你就能理解它的超验含义”(Wright 1988b:155)。总之,赖特探索死亡的超验意义说明: 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与生对应的存在。赖特探寻“死亡”超验意义归根到底是对“未知死,焉知生”的回答。
结语
20世纪美国实用主义大潮风起云涌,接受西方正统智识教育的赖特也卷进了基督教与世俗主义的论争大潮,他的宗教观不可避免地受到“上帝已死”或“主体消亡”思想的影响。这或许是为什么赖特一直以神性的冥思作为创作主题,却又总显露出不完全信服的宗教思想。赖特诗歌作品折射出来的“徘徊的信仰”“怀疑的忏悔”和“死亡的超验”再现了一名清教徒在信仰中真实的状态——既有热切的期盼、耐心的等待,更有间或的迟疑、困惑和迷茫。赖特“重彼岸、善超验”的诗歌艺术源于他一贯坚持的诗学理念,因为他一直坚信“诗歌真正的意图是神性的沉思及对神性之神秘的探寻”(Wright 1988a: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