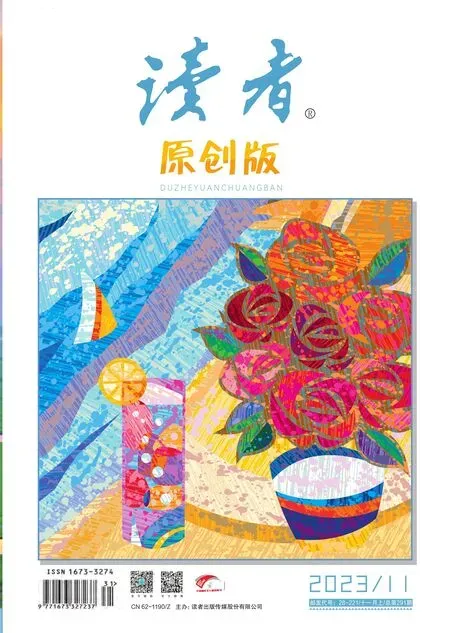轻轻读,苏武的那首诗
文 | 樊晓敏

一
先读一下这首诗吧。
结发为夫妻,
恩爱两不疑。
欢娱在今夕,
嬿婉及良时。
征夫怀远路,
起视夜何其?
参辰皆已没,
去去从此辞。
行役在战场,
相见未有期。
握手一长叹,
泪为生别滋。
努力爱春华,
莫忘欢乐时。
生当复来归,
死当长相思。
据说,这首柔肠百转的诗是苏武在临行前写给妻子的。
初读这首诗时,是有一点儿震动的—这不是我们印象中那个绝烈刚直的大丈夫苏武,这是一个忧伤深情的丈夫在告别和宽慰自己深爱的妻子。
但据考证,这首诗是后人托苏武之名的伪作。
在班固的《汉书》中,我们丝毫看不到这样的苏武。
我们熟知的是,到匈奴部落后,因属下张胜卷入匈奴内讧,苏武受到牵连,不愿蒙羞的他拔剑自杀,两次求死不成后,迎来的是长达十九年的折磨。
在匈奴的十九年,苏武先是被置于冷湿的地窖,靠吞吃雪和毡毛才活下来,后被放逐到荒凉苦寒的北海放羊。饥寒交迫时,他掘开野鼠窝,“抢劫”野鼠所藏籽果。
苍茫无边的北国,陪伴他的只有羊群、野鼠、头顶零星的飞鸟和手中旌旄脱落的汉节。
但最大的考验还不是这些。差不多十年过去,他迎来一位旧友:李陵。那个因寡不敌众被匈奴所俘,司马迁为之辩护而下狱的李陵;那个因武帝误听俘虏之言,全家被杀的李陵;那个在匈奴做了高官的李陵。
李陵的话字字锥心。
李陵对他说:“你的兄弟均因为小过错触犯了汉法而被迫自杀,你的母亲已去世,你的妻子也改嫁了。人生如朝露,你又何必这样固执?”
史书上,苏武答道:“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无复再言。”
每每读到这段话,总被这种凛然和坚定感动;但同时也常常在想,史书中没有记录的是什么?比如听到兄弟、母亲去世时的悲伤,比如听到妻子改嫁时的沉默或叹息,他就不能像一个寻常的儿子、兄长,一个寻常的丈夫?
也每每到这时候,那首据说是伪作的诗总在我脑中低回不去。
漫漫十九年的困守,上天或许终于不忍,历尽一番周折,苏武终于能够回归故国。
临行那天,身着胡服的李陵拔剑起舞,苍凉高歌:“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他在送别一个要回家的男人,而他自己,路穷名灭。他的孤魂将永远飘荡于广袤荒凉的北地,飘荡于故土万里之外。
一曲唱罢,李陵痛哭不止。
二
苏武来匈奴时正值盛年,还有一百多个意气风发的使者与他同行。归程时,连他一共只剩十人。其他人和他一样,岁月漫漫,粗粝的风沙已经销蚀了他们昔日容颜,脸上一道道刻痕,黑发尽变白发。
走在长安城的街头,他们会是什么心情呢?旧友、妻儿,还有他们的圣上,很多的人和事都变了。
十九年前,苏武从武帝刘彻手中接过使节,出去办事。现在他终于办完了事,可是回到家时,主人已经走了六年。不管他把任务完成得怎样,总要向给予他使命的人汇报一下情况。
后继者也知道苏武这些年不容易,所以允许他用最高的规格—太牢(牛羊猪三样具备)去祭拜刘彻。
感于他的忠义,朝廷给了他很高的恩宠,苏武被拜为典属国,赐钱二百万、田二顷、住宅一座。
苏武呢?他当然很感激,然后把所有的财产散尽。
苏武归来后不到一年,他仅存的儿子苏元卷入党争,以谋反之罪被杀。廷尉上书,要求依法将苏武下狱。但举国上下对他的赞誉之声那么高,仅过去不到一年就把他杀了,影响实在太坏。最终只将苏武免官。
但故事并没有完。
史书上这样写,党争之后,汉宣帝即位,因“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闵之,问左右:‘武在匈奴久,岂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发匈奴时,胡妇适产一子通国,有声问来,愿因使者致金帛赎之。’上许焉”。
汉宣帝刘病已能够即位,纯属命运的奇妙安排。公元前74年,昭帝崩,无子,昌邑王刘贺继位,但仅仅做了二十七天皇帝,就被权臣霍光废黜。此时的皇室已无人选可以承续大统,幸运的冠冕就这样落到了刘病已头上。
刘病已即位后很快就面临立后一事,权倾朝野的霍光一心想让他立自己的孙女为后,但病已微时已经娶许平君为妻,他不忍伤害随他度过孤苦生涯的伴侣,又不敢直接忤逆霍光。他发了一道很奇怪的,也被后人称为最深情的诏令:我在民间时有一柄剑,现在找不到了,大家帮我找一找。
剑犹如此,何况人呢?明白“故剑情深”之意的霍光也就不好强求了。
而“故剑情深”的宣帝也是最懂得苏武心底悲凉的吧。只有他给了苏武一个“闵”字,给了这个壮烈故事唯一的柔软的一笔。
这个“闵”也让我想到很多。
史书上说,汉武帝驾崩后,“武闻之,南乡号哭,欧血,旦夕临数月”。苏武是这样忠义重情,可是重情的苏武,是只重圣上的情吗?

在苦寒的北地,苏武喃喃念着的不只是他的圣上,也有妻儿的名字吧;走进他孤苦梦乡安慰他的,不只是大汉天子的容颜,也有亲人的微笑吧;晚上醒来,看到头顶凛冽的明月,他也会想起离别那晚的故乡月吧?
在那令人绝望的漫天风沙中,支撑他的,除了那旌旄脱落的汉节,也有苏通国的天真嬉戏吧;在他十九年荒凉荒芜的生命中,那不知身世、不知名字的胡妇也给过他很多安慰吧?
他离开北地时,胡妇和苏通国有没有送君千里、牵衣顿足?而他的脚步里,又有几分轻快、几分沉重?
三
然而这些,不过是我天马行空的虚妄猜想。班固笔下给苏武的只有纯粹,给胡妇的只有“胡妇”二字,丈夫离去,儿子离去,她拥有的也只是这两个字。
一千年后,苏东坡评价“胡妇”一事时则说:“苏子卿齿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东坡做出结论,“去欲最难”。
思维范畴更为广阔的当下,也有人猜说苏武是为顾全自己的完美形象,才在一开始就刻意隐去“胡妇”一事的。
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所有的故事都已隐入尘烟,史书上的“胡妇”,苏武和胡妇的故事,只有亘古的简陋、亘古的沉默。
再读那个“闵”字,不由湿了眼眶。
原谅我的脑回路跳跃,不由想起了几年前《见字如面》上读过的一封信:
华:
七年了!
七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你受苦的时间也很长了。我实在对你不起,让你苦痛了这样久,而就是现在,我还是没有办法来安慰你。
我闲着无聊时,常常来回想过去的旧事作消遣。每次想到我们在会府住着的一段生活,我就记起自己的过错了。
我更想到,你在什么地方做一点小事,还有一位比我好的人在帮助你,你过着很好的生活。想着,这样想着,我心里舒畅得多,好像肩膀上的一块重石头放下了,也好像丢掉了人家一样重要东西又找回来了一样。
请你不要怪我胡思乱想,我这样想确实一点没有坏心,不过这样想着玩罢了。至于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梦话,那不过是顺便提起,让你晓得我曾经做过这些梦而已。并且我迟早总说不定要回来吧,回来之后把这当着笑话谈也是好的。
还要申明一句,如果有机会,我决定要回来的。虽然我这一辈子大概免不了在外边奔波,但回一趟家是一定无疑的。并且如果你愿意又不怕劳苦,而且机会又许可的话,那我们一同到外边走走也不错啊。说着说着,又扯远了,远了的事,世界上没有神仙,谁料得定呢。
写信的人叫许晓轩,是《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
地狱一般的渣滓洞里,领导地下党工作的许晓轩是受酷刑折磨最多的一个,甚至曾经一个人被关在暗无天日的水窖里长达一年之久。
信中的许晓轩和我们常人没什么两样,离别的痛楚、对不可知未来的左思右想,人性中的缺点和软肋,他们都有,不过如此。
不是吗?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这有血有肉、跨越时间的人性中共通的柔软和脆弱,让人心里一紧一疼的地方,才更让他们的每一份爱与牺牲令人感到切肤之痛,更令人感受到那种跨越人性、超拔人性的磅礴力量。
而这些,是苏武的故事里看不到的,是班固不能、不想、不愿或不屑书写的。
又一次想起那首据说是伪作的诗,我更相信它是真的,即使它从来没有被苏武写出来。
我轻轻地读,生怕打扰了他们那夜的温柔和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