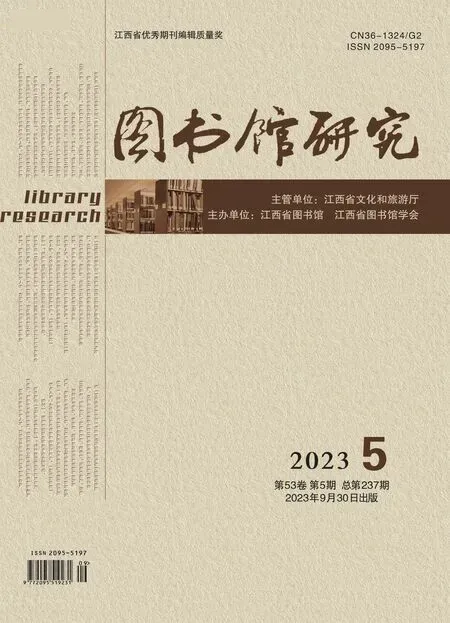“考证之所必资”
——四库馆臣对《直斋书录解题》的接受与评判
张小伙
(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是现存较早的私家目录之一,与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被称为我国目录学史上的双璧,为后世了解宋代文献情况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因而,四库馆臣(以下简称馆臣)评价其“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1]730。更有今人称“古代文化之盛,莫盛于宋代;宋代典籍之富,莫富于直斋”[2]。本文具体考察馆臣对《解题》的参证利用情况,从而进一步揭示其目录学价值。
陈振孙,字伯玉,号直斋,吴兴(今浙江湖州市)人。又称湖州人,或安吉人。正史无传,生平资料散见于宋元人笔记、诗话以及地方志中。早年一直在江苏、浙江、福建等书籍印刷兴盛的南方做地方官,与书商交往密切,这为其从事古籍收藏提供了时间和财力的支持。后出任京官,更得以阅见内府藏书,以通奉大夫、宝章阁待制、某部侍郎的身份致仕。还乡后修撰了《吴兴人物志》。陈振孙每到一处任官即访书、抄书,几尽毕生之力完成巨著——《直斋书录解题》(以下简称《解题》)。自成书以来就为时人所重,但流传不广,可能没有付梓,一直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现存最早的也只有四残卷的元抄本。宋元明清公私书目亦罕有著录,王应麟、袁桷等著名学者都未得见全本,直到清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时,馆臣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来,使得秘笈重现人间,一时为学者研究所重。
据笔者粗略统计,《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直接或间接引用陈氏《解题》的内容达500 条以上,而《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经籍考》、《经义考》以及《读书敏求记》等其他目录著作的单书引用则多在200 条以内。这么巨大的引用足以说明,在编纂《总目》的过程中,《解题》是馆臣重要的参考书。
1 类目设置的因袭与借鉴
《解题》虽不标四部之名,但也是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之下细分为53 小类,收书3 096种,51180卷。较之前的《遂初堂书目》与《郡斋读书志》在收书质量与数量上均有显著提升。在数量方面甚至超过了当时南宋政府编的《中兴馆阁书目》所收的44486 卷。正如王重民先生所言:“在图书的著录和内容的概括上,《解题》的参考使用价值也比《中兴馆阁书目》为优,使私人藏书目录在质量两方面都压倒了官修目录。从《中兴馆阁书目》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600 年间,元明清三个朝代都没有编出过一部像样的(或者说是正式的)官修目录,这是我国目录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变化,而《解题》则是这一巨大变化的转折点。”[3]在类目设置与提要的撰写方面,陈振孙在继承前人的成果上有所创新,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后世书目的编纂。陈氏在《解题》中,并经部“论语类”与子部《孟子》而新创“语孟类”,这类目设置上的重大变化,既反映了唐以来统治者对于《孟子》的重视,也体现了学术与现实政治统一的目录原则。其后清人修《明史·艺文志》则在此类目基础上进而设置了“四书类”,因为宋以后科举考试以朱子所定四书为官方教材,关于此类的书籍也不断增多,反映在目录学上即是“语孟类”向“四书类”的过渡。馆臣在“四书类”小序云:
元邱葵《周礼补亡序》称“圣朝以六经取士”,则当时固以《四书》为一经。前创后因,久则为律,是固难以一说拘矣。今从《明史·艺文志》例,别立“四书”一门,亦所谓礼以义起也。朱彝尊《经义考》于“四书”之前仍立《论语》、《孟子》二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凡说《大学》、《中庸》者,皆附于礼类。盖欲以不去饩羊,略存古义。然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明史》并入四书,盖循其实。今亦不复强析其名焉。[1]289
馆臣虽说是依《明史·艺文志》而设立“四书类”,其源头即是陈氏所创“语孟类”,这一点毋庸置疑,陈氏首创之功不可没。
陈氏《解题》“时令类”小序:“前史时令之书,皆入‘子部农家类’。今案诸书上自国家典礼,下及里间风俗悉载之,不专农事也。故《中兴馆阁书目》别为一类,列之‘史部’,是矣。今从之。”[4]189可知,前代书目将“时令类”书籍都归入“子部农家类”,而陈氏以为不妥,因而依据《中兴馆阁书目》别为一类,升入史部。这一点也得到了馆臣的直接继承:“其本天道之互以立人事之节者,则有时令诸书。孔子考献征文,以《小正》为尚存夏道。然则先王之政,兹其大纲欤。”[1]592《总目》史部分15 类,第10 类即是“时令类”,位于“载记类”之后、“地理类”之前。
前志“起居注”中“实录类”与“诏令类”混在一起,陈氏在《解题》中则别出“诏令”为独立的一类,这是因为起居注书籍大量亡佚,“诏令类”书籍在性质上又与“实录类”不同体,因而其独立成类也是合情合理。同时,在集部依尤袤《遂初堂书目》之例从别集中析出“章奏类”,曰:“凡无他文而独有章奏,及虽有他文而章奏复独行者,亦别为一类。”[4]634馆臣在此基础上合其两类为“诏令奏议类”一类,并入史部,而三级类目依旧分为“诏令”与“奏议”两类,可谓对陈氏分类的肯定,《总目》“诏令奏议类”小序云:“夫涣号明堂,义无虚发。治乱得失,于是可稽。此政事之枢机,非仅文章类也。抑居词赋,于理为亵。《尚书》誓诰,经有明征。今仍载史部,从古义也。”[1]492陈氏将前志中的“刑法类”改为“法令类”。因为其已经名不符实,不止收录“刑法”,还兼收诸如贡举法、学法之类,改为“法令类”更为相称。《总目》则合并其“典故类”“时令类”等设立“政书类”,三级类目下仍然沿用“法令”,可见也是对陈氏之举的认可。
陈氏“别史类”小序今不传,无由得知其设此类目的缘由,但“别史类”被《总目》直接继承,小序曰:
汉《艺文志》无史名,《战国策》、《史记》均附见于《春秋》。厥后著作渐繁,《隋志》乃分正史、古史、霸史诸目。然《梁武帝》、《元帝实录》列诸杂史,义未安也。陈振孙《书录解题》创立别史一门,以处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义例独善,今特从之。盖编年不列于正史,故凡属编年,皆得类附。《史记》、《汉书》以下,已列为正史矣。其岐出旁分者,《东观汉记》、《东都事略》、《大金国志》、《契丹国志》之类,则先资草创。《逸周书》、《路史》之类,则互取证明。《古史》、《续后汉书》之类,则检校异同。其书皆足相辅,而其名则不可以并列。命曰“别史”,犹大宗之有别子云尔。包罗既广,六体兼存。必以类分,转形琐屑。故今所编录,通以年代先后为叙。[1]445
可知馆臣非常认可陈氏“别史类”之设立,认为“义例独善,今特从之”。其收书原则定位为“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这是由于“正史”观念的不断强化,自唐以来史馆制度完善,正史的修撰完全由官方主导,但私人著述的史书数量又不断增多,因而有了“别史类”这一折中之法。所谓“正史体尊,义与经配”,所有“未经宸断”而“下不至于杂史者”的史书不能入“正史类”,只能入此“别史类”。这个类目的设置可谓深谙馆臣之意。其实“别史类”,宋代官修《中兴馆阁书目》即已创立,这也与宋朝统治者强调未经官方钦定的史书不能入正史的政策相合。
又陈氏《解题》对一些类目的收书范围进行了重新定义,如“小学类”剔除了书法相关书籍,“农家类”剔除了“《钱谱》、《相贝》、《鹰鹤》之属”等书,这种调整更符合实际,后世书目多因循。如《总目》“小学类”下面三级类目只有“字书”、“韵书”、“训诂”三类,而无其他杂入。“农家类”则“惟存本业,用以见重农贵粟,其道至大,其义至深,庶几不失《豳风》、《无逸》之初旨”,也不收前志杂入的《相牛经》、《相马经》、《相鹤经》、《鹰经》、《蟹录》、《相贝经》、《香谱》、《钱谱》等。保持了类目的独立性与纯洁性。显然,这或多或少受到了陈氏《解题》的影响。
2 提要内容的征引与鉴别
陈氏《解题》收录书数量高达五万余卷,而每书又有或繁或简的提要,对于后世已经亡佚的书,可以从中窥见其厓略,对于还流传的书则可以考察其版本、阙佚以及辨伪等。因而《解题》对于考察宋代文献的流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得益于陈氏收书的“厚今”思想,即所收之书以“今人”为主,此沿袭自郑樵《通志·艺文略》,以集部为例,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宋人之书。如来新夏所说:“《解题》著录多详今书,如卷二一‘歌词类’,除《花间集》、《南唐二主词》、《阳春录》及《家宴集》为唐五代作品外,其余一一五种皆宋人词集。”[5]145其他三部收书情况亦如此,因而提供了大量宋代文献情况。馆臣对这些材料的使用又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2.1 借助《解题》考证一书版本与流传情况
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书名卷数往往多有变动,诸如篇数多寡、书名改易以及卷数分合等情况,需要通过考察前代目录书才能了解源流。因而馆臣常据陈氏《解题》的记载来判别版本情况,如《六经图》六卷提要:
陈振孙《书录解题》引《馆阁书目》,载邦翰所补之本,《易》七十图,《书》五十有五图,《诗》四十有七图,《周礼》六十有五图,《礼记》四十有三图,《春秋》二十有九图,合为三百有九图,此本惟《易》、《书》二经图与《馆阁书目》数相合。《诗》则四十有五,《礼记》四十有一,皆较原数少二。《周礼》六十有八,较原数多三。《春秋》四十有三,较原数多十四。不知何人所更定。考《书录解题》载有东嘉叶仲堪字思文,重编毛氏之书,定为《易图》一百三十、《书图》六十三、《周礼图》六十一、《礼记图》六十三、《春秋图》七十二,惟《诗图》无所增损。其卷则增为七,亦与此本不符。然则亦非仲堪书。盖明人刊刻旧本,无不臆为窜乱者。其损益之源委,无从究诘。[1]271
馆臣通过与陈氏《解题》所记载的篇数对比,发现具体篇章有所增益,已非其旧,因而批评“明人刊刻旧本,无不臆为窜乱”,亦透露其所用底本即是明刻本。在馆臣观念中,宋时旧本即是善本。叶德辉云:“自康、雍以来,宋元旧刻日稀,而搢绅士林佞宋秘宋之风,遂成一时佳话。”[6]因而,馆臣对明人篡改古书之风颇多批评。
同时,卷数分合也能引起馆臣极大注意,“卷数差异往往是同书异本互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卷数不同,也就意味着版本的不同”[7]。对于陈氏《解题》著录书卷数的考察,是馆臣纂修提要的重要参考,也是其征引《解题》较多的部分,通过卷数的不同可以判断是否经过后人改动以及阙佚情况,如《墨客挥犀》十卷提要:“陈振孙《解题》载此书十卷,续十卷,称不知撰人名氏。今本为商濬刻入《稗海》者,卷首直题彭乘姓名,盖以书中所自称名为据,而止有十卷,则已佚其续集矣……疑原本残阙,后人又有所窜入。”[1]1195-1196又《唐语林》八卷提要云:“惟陈氏作八卷,晁氏作十卷,其数不合。然陈氏又云《馆阁书目》十一卷,阙记事以下十五门,另一本亦止八卷,而门目皆不阙。盖传写分并,故两本不同耳。”[1]1196对这种卷数分合,馆臣坚持“盖或合或分,各随刊者之意。但不改旧文,即为善本。正不必以卷数多寡,定其工拙矣”[1]1686,这是值得肯定的。又如《乌台诗案》一书,陈振孙《解题》著录为十三卷,而胡仔《渔隐丛话》所录则只有三卷多,与馆臣所据本卷数皆不合,同时通过内容的比勘,馆臣发现其所据本既非“仔所见本”,也不是“振孙所见本”,于是怀疑为后人摭拾增益之书。这种推测较为合理,有赖于陈氏之著录才能有此判断。
早期古人著书往往不题书名,因而后世易发生混乱。余嘉锡言:“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故惟官书及不知其学之所自出者,乃别为之名,其他多以人名书。”[8]后世书名改易则往往与版本相关,即如卢贤中言:“不同古书的卷端上下题固然不同,同一古书而不同版本的卷端上下题也往往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为书名穿靴戴帽,有时还表现为书名用字不同,所谓用字不同,多表现为不同写法的异体字。古书卷端题名用字不同,往往表明是不同的版本。”[9]但也有可能是误题。馆臣对前代亡佚之书,通过辑佚后书名的拟定,《解题》的著录是非常重要的依据之一,如《易学辨惑》提要:“此本自《永乐大典》录出,盖明初犹存。《宋史·艺文志》但题《辨惑》一卷,无‘易学’字,《永乐大典》则有之,与《解题》相合,故今仍以《易学辨惑》著录焉。”又《春秋集注》一书久佚,但《宋史》著录为《春秋集解》,最终馆臣以陈振孙《解题》所录书名与卷数为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
对于不同书目中同一书名记载不一致,馆臣往往倾向于陈氏《解题》为是,如果又有其他书目与陈氏记载合,则更不疑虑,径以为宋本原题。在关于宋代书目中,馆臣极不满《宋史·艺文志》,因而其与《解题》有异时,往往采纳陈氏。如《小畜集》提要:“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皆作三十卷,与今本同。惟《宋志》作二十卷。然《宋志》荒谬最甚,不足据也。”[1]1103又如《栾城集》,馆臣批评:“《宋志》荒谬,《焦志》尤多舛驳,均不足据要。当以晁、陈二氏见闻最近者为准也。”[1]1328可见,馆臣对于陈氏记载之认可。
陈氏《解题》对于一书著录与否是馆臣判断一书成书年代、流传情况以及亡佚年代的重要依据,如郑兴《郑忠肃奏议遗集》,馆臣通过考察《解题》及《宋史·艺文志》都没有著录。因而断定其成书于南宋之后。又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有甲乙丁戊四集,其书在宋代有刊本,现存只有有甲丁两集写本,而陈氏《解题》亦没有著录丁戊两集,因而馆臣推测后两集乃其晚年辑成,故《解题》没有著录。同样,宋人刘荀《明本释》一书《解题》未载,《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经籍考》亦不载,只有明代《文渊阁书目》与焦循《国史经籍志》著录,由此馆臣认为此书在宋代流传不广,而在明代则稍显。另外,陈氏的不著录有时也可作为判定一书亡佚年代的依据,如《论语义疏》一书,《国史志》、《中兴书目》、晁公武《读书志》以及尤袤《遂初堂书目》都有著录,但陈氏《解题》未著录。因此,馆臣推断其在南宋时亡佚。
陈氏《解题》之著录也为馆臣辨伪提供了重要依据,关于古书作伪的原因有许多,前人已总结过,如卢中贤归纳为五方面,即托古、邀赏、宗派、附会以及误断等。所以,伪书产生常常和古书亡佚具有一定联系。如《二南密旨》一书,陈氏在《解题》中已疑其伪,馆臣更通过内容差异以及体例问题,确为伪书无疑。又宋人严有翼《艺苑雌黄》一书,《解题》入子部杂家,并著录其目录包括子史、传注、诗词、时序、名数、声画、器用、地理、动植、神怪、杂事等共二十卷四百条,馆臣所据本与此对比,目录与卷数具不合,因而认为是后人摭拾之本,而原书已亡佚。因而《解题》的著录为馆臣考察宋以前文献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
2.2 借助《解题》纠正他书记载之误
后世志书诸如《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之类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字句舛误或者记载本身就有问题,馆臣通过《解题》及其他佐证对其进行纠正。馆臣对于《宋史》评价尤低,认为其“其书仅一代之史,而卷帙几盈五百。检校既已难周,又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馀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1]412对于《宋史·艺文志》更是觉得“不足为凭”,因而在提要中屡有援引《解题》对其进行纠误之举,如《浮沚集》提要云:
宋周行己撰。行己字恭叔,永嘉人。元祐六年进士。官至秘书省正字,出知乐清县。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为太学博士,以亲老归,教授其乡。再入为馆职,复出作县。乡人至今称周博士,盖相沿称其初授之官也。振孙载《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后集》三卷。《宋史·艺文志》载《周行己集》十九卷。正合前后两集之数,而又别出《周博士集》十卷,已相牴牾。《万历温州府志》又称《行己集》凡三十卷,更参错不符。考振孙之祖母,即行己之第三女。振孙所记,当必不误。《宋史》及《温州志》均传讹也。[1]1341
馆臣以周行己为陈氏外曾祖,所记当不会有误,因而据此来纠正《宋志》之谬。又《东溪集》作者为宋人高登,《宋史》本传载其死后二十年被追复迪功郎,又十年追赠承务郎,馆臣据《解题》所载则认为高登生前即已是迪功郎,死后亦未被追赠承务郎,因而“足证《宋史》之瞀乱失实也”[1]1358。对于宋人词集,馆臣所用底本多为毛晋汲古阁刻本,但是对于毛氏校勘不精与考证不当多有批评,也通过《解题》来纠正其谬。如关于《西樵语业》作者,《解题》著录为杨炎正济翁撰,即杨炎正,字济翁,而毛晋刻六十家词,竟误以杨炎为姓名,以止济翁为别号。馆臣又通过其他人的记载,断定“毛氏旧印之本为不足凭矣”。又如卢炳所撰《哄堂词》,毛晋刊本则作“烘堂”,陈氏著录为“哄堂”,馆臣又通过词义辨析断定毛氏讹误。
《文献通考·经籍考》在传写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错误,如《大唐创业起居注》提要:
《唐志》、《宋志》皆作三卷,惟《文献通考》作五卷。此本上卷记起义旗至发引四十八日之事,中卷记起自太原至京城一百二十六日之事,下卷记起摄政至即真一百八十三日之事。与《书录解题》所云记三百五十七日之事者,其数相符。首尾完具,无所佚阙,不应复有二卷。《通考》殆讹“三”为“五”也。[1]420
至于焦竑《国史经籍志》,馆臣对其评价也很低,认为其“诞妄不足为凭”,对其纠缪也有不少,如《演山集》提要:
见於陈振孙《书录解题》者六十卷。今此本卷目相符,盖犹宋时原本。《国史经籍志》作“黄裳《兼山集》四十卷”。书名卷数俱不合,盖焦竑传录之误耳。[1]1336
同时,馆臣也通过陈氏《解题》纠正地方志记载的错误,如《䂬溪诗话》作者黄彻,《解题》称莆田人,而《八闽通志》称邵武人,馆臣认为“振孙时去彻未远,当得其真也”。又《王著作集》提要:
宋王苹撰。苹字信伯,福清人。《福建通志》称:“绍兴初,平江守孙祐以德行荐於朝,召对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累官左朝奉郎。”陈振孙《书录解题》则作“以赵忠简荐赐进士出身,官至著作佐郎。秦桧恶之,会其族子坐法,牵连文致夺官。”与《通志》所记不同。然此集以“著作”为名,则陈氏所言为是矣。[1]1357
有一点需要注意,因为《总目》部头大,成书迅速,难免会有错误,这一点前人早已有所指正,如余嘉锡、胡玉缙等前辈。在馆臣征引文献时,有时会弄错书名,比如引用的实际是《郡斋读书志》的内容却写成《解题》。黄嬿婉在其文章《〈四库全书总目〉误引〈直斋书录解题〉订正十七则》就发现了好几处,如《营造法式》提要《总目》所引“故陈振孙《书录解题》以为远出喻皓《木经》之上”[10],其实是《郡斋读书志》的内容。因而在分析馆臣对于《解题》的征引时,尽量与《解题》原文做一个比勘为好。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对馆臣于陈氏《解题》征引借鉴情况有一个大致的梳理,可知在撰写提要过程中,《解题》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宋代文献流传稀少的现状下,许多书籍的相关信息,只有通过前代书目的记载才能窥其厓略。在乾嘉考据之风盛行下,任何可供考证之资都被馆臣加以利用。
3 馆臣对《解题》的指摘
《解题》并不是完美的,也存在着各种问题,毕竟经过一个由佚复出的过程,加之《永乐大典》的抄录将原书割裂分散在各韵部之下,又无其他版本校勘,导致重辑出来的时候出现字句讹误、次序颠倒等问题。因而,馆臣在征引过程中对于《解题》出现的书籍归类不当、考辨失误等问题也会予以指摘批评。
3.1 对《解题》分类不当的隐性批评
在《总目》凡例中,馆臣特意就前志对某些书籍的分类不当指摘批评,这些书籍的分类历代沿袭,不是某家的分类失误而是共性失误,当然也包括《解题》在内。如《穆天子传》旧入起居注类,《山海经》旧入地理类,馆臣“以其或涉荒诞或涉鄙猥”而改入小说家类。又如扬雄《太玄经》,旧入儒家类,馆臣改入术数类等。对这些书籍分类的调整,一方面体现了循名责实的目录学原则,另一方面则反映了馆臣分类思想的承前启后性。又如《尚书大传》一书,馆臣认为其为“古之纬书,诸史著录於《尚书》家,究与训诂诸书不从其类。今亦从《易纬》之例,附诸经解之末”[1]108,此书《解题》置于“书类”中第五,《尚书释文》后,《汲冢周书》前,陈氏在《解题》中以为“当是其徒欧阳、张生之徒杂记所闻,然亦未必当时本书也”[4]28,馆臣则更以为其“古之纬书”,与训诂无关,因而置于诸经解之末。
正如上文提到《总目》本身也有不少字句讹误以及张冠李戴等问题,在指摘《解题》具体书籍分类上也有失误,如《小学集注》提要:“是书自陈氏《书录解题》即列之经部小学类,考《汉书·艺文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小学家之所列,始於史籀,终於杜林,皆训诂文字之书。今案以幼仪附之《孝经》,终为不类。而入之《小学》,则於古无征。是书所录皆宋儒所谓养正之功,教之本也。改列儒家,庶几协其实焉。”[1]782核查陈氏《解题》原文,发现其“小学类”下并无《小学集注》一书,因而此批评完全是张冠李戴。馆臣所引内容实出自陈氏《解题》卷九“儒家类”下的“《小学书》四卷”条。此书为朱子所著,而馆臣撰写提要之书为明代陈选注本。陈氏也并未把朱子此书置于经部小学类中,馆臣所指责失于核查。
3.2 对《解题》著录书籍信息的辨误
陈氏《解题》虽然著录书籍信息严谨,但流传过程中出现字句讹误也在所难免,如《南阳集》·三十卷、《附录》一卷提要:
宋韩维撰。维字持国,颍昌人。……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二十卷,称后有其外孙沈晦跋,前有鲜于绰所撰行状。此本凡诗十四卷,《内制》一卷,《外制》三卷,《王邸记室》二卷,《奏议》五卷,表章、杂文、碑志各一卷,手简歌词共一卷、附录一卷,较陈氏所载多十卷。疑陈氏讹“三十”为“二十”。[1]1323
关于陈氏所记卷数与馆臣所用底本卷数之间有十卷的差异,又无其他增益的证据,因而馆臣认为陈氏记载有讹误。又如叶梦得所撰《石林居士建康集》,馆臣所用底本为八卷,而陈氏记载叶梦得“《建康集》十卷”,但此书末有其孙叶辂的题跋,亦是说八卷,因而馆臣怀疑“《书录解题》屡经传写,误以八卷为十卷。抑或旧本残阙,亡其二卷,后人追改辂跋以伪称完帙。则均不可考矣”[1]1349。再如《渭南文集》五十卷、《逸稿》二卷提要:
宋陆游撰。游晚封渭南伯,故以名集。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三十卷。此本为毛氏汲古阁以无锡华氏活字版本重刊。凡表笺二卷,劄子二卷,奏状一卷,启七卷,书一卷,序二卷,碑一卷,记五卷,杂文十卷,墓志、墓表、圹记、塔铭九卷,祭文、哀辞二卷,《天彭牡丹谱》、《致语》共为一卷,《入蜀记》六卷,词二卷,共五十卷。与陈氏所载不同。疑三字五字笔画相近而讹刻也。[1]1381
这种关于卷数方面的讹误还有很多,也有关于作者姓名字号以及郡望方面的失考,如《开颜集》的作者是宋代周文玘,而《解题》与《文献通考·经籍考》都讹误成周文规。又如《芳兰轩集》作者徐照,自号山民,其集名与赵师秀的《清苑斋集》都是佐证,而陈氏则称其号天民。再如将《女孝经》作者题为班昭,将李之仪的籍贯说成赵郡,称王得臣为王铚之伯父以及《石林燕语》《仪礼图》的成书年代等,陈氏均失考而致误。馆臣在提要中都予以辨驳。
3.3 对陈氏观点的考辨
馆臣对陈氏《解题》并非一味接受,对于陈氏的某些观点是否妥当,会根据其他材料予以确证,这是他们严谨治学精神的体现,如《欧阳行周集》提要:
唐欧阳詹撰。詹字行周,泉州人。……韩愈为《欧阳生哀辞》,称许甚至,亦非过情也。《太原赠妓》一诗,陈振孙《书录解题》力辨函髻之诬。考《闽川名士传》,载詹游太原始末甚详。所载《孟简》一诗,乃同时之所作,亦必无舛误。又考邵博《闻见后录》,载妓家至宋犹隶乐籍,珍藏詹之手迹,博尝见之。则不可谓竟无其事。盖唐、宋官妓,士大夫往往狎游,不以为讶。见於诸家诗集者甚多,亦其时风气使然。固不必奖其风流,亦不必讳为瑕垢也。[1]1291-1292
关于《太原赠妓》一诗陈氏不相信出自詹之手,因为他相信“詹之为人,有《哀辞》可信矣”[4]478,因而力辨是黄璞的诬陷。馆臣则通过《闽川名士传》与《闻见后录》中的材料佐证,确定其出自詹之手无疑。狎妓是当时的风气,留下此作也非不可能。又如《新唐书》提要:
宋欧阳修、宋祁等奉敕撰。其监修者则曾公亮,故书首《进表》以公亮为首。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旧例修书,止署官高一人名衔。欧公曰:‘宋公於我为前辈,且於此书用力久,何可没也?’遂於《纪传》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逊,故书中《列传》题祁名,《本纪》、《表》《志》题修名。”然考《隋书》诸志,已有此例,实不始於修与祁。[1]410
类似这样的失考还有很多,陈氏本人也并非以学术知名,况且《解题》也只是陈氏对于个人藏书的著录,偶有舛误也能理解,不能求全责备苛求前人。因而馆臣高度评价其“古书之不传於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於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1]730,可谓名副其实,即使有瑕疵仍不能掩盖其在目录学史上的价值。
4 结语
《解题》虽然流传坎坷,几于湮灭,幸而《永乐大典》犹存其全帙,方不使秘笈亡于人间。宋代官修目录书基本亡佚,仅有简本《崇文总目》而且还残缺大半,流传于今的宋代私家书目仅有三家即《解题》《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三家目录各有特点不可偏废,《遂初堂书目》著录版本,开后世版本目录之风。《郡斋读书志》偏于考订,多为精审。《解题》则著录最为丰富并以“解题”命书,开此先例。因而,来新夏评价:“这三种私家目录是宋代目录事业中的重要成就。它们为古典目录学的发展作出了创制体裁,保存宋以前学术资料的可贵贡献。”[5]146但不可否认,陈氏《解题》将刘氏父子开创的书目解题传统重新发扬光大,并且对南宋以前的当时尚在流传的图书著录最为全面,因而在目录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