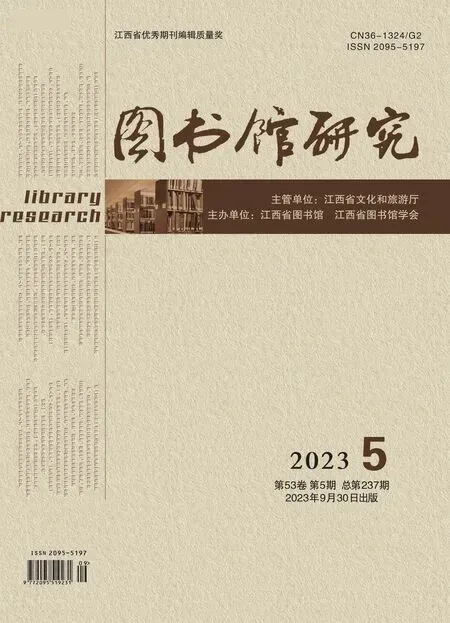国家图书馆藏李盛铎题跋辑释
孙天琪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晚清民国时期藏书家之中,江西德化李盛铎堪称执牛耳者,庋藏之品类、质量皆为并世稀见。傅增湘赞曰:“统观藏书全部,量数之丰,部帙之富,门类之赅广,为近来国内藏书家所罕有。”[1]1096李氏木犀轩积书近六万册,兼具宋元本、四部普通善本、旧钞本、名家校本和日本、高丽旧本,包含宏博,尚多妙品。这既得益于家学传承,又与其身居高位紧密关联。其利用担任学部大臣职务之便,搜罗敦煌写本精品五百余号,尤可宝贵。出使东瀛期间,结识目录学家岛田翰,回购大量宋元版书,对典籍文化传承不无贡献。藏书之外,盛铎又喜抄校、刻印书籍,辑刻有《木犀轩丛书》及《续编》。光绪十三年(1887)在上海创办蜚英馆石印局,率先引进石印技术,印行《皇清经解续编》《古经解汇函》等重要著作,在出版史上颇具标志性。李氏身后,所藏珍籍经由傅增湘介绍归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大图书馆),成为该馆古籍收藏大宗。
李盛铎晚年寓居天津,以整理个人藏书为乐,撰成《木犀轩藏宋本书目》《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木犀轩藏书书录》等,并手书跋语述版本源流、校勘得失、递藏经过,这些书目和题跋对研究其藏书思想至关重要。赵万里先生主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之时,就曾提出辑录李氏书跋构想。1985年,张玉范先生从北大图书馆藏李氏书中辑录题跋一百七十三篇,整理成《木犀轩藏书题记》,学界受益颇多。此外,《木犀轩藏书题记》还附录了国家图书馆藏李盛铎题跋十三则,皆属李氏为袁克文藏书撰写的跋文。近年来,笔者在国家图书馆藏书中又发现了李盛铎题跋九则,为《木犀轩藏书题记》所未收,这些题跋涉及递藏源流、校勘过程、版本质量及价值品评,对研究李盛铎藏书思想和交游不无裨益。兹予以整理,并加以考释,供学界同仁参考。
1 《群经音辨》[七卷,(宋)贾昌朝撰,南宋绍兴十二年汀州宁化县学刻本。书号:12354]
此书各家著录多系景宋本,以宋刊原帙久归天禄石渠,无由获见。此本玺识宛然,殆何时失散流出,归于郁华阁。今为抱存所得,洵可珍也。此绍兴壬戌汀州宁化县所刊,故避讳至“觏”字止,于宋代为此书第三刻。乙卯夏日,盛铎记。(下钤“李盛铎印”朱文印)
按:《群经音辨》专辨群经音诂殊别之字,赵宋朝凡三次刊行,《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记载详备[2]。北宋国子监刻本早佚;南宋绍兴九年(1139)临安府学据国子监旧版重雕本存一部,曾在朱承爵处,后入清宫天禄琳琅,今藏国家图书馆,《中华再造善本》据以影印,是本校勘不精,讹误较多[3];南宋绍兴十二年汀州宁化县学刻本存一部,亦在国家图书馆,即李盛铎题跋者。此本流传颇复杂,先经陈惟允、唐寅、毛晋递藏,后入清宫天禄琳琅。其中,卷一、卷二、卷五至卷七久贮内阁大库,未曾流失,钤印有“汲古阁”“毛晋私印”“乾隆御览之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等。而卷三和卷四在清末散出,归入盛昱郁华阁,寻为完颜景贤购得,而后转售袁克文。袁克文称赞此为“盛氏书中之上驷”,并题跋两则,认为装帧古雅,校勘精审。傅增湘曾假袁克文藏本对校康熙五十三年张士俊翻宋本,凡得七十余字。1920年,袁克文藏残本被傅增湘买去。1930年,周叔弢用唐写本《鶡冠子》与傅增湘交换此残卷。故卷三、卷四中多“皇二子”“寒云秘笈珍藏之印”“双鉴楼主人”“周暹”诸印。1947 年,周叔弢将卷三、卷四捐赠故宫博物院,复成完帙,新中国成立后拨交国家图书馆收藏[4]。毛氏汲古阁曾据绍兴十二年汀州宁化县学刻本影抄一部,经皕宋楼收藏,今存日本静嘉堂文库,《四部丛刊续编》据以影印。盛铎言“各家著录多系景宋本”,“景宋本”并非指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而指清康熙五十三年张士俊《泽存堂五种》本。张氏据宋本翻刻,在清代流传较广,惠栋、顾广圻等皆据是本校勘。光绪十四年(1888)李盛铎开办的上海蜚英馆石印局曾影印《泽存堂五种》。
袁克文于民国初年开始收藏古物,先师从方尔谦,后专从李盛铎习版本之学,萃集宋元名椠百数十种,遂有“后百宋一廛”“皕宋书藏”室名。李盛铎之子李滂回忆:“抱存乃奉贽家君,从而受学。家君与袁氏旧有年谊,且悦其聪颖,悔之不倦,曾钞瞿杨丁陆四家书目贻之。半载后,学大进,试举一书,抱存皆能渊渊道其始末。”[5]李盛铎在1915 年前后频繁为袁克文所藏宋元珍籍撰写题跋,袁克文也曾为李盛铎所藏宋刘氏天香书院刊《监本重言重意互注论语》(今收藏在北大图书馆)等撰写题跋,书札往还不断,这是二人书籍交往最紧密的时期。袁克文《寒云日记》亦记载与李盛铎讨论珍籍之事,其中录李盛铎撰写的咏书诗及题记,曰:“乙卯夏日,暑热殊甚。抱存仁弟每约过流水音,出所藏古书名画相与玩赏。率拈小诗,以志眼福。”[6]178此时,袁克文之父袁世凯复辟帝制,故袁克文常钤“皇二子”细朱文印。
2 两汉书(存六十卷,清初影宋抄本。书号:18135)
此景宋写本两汉书惟缺列传,经藏大兴朱氏、常熟翁氏,笔墨精妙,字画蔪方,真印钞之极工者。相传出自汲古阁,但无毛氏图记,为可疑耳。然开卷标题师古结衔、行款、字数皆与景祐本及福唐本为近,决非三刘《刊误》以下所能比拟。偶捡高纪二年六月置中地郡,服虔注“中地在扶风”,宋祁曰“注文‘在’字改作‘右’”,此本正作“右”,可为源出景祐本之一证。矧如此巨帙阅二百余年完好如新,岂非毛氏所谓“在在有神物护持”者耶!当定为三琴趣斋景宋本之冠。李盛铎识。(下钤“李氏木斋”朱文印)
按:此本半叶十行,行十八字至十九字,小注双行二十七字至三十字,黑口,左右双边。《汉书》存帝纪十二卷、志八卷,计二十卷;《后汉书》存帝纪后纪十卷、志注补三十卷,计四十卷。经大兴朱氏、常熟翁同书、袁克文、陈澄中递藏,今藏在国家图书馆。《后汉书》卷末有“毛晋”、朱锡庚、翁同书、袁克文、李盛铎跋语。李盛铎之前的诸家跋语有较多因袭成分,在版本鉴定上贡献不多。李盛铎率先指出毛晋跋语恐不足据,值得重视。袁克文在李盛铎跋后注曰:“木斋师题时惟见首册,谓无图记为可疑,盖未知有毛晋手跋也。”然全书确无毛氏汲古阁钤印,《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未著录。细审毛晋跋语书迹,与国家图书馆藏汲古阁抄本《清塞诗集》等附毛晋手跋相差甚大,颇疑为后人伪作。
《寒云日记》1916年正月初五日载是书为“钱葆奇自上海购得”[6]155。袁克文两跋皆作于1916年,李盛铎跋则是当时受袁克文嘱托另纸撰写并贴于书后的[7]。“毛晋”跋语中言“借牧翁宋本缮写”,故袁克文、傅增湘皆以为从绛云楼所储景祐本影写。经赵万里、尾崎康两先生研究,两汉书之“景祐本”实际是北宋末南宋初之覆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北宋递修本《汉书》即“景祐本”,曾经毛氏汲古阁收藏,《中华再造善本》据以影印。细勘“景祐本”与袁克文旧藏影抄本,行格虽同为半叶十行,但各行大小字排列并不一致,且存有诸多异文。如《汉书·高帝纪第一下》“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句下,颜师古注曰“复音方目反”。“景祐本”无颜师古注,而影抄本有。又如《汉书·高后纪第三》“夏五月辛未,诏曰……高皇帝兄姊也”句下,张晏注曰“高帝兄伯也”。“景祐本”无张晏注,而影抄本有。另外,“景祐本”因剜改版面出现的诸多拥挤或稀疏之处,在影抄本中并未出现。“景祐本”版心有刻工姓名,而影抄本无。现存“景祐本”“福唐郡庠本”、庆元本、明正统本皆为半叶十行,版式特征相近,源流关系十分密切,影抄本应当属于此一系列。李盛铎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明言“与景祐本及福唐本为近,决非三刘《刊误》以下所能比拟”,并通过校勘认为源出于景祐本。可见,其在古籍版本学上是有一定造诣的。至于影抄本与“景祐本”一系的具体关联与差异,仍需细考。
3 《中吴纪闻》[六卷,(宋)龚明之撰,明弘治七年严春刻本。书号:11307]
《中吴纪闻》,各家著录仅有明宏治本。昔毛斧季借叶九来菉竹堂藏本,从卢公武本传录者,改正一百三十余处,并多翟超一则。此后,义门校本亦从叶本传出,是毛、何当年皆未目睹元椠也。此本字仿欧波,为至正廿五年卢公武所刊无疑。乃后斧季二百七十年,寒云竟得藏此元刻,觉隐湖缥帙皆形减色,而我辈亦得以眼福自于矣。乙卯中元日德化李盛铎识。(下钤“李氏木斋”朱文印)
按:《中吴纪闻》为两宋之际文人龚明之记述吴中风土人文之笔记,可补范成大《吴郡志》记载缺憾。李盛铎跋语对版本鉴定存在较大失误。此本为明弘治七年严春刻本,李氏误定为元刊本。是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双边。前有行书龚明之序言。钤“武丘山人”“南畇”“吴树葑印”“香严审定”“沈氏藏书”“石埭沈氏藏书”“吴兴沈氏渊公考藏书画之印”“三琴趣斋”“寒云秘笈珍藏之印”诸印。《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并附注“余藏”二字,可知在袁克文身后归傅增湘持有,而后入国家图书馆。傅增湘判定为明弘治严春刊本,1935年撰跋语曰:“此书董氏诵芬室覆刻,号为元本。后见毛斧季跋及正德龚弘本跋,始知为弘治严春本,别为跋详志之。”[8]362李盛铎以及清代的诸多藏书家为何会出现鉴定和著录失误呢?主要是因为至正二十五年(1365)武宁卢熊(字公武)曾校补《中吴纪闻》并撰记语,故很多藏家认为该书在元代有过刊印过程。张元济则指出“昔人仅见卢记,故多认为元刻,然记实云校正增补,记其大略,并未有刊行之语。”[9]其实弘治本卷首原有弘治七年(1495)昆山知县杨子器《新刊中吴纪闻序》(国家图书馆书号:03443、07447),曰:“元运迄至正三十二年,及至皇明,通记三百六十余年,未有刻而传者,乃重加校勘,命邑义民严春刻而传之,所以成公武之志也。”已经明确指出了元代未曾刊行。后世坊贾射利,多将杨序抽毁,加之弘治本字体颇有元代风气,故常被误定为元椠。
《中吴纪闻》又有明正德九年龚弘刊本,乃据弘治本重寿诸梓。龚弘跋曰“武宁卢氏刻之,是为元至正二十五年”[10],对卢熊校补亦存在认知错误。李盛铎有一部正德刊本,并撰跋曰“从宋本校过”且认为书内另纸校语七行“系荛圃手笔”[11]10,皆不足据。毛氏汲古阁据叶氏菉竹堂所藏旧录本校刻,订误一百三十余处,并补录“翟超”一则,是本流传较广。毛扆跋语述菉竹堂本尚出卢熊。康熙三十九年(1700)何焯手校汲古阁刊本,又有所补。而后,《知不足斋丛书》《四库全书》《学海类编》《粤雅堂丛书》《汇刻太仓旧志五种》皆收录是书。另有抄本、校本数种,陆贻典、黄丕烈、缪荃孙、罗振玉等批跋,校勘价值很大。中国台北“故宫”藏“影元抄本”一部,末有黄丕烈跋语,言为绛云楼主人借汲古阁藏元本影抄,颇不可信。粗校是本,或源出于明弘治刻本也。《中吴纪闻》明清诸刻本、抄本、校本的源流关系尚不明晰,但笔者认为均源出弘治本、汲古阁本两端。
4 《述史楼书目》[不分卷,(清)徐维则撰,清抄本。书号:16851]
此书目一册,不知谁氏所藏,意当日必求售或托鉴定者,已茫不记忆矣。目中所列多注重需用之书,不计版刻远近,然明刻、秘钞亦间有一二。藏书至数万卷,而名氏翳如,颇为惜之。目中抄本书,多不题何人所抄,独有题“述史楼抄本”者十余种。《信摭》一卷,题“述史楼刊本”,或即藏书人欤?姑记此以俟考。乙卯中秋前三日,盛铎记。
目中所收,于光绪甲午以前新刊善本书籍略备,可以知其藏书之时代。又各省府志中,省志有三,而浙居其一。府县诸志,浙尤多。新府县志则广东为多,且有《广东图说》等书,意其人必浙籍而游粤者。并志于此,为他日考证之资也。盛铎又记。
按:此书一册,卷端手书“述史楼书目”五字,分经、史、子、集四部,著录书籍两千余种,简记书名、卷数、版本,无提要。李盛铎前一跋作于1915年,后一跋未题时日,大概两跋作于同一时期。该书卷首钤印“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卷末钤印“长乐郑氏藏书之印”,可知李氏身后归郑振铎收藏,《西谛书目》收载,其后捐赠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影印。
李盛铎在跋语中提到此抄本的来历,“意当日必求售或托鉴定者”。盛铎注意到书目中著录版本项有“述史楼抄本”“述史楼刊本”,猜测为藏书处名,但未详为何人。后一跋中又通过著录书籍刊印年份下限和收载方志地区分布,断定藏书者为“浙籍而游粤者”。现在来看其推论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郑伟章等已考定述史楼为浙江会稽徐友兰、徐维则父子藏书处[12],[13]189-197,[14]。徐氏藏书处有铸学斋、述史楼、八杉斋、融经馆等名。光绪时期,徐友兰在上海从事工商活动,命其长子徐维则广搜珍籍,辟铸学斋、述史楼藏之。《述史楼书目》即为父子二人收藏书籍的简目。徐友兰差旅中逢日俄黄海海战,备受惊吓,次年(1905)病卒。徐维则继承了父辈的藏书、刻书、校书事业,“徐氏藏书目录亦由他手编而成,他学问颇深,徐氏铸学斋藏书题记一类文字多出自其手。”[13]193徐友兰病逝后,藏书陆续散出,部分经蔡元培介绍归入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徐氏父子藏书在当时似乎名声甚微,与之同时代的大藏家李盛铎竟不知其人。李盛铎在上海开办蜚英馆石印局,具体业务由费念慈等人操办,虽与徐友兰同为上海农学会会员,但未有交集。1918年徐维则前往北京大学工作,并且与蔡元培共同促成了李慈铭藏书入藏北平图书馆。1922 年徐维则病逝,精抄之本多归沈知方粹芬阁。
徐友兰、徐维则父子藏书以抄本最具特色,沈知方称“徐氏铸学斋旧藏钞本,尤为精绝”[15]。从《述史楼书目》看,徐氏藏书中抄本和明清刻本占多数。除李盛铎提到的“述史楼抄本”“述史楼刊本”之外,书目中还有铸学斋抄本《串雅外篇》四卷等。今尚存数种徐氏藏书目录,浙江图书馆藏稿本《述史楼书目》一册,蓝格,书口下方印有“铸学斋”三字。浙江图书馆藏本著录书名、卷数、著者、版本,比国家图书馆藏本多著者一项,但著录书籍数量比国家图书馆藏本少。如:国家图书馆藏本易类书籍有二十五种,而浙江图书馆藏本仅著录八种;国家图书馆藏本书类有十九种,而浙江图书馆藏本仅七种。国家图书馆藏本的编成时间可能晚于浙江图书馆藏本。另外,浙江图书馆还有抄本《述史楼藏书目》一册;湖北省图书馆藏稿本《述史楼语古录》一册,蓝格,书口下方印有“铸学斋”三字,首列“精本书目”百余种,其中抄本六十余种,属徐氏藏书上品。
5 《虞山毛氏汲古阁图》[明崇祯十五年(1642)王咸绘本。书号:09656]
古今文字奥,读者圣贤跻。朝廷置写官,卷轴分绿绨。天水富雕板,官私名各题。汲古多储藏,善本互考稽。高阁倣石渠,罗列如町畦。晨兴或启椟,夜坐偶然藜。风流三百载,迄今无与齐。乙亥秋日,李盛铎题,男少微录。
按:长洲王咸(字与公)在明崇祯十五年(1642)应毛晋之请,为汲古阁绘图并系五言诗一首。王咸题中曰“予寓读湖斋,遂盈一纪”,可见其与汲古阁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其寓居汲古阁之时,曾襄助毛氏勘校书籍。国家图书馆藏元至正元年(1341)集庆路儒学刻明修本《乐府诗集》,乃毛晋、王咸据钱谦益藏宋本手校并题跋,并以此为底本刊成汲古阁本[16]。《虞山毛氏汲古阁图》在嘉庆间为嘉定瞿中溶购得,延请钱大昕、黄丕烈、顾广圻、段玉裁、钮树玉等三十位著名学者题诗,多沿用王咸题诗原韵,盛赞汲古阁藏书、刻书事业,使得文物和文献价值倍增。道光间转归上海徐渭仁,又请韩崇、杨文荪等续题。关于《虞山毛氏汲古阁图》流传及题跋,郑炳纯《汲古阁图及诸家题咏》[17]一文已有著录与研究。陈红彦《明崇祯十五年绘本〈虞山毛氏汲古阁图〉》进一步提到:“徐渭仁之后,此画曾为著名藏书家李盛铎收藏,后转归银行家许汉卿手中,并于1938 年请人重装。”[18]1949 年前后,陈澄中携往香港,20 世纪60年代由国家回购,入藏国家图书馆。
李盛铎题诗在1935 年秋,由其第十子李滂(字少微)代为录写。民国时期曾有连史纸套色影印件,含李盛铎题诗,说明是在1935 年之后影印的。瞿凤起《虞山毛氏汲古阁图题咏》云“曩年武进陶兰泉湘书据以石印”[19],这说明民国影印本可能是陶湘所为。李盛铎对毛氏汲古阁藏书、刻书、抄书极为推崇,其藏有毛氏影宋抄本《九僧诗》(现藏国家图书馆)、影宋抄本《谢宣城集》(现藏北大图书馆)、毛氏抄本《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现藏北大图书馆)、明抄毛校《宋元名家词》(现藏北大图书馆)等皆属汲古阁精品。李滂继承了盛铎的藏书事业,并在版本目录学领域有一定的成绩,撰有《黄荛圃先生年谱补遗》一卷、《宋金元本书行款考略》六卷、《二十四史疑年录》十二卷、《息厂读书随笔》十卷、《校书述例》二卷、《麐嘉居士年谱》《近代藏书家考略》等[20-21],李氏藏书最后由其经手售归北大图书馆。
6 《忆书》[六卷,(清)焦循撰,清光绪间李盛鋐抄本。书号:11848]
此为少轩六弟手钞。弟名盛鋐,戊子优贡,朝考以教职用,写是书时在癸未、甲申间也。辛酉六月捡书因记。茮微。(下钤“木斋”朱文印)
按:《忆书》(六卷),焦循撰,辑录平日所见奇闻轶事,共一百三十余条。稿本在上海图书馆,卷末有赵之谦跋语。光绪间赵之谦得手稿本,删节“微伤忠厚”者十条,刻入《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李盛鋐抄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黑格,黑口,左右双边。卷端钤“李盛铎印”“木斋审定”,抄写工整。卷末李盛铎跋语曰“写是书时在癸未、甲申间也”,即光绪九年至十年间,彼时《鹤斋丛书》还未刊印。详校诸卷,李盛鋐抄本恰比《鹤斋丛书》本多十条,应是据稿本抄录,具有校勘价值。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卷末赵之谦跋语云:“光绪九年,儿子寿佺见之扬州市肆,书来告余,因命购归。朱君养儒闻余之求是书也,买以见赠。十年三月,始寄南城。”[22]李盛鋐抄录当在赵之谦得书之前。李盛鋐,字少轩,生于清同治三年(1864),为李盛铎叔父李明塾长子[23]。此跋作于1921年,彼时李盛铎已辞官隐退,寓居天津,专注于藏书、校书。李盛铎向来对焦循著作十分用心,其收藏有焦循稿本《注易日记》、稿本《大衍求一释》、手抄本《西镜录》等,今存北大图书馆。另外,在《木犀轩丛书》中重刻了焦循的《易余龠录》《论语通释》《开方通释》。
7 《席上辅谈》[二卷,(宋)俞琰撰,明抄本。书号:08354]
沅叔新得此本,持校宝颜堂所刻,互有胜处。戊辰长至,李盛铎。
按:此本为傅增湘旧藏,后转售周叔弢,今在国家图书馆。半叶十行,行十七字。卷末录商丘老人宋无志跋,曰“玉吾余友也”,知宋无志与俞琰生活在同一时期。宋跋后有“常熟周异缮写”一行,周异或即此本抄写者。又有朱存理、沈文、金俊明、黄丕烈、李盛铎、邵章跋,钤“停云”“凤巢藏书”“俊明”“孝章”“黄丕烈印”“秋清逸史”诸印,递藏之迹可以考见。《藏园群书题记》卷十“明钞本《席上辅谈》跋”及《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皆录诸家跋语。朱存理注意到了书名和卷数的问题:“旧见俞氏家集云腐谈四卷,今止二卷,卷后有宋无志跋,盖全书也。今本曰辅谈者,恐后世易此字,非以音相近而致讹也。”[1]526《四库全书总目》则言:“考《永乐大典》所引或作辅,或作腐,参差不一。观存理跋,知当时本自异文,非有两书矣。”[24]今传明清诸抄本、刻本,有作“辅谈”者,亦有作“腐谈”者。众书目著录有“一卷”“二卷”,乃因原书分上下卷,著录规则有别也。传世之本未有四卷者。
李盛铎言“持校宝颜堂所刻,互有胜处”,“宝颜堂所刻”指明嘉靖陈继儒编纂的《宝颜堂秘笈》,共六集,收书二百余种。傅增湘也曾取《宝颜堂秘笈》对校,改定凡八十一字,较刻本为长者多。李盛铎藏清抄本《席上辅谈》二卷,现存北大图书馆,内有据傅增湘藏明抄本校改处[11]29。邵章跋语云:“戊辰一岁中,藏园主人所得书以宋抄《洪范政鉴》为称首,次则正德抄本《席上辅谈》……十二月岁除前二日,举行祭书之典,沿往例也。”[1]527能入藏园祭书会,足见是本之精善。李盛铎跋语作于“戊辰长至”,即1928 年夏至日。
8 《月屋漫稿》[(元)黃庚撰,清康熙十二年王乃昭抄本。书号:08504]
天台山人《月屋漫稿》,一名《月屋樵吟》,余曩年曾假钞一帙,嗣得刘燕庭藏本,经前人校勘者,以为精美。兹又获见嬾髯野叟王乃昭手录本,谓“得元人手钞天台山人集,喜而录之”,末有“清源门壻林伯良编集”“西秦菊存张楧校正”字样,为他本所无,因以重值收之。当携归南中一校,必有异同也。丙寅元日试笔。盛铎。
按:《木犀轩藏书书录》著录《月屋樵吟》一部,言“自序题‘漫稿’。铎从旧钞本传录。”[11]313盛铎跋语中“余曩年曾假钞一帙”当指是本。《书录》又有旧钞本《月屋漫稿》一部[11]33,嘉庆、道光间谢宝树校并跋,或即经刘喜海收藏者,两本今俱存北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抄本卷末有王乃昭识语:“康熙癸丑小春廿有四日,嬾髯野叟偶得元人手钞《天台山人集》,喜而录之,时年六十有六。”[25]故而著录为“康熙十二年王乃昭抄本”。王乃昭为明末清初藏书家。钤印有“王氏乃昭”“谦牧堂藏书记”“兼牧堂书画记”“礼邸珍玩”“周暹”,知其先后经纳兰揆叙、礼亲王昭梿、李盛铎、周叔弢收藏,后归国家图书馆。
《月屋漫稿》不见元代刻本传世,一度被认为是伪书,王乃昭抄本恰好提供了诸多证据①杨镰在《元诗文献辨伪》(《文学遗产》2009 年第3 期)一文中明确“《月屋漫稿》与《月屋樵吟》都是伪题书名、虚拟作者。”叶会昌《<月屋漫稿>“伪书说”考辨》(《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9 年秋之卷)对杨文观点进行了反驳。。
李盛铎在跋语中说:“末有‘清源门壻林伯良编集’‘西秦菊存张楧校正’字样,为他本所无,因以重值收之。”这说明他已经注意到了王乃昭抄本在版本和辨伪方面的独特价值。王乃昭在康熙十七年又将《月屋漫稿》抄录一部(大仓文库旧藏,今存北大图书馆),卷末亦有林伯良、张楧题名。王氏抄本之外,清代还有金俊明抄本、王闻远抄本,卷末均有林、张二人题名。林、张皆为元人,可视为《月屋漫稿》成书于元代之一证。
9 《攻媿集》[一百十二卷、拾遗一卷,(宋)楼钥撰,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五年广雅书局重刻《武英殿聚珍》版。书号:387]
沅叔是本缺校此二卷,假吴氏藏宋本补之。丁卯处暑后一日,盛铎。
按:是书为傅增湘旧藏,诸卷末有傅增湘识语,然识语均极为简短,主要注明校勘时间。如卷二十末叶识曰:“丙寅正月十一日校宋本,订正五十六字。”[26]傅氏在丙寅正月十一日至二月廿二日据宋刊本校勘,并补抄缺文,书末附纸补录了缺卷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真德秀序言、目录。那么,傅氏所校宋本是谁收藏的呢?《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四载宋刊本,言“余尝取校聚珍本,补正甚夥,别为跋详之。(瀚文斋送阅,徐梧生遗书,丙寅正月十一日。)”[8]1033傅增湘据校宋本即指是本。傅氏又著录宋本钤印有“吴”“孟章”“青华小阁藏”“楝亭曹氏藏书”“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印”“滇生珍藏”等印[8]1033。此宋刻今在北大图书馆,为《攻媿集》传世唯一宋刻本。从钤印看,先后经徐乾学、曹寅等递藏,近代归徐坊。李盛铎跋语在傅增湘旧藏本卷五十末叶,言语中可知傅氏未校勘卷四十九和卷五十,盛铎助其补校。李氏言“假吴氏藏宋本”,吴氏即吴孟章,与傅氏据校本当指同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