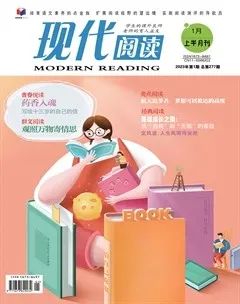苏堤
我们游了三潭印月回到船上,月亮已经从淡墨色的云堆里逃出来了。水面上静静地笼罩了一层薄纱。
船向博览会纪念塔驶去。张忽然指着我背后的方向问道:“前面是什么地方?”
“那是苏堤。”黄接口说。他们说的是那一带被黑黝黝的树木遮掩了的长堤。
“要是能够上去走走也好!”张渴慕似的说。
“那里灯也没有,又没有码头,不好上岸。”船夫用干燥的低声回答我们。
“不行,我们一定要上去。你看现在月亮这样好。机会万不可以失掉。”张热心地说。
船到了苏堤,船夫停了桨,说:“你们先生看可以上去吗?”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可以上去。这一带尽是树木,并不很密,树丛中也有可走的路。
“等我试试看。”黄马上站起来,拣了干燥的地方走上去了。他站在树丛中,回头叫我们。
“先生,我不划了。请你把钱给我,让我回去吧。”船夫说。
“为什么不肯划呢?”我惊讶地问,“我们还是照钟点算钱,上岸去玩一会儿,你不是可以多得点钱吗?”
“你们上岸去,又不认识路,说不定把路走错了。会叫我等三五个钟头。”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我气愤地对站在堤上的黄叫道:“黄,不要去了。他不肯等我们。他疑心我们不给他船钱,就从岸上逃走……”
“你快点上来,不要管他。”张这样催促我,我没法,只得把脚踏上岸去。船夫忽然抓住我的膀子。我吃惊地看他一眼。虽然是在树荫下,月光被我们头上的树叶遮住了,朦胧中我看不清楚他的脸,但是我却仿佛看见了一对忍受的、苦恼的眼睛。①
“先生,请你看清楚这只船的号头,请你放点东西在船上……”
我不再听下去了。他还是不相信我们。我一定要使他明白自己的错误。如果我留下东西,岂不是始终没有机会向他证明我们并不是骗子吗?我短短地说了“不要紧”三个字,就迈着大步走上去了。
我们已经走出了树丛。现在是在被月光洗着的马路上了。眼所触,都是清冷、新鲜。密密的桑树遮住了两边的景物。偶尔从枝叶间漏出来一线的明亮的蓝天——这是水里的天。
“你还叫我们不要上来,你几乎受了船夫的骗。”黄得意地对我说。我只是笑。我觉得我笑得有点不自然。我在赶走我脑中的另一种思想。
我突然被一种好奇心抓住了。我想要是我们果然就在白堤上坐了车回旅馆去呢?我们明天就要离开杭州了。我们是很安全的。而他呢,他就会受到一次惩罚了,他会后悔不该随便怀疑人。他会因为这笔快要到手却又失掉的钱苦恼,或者他竟然会因此失去一顿早饭。于是我的耳边响起了他的自怨自艾的话,他的叹气,他的哭泣,他的咒骂。我觉得我感到了复仇心和好奇心的满足。
过了一些时候,我开始感到心里空虚了。这时候我再想到逃走的打算,觉得毫无意义。我只感到一种悲哀,一种无名的悲哀。
走过了最后的一道桥,我们走完了苏堤。
船摇过来了。
我不由自主地看他的脸。他无意间把头往上面一仰,月光在他的脸上掠过。我看见那是一张朴实的、喜悦的脸。我觉得自己也被一种意外的喜悦感动了。②
最后,我在他应得的船钱以外,多付了一半给他。他非常喜悦、非常感动地接了钱。
我问他:“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只有一个女儿……十多岁的女儿……她在家生病……我现在就要去买药……”他断续地说,他的喜悦在一刹那间完全消失了。③
我呆呆地立在码头上。我想不到会从他那里听到这样的答话。
他忽然拔起脚就跑,一转眼间就消失在人丛中了。(来源:当代世界出版社《巴金经典作品》)
·文意点睛·
脆弱的信任纽带
文章题目为《苏堤》,却非写景散文,“苏堤”只是线索,作者写作的重心是船夫与“我们”的故事。
张、黄两人不顾船夫的反对,执意要游苏堤,船夫担心“我们”一走了之,这种不信任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上岸之后,“我”一面猜想船夫因拿不到报酬而自怨自艾,一面又想到这对船夫是一种精神折磨进而感到内心空虚。
这正是本文的动人之处,作者对底层民众有着深刻的同情,这种同情在文章的结尾处“我呆呆地立在码头上”得到了极大的升华。同时,这也让读者理解了船夫,人物的深刻性在结尾得到了极致的展现。
·写作借鉴·
一波三折
对于叙事作品,我们经常讲“文似看山不喜平”,就是写文章要有起伏和波折。具体到本文,一开始船夫反对游苏堤,且希望“我”留下东西作为抵押。读到此处,我们虽也觉得张、黄有点雇主的脾气,不能理解船夫的为难,但也觉得船夫挺势利的,不能信任人;读到结尾,知道船夫如此行为是为了尽早地拿到钱给女儿买药,我们才发现自己错怪了他。
在这里,情节发生了逆转,船夫前文所有的焦虑和不配合,成为我们理解人物的线索,使得人物形象更为深刻和生动,也更能打动人。
传神的神态捕捉
“我”每每看向船夫,捕捉到的不同神态,实则层层递进着人物线索,牵引着“我”的情绪,感染着我的“行动”,暗示着情节的走向。文中①②③处船夫神态的微妙变化,令船夫的形象更为立体、鲜活。
细腻的心理描写
本文不仅仅写了一个值得同情的底层的船夫,也写了一个能够“同情和理解”底层民众的“我”。
在“我”不顾船夫反对,不留下任何东西离开船后,“我”一开始是“感到了复仇心和好奇心的满足”:想象船夫得不到报酬的苦恼,想到他可能因此失去一顿早饭,想象“他的叹气,他的哭泣,他的咒骂”。
但是,这种复仇的快意很快转化为“空虚”“悲哀”。这种悲哀,就是对底层民众的深深同情。 (分析人:许泽平,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