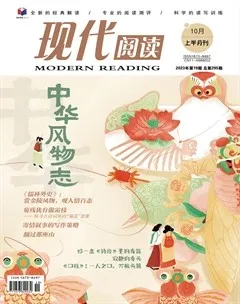《背影》:从隔阂到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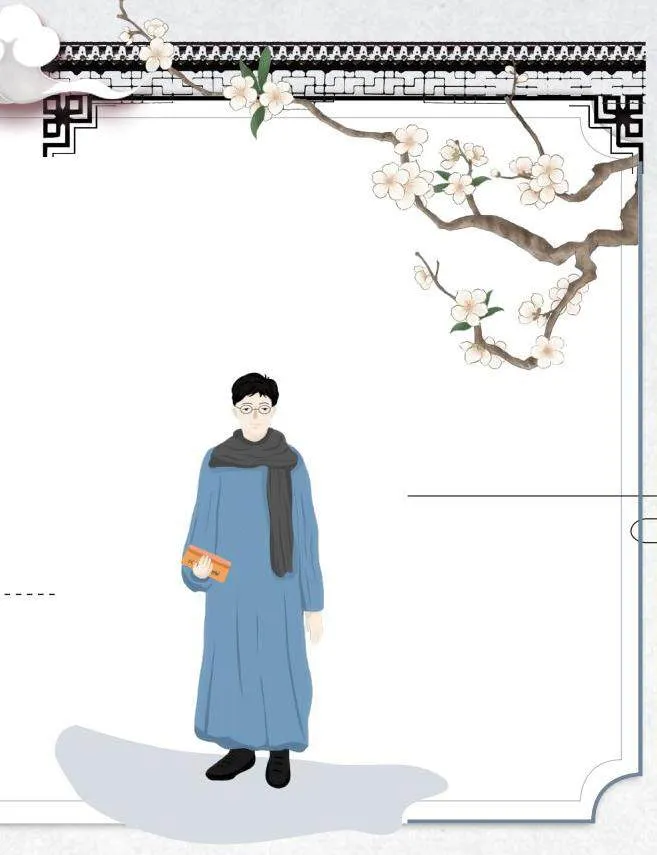
朱自清的散文名作《背影》,其主题历来被解读为表现“父子深情”,叶圣陶先生就认为《背影》写了“父亲爱惜儿子的一股深情”(《文章例话》),大部分语文老师在探究这篇作品的主题时,往往也会在这一点上着重用力。
《背影》真实而诚挚地表现了父子深情,这一结论不应有异议,毕竟有感人肺腑的车站送别为证,有动人心弦的“四次背影”和“四次流泪”为证。然而,我们也不得不说,这种认识是略显单一的、浅表化的,是几乎所有阅读者都能够一眼洞穿的,既忽略了文中的迂曲深婉之语,又没有提供它之所以成为不朽经典的更充足和更合理的证据。
对本文主题的解读之所以长期止步于“父子深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只把《背影》当作写人记事的记叙文,而不是当作以事写人并带有强烈抒情意味的散文,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记叙文的各要素及其各要素的印证上,殊不知对文本的形象性和情感性的探究、对作品深层意蕴和言外之意的叩问,才是打开这篇经典的正确方式。诚然,就自由阅读而言,不妨深者见深、浅者见浅,但从语文教育的立场出发,还是要透过语言的表象,还原人物的真实样貌,倾听作者内心深处细微的声音,这是有意义教学的应有之义,也是培养学生理解力、阐释力和鉴赏力的有效路径。
错位的父子之情
理清时间线索在《背影》解读中是十分重要的。为此,我们必须了解“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中,“二年余”之前是哪一年;“那年冬天”亦即父亲赋闲、祖母病故、浦口分别是哪一年;作者写作此文又是哪一年。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把《背影》当成一般意义上的回忆,而是把它视为作者在某一历史语境中的情感史和精神成长史。我们才会明白:《背影》中父子之情是错位的、不对等的。父亲把儿子当作永远的孩子,无微不至,照顾有加;儿子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说话漂亮的成人,并总是暗笑父亲的“迂”。“父爱子”一以贯之,尽管在不同境况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子爱父”却有一个十分纠结的过程。父亲对儿子的爱是无条件的,儿子对父亲的爱则是“有看法”和“有计较”的。正是这种错位,构成了《背影》的丰富内蕴和美学张力,也正是对这种父子关系普遍性的揭示,使得它拥有了能够引起广泛共鸣的情感基础。
父子关系在反思中“和解”
当然,理清“我”的心理发展线索同样重要。“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为什么?在这之前还发生过什么?“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我”到底有怎样的“不好”?作品开头段和结尾段中的这两句话容易被忽略,我们只有弄清其中的来龙去脉,才能真正搭建起走进文本内核的背景支架,才能在草蛇灰线中发现静水流深、不足为外人道的情感秘密。
众所周知,《背影》叙及的故事发生在1917年,朱自清“那年已二十岁”,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背影》写作的时间是1925年,此时他已是清华大学的教师了。从“为人子”到“为人父”,八年之中,他的反叛让位给了反思,他的感性逐渐让位给了理性,他与父亲之间的“战争”,也在时间和自我诘问的共同作用下终于落幕了。
而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两个“自然”之中。“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所有的摩擦与疏离,都在这两个“自然”中—在现在的“我”对过去的“我”的解剖中,在“回忆者”对“亲历者”的检省中—涣然冰释了。因为懂得,所以柔软;因为懂得,所以放下。
“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们常会忽略父亲信中的这段话,然而,父亲的这段话却是我们沿波讨源的重要入口,寥寥数语中,自有深意存焉。父亲的体谅,父亲在某种程度上的“服软”,不仅有对儿子的理解,也有对岁月的臣服。“身体平安”与“大去之期不远矣”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而这正是一个心气不再的父亲的无所遮掩的表达:一方面不希望儿子为自己担心;一方面又通过这种“言过其实”的话语,唤起儿子的注意。父亲的要强此时完全被无力感和倚赖感所代替,当年“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的父亲已成为一定程度上需要儿子的情感支持而活着的垂垂老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段话不仅是我们发现作者写作动因的锁钥,也是我们窥探作品“从隔阂到和解”的深层主题的通道。而所谓“和解”,与其说是与对方的和解,不如说是与自己的和解。时移势殊,血浓于水,他们卸下情感的铠甲,终于回到了父子关系的本真状态。就这样,作者将浓郁的情感凝聚于孤寂落寞的“背影”之中,同时又历时性地、或显或隐地表现了父子之间情感的变化过程,从而在“个人情思”之中赋予了“天下父子”的普遍意义。
对《背影》主题的解读,应该包括“父子情深”和“父子关系由隔阂到和解”这两个层面。只关注前者,未免失之浮浅;只关注后者,又容易滑向文本之外,在知人论世上走得太远。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是立体的、完整的、圆融的、符合文本内在逻辑的,有助于学生审美能力的发展与进阶的。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朱自清的父亲是1945年,也就是写这封信之后20年才去世的,所以,父亲信中“大去之期不远矣”的说法十分值得玩味。统编版教材助学系统的补白文字中有一段朱自清三弟朱国华的回忆,他写道:“父亲在看到《背影》的几年后,便去世了。”这里所说的“看到《背影》”的时间应该是1928年,也就是《背影》问世之后的第三年。显然,朱国华“几年后”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不知这是作者的笔误还是编者的疏漏,不管怎样,把长达17年的时间表述为“几年后”,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
(注:链接《语文·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