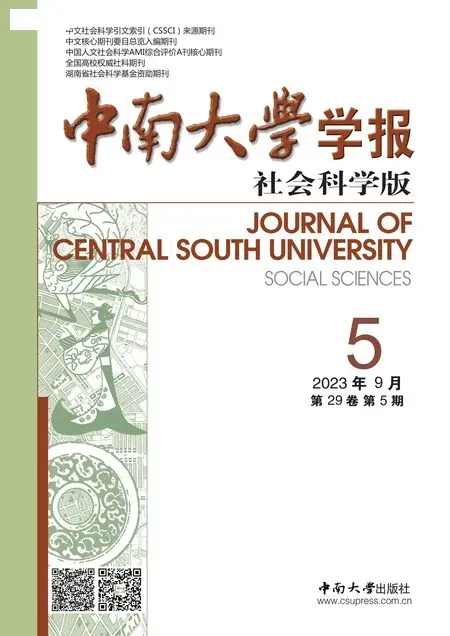以传统作为参照系——贡布里希对现代艺术观念的理解与批评
牟春
以传统作为参照系——贡布里希对现代艺术观念的理解与批评
牟春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200234)
贡布里希对现代艺术思潮的关切与他对西方艺术传统的研究密不可分。他追源溯流,把表现主义、原始主义、立体主义等现代艺术运动联入西方艺术史的整体叙事之中;通过对个别艺术家、艺术作品的独到阐发,呈现现代艺术观念图景的复杂画面;从具体的文化传统与艺术语境入手,分析现代艺术思潮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克服与现代艺术相关的流行见解,同时也拆解抽象措辞对现代艺术进行的理论虚构。贡布里希对现代艺术观念的阐释力度源于他以传统为参照系,通过艺术史叙述,让传统思想和当下观念互鉴,使传统成为深刻理解当下和承载未来可能性的源头活水。
贡布里希;现代艺术观念;传统;参照系
1960年,贡布里希的成名作《艺术与错觉》由费顿出版社出版,引发了学界对再现视觉心理学问题的热议。此后,他的《图像与眼睛》、研究文艺复兴艺术的四卷论文集,亦聚焦于西方传统再现艺术。这些研究主题使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贡布里希是一名复古主义者,只推崇西方传统的错觉性写真艺术。此误解进而又衍生出两个流行的主张:一是贡布里希对其他不以写真为目标的艺术抱有成见;二是贡布里希轻视、指摘甚至憎恶所有非写真性的现代艺术。化解第一个流行主张比较容易,只要读读贡布里希对中国艺术、漫画艺术、现代招贴画的诸多精彩解读和赞赏之词即可。但要破解后一个有关贡布里希鄙视现代艺术的流行主张,却得花些气力。因为贡布里希从不掩饰他对20世纪先锋艺术实践的批评,他的主要工作,甚至其毕生的努力,就是揭露各种流行的虚假现代艺术观念,把人们对现代艺术的理解汇入艺术史的整体叙事框架之中。这使他赢得了“逆向思想者(reverse thinker)”[1](836)的称号,也使他与各种决意与传统疏离甚至决裂的现代艺术思潮形成了对峙之势。
一、瓦解理性传统与历史间距的表现主义
在《世纪末的维也纳》这本探讨早期现代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卡尔•休斯克曾指出,从18世纪到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甚至现代主义学术走过了从“反对”过去到“独立”于过去的征程,以至于“现代心灵对历史越来越漠不关心,因为被视为一种持续提供滋养传统的历史,已经毫无用处了”[2](1)。然而,休斯克恰恰以思想史的方式,描述了19世纪末维也纳现代主义艺术摆脱历史桎梏的诉求,以及它的观念温床和意识链条,提供了对历史与传统的有力辩护。贡布里希对现代艺术起源和发展的铺叙与讨论,同样致力于此。贡布里希最为脍炙人口的艺术史著作《艺术的故事》,为艺术爱好者勾勒了一份艺术史地图,叙述了艺术不断演进发展的故事。在这一故事中,各个事件经纬交错的端绪,及其内在联络的线索,乃是问题的出现和解决。对贡布里希而言,在艺术发展过程中,任何原有问题的解决都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被统称为“现代艺术”的各种思潮也不例外。和休斯克一样,贡布里希对现代艺术起源和发展的铺叙凸显了历史叙述既是理解当下的有效手段,也是激活传统和丰富传统的最佳途径。
印象派艺术的确取得了更为真实自然的光影效果,但它的这一成功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塞尚敏感于瞬间印象造成的物象恍惚,希望重拾物象的稳定感与坚实感,开启了立体主义的探索;高更不满于印象派在光影关系上的精心设计,渴望艺术重回质朴单纯的境地,引发了原 始主义的觅求;凡•高则警惕单纯视觉印象对情感的剔除,着意为艺术贯注富有感染力的激情,带动了表现主义的追寻。贡布里希把这三位现代艺术大师称为“现代艺术中三次运动的理想典范”[3](554−555)。然而,在人们对典范的竭力效仿中,在把典范树立为旗帜的过程中,典范却被简化为“偶像”,成了某种“主义”的代言人。现代艺术思潮所携带的流行观念之所以能深入人心,既源于人们对现代艺术家的作品与性情的仰慕,也源于人们对他们的误解。许多现代艺术家不善言辞,无法通过文字叙写其遭受误解的苦楚。不过,凡•高却是一个例外,他的信件和他的绘画一道,记录了他与各种浅薄观念的抗争。
麦格雷格考察发现,表现主义作为一种流行艺术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凡•高。1912年,在科隆举办的国际当代艺术展中,凡•高被视为“表现主义各种形式背后的先驱和刺激来源”[4](222)。 凡•高用色的浓烈及笔触的旋转极为触目,而其生活史又携带几分传奇色彩,很容易唤起有关“天才的疯狂”或“疯狂的天才”这类自柏拉图以来就蔓延不绝的遐想。直到18世纪,人们仍坚信天才和疯子只在外表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天才的“迷狂”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性迷狂。然而,到了19世纪,受精神病理学的影响,人们开始在天才身上寻找精神病的踪迹。20世纪初,表现主义的艺术思潮又鼓励人们从精神病人中发现天才。据传,在罹患精神病之前,凡•高为了创作就已试图通过抽烟和酗酒来达到神迷意醉的疯癫状态,而他后期的传世之作又产生于他罹患精神病之际。因此,长久以来人们不断揣测,凡•高的艺术作品是他精神无法自持的产物。然而,在贡布里希看来,凡•高本人的书信早已驳斥了这种把艺术表现等同于精神妄想的偏见。但其驳斥本身也表明,当时这种瓦解理性构思传统的表现主义观念已流布甚广。
“平衡赤、蓝、黄、橙、紫、绿六种基本颜色是件费神的事。这活儿需要大量工作和计算(calculation)……不要认为我故意使自己处于狂热状态。相反,请记住,我处于一项复杂的计算过程之中。计算导致了一幅幅快速挥就的作品迅速产生。不过,计算事先就得做完。所以,如果他们告诉你这幅画绘得太快了,你可以回答,他们看得太快了。”[5](606−607)凡•高告诫我们,切勿以为他在创作时处于某种不可理喻的疯魔状态,他抽烟喝酒只是为了放松,因为精心“计算”使他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太耗心神。在贡布里希看来,凡•高的“计算”肯定不是什么数字演算或公式推导,而是对色彩和笔触的相互配合进行综合性思考,揣测和检验下一笔的可能性与效果。与写真艺术传统中的众多大师一样,这种不断平衡、调试色彩和构型的事业无关神秘狂想,而是理性构思的能力。贡布里希之所以对凡•高的“计算”作出如此诠释,首先是为了应对彼时表现主义观念对传统创作论的挑战。正如坎利夫(Leslie Cunliffe)所言:“贡布里希所受的教育和培养为他研究古典文化传统、基督教文化传统、启蒙文化传统和浪漫主义文化传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习得这些教养的贡布里希当时正经历着维也纳现代思想和艺术实践对这些旧传统的冲击。”[6](61)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也纳甚至整个欧洲最为流行的现代思潮和艺术实践正是表现主义。深谙艺术传统的贡布里希的志向则是“去解释”这些新生的艺术现象,“从稍远的距离观察艺术的发展”,“看看到底发生的是什么”[7](82)。事实上,正是凭借对西方传统理性构思能力的深刻领悟,贡布里希才能与当时流行的表现主义艺术诉求拉开距离,成为凡•高艺术的真正“知音”。
凡•高对艺术抱有宗教般的虔诚,想使绘画获得直接感动人心的力量,这些成了后世追慕现代艺术的驱动力,却也成了鼓舞现代艺术家甚至普通人不断模仿的教条。模仿者们极力摒弃清醒的意识,意欲进入沉醉状态,认为借此便可获得凡•高超凡的创造力。在参观1912年科隆艺术展时,精神病理学家和哲学家雅斯贝斯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来自全欧的表现主义画作以一种惊人的单调包围着凡•高伟丽的作品,让我不禁感慨,在如此之多佯装狂人的正常人之中,唯有凡•高是真正伟大之人,他不愿发疯却发了疯。”[8](203)在雅斯贝斯看来,这些东施效颦的模仿从未使任何人获得艺术创造力,它们是表现主义艺术追求戏剧化情感的产物,反过来又推动了这种观念和情绪在艺术领域之外的流行。
凡•高的敏感细腻、深邃多情并不等于也不“导致”他精神失常;反之,他的精神失常也不是他成为出色艺术家的必要条件。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的转向之作《斯特林堡与凡•高》对此已多有论及。雅斯贝斯对当时各类表现主义艺术实践的评价是否恰当,我们无需多论,毕竟雅斯贝斯不是艺术批评家,也从未把自己看作一名艺术理论家。不过他对斯特林堡、凡•高、荷尔德林 等人的讨论确实触及了表现主义艺术观念的困境与危机。对此,长期反思艺术现象的贡布里 希更为敏感,论述也更为犀利。贡布里希生动地描述了20世纪初流行的表现主义艺术观念对“历史间距”和“艺术传统”的瓦解,以及这一瓦解带来的“解放”。
1912年科隆举办现代艺术展时,表现主义观念在艺术家中已广有市场;在这之后,它又辐射和渗透在艺术批评话语之中。其辐射度有多广呢?贡布里希观察发现,20世纪20年代中欧的批评家和艺术史家们仿佛瞬间获得了“上观千年、下观千年”的直观能力。古典时期、哥特时期、巴洛克时期的艺术,东方艺术与黑人艺术,都具有了直接的感染力,甚至仅观看其照片或图册,艺术品表达的“时代精神”亦能如在目前[9](100−101)。那么,其渗透力又有多强呢?在贡布里希看来,即便有意对抗和抵御表现主义观念的安德烈•马尔罗也在不经意间落入了表现主义的观念窠臼,“将每一位艺术家对形式语言的转变看作是一种自我张扬”[9](104)。贡布里希之所以在诸多著述中紧抓马尔罗不放,是因为马尔罗的著述既是表现主义艺术观念的产物和集中体现,也是其巨大的助推力。不过,让艺术品具有直接的感动力量,使心灵直面艺术获得超越古今、跨越文化的穿透力,把色彩和形状化为张扬艺术家个人情感的通用语言,这些使马尔罗臣服的表现主义观念,这些现代人对艺术想当然的期许,难道不曾受到现代艺术大师和艺术杰作(比如凡•高及其作品)的激励吗?就连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在其《论艺术》中也把艺术的实质归为“感人”。
当然,如果这些观念全然无理,那么它们就不可能流布甚广,经久不衰。然而,“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它们的虚假性也经不起理性的反思和审查。在贡布里希看来,各种表现主义艺术的感染力并不来自心灵情感的直接投射或直接接收,而是坐落在具体的文化语境和艺术传统之中。克莱因涂满蓝色的画面之所以带给我们震撼,并非因为他的表现主义式的主张,即纯色才能唤起最强烈的心灵感受,而是因为之前从来没有画家这么干过,其所为超出了我们对绘画的心理预期。假如所有的绘画一开始都是单色画,能带给我们震撼的就将是彩色画。要想识别蒙德里安《百老汇的布吉−乌吉》这幅画描绘的是一支轻松欢快的乐曲,想欣赏其“创意”,对观者的要求则更多。它既有赖于我们对蒙德里安绘画风格的了解,也有赖于我们对百老汇流行音乐的熟悉,而且我们还得领会绘画和音乐这两种艺术手段之间的匹配效果。因此,作为“艺术手段”的色彩和形状,既非艺术家个人感情的包裹皮,也非抽象“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它与“心理预期”和“等效问题”一道影响着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贡布里希把这三个因素比作艺术冰山隐没在水中的那九分之八,认为它们太容易被人们忽视,因此“许多美学家在此覆舟”[10](312)。而恰在美学家覆舟之际,表现主义对艺术作品直接产生感动的要求获得了其畅行无阻的通行证。
的确,如果不考虑文化语境,甩掉艺术传统,把“艺术手段”“心理预期”“等效问题”等抛诸脑后,你也能“欣赏”艺术,或许竟能获取更多的“感动”。毕竟,谁也阻止不了廉价的悲剧赚取无知少年的眼泪,亦阻止不了存心感动的你在艺术品前狠狠感动一番。然而,贡布里希提醒我们,应该“学会区分自我投射(产生)的刺激和那种源于理解(无论这一理解多么微弱与不完美)一件伟大的艺术品真正想要传达的内容的丰富体验”[9](107)。如果我们混淆了这两者,就等于把自己封闭起来交给了“神话”。在异想天开中“通古今之变”,任心灵在马尔罗的“无墙博物馆”中自由穿梭,这种掌握一切的感觉舒适惬意,省却了因不了解而无法欣赏某些艺术作品带来的羞赧与懊恼。因此,取消历史间距,无视视域融合所需的智性努力,乃是表现主义观念最为蛊惑人心之处,也是它最大的危机。
不过,另有一种表现主义的观点,主张所有往昔的艺术都是无法理解、无法靠近的神秘之物。乍看之下,这种“谦卑的”观点似乎与之前那种洞悉一切、轻松跨越历史的观点正相反。但在贡布里希看来,此类主张不过是表现主义放弃理性理解而向“神话”投降的另一版本,是把各种历史间距统统夸大为历史鸿沟的表征。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其中的一部分,难以理解其中的另一部分,而某一部分只有通过大量的努力之后才能理解。”[9](106)表现主义理论要么把艺术作品看作是清澈透明、一望而知的情感宣泄,要么把艺术作品归为迷雾 重重、无法接近的黑暗世界,这些非此即彼的 两极化主张皆出于对历史和传统的简单化处理,是情感上的懒惰,亦是智性上的不诚。它们都是情绪高涨、智性低下这一现代性文化病症的表征,而表现主义的流行观念既是其催化剂,又是其症状。
正是借助对西方艺术史的研究和古典教化传统孕育的理性常识,贡布里希才能把“神话”“激情”“无墙博物馆”等表现主义营造的“七宝楼台”拆了个七零八落。但凡•高的模仿者和倾慕者们可能依然“意难平”,在他们看来,即便凡•高的画作不是激情的宣泄,可他精神失常乃是事实,难道他的精神失常对他的创作没有影响吗?柏拉图所说的“迷狂”,尼采所谈的“酒神精神”,不正是指出了艺术家与疯癫者的一致性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把我们引向原始主义。比起表现主义观念,原始主义观念更富弥散性地体现在各种现代艺术思潮之中。不过,和包括表现主义在内的各种现代主义思潮一样,原始主义观念同样意欲瓦解传统与历史。正如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所言:“在现代性和历史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冲突,但这种冲突本身有其历史。”[11](88)正因如此,贡布里希才会以史家的眼光追踪表现主义与原始主义,以期化解凡•高的模仿者们渴望疯癫的执念。
二、意欲摆脱传统的原始性偏爱
如果说凡•高带动的表现主义意在对艺术传统发起某种“挑战”,那么高更催生的原始主义则是要“脱离”传统。无论是他以“要神秘”为名创作的画作,还是其只身前往塔西提的举动,都表明了高更对西方文明的极端厌恶。在他看来,只有未遭受文明腐蚀的原始世界才能克服文明的矫揉造作,因此他要不顾一切成为“原始人”,绘出“原始性”。对于那些对这个世界感到疏远隔膜、愤懑不平的敏感心灵而言,高更的传奇人生可能带有直接的救赎力量,回归原始、回归自然成了他们对抗主流趣味的旗帜。不过,这面旗帜之所以极富号召力,引无数艺术家、艺术批评家甚至普通人竞折腰,不仅是因为高更的传奇人生,更是因为人们从来未曾摆脱对原始性的偏爱。和表现主义思潮一样,原始主义运动也有一个悠长深远的观念传统。正因如此,贡布里希的最后一部著作《偏爱原始性》,力图勾勒“原始性偏爱”在艺术史中的前世今生。在这本书中,贡布里希以“原始性”概念为视角和切面,意欲勾连不同历史时期艺术向原始性回归的冲动,进而把原始主义艺术思潮绘入西方艺术史的大图景,重述整个西方艺术发展的故事。保罗•泰勒指出,贡布里希谈论艺术的第一部著作《艺术的故事》从叙述原始艺术开始,而他最后一部有关艺术的著作《偏爱原始性》则以谈论“原始性艺术”告终,因而使得“‘原始艺术’的概念充当了贡布里希身为美术史家的生涯的一种框架”[12](92)。
在贡布里希看来,人们对原始性的偏好来自对过度感官愉悦的回避性反应。太甜太软的东西吃多了令人反胃,精致华美的东西看多了让人心生厌倦,错彩镂金带来的雕缋满眼,终不及清水芙蓉来得自在自然。尽管这种以生理厌恶反应为起点发展起来的审美偏好在西方艺术史中一再现身,但直到20世纪它才发展为一场轰轰烈烈的艺术运动,一场回避媚俗的艺术运动。如果我们追问:何种艺术陷入了媚俗的泥淖之中?原始主义者将回答:几乎所有。流行的伤感艺术满是做作,官方的沙龙艺术令人厌恶,即便那些久负盛名的大师也因写实技巧高超而显得乏味无趣。难怪原始主义者们要逃离规则和传统,渴望退回到趣味未经技术败坏的“原始状态”。
据说,只有三类人尚停留在那高贵的“原始状态”之中:婴儿、精神病患者和当时仍处于部落生活状态的原始人。这种看法在20世纪非常流行,以至1930年法国蓬蒂尼召开的国际心理分析年会的主题便是“婴儿、原始人、精神病患者的心理学究竟是三种还是一种”[13](65)。同时,为了回到“原始状态”而对这三类人进行仿效也蔚然成风。儿童绘画受到崇拜和热议,因为他们的绘画不假参照、不施巧计,有原始的质朴风味;精神病患者的制像受到重视,因为他们的制像天马行空、富于原始的神秘感;高更等艺术家更是亲赴原始部落,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希望重获“混沌未开”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贡布里希看来,这些主动向儿童、精神病患者、原始人的“退行”虽打捞上了一些宝贵的财富,但也助长了许多虚妄不实的谬见。
儿童绘画真的可以不参照任何现成“图式”而从原始心灵与情感中流泻而出吗?贡布里希提示我们,儿童在成人的世界中成长起来,他们耳濡目染的物象功能丰富且形式多样,一旦懂得拿笔作画,儿童就处于绘画的传统之中了[10](101−102)。而且,艺术家效仿儿童画所取得的成功并不在于他彻底退回到了婴儿般的原始状态,而在于借助“退行”,他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意识的控制,达到了现存技巧无法达到的强烈效果。无论是米开朗基罗、丟勒这些偶绘“童心之作”的大师,还是毕加索这位决心效法儿童艺术的现代艺术领军人物,他们和漫画艺术家们一样,是在玩为世界重新分节的游戏①,而不是让理性彻底缴械投降。
贡布里希曾把彻底倒退之前的这段退行区域称为艺术的“特许区域”[14](243)。效仿儿童艺术的艺术家在这个区域活动,精神病艺术家亦然。凡•高、荷尔德林、梅塞施密特、约瑟夫森等人之所以仍能进行艺术创造,是因为他们停驻在这个区域。换句话说,他们并未彻底发疯。艺术史和心理分析学家恩斯特•克里斯研究发现,精神病艺术家们的艺术成就的确与其所患的精神分裂症相关,但这些成就并不来自精神病症本身,而是源自艺术家的强大自我对精神病患的抵抗。他们的自我还未被精神病患摧毁,自我的功能还具有某种程度的完整性,可以控制甚至利用伴随精神病症的“心理退行”[15](177)。由此观之,我们或可疏解上文凡•高的效仿者和倾慕者们的“意难平”。靠买醉发疯也许确能回到“原始状态”,却无法获得凡•高的创造力。凡•高之为艺术家并不在于他得了精神病,获得了所谓的“原始表现力”,而在于他强大的自我对“退行”的理性把控。表现主义和原始主义在对“原始激情”的期待和臆想中汇聚,使得现代人对原始人的想象越发充满了奇幻色彩。
然而,对贡布里希而言,现代人对“原始部落”“原始艺术”的浮想联翩不过是另一套现代主义的“神话”,因为“人类从来没有一切都是魔法的原始阶段”[10](96)。虽然列维•布留尔、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类学家发现感应思维、图像魔法的确在原始人的思维中大量存在,原始人理解事物“不需要经验来确证存在物的神秘属性”[16](56),但是除了迷信和施行巫术之外,原始人还得做很多事才能活下去。他们不可能一天到晚待在洞穴里画野牛图,等着野牛坐以待毙或从天而降,他们像我们一样,得烧火做饭、航海狩猎、辛勤耕作,并从这些实践活动中发展出赖以生存的技术。而他们制作的“艺术品”也像其他劳动实践产品一样,并非摆脱了一切技巧,有些绘制甚至可以达到技巧惊人的地步。我们在“原始艺术”中感到的神秘感,与其说是由于原始人身上有未经文明污染的“粗野质朴”,不如说是由于我们对其观念世界太过隔膜,因而只能对其进行虚幻性投射。
因此,不是说不可以对儿童艺术、原始艺术甚或精神病人的绘制有所偏爱,如果能达到“天工与清新”的艺术化境,谁会不偏爱呢?然而,在《偏爱原始性》的最后,贡布里希告诫我们,偏爱是为了借鉴而不是模仿,“退行”也不是要绝对放任,艺术家往往需要借助理性反馈牢牢把控走在其意图之前的物象;相反,艺术家越是想挣脱一切束缚,“越是偏爱原始,就越不可能达到原始”[14](295)。有鉴于此,我们便能理解卡里尔(David Carrier)对贡布里希艺术史观的准确概括:“正是通过理解非理性是如何被理性把控的,我们才能反观艺术史的本性。”[17]在卡里尔看来,贡布里希的艺术史书写与高更的艺术创作在这一点上并无差别,即他们都不是放纵非理性的原始性渴望,而是以某种方式对非理性诉求进行转化。正如笑话通过机智转化攻击性一样[18](86−88),高更的绘画通过理性构思转化退行的渴望,贡布里希则通过对西方再现传统的研究获得“心理学的定力和理解”,从而使“激情和非理性的力量停留在安全的港湾”[19](247)。
因此,亲赴原始部落生活的高更并非获得了“原始心性”,其绘画乃是自我意识利用“退行”的创造物。他的作品别具一格,使得高更对绘画至死不渝的奋斗精神愈加令人印象深刻。贡布里希对现代艺术家的传奇想象性元素深有洞见,但即便是他也承认,“被笼统地叫做‘现代艺术’的东西的确开始于反抗灵魂中的欺骗,或对虚假价值的激烈反叛”[9](169−170)。然而,贡布里希更希望我们警惕的是,当原始性偏爱从深流变为浮于表面的浅流时,当反抗演绎为冲撞和破坏所有的传统和规则时,当“退行”退到一无所退之处时,反抗与倒退将凝固成一个空洞的手势,进而会变成新的道德矫饰与灵魂欺骗。
的确,经过左拉、毛姆等艺术批评家、小说家的渲染,高更借原始粗野叫板艺术传统和社会准则的态度就更为激烈了。然而,贡布里希认为,我们不能把艺术家在某些场合的慷慨陈词与批评家的议论混为一谈,即便它们表面上看来并无不同[14](219)。事实上,贡布里希从不和个别艺术家争论,因为艺术家表达其思想的媒介并非其言辞而是其作品。贡布里希只和虚假的艺术观念较真,只向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借以侃侃而谈的概念和术语发问。在他看来,不是艺术家而是艺术批评家和艺术理论家,真正面临着与传统脱节的险境,同时也面临着无法进行深入自我理解的困难。如果“现代建筑、现代音乐、现代哲学、现代科学,所有这些在界定自己时,都不认为自己‘出自’过去”[2](1),那么贡布里希凭借历史与传统反思现代艺术思潮的方式自然会使他陷入某种孤军奋战、进退维谷的境地。
三、从再现传统获取意义的立体主义
与引领表现主义的凡·高和倡导原始主义的高更都不同,立体主义的开拓者塞尚似乎无意背离西方传统艺术的写真追求,他的理想是“依照自然重建普桑”,因为普桑所绘的形象轮廓坚实、自然美丽。然而,塞尚认为自己不可能跳过印 象派获取的真实视觉印象而简单地回到普桑,他得把印象派闪烁不定的瞬间印象与普桑绘画的视觉稳定性和意义统一性结合起来。在贡布里希看来,这本是两个背道而驰的要求,塞尚的成就恰恰在于他居然奇迹般地同时满足了二者的要求[3](539)。为了绘出“自然原本的面貌”,塞尚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不惜突破所有的传统构形法则。在一封给毕沙罗的信中,塞尚曾表达过他对传统明暗造型法的质疑:“植物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像橄榄树和松树总是保留着它们的叶子,倾泻在叶子上的阳光让我觉得物体的剪影不仅呈现出黑或白色,还有蓝、红、棕色和紫色的剪影。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但这与想用浓淡法让物体突出的手法完全相反。”[20](151)如果传统的明暗造型法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就把它扔掉;如果直线透视妨碍工作,那么就把它抛开;如果对事物进行局部变形可以更好地传达事物的坚实感与质地,那么放弃程式化的素描又有何妨。贡布里希指出,塞尚追随传统写真目标而放弃传统构形法则的实验其实引发了“艺术中的山崩地裂”[3](544)。因为正是塞尚启动了凡•高、高更等现代艺术家对“形象准确”的反叛,更引发了立体主义对定点透视写真传统的不满。
人们之所以要把立体主义先驱者的头衔加给塞尚,是因为塞尚试图增强印象派物象的空间感和体积感。然而,生活中我们对空间的感觉并非依靠小孔成像或单眼透视,我们在运动中用两个眼睛看世界,而且我们可以触摸事物。如果我们能把物象各个角度的样貌及其移动甚至是触觉信息统统加进绘画,那岂不是获得了塞尚梦寐以求的“自然原本的面貌”。这是曾使毕加索和勃拉克激动不已的理想,也是过去和现在某些理论家对立体主义所持的一般性解读,以至稍涉现代艺术的公众大多也是如此看待立体主义的艺术成就的。
然而,贡布里希完全不这么看。在他看来,如果硬要依据“立体主义”的名称,把增强空间感看作毕加索和勃拉克绘画的目标,那么“就应该宣告它的失败”,立体主义的真正成就在于“抵消了错觉主义解读的变形效果”[10](239)。也就是说,立体主义并非继承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写真传统,也未实现塞尚的目标与志向,而是发明了新的艺术游戏,开启了新的探索之旅。然而,要理解和进行这个新游戏,仍需参照以写真为目标的错觉艺术传统。换言之,毕加索、勃拉克的新奇物象必须参照写真再现的传统读图方式,才能获得其意义与令人惊讶的效果。
在贡布里希看来,立体主义绘画的意图是要把再现碎片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拼接组合、添加压缩,以制造一些矛盾线索,让我们在对二维图像进行三维解读时陷入“视觉僵局”。然而,只有获得了西方写真绘画的读图习惯,我们才能依照图像暗示出的某些线索对立体主义物象进行三维解读,把它们看成瓶子、罐子、小提琴。今天,由于写真图像的获得太过容易,我们把这种“惯习”看成了自古有之的当然之事,以至于在把二维图像读作三维世界的投影时,很少注意到二维图像与三维世界并非一一对应,一种二维图像其实可以有多种解读方式。据此,贡布里希才主张立体主义的“探索之旅中发现的大陆并不是第四维度的幻岛仙境,而是一个迷人的事实——视觉多义性(visual ambiguity)”[21](169−170)。
视觉多义性问题是贡布里希读图心理学的核心问题。心理学著名的图画《兔鸭头》便是 把我们平时忽略的多义性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许多杰出的漫画家之所以能绘出视觉双关,亦是利用了视觉的多义性。谈到“第三维的多义性”,贡布里希经常提到幽默大师索尔•斯坦伯格。在斯坦伯格的笔下,一条直线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是直线、桌子、天花板、铁路、地平线,等等,而拇指印则可以“读作”人的脑袋与凡•高的画。由于我们对意义统一性的寻求,视觉多义性经常是隐而不现的,而立体主义恰恰是通过抵制一致性的解读而迫使我们承认:我们面对的不是瓶子、罐子、小提琴等三维世界的提示物,而是“一幅画”,一个二维的图像。正如贡布里希所言:“在立体主义绘画中,再现线索的功能不是向我们提供关于吉他和苹果的知识,也不是刺激我们的触觉,而是缩小可能的解释范围,直至我们被迫接受这个平面图案及其内部的一切张力为止。”[10](243)
立体主义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成就,恰恰是因为作为读图者的我们熟知写真绘画的读图模式,既熟知其构型法则,也熟知其指示光线色彩的明暗标记,因而不自觉地要把二维图像投射成三维世界的真实事物。对一个把“图画文字”作为读图心理定向的埃及人而言,立体主义绘画大概既不会带来困惑,也不会带来惊讶。立体主义营造“视觉僵局”的成就也可以用艺术史上的一则轶事加以解释。据说,有位参观画展的女士嫌马蒂斯把女人的手臂画得太长了,马蒂斯回答说:“夫人,您弄错了。这不是女人,这是一幅画。”马蒂斯的嘲讽即是立体主义的提示,他们使我们注意到“图画艺术”这一类的目的独立性,并催促我们对自己的读图心理和读图过程进行反省。而我们默认的读图心理正是由西方传统写真绘画奠定的,我们早已习惯了写真照片和霓虹灯广告营造的写真图像世界,习惯了把这些图像解读为周遭真实存在的事物。事实上,如果那位受到马蒂斯嘲讽的女士不具备从绘画人物指认现实人物的强烈意图,马蒂斯的嘲讽和立体主义的游戏都将无的放矢、烟消云散。因此,立体主义的探索和游戏虽未继承西方艺术传统的写真目标,但却是写真传统孕育的奇花。离开了写真传统的土壤,这朵奇花不是要枯萎,而是一刻也无法存在。
贡布里希参照写真传统对立体主义艺术成就的重新解读,并非着意于向艺术家发难,而是要挑战大众共享的时髦观念,以及艺术批评家、艺术理论家创制的抽象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贡布里希继承了文化史家布克哈特的历史意图,即在不同时代观念的对照中阐明流行观念的意义和局限。同时,贡布里希也和他所看重的莱辛一样,是“一个真正的苏格拉底式人物”[22](57),不断对浮华浅薄的时兴舆论与故弄玄虚的深奥言辞开战。然而,扑灭流行见解中诱人的鬼火,拆解抽象措辞营造的空中楼阁,也许既有可能得罪爱好艺术的大众,又有可能惹恼以专家自许的同行,但作为一个跟随苏格拉底对真观念抱有执着态度的艺术史家,贡布里希不可能三缄其口,明哲保身。其实,正是对流行见解和抽象措辞双线作战的学术进路,使贡布里希对现代艺术思潮的诠释、反思和批评获得了深度和力度。贡布里希奋战的武器既来自他对西方写真艺术传统的深入研究,也来自他史家的深邃眼光,即他把各种艺术传统作为反思现代艺术之参照系的努力。
四、传统作为参照系的两重意义
作为现代艺术运动的典范人物,凡•高、高更、塞尚生前都默默无闻,几乎没什么人能理解他们的工作;直到死后,他们的作品才进入博物馆为世人瞩目和崇拜,成为价值连城的私人收藏品。这一点给艺术家、艺术批评家和公众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艺术家都是具有前瞻性的先知。于是,一边是遗世而独立的天才艺术家,另一边是不知所措的批评家和愚昧无知的公众,好像这种分离对立是天然之事。然而,纵观西方艺术发展历程,无论是在希腊时期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们往往生前就受到批评家们的认可和公众的仰慕,他们的分道扬镳是直到印象派才发生的事件。贡布里希分析这一分裂事件的视角相当独特,他论述的重点不是艺术家的独创性和公众的保守性之间的冲突,而是印象派的艺术革新为何那么快就得到了公众的接受和认可。“相对而言,青年艺术家的那些观点遭到抵制大概并不奇怪,而它们很快被视为理所当然却令人惊讶。因为尽管斗争是那么剧烈,当事的艺术家是那么艰苦,然而印象主义获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3](522)印象派艺术之所以极富视觉冲击力,是因为它动摇了公众的视觉稳定性,强烈撞击着人们日常观物的分类框架,改变了通常的视觉语言。然而,这一切若没有乐于参与这场视觉投射游戏的公众,别说获得成功,就连其所谓的“视觉冲击力”也会变得无从索解。在贡布里希看来,现代艺术家传记和小说不断书写艺术家与公众的激烈对抗,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艺术家创造了自己的巨擎,巨擎也创造了自己的艺术家”[10](196)这一更为根本的事实。
贡布里希之所以能以如此独特的角度分析印象派的这一事件,处理艺术家和公众简单对抗的成见,是因为他对西方艺术的整体发展有了如指掌的通观,对不同历史时期艺术观念的更替转换有超乎寻常的敏感。可以说,正是通过对各个时期艺术传统的深入研究,贡布里希获得了史学家所应具备的超然而博大的眼光,使他能与他所处的观念环境拉开一个有效的反思距离。正如伍德(Christopher S. Wood)所言,贡布里希从不轻易接受现代哲学家对现代艺术的观念引导,无论是大名鼎鼎的尼采、海德格尔,还是他著名的同侪阿多诺、梅洛−庞蒂,即便现代哲学与现代艺术观念之间确实有一种亲和力[1](837)。贡布里希更多采用了历史的视角和心理学的方法来考察他所关注的现代艺术,因而许多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现代艺术观念就不再那么理所当然了。艺术是个体情感的自然宣泄,是直接的表达和自发的本能吗?如果得知这种表现主义的艺术观点源于浪漫主义传统对灵感的极端强调,也许我们就不得不怀疑它的可信程度。艺术家应该剔除技巧回归原始状态才能摆脱矫揉造作的程式化制作?如果对儿童艺术、精神病艺术和原始艺术的复杂性稍有了解,大概我们就不会迅速陷入对原始性的单纯渴望之中。立体主义、抽象主义、行动画派等不断更迭流行的现代艺术思潮是历史进步不可阻挡的力量和表征?如果我们得知这种进步观念其实不过是近代史观的虚构,恐怕我们也就不会再慌乱地追赶此起彼伏的思潮与主义了。王国维先生论词谈诗时,认为“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23](15)。然岂独诗人为然?一个人文学者倘若对周遭世界置若罔闻,他的工作就成了故纸堆前的游戏;但他若只限于追踪热点、贪新骛奇,他就始终停留在道听途说的表面之见上。对西方艺术传统的通观为贡布里希思考现代艺术思潮提供了一条“出乎其外”的通道,而对现代艺术思潮的持续性关注则是他研究各种艺术传统,特别是西方写真传统“入乎其内”的动力。
因此,把传统作为当下的镜像,让传统思想和当下观念互鉴,出离自身进而反观自身,这是贡布里希把传统作为参照系的第一层意思。然而,艺术传统对现代艺术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现代艺术运动是以激烈对抗传统的样貌出现的,人们感觉现代艺术与传统艺术已彻底决裂,而当代艺术家不断挣脱原有艺术媒介的尝试又加深了人们的这一感觉。于是,有些信奉进步观念的人唯恐“落伍”,就像追星、追时尚一样追赶各种新近的现当代艺术风潮,不管是否真的能理解;而另一部分人则扮演了保守主义者的角色,厚古薄今地追忆“美好的往昔”。贡布里希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他曾明言:“‘支持现代艺术’跟‘反对现代艺术’一样,都是轻率的。”[3](596)在他看来,和传统艺术一样,现代艺术也是对一些明确具体的问题的反应。这些问题从传统而来,伴随其解决又会引发新的问题,并改变我们对各种艺术传统的理解。比如我们曾提到,立体主义本想探索如何增强二维图像的空间感和体积感这一传统问题,但最后它引导我们重新考虑定点透视这一西方再现传统,重新考虑我们把二维图像解读成三维事物这一基本经验。在现代世界,照片、霓虹灯等错觉性图像太常见了,以致我们丧失了对写真图像的惊异感。然而,如果我们不是早已默会了西方写真传统,习惯于在二维图像上寻找三维世界的统一性解释,立体主义绘画就不可能带给我们视觉屡屡受挫的经验。换言之,如果参观马蒂斯绘画的女士不是按传统读图法把绘画上的女人读作现实里的女人,马蒂斯绘画的新奇效果就不会释放,他把观者带回二维图像艺术的“努力”也无所谓奏效。
由此,传统作为参照系更深层的意思是:现代艺术如果不参照传统就无从索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把现代艺术汇入对艺术的整体叙事中,作为一门实践活动的艺术就面临崩解的危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看似只是在研究与现代艺术的信念与价值无涉的再现心理学问题,其真实的目标和抱负却是要打通再现与表现之间的屏障,用“视觉等效性(visual equivalence)”把传统再现艺术与现代表现艺术汇入一个生动且富有反省力度的连贯叙 事之中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和批评表现主义流行观念才对贡布里希尤为重要。正如坎利夫(Leslie Cunliffe)所意识到的:“对贡布里希而言,有关艺术和自我表现的表现主义理论必须得到阐释,因为这种极端的理论否定艺术是一个文化、社会与认知的过程,而这正是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中提出的有关再现图像制作的关键因素。”[6](69)
正如写真不是对现实的复制模仿,表现也不是对情感的直接袒露,它们都有赖于程式,需要根据色彩和构型的传统语汇探索一种新的整体性效果。因此,在艺术史叙事中,往昔和当下具有同样的分量,并在对未来的张望中完成自身。重视艺术史书写的贡布里希一定会同意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有关叙事复活传统的论述:“对传统的充分领会是在对未来可能性的把握中显示自身的,并且正是过去使这些未来可能性有益于现在。各种活着的传统,恰恰因为它们继续着一个尚未完成的叙事,所以就面对一个未来。而这个未来的未决和可决的特征(就它有这种特征而言)恰恰又源于过去。”[24](283)因此,作为参照系的传统不是一堆既成的事实组合,也不是一个稳定不变的现成存在者,它因对当下的领会和对未来的盼望而成为一股鲜活的创造力。无论是对艺术传统的研究,还是对现代艺术的关切,贡布里希从未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即对其中一个宣誓效忠,而对另一个鄙夷不屑,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复活传统,使自己的艺术研究和观念批评汇入那股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之中。
对一个关心艺术命运的艺术爱好者而言,对一个渴望复活艺术传统的思考者而言,也许当下最紧迫的工作就是理解现代艺术赖以生长的观念环境。而这一环境不仅是凡•高、高更、塞尚、毕加索等伟大的现代艺术大师所创建的,也是作为现代艺术的公众的我们所缔造的。我们是否能在艺术传统和文化地图中理解现代艺术的奋战和目标,能否在参照传统的过程中使艺术世界更为丰厚,能否在联系其他社会生活时让艺术活动更为具体充实,这些都将深刻影响着现代艺术的走向和我们自身生活的价值。正因如此,在《艺术的故事》的最后,贡布里希对“我们”发出了热情的召唤和深切的期待:“通过我们的冷漠或我们的关心,通过我们的成见或我们的理解,我们还是可以决定事情的结局。恰恰是我们自己,必须保证传统的命脉不致中断,保证艺术家仍然有机会去丰富那串宝贵的珍珠,那是往昔留给我们的传家之宝。”[3](597)
① 在贡布里希看来,正如语词为世界分节一样,图像也为世界分节。儿童把盆子当头盔,把笤帚当马骑,是把原本不相干的事物拉入一个类目,即对世界重新分节。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把汽车的车篷和风挡改造成一张狒狒的脸,亦是尝试一种新颖的分节方式。通过对世界重新分节,毕加索的这个雕塑作品带给我们观看世界的一个“新隐喻”。而漫画家们则着重对面部特征进行重新分节和组合,探索表情相貌的奥秘。参看: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杨成凯、李本正、范景中译,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2: 76—78,87—89,279—303页。
② 请参看拙文《贡布里希对柏拉图模仿说的诠释与批评》。在那里,我讨论了为什么贡布里希认为西方传统的写真艺术也非模仿现实的产物。在贡布里希看来,写真并非是对现实事物外观的复制,而是追求一种能唤起我们视觉逼真效果的构型。因此,和表现主义艺术试图构造能够唤起强烈情感效果的构型一样,写真艺术试图构造唤起逼真效果的构型。正因如此,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的最后一章的标题叫作“从再现到表现”,意在用“视觉等效性”勾连起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的探求。参看:牟春.《贡布里希对柏拉图模仿说的诠释与批评》.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5(2):13—20。
[1] WOOD C S. Art history reviewed VI: E.H. Gombrich's “Art and illusion: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1960[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2009, 151(1281): 836−839.
[2] 卡尔•休斯克. 世纪末的维也纳[M]. 李峰, 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22.
[3] 贡布里希. 艺术的故事[M]. 范景中, 译.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8.
[4] MACGREGOR J. The discovery of the art of the insane [M].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5] VAN GOGH V. The complete letter of Vincent Van Gogh[M]. New York: Bulfinch Press Book, 2000.
[6] CUNLIFFE L. Gombrich on art: A social-constructivist interpretation of his work and its relevance to education[J].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1998, 32(4): 61−77.
[7] GOMBRICH E. A lifelong interest: Conversations on art and science with Didier Eribon[M].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3.
[8] JASPERS K. Strindberg and Van Gogh[M]. trans. Oskar Grunow and David Woloshin.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7.
[9] 贡布里希. 马尔罗与表现主义的危机[M]//木马沉思录. 曾四凯, 徐一维, 译.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5.
[10] 贡布里希. 艺术与错觉[M]. 杨成凯, 李本正, 范景中,译.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2.
[11] 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 顾爱彬, 李瑞华,译. 南京: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5.
[12] 保罗•泰勒. 贡布里希与原始艺术的观念[C]//贡布里希遗产论铨. 李本正, 译.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8.
[13] 路易斯•罗斯. 心理学、艺术与政治—— 恩斯特•克里斯、E.H. 贡布里希与漫画研究[M]. 牟春, 译.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22.
[14] 贡布里希. 偏爱原始性[M]. 杨小京, 译.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6.
[15] KRIS E. Psychoanalytic explorations in art[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74.
[16] 列维•布留尔. 原始思维[M]. 丁由,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17] CARRIER D. Gombrich on art historical explanations [J]. Leonardo, 1983, 16(2): 91−96.
[18] 弗洛伊德. 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M]. 阎广林, 张增武,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0.
[19] GOMBRICH E. The sky is the limit[C]//MacLeod, ed. Perception: Essays European Culture A.D. 500—15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20] 塞尚. 塞尚书信集[M]. 约翰•雷华德, 编. 刘芳菲,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21] 贡布里希. 错觉与视觉僵局[M]//木马沉思录. 曾四凯,徐一维, 译.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5.
[22] 贡布里希. 艺术的多样性——《拉奥孔》在G.E.莱辛(1729—1781)生平和创作中的位置[M]//敬献集. 杨思梁, 徐一维, 译.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5.
[23] 王国维. 人间词话[M]. 北京: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24] 麦金太尔. 追寻美德[M]. 宋继杰,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Tradition as a frame of reference: Gombrich's understanding of and critique at the ideas of modern art
MOU Chu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China)
Gombrich's concern about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modern art is inseparable from his research on the western art tradition. By tracing back to its origin, he integrates various modern art movements such as Expressionism, Primitivism, and Cubism into the overall narrative of western art history. By offering a unique analysis of individual artists and art works, he presents a complex picture of the ideas on modern art. By elaborating the specific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artistic contexts, he analyzes the crisi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modern art, overcomes the vulgar opinions related to modern art, and dismantles the abstract theory of it at the same time. Gombrich's interpretations of modern art stem from the fact that he takes tradition as a frame of reference, makes traditional thoughts and popular ideas learn from each other by virtue of art history, and renders traditional thoughts the source of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sent and bear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future.
E.H. Gombrich; ideas of modern art; tradition; a frame of reference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3.05.003
J0
A
1672-3104(2023)05−0022−11
2023−04−21;
2023−06−15
牟春,女,河南郑州人,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艺术哲学、美学,联系邮箱:muchunivy@163.com
[编辑: 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