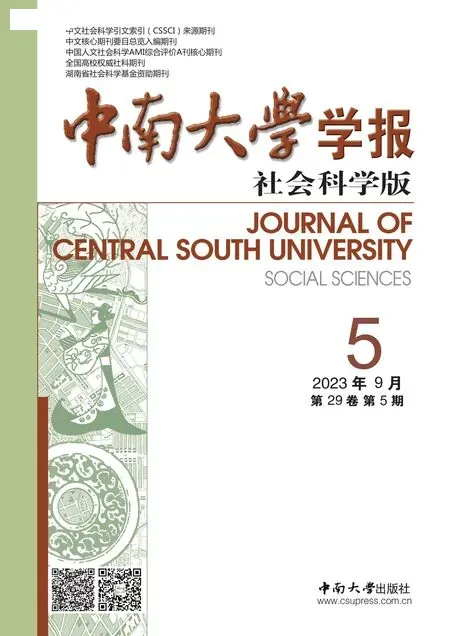文质论的两种形式与刘勰的立文之道
付佳奥
文质论的两种形式与刘勰的立文之道
付佳奥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00)
在早期二元对立思维影响下,汉儒偏重观察文质的历时意义,将文质应用于政治,打造文质循环、损益救弊之说,以质为先,长期影响着文质论的表述形式。魏晋之际,二元思维在玄学清谈和佛教义解中出现新变。佛经翻译使形而上的文质论和形而下的翻译行动发生联结,揭示出以旧文质观观照文学的问题所在,使文质在共时层面的和谐成为当务之急。在《文心雕龙》中,文质论历时、共时两种形式交融。刘勰更加明晰了文、质两端与“情”在共时层面的联系,以“情文”为“立文之道”,并从质体文用的角度,提出了对“情”的价值判断,在肯定文华的同时折衷了质派,丰富了文学文质论的内涵。
文质论;刘勰;立文之道;“情文”
文质论是古人以二元思维认识世界的产物,不仅用它观照人物与政治,而且在东汉以后,多有论者以之分析文学,其影响力至清代仍经久不衰。学界对早期文质概念的讨论成果极丰,但有关中古文人对文、质认识的变化及其成因,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文质概念既包含从质朴到文华的人类早期社会线性发展过程,又指向同一时期内事物的质性和文饰两个方面。它既具有历时的意义,能够反映事物的变化,又具有共时的展开空间,可以从另一角度深入探讨事物的内部要素。构成这一对概念的字义本身即具有包孕性①。文质论在古代的发展有两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为先秦至两汉,重视文质二元对立转化在历时层面的意义,应用代表为公羊家的循环改制之说;第二阶段为魏晋至唐,逐渐发掘出同一个系统内文质二元的互动关系,亦即在共时层面的意义,其代表为刘勰提出的“形文”“声文”“情文”三位一体的“立文之道”。从文学的角度上来看,第二种形式使文质论初步摆脱了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不拘于一端,有助于呈现独立而完善的文学批评结构。同时,第一种形式仍然在持久地为文学文质论提供影响,二者在《文心雕龙》中呈现为折衷和合流。刘勰建立的新型文学文质论进一步影响到了唐人的相关转述,为唐诗的尽文尽质、文质双美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循环改制:历时的政治文质论
文质观的渊源,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学批评中的文质论》一文已作系统的分析,此处不赘[1]。但文质本身是由二元概念组成的认知视角,对其含义引申过程中引发的一些分歧和争论,还需要略作申说。
在先秦诸子环绕着“礼”的争议中,“质”与“文”都已有初步的引申义,二者与事物发展的阶段变化紧密相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质、赘双声,以物相赘,如春秋交质子是也。引伸其义为朴也、地也,如有质有文是。”[2](281)《论语》对文质的运用奠定了后世文质论的基本规模,典型的用例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3](400)、“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3](182)。按孔安国、邢昺、何晏等的训解,“质”指朴野之貌,“文”与之相对②。君子野人之别在于野人质木无文,君子则有文华修饰,有“行礼及言语之仪”[3](842),在“文质彬彬”的表述中,文质本是事物共时的两面,但因为和周礼发生了联系,文质又代表着历时的阶段特征。周朝礼仪制度完备繁复,所以孔子称“郁郁乎文”,与前代相较,周礼发展出“文”的特点,孔子进而做出了“吾从周”的价值判断。
争议由是而生。“文”“质”二元和“内容—形式”二分法的重要区别在于,“文”“质”概念和时间顺序有关,“质”意味着纯朴原始,而“文”则是发展累积的结果。“内容—形式”作为事物的两面,并不具备这种历时意义。“从周”也就是“从文”,是否一定合理?《论语》中记载了一则问答,棘子成向子贡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替孔子做出了解答:“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3](840)在棘子成眼中,人们似乎没有必要改变“质”胜“文”的初始面貌。子贡则认为,在文、质的对立中,“文”天然是“质”的一部分,“质”展现为外在的“文”。他用自然界的虎豹与犬羊举例,认为外在皮毛文采的区别也是它们本质上的区别,言下之意即在于人们不能满足于质胜文的初始阶段,有必要增添一些文华,使文质达成平衡状态,带来整体上的不同。换言之,重礼绝不是表面功夫,它也意味着整个国家质性的不同。
这只是先秦时期思想争鸣的一个缩影。不仅棘子成为此感到困惑,道家与墨家更是明确反对追求文华,维护质朴,与孔子的观念有很大的分歧。《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4](45−46),“信言不美,美言不信”[4](310),《庄子》中则说“文灭质,博溺心”[5](552),“天地有大美而不言”[5](732)。道家认为“质”是本初自然状态,本身就是“大美”,无待“文”来补救,“文”只会扰乱人们的体验,二者不可兼得。“擢乱六律”,才能“人含其聪”;“灭文章”,才能“人含其明”[5](362)。他们从事物的极端情况立论,认为人类社会应该返回本初状态,废弃文的一面,试图以此拯救颓圮的现实。墨家则从尚用的角度出发,认为“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先 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6](516),强调质文的先后顺序,反对铺张,进而宣扬薄葬。荀子与之针 锋相对,称“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之丧,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7](372)“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7](392)。韩非能够认识到“文”的作用,指出“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但马上又说“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8](133),抓住文华的负面影响,釜底抽薪般反转了其师荀子的立论,其文质观更偏向于道家。“饰”在韩非眼中也成为贬义词:“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8](133)韩非完全认可老子的文质观念,以此为武器批驳儒家重礼的思想,抬高“质”的价值,贬低“文”的意义。
怎么看待“文”的价值,意味着怎么看待周朝的礼仪制度,道家、墨家、法家都有着和儒家不同的立场。先秦儒家受限于现实政治,并未能说服他人。面对礼崩乐坏的无奈事实,荀子也只能用“愚者闻其略而不知其详,闻其详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7](82−83)来解释。直到汉朝走向强盛,儒家受到了空前的重用,公羊家获得一定的话语权后,文质论才在政治层面得到了充分而一致的应用,但他们“质文代变”的观念和先秦儒家已经大不相同了,重心几乎完全落在了历时层面。
公羊家发挥董仲舒“春秋改制说”,提出三代改制、质文代变的政治观点,目的是由文质二元推导出更丰富的宇宙规律和伦理系统,利用二元之间的对立转化关系来推动政治改革。这种文质论在汉代文献中表述为“文”与“质”在时间线上的运转,如“是以物胜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始终之变也”[9](1442),“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10](204),“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11](2519)等,将文质树立为对立且互替的两端,为改革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周朝的礼仪制度成为循环中的一环,而不是事物发展的终点,同样的,汉代的儒者既不必像孔子那样维护复杂的周礼,也不必像道家那样将之全然否定,他们可以建设汉代所专属的制度,推动文质循环。《春秋纬》中有一段完整的文质循环论,可为代表:
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救野莫若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 荡,故救荡莫若忠。如此循环,周则复始,穷则相承。[12](393)
这是关于夏商周三代制度的总说。夏之治质朴,因此出现了质胜文则野的弊端;商之治重祭祀,有得有失;周之治重礼乐,由质趋文,虽然救了“鬼”,但也带来了“荡”,并不像《论语》所说的那样美妙。这是因为周朝已经灭亡,公羊家不可能不吸取其经验教训,必然要修正发展的方向。因此,在他们的眼中无论是“质”还是“文”,皆有其弊,沿着质文发展的循环而加以损益成为一种时代需要。
在公羊家的眼中,质文代变并互救,组成了可以解释前代历史经验的模型。文质盛衰构成了逻辑上的封闭循环,由此可以将目光下移至具体的帝王理乱之道。周之后,秦国祚不长,那么汉之治便应当损周之“文”,回返到“质”的一面,以补救周之“荡”,正如马泰·卡林内斯库所说:“历史上的大多数革命都把自己设想成回归到一种较纯净的初始状态,任何一贯的革命理论也都隐含着一种循环的历史观—— 无论那些前后相继的周期被看成交替式的(光明、黑暗),还是根据一种更系统的进步学说被看成有象征意义的螺旋式上升。”[13](21)汉儒需要替新兴王朝打造一种可以合乎宇宙间神秘规律的政治体系,他们必须将自己看作救弊、进步的一方。先质后文的政治理念也由此确立,所以《春秋繁露》又云:“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其质而无文。”[10](27)宁愿舍文以就质的观念实际上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确定了“质”拥有更高的地位,和《论语》所表达的文质思想并不相同。
这种“循环改制”式的文质论偏重于历时 性认知,认识到事物由质向文、由文复质的发 展规律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弊端,标出“救”的时间节点,并制造出可以无限推导的质文代变模型。它在黄老思想流行的汉初调和了儒、道之间的矛盾,在政治应用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朝代更迭频繁的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如王夫之认为“商周之革命也,非但易位而已,文质之损益俱不相沿……一代之必废,而后一代以兴;前王之法敝,而后更为制作”[14](397);章学诚云“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15](61);康有为称“汉文而晋质,唐文而宋质,明文而国朝质。然皆升平世质家也,至太平世,乃大文耳”[16](122−123)。这些观念,无不受到循环改制说的深刻影响,将历史看成是质与文一代一代此起彼伏的发展过程,强调其阶段性。反过来,这种政治文质论也为此后一些特定时期的变革诉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使与之并行的文学文质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脱离它的笼罩③。
总之,在先秦的文质争论后主导着汉代文质观的,是质朴与文华在时间上早期线性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此消彼长,而不是事物在同一时间上的内外两面。胡塞尔认为,“根据经验动机,我们从直接的被经验之物中推演出未被经验之物……认识并不只是完全依照顺序相继产生的,它们在逻辑关系中相伴出现,它们相互产生于对方之中,它们相互‘肯定’,它们相互证明,仿佛在相互加强它们的逻辑力量。”[17](19)这种来自经验的“自然的精神态度”,强化了文、质之间的对立,也认识到转化的必要性,但总的来说还不能够对事物的发展做出完整、准确的认识。不仅文质对立相替的论调不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实际情况,它对文与质两端的具体理解、二者在同时间内的互动关系都没有增进。以“质文代变”作为理论依据推动的政治改革,为了革除旧弊,常常也走入矫枉过正的境地。
文质概念本不限于观察政治史时使用,当人们用它考量文学时,这种循环改制说的问题尤为突出,并不匹配文学的发展规律。扬雄和王充都是循环改制说的拥趸,但他们考察文学时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新的文质眼光。扬雄“文以见乎质,辞以睹乎情”[18](190)④、王充“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19](609)的观点,都接续了先秦儒家的观察角度,重新考虑到了同一时间内文对质的表现作用,于对立之外思考二元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恰恰是文学文质论和政治文质论后来最大的不同。也意味着从他们开始,早期文与质二元对立、历时转化的思维形式不能够再满足论者的需要了,另一种共时的形式开始被人们逐步接受。
二、文质彬彬:共时的文学文质论
先秦至两汉的文质论,尽管已经认识到相互转化的过程,但其重心始终落在对立上,持论往往偏于一端,舍此就彼,孔子理想的“文质彬彬”并未得到进一步的诠释。魏晋时期,文质论的应用由政治向文学层面迁移,接续了此前扬雄、王充的论述,并有所新变,在历时性的质文代变之外,更加重视质文共时性的内外两面,结构更加完整的文学文质论也由此成为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版块。新型文质论的形成,不仅与玄谈对二元思辨的促进有关,更受到了佛教传入中国、译经需要调和文质的直接影响。
佛经译入东土是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它非常直接、不容回避地面临质、文之间如何处理的难题,和政治上的循环改制说一样,文质讨论没有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而是向下指导着具体的实践,并在实践中发现了问题。
一开始,译者仍分为质、文两派,质派追求意义的传达,不重视文辞面貌,而文派反之,两派呈现出鲜明的对立。《法句经序》记载,僧人支谦曾认为有的译本“其辞不雅”,遇到质派的驳难:
维祇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20](273)
此序作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质派援引传统的二元对立观念为自身张目,选择道家“舍文就质”的权宜之计,但佛经翻译仅仅保持意义的准确并不能使人满意,梵文原本美丽的文辞能够为佛教的宣传减少很多阻碍,本身就是佛经中的应有之义。质派并没有能够说服以支谦为代表的文派,然而,从支谦遇到的驳难来看,文派在当时恐怕亦不能说服质派。这时,旧有历时循环的文质推移就不能为佛经翻译提供指导了。慧远称:“自昔汉兴,逮及有晋,道俗名贤,并参怀圣典,其中弘通佛教者,传译甚众,或文过其意,或理胜其辞。”[20](380)佛经翻译要求文本的最终呈现在共时层面达到一个内外和谐、文质并进的完美状态,无疑给当时的译者带来了难题。
面临文质上的选择,竺道生、释僧肇等名僧干脆持得意忘言之说,绕开争论。他们认为“自经典东流,译入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21](256),“道与神会,妙契环中,理无不晓”[21](251),索性避开文字,寻求神会。这种观念一度颇有影响,然而对具体的翻译却并无帮助,反而说明他们对当时的佛经翻译情况并不满意。梁武帝在为释宝亮《涅槃经疏》所作的序中,也认为如来“离文字以设教,忘心相以通道”,但同时他又指出“非言无以寄言……言息则诸见竞起”[22](371),并支持释宝亮的义解行动。可见,在落实到具体工作时,还是需要保持言和意的和谐,只有借助高超的翻译和义解,才能更好地宣扬佛教的教义。因此,《高僧传·义解传论》云:“是以圣人资灵妙以应物,体幽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托形像以传真。故曰:‘兵者不详之器,不获已而用之;言者不真之物,不获已而陈之。’……故须穷达幽旨,妙得言外。”[21](342)以“义解”名世的高僧也越来越多,对译经的推进带来了正面的影响。因此,用“言”来“穷达幽旨,妙得言外”,成为一条不得不走的道路,而如何调和“文质”二端,尽文尽质,也就成为理论上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这时,扬雄“文以见乎质,辞以睹乎情”的发明就显得重要起来。他敏锐地指出了文与质、辞与情在共时层面相互联结、相互促进的关系,而否定了以道家为代表的“文灭质”式的思维。
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最终没有以某一派的胜利宣告结束,而转变为文质调和、意以言传的新路径。释道安在长安组织译经多年,在保持佛经原意的基础上,提出“译胡为秦,有五失本”[20](290),其中“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20](290)就允许对佛经的译文进行一定的修饰,以求合乎汉语的表达方式。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认为“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蒲萄酒之被水者也”[20](413),意为图方便而有意简省的译文,就如同掺水变味的葡萄酒一样。释道安地位尊崇,影响很大。如在翻译《僧伽罗刹集经》时,主译者佛念“学通内外,才辩多奇”,但译经时“常疑西域言繁质,谓此土好华,每存莹饰,文句减其繁长”,带有为质削文的倾向,主持译经的武威太守赵政和释道安对此并不满意,又做了一番“穷校考定”的工作,以“务存典骨”[20](374−375);《婆须蜜集序》又载,是经于建元二十年由“佛念译传,跋澄、难陀、禘婆三人执胡本,慧嵩笔受……余与法和对较修饰,武威少多润色”[20](376),佛念确保经义的准确,但仍需进行校对和润饰。由译传者、执胡本者、笔受者先将佛经翻译为汉文,再由校对者、修饰者加以检查、润色,多人合作,成为一套译经的标准流程,使佛经既能保持本义,又能不废文华。释道安之后,北方最有名的译经人鸠摩罗什再度宣称“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21](53),旗帜鲜明地批判只传文意,不顾修饰的翻译方法。他的弟子僧叡在《小品经序》中也认为“胡文雅质,案本译之,于丽巧之不足,朴正有余矣”[20](298)。释道标《舍利弗阿毗昙序》记载了后秦时期一次漫长的翻译过程:弘始九年,由昙摩崛多、昙摩耶舍等人书写梵文本,但因为“直委之译人者,恐津梁之要,未尽于善”,一直等到弘始十六年“经师渐闲秦语”之后,才开始翻译,达到“言意兼了”的程度,才笔受为汉文。上呈姚兴之后,又令“文之者修饰,义之者缀润,并校至十七年讫”[20](373)。可见,在释道安之后,这种环环相扣、文质并重的翻译方式也被传承了下来。
在南方,佛经译解同样不废文华。谢灵运与慧严、慧观重译《大涅槃经》,“文有过质,颇亦治改,始有数本流行”[21](263)。据姜剑云考证,这三个人还曾合作将《华严经》译本由五十卷润色增编为六十卷[23]。梁武帝在亲自撰写的《注解大品序》中,记录了他曾“集名僧二十人,与天保寺去宠等详其去取,灵根寺慧令等兼以笔功,探采释论,以注经本”,尽管当时此经传入中国两百多年,已经“三译五校,可谓详矣”,他仍希望能够达到“质而不简,文而不繁”[20](296)的更高境界。
经过释道安、鸠摩罗什等不废文华的译者的努力,佛经的翻译最终在玄奘的时代结出了文质彬彬的累累硕果。佛教徒并非一头转向对藻绘文华的追求,而是尽可能地用更文雅精确的语言去表现内质,追求文质两端的齐头并进,更好地表达经典中的内容,将形式转化为有意味的形式。玄奘建立的被宋代法云大师总结为五种“不翻”的翻译法则,致力于保存原文庄严华美的风格面貌,也“有利于术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24],为后世的佛经翻译树立了标准。这也说明,舍此就彼的对立循环是不能解决文学问题的,和政治不同,文学作品更看重文与质呈现出的共时状态。
周小羽在板凳上嗷嗷直叫,这个样子跟年三十我们岭北镇杀猪的情形一模一样。但周小羽却没有讨饶,只是一个劲地叫着,打死我好了打死我好了。
在译经文质之争的同时,西晋陆机所作《文赋》接续扬雄以文质论文学的说法,提出为文的难点在于“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25](762)。自扬雄以后,文人们开始认识到言与意、文与质之间的相互性,以言达意、以文见质。陆机则认为最难的不是明理,而是将其付诸实践,这和译经上的要求是一致的。他认为作文有情意和文辞两部分——“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25](20),“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25](60)。“每变而在颜”的真情即质,如同树的主干,“丽藻之彬彬”的辞句即文,如同树的枝叶,二者结合,才有完整的文章;“信情貌之不差”这句话的重要性不下于前两句,在道家的眼中,情即质,貌即文,貌能假饰情,文能假饰质,所以文质永远不能统一。陆机在扬雄“辞以睹乎情”的观点上进一步下断语以“信”,反假为真,认为人的外在表现和真实情感是一致的,也就意味着文辞的琢磨和情感的表达相一致,给自己因情立文的文学观奠定了立论基础。
陆机先确定情貌不离、文质统一的关系,然后进一步以文质观察不同文体,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明确的标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25](99),这一段话历来极受重视。陆机摆脱了历时的统摄,进入共时层面,细分具体文体内部的文质要求,文体不同,要求也就不同。对于诗体,他认为诗情是诗的质性,文华可以增进诗情的表现,最终形成“绮靡”美丽之貌;赋的质性是体物,所以要达成“浏亮”的表达效果。文体特性不同,决定了文华的具体取向。因此,陆机对碑的要求是“披文以相质”。这里明确拈出了文质概念,论者解释不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认为陆机主张文质相半,如李善“碑以叙德,故文质相半”,黄侃“碑是颂体,而当叙事,故文其表而质存乎里”;第二种认为陆机主张以质为主,如张凤翼“碑以叙德,故质为主而文相之”,闵齐华“披言相质,使质有余也”;第三种则认为陆机以文为先,如王闿运“以文述事,而不可以事为主。相质者,饰质也”[25](113−114)。
陆机的这四句话,第二、三字都是表达该文体的特性,诗缘情、赋体物、诔缠绵,莫不如是,碑“披文”也不例外。换言之,碑本身的特性就是带有装饰作用的颂德文字,而不是纯粹的现实叙事,这决定了它必然趋向质文两端中“文”的一面。所以陆机用“相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约束“文”的发散方向,具体创作时体现为据事颂德,不可离事夸谈,因此黄侃强调“碑是颂体,而当叙事”。上述认为陆机主张以质为主的第二种观点,忽视了陆机对不同文体的区别定位。文华虽然是外在的,但碑体恰恰就需要这种外在的装饰,由此也转化成它内在的文体质性。王闿运则意识到碑颂对“文”有在先的要求,他的观点也更符合陆机的文体理念。
陆机围绕文、质这对概念进行的架构并不是历时的循环系统,而是共时的内外系统。文士作为创作者,拥有“文”的能力和技巧,有作文的情感和目的,因情立文、以文相质,以求共进,是陆机眼中创作的法门。陆机随后在提到“尚巧”“贵言”这些尚文一面的同时,也举出“铨衡之所裁”“绳其必当”这些约束方式,意在技巧的取用要根据具体的创作目的来决定,两方面同时下功夫,才能达到普遍意义的文质结合。他最后放眼文学的本质,认为“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25](261)。“众理之所因”即“质”在形而上层面的总和,“质”为体,“文”为用,合乎此的文章,才能流广而日新。总的来说,《文赋》极大地肯定了“文”的价值。
与译经中的文质之争一样,陆机的文质论虽有新的发明,但也还不能完全服众。挚虞《文章流别论》的论述重心又在陆机的基础上有所调整:“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26](1905)他虽然不再取道家“文灭质”的极端观念,但也意识到了言语文辞的不稳定性,认为言与类、事、义、情四要素是应当互相制约的。尽管挚虞和陆机的观念并不一致,但他们所思考的文质关系都已不再是简单的对立转化,而注重在应用中对文华和质实的动态调整。这是文质论的新形式,上接《论语》《太玄》,下启《文心雕龙》。这种新形式的出现,代表着文质论在文学应用上自发性的改变。此后,历时与共时的两种形式在不同的文质论述中一直共存着。
文质论的具体内涵之所以难以厘清,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使用过程中两种形式的混杂。基于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以质为本、循环损益的旧说仍有极强大的影响力。齐梁之际,裴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27](443)。环绕着裴子野,有一个文学主张大体相近的圈子,他们重视质朴和法古,和齐梁时代的华靡文风相判别。裴子野著《雕虫论》,认为从楚骚和司马相如开始,“随声逐响之俦,弃指归而无执”“圣人不作,雅郑谁分”,即颜延之、谢灵运,也不过是“无取庙堂”,至他所处的时代,更是“淫文破典,斐尔为功”[26](3262)。他指出了一条随着时间而流荡的文学发展线索,将质朴和法古等同起来,强调质与古的先天联系,进而反映为崇尚自然和质朴的审美追求。每当有论者对文学现行的整体面貌产生不满、希望回到初始纯净状态时,这种旨在变革的历时形式仍有很强的号召力。
此外,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打破对立,寻求文质二元协同并进的理论方法。如谢灵运认为“夫能重道则轻物,存理则忘事。古今质文,可谓不同,而此处不异”[28](1755),在强调道、理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暗示了物、事对道、理的表现作用,所以他在《答范光禄书》中又说“虽辞不足睹,然意寄尽此”[22](294),意指文辞是情感的寄托。又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称:“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 嗣响。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28](1778)沈约特别推举以抒情小赋见长的张衡,认为他“文以情变”“绝唱高踪”,欣赏他文中协调的文情关系,并将建安时期的写作方式总结为“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而加以褒扬,意即缘情而发为文采,以文采帮助质性的表现。经由晋宋以来文论家的完善,文质在共时层面的关系最终体现为刘勰的“立文之道”。
三、刘勰对文质论两种形式的折衷
《通变》篇展现为历时形式:“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也。”[29](519−520)其借鉴了公羊家的文质循环论,来概括文学史不同时代的总体风貌,并树立了“由质及讹,弥近弥澹”的大框架。在这里,他对循环论稍加改动,将“文”改造成了“讹”,保留了“文”的价值意义,措辞十分严谨,但实际上仍然是质文代变的旧说,将上古视为某种纯净状态,而当下则问题重重。要解决问题,刘勰认为最好的方法便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9](521),将今古所代表的两种状态进行一定程度的调和。
刘勰在《通变》中的总论过于粗略,并不符合实际状况,他自己也另立《时序》篇,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29](671)“蔚映十代,辞采九变”[29](675)的观点,补充《通变》所论不足之处,二者颇有出入。首先,“魏晋浅而绮”就不那么站得住脚,刘勰在《时序》篇评价建安文学“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29](674),又在《明诗》篇中称建安诗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正始“嵇志清峻,阮旨遥深”,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到了“晋世群才”,才“稍入轻绮”[29](66−67)。从存世作品上看,魏晋的文学肯定不至于沦为浅绮,刘勰对作品把握娴熟,自然也明白这一点。又如,《时序》篇论刘宋文学,认为“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才云构”“缙绅之林,霞蔚而飇起”[29](674),与他《通变》篇“宋初讹而新”的泛言亦有所不同。刘勰仍然在《通变》篇中采取传统叙事方式,不外乎是用循环论的理论模型来明确当下救弊的需要。《时序》篇则意在分析时代与文学变化的成因,因此细节上多有不同,但二者总体上是相辅相成的,大旨都落在“质文代变”上。
《通变》篇有鲜明的复古色彩,持论甚高,但还没有触及文学诸元素的内部关系。当刘勰需要建立文学的本体论和创作论时,历时形式便不能完全满足其需要了,而陆机、沈约等人呈现的新型文质论更能深入文学的内部。
刘勰循此门径而入,设立《情采》篇,从共时层面,系统地探讨了文与质、言与意之间的关系,相对《通变》篇更有发明:“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教也。”[29](537)所谓“立文之道”,即“文”与其他形式相区别的内在特性,刘勰析为三种。“形文”是古人最早发现的一种文理,以外在的色彩为代表;“声文”是《毛诗序》“声成文,谓之音”[30](270)的转述,在上古时期则反映为韶、夏乐章;“情文”和“辞章”的联系最为紧密,发挥陆机“诗缘情”、沈约“以情纬文”之说,将“情”确立为“文”的一种存在依据,这也是为什么刘勰要专门列《情采》篇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五情”借助辞章形式的抒发,和黼黻、韶夏一样,自然外显为一种文采。
对于文学而言,“文”是如何由“质”生出的呢?刘勰认为这正与“情”密切相关。他明确了质文的并生关系:“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29](537)这两句和“五情发而为辞章”是同一结构,换言之,也可以说“五情发而为辞章,文附质也”。沦漪、花萼和辞章是“文”,水性之虚、木体之实和五情之待发是“质”。他又说“研味李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29](538),将“情”树立为文、质联结的纽带,正如“水性”和“木体”一样,既是“质”和“性”的体现,又可以通过文字,外显为和“沦漪”“花萼”同等的“文”。在此基础上,刘勰指出“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29](538)。“志”与“情”如果和文字保持一致,那便自然达到“五情发而为辞章”的效果,“质”通过“文”获得了外在表现,因而观察者可以借助“文”获得对“质”的深层理解。如果不一致,也就不足道了。
尽管刘勰的观点在魏晋以降的文论中可以找到一些更早的、相近的表达,但其他人所论,都没有如刘勰这般明确而具体地将“情”与“文质”联系起来。“情文”可以说是刘勰“立文之道”的核心,经由“情”这座桥梁,辞章便能自然生出华彩,达成文与质的齐头并进,而不必担心二者此长彼消。同样讲文质,《通变》和《情采》在理论出发点上是有矛盾的。前者要求复质,后者要求立文。刘勰“情文”说的另一个要点,是从质体文用的角度,提出了对“情”的价值判断,以这种方式在肯定文华的同时折衷了文人群体中分裂出来的质派,同时也调和了文质论的两种形式,对后世影响深远。
质有质性,情有情性。对于挚虞提出的“四过”和文质之间的制约关系,刘勰认为“若择 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29](538),具体的做法,则是强调“为情造文”的自然生发。刘勰说“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29](538),并不否认文采的假饰作用,所以回到创作动机上,借鉴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观点,将“诗人”和“辞人”区别开来看待,并不认为铺张藻绘就可以写出好的辞章。特别能够反映刘勰对“丽以则”有所吸收的,是他对《离骚》文学系统的认识。风、骚为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但在后人的解读中,却呈现出两种面向:将《诗》视为经典,对《离骚》则间有微议。其中,对《离骚》的批评之声,往往针对的是屈子强烈的自我抒情意识。刘勰专门用《辨骚》篇来谈这个问题,既摘出《离骚》异于经典的“狷狭之志”“荒淫之意”“诡异之辞”“谲怪之谈”[29](46−47),又肯定它有四点合于经典,同于风雅,并且赞扬它对后世文学的正面影响。罗宗强先生指出,刘勰在《宗经》《正纬》之后接以《辨骚》,并非否定“诡异之辞”“谲怪之谈”,而是正视骚体“情与奇”的价值,肯定了情感需要用奇文表达的创作观念[31](328−329)。沿着骚的线索,刘勰认为这一脉的文学作品“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29](47)。“情怨”“离居”等都是待发的内容,而好的文采则有助于内容的表达,让读者能够“易感”“得貌”。既然文采对抒情有促进作用,那只要“为情而造文”的“情”没有问题,“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29](538)的过程也没有问题,“文”就不必遭到质疑,不必再重复道家“文灭质”的论调。无论是奇文还是丽文,都可以增进对“情”的表现作用,有助于达成“文不灭质,博不溺心”“彬彬君子矣”[29](539)的最高理想。所以,刘勰认为楚骚的后继者应当“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堕其实”[29](48)。
但是,在折衷思想的影响下,刘勰对情的认识又不能摆脱时代的影响和局限。他肯定《离骚》的文学价值,对其情志却不无微词。这也是南朝文坛普遍的价值取向,在追求清平雅正的共同趣味的同时,否定那些放情纵意、强调个体抒情的书写方式。鲍照一脉在齐梁时代所受到的批评,即明确地反映出这一点。例如,陆厥曾经驳难沈约:
意者亦质文时异,古今好殊,将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恶犹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缓,故合少而谬多。义兼于斯,必非不知明矣。[32](899)
陆厥认为文质风貌是不断历时变化着的,其中决定性的元素是“情物”,而不是“章句”。但是,“情物”本身并不天然为美,而是美恶相半,意即情志与物象都有美好与恶劣之分,如不能辨明美恶,即无取于文字。美恶尚且不辨,章句上的那点技巧也就更不足道了。这是带有功利色彩的论调,本意在于反驳沈约的声律观念。陆厥认为古代贤人并非不明声律,只是不认为它重要,用釜底抽薪的方式削减了声律的价值。陆厥引圣人为援,沈约在答书中也不得不承认“若斯(五声)之妙,而圣人不尚,何邪?此盖曲折声韵之巧,无当于训义,非圣哲立言之所急也”[32](900),对于陆厥的刁难并无有力的回应,最后只能说:“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老夫亦不尽辨此。”[32](900)沈约将“声韵之巧”与“以情纬文”并列成实践的两大方向;刘勰倾向于反质复古,试图使文学回归纯净状态,革除浮华之弊,所以他并没有继续推进沈约的声律秘见,所论“声文”只是一般性的说法。刘勰的“情文”所本,正和陆厥一样,也都包含着对情志本身的价值判断,被笼罩在“思无邪”的传统之下。但他毕竟没有像陆厥一样将“情物”与“章句”视为割裂的两端,而视其为统一体,肯定了“章句”对“情物”的表现作用,这无疑是理论上巨大的进步。
在齐梁时代,“诗缘情”已经被普遍地接受了,但对所缘的是什么“情”、什么“情”不应当入诗之一体,诗坛的主流看法仍然是十分传统的。从玄言诗到永明体,再到宫体诗,并没有突破这一点,仍然被群体清趣所笼罩着。这也是为何“诗缘情”的理念已被普遍接受,刘勰更明确地提出“情文”说,齐梁诗的创作内容仍然显得偏狭的原因。诗人的创作仍然被要求反映情性上的清浊,这就限定了诗的表现范围和表现手法,稍不留神,就会被指为“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的“鲍照之遗烈”[32](908−909)。反之,即使如萧纲、徐陵、庾信所作宫体,亦不令当时人觉得险俗,最多只是伤于轻艳。
正因刘勰持以折衷思想,其文学文质论虽然综合了历时与共时两种形式,创作典范却殊途同归,最终指向汉魏风骨。《通变》篇指出“今才颖之士,多略汉篇,师范宋集”,又引桓谭语称“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29](520),这是从救弊的角度出发,要求进行一定程度的复质,学习汉魏篇章中真挚的古意古情,以上通风雅。《情采》篇亦指出“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29](538),要求创作上秉持为情造文的方式,拒绝华伪不实。历时层面的批评(由质及讹)为共时层面的分析(为情而造文)建立模范和标准,后者再为前者提供创作论上的指导,这也将两种形式合为一种,成为古人文质论的一种常见情形,从而与“内容—形式”二分法相区别。
刘勰文质一体、以文附质并要求减去浮华、恢复风骨的理论首先为唐初南北文风交融的文学道路提供了指引。历来为人所称许的《隋书·文学传序》吸收了刘勰在文质上的折衷论调,认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33](1730)。“气质则理 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的表达源出慧远“文过其意,或理胜其辞”[20](380),即佛经翻译中的两种问题,魏征借以说明南北方文风皆有其不足,意在综合其长,文质并进。但在综合南北文风的同时,也应看到“梁自大同以后”的诗歌,《隋书》则目为“雅道沦缺,渐乖典则”“盖亦亡国之音”[33](1730),将南方此后取得的文学成就一笔抹杀。这一批评逻辑和刘勰“由质及讹”的流变观念没有本质不同,同样体现出历时层面的价值判断。
陈子昂、李白在随后掀起的复古诗潮亦继承了刘勰的文质观,同样展现出一些矛盾之处。周振甫曾举陈子昂、李白对张华、谢朓的高度评价与他们对晋宋以来诗风的整体批判之间的矛盾为例,将之解释为“总体倾向”与“个别作家”之间的不同[34]。“总体倾向”正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叙》所称:“贞观末,标格间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35](156)与要求改制的公羊家一样,这种要求“尊古”的文质观有利于追溯本源,为事物的革新找到合法依据。然而,一旦进入到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或是自身的创作,就必须用另外的方式弥补“总体倾向”的不足。
尽管唐初史官和陈子昂、李白等人普遍强调对浮华的抑制,但他们也广泛地接受了刘勰对“情文”的看法。如《晋书·文苑传》:“史臣曰:夫赏好生于情,刚柔本于性,情之所适,发乎咏歌,而感召无象,风律殊制。”[36](2406)《北齐书·文苑传序》:“文之所起,情发于中。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气,顺四时之序。”[37](602)《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38](744−745)顺流而下,诗人更加重视辞采对情意的表现作用,如殷璠称“文有神来、气来、情来”[35](156),以“情来”为一种主要的创作动机,他选诗的宗旨最终也呈现为“文质半取,风骚两挟”[35](157),而不是完全的尊古返质;旧题王昌龄《诗格》既说“晋、宋、齐、梁,皆悉颓毁”[39](160),又大力称赞谢灵运诗,同时认为诗的创作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然后书之于纸也”“不立意宗,皆不堪也”[39](161),用他归纳出来的“十七势”极尽强调文字对情意的表现作用;皎然《诗式》一面说“将恐风雅寖泯,辄欲商较以正其源”[40](1),一面又说“虽欲废巧尚直,而思致不得置;虽欲废言尚意,而典丽不得遗”[40](16),认为高手应该“但见性情,不睹文字”[40](32)。在这一理路中,“诗人将特定的情感举重若轻地寓托其中,却丝毫没有影响对眼前境界的逼真描绘,愈藻愈真,愈华愈洁”[41],刘勰的“情文”说遂成为调和文质的法门,在此后的唐诗创作中得到了实践的印证。
总之,如果未注意文质论历时、共时两种形式留下的潜在意识及其在《文心雕龙》中的合流,就容易将“文质”等同于“形式—内容”二分法,误认为陈子昂、李白、王昌龄等人的文论和实践有严重的疏离,或简单地或认为古人的文质观驳杂不纯,难以定性,而忽视它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实际影响。
① “文”“质”字义在先秦时期的发展,可参见陈伯海《“文”与“质”:中国诗学的文辞体性论》第一小节,《学术月刊》2006年第1期。
② 文质概念在后世的诠解中仍然在不断向外引申,如皇侃云:“质,实也。胜,多也。文,华也。言实多而文饰少,则如野人。野人鄙略,大朴也。”(皇侃《论语义疏》卷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08页)“质”由“朴”继续引申,也就使其偏向了“实”。但是如果直接以“实”字取代《论语》中的“质”字,语义显然会发生改变。又如“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指礼有其本,文者,礼仪之节文。”(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33页),这种以质为本的观念严格上说也越出了《论语》的表述范围。
③ 参考杨念群《文质之辩与中国历史观之构造》,《史林》2009年第5期。最典型的例子是隋文帝、唐太宗都曾试图将“复质”理念贯穿到文学应用中,打造他们眼中区别于南朝短命王朝的理想政治。
④ 扬雄对文质的理解受到《论语》较大影响,如:“阴敛其质,阳散其文,文质班班,万物粲然”(见《太玄集注》卷四,第97页),“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谓也?’曰:‘玉不雕,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法言·寡见》,汪荣宝《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21页)。程千帆先生指出:“若事辞之说,则扬子本孔氏而推衍之,当汉赋大行,劝百风一之际,以箴砭时尚者也。”见《文论十笺》,莫砺锋编《程千帆选集》,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99页。扬雄重视“文”在表情达意上的重要作用,他自己放弃作赋,苦心经营《太玄》《法言》,也是希望别人能过通过他的“文”,来体会他“作经”的用心。
[1] 王运熙, 杨明. 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学批评中的文质论[J]. 文艺理论研究, 1980(2): 139−148.
[2]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
[3] 程树德. 论语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4] 朱谦之. 老子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5]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6] 向宗鲁. 说苑校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7]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8]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9]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0] 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11]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2] 赵在翰, 辑. 七纬附论语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13] 马泰·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 顾爱彬, 李瑞华,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
[14] 王夫之. 周易内传[M]//船山全书: 第1册. 长沙: 岳麓书社, 1988.
[15] 章学诚. 文史通义校注[M]. 叶瑛,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16] 康有为. 春秋董氏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7] 埃德蒙德·胡塞尔. 现象学的观念[M]. 倪梁康,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18] 司马光. 太玄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19] 黄晖. 论衡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20] 释僧祐. 出三藏记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21] 释慧皎. 高僧传[M]. 汤用彤,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22] 释道宣. 广弘明集[M]//四库提要著录丛书: 子部第244册.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1.
[23] 姜剑云. 谢灵运与慧严、慧观[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6): 80−85.
[24] 刘长庆. 佛经译场中的翻译理论探索[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9(S1): 106−109.
[25] 张少康. 文赋集释[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26] 严可均, 辑.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27] 姚思廉, 等. 梁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28] 沈约. 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9]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30] 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31] 罗宗强.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32] 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33] 魏征, 等.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34] 周振甫. 释“建安风骨”[J]. 文学评论, 1983(5): 3−8.
[35] 傅璇琮, 陈尚君, 徐俊, 编. 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36] 房玄龄, 等.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7] 李百药. 北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38] 令狐德棻, 等. 周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1.
[39] 张伯伟. 全唐五代诗格汇考[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2.
[40] 李壮鹰. 诗式校注[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6.
[41] 张甲子. 南朝诗风新动向与“秀”的理论形成[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2): 187−191.
The two forms of Wen-Zhi theory and Liu Xie's methodology of literary creation
FU Jiaao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00, Chin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arly binary opposition thinking, Han Confucianism focused more on observing the diachronic significance of "quality of literature"(Wen-Zhi), applying it to politics and creating the theory with quality of literature cycling that points to correct the defectives by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one of the benefits. This approach of prioritizing the quality of literature has long influenced the expressing ways of Wen-Zhi theory.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connected the metaphysical Wen-Zhi theory with the specific translation practice, disclosing the problem of observing the literature with the old view of Wen-Zhi theory, making the harmony of Wen and Zhi at the synchronic level a pressing task. Subsequently, the two forms of Wen-Zhi theory were integrated in: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in which Liu Xie further clarifies the two extremes of quality and literature and their connection with "emotion" at the synchronic level, takes “emotional literature” as the Tao of literary creation, puts forward value judgement of “emo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artistry. In this way, he compromised with the Quality School while affirming the artistry of literature, ultimately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literary theory of Wen and Zhi.
theory of quality of literature (Wen-Zhi theory); Liu Xie; the Tao of literary creation; "emotional literature"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3.05.018
I206.2
A
1672−3104(2023)05−0210−11
2023−04−15;
2023−05−27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永明至大历时代的诗学问题研究”(SWU1909742);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永明至大历时代诗歌意法研究”(22FZWB020)
付佳奥,男,湖南浏阳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唐代诗学,联系邮箱:erduhegu@sina.com
[编辑: 陈一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