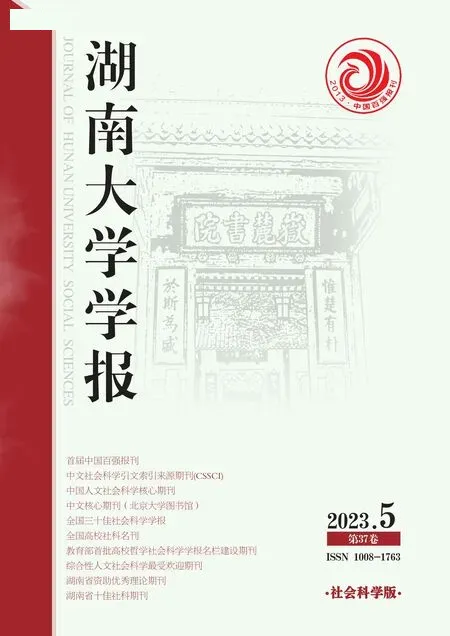《群玉山头》中英译杜甫诗的文化误读及其应对措施*
王敏琴,罗妙华
(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一 引 言
《唐诗三百首》汇集唐代名家名篇,体现了中国古诗的魅力,至今已流传了两百多年,展示了中国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在我国,《唐诗三百首》在文化和教育中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唐诗三百首》已有20多部译本,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就是威特·宾纳( Witter Bynner,1881-1968)的英译本《群玉山头》(TheJadeMountain:AChineseAnthology,BeingThreeHundredPoemsoftheTangDynasty,New York: Alfred A.Knopf, Inc,1929)。
宾纳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曾赴日本进行诗歌交流,后曾于1920年与费克一起到中国旅游,并由江亢虎介绍,在上海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并与其长谈。这次中国之旅对他的诗歌创作和唐诗英译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195。此外,赵毅衡曾在宾纳与许地山的来往信件中找到有关几种中国花草鱼虫的解释,以及其拉丁语和英文译法[2]111。宾纳也有汉语名字——陶友白。在江亢虎的支持与协作下《群玉山头》得以问世。1929年《群玉山头》出版后声名鹊起,受到了当时美国诗坛的高度赞扬,即使是一向看不起别人翻译的韦利( Arthur Waley,1889—1966),对这本翻译评价也很高[2]112。同样,宾纳的译本在中国评价也较高。《群玉山头》是《唐诗三百首》的第一个完整的英译本,还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自1929年首次出版后再版十余次,成功进入了英语文学体系,入选各种诗歌选集与大学文学教材,被誉为“本世纪最优秀的美国诗歌之一”[3]46。由此可见,《群玉山头》对传播中国文化的文学艺术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殖民与被殖民关系已经不再仅仅体现在经济、政治与军事方面,文化意识层面也体现着殖民关系,文化殖民与文化霸权主义兴起。萨义德的《东方学》(Orientalism)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西方人的殖民话语,体现的是以西方为中心的霸权主义以及西方人对东方人的殖民思想。“东方主义”应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东方主义”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4]4。因而我们要警惕在学术中充斥的殖民话语。在后殖民语境下,被殖民者的身份被殖民者视为“他者”(the other),受到“自我”(self)意识身份的打压。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后殖民理论传入中国以来,大量学者发表论文或著作对该理论进行研究、解释、讨论或翻译,形成了后殖民理论研究的热潮,促进了该理论在国内的传播。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翻译俨然包含着在不同文化碰撞下体现出的不平等观念。
以“文化转向”为标志的翻译与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继续成为翻译理论的一个主要焦点。巴斯奈特认为,翻译不是发生在水平轴上的,因为在文化和文学系统之间有不同的权力等级,也有不同的语言等级。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要求我们重新定义译者、作者和目标读者之间的关系,认识到翻译的复杂性和隐含的权力关系.[5]81-88在20世纪后半期,掀起了后殖民主义学术思潮,并在80年代末进入翻译研究领域。这一理论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强调文化之间的斗争性,使翻译研究的文化专向具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后殖民理论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6]。在后殖民翻译理论看来,翻译体现了征服与依赖关系、主导与支配地位、殖民与被殖民关系。尽管相比于后殖民文学,后殖民翻译受限于既存的源文本,但比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更具选择性和显性[7]。因此,我们应该警惕翻译中的文化霸权主义,提高文化话语权意识,主动将翻译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工具。
翻译也是一种再创造的行为,意识形态始终对译者和翻译过程起作用。意识形态影响翻译行为,译者发挥主体性采取不同的翻译方式和策略,创造不同的译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受自身政治文化背景的影响,使弱势文化屈服于强势文化,即采用归化的方法。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中提出归化( domestication)、异化(foreignization)两个翻译术语[7]15-40。他认为翻译应将源语文化纳入到异语文化中去,其目的是交流语言和文化中的差异,而并非追求流畅性[7]2。韦努蒂也在书中提出,异化翻译旨在对抗称霸的英语国家及其与全球其他国家进行的不平等文化交流,可以是一种对抗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文化自恋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形式,有利于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7]20。在后殖民视阈下,归化与异化两者本质是话语权力之争,体现了文化的不平等地位。因而,翻译不仅具有传播文化的功能,还能体现文化权力差异、身份差异以及谁掌握话语权。掌握话语权的文化在目的语文化中才能得到理解与尊重。
20世纪,随着汉诗越来越受欢迎,西方译者逐渐翻译更多中国诗人的作品,杜甫的诗开始出现英译本。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李白并称为“李杜”。其诗歌既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厚的政治色彩,又有心怀天下的高尚情操,是中国文学宝库的璀璨明珠,也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中国传统的独特文化内涵。尽管宾纳对中国文化十分感兴趣,也曾有机会来到中国与中国学者交流,但其译本中仍然存在对中国文化误读的现象。而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下,译者在翻译中所做出的选择正反映了两种语言文化在译者心中的主从关系,体现了译者的文化身份和价值取向。[8]译者的文化误读,体现的是译者对“自我”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他者”文化的排斥,阻碍了源语文化的输入与传播。本文以《群玉山头》中的杜甫的诗歌为研究对象,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角度分析译文中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体现的文化误读现象,旨在提高我国译者的主动性,帮助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二 物质文化的误读
文化负载词蕴含着具有每个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的词汇或短语,对于作为跨文化交流桥梁的翻译来说,文化意象的翻译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地方。杜甫的诗中出现的文化意象很广泛,包括动植物、乐器、地理名词等。而文化负载词的确切翻译,能使译文更加完美地呈现文化内涵,也更加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杜甫是一位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他的诗歌许多都描写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反映了唐朝由盛转衰的整个过程,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诗中包含了许多中国文化中特有的词汇。在宾纳的译本中,宾纳致力于正确地表达诗歌的内容,但是在一些具体的文化意象的翻译上仍采用了归化的译法,削弱了诗歌的中国文化特色,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从后殖民主义角度来看,这体现了译者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将西方人眼中的作为“他者”的中国文化转化为自身文化意象。
(一)对动植物的误读
诗中包含了许多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动植物名词。例如,在“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天末怀李白》)中的“鸿雁”,指代使鸿雁传递的来往书信。宾纳的译文是:“The wild geese never answer me. Rivers and lakes are flooded with rain.”[9]150,并没有正确地表达名词的真正含义,若译为“The message-sender wild geese never answer me. Rivers and lakes are flooded with rain.”则能较好地传达原诗的意蕴。此外,“龙”的意象也经常出现。“龙”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图腾和文化意象,在古代多为皇家专用之物,中国文化意象赋予了龙高贵、吉祥的含义,象征着活力与辉煌。但是,西方的龙(dragon)和中国龙的传说和象征是完全不一样的,其蕴含的文化意象也有很大差异。西方一直有勇者斗恶龙的传说,《圣经》中的龙是邪恶的化身,西方龙就是残暴的动物,其含义与恶魔无异。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意象差异会造成西方观众对“中国龙”的理解障碍甚至是误解。在杜甫的诗中,有许多处出现“龙”。例如,《阁夜》中“卧龙跃马终黄土”、《丹青引赠曹霸将军》中的“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宾纳的译文分别是:“Sleeping-Dragon, Plunging-Horse, are no generals now, they are dust”[9]156、“And later, when your dragon-horse, born of the sky, Had banished earthly horses for ten thousand generations”[9]164。首先这两个译文都将“龙”直译为“dragon”,体现了译者对我国文化的误读。这种文化误读不仅磨灭了中国文化的特色,还容易加深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在中国,本应该代表着尊贵的文化意象“龙”变成了凶狠的恶兽。这体现在译者心中中国文化处于“他者”地位,缺乏话语权,进而阻碍了中国文化的传播。从异化的翻译策略来看,将“龙”音译为“Chinese dragon”更好。“Chinese dragon”不仅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特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还能维护中国友好的国际形象。再根据我国历史典故来看,前一个例句中的“卧龙”指的是三国时期蜀汉的丞相诸葛亮。“跃马”指的是公孙述,西汉末年,他依靠自己所统治的奸诈之地,自立为白帝。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公孙则因为他的行为被认为是愚蠢的。所以这里的“卧龙”对应的是诸葛亮这样有谋略而志不在称帝的人,而“跃马”对应的是公孙述这种乘乱掌权的卑鄙之辈。诗人想表达的意思是:无论生前权势、声誉如何,聪明的人和愚蠢的人都会被埋在地下。许渊冲的译文采用的是“Premier and Emperor”,是两位人物的政治地位,在内容上也与原文更贴切。而宾纳的译诗采用了直译的方法,忽略了原文的历史文化内涵。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宾纳曾与许地山探讨过中国花草树木的英译,因而对花草树木的翻译较为正确,这就可以体现在这首诗的译文中。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草意象常被认为是孤独和无尽悲伤的象征。草是绿色和长,它们经常被描述为过度生长的大量。这让人们想起了他们无尽的悲伤,所以草的特性被映射到人类的情感上。但在西方文化中,草的意象却没有这样的隐喻。在《佳人》中提到佳人沦落至“零落依草木”,其中的“草木”形容卑身贱体、身世坎坷。宾纳就意译为“Which is humbled now into the dust”[9]192,正确地表达了内在含义。但是其他具体意象的花草植物,宾纳采用了归化的译法,使用西方人熟悉的、又有相似之处的单词代替,体现了译者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价值取向。例如,“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这句诗中的“合昏”是合欢花,也叫夜合花,具有朝开暮敛的特点,所以有合昏、夜合等别名。宾纳采用了归化的方法将“合昏”译为同样具有朝开暮合特点的牵牛花“morning-glories”,准确地表达了原诗的意象与含义。
(二)对乐器的误读
琵琶是我国的传统弹拨乐器,大约在中国秦朝出现,已经具有两千多年历史,是我国艺术文化的瑰宝。无论从器形器声、弹奏方式还是演奏者这三个方面来看,琵琶都包含了悲苦、离别与暧昧的内涵[10]。这便使得“琵琶”在我国的古诗中,常带有凄凉的象征意义。杜甫的诗就多次出现“琵琶”。例如,《咏怀古迹(其三)》中“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宾纳将其译为“guitar”,同样是采用了归化的方法。正是由于在西方没有与“琵琶”这种弹拨乐器完全一致的乐器,所以译者将“琵琶”翻译成西方乐器“吉他”( guitar) 。译者将其近似译为吉他,虽然意思不完全准确,但不影响整首诗意思的理解,反而更加利于目标读者的理解。但是这种用译入语文化的名词替代的方法使诗歌失去了原文中包含的文化意象。
译者这样绝对的归化译法,用西方乐器名称代替中国的传统乐器,不仅使翻译不准确,也失去了民族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不利于文化之间的交流。根据关联理论翻译观,结合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把中国传统乐器的英文译名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用汉语拼音表示 (音译) ,第二部分标明乐器族,并将该策略应用于部分常见的中国传统乐器译名之中[11]。因此,从文化输出与交流的角度来看,“琵琶”最佳的译文应是“pipa lute”,既保留了中国传统乐器文化,也有助于目的语读者的理解。
(三)对地理的误读
除此之外,宾纳译本对诗中出现的地理名称的翻译也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地理名词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地理名词的翻译也应彰显其包含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色。但是为了让对中国诗歌不怎么熟悉的英语读者能快速准确地欣赏中国诗歌,宾纳在翻译中用一般的地理词汇去替换原文中具体的地点名字或者干脆回避典故,以让译文的可接受性更强。例如,《望岳》中“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宾纳的译文是:“What shall I say of the Great Peak? The ancient dukedoms are everywhere green.”[9]191,将“岱宗”译为了“the Great Peak”,意思是“巨高的山峰”。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五大名山,并称为“五岳”,也就是五座山峰,诗名中的“岳”就是指山,而诗句中的“岱宗”指代的就是“泰山”。宾纳的译文虽然不会造成读者的误解,但是这样宽泛的译文让外国人失去了更多地了解中华文化的机会。而我国的译者吴钧陶就采用了意译的“Mountain Tai”,引发读者对中国地理文化了解的欲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对于其他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名,宾纳采用的则是音译法。例如:“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诗中提及的是唐朝时期的安史之乱,发生于唐朝国都长安(如今陕西西安),而“关中”就是指陕西中部地区。宾纳采用英译法,将“关中”译为“Kuang”,没有增加注释等其他介绍关中地区的信息。对于不精通我国历史文化的读者来说,他们无法更深入地了解我国历史文化与诗歌内容之间的内在关联。这就使译文失去了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作用,也使诗歌意义不完整。从这点来看,许渊冲的译文“Central Plain”更有推动文化走出去的意义。
三 精神文化的误读
精神文化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精髓。相比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更具有抽象性。而且,由于中外文化的伦理道德基础和各民族的发展历史都存在较大差异,跨文化译者与读者较难准确理解我国文化。宾纳的译本在伦理文化和历史典故两个方面对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读。
(一)对伦理文化的误读
儒家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文化深受儒家伦理影响,儒家伦理也逐渐内化为中国人的品行修养。而西方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较大,西方伦理文化背景下的译者,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来处理与中国伦理文化相关的翻译,造成了对原文中的伦理关系的误解。聂珍钊教授认为,文学是因为人类伦理及道德情感或观念表达的需要而产生的[12]。伦理规范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是“风俗沿袭而来的,因此把‘习惯’(ethos)一词的拼写方法略加改动就有了‘伦理’(ethike)这个名称”[13]3417。可见,伦理是规范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规范准则,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统,与民族的历史发展关系密切。
中国自古以来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宗族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强调家国观念,移孝为忠。中国深受家庭伦理关系的约束,家族观念尤其深重。因而在古代,个人会因家族昌盛而尊贵,也可能因家道中落而沦为卑贱。儒家伦理推崇周朝的礼乐等级制度,正如荀子提出的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荣辱》)。这种等级观念同样体现在婚姻里,强调门当户对。随着女子家族的没落,两个家庭之间出现的阶级差异,也会使婚姻破碎。诗中的佳人就是面临这种困境。在《佳人》这首诗中,佳人因兄弟在战乱中丧命,家族没落,才落得被丈夫抛弃的下场,因而感叹道“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也就是无论家族曾经多么身居高位,如今家族没落后,也没有人愿意收养这个家族中幸存的女儿。所以这里的“骨肉”应该代指诗中的“佳人”,而不是死去兄弟的身躯。但是,宾纳将这句话译为“What use were their high offices, Not even shielding their own lives?”[9]192,一方面是由于宾纳对中国语言的不完全了解,不知道“骨肉”在中国也可以指兄弟、至亲。所以,此句可译为“What use were their high offices, Not even shielding their own kindred?”。另一方面,是由于宾纳对中国的家族观的误读,不知道个人因家族没落而遭遇变故。由此导致宾纳对原文的理解存在偏差。正是西方文化强调的个人主义思想影响了译文,将中国文化中的伦理关系转变为西方人理解的关系,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从属地位。
儒家伦理以家族血缘关系为重,而家庭中的伦理关系是“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礼记》)。即以夫为尊而以妻为卑。但董仲舒也提出“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春秋繁露·基义》)。孔子认为要做到“夫妇和”就要互敬互爱,相互忠贞。所以儒家倡导的夫妻秩序应该是男女有别,阴阳合德的和谐关系。但是《佳人》这首诗中的丈夫喜新厌旧,抛弃发妻,这些都是有违伦理的行为,被她称谓“轻薄儿”。这个词就应该包含了对丈夫的控诉之情。相比之下,佳人被负心汉抛弃之后并没有迷失道德,而是选择深居幽谷,过着卖珠宝首饰维持生计的清贫日子,不再注重容貌修饰。诗中出现的“竹”的意象,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正人君子的优秀品质,高风亮节,意志坚定。这就是对佳人高洁情操的赞美。但是宾纳的译文中采用的是“vagrant”一词。这个词的含义是“流浪的、游离不定的”,只体现了男子在感情中摇摆的状态,未能体现女子对不忠丈夫的怨恨之情。相比之下,许渊冲的译文“My husband’s fickle, I’m afraid”[14]136中使用的“fickle”,更能体现女子对男子在情感上三心二意不忠品行的鞭挞。译者所处的西方向来强调自由和个人权利,在爱情婚姻里有十分自由的选择权利,因而在他们看来亲近新欢是个人权利而不是缺乏道德的行为。“vagrant”对中国伦理规范的理解不够深入,无法完整地体现诗歌情感,削弱了诗歌的感染力,也无法体现中国的伦理道德评价标准,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译者与读者处于同一种文化背景,更有利于西方人理解译文。
(二)对历史典故的误读
杜甫善于引经据典,诗中多引用典故表达情感。这些典故包含着中国的历史,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中的瑰宝。宾纳在翻译这些带有典故的名词时多采用音译或是直译的方法,磨灭了原诗中的文化内涵,不仅不利于完整而正确地传达原诗句的意思,而且还不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这也体现了在西方文化的强权下,中华文化在西方的话语权被剥夺[14]。
《咏怀古迹(其三)》中的“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Ten thousand ranges and valleys approach the Ching Gate and the village in which the Lady of Light was born and bred . ”[9]190)“明妃”指的是王昭君,全诗也是对她的咏怀。在《后汉书·南匈奴传》中提到“昭君字嫱”,即王昭君原名可能是王嫱。为了让身为宫女的王嫱代表汉朝与匈奴和亲,将“昭君”作为封号赐予她。因而“昭君”不仅体现了她的倾城容貌,还包含了她代表汉皇光照匈奴的政治使命。后为避司马昭的讳,王昭君改名王明君。因而,此处的“明”更强调的是明妃做出的历史贡献和政治意义,所以,“Princess Ming”更好。
再如,杜甫在《天末怀李白》中表露出对处于流放途中李白的忧虑与挂怀,为李白蒙冤的悲惨遭遇愤愤不平。诗人在最后一句中引用了屈原的典故,“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诗中的“冤魂”就是蒙冤投身汨罗江的屈原。宾纳的译文是“Ask an unhappy ghost, throw poems to him. Where he drowned himself in the Mi-lo River. ”[9]150。采用了直译的方法,虽然不影响全诗的理解,但是造成了文化典故的流失。相比之下,许渊冲的译本保留了历史典故,而且采用释译法也能帮助读者理解为什么李白要写诗给冤魂,“Would you confide to the poet wronged long ago. Your verse which might comfort his soul in weal and woe?”[15]152。除此之外,前文提及对“卧龙”“跃马”的直译“Sleeping-Dragon”“Plunging-Horse”,也是对我国历史典故的误读与忽失,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
四 总 结
译者宾纳曾亲自到访中国,对中国文化了解较多,但其译作《群玉山头》中仍体现了对中国文化误读的现象。文化误读对于与译者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来看,更有利于他们的理解。而从后殖民主义理论来看,翻译体现的就是文化话语权的问题。宾纳对杜甫诗歌中的文化现象多采用归化法翻译,既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也体现出西方文化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文化在译文中失去了话语权。这就使中西文化处于不平等的交流状态,中国文化不能有效地传递出去。近几年,我国加大了外宣的步伐,以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翻译既是桥梁也是屏障,如何让我国国学和文化“走出去”是我国译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但同时,翻译也是一个形象构建的过程,译者可以通过重译,修改“他者”的归化翻译,达到反殖民和传播文化的目的。
对于消除译作中存在的文化误读现象,一方面,译者应加强文化自信,肩负起传播文化的使命,在翻译中掌握主动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另一方面,我国应加强版权意识,严格审核海外译本,以遵守维护我国文化与形象为底线。作为拥有作品版权的作者,可以选择合适的版权代理人,在海外出版贴合原文的译本,从而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而另一类作品,在作者逝世50年后,其著作权的保护期截止,作品进入公共领域,但是该作者的署名权和修改权仍受保护。对于这类作品,我们较难通过法律的手段要求译者修改内容。但是我国译者能通过在海外出版更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译作,推动译作广泛传播,纠正海外读者对我国文化和形象的认识。综上所述,版权保护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最佳时期,由此便可以运用法律的手段高效地消除文化误读现象,维护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简而言之,我们只有提高文化认同感、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在跨文化交流中掌握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