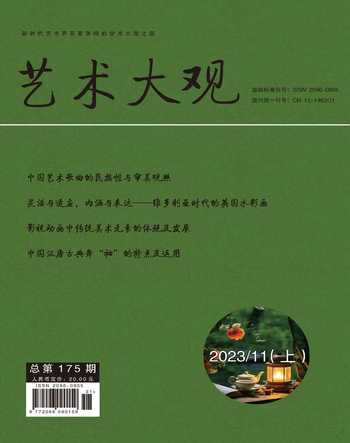当代“新工笔”人物画中的图式表达
高青青
摘 要:在现代社会日益发展的当下,传统工笔画被迫探寻新的绘画语言以及当代性观念表达方式,“新工笔”画应运而出,逐渐实现艺术创作在图像与精神意图上的融合。“新工笔”人物画在完成传统工笔画当代性绘画语言转变的同时,受到当代观念、外来艺术思潮的冲击、媒介材质多样性选择等因素的影响,仍然作为继承传统绘画的现代性绘画程式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关键词:新工笔;绘画图式;当代性;观念先行
中图分类号:J2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905(2023)31-00-03
“新工笔”作为当代中国画的新现象,凭借其独特的绘画图式语言,为工笔画领域丰富了新内容,其内容上的观念性表达,传达出当代人对社会、对家园、对自我的慎思和难以名状的忧虑,在较为平稳和安定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更多是在随波逐流的生活浪潮中麻痹自我,缺乏自醒的能力,这正是新工笔画所传达的一种信息。另外,“新工笔”是以传统绘画为基础以“观念先行”的思想来发展的,若是一味地在自我感悟的精神世界里追寻观念性的事物,故步自封,脱离了传统工笔画的基础,那么就无法在要求创新性发展的社会立足。本文从“新工笔”人物画的内涵和现实意义出发,结合文章主题阐述绘画图式的基本概念,通过个例分析阐述“新工笔”人物画中的图式表达,将绘画图式与画家的精神语境结合在一起,探讨“新工笔”绘画的当代性,以期探索“新工笔”人物画图式语言更多的可能性。
一、当代“新工笔”人物画的概念及现实意义
(一)“新工笔”概念的产生和发展
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内艺术思潮经历了西方艺术的冲击和鼓舞,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傳统绘画形式开始受到重视,并使得中国传统绘画逐渐开始向现代化转型。而工笔画这一传统画种,也涌现了一批批优秀画家展现出其蓬勃发展的生命力。“新工笔”逐渐成为现当代工笔画的一个重要研究现象,涌现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越来越多的画家开始用个人鲜明的风格去尝试和表达并逐渐扩大新工笔的范畴,而其中以工笔人物画居多。相比工笔花鸟画而言,人物画因其画面构成的多样性,人物形象的可塑性,都使得许多画家选择工笔人物画的方式。
而当代新工笔人物画有何创新,与传统工笔人物画有何不同,新工笔作为当代工笔画的一股新兴力量是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开创性探索的,接下来将从观念表达上和画面内容上这两个方向进行阐述。
(二)当代“新工笔”人物画的崭新之处
“观念先行”一词出自当代工笔人物画家张见的《我画之我见再议》一文[1],在文中提到,相对于传统工笔画和当代工笔画,“新工笔”的第一要义是“观念先行”。纵观众多新工笔系列画作,我们可以略微总结出,他们的作品从直观而言多具形式感和画面色彩的高度协调统一,但从画面内涵而言他们的作品体现出强烈的个人主观观念和情感色彩,这与传统工笔画崇尚弘扬时代感的特点大相径庭。而到了近现代,物质世界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精神世界也愈发丰富起来,现代人更加注重自身的情感表达和宣泄。工笔画这一传统绘画方式也逐渐在现代的潮流中慢慢转变。
新工笔人物画家的画面中经常运用多种象征手法,用隐喻、暗示的方法给观赏者留下思考的留白空间。这类新工笔画家认为:“用暗喻的方式创造源于现实的理想世界——这样的世界远比客观世界更为真实和永恒。”他们的作品往往是反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因此他们所描绘的画面常常是不真实的场景,梦境般的时空,甚至是没有背景仅仅只有缥缈虚无的颜色。
而新工笔相对于传统工笔画另一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新”字,“新”指的是在继承传统绘画技法的基础上,转变绘画语言所带来的新的视觉感观。而形成这一转变则有赖于新工笔画家在线条、用色、构图等方面颠覆性的尝试。
(三)当代“新工笔”人物画的现实意义
当代“新工笔”画不论是以“观念先行”为第一要义的要素,或是技法和画面构成上的突破性创新都是对传统工笔画的一次更新,它重新构造了工笔画语言并使其向现代化转型,展示出传统工笔画绵长的生命力。
工笔人物画方面,何家英等一批走在时代前沿的画家,对工笔人物画的探索达到近代的一个新高度,他们的作品成为当时直至如今各美术院校学生的临摹范本,对工笔人物画向现代化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1世纪信息时代化的浪潮推动了中西绘画的融合,促使传统绘画向现代化转型,当代“新工笔”画应运而出。当代“新工笔”人物画家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寻求创新,在遵循“三矾九染”的绘画程式上,多采用绢本(也有多数宣纸)这样具有薄而透特点的绘画载体,使画面达到虚幻迷离、缥缈如梦的效果,并开始运用综合材料,将创作与绘画媒介的关系逐渐扩大化。在用线方面,与崇尚“骨法用笔”,以“吴带当风,曹衣出水”为美的传统工笔人物画不同,当代“新工笔”人物画家更加注重线条在画面情感中的表现力,工笔画家杭春晖认为:“线条并不是中国画尤其是工笔画的目的,它仅仅是一种手段……线条背后应该是一种精神的表现。”[2]在创作过程中,他们更是选择弱化以线造型的作用,更多依附于色彩搭配和色块组成。这些都足以显现出,传统工笔画在现实语境中以一种更具创造力、想象力的方式再现,工笔画语言逐渐实现现代化的转变,当代“新工笔”人物画正以它独特的方式传达出工笔画的审美内涵。
二、当代“新工笔”人物画中的图式表达
(一)绘画图式的概念阐述
图式一词属于哲学和心理学的范畴,言简意赅地说一个符号,一个物体均可以被当作一种图式。对于绘画来说,图式是画家自身经常在作品中描绘的带有一定特殊含义的样式,它来源于画家自我对现实世界积年累月的主观认识所简化成的抽象概念。客观世界是艺术创作不竭的源泉,但创作内容取决于画家主观认识和自觉选择,如果只是简单地再现和临摹写照,缺少了主体的精神和情感表达,那就不能称之为艺术作品。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认为:“没有一种媒介,没有一个能够加以塑造和矫正的图式,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不能模仿现实。”[3]图式与艺术家的个人精神情感以及审美观念密切相关,文化环境不同,中西方绘画所呈现的视觉要素也就不同,西方绘画讲究光影明暗、体积、透视关系等,而中国绘画则遵从“气韵生动”,注重笔墨等。
中国传统文化受儒释道的影响,在绘画上强调天人合一,情景交融,客观景象同主观精神相契合的意象表达。但由于画家不同的文化基础、地域、社会阶层以及后天形成的品性品格、道德修养等,都会形成不同的绘画风格,而艺术创作中所展现的具体“图式”也就大不相同了。与西方绘画相比较,能比较直观地总结出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意趣,中国绘画的传统图式特征也就可以稍作归纳,首先,以线造型,以形写神是传统绘画的造型规则,谢赫的“六法论”确立了中国画创作的基本方法;其次,深入画面内容上来讲,有着高度程式化总结的创作手法,如山石的各种皴法,树木的画法,工笔人物画中衣服褶皱的十八描等。
(二)东方与西方——以新工笔画家张见为例
在工笔人物画家张见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东方与西方极致的融合,画面构成和线条疏密关系是偏中国传统工笔画的,而他的色彩观念却完全是西式的。这源自画家本人对西方古典作品的偏爱,大学期间,张见接触到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作品,并受到德沃尔画风、玛格丽特画风的影响,他的画面中存在超现实的元素,还运用了多种象征、暗喻的手法。张见还尝试借用传统国画里略犯忌讳的桃红色、粉蓝色等色彩完成别具一格的画面感观,因为他认为传统上的线、色彩、人物、置景等都是服务于画面的元素,作品的整体效果才是最重要的。
对他笔下人物形象具有启示作用的一位画家则是波提切利,波提切利画中人物遵循着极其优美的形态却忽视了人体结构,这样的人物造型特点与中国传统人物画中“以形写神”的意象表达不谋而合。对于张见来说,人物只是组成画面的元素,与他画面中时常出现的植物,具有机械感的电线杆等图式表达是关系等同的。一系列带有工业文明和现代感的图式表达联结在一起,使画面产生超出单个物体本身所带来的精神意义。
他注重画面的故事叙述性,如《向马格丽特致敬》这幅作品,画中身披婚纱的主人公为张见好友的妻子,人物的目光正前方立着一支烟斗,一行小字“这不是一支烟斗”正印刻在那支烟斗的正下方,正因有了这行小字的存在,马格丽特的烟斗不仅是一支烟斗,这幅画便具有了意义。也正因如此,在张见的画中每一个置景置物都不是虚设,每一样图式表达剥离画面而言都有着他特殊的含义,是从张见个人长期积累的视觉记忆中得来,值得我们深深品味。[4]
(三)虚幻与现实——以新工笔画家徐华翎为例
与张见作品中东西方极致化的画面和机械文明下的疏离感不同,工笔画人物画家徐华翎则呈现出“新工笔”画的另一种面貌,她的画面体现了都市文化下现代年轻女孩的青涩懵懂,整体画面呈现一种纯真、虚幻和朦胧的美感。她从女性的角度,集中地描绘女性的人体美,她的绘画风格虽是从学院派而来,但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当代艺术的特质。[5]
徐华翎作品中最直观也最常见的一种图式表达就是年轻女生的躯体,她以人体为主题但又不像传统工笔画中那样完整地展现一个或一组人物,而是从人体的局部入手,只表现一部分躯干、后背、侧面、一双手,或一只手拽拉衣物的动作。这样极度特写化的手法使构图得以十分饱满,表现力极强,这一点也得益于西方黑白摄影的影响。在绘画载体方面,徐华翎也如许多新工笔画家一样选择了绢本,传统的绢既有薄透的特点,也有纹路的质感,与她选取的人体题材十分契合。
作为一名女性画家,对女孩生活日常和对女性私密空间的切身体验,对人体感兴趣,是徐华翎选取女性人体为画面主体的主要缘由,但在创作过程中,她发现传统工笔画语言的那种勾勒再染色的方法难以表现出她内心理想的微妙、丰满的人体表达,于是她开始尝试将轮廓线去除,弱化线条以及以线造型的作用,但又因为对传统绘画长期的汲取,她内心还是认为线条是很重要的,于是让线在画面中以另一种方式呈现,比如人物衣服上的蕾丝,完完全全是用墨线勾勒而成,比如女孩的头发,朦胧的色彩当中还是有线条的存在。与张见等一些新工笔画家一样,他们逐渐转变思想,将传统工笔画中的线条为己所用,将线条当作一种手段为自己的画面而服务。
(四)童话与静穆——以新工笔画家杭春晖为例
杭春晖作为一名当代艺术家,近两年来以综合材料实验性绘画作品活跃在艺坛,但他早期工笔画作品被认为是当代“新工笔”画的一股新兴力量,这里主要是基于他2010年前后的一些工笔作品来进行探讨的。杭春晖工笔作品中的图式表达是有迹可循的,从一开始的抒情性人物画系列,之后的“玩具熊”系列,再到后面对绘画语言的探寻上进行实验的太湖石系列,最后是绘画语言与内在精神达到统一的光感系列。从他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出,他认为画家的个人绘画语言是区别于其他画家的重要因素,一个成熟的画家不应看他画的是什么,而应看他怎样画,因此他也从未停止过对个人绘画语言的探究。
因为有过优异设计经验的关系,在他的“玩具熊”系列作品中,作品名称包括主体物都有他设计思维的展露。画面中毛绒玩具熊和鲜血是两种非常强烈的图式表达,画中主体玩具熊所带来的童话寓意与灰色抑郁感的画面产生强烈对比,整体画面色彩呈灰色调,情绪基调是压抑、沉郁的,这与他个人的敏感性是有关系的,作品凸显了他主体的精神意图,借用小熊系列表达出渺小个体在社会环境下的失迷,以及每个人所遭受或多或少的伤害等。杭春晖的工笔作品探讨了一种传统工笔画语言在当代的变迁,我们不能用过去的语言来表现当下,正如他相信一个时代的社会文明有一个时代所需要的表现语言,工笔画人物画亦是如此。[2]
三、结束语
工笔画根源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是属于东方特色的艺术语言,“新工笔”则根植于现代社会下个体想要强烈传达出自我精神意图的诉求,“新工笔”人物画家凭借其细腻独特的图式表达,表达出关于个人、社会以及当代文化的精神图谱。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同时,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融合西方古典图式内涵、用当代性语言去抒发个人观念,完成工笔画传统艺术语言的现代化转变。本文通过对几位“新工笔”人物画家的作品中绘画图式表达的阐释,去感受和学习他们笔下的艺术构造,同时启发笔者自身工笔创作中的选材与构思。面对“新工笔”绘画的发展我们应当用辩证的眼光去审视,肯定其中当代绘画语言的可能性,规避其过度的意象表达可能导致的虚无主义,使工笔画人物画能够以绵亘的生命力持续发展下去。
參考文献:
[1]张见.我画之我见再议[J].美术观察,2019(12):102-107+2.
[2]杭春晖.新工笔文献丛书[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0.
[3]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4]张见.新工笔文献丛书·张见卷[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0.
[5]徐华翎.新工笔文献丛书·徐华翎卷[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