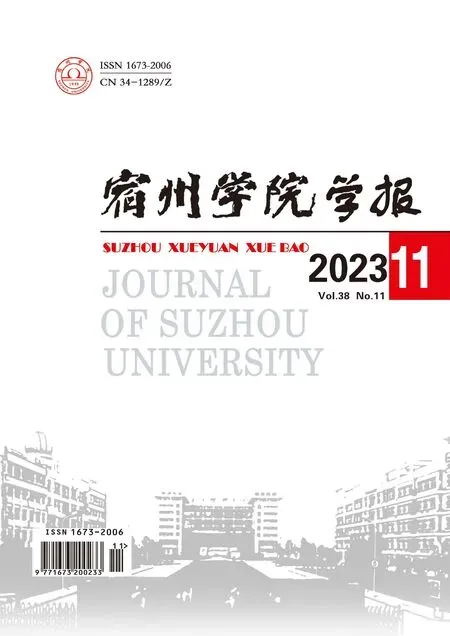安徽萧县圣村M1画像石综合研究
王 倩
安徽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安徽合肥,230033
萧县画像石墓是皖北地区汉代画像石墓重要分布区之一,萧县近些年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画像石墓,主要分布于孙圩子乡破阁村、龙城镇陈沟村和圣泉乡圣村。其中圣泉乡圣村M1是由萧县博物馆于2003年抢救性清理,后王小凤、周水利、孙伟等对该画像石墓进行研究,王小凤虽然按照墓室详细叙述了十一块画像石,但未指明画像石的具体空间位置[1]。周水利也公布了其中九块画像石,但没有按照墓门、甬道、前室、耳室和后室的顺序描述[2]。2018年出版的《萧县画像石图录》中并未将M1作为一个整体将画像石配置资料公布,读者仍不了解M1的布局情况[3]。2019年出版《汉画总录萧县卷》中全面公布了圣村M1的画像图片资料,但未有进一步研究[4]。上述研究积累了一定成果,但读者仍不能一窥M1全貌。所以笔者根据已公开的资料和实地考察为线索并结合墓葬形制、画像石配置复原M1具体画像石的空间布局,方便认识M1的墓葬等级、画像布局和丧葬含义,以求教于方家。
1 画像石布局
圣村M1为砖石结构多室券顶墓(图1、图2),平面呈“中”字形,由墓门、门扉、甬道、前室、后室、西耳室、东耳室组成,墓向北偏东15°。出土几件陶壶和罐,还有人骨。这种墓葬形式在皖北地区较常见,如宿州埇桥区栏杆镇金山寨汉画像石墓[5],还有淮北花山公园发掘的中型汉画像石墓,也是前后室的砖石混筑墓。笔者根据前人研究并结合实地考察对M1做了一个复原图(图3),下面根据墓室空间位置分别研究各部分画像石内容。

图1 实景照片

图2 考古现场

图3 画像分布图
墓门。门额和门楣有画像石,门额是椎牛图,无边饰。椎牛图是苏鲁豫皖画像石中常见题材,如徐州贾汪北部地区出土的击牛图[6]。椎牛和祭祀祖先有很大关联,是一种“椎牛祭祖”行为[7]。圣村M1椎牛图也属于一种祭祀行为,是通过椎牛图表示已进入墓葬空间区域。门楣为龙虎画像,均为兽形,背部有羽翼,属于飞升瑞兽,边饰为锯齿纹。龙虎之间有柿蒂纹,中间的圆钮高高凸起,柿蒂纹在铜镜、漆器、青铜器和画像石上较为常见的纹饰,关于柿蒂纹李零先生曾考证为“方华纹”或“方花纹”[8]。门楣下两立柱皆饰十字穿环图案。门扉是否有画像未见资料。
甬道。两侧是青砖砌筑,后壁有画像石,由门额、门楣和立柱组成。门额是半圆形石块,上雕刻龙虎相向飞奔图,形象更加高大雄壮,身上无羽翼。门楣正中雕刻有太一和伏羲女娲图,太一坐着中央,两侧是伏羲女娲面对太一。边饰为锯齿纹。东边立柱较窄,正面雕刻羽翼白虎,作奔腾状。西边立柱较宽,雕刻有楼阁图,一楼厅堂内雕刻有一只大吉羊东向立,其上站有一羽人,东边有一只鸮西向跪坐,厅堂西侧有一个楼梯通向二楼。二楼房屋是庑殿顶,屋内坐着墓主夫妇,东侧是男墓主人,西侧是女主人,右下角还雕刻一个小侍女。立柱外各站立一佣人,其中西侧佣人背着囊袋,东侧佣人手持一物。屋顶上东侧是一只鸮,西侧是一只凤鸟,均做攀援状。
前室。北壁,门楣,断裂,并列雕刻五格图案,自西向东图案依次是:第一格是月亮图,方框内有四出草叶纹,月亮内是玉兔捣药和蟾蜍;第二格是夫妻对饮图,西侧是女主人,左侧放置有漆酒奁和两个漆盘,右边有一侍者仅雕刻半身入画,东侧的墓主人因为石块断裂缺失太多;第三格位于正中央,是一个高高柿蒂纹;第四格是饮马图,马被拴在扶桑树的树枝上面,树下站立一只健硕的公鸡,御者站在神树的东侧,最右上角仅刻有一只大鸮首入画;第五个是太阳纹,方格内有四出桃形纹,太阳内站立一只三足金乌鸟。边饰上有垂蔓纹下有菱形纹。
南壁。门楣雕刻五格图案,从西向东依次是:第一格是西王母正面端坐在昆仑山的天柱上,左侧有一侍女跪坐。第二格是高凸柿蒂纹;第三格是主体图像宴饮图,中间摆放一张六博棋局,上面是个六博棋盒,再上面漆酒奁、漆盘和耳杯。西侧榻上跪坐着三个人;第四格是高凸柿蒂纹;第五格是东王公正面端坐在昆仑山的天柱上,右侧一男侍者跪坐向东王公。边饰有垂蔓纹和曲线纹组成。西侧门柱雕刻站立的蛇尾伏羲,东侧门柱雕刻站立的蛇尾女娲,门柱的一侧均是十字穿环图案。中间的立柱是四面雕刻,其中北面雕刻常青树,树周围有多只猴、鸮两种动物;东面雕刻连理枝,树周围同样有猴和鸮;西边是十字穿环图案;南边雕刻站立属吏,左右上角各有一只鸮首入画。
西耳室。由门楣和两立柱组成。门额是乐舞图,正中是建鼓舞,虎形座。建鼓右边依次是跳丸、倒立、摇铃;建鼓左边依次是吹竽、吹箫、吹排箫。边饰是垂蔓纹和曲线纹结合。北侧立柱正面雕刻有凤凰、燕子和大鱼。中间雕刻一只变体的骆驼,最下部是一头大象,上面端坐一个胡人,手拿塵尾。南侧立柱正面是人面兽身蛇尾,双手托举日轮,太阳内是三足乌,立柱侧面雕刻扶桑树,树下多角的神鹿,树稍上蹲坐着一个羽人。画像最下端是垂蔓纹。
东耳室。由门楣和门柱组成。门楣是车马出行图,方向朝北,中间单驾轺车,车夫手持缰绳和木棍,后面坐着一位官吏。后有骑吏跟从,前有骑吏引导,导骑前跪拜两位属吏,后面站着一位属吏。北门柱,正面是站立的拥彗属吏,属吏上方是一个正面羊首;门柱内侧面是一条翼龙,走兽型。南门柱,底面雕刻一有羽翼的吉羊,犄角卷曲,上面坐着一人。中间是一只飞翔的大燕。最上面是手持钩镶和环首刀的武士。
后室。南壁由山墙和横梁组成。山墙是半圆式构图,画面正中是庑殿顶的厅堂,内坐夫妇对饮,中间是漆酒奁,上面有两耳杯。西边是男主人,东边是女主人,两侧各有一侍者。厅堂屋宇上站立一只展翅的凤凰,前面有一个跪拜的羽人手持宝珠。屋宇两侧各蹲伏一只人面鸮。厅堂两侧各站立执戟属吏,再向外是高耸的双出门阙,门阙外各站立一个扭曲的力士舞者。边饰是一圈锯齿纹。横梁雕刻了神兽,有白虎、熊、开明兽、人面鸟身、飞鸟等。边饰是锯齿纹。北壁门额是羽人双凤双龙图。羽人站立在正中央,头上伸出两个似胜的物件,身披羽翼,两旁双凤口衔连珠仙枝,最外侧是卷曲的羽翼团龙,无边饰。
2 画像石内容的丧葬意涵
圣村M1的画像石内容十分丰富,画像雕刻技法属于上乘之作,浮雕式的技法干净利落,线条和细节刻画入微,雕刻功力极深。在构图上较多地采用对称构图,熟练的运用线条表现场景和人物。不管是神话、瑞兽还是刻画现实生活的题材上,其造型是呈现平面性、意象性的。表现这些造型的线条古拙遒劲,造型简练有趣,采用各种弹性的线条装饰这些形象[9]。
圣村M1画像石内容比较丰富,画像石中还存在一些具有装饰意义的边饰、十字穿环纹饰,这些装饰纹样也具有诸多学术价值[10],本文不做深入探讨,主要研究具体形象的画像,根据丧葬习俗含义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反映墓主人生前的现实世界;第二类是藏形安魂之所。
2.1 生前现实生活场景
反映墓主人生前现实世界的图像在甬道、东耳室、前室和后室均有,题材主要是夫妻对饮图、车马出行图等。尤其是夫妻对饮场景共出现两次,分别位于甬道南门柱和后室南壁门额,两次对饮的男女座次存在差异,这种对饮图一般与宴乐图构成组合,但圣村M1的宴乐图在西耳室的门楣上,没有和夫妻对饮图相呼应,这是比较奇怪的。夫妻对饮图所表现的是墓主人生前场景的延续,同时也是家庭礼乐的直接体现。宴饮图不仅仅是生活享受延续,同时也是乡饮酒礼的仪礼规范[11]。甬道南门柱夫妻对应图旁边还有一位背着囊袋的侍者,是一种缴赋税的形象,这是东汉时土地赋税的直接体现。在前室门楣还有一幅六博对饮图,六博棋游戏是两汉时期比较流行的行酒游戏,如《史记·滑稽列传》有云:“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12]。六博棋游戏主要流行于汉代中上层阶级内,是一种社会交往的手段,在汉画、铜镜和陶俑中具有体现,如大英博物馆还藏了一件东汉时期的六博俑[13]。六博棋画像反映了浓重的现实的题材,体现出很强的世俗性,是希望将日常娱乐生活带入地下陪伴墓主人,具有“事死如生”的观念[14]。
甬道南壁门楣画像上还有一幅扶桑树、吊桶饮马图,画面内容有御者、扶桑树、马、鸡等,构成了东汉时期庄园生活的场景。东汉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地方豪族拥有大量土地,兴建地方庄园经济,通过农、林、牧、渔等发展经济,于是出现了猪马牛羊等形象的场景。从诸多考古资料也可以反映出东汉时期庄园经济的实况,如猪圈、望楼等模型明器的大量出现,还有相关农业、手工业画像石也在多地考古中出现,如四川的画像石[15]。由于庄园经济的发达,出现了很多富有的阶层,如“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16]这种东汉时期比较常见庄园经济的题材在徐州佛山画像石墓中也出土类似的饮马图[17]。
东耳室门楣和门柱上的画像大部分是表现现实生活场景,门楣的车马出行拜谒图,车骑前有两位属吏跪拜,通过简单的场景,营造出墓主人生前出行仪仗的社会氛围。也有学者认为车马出行是祭祀的一种含义,体现的都是墓主人的灵魂从地下世界赴墓地祠堂去接受子孙祭祀的车马出行场面[18]。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目前最早的车马出行图可以追溯到战国中晚期的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的车马出行图,使用车马的制度,也同礼乐、服饰、玺印、佩饰等等一样,也是有其严格的等级制度,以别贵贱、序尊卑[19]。并且东汉时期车马出行图比较普遍,场面壮观程度体现了等级制度,如山东临沂县白庄画象石出土的车马出行图[20]。所以类似车马出行图的性质需要针对具体墓葬画像整体构图来甄别判断。门柱南边正面是文官属吏,北边正面是持钩镶的武士图,一文一武守卫墓主人的阴间生活场景,其中钩镶在汉墓中也经常有出土,是一类符合型武器,这样的兵器不单纯是只起防御性盾的作用,这种又钩又镶的新兵器,是和革、木之类的普通盾同时使用的两种防御兵器[21]。
2.2 藏形安魂之所
墓葬是埋葬死人的处所,在于藏形于内,《礼记·檀弓上》所谓“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22]汉代以后墓葬和宗庙、祠堂一样成为安魂之所,墓葬既可藏形,亦可安魂[23]。墓葬画像石是墓室构造空间的延续,也是墓室装饰的氛围营造,东汉张衡在《冢赋》写道:“有觉其材,以构玄室。奕奕将将,崇栋广宇。在冬不凉,在夏不暑。祭祀是居,神明是处。”[24]圣村M1的后室出土有人骨,是放置棺椁的地方,同时也是死人灵魂的居所,在汉魏时期墓葬中西耳室是灵魂安放治所。在西耳室的门楣和门柱上刻画的内容是一种安魂祭祀的图像,门楣上的乐舞图是墓葬祭祀的重要环节,其中建鼓在画像石中出现一般存有特殊含义,有作为百戏表演的符号和礼仪用具的符号表征,将建鼓融入祀、戎、舞、乐、礼的场阈之中[25]。北侧门柱上的飞凤、仪鱼、骆驼和大象这是灵魂引导西方的重要媒介,其中大象上还坐着一位胡人,尤其是大象和骆驼是受西方艺术影响的形象。大象的形象在山东、苏鲁豫皖交界、河南等地的画像石中较为常见[26],这与该地区东汉时期是西方外来文化聚集区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徐州地区出现了早期的西方罗马柱的实物、佛教形象等。大象和骆驼画像出现的场景来看,它们绝大多数都不是出现在表现祥瑞的图像中,而往往与昆仑、西王母信仰有关[27]。
前室南壁的门楣东西两端各有东王公和西王母的形象,这是东汉时期阴阳信仰世界中的固定组合,两位均坐在昆仑山的天柱之上。《神异经·中荒经》载:“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圆如削……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28]7此处东王公和西王母的形象与甬道南壁门楣上东西两端的太阳和月亮画像石对应的,太阳内有金乌,代表阳界,月亮内有玉兔和金蟾代表阴界,均附属于东王公和西王母体系之内。这种组合在山东孝堂山石祠中也有出现,在西王母周边陪伴她的有正在捣碎长生不老药的兔子、九尾狐、三足乌、月神、蟾蜍以及其他人类或神灵侍从[29]。东王公信仰一开始是出现在东部沿海地区,是因为求长生思想而逐渐创作出来的形象,后来与西王母结合并形成固定组合,反映阴阳相合,转换重生的模式,并且这种西王母与东王公联袂的艺术形象很快在东部地区得到认同,接着从这里流传到中原地区这种艺术形象普遍地存在于绘画艺术作品中,出现于建筑物、家具、铜镜以及坟墓里[30]。并且两门柱的伏羲女娲形象也是配合东王公和西王母组合而存在的,伏羲女娲分列两侧,不是以交尾形象组合体出现的,但这并不影响作为一个固定组合存在。伏羲女娲组合的演变过程也是由单一形象逐渐发展为固定组合模式的,成为阴阳代表。
圣村M1画像中还有一类鸮形象,又称“鸱鸮”,属于猫头鹰类,在甬道、前室和后室的画像中均有出现。东汉时期鸮的形象也有陶鸮俑出土[31],刘敦愿先生对中国古代鸮类的题材和时代演变做了系统研究[32],赵超先生认为圣村M1出土的鸮是一种祭祀行为[33]。笔者认为此处的鸮是守卫墓主人灵魂的守护者,猫头鹰是夜间猛禽,也代表在阴间能够“饕餮贪污,臭腐是食”,保障了阴间世界的洁净。《后汉书·朱穆传》李贤注引《文士传》朱穆与刘伯宗绝交诗云“北山有鸱,不絜其翼。飞不正向,寝不定息。饥则木揽,饱则泥伏。饕餮贪污,臭腐是食。填肠满嗉,嗜欲无极。”[34]同时鸮也是长寿的象征,《神异经·西荒经》载:“西海之外有鹄国焉,男女皆长七寸。为人自然有礼,好经纶拜跪。其人皆寿三百岁。其行如飞,日行千里。”[28]4同时鸮也具有胜利的含义,《后汉书·张衡传》描述张衡同人辩论时说:“咸以得人为枭,失士为尤。”注云:“枭犹胜也,犹六博得枭则胜。”[35]后室北门正中的立柱,四面中三面有鸮的形象,与常青树、连理树、猴、飞燕等组成吉祥长生的元素,鸮守卫着墓主人陈放尸体的后室,能够在阴间保障墓主人的安宁,是阴间守卫的重要代表。
3 墓室画像造型艺术分析
萧县圣村M1画像石艺术手法表现是在具象形和几何形相互转换,思维逻辑表现上具有极强的联想、创作和想象。视觉审美体验上将功能与形式完美融合,营造出灵动、通透的空间感。在材料质感单一的物质载体上,运用纯粹的以具象图形为基准特征,结合几何形的点线面、方圆角等简洁元素并遵循正负形的语法结构构成的视觉语言秩序重组。不注重直观视觉形体的艺术性,而是重视形体与形体之间或者单个形体的叙事性的表意。这是萧县圣村M1画像石艺术的主要特点。
夫妻对饮图的构图采用横平竖直与室内空间结构相呼应。物象组合具有稳定的整体秩序和内在韵律。例如,屋顶所占的画面平面空间与人物及瑞兽活动空间的比例为1/3关系,夫妻出现的视线位置正好是画面的黄金分割点附近,使得画面一开始跳入眼帘的就是夫妻对坐于画面中心,形成对称式分布排列的平行空间。
在物象造形方面,夫妻二人和侍从采用自然基本形,男性身形饱满,女性形体转折部位浑圆内收,形态结构的曲直、方圆还具有自然物本身的体现。然而,其他神兽物象造形有创造、联想、观念三个方面依据理性拼接而成。画面中的一处自由空间体现在羊与人的大小差异,这是创作者有意在二维空间中表现三维空间的视错觉。所以,可以体现出雕刻师具有丰富的具象思维解构与重构能力。画面结构空间的运用上受既定空间的限制,又智慧的突破既定空间的束缚,艺术布局把握得当,明显感觉惬意、祥和愉快地意味。
东王公和西王母两形象完全采用艺术形的物象表现,采用类似坐姿,基本形由自然形和联想形拼合而成,但二者有所差异,正负形中的形体特征处理略显不同,人物艺术性格略显不同。两者均运用简练概括的跪坐动态,运用线条的方向变化表现出人物身体不同部位的空间轮廓。虽然众多人物处于同一场景之中,构图结构是横向串联方式依次排开,不排除有相似造型因素存在,但为了区分人物等级,画面采用概括性的几何图形状出现,即一段现实历史场景结束后转向叙事图像形态的呈现。在平远的横向空间采取分段式故事讲述,在人物造形艺术化处理表现上有明显的人神区分,人物高低位置处理具有一定画面韵律性。画面形式中的东王公、西王母具有平衡、呼应画面作用。
甬道西北立柱画像在原有的有机形因素基础上融合了一定的审美情趣,注重边缘形和内轮廓的准确性,不同部位的装饰肌理具有很强的具象写实思维理念,有意强调立体图形,将三维空间语言逻辑融入造形中的极致表现。每一个物象呈现出质朴的呆萌感,而猫头鹰的头部形象采用以点为中心用放射性的圆线来突出眼部特点,夸大猫头鹰自然形态特点,用圆三角序列重复装饰手法刻画羽毛质感,使画面在夸张的视角下又极具写实视觉感受。
总之,圣村M1的画像艺术充分运用了具象形、几何形和艺术形的物象表现完美地呈现了东汉中晚期画像的成就,同时在构图上兼具写实与想象的手法使画像极具观赏性和创新性。
4 结 语
圣村M1是萧县画像石的典型代表,也是东汉时期画像石技术和艺术的重要体现,其画像分布在整个墓室之内,丰富了墓葬空间,延续了墓主人的阴间世界。本文复原了M1墓葬空间中画像内容具体布局,画像内容可以分为反映墓主人生前的现实场景、藏形安魂之所两部分。圣村M1的画像内容也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史实,如大象、骆驼和胡人形象的出现,还有东王公和西王母形象也是受到西方世界和沿海海洋文化的影响。在淮北和宿州汉代画像石中也有胡人骑射的形象存在,可以证明淮北、宿州还有萧县地区在画像石题材中含有中西文化交流的因素。综合考察圣村M1的墓葬规格与宿州褚兰胡元任画像石墓类似[36],同时也与徐州清泉山白集东汉画像石墓比较一致,白集汉墓是六百石等级葬制[37],可以判断圣村M1等级也在六百石左右。圣村M1画像石的复原探讨更是对该地区画像石研究的有益补充,也为墓葬画像石完整性研究提供参考。